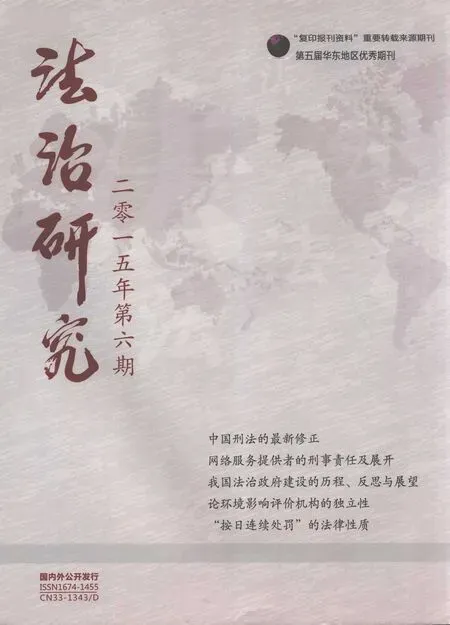诉讼欺诈按诈骗罪论处是非探讨*——兼论《刑法修正案(九)》之诉讼欺诈罪
杨兴培 田 然
一段时间来诉讼欺诈行为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滥用诉权,通过虚构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意图骗取法院的有利判决,从而侵占他人财物或者免除自身债务。据报道:广州市人民检察院2013年至2015年6月共受理虚假诉讼申诉案件97件,涉案金额2.63亿元。①凤凰网广州:《制造虚假诉讼被罚80万》,http://gz.ifeng.com/zaobanche/detail_2015_06/29/4050652_0.shtml。据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披露:2012年至2014年9月,温州市检察机关共查处虚假诉讼201件,审查后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122件,公安机关刑事立案77件103人,法院刑事判决25人。②浙江新闻网:《温州市3年查处虚假诉讼201件 多为逃避执行转移财产》,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4/10/15/020304433.shtml,2015年6月30日访问。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着诉讼欺诈现象的日益严重。诉讼欺诈对司法秩序、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它使人民法院的庭室殿堂成了竖子之辈弄虚作假的暗室舞台,司法权威成了宵小之徒敛财避债的保护伞,裁判文书成了社会恶棍肆意侵犯他人财产的工具。同时,这种行为也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一种恶意侵占和肆意挥霍,司法机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换来的却是惹人非议的错案一桩,使得本就饱受争议的司法公信力雪上加霜,也使得被害人或是怀疑人民法院与犯罪行为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移恨整个社会,或是采取极端手段抗拒裁判不公的执行而又锒铛入狱,或是走上旷日持久的上诉申诉之路而惶惶不可终日,这都将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对他人合法权利造成严重侵害。因此,《刑法修正案(九)》的补充规定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但毋庸讳言,由于这一法律规定尚有诸多待解的难题和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集思广益,以图破解之,故作努力一试。
一、诉讼欺诈的界定
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诉讼欺诈行为的犯罪主体、主观目的、行为类型以及行为的定性等问题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刑法修正案(九)》第35条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是诉讼欺诈行为,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分歧,明确规定诉讼欺诈行为是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中,诉讼主体通过虚构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等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就是诉讼欺诈犯罪。然而,诉讼欺诈行为是否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诉讼欺诈行为是否仅限于诉讼当事人间的“恶意串通”?诉讼欺诈行为是否仅仅限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发生在民事调解程序、执行程序以及行政诉讼、仲裁程序中的欺诈行为是否也应当纳入犯罪?这些疑问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一)诉讼欺诈概念之聚讼
何谓诉讼欺诈行为,学界早已给出不少见解,有学者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是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恶意串通提起的虚假诉讼行为:“诉讼欺诈指诉讼参加人恶意串通,通过符合程序的诉讼形式,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从而达到损害他人利益、谋取非法利益目的的违法行为。”③陈桂明、李仕春:《诉讼欺诈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诉讼欺诈并不仅限于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还应当包括原告单方提起的恶意诉讼,如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研究视野中的‘诉讼欺诈’的内涵不仅包括‘串通欺骗法院’的行为,也应包括‘单方欺骗法院’的行为。”④高铭暄、陈冉:《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与“诉讼欺诈”定性诈骗罪者商榷》,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4期。可见,学者们对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属于诉讼欺诈没有争议,而对单方欺诈行为是否属于诉讼欺诈还存在不同的见解。
就诉讼欺诈行为主观上是否应当具有特定目的而言,不少学者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诉讼欺诈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目的,这与诉讼中的陈述不实、过失提出虚假证据有着本质的区别。”⑤郑薇:《论诉讼欺诈及其刑法调整》,华东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诉讼欺诈罪不应该对目的作出限定,原因在于诉讼欺诈罪侵害了司法秩序,而不论行为人基于何种目的,无论是为牟取正当利益还是非正当利益,只要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都是严重妨害司法诉讼秩序的行为。⑥梁根林:《虚假诉讼行为入罪要斟酌三个问题》,载《检察日报》2015年1月29日。
就诉讼欺诈行为的发生领域而言,有观点认为诉讼欺诈罪不仅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行政诉讼以及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欺诈行为也应构成该罪:“为了骗取法院的裁判文书或执行,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申请强制执行,在诉前或诉中虚假陈述、妨害作证、毁灭伪造证据等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法院,从而达到损害他人利益,或谋取财物或非物质利益目的的行为。”⑦吴仁碧:《诉讼欺诈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4页。
就诉讼欺诈犯罪的既遂状态而言,有不少观点认为应以法院是否作出“错误判决”或者是“有利判决”为标准:“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民事诉讼为手段,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虚假证据欺骗法院,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从而骗取了公私产物的行为。”⑧董玉庭:《论诉讼诈骗及其刑法评价》,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二)诉讼欺诈罪主要观点之述评及应然概念之探寻
1.诉讼欺诈罪应当仅限于民事诉讼领域。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都属于“诉讼”,都有可能发生诉讼参与人的欺诈行为,诉讼秩序也同样能够被诉讼参与人的欺诈行为所干扰破坏。然而,这几类诉讼程序的启动与展开有着极大的不同。与其他诉讼程序相比,民事诉讼活动有着鲜明的当事人主义色彩,民事法律关系的建立、民事纠纷的解决、民事诉讼的提起、民事证据的收集都依据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展开,法院介入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关系是非常被动的,即便是已经介入,法院仍然还是热衷于鼓励当事人通过和解、调解等非诉方式化干戈为玉帛。民事诉讼的这些特征易于滋生诉讼欺诈。刑事诉讼则是一种国家行动,诉讼程序的启动与展开有着鲜明的公权力运作色彩,我国刑法对刑事诉讼活动的保护已十分全面,公诉机关如果捏造事实提起刑事诉讼将面临着徇私枉法罪、妨害作证罪等罪责,自诉人捏造事实提起刑事自诉案件的将被追究诬告陷害罪。因而在刑事诉讼领域,控诉方和自诉人的捏造事实行为现有罪名都已经涵盖,而无需另设新罪。我国的行政诉讼中的证据材料往往保存在行政机关一方,行政诉讼采取证明责任倒置的证明规制,行政机关要对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否则便要承担败诉结果。面对占有充分证据材料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捏造事实、虚构证明材料的空间极其狭小,虚假行政诉讼严重损害司法秩序的情形更为少见,将其入罪也有违刑法的必要性和节俭性,因此将诉讼欺诈的范围限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既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
2.诉讼欺诈罪不应以“恶意串通”为限。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内的欺诈行为本是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2、113条也将虚假诉讼行为限定为“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笔者认为,原告单方恶意诉讼类型的单数主体的诉讼欺诈行为与原被告串通型的复数主体的诉讼欺诈行为的确存在不同之处,在单数主体的情形下,原告与被告之间就法律事实、系争标的、证据材料有一个质证和辩论的过程,被害人能够及时意识到权利受到侵害也能及时救济自身的合法权利。而恶意串通型的诉讼欺诈,被害人系案外第三人,对诉讼欺诈行为往往不知情,因而恶意串通型的诉讼欺诈更容易得逞。诉讼欺诈罪旨在保护民事诉讼司法秩序不被虚假诉讼所利用和破坏,而无论是原告单方的虚假诉讼行为,还是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实施的诉讼欺诈行为,对司法秩序的破坏效果并无二致,因而诉讼欺诈应当包括原、被告双方串通实施的意在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欺诈行为,也应当包括原告针对被告所实施的单方欺诈行为。
3.“非法占有目的”不应是本罪成立的要件。
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的目的既可能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也可能是为了逃避债务,或者是为了获得其他利益,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诉讼欺诈行为都是以骗取法院的民事裁判,进而获取他人财物或者是减免自身债务,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诉讼欺诈罪就是一种财产性犯罪?财产类犯罪最为鲜明的特征便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直接作用于财物,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中规定的十三类财产性犯罪都是以他人的财物为直接对象的行为。而诉讼欺诈行为则并非是直接针对被害人财物的犯罪行为,它采取了率先骗取法院判决,依靠法院判决之效力间接获取被害人之财物,其行为的直接对象不是取得被害人财物,而是骗取法院的有利判决,因而有学者指出:“‘诉讼欺诈’妨碍干扰诉讼是直接和必然的,而导致公私财产受损则是间接的、附带的和偶然的。”⑨同注④。这一观点不无道理,行为人提起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直接目的是骗取法院的有利判决,该行为本质上是对司法诉讼秩序的侵害,因而“非法占有目的”不应是本罪成立的要件。
4.“骗取法院的错误判决”不应是本罪既遂的标准。循着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两条径路,刑法也面临着应以行为还是以结果为处罚基础的艰难抉择。就行为犯而言,刑法预先设定了只要行为符合了法条中所凝固的构成要件,就推定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需要等待危害结果的发生便能将其入罪。而结果犯则强调,一定危害结果的出现才能认定犯罪之成立或者犯罪之既遂。诉讼欺诈罪属于结果犯还是属于行为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夸大自身的损失,放大对方的过错是民事诉讼中极为常见之现象,对此民事诉讼法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在前置法已有规定的情形下,为区分诉讼欺诈一般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将一定的危害后果的出现作为刑法介入的条件十分必要,因此诉讼欺诈在广义上可以视为“结果犯”,以出现严重的危害后果为该罪成立之必要条件。但这种危害结果不应仅限于获得了法院的“错误判决”为限,结合诉讼欺诈行为的一般模式,这一严重的危害结果应当是指:诉讼欺诈行为严重妨害了司法秩序以及诉讼欺诈行为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诉讼欺诈是对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内,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方式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行为的影射。诉讼欺诈行为的发生领域为民事诉讼领域,包括民事一审、二审、再审以及反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多个程序内涵。
二、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纷争与解析
面对诉讼欺诈行为的频发,无论是立法部门、司法实践部门还是学理界都在激烈探讨如何规制诉讼欺诈行为,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依照诈骗罪、妨害作证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行为人的诉讼欺诈行为。
(一)司法实践中的定性纷争
早在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发布《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该《答复》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 http://www.spp.gov.cn/site2006/2006-02-22/00024-230.html,2015年6月2日访问。2002年的《答复》旨在澄清诉讼欺诈不同于诈骗罪,在一段时间内对司法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然而对此质疑声也随之而起,各地司法实践仍不断探索如何规制诉讼欺诈行为。2010年7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明确界定虚假诉讼犯罪是指为了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恶意串通,虚构事实,伪造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构成犯罪的行为,并从犯罪行为人的作案目的、作案手段入手,分别予以定罪处罚,共涉及妨害作证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贪污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10项罪名。类似的规定还有2010年9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处理虚假诉讼行为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1年3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防范和治理民事虚假诉讼行为的若干意见》。近年来各地区相继颁布的司法适用指南则更倾向于将诉讼欺诈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认定为是诈骗罪、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类犯罪。
笔者以“诉讼欺诈”为关键字,以“精确”为匹配方式,以“全文”为范围检索“北大法律信息网”,得到如下数据,截止到2015年6月15日,北大法律信息网共收集到有关“诉讼欺诈”案例与裁判文书共计181份。其中,以刑事案件立案的共计14份(其中有两份为“案例”与“裁判文书”的重复,有效份数实为12份),以民事立案的共计164份。⑪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www.pkulaw.cn/case/,2015年6月15日访问。笔者以“虚假诉讼”为关键词,日期设置为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共获得了4201条案件记录,其中刑事裁判文书约80份,其余皆以民、商事案件结案。也即是说,目前当事人虚假诉讼主要还是按照妨害民事诉讼司法秩序的一般违法行为处置,而依靠刑法调整的这80份文书中,以妨害作证罪论处的为45份,以诈骗罪定性的为21份(其中有两份以合同诈骗罪定性),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的为4起,以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论处的为4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的为3份。
通过对大量诉讼欺诈案例的考察可以总结出司法实践中规制诉讼欺诈行为的一些基本特征:自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的《答复》颁布以来,司法实践中的诉讼欺诈行为多按照手段行为或者是结果行为定性。而自2010年至2014年之间司法实践中多将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为诈骗罪,自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颁布以来,司法实践中多将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为“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以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危害司法秩序类犯罪。
(二)理论界的定性之争
面对诉讼欺诈案件,理论界也长期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难题所困。我国理论界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有较大争议,目前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也是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⑫参见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页;诸葛肠、文明:《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分析》,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2期;郑薇、吴巍:《诉讼诈骗的刑法分析——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答复〉》,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视三角诈骗是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因而诉讼诈骗也属于诈骗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侵财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当事人并没有因被骗而陷入认识错误(通常情况下被害人对诉讼骗局十分清楚,但因举证不能而败诉,或者在原被告串通型诉讼欺诈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本就不知情),被害人也没有在意思瑕疵下的处分行为,法院的判决以及强制执行对被害人形成一种强制,因而应当成立敲诈勒索罪。⑬参见王作富:《恶意诉讼侵财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载《检察日报》2003年2月12日;王飞跃:《论诉讼欺诈取财行为的刑法规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构成抢劫罪,“在诉讼诈骗行为中,法院基于形式真实主义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判决,进而将之执行,受害人便面临暴力的威胁,诉讼欺诈的行为人是将法院的强制执行当成工具加以利用进行抢劫的间接正犯”。⑭李翔、黄京平:《论诉讼欺诈的可罚性及其立法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四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行为可以通过改造伪证罪后,按照伪造罪处罚,诉讼欺诈行为主要是通过伪造证据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然而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只能是发生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才得以构成,因而应当修改刑法第305条伪证罪的构成要件,将民事诉讼中的该类行为归于伪证罪较为适宜。⑮参见侯国云、徐梦:《对伪证罪的修订与整合——兼论亟待增加的两个罪名》,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1期。
(三)以敲诈勒索罪、抢劫罪、伪证罪评价诉讼欺诈行为之不足
以敲诈勒索罪、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观点认识到了诉讼欺诈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的区别,但这些观点本身并不妥当。敲诈勒索罪是指行为人采取威胁、要挟或者恫吓的方式使他人陷入恐惧而被迫交出财物,威胁、要挟和恫吓主要是指行为人以恶害、揭露隐私等要求被害人交付财物,威胁和要挟的事项较为广泛,既可以是被害人本人以及亲属的生命、健康、利益等的侵害行为,也包括以揭露隐私、揭发违法犯罪等事实为内容而要挟或威胁。法院的不利判决以及强制执行,虽也具有强制性,但并不等同于以恶害相要挟。因而将诉讼欺诈行为按敲诈勒索罪处理其理由并不充分。抢劫罪的暴力胁迫和取财行为都具有时空性特点,要求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者是以暴力相威胁,抢走他人财物的行为,抢劫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针对被害人的暴力、胁迫行为,而且暴力、胁迫程度要到达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而诉讼欺诈行为人并未针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者胁迫,法院的不利判决以及强制执行也并没有达到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的程度。因此按抢劫罪处理诉讼欺诈并不符合抢劫罪之构成。
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改造伪证罪之构成,将民事诉讼纳入到伪证罪。该观点同样不妥。伪证罪仅处罚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诉讼参与人的伪证行为,其原因在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程度只要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即便是当事人指使他人故意做虚假证明、鉴定、记录和翻译的,被诉方如果不能提出相应证据反驳,被害人也仅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伪证行为将会使被害人无故承担刑事责任,亦或者是帮助行为人逃避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严重危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以及正常的司法秩序,滋生冤假错案,其造成的危害程度是民事诉讼中的欺诈行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将伪证罪仅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内有其合理之处,不能随意突破。也有观点认为应当扩大伪证罪的主体范围,将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自诉案件中的原告纳入其中。⑯同注⑮。然而这一观点同样有不妥之处。《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文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相对于控诉方,被告人处于防御、辩护地位,被告人如有隐瞒自己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证据的行为,因其享有不自证其罪的特权,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倘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直接构成妨害作证罪,也不需要以伪证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倘若被告人并未指使他人作伪证,而是自己捏造事实,破坏或者是伪造证据,意在逃避、减轻或者降低处罚的,实践中可以将此类行为认定为妨害作证罪,通常也不需要按伪证罪定罪论处。因此通过改造伪证罪的构成要件,将诉讼欺诈行为放置在伪证罪的名下也是不合理的。
三、诉讼欺诈不构成诈骗罪
随着将诉讼欺诈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抢劫罪以及改造伪证罪的方案相继失败后,将诉讼欺诈按照诈骗罪处理的“诈骗论”便就“顺理成章”,成了备受刑法学界青睐的主流观点。然而笔者认为将诉讼欺诈按照诈骗罪这一削足适履的做法也同样从本质上违背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目前,刑法学界将诉讼欺诈按诈骗罪论处的观点主要是从两条路径进行努力的,一是将三角诈骗理论引入,对诈骗罪的行为结构进行重新解释,认为诉讼欺诈是一种典型的“三角欺诈”,视三角诈骗是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因而诉讼诈骗也应当以诈骗罪论处。⑰参见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二是直接将诉讼欺诈认定为诈骗罪。这种观点认为被害人对财物的转移是否自愿与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并无关系,法院是被骗人,也是财产处分人,诉讼诈骗是法院与行为人之间的诈骗关系,与实际被害人无关,诉讼诈骗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论证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并不需以三角诈骗为桥梁”⑱赵冠男:《“诉讼诈骗”的行为性质》,载《法学》2015年第2期。。然而,笔者认为将诉讼欺诈认定为是诈骗罪,无论是以三角诈骗论还是直接认定构成诈骗罪为解释路径和方法选择都有着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之处。
(一)三角诈骗论是一个伪命题
将诉讼欺诈按诈骗罪论处的观点试图改造我国诈骗罪的传统理论,希冀通过借鉴德日刑法理论,力求在理论基础与观念上与德日诉讼诈骗理论构造趋于一致。然而诉讼欺诈发生在行为人、法院以及被害人三个主体之间,与传统的被害人因受骗而处分财物的诈骗罪的构成模式之间有着本质之别,为了勾连传统的仅仅发生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诈骗罪与行为人、法院、被害人三者之间发生的诉讼欺诈之间的沟渠,不少学者架起了三角诈骗理论这一桥梁。但是发端于德日刑法理论的三角诈骗论,将诈骗罪中的被害人与受骗人分离,认为受骗者和被害人不必一致,“诈骗罪中,受骗者和被害人不一致,但受骗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能或地位时,是三角诈骗”⑲Vgl. WesselsHillenkamp, StrafrechtBesonderer Teil/2,23. Auf.C.F. Müller 2000,S.251.。三角诈骗论者将诉讼欺诈罪中的受骗人之地位限定为既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不是财产的占有者,但又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享有财产处分权或者是居有财产处分之地位,这样事实上是将实际损害后果承担者等同于诈骗罪中的被害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很难成立。
1.间接受害人并非是诈骗罪中的受害人。按照三角诈骗理论,“在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处分的既可能是自己占有的财产,也可能是自己没有占有的财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骗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他人财产的地位。”⑳同注⑫。因此,成立三角诈骗的被骗人还必须具有等同于被害人地位的处分权限(唯有如此才能将被骗人的处分行为视为是被害人自己的处分行为,并且被骗人对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三角诈骗中的被骗人对被骗之财物具有处分权限,并且三角诈骗中的被骗人也不能是被骗之财物的所有权人或者是占有人。因为被骗人一旦具有占有权或者所有权,此时的诈骗便是行为人直接从财物的占有人或者所有人那里骗取财物,这是典型的二者之间的诈骗罪,行为人直接从所有权人或者占有权人处骗取财物的,是普通的二者之间的诈骗,而非所谓的三角诈骗。然而,脱离于所有权人与占有人之外的处分权能是否存在呢?事实上,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确实存在这类既不是占有人或所有权人而又享有处分权的权利人。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除财物所有人外,可以代替所有权人行使处分权能的人主要有代理人、被委托人、监护人、遗产管理人等保管人员。依据民事法律关系,民法上的代理人、受托人、遗产保管人、财产保管人等管理人具有财产保管和处分之权能,其在从事管理事项、委托事项时因不可归责于己之责任而产生的损害后果,由被代理人、委托人承担,也可以向被代理人、委托人追偿。民事法律中的代理责任制度、委托责任制度是对损害后果如何分配的规定。然而,从刑事法律关系上看,刑事被害人应当是指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受托人、代理人、管理人等受欺诈而产生的损害后果由委托人、被代理人承担是对损害后果的分配,这一责任分配并非是将发生在行为人与代理人、委托人之间的欺诈行为直接视同为是欺诈了本权利人,而是在行为人、被骗人和本权利人之间分别有着两层法律关系。一是行为人与被骗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就这一关系而言,由于管理人具有处分权能,行为人基于欺骗手段而从管理人处骗取财物的自然成立被骗人与行为人两者之间的刑事诈骗关系,受到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管理人。由此,管理人应当是受害人。二是被骗人与实际的财产损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相应的民事制度,代理人、监护人如按照约定或相关规定已恪尽职守而仍然被骗的,他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并且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其受到的损失还可以向委托人、代理人追偿。然而,代理人、委托人基于相应的代理制度、监护制度或者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承担赔偿责任,其自身受到的损害还可以向委托人、被代理人追偿,不等于诈骗关系中的被害人身份也直接发生了转移,保管人、监护人等管理人仍是诈骗刑事法律关系中的受害人。而委托人、被代理人等被管理人不是诈骗行为的直接受害人,而是基于代理制度、委托制度、管理制度承担损害后果而事后塑造的受害者之身份。
2.三角诈骗论是对现存刑事诈骗关系的曲解。三角诈骗论者以“保姆案”㉑“保姆案”:行为人谎称是洗衣店员工欺骗保姆将雇主的衣物拿去干洗,保姆因被骗而将雇主的西服拿给行为人。“、代理案”为例㉒“代理案”:代理人在从事代理事项时被骗,代理人处分了被代理人的财物。,认为我国刑法金融诈骗罪之立法是三角诈骗理论成立之明证。然而,笔者认为将类似于“保姆案”、“代理案”的情形认定为是三角诈骗,这种做法要么是对两者之间的诈骗关系的曲解,要么是将盗窃行为按照诈骗行为处置的错误攀缠。就“保姆案”而言,保姆与雇主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保姆对雇主之财物一般都负有保管义务,一般情形下,没有雇主之授权保姆不具有处分雇主财物之权能。行为人从保姆处骗取雇主之财物,如果保姆获得了雇主的授权或委托具有处分之权限,诈骗关系得以生成,但并非三角诈骗论者声称的行为人与保姆以及雇主之间的三角诈骗关系,而是成立了保姆与行为人之间的诈骗关系,诈骗行为针对的被害人是保姆本人。保姆与雇主之间因民事代理或者委托制度,保姆因不可归责于己之责任可以不承担赔偿损失。而倘若保姆没有获得授权或委托,即受骗之保姆并不具有处分权,此时诈骗罪便难以成立,行为人的行为是盗窃。就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而言,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意志而取得财物的,诈骗罪是利用被害人的瑕疵意思而取得财物,行为人从无处分权能人处骗得财物的行为是盗窃,而不成立三角诈骗。
三角诈骗论者认为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罪,是三角诈骗理论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刑法分则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事实上包含了三角诈骗的情形。”㉓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应包含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而票据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汇票、本票、支票’的行为以及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均为三角欺诈的典型情形。”㉔吴玉萍:《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4期。事实上这一论断曲解了诈骗人与信用卡诈骗或票据诈骗罪中的商业银行或者特约商户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目前,信用卡的付款确认方式种类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只需要签名确认即可,特约商户和银行职员比对签名的审查义务。而一旦信用卡被他人冒用,持卡人能够证实签名错误、或者非持卡人本人消费的,持卡人不具有还款义务,特约商户或者是发卡银行需要自行承担损失,银行以及特约商户是金融诈骗罪的直接被害人,这种冒用事实上是普通的二者之间的诈骗关系。另一类是密码和签名双重确认的方式,这一确定方式要求持卡人妥善保管密码,因票据的无因性,特约商户以及银行职员只要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以及通过了银行的自助取款设备的密码识别或者是票据的背书审查,其根据先前的发卡协议、开户协议、存款贷款协议就应当根据持卡人或者票据持有人的指令无条件支付款项,在这一情形下,银行或者是特约商户的行为是一种履约或者是履职行为,而非是因被骗而处分财物,所谓的处分权是民法上的行为人基于自由意志对财物作出交易、转让、抛弃等处分行为,包括所有权的处分,也包括对占有权的处分。诈骗罪中的被骗人虽因被害人的受骗而陷入了认识错误,但其作出的处分行为仍是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表意行为,而机械的执行命令或者是履行义务的行为不应该视为是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冒用、冒领密码卡或者背书、支票等金融凭证的,承受诈骗之侵害被害人是持卡人、付款人本人,银行承担的是履约行为,此时的金融诈骗行为仍是两者之间的诈骗关系,而非三角之诈骗。有学者指出:“从法理上看,三角诈骗等主体结构复杂的多角诈骗最终都可以并应划分为诈骗与被诈骗两方或两角”㉕黄龙:《“诉讼诈骗”批判》,载《刑法论丛》2010年第1卷。,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二)将诉讼欺诈直接认定为诈骗罪违背诈骗罪的构成原理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日新月异,人们对财物的占有和控制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以财物为对象原体的财产犯罪形态也是新样态迭出。诈骗罪作为古老而又传统的财产犯罪形式之一,其犯罪样态也在不断地去陈出新。然而,无论行为变体如何地五花八门,但诈骗罪核心形态仍然是因行为人的欺骗、隐瞒行为本质致使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而处分自己占有的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是由于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自愿交付财物。在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化凝固样态的规定中,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物始终是颠簸不破的模型原体,诈骗罪中被害人与受骗人是一致的,被害人因为受骗而处分了财物,行为人因被害人的处分行为而取得财物。与其他财产性犯罪相比,诈骗罪还有着浓厚的被害人参与性的色彩,被害人对诈骗行为的处分财物之回应行为成为了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诈骗罪是最典型的犯罪人——被害人互动型的犯罪之一,它既不同于直接对被害人身体或精神实施强制的犯罪(如抢劫),也不同于正面回避和躲闪被害人的财产犯罪(如盗窃)。诈骗的成功,是行为人与被害人‘面对面’甚至是‘光明正大’地进行沟通和‘交易’,在被害人的‘积极配合’下,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和平完成的。”㉖车浩:《从华南虎照案看诈骗罪中的受害者责任》,载《法学》2008年第9期。被害人因被骗而为的处分行为仍是诈骗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尽管诉讼欺诈的行为人采取虚假陈述、伪造证据、指使他人作伪证等手段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骗取法院裁判,进而侵占他人财产或者逃避义务,诉讼欺诈罪与诈骗罪都有着“欺诈”的色彩,然而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从犯罪对象这一要素来看,诉讼欺诈罪骗取的是法院有利判决,而诈骗罪骗取的是财物。诉讼欺诈罪与诈骗罪的受骗对象不同,诈骗罪中受骗者为财产的所有者或是财产的占有者,而诉讼欺诈中受骗的是法院。诉讼欺诈中欺骗的直接对象并不是被害人,而是法院。法院既不是财产占有者,也不是财产所有人,行为人欺骗行为的直接目的也不是骗取财物,而是骗取法院的支持,利用法院的判决、裁定、执行等减免自身债务,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利。
其次,从“自愿处分”这一构成要素来看,法院的判决不能认定为是“自愿处分”。“自愿处分”是诈骗罪得以成立的必要要件,倘若诉讼欺诈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法院的判决或者是法院的执行行为应当被视为是对财产的自愿处分。然而,人民法院的判决并不等于是自愿处分行为。诈骗论者认为,法院享有对诉讼当事人的财产进行处分的权利,我国《物权法》第28条也已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然而法院的处分行为并非是“自愿处分”。所谓的自愿处分,是指被害人有是否作出处分与否的选择性,而法院依据证据规制、法律事实作出的民事判决没有选择性,不等同于诈骗罪中被害人的“自愿处分”行为。
再次,从“自愿交付”要件看,诉讼欺诈与诈骗罪也有着本质的不同。“交付(处分)行为是诈骗罪成立不可缺少的要件”㉗刘明祥:《论诈骗罪中的交付财产行为》,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通说认为的诈骗罪的客观构成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致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对方因陷入错误认识而主动处分财产,行为人从而取得财产,即本质特征是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作出错误判断而“自愿”交出财物。诉讼欺诈中,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失并不是因为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是因为法院的判决而其必须承担的败诉结果,实难谓被害人是因受到欺骗而自愿处分财产。事实上诉讼欺诈中,尤其是以被害人为被告的诉讼欺诈中,被害人对行为人的弄虚作假行为是深知肚明的,但在客观上却无力阻止法院的不利裁判。诉讼欺诈中被害人交付财物并非出于自愿,法院虽支持了行为的诉求,但法院并不是交付财物的主体。法院对被害人的财物既没有占有权也没有所有权,交付财物的主体仍然是被害人,但被害人绝非是基于自愿交付财物,被害人因败诉结果而交付财物或者是因法院的强制执行而交出财物,往往是被逼无奈亦或者是因上诉无门、申诉未果的情况下被迫交出财物,实难谓是自愿交付财物。由此可见诉讼欺诈并不符合诈骗罪“自愿交付财物”的本质特征。
(三)《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诉讼欺诈罪具有合理性
诈骗罪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私财产免受诈骗行为的不法侵害,从保护被害人的财产权益角度而言,无疑将诉讼欺诈行为认定为是财产性犯罪更为有利。然而将诉讼欺诈行为按诈骗罪论处的主张与做法并不是根据行为的本质、行为的类型以及行为的危害性而形成的,而仅仅是从保护被害人财产安全的目的出发,刻意扭曲诈骗罪的构成形态。这种做法虽能较好保护公私财产安全,但却以突破犯罪构成对犯罪行为的凝固效果,以破坏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稳定性以及科学性为代价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其对刑法理论的科学性和司法实践的严肃性产生的危害极大,纯粹是刑法实践功利主义的反映。笔者认为,按照三角诈骗理论而将诉讼诈骗定性为诈骗罪不可行,而将诉讼欺诈直接定性为诈骗罪因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悖同样不可行。诉讼诈骗不能按照既有的伪证罪、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予以定罪量刑的时候,其特殊的行为构造将其推向了犯罪独立化的境域。我国《刑法修正案(九)》采用的专设诉讼欺诈罪正是这一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次审议稿中将诉讼欺诈行为按照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同,将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定性为是诉讼欺诈,而将侵占他人财产和逃避合法债务的行为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2015年6月,我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第二次审议稿中规定,在刑法第307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07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㉘中国新闻网:《刑法修正案审议 虚假诉讼或入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6-24/7364013.shtml,2015年7月10日访问。第二次审议稿中将草案中“按照诈骗罪从重处罚”的规定修改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2015年8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最终沿用了这一规定。可见立法机关也在有意地扭转将诉讼欺诈行为有可能被简单地认定为诈骗罪的理论与实践倾向而尽了自己的曲折努力。
四、结语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㉙《韩非子·心度》。法律的修改与制定并非是随心所欲的。诉讼欺诈罪为打击日益猖獗的诉讼欺诈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仅将诉讼欺诈行为禁锢在冰冷的法条里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仍需反思如何减少实践中频发的诉讼欺诈现象,如何防止司法审判沦为犯罪工具。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法院以及法官对截流诉讼欺诈还可以作出更好的努力,“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在法律帝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㉚[美]德沃金:《法律的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一旦神圣的司法审判为虎作伥,便动摇了司法公正的根基,冲击法院裁判的公信力。诉讼欺诈行为虽已经入罪,但预防和瓦解诉讼欺诈犯罪的拉锯之战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