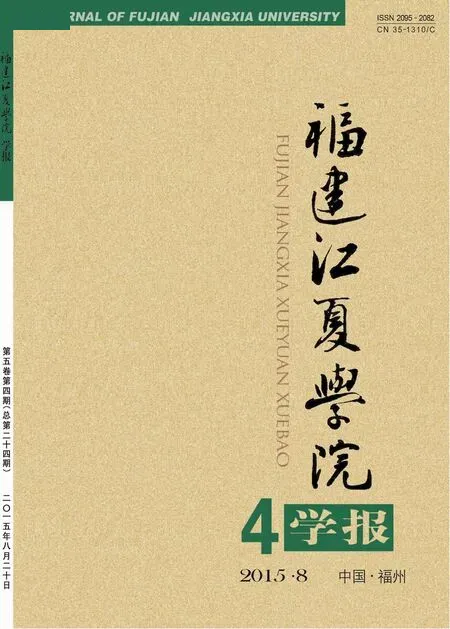《列女传颂》:中国现存最早的题画诗
魏伯河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山东济南,250031)
多年来读刘向(约前77—前6)的《列女传》,常有一种困惑,即讲述完每则故事后,作者已经模拟《史记》“太史公曰”的体例,用“君子曰”①《列女传》各篇此类表述不尽一致,或“君子曰”、或“君子谓”“仲尼谓”,这里的“君子”应指刘向本人;亦有个别没有此类领属语而直接加以评论者,或当属脱文所致。式的评述性语言,对故事的涵义进行了必要的阐发,而且还全都引用了《诗》《书》或《论语》中的名句加以印证,可谓言尽意足,何必还要于每篇之后再用一段“颂”来概述故事呢?以布局谋篇而论,岂不是画蛇添足吗?那时造纸术还不发达、印刷术还未问世,著述条件远不如后世简易便捷,主要通行的书写材料还是竹木简,数量多了,就相当笨重,以至于“(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1]因而我们的古人写作无不力求俭省,惜墨如金,何以此书中如此反常呢?最近通过研读有关史料与研究成果,这一困惑终于得到解决,而且借此有了新的发现。
一、《列女传》本来就是一部与图画相辅而行的书
班固(32—92)《汉书·楚元王附刘向传》载: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2]1958
这一记载,说明:(1)《列女传》的资料来源于《诗》《书》所载,不是无根之谈。(2)《列女传》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让天子——汉成帝刘骜(前51—前7年)引以为“戒”,也就是说,此书是刘向的另类“谏书”,并且对汉成帝也曾产生了触动。至于成为民间流行的读物,用于对妇女、儿童的启蒙教育,则是宋代以后的事。有的论者径直将其视为幼学启蒙读物,②如日本佛教大学教授黑田彰在《列女传图概论》一文中,就径称“《列女传》与《孝子传》同属幼学启蒙读物”。是有失妥当的。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有班固自注云:
《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2]1727
这一注文告诉人们:传世的《列女传》一书又名《列女传颂图》,也就是说,此书本来就与一般纯文字作品不同,是由《列女传》《列女颂》《列女图》3部分组成,三位一体,其中的“颂”并非传文的组成部分。这一点,还可通过《太平御览》所载的《七录别传》佚文得以证明。刘向在这篇奏疏中说:
臣与黄门侍郎歆以《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3]
这一佚文的价值,在于说明了:(1)刘向的儿子刘歆(前50—23年)参与了《列女传》(即《列女传颂图》)的编撰,以后世观念论之,刘向《列女传》之著作权是与其子刘歆共享的;(2)《列女传》“七篇”是就文字著作而言,而图画是根据传文而作;(3)《列女图》最初是画于刘向家中屏风上的,后来才将其奉献于汉成帝。尽管佚文到此为止,没有说明其是否呈献,但通过前引班固《汉书》的记载,可知刘向父子肯定曾送成帝御览。至于刘向父子煞费苦心进谏的结果如何,通过汉成帝此前此后的表现来看,可知并不理想。
因当时造纸术还不发达,纸张尚未用作书写和绘画材料,刘向父子所作(更大可能是请画工绘制)、以列女为题材、先画于屏风四堵、后进献于汉成帝的《列女传颂图》,其传文未必不是竹简,但画图则应为帛画。1972—1974年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画,是汉文帝时期的作品,其绘画艺术已达到相当水准;至汉成帝时,帛画流行且更适于观赏,应无疑义。而在帛画上题写文字,是很容易的。刘向著书,采取以图文相辅的形式以方便读者接受、扩大社会影响,应属创举。③参见黑田彰《列女传图概论》。作者虽然没有从题画诗发展史的角度立论,但指出这种图文结合的形式“是《列女传》作者的发明”,是有见地的。传世资料证明,《列女传》之外,刘向还有一部《孝子传》,也是图文相辅的。该书虽不见于史志著录,但《法苑珠林》《文苑英华》均载有其佚文,且后世征引者颇多,或称《孝子传》,或称《孝子图》,可知也是有传、有图的。[4]
值得一提的是,刘向父子初创的在屏风上图画列女以规谏皇帝的做法,在后世亦有继其遗风者。据《后汉书·宋弘传》:
弘当宴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则服,可乎?”对曰:“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5]
这一资料说明:至少到了东汉初年,在光武帝刘秀御座旁的屏风上,也有图画的《列女传》故事。至于是临摹刘向父子原作,还是另有丹青妙手重新绘制,已难以考证。可能是这些列女们都被画得倾国倾城,以致光武帝在接见宋弘时仍忍不住频频顾望。这样,《列女图》的作用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异,成了满足色欲的物事。结果引起了宋弘的不满,当面予以谏止,于是被光武帝随即 “彻(撤)之”了。其实,《列女图》何辜?观赏《列女图》未必就算是好色,宋弘未免责之过苛了。
根据《太平御览》所载《七录别传》佚文,邢培顺以为:“刘向的《列女传》不是史学意义上的人物传记,而是对画在屏风四堵上的列女图的说明”。[6]此说近是,而犹未尽确。下面试作进一步探讨。
按照常识,对图画的说明文字,一般应写于画面之中,至少应该附于画面一侧或其下方。要之,必须连为一体。否则与图画分离,不仅阅览不便,而且容易丢失。而《列女传》传文每篇少则数百字,多则一两千字,无论写在画面之中、画面一侧或其下方,都无可能。显然是无法直接起到图画“说明”作用的。
此路不通,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今通行本《列女传》各篇后面的“颂”。为了了解“颂”在《列女传颂图》这一特殊著作中的地位,需要回顾一下《列女传》的版本流传和变异情况。
在《列女传》版本流传中,其篇(或卷,当时篇、卷通称,故无区别)数屡有变异。《七录别传》刘向佚文自称“七篇”,应为专指传文(包括《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而言,是不包含《列女颂》在内的;《汉书·艺文志》及《汉书·楚元王附刘向传》均著录为“八篇”,当为《传》文七篇外加《列女颂》一篇,共合八篇;而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著录为“《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当为班昭(即曹大家,约45—约117)加注以后,文字增多,于是将《传》文每卷析为上下两卷,共十四卷;加《列女颂》一卷,合为十五卷。北宋嘉佑年间,苏颂(1020—1101)、曾巩(1019—1083)、王回(1048—1101)等人根据颂义、篇次,重新整理,把《颂》分别加入各传之后,定名为《古列女传》,以与各种后起的《列女传》加以区别,成为今天的流行本。[7]这样编排,固然是方便了后来的读者,但却肯定不合刘向当初编次的原意。因为,《列女传》的《传》与《颂》虽然内容上有相关性,但决非一体,而且它们与图的关系也是有区别的。日本学者黑田彰指出:“将颂置于文末的这种形式并不是《列女传》原本的形式,这是南宋蔡骥编定本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这些颂原来单独成为一卷,与《列女传》的七卷正文是分开的,因而,《汉书·楚元王传》记载的《列女传》加上颂一卷共有‘八篇’。那么,《列女传》的文末形式本来是‘君子谓’和‘诗云’这两部分,‘颂曰’之后的内容与正文的叙述没有关系,而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被放置于文末的。”[8]108此说除《古列女传》编定者存在异同外,对《传》与《颂》关系的判断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前文已述及,因为《列女传》传文篇幅太长,不可能写进画面或附于一侧,能写进画面之中或附于一侧的,以情理揆之,只能是简洁凝练的“颂”词。我们看到,这些从形式上模拟《诗经》,均为四言八句,长短一致,檃栝了故事梗概的“颂”,实为简短的叙事诗,无论写在画面上或附于画面一侧,作为读画提示都是很相宜的。读画时同时阅读“颂”,可以了解画面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因为仅看画面,读者未必能明其所以;而借助于“颂”,则可以“知其然”。黑田彰指出:“《列女传》文末的‘颂’主要是点明故事特点,展现故事主要情节,读者阅读‘颂曰’部分,就能了解故事整体内容。”[8]108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列女传》的传文,则是每幅画的本事,除了事先作为创作图画的依据之外,在画作完成后的欣赏过程中,恐怕只能集为一册,置于画旁,以便读画者作进一步了解、“知其所以然”之用了。由此可以知道,当初刘向父子为了规谏皇帝,是何等的煞费苦心。
弄清楚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列女传·颂》为什么内容与传文重复,只是言简意赅地檃括故事,却于传文无所发明,因为其作用本来就是作为画面提示,而并非用来对传文进行阐发的;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刘向自称《列女传》为“七篇(卷)”,因为写于画面(或附于画面一侧)的“颂”本来就是附着于画面,而不是写在书内或附于书后另作一卷的;而早期(刘向之后、宋代之前)的《列女传》版本把“颂”另外作为一篇(卷)附于前七篇(卷)或加注后的十四篇(卷)之后,也是因为“颂”与“传”文本来并非一体;“颂”是专为题画而作,原本分散于各张画面之上,是后人辑录起来作为一卷附于书后(或单独成书,见后文)的。再到后来,因原画早已失传,整理者不知其意,或为了实现新的编辑意图,将“颂”与传文强行连缀起来,才导致叠床架屋之弊。
至于在刘向父子合作的《列女传颂图》中,《传》与《颂》孰为主次的问题,有人以为“这些颂是为了让妇女、儿童们更容易背诵而放置于此的。颂的特征使其能够巧妙地压缩故事的内容,通过背诵这些压缩的内容而联想起故事的全部。像这样单独的一篇颂与《列女传》正文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列女传》作为幼学启蒙书籍所特有的性质。一般来说,幼学书籍由正文(韵文)和注(散文)两部分组成,幼童首先背诵正文,然后再跟随老师学习其内容(注)。如果我们把《列女传》的颂当作正文,把每个传的故事当作是注,便很容易明白这是一种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很正确、传统的学习方法。”[8]108-109此说把颂视作正文,而把传视为注,是完全把《列女传》视为幼学启蒙读物的产物。按照中国传统幼学启蒙读物的样式,这样的说法似乎可以言之成理。用以评论经宋人改编后作为通俗读物的《古列女传》,于人不无启发,但以刘向父子当初创作《列女传颂图》的初衷来说,则显然并不符合,乃至近乎荒谬。因为该书最初的特定读者是汉成帝,其时绝非幼童;而且颂本来是附着于图的,与传文绝非正文与注的关系。
二、《列女传颂》是中国早期的题画诗
《列女颂》如果是直接题写于《列女图》画面之上(或附于其一侧)的颂诗,便成了画作的组成部分。这类诗歌,是中国诗歌里的一个专门种类——题画诗。
何谓“题画诗”?有人以为:“题画诗,顾名思义,是一种以画为题而作的诗,其内容或就画赞人,或由画言理,或借画抒怀,或另发议论。但因这些诗都是缘画而作,所以统称题画诗。”[9]1此说大体不错,但把题画诗解释为“以画为题而作的诗”,这样“顾名思义”,显然是有失准确的。因为“题画诗”之“题”,其本义为“书写”,而并非指“题材”。只是到了后来,题画诗这一概念的涵义泛化之后,才把所有“缘画而作”的诗都纳入了广义的题画诗的范畴。
中国的题画诗,是世界艺术史上一种极其特殊的美学现象。把文学和美术二者结合起来,在画面上,诗和画契合无间,浑然一体,成了一幅美术作品构图上、意境上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诗情画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因此,画面之有题画诗,是中国画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独有的民族形式和风格。
关于题画诗的起源,众说纷纭而分歧颇大。
有人认为:《周易》中的“卦象是图画,画下有彖象释词,且多为诗歌韵文,诗画一体,不可分割,是中国画与题画诗之滥觞。如果《彖传》确为孔子所撰,据此推知,中华人文史上第一位题画诗(作)者,当是孔子。”[10]99称之为“滥觞”,或无不可,但《周易》中的图文离人们普遍认可的题画诗,距离未免过于遥远。
也有人认为屈原的《天问》为中国最早的题画诗,其依据是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言:“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奇伟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11]若果如其言,是屈原“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则《天问》至少应与题画诗有关。不过,姜亮夫(1902—1995)、游国恩(1899—1978)、郭沫若(1892—1978)等《楚辞》研究名家均不认可此说。而坚持此说者仍颇有人在。如刘继才在《中国题画诗发展史》中就力排众议,认为“云气鬼神图式当是战国时楚人祭祀时天人交通的一种媒介。屈原的《天问》也当是诗人看到祠庙壁上所绘的神灵圣贤像而引发联想,呵问咏叹。”[9]24如果此说成立,《天问》的创作当为由赏画引起,但是否写于画壁,仍宜存疑。因为《天问》涉及的众多神奇瑰丽的景象,不可能全都出现于壁画;而把一首长诗写于早已完成的壁画上,可能性也大可怀疑。如果并未题写于画面,没有成为画作的组成部分,还能不能算是题画诗,便很值得商榷了。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前318-前296在位)墓,得竹书数十车,共75篇,其中有“《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12]据此可知,战国时代已有“画赞”之类作品。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信息,可惜这篇《画赞》今不传,其具体内容已无从详考了。
上述观点之外,还有以下几种说法:(1)认为东汉武氏祠石室画像的赞文是最早的题画诗;(2)认为题画诗产生于魏晋南北朝之际,如西晋傅咸的《画像颂》、杨宣为宋纤像所作的颂等;(3)认为庾信的《咏画屏诗》“是题画诗始作俑者”;(4)认为题画诗从北宋开始;(5)认为题画诗起于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等等。[9]21之所以有这样多种差距甚大的认识,除了掌握材料的多寡之外,对题画诗内涵、外延的理解不同应为主要原因。
题画诗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题画诗特指写于画面中的题诗,作者可以是画家本人,也可以是别人。但题诗内容应与画作有关联。因为题诗要以书法的形式呈现于画面,而中国书法又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所以画作、题诗与书法珠联璧合、均臻上乘者往往被誉为“诗书画三绝”,成为艺术珍品。广义的题画诗,除包括狭义的题画诗之外,还包括赏画者受画面内容或其作画艺术引发所写的诗。这类题画诗,独立于画面之外,严格地说应属于对画所作的诗体评论(故有人称之为“赞画诗”或“评画诗”)。至于那些仅以画作作为引子,其实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诗作(如屈原《天问》),严格讲来,是否还可以算作题画诗,已经十分勉强了。
比刘向略晚、而与刘歆同年的扬雄(前53—18)曾应汉成帝之命为赵充国画像作《颂》,因而也有人以为“扬雄此作似可作为中国第一首题画诗”。[13]此《颂》载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列传》,其文为: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2]2995
孔寿山认为:“中国题画诗最早起源于人物肖像画赞颂体,完全符合中国绘画的发展规律。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扬雄此作似可作为中国第一首题画诗。”[13]说“中国题画诗最早起源于人物肖像画赞颂体”,是不错的,但是,具体就扬雄所作《赵充国画像颂》来说,尽管与赵充国画像有关,但并非与画像同时所作,④赵充国画像作于宣帝时,扬雄的颂则作于成帝时。而且其文长达128字,不可能直接题写于画面之上;其内容仅为颂扬历史人物赵充国功绩,与画作并无直接关系,最多可以算作“广义”的题画诗,而与后世人们普遍认为的题画诗尚有距离。论者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接着说道:“我们认识到扬雄所作的《赵充国画像颂》只是以赵充国画像为赞颂的对象,本是《赵充国颂》,并未涉及绘画本身,还不是今天我们所谓的诗与画相结合之题画诗。”
回头再看《列女传颂》,就会发现,与屈原《天问》和扬雄《赵充国画像颂》不同,它应该是刘向、刘歆父子撰述《列女传颂图》之初,即已纳入三位一体的整体构思,而且很有可能是直接题写于画面之上(至少是附于一侧,与画作相辅而行),因此应属于比较正宗的题画诗。不仅如此,《列女传颂》的创作时间应该早于扬雄的《赵充国颂》。因为扬雄到了40岁,才于永始四年(前13)经人举荐入朝,而刘向早已是朝中老臣,并且从河平三年(前26)就已经开始受命与刘歆一起校中秘书了。因此,就中国题画诗之历史而论,《列女颂》应属存世最早的题画诗;而且其数量多达百余首,这样的发现无疑是令人惊喜的。
有人认为:“总起来看,中国的题画诗从西汉扬雄《赵充国画像颂》,中经曹植、傅玄、陆云、陶渊明的画像赞,而至南朝之江淹、沈约、萧纲、庾肩吾的看画诗,逐渐转变为北朝的庾信正式以《咏画》命名,为题画诗的形成及其体制完备作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准备,是题画诗这一艺术形式上的萌芽期。”[10]99这样的排列,总体趋向不错,但完全无视很可能早于《赵充国画像颂》的《列女传·颂》在题画诗发展史上的存在和重要作用,显然是一个严重缺陷。究其原因,应是论者仅仅把《列女传》看作一部文字古籍,而没有注意到《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和《太平御览》所引《七录别传》佚文,尤其没有意识到《列女传·颂》的独特功能和实际用途所致。
三、刘歆应为《列女传颂》的作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内府藏本)”条对《列女传颂》的作者曾作辨正云:
其《颂》本向所作,曾巩及(王)回所言不误。而晁公武《读书志》乃执《隋志》之文,诋其误信颜籀(字师古)之《注》。不知《汉志》旧注,凡称“师古曰”者乃籀《注》,其不题姓氏者皆班固之《自注》。以《颂图》属向,乃固说,非籀说也。考《颜氏家训》,称“《列女传》刘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是讹传《颂》为歆作,始于六朝。修《隋志》时,去之推仅四五十年,袭其误耳,岂可遽以驳《汉书》乎?[14]
据此可知,在《列女传·颂》作者问题上,历来颇有争议。坚持《列女传·颂》为刘向所作者有曾巩、王回,认为为刘歆所作者有颜之推(531—约595)、《隋书·经籍志》作者及晁公武(1105—1180)。四库馆臣则赞同曾巩、王回的意见,不认可颜之推等人的意见,似乎对这一争议做出了定论。
但这一所谓“定论”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
不错,《汉书·刘向传》和《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是把《列女传颂图》的著作权系于刘向名下的。但这应该是就其主要作者而言,不代表没有其他人参与。这与《汉书》仅主体为班固所作,前由其父班彪开其始,后有其妹班昭续其书、班昭门生马续补其缺,历来著录却只系于班固一人名下,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注意到《太平御览》所载《七录别传》之佚文所说“臣与黄门侍郎歆以《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的话,则刘歆曾参与《列女传颂图》的写作,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刘歆所做工作为其中哪一部分,因佚文为断简残编,虽已难得其详,但可以推测。作为此书主体的《传》文,理应属于刘向的作品,刘歆最多做过一些辅助工作;列女画像图,有可能是刘向父子的作品,但也很有可能是刘氏父子另请画工所作(因为存世材料尚未发现刘氏父子兼工丹青的其他证据);而《颂》诗,则只能是刘向父子之一所作。刘歆参与《列女传颂图》写作,既然已有《传》文和画像,他所能做的,也就只有《颂》诗了。他作完之后,自然也会请其父过目审核,提出修改意见,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撰写《颂》诗的事实。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刘向父子在准备进献给汉成帝《列女传》与《列女图》时,考虑到对方在欣赏图画时翻检传文多有不便,所以才又由刘歆为每幅画题写了颂诗作为画面提示。
如果上述意见尚属推测之词的话,颜之推《颜氏家训》所说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则可视为有力的书证。笔者认为,颜之推关于“《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15]的说法,显然是合于情理的。尽管他是否还有其他材料作为依据,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的学术造诣不次于乃父,“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2]1967是载于史传、人所共知的,他参与《列女传颂图》的写作,自不应无所作为,由他来为《列女图》作《颂》,顺理成章而且可以应付裕如。否则,刘向是没有必要把《列女传颂图》作为他们父子的共同作品的。班固著录《列女传颂图》,系于刘向名下,盖因刘向是第一和主要作者,并无不妥。由此观之,《隋书·经籍志》著录“《列女传颂》一卷,刘歆撰”,[16]未必仅仅是因袭颜之推之说,而极有可能是当时府藏图书确有与“《列女传颂》一卷,曹植撰”和“《列女传赞》一卷,缪袭撰”并存、署名为“刘歆撰”的单本《列女传颂》同时存在,史书作者仅为实录而已。也就是说,在唐人编定《隋书》时,刘歆所作《列女传颂》很有可能仍有单本存世。四库馆臣于1000多年后,在缺乏有力佐证的情况下,轻易否定颜氏之说和《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未免失之于武断。其原因,盖由于过分拘泥于《汉书》记载,又没有注意到《太平御览》所载《七录别传》之佚文,故而做出了完全排除刘歆曾参与其事的结论。
若此说成立,刘歆以《列女传·颂》而跻身于现存中国正宗题画诗之第一人,应无争议。
四、结论
刘向《列女传》一书记载了先秦至西汉104位女性的故事,具有多重开创性意义。首先,此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记载妇女生活为对象的专著,对弘扬优秀女性的美德、引起人们对女性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的关注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在史书体例上,此书与其另外两部著作《新序》《说苑》开创了史籍“杂传”类的先河。这都是人们所公认的。现在看来,不仅如此,此书还是传世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与图画相辅而行的著作,其中的“颂”更是中国最早的题画诗,而《颂》的作者,则应当是其子刘歆。刘氏父子之后,为图画作颂赞乃大行其道,以至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了。
笔者于读书中偶有所得,特不揣浅陋,草成此文,以为野芹之献,谨供研究中国题画诗发展史及《列女传》之学者参考。
[1] 司马迁. 史记·滑稽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205.
[2] 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李昉,等. 太平御览(第七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36.
[4] 李剑国.略论孝子故事中的“孝感”母题[J]. 文史哲,2014,(5):54-60.
[5] 范晔. 后汉书·宋弘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65:904.
[6] 邢培顺. 论刘向《列女传》中所载齐鲁女性[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6):47-55.
[7] 詹晓青,谷文珍. 刘向《列女传》研究的成绩与不足[J]. 龙岩学院学报,2010,(3):23-26.
[8] 黑田彰. 列女传图概论 [J]. 隽雪艳,龚岚,译.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3):107-122.
[9] 刘继才. 中国题画诗发展史[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1.
[10] 东方乔. 题画诗源流考辨 [J]. 河北学刊,2002,(4):97-100.
[11] 王逸. 楚辞章句·天问序[M]// 洪兴祖. 楚辞补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83:85.
[12]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1433.
[13] 孔寿山:《论中国的题画诗》[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6): 105-109.
[14] 纪昀,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三·传记类一·古列女传(第2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7.
[15] 颜之推. 颜氏家训[M]. 北京:中华书局,2011:272.
[16] 魏征,等. 隋书·经籍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3: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