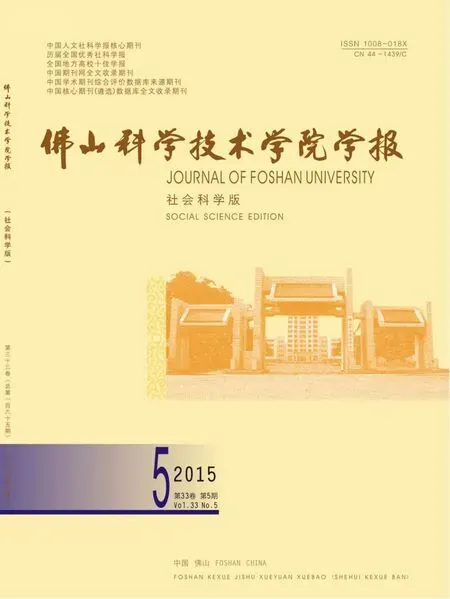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科技思想探析
晏湘涛,张 华
(1.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74;2.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科技思想探析
晏湘涛1,张华2
(1.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74;2.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科技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时间尺度来看具备正面的价值;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成为工人受奴役的重要根源,而正确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有赖于根本的社会变革;指出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利用科学技术来构建生态文明必须变革社会制度;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规律,从而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科技思想;科技价值观;生态观;科技发展规律
张华(1974-),男,湖南怀化人,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晚年恩格斯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时,曾经谦虚地指出:“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1]综观恩格斯的工作,这几个“专门的领域”应该集中在恩格斯在科技思想、军事思想、语言学等领域。尤其是恩格斯的科技思想(在《自然辩证法》中进行了集中论述),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科学计量学等领域的进展。
恩格斯的科技思想虽然在《自然辩证法》中集大成,但是许多重要观点在其青年时期已经基本形成。正是他在早期生涯中的这种敏锐、深刻,促使他和马克思走到一起,共同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因此,把握恩格斯早期的科技思想,是我们理解唯物史观的一个线索,也是我们当前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推进科学技术事业健康发展的理论基点。
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早年恩格斯的研究[2]。早年恩格斯的著作中,《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大纲》使马克思开始注意到恩格斯的工作,并促使马克思开始从哲学批判转向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开始了与恩格斯近40年的合作,从而结束了恩格斯的早年时期。针对《大纲》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恩格斯的经济学思想、社会主义理论、社会建设思想等方面。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大纲》中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而挖掘早年恩格斯的自然观,为我国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然而,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马克思实时关注“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一样,他自己从青年时期开始就非常注重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此前所有的思想家不同,恩格斯逐步形成了唯物史观,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科技观。在《大纲》中,恩格斯的科技观远远超出了生态自然观的范围,集中表现为一种崭新的科技思想。
一、确认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恩格斯在梳理历史上的经济理论,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德国即为“国民经济学”理论)时发现:以往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细胞”的“商品”的生产费用时,忽视了科学技术这一重要要素。他指出,生产费用包括“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这两个方面,而劳动除了资本(积累起来的劳动)、简单劳动(单纯肉体要素)之外,还有“第三要素”,即“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他指出,“科学……把生产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3]67-68。
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内部要素(变量)而不是外部要素(常量)来考虑,这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的基础和核心。然而,这个重要的理论的要点,在恩格斯的《大纲》已经初见雏形。
恩格斯在理论上解决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后,随即用其来解决当时争论非常激烈的人口问题。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是将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和痛苦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而是归结为人口生产过快和过多。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指出马尔萨斯的错误,而是在肯定马尔萨斯人口增长规律的基础上,指出应对人口增长必须立足于人类自身的进步力量,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他指出:“即使我们假定,由于增加劳动而增加的收获量,并不总是与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这时仍然还有一个第三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3]82因此,只要改革社会制度,发展科学技术,解放社会生产力,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而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各种反人类的减少人口的措施来予以解决。
恩格斯坚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粮食生产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对其他社会问题也是如此。“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祝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它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之中起作用。”[3]77恩格斯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科学技术将得到长足发展并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一点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大不相同,也与当代中国社会中逐渐流行的思潮大不相同。有许多人认为,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还是要靠资本主义;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是值得期许的。如英国著名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强调:“资本主义创造了自身无法驾驭的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将之置于人类控制之下而不是继续刺激它膨胀。”[4]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其中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长期接受或浸淫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们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科技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中存在的反科学主义也反映了这种冲突。通过深刻理解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成功运用科学的力量“并为大众祝福”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科学技术的历史价值,坚定不移地执行“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
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恩格斯敏锐地看到,资本在运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由于纯粹的牟利目的将工人塑造成机器。“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被用来做一定的细小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3]86如果工人一直从事简单、重复、长时间的奴隶劳动,也就相当于剥夺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权力和能力,最终也会阻碍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值得我们十分警惕的“科技异化”现象[5]。所以,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强调工人要开展积极的社会活动,降低劳动强度和减少劳动时间,为掌握科学与文化提供条件;先进知识分子要在工人阶级中大力普及科学与文化,带领自觉的工人阶级赢得社会革命的胜利。
二、一种理论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息息相关
科学知识到底是人类对自然本质的认识,还是知识发现者个人立场建构的结果?围绕这个问题,科学哲学界开展了长期激烈的争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阶级性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大纲》中分析了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经济科学发展的脉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长时段分析方法,那就是:从历史长时段来看,一种理论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息息相关,站在落后阶级立场而发展出来的知识不具备科学性。
任何时代都是进步力量与落后力量斗争的结果,所以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是站在进步与落后的十字路口上,只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而已。早年恩格斯生活的社会环境里,神学世界观逐步崩溃,自由主义慢慢成形。时代的矛盾反映在哲学上,使得黑格尔的哲学一方面成为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德国思想界的反映,另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宗教启示意蕴。恩格斯在参与“青年黑格尔”运动中感同身受,进而发现任何一种理论中包含的这种二重性,实质上是与社会现实分裂息息相关的。他指出:“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得前进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消灭。”[3]59也就是说,社会的任何进步都不是绝对的;社会各阶层对社会进步的理解也绝不相同。当神学前进到自由哲学的时候,对社会保守势力而言,这是一种大大的退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在走下坡路;社会应该朝着更加保守、更加固化的方向,才是正道。同样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时,必然会遭受到两个方面的阻击:一方面是由于触犯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重新回到重商主义体系中;另一方面是产生了庞大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要求进步到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种状况反映到一个时代的科学中,就必然导致一个现象:流行的理论在应对落后方面来的批判是应对合理的;而在应对先进方面的批判时就一定只能采取诡辩的手法。
例如,恩格斯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经济现象,指出:“贷款生息,即不花劳动单凭贷款获得收入,是不道德的,虽然这种不道德已经包含在私有制中,但毕竟还是太明显,并且早已被不持偏见的人民意识看穿了,而人民意识在认识这类问题上通常总是正确的。”[3]70“利息”是经济科学中的基本概念之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各个派别都同意:“资本”有取得“利息”的“天然权利”。然而,恩格斯发现,不管何种形式的“利息”,都是不劳而获,可以归结为“不道德”。这一点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看清楚的。特定时代的经济科学无法看到这一点,充分说明了经济学家们所持有的资产阶级立场。
而经济学家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流行,关键还在于社会需要。恩格斯认为,理论总是需要解释现实的,而什么样的理论能够流行,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则是利益的产物。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其产生而言是很正常的,因为人口过多这种现象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何解释人口过多的实质,就使得统治阶级筛选、精炼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是,既然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为了使这种事实与理论一致,就发明了人口论。”[3]78恩格斯用“发明”而不是“发现”,说明他对于理论构成的社会基础有清醒的认识。进一步,恩格斯还指出:“我是否还需要更详尽地阐述这种卑鄙无耻的学说,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污蔑,并进一步探究其结论呢?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3]79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有一个“道德”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站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炮制出来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受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来说,是无耻、荒谬,因而是不道德的。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例,之所以说它“恶毒污蔑”自然和人类,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回避制度的矛盾,而是先在地认定“制度合理”、“既得利益合理”。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进步的阶级立场意味着敢于揭露社会矛盾的本质,这就是其科学性的根源;反之,落后的阶级立场为了保守现有统治阶级的利益,着意挑选、扶植那些掩盖、歪曲社会矛盾本质的理论体系。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宗教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阻碍、对科学家的迫害,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当然,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不是简单、线性的。现代社会不时出现的反科学、反技术潮流,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现实:科学技术在短期内总是使统治阶级受益,因为统治阶级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早学会应用科学技术。所以,“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是用来反对劳动的。”[3]85恩格斯接着指出,科学技术帮助资本来反动劳动,是通过降低劳动需求,从而使工人不得不陷入对资本更深的依赖之中:“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这项发明使机器劳动增加了一倍,从而把手工劳动减少了一半,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了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项发明破坏了工人对工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3]86统治阶级将科学技术作为巩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造就了科学技术“助纣为虐”的表现。但是,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推动作用,不能只从当代的社会表象来看,而应该将之推到历史长河,扩展到世界层面来关注。蔡伦在皇宫发明纸,不能用于说明皇权对文化普及的重视;雕版印刷最先用于印制佛经,不能证明佛教推动了科学发展;古腾堡活字印刷技术最早用于印制《圣经》,不能用于说明基督教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进步作用;当代绝大多数技术最先用于牟利,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推动科学技术的根本动力;这些问题,只能说明皇权、教权、财富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具备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可理解性、进而带来可学习性。由于这种可学习性,这种知识必然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最终,这些知识极大地改变了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力量对比,最终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或全体)上升为统治阶级。历史在这样的推动下不断进步。因此,科学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
三、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
恩格斯在《大纲》中的生态思想,是关于《大纲》研究的热点,成果也比较多。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大纲》中的生态和进化思想进行过长篇评述[6],常艳注意到《大纲》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实现“和解”的思想[7],倪志安将《大纲》中的“和解”思想解读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解”[8],刘英评述了《大纲》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生态性的批判[9],许俊达、何峻指出《大纲》中的“和解”思想意味着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本身必须进行重大变革[10]。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恩格斯在《大纲》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下要点:
一是生态批判本身是一种哲学形式,所以不同的生态思想背后也隐藏着立场问题,这是我们考虑各种生态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恩格斯强调:“马尔萨斯的理论只不过是关于精神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关于二者的堕落的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我希望也在经济学领域揭示这个对宗教来说并与宗教一起早就解决了的矛盾的虚无性。”[3]8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批判理论的基础是哲学,每一种生态学背后都有一定的哲学理论。
二是恩格斯在考虑任何生态问题时,都是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维度来进行考察的。生态问题表现为自然条件的恶化,但是其根源却在于社会制度。恩格斯明确指出:“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其次,我们看到,人的活动又怎样分解为劳动和资本,这两方面怎样彼此敌视。这样,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这三种要素的彼此斗争,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支持;现在,我们还看到了私有制使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分裂。”[3]72也就是说,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这种恶果同时伤害了自然与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各种力量、各种流派都提出自己的生态环境改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所批判的“私有制”力量的体现。关注自然这一端的主要是两种思想:一种强调敬畏自然,不干预自然,鼓励人们回到原始状态,这种思想已经被广泛用于发达国家劝说发展中国家放弃、放缓发展,以维持发达国家高消耗的生活质量;第二种是强调科学技术的力量,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这种思想也很快形成以新技术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关注社会这一端的主要也是两种思想:一种强调制度设计,如碳排放交易、引入生态成本等,将环境改善纳入资本范畴,没有考虑到资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放弃生态责任;第二种是强调制度根本变革前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实际上成了生态空想社会主义。所以,恩格斯关于综合考虑自然与社会的思路,就显得尤为可贵。
四、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规律
恩格斯从早年开始就密切关注科学技术的进展,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规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科学技术作为人的能力的象征,人类解放的动力,必须要得到健康的发展。
恩格斯首先看到,科学技术事业要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必须要“超越利益的分裂”[3]67,也就是说,在社会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的情况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受到限制的。统治阶级倾向于利用科学技术的成就来维持其统治,这就大大损害了科学技术事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而且,统治阶级对于那些无助于统治甚至有害于统治的科学技术进展百般阻挠,直接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将大量精力用于阶级之间的对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军事技术的优先发展”的规律[11]。掌握政权、掌握军队的统治阶级,在与反抗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中,总是极力运用科学技术保持军事优势。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层出不穷。这就造成科学技术资源的极大浪费。只有在超越利益分裂的共产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能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恩格斯发现,就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来说,由于科学技术意味着人类知识和能力的增长,所以其发展具有累积的性质。也就是说,“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3]82现代科学计量学研究表明,科学知识的增长服从指数增长规律,这与恩格斯的判断是一致的。而现代许多科学哲学家不相信科学技术的增长是无限的,认为这种指数增长一定会遇到“天花板”。其实,这种担忧正反映了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发展受限的性质。而恩格斯相信,只要摆脱了利益的分裂,科学的进步“与人口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3]82
第三,具体到特定学科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要与社会发展同步,但由于科学知识的继承、累积性质,使特定学科的发展不是线性前进的,而具有阶跃的性质。他以经济学的发展为例。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的发展就受到社会实践发展的多方面影响。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体系,还是自由贸易理论体系,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个理论体系如果符合时代的需要,就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理论的解释力就会出现问题;但是,理论本身由于受到诸多利益集团和理论家的支持,不可能实时进行修正。于是,“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3]59这一点与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看到,只有在“理论自觉”的人民那里,“与时俱进”才是可以预期的。
最后,由于恩格斯在早年就敏锐地发现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质,所以,他预测社会必然要对科学技术事业进行管理。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研发的费用要成为社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社会也必须从总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科学技术工作。他指出:“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正如在经济学家那里发生的那样——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植科学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3]67恩格斯指出,社会(特别是经济部门)必须系统地支持科学技术事业。这就是科学技术建制化的先声。
当然,恩格斯的科学技术思想到晚年更加深刻、更加体系化,他在《大纲》中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到晚年转变为对人类无限索取自然的深深担忧。而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肯定,对资本阻碍科技发展的批判,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信念,对科技发展宏观规律的把握,是前后一致的。我们要更深入地理解《大纲》中的科学技术思想,为我国当前的科技事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42.
[2]孔寒冰.早年恩格斯:经历与思想——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5): 37-4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EAGLETON Terry. Why Marx Was Right[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6.
[5]张青卫.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技术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2): 117-123.
[6]王圣祯,张鸿冰.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道德建设的启示[J].学术交流, 2013(8): 10-13.
[7]常艳.恩格斯生态思想初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4): 46-49.
[8]倪志安.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J].哲学研究, 2012(10): 30-34.
[9]刘英.论恩格斯1844-1846年著作中的生态思想[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5-9.
[10]许俊达,何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启迪[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 16-23. [11]刘戟锋.哲人与将军——恩格斯军事技术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Research on Engels’Though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YAN Xiang-Tao1, ZHANG Hua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4, China; 2.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Engels had formed complete though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reflected in the article of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ngels emphasize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strong power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S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ositive valu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apitalist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came important causes that workers were enslaved. So, it was depended on social changing to play a correct rol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italist system was the root cause of ecology damage. Engels revealed the macro laws, which supplied the new angl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Engels;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ough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lu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lues of Ecology; la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晏湘涛(1978-),男,湖南株洲人,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21)
收稿日期:2015-04-20
中图分类号:A8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15)05-00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