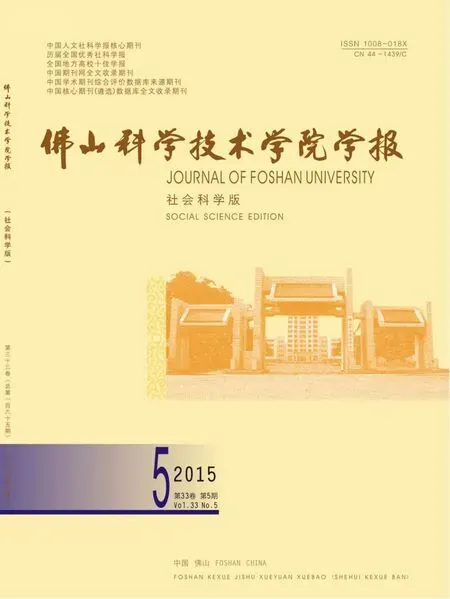论何焯对柳文的批评
梁必彪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354300)
论何焯对柳文的批评
梁必彪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354300)
摘要:何焯很关注柳宗元的古文,对柳文有很多评论。但何焯对柳文基本持贬抑态度。何焯对柳文之“道”,颇有疵议,认为柳文之“道”不合圣人之旨。同时,他以“雅”、“洁”的标准来批驳柳文之“文”,认为柳文不“雅”、“少味”、不含蓄,需要删削。何焯对柳文的批评解读虽有不透彻且极为苛刻武断之处,但其对清代雅正的古文规范的建立、对方苞及桐城后学的文论产生重要影响,引领了桐城派文论的发展。
关键词:何焯;柳文批评;抑柳扬韩;桐城派
何焯(1660—1722),初字润千,后字屺瞻,号义门,晚号茶仙,江苏长洲人,学问渊博,著述丰富,是清代前期著名的学者。何焯擅长校勘经、史书籍,由其儿子及门人整理的《义门读书记》在校勘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同时,何焯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文学批评的成果,其中对柳宗元古文及其思想的批评很有特色,能典型地反映清代前期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潮流所趋。
一、论柳文之“道”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关系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命题。
刘勰最早以文论家的视野将“道”纳入文学批评领域。他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1认为“道”的本质含义是“自然之道”,即自然的道理或规律。接下来他谈及文、道、圣的关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2刘勰奠定了后世的文道关系的基本模式。文原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等等,都是刘勰的文道关系模式的发展。文道关系的基本模式确定了,但道的含义,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具体指向。大抵有自然规律、儒家政教、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含义。“道”有时又指文章的思想、观点、内容之属,与文章的修辞、语言、技巧、布局等属于艺术形式的“文”相对。
何焯批评柳文所涉及的关于“道”的表述有很多种。但不管是从程朱理学角度所说的孔孟之儒道,还是指道家、释家之道,抑或更为开放地泛指文学思想、观点等方面的“道”,何焯对柳文之“道”基本持贬抑的态度。
何焯首先对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观点不满,他认为柳宗元混杂了夷夏之别。
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为了反驳韩愈以外夷之嫌而斥浮屠时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2]425
季札是吴越之人,由余为戎狄之后,在身份和血缘追认上虽然有一定的非中原正统的渊源,但是已经是得到孔子及儒家后学公认的圣贤。何焯不满柳文将季札、由余与浮屠相提并论,因此反驳道:“而贱季札、由余乎?季札、由余用夏变夷者也。”[3]641认为季札、由余是为传播华夏正统文化以教化夷邦做了贡献的人,不应受到“贱”视。
实际上,何焯这里对柳文的解读不透彻。公羊春秋学以礼乐教化程度区别“华夏”与“夷狄”,不会机械地以地理位置区分“华夏”与“夷狄”,作为受学于啖助、陆淳春秋学的柳宗元肯定不会因为季札、由余不来自“华夏”地区“贱”他们。柳宗元用比拟的方法反驳韩愈重名不求实,无视释、儒之“道”内在的相通而盲目地以“夷”、“夏”之别贬斥浮屠的态度。柳宗元的用意不难理解,但何焯似乎有意曲解柳宗元的比拟,目的是为了反驳柳宗元对释氏的倡导。
柳宗元认为佛教也有教化的功能,但何焯为了倡导儒家的教化之道,将柳宗元所指的佛氏之教化附会到儒家之教化中。柳宗元《柳州复大云寺记》说:“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宗元看到当地人民因虔信鬼神而荒废田地、人畜不凋敝,而且“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柳宗元导之以“浮屠”之事教化百姓,希望改变这种现象。柳宗元意谓儒释之道是相通的。据此,何焯言“先王为治,百家皆所用……柳子至此信奉佛氏似少衰矣。盖读书久而少有悟也。”[3]645因为儒家所推崇的“先王”是融合百家为治的,所以何焯在这里没有直接驳斥柳宗元对佛氏教化功能的肯定,而以“柳子至此信奉佛氏,似少衰矣”来自圆其说。
柳宗元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改革家,他的一些古文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极为精辟。但只要这种言论违离或跨越了孔孟圣贤之道,何焯就会不满。何焯对柳文的社会思想批评最犀利的当属对《封建论》的批判。
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利弊作了辩证的分析,论证充分,气势凌厉,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苏轼云:“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4]104然何焯以“至言圣人不废封建,私其力于己,私其卫于子孙,柳子之言何其悖乎?”[3]607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论》中的社会思想。何焯是为了捍卫圣贤之“道”而断章取义地否定柳文之“道”。林纾就此抨击以何焯为代表的卫道者:“圣人不欲违势以戾民,故因势而成封建,正是圣人圆通广大处。腐儒见一‘非’字,便以为开罪圣人,抵死与争,谬矣。”[5]72章士钊也批判何焯说:“义门指子厚言封建私力私卫为悖,即其开口便错处,不足深辩。”[6]64
柳文中之“道”除了儒、释之外,还有道家之“道”,这也是何焯不接受的。柳宗元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表达了对从弟柳谋懂得进退,不勉强求进身而终究身安心闲,令名彰显的处世之道的敬佩:“不谋食而食给,不谋道而道显。则谋之去进士为从事于远,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2]403柳宗元遭贬永州多年,那场刻骨铭心的政治运动或许磨灭了他往日的进取之心。所以这里流露的就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但何焯不理解柳宗元的这种态度,他说:“不谋道而道显,道可以不谋而显乎?”[3]638显然,何焯用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入世的态度否定柳宗元的道家无为退让之“道”。
何焯不仅从官方意识形态上批驳柳文中的“道”,也从道德涵养的角度评价柳文的“道”,认为柳宗元为学不精。何焯评《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时,开篇就说:“多有不足。缕缕致辨者,而亦毛举不已,所谓道不足而强有言也。”[3]655这里的“道”当指道行,涵养。儒家很看重作文者的道德修养。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孟子言要养“浩然之气”,韩愈也说“气盛言宜”。何焯说此文层层盘剥,分析过于细致,显得烦琐不堪。何焯认为这样的作品“均非中道”的原因是涵养不够而强为之的结果。
由此可见,何焯在儒、释、道以及作文的涵养等面展开了对柳文之“道”的批评,而且,总体上对柳文之“道”呈批判态度。他对柳文“道”的否定,势必影响他对柳文之“文”的价值判断。
二、论柳文之“文”
儒家传统的古文观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在古文批评家看来,优秀的古文的价值在于“载道”和“明道”。在这种文道关系的模式中,如果批评家不认同某位文家的“道”,那么“载”其道或明其“道”所需的词句语言、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等艺术技巧方面的“文”也得不到认可。
何焯对柳文之“道”不认同,对柳文之“文”自然也多有否定。何焯对柳文之“文”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主要以“不雅”、“俗”、“少味”、“删削”、“鄙薄”等非议柳文。一言以蔽之,何焯是以“雅”“洁”之标准批判柳文之“文”。
(一)柳文之“不雅”
何焯往往以“不雅驯”、“偏激”、“轻薄”、“浅薄”、“凡近”等与“雅”的审美规范相反的词语来批驳柳文。
何焯批评柳宗元的《说车赠杨诲之》:“词胜理。以为车说则备矣。‘视叱齐侯类畜狗’,李云:柳文不雅驯若此,此言蔺相如犹不可也。”[3]628引用李光地的评论,言柳宗元的比喻夸张不恰当,失之“不雅驯”。
再如论《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谷梁字曰’五句,直斥其无自而托为自反之辞,赖引《谷梁子》数句,粗存墙仭。此篇诙啁之作,要之轻薄,作者不尚,发端亦太尖。”[3]638
柳宗元的《送薛存义之任序》表达的是尊民恤民的思想,这与孟子的君轻民重思想是一致的,但何焯认为其文辞激烈:“‘以今天下多类此’至‘势不同也’,此言岂可公传道欤?此序词稍偏激。孟子虽发露,犹自得其平也。”[3]636认为孟子的言论虽然有“发露”之处,但终究能落于平正,而柳宗元却失之不“平”。其他的如论《送赵大秀才序》:“辞旨浅薄,吾岂丐夫隶人哉!”[3]636论《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此永州文,犹未能脱弃凡近。”[3]639,等等。何焯以“雅”作为古文评价的典范标准,指出了柳文有诸多失“雅”之处。
(二)柳文之“不洁”
柳宗元作文很看重“洁”。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言:“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騒》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3]543明人王世贞、清人包世臣、刘熙载等都曾言及柳文风格峭拔峻洁。但是在何焯看来,柳文还是失之“洁”,柳文的字词、语句需要删削,甚至柳宗元文集中的部分作品需要全篇删除。
何焯评《岭南节度飨军堂记》:“更简百余字,则笔力益高。”[3]642认为字词上可以更为简洁。何焯更多地指出了柳文中语句段落的不“洁”,需要删削,比如:评《捕蛇者说》:“‘永之人争奔走焉’,此句伏下‘悍吏之来吾乡’至‘又安敢毒耶’,虽无奇特,亦自隽快。此篇宜削去其三分之一何如?”[3]627
评《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此文削其半,则及与古矣。”[3]656
评《游黄溪记》:“发端既涉模拟,又未必果然也。删此,而直以‘黄溪距永州治七十里’起如何?”[3]646
更其甚者,何焯往往对柳文全篇否定,认为柳文集中有些篇目应该通篇删削。何焯评《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如此文宜悉削去。梦得编集,更少百篇,则柳之道益光。”[3]637认为刘禹锡编集的柳宗元文集,需要删除部分无益于彰显柳氏之“道”的篇章。其他的如:
论《永州铁炉步志》:“‘则求位与德于彼’数语,笔亦膠绕不圆快。‘大者桀冒禹’云云,此文直斥在上者徒建空名,旨趣已偏宕,求其警策,则又无有,何以存诸集中?”[3]645;论《答貢士沈起书》:“此早年最卑浅之作,宜削。”[3]656论《送苑论登第后南归觐诗序》:“如此作宜从削略矣。”[3]636;论《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此篇可削。”[3]637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素来与韩愈并肩齐名,享有盛誉。即使对柳宗元有非议者,多言其所附非人,参与了“奸人”的政变。但是如此大胆苛刻地非议柳文、辄言删削的,在何焯之前,罕见其匹。何焯对柳文的贬抑态度可见一斑。
(二)柳文之“少味”
对儒家的古文批评者来说,古文的淳雅与含蓄有味是密不可分的。何焯以不雅非议柳文的同时,也往往以“少味”批驳柳文。
何焯评《愚溪对》云:“中间颇指斥举错倒谬,则后之所谓己之愚者,无非所遭之不幸,非其罪也。然稍乖敦厚……‘汝欲为智乎’至‘使一经于汝’,无须臾忘报复,宜人之畏而摈也。词旨亦激迫少味。”[3]623-624;“然稍乖敦厚”、“词旨亦激迫少味”不仅言其不合雅,而且“少味”。
与此相似的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仆自卜固无取’五句,笔善折,故常语皆遒,然不应若是之费墨也。吾以为柳子之未远于六代者,以此。‘然雪与日岂有过哉’二句,李云:词无涵蓄至此。‘平居往外,遭齿舌不少’二句,此等语亦何味,但觉其尖薄耳。”[3]656-657《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后世称道,但何焯言此文“费墨”、“无涵蓄”、少味。何焯所批驳柳文之“文”的三大缺陷,在这里集中呈现,可见何焯对柳文之“文”的批评是相当苛刻的。
何焯对柳文的“少味”、不含蓄的批评是很频繁的,其他的如评《对贺者》:“‘嬉笑之怒’四句,太尽反少味。”[3]624;评《鞭贾》:“此文何味之有?不作也可。”[3]634;评《序棊》:“通篇少味。”[3]639;评《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森然炳然,若开群玉之府’六句,点染类字,然似少味。”[3]635
三、何焯抑柳扬韩与方苞及桐城文论的发展
如上所述,何焯对柳文总体上是持贬抑态度的,但对与柳宗元齐名的韩愈的古文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对韩文之“道”和“文”都显示出大力的推崇和尊扬。
何焯对韩愈之仁义、心性之说评价极高,认为韩愈是继孟子之后的儒家的真正传人。何焯在评论《原道》时引用李光地的话说:“安溪云:‘韩子言道,其论仁义之意甚美;其觝佛老所谓争四代之惑,比于距杨、墨之功者也。’”[3]527认为韩愈辟佛以弘扬儒家之仁义,比得上孟子拒杨、墨之言以捍卫儒道的功绩。
何焯认为韩文所体现的经术思想纯明,对之大为赞赏。何焯将韩愈的《祭鳄鱼文》追捧到近六经的高度:“此文曲折,次第曲尽情理,所以近于六经。……韩子斯举,明于古义矣。辞旨之妙,两汉以来未有。”[3]592
何焯尊奉韩文之“道”,对韩文之“文”也多为溢美之词,他往往以“妙”、“洁”、“淳雅”等褒扬韩文。何焯评《上贾滑州书》:“雅洁古节。”[3]599再如评价《请迁玄宗庙议》:“谨洁似经。”[3]598
更能体现何焯尊奉韩文的是,何焯以时文评点法大力评点韩愈的古文。他从字法、句法、章法、文章的起承转合、伏应断续、层次结构等多方面展开对韩文的评点。何焯对韩文的评点往往冗长无味,如他以813字的大篇幅评点《平淮西碑》,但是这些评点平实无奇,赘语冗词,不忍卒读。如此评点虽备受訾议,但由此正可以看出,何焯对韩文的重视。相比之下,他对柳文的评价,多从宏观大体处着手,很少鞭辟入里地分析,而且多持贬斥否定态度。
何焯对柳文的贬抑和对韩文的尊扬,是康熙皇朝文化上“崇儒重道”、“尊孔尊朱”、文学创作上日渐追求“清真雅正”的美学风范在文学批评上的反映。在这种文化思想影响下,柳文因含有儒家的异端思想(柳宗元的《六逆论》攻击周礼,《吏商》、《天爵论》反驳孟子的思想,并且把尧舜之道与文、武、周公之道对立等等),必然受排斥,而何焯作为备受康熙皇帝赏识的重臣,他在文学批评上必然首先扛起卫道的大旗,打压贬抑柳文,而尊扬相对保守的韩文。何焯在柳文批评上体现出来的正统保守、为皇家治策张目的文学观,直接影响了稍其后的方苞及桐城后学的古文观。
桐城人总体上尊奉唐宋八大家,但是在韩柳并提时,便有抑柳扬韩的倾向。方苞说“子厚自述为文,皆取源于六经,甚哉,其自知不能审也!彼言涉于道,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7]112而说韩愈“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后文士所可比并也”[7]164在方苞看来,韩愈能得“六经之旨”,而柳宗元之道,是多“支离”、“未当”的。故清人凌扬藻云:“望溪宗法昌黎,心独不惬于柳。”[8]480桐城文派集大成者姚鼐对柳宗元也多有微词,清人陈衍云:“桐城自望溪方氏,好驳柳文,姚氏亦吹毛求疵矣。”[8]556桐城人抑柳扬韩的态度与何焯如出一辙。
何焯抑柳扬韩,在审美上以“雅”、“洁”为规范,这也是桐城派文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方苞在《答程夔州书》中说:“凡为学佛者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7]166认为柳文用语庞杂,未能雅驯,不像韩愈那样“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方苞以雅洁为古文规范,可以说是康熙文坛的时代潮流所趋,然不能说没有受到何焯这位前辈的直接引领。
何焯以时文评点法评析韩柳文,也受到桐城人的追捧。方苞主张以古文为时文,以救时文之弊。其《古文约选序例》中说:“学者能切究与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7]613在《礼闱示贡士》中方苞也表明了这种主张。
方苞作古文很在意何焯的意见。据《清史列传》记载:“然苞有作,必问其友曰:‘焯见之否?是能纠吾文之短者!’”[9]5817方苞生平稍后于何焯,与之共处清前期的文化政策中,他与何焯同朝为官,而且与何焯有私下的交谊,他的文论必然受到何焯的这样的前辈的影响。
桐城派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古文的做法。方苞被认为是桐城初祖,是桐城文论的建立者。但是桐城文论的一些关键问题,都在何焯的柳文批评中,有了较为明晰的表述。何焯对柳文从“道”和“文”两方面进行贬抑的“破”,为雅正的文学观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桐城派以“义法”、“雅洁”为核心的古文规范正是在何焯对柳文的“破”的基础上“立”起来的。雍正时期正式提出“清真雅正”古文审美要求,正是这种“破”与“立”的辩证运动的结果。桐城文派与清代命运相始终,所以,何焯的柳文批评,对有清一代以桐城文论为主体的古文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何焯.义门读书记[M].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7.
[4]苏轼.东坡志林[M].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1.
[5]林纾.韩柳文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6]章士钊.柳文指要[M].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0.
[7]方苞.方苞集[M].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8]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64.
[9]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责任编辑:张惠fszhang99@163.com)
He Zhuo’s Comments on Liu Zongyuan’s Ancient Chinese Prose
LIANG Bi-biao
(Chinese Department of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354300, China)
Abstract:He Zhuo paid much attention to Liu Zongyuan’s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d took a lot of comments on Liu’s writings. But He Zhuo took negative attitudes to Liu’s writings. He criticized the“Dao”of Liu’s writings for its not being in accord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Meanwhile, He Zhuo refuted Liu’s writings because of being not elegant and concise, and he thought Liu’s writings should be cutting out unnecessary details. He Zhuo’s critical attitude to Liu’s writings help to establish the classic creating concept for ancient Chinese prose, which had 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Tongcheng School.
Key words:He Zhuo; comments on Liu’s ancient Chinese prose; respecting Han’s writings and depreciating Liu’s writings; Tongcheng School
作者简介:梁必彪(1974-),男,江西上饶人,武夷学院讲师,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6-21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15)05-008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