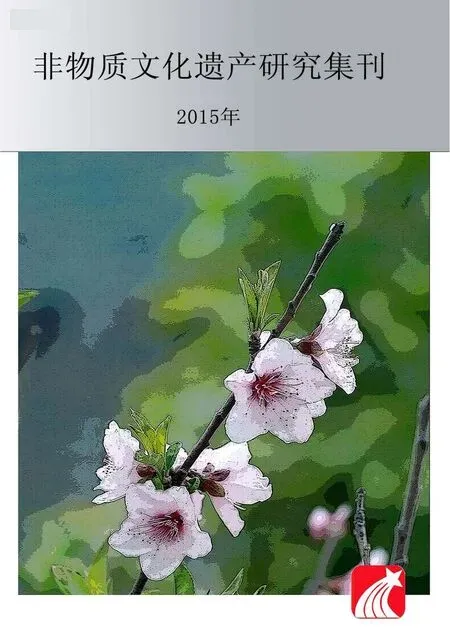浙西南菇民宗教信仰研究
杨震山
(浙江师范大学文学分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浙西南菇民宗教信仰研究
杨震山①
(浙江师范大学文学分院 浙江金华 321004)
菇民的宗教信仰是南方民间宗教信仰的一种类型,兴盛至今。因菇业生产环境随季节变化,存在多种形态。笔者以菇神庙的多样性为切入点,选取菇山和菇民生活区为考察地点,描述宗教信仰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形式,探讨菇民宗教崇拜的起源与发展,分析菇民宗教信仰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菇民 菇民宗教 菇神庙 菇帮
菇民是中国浙江南部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自古以来半种田半种菇的特殊农民群体。他们生于山区,每年清明至中秋经营单季稻生产,整个家庭从事土地上的耕作,所以他们属于农民;秋分至来年清明的这段时间,家庭中的成年男子则背井离乡,远赴中国南方11个省的山区从事香菇种植,所形成的庞大种菇群体称为菇民。
一、菇民宗教概况
(一)香菇栽培与菇民宗教
1.香菇栽培史
我国的野生菌食用历史悠久,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史稿》记述:“至少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开始采食蘑菇。”①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7页。人们在采集过程中,认识并学会某些食用菌的种植方法,逐渐掌握了人工栽培技术。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江南诸山郡中,大树断倒者,经春夏生菌,谓之葚。”②张华:《博物志》卷三“异草木篇”,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页。“葚”与“蕈”同音,后者出自王祯农书《菌子篇》,用于称呼香菇,也是后世文献对香菇的统称。“断”在这里是动词,指人工截断树木。生于人工断截的大树,正是种香菇的基本方式。按照张寿橙教授论证,我国人工栽培香菇的历史由晋代开始至少已有1800年。宋代《咸淳临安志》载:“永嘉人,以霉月断树,轩深林中,密斫之,蒸成菌。”“霉月断树”③张寿橙:《浙、闽、赣、粤等省的香菇发展史(三)》,《食药用菌》2011年第5期,第53页。指菇民砍木季节,“密斫之”指菇民在伐倒的菇木上进行砍花栽培。古代的“永嘉郡”曾包括今温州丽水及福建江西的一部分。当年龙泉、庆元、景宁均属于永嘉郡管辖,此为最早记载菇民外出从事香菇种植的文字。宋嘉定二年(1209),龙泉人何澹所著《龙泉县志》对香菇的砍花栽培,留下了185字的叙述:“香蕈,唯深山至阴处有之。其法,用干木心,橄榄木,名蕈樯,先从深山下砍倒仆地,用斧斑驳锉木皮上,候淹湿,经二年始间出。至第三年,蕈乃遍出。每经立春,地气发泄,雷雨震动,则交出木上,始采取,以打篾穿挂,焙干。至秋冬之交,再用偏木敲击,其蕈间出,名曰惊蕈。惟经雨则出多,所制亦如春法,但不如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少者,香味具胜。又有一种适当清明向日处出小蕈,就木上自干,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晒干,同谓之日蕈,香味尤佳。”①张寿橙:《惊蕈录考》(连载),《中国食用菌》1988年第3期,第23页。因当地山高水冷,土地贫瘠,严重缺粮,所以在农闲季节外出伐木种菇、食粮于外,成为既解决粮荒又能赚钱的好办法,遂逐渐形成菇民区。据1948年庆元县长陈国钧《菇民研究》中的统计,“清乾隆年间三县菇民达15万人”②陈国钧:《菇民研究》,庆元博物馆藏本。。
2.菇民宗教信仰发展史
三县现存最早的五显庙遗址为建于唐代的查田值壁殿,由此可推断菇民宗教信仰形成于唐之前。菇民对神的虔诚心理之形成,在于对香菇作为一种真菌的特殊生产规律理解模糊。与普通农作物的生产方式不同,香菇无须播种,也不会开花,突兀地自树皮内长出;它承受着自然界的风霜雨雪,又那么敏感。风调雨顺时,不仅他们亲手完成砍花作业的菇树密如鱼鳞地重叠长出香菇,竟连无心栽培的死树也出了菇。而当天气干燥、气候恶劣时,则只能祈求神祇。况且,香菇种植在深山中,菇民在远离人烟的野外生存和劳作,疾病突然来临、没有医生可找、猛兽随时可能出没、气候无法预知、产量和价格不可预测……总之,生命和利润都处于一种比平常生活更不可预知的状态。这种不可知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菇民期待以某种方式将愿望发展为现实,只好寄希望于苍茫中的神祇保佑。
菇民宗教信仰作为菇民群体的特有现象,一直以来保持高度神秘性。古代菇民普遍认为香菇栽培为神授之技,对于种菇技艺向来讳莫如深,为防止信息泄露,甚至创造了专门的菇山用语“山寮白”,以及专司审判的菇民机构“菇帮共厅”。史料中关于菇民生产生活的记载已是吉光片羽,更不必提埋藏在这“神秘部落”背后的宗教信仰了。笔者通过对各地菇神庙的实地考察,结合对菇民的采访,分析了菇民代代相传的传说故事,并借鉴了张寿橙教授“约束菇民”与李天民教授“火神崇拜”的观点,认为菇民宗教信仰是一种集自然崇拜、发展生产、信息保密为一体,宣扬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
(二)神祇的多元性
菇民宗教信仰正是源于古代菇民对神秘力量的尊崇与敬畏,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火神崇拜,火作为一种自然力,在原始社会被当作一种神秘力量,为人类所不解和恐惧。原始人在万物有灵的认知下,以各种形式对其崇拜,以祈求自然的恩赐与宽恕,当人类学会支配火时,对火的崇拜便不再局限于崇拜自然火,而是将火人格化。①胡宁:《中原火神信仰与地方社会》,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3年。香菇生产需要火焰焙干,菇山作业离不开火,同所有用到火的行业一样,火神是菇民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神明。菇民信奉的火神名为“五显灵官”,即“五显大帝”,这是我国南方农村供奉最为广泛的神道,而非菇民之独有。据称,其有兄弟五人,唐末即有香火,宋徽宗年间赐庙曰“灵顺”,宋代由庚加封至王,因其封号第一字为显,故称五显公。菇民敬奉之原因是其统领诸路神道,传扬香菇生产技术,保佑菇民四季吉利、丰衣足食。②张寿臣:《中国香菇栽培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佛教称其为“华光天王佛”,道教尊为“五显灵观大帝”,是佛、道共同承认的守护神,又因其手捧三角金砖,在民间也被奉为财神。
菇民信奉的另一位神明“吴三公”,是南宋庆元县百山祖乡龙岩村人,因其在家族中排行老三,后人敬称“吴三公”。明万历三年,皇帝又敕封其为“判府相公”,从祀于龙泉凤阳山五显庙。有人认为他是香菇人工栽培技术“砍花法”的创始人,但据菇民传说和相关资料考证,他仅仅是一位道士,教授了菇民捕捉野兽和镇邪的本领,又发明了“惊蕈”的手段(一种通过拍打菇木促进菌类生长的方法),对菇民的生活生产有功,值得菇民敬奉。
菇民信奉的第三位神祇刘伯温即明代的开国大臣刘基。据1924年叶耀庭的《菇业备要》记载:“朱元璋求雨茹素,苦无下箸之物,刘伯温以菇进献,太祖嗜之喜甚,论理令每岁制备若干菇。”刘伯温系处州青田人,顾念龙泉、庆元、景宁田少山多,乘间奏请“以种菇为三县之专利”①叶耀庭:《菇业备要》,庆元博物馆藏本。。此事三县县志均有记载,比较可信。三县菇民因刘伯温而得到皇权庇佑,外地人都因敬畏皇权不敢从事或破坏香菇栽培。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菇业因在政治上获得皇权和官方人士支持,走向鼎盛期。三县种菇的专利得到皇权的保护,自明初到民国政权结束,为期600余年,成为中国最早有皇权保护的农业专利,菇民为了感恩将刘国师尊为神供奉。
菇民信仰的神明中既有从属佛道,集火神、财神、守护神为一体的五显大帝;又有修习道术,改良种菇方法,教人狩猎的吴三公;更有体恤百姓,将菇业发扬光大的宰相刘伯温,可见菇民宗教信仰并非独门传承,其发展经历了佛道与俗世权力的熏染,是一种宣扬实用主义的衍生宗教信仰。
(三)分布的广泛性
从地理与气象学上可知,海拔显著影响着降水、气温、湿度和光照,关系到植物的分布与植被的类型。1000米以上,许多农作物难以生长;1500米以上,即便是常绿阔叶林也难以生长。龙泉、庆元、景宁三县交会之地位于浙西南大山深处,在以凤阳山和百山祖为核心的区域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站在江浙第一高峰黄毛尖(1929米)放眼望去,但见奇峰突兀,云遮雾绕着几亩山垅梯田,极少一片平地。历史上这里分龙南、屏南两个区,海拔分别达到1087米和1114米,无霜期仅187天,农耕条件非常艰苦。山垅田人均不过半亩,亩产不过百斤,粮食匮乏。加之这里山高水冷,雾寒风烈,土地贫瘠,一年一季的水稻也只能靠天气好收些许粮食,冬、春两季也只有少许马铃薯生产。几百年来,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辣椒当油炒,火篾当灯草,火笼当棉袄,糠菜半年粮,讨饭去菇山!”龙泉、庆元、景宁三县地域达到5000多平方公里,森林蓄积大,但适合香菇种植的阔叶树面积并不大,而低海拔、适宜香菇生产的林地更少。低海拔的林地租赁为菇场的价格并不便宜,再加上本县菇场难以隐藏香菇,易被偷盗。而香菇种植所需菇山面积又比较大,远远不能满足众多菇民的实际需求。人多地少,田间的年成无以为继,山民不得不求生存他法,远走他乡种菇成为为数不多的选择。又因南方其他省的粮食比较充裕,能就地度过饥荒的冬、春两季,于是做这门营生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菇民区。
菇民远走异乡,与当地山主签订租用协议,菇民称为“判山”(一种不能用度量衡估值的有条件买卖、租用形式)。“判山”合同注明了菇民租赁山地所需缴纳的报酬,明确禁止菇民滥砍滥伐。香菇收益事关菇民生存,森林的存在也就是菇民自身的存在,因此怜惜资源、培植资源、爱护资源,早已是菇民的自觉行为。几千年来,菇民总结出一套可持续的采伐理论,即利用休眠期伐木,采取先剔桠后砍伐的手段对南方山区菇场林木资源进行轮换利用,既保护了当地林业,又保证了香菇的品质。特别是朱皇封赐种菇专利以后,菇业生产得到皇权庇护,三县从事菇业的人口不断增多。同时扩大的是对菇场的需求,为保证林业资源有序发展,菇民不断奔赴更远的省份开辟新菇场。西至云南丽江大理、四川南江、贵州凯里、广西融水,中到湖北荆门、湖南会同、安徽祁门,东到江西瑶里、浙江丽水、广东韶关、福建福州甚至台湾全省历史上都是香菇产区。
菇民部落的迁徙,间接带动了菇民宗教信仰的传播。有菇民的地方,菇神庙遍地开花,它不仅是菇民祈神求福、寄寓乡愁的场所,也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和尊崇。以江西瑶里五显庙为例,该庙的存在昭示了菇民宗教信仰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是菇民与当地百姓共同信仰的结晶。当地百姓敬佩菇民高超的种菇技巧,认定他们受到神明眷顾,将菇民说的菇山话“山寮白”称作“天上的语言”,并与菇民一道尊奉五显大帝。每有嫁娶,乡民甚至远涉深山邀菇民下山喝酒吃肉,并让菇民身配红花、持锯斧于迎亲队伍前开道,以期获得菇神保佑。
在闽粤地区还存在大量由菇民兴建的菇神庙,同治十一年(1872),《景宁县志》记载:“旧志云(指明嘉靖始修,完成于万历年间的第一本县志):乡民货香菇者,曩时皆于江右、粤、闽,今更远在川、陕、楚、襄间。”①《景宁县志》,龙泉图书馆藏本。足见菇民贸易范围扩大,更可依此推知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在清代之前菇业贸易就非常发达。乾隆年间(1736-1795),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菇民人数达到10余万人,其在福建开设菇行240余家。②张寿臣:《中国香菇栽培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一部分菇民借助经营菇行,在沿海地区参与各大口岸经销,成为资本雄厚的商人。一方面,他们是虔诚的宗教信仰信徒,在发家致富后无不感恩神灵的保佑,在香菇集散地兴建神庙符合宗教信仰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五显大帝本就是客家信奉的神灵,在闽粤等客家地区建设五显庙,当地百姓不会有抵触情绪,反而皆去帮助规划,贡献香火。同宗同源的宗教观,直接推动了菇民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丰富了菇民宗教信仰内涵,提升了两地文化的包容性。时至今日,五显文化作为游子精神联系的纽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当时,五显文化既发挥着团结菇民的作用,又间接调和异地矛盾,方便菇民在外省立足。
(四)神庙的多样性
秋去春归的候鸟式生活,彻底改变了菇民部落的年节习俗,也深刻影响了菇神庙的形式。它们中的一部分随着菇乡游子的迁徙落地生根,成为深山菇寮的一处神坛---菇山神坛为菇民上山时在菇寮里供奉菇神的场所。此类神坛大多建于菇寮中,神像以木头雕刻或泥塑成,长20-30厘米,由一寮之主从家乡带出。①张寿臣:《中国香菇栽培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村落神殿是明清以来广泛建造在菇民聚居区大大小小的吴三公殿,每个殿40—50平方米,也有的仅有2—3平方米,其中供奉的神像,大多为五显灵官,木雕、泥塑均有。这类神殿供菇民下山返村或离家外出时祭祀用,香火兴旺。“文革”期间,此类神殿基本上被扫光,有的改为工房或灰铺,有的因不许祭祀、缺乏维修而损毁。但在“文革”暗自保存殿内神像的菇民也大有人在。②同①,第45页。
此外,还存在由三县菇民合资兴建的大型神庙,他们多位于三县交会的风水宝地,是举行庙会庆典、菇帮商议菇业大计的重要场所。如龙泉凤阳山神庙,建于乾隆年间,由三县菇民集资建成,坐落于江浙两省最高峰黄茅尖山凹处,与吴三公诞生地龙岩村毗邻,为三县菇民区之正中心。神庙雕龙画凤,碧瓦飞甍,不单规模宏大,更匠心独具地将戏台搭于庙堂,这在中国的宗教信仰史上是一次创举,菇民朴素的宗教信仰观念认为神格与人格存在共性,不光人喜欢看戏,神也喜欢看戏,菇民如此大张旗鼓地举办庙会乃是希冀平日高高在上的神灵,也能放下身段与民同乐。
(五)传说故事的类型性
关于菇业主神五显大帝的传说故事在中华大地广泛流传,五显大帝作为神祇的历史已不可具体考评。传说他诞生于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557年),第一世是释迦牟尼如来佛祖的法堂前的一盏莲花油灯,每日煌煌听经问法,灯花堆积日久,经释迦牟尼如来佛祖为其做法,化成人身,名妙吉祥诞生。第二世:以五通火光,自半空中,飘飘而下,投胎到马耳山马氏金母身上,生下一子,脸有三眼,取名三眼华光天王,马子贞。第三世:再投胎出生于斗梓宫赤鬚炎玄天王之家,脸上有三眼,左手掌上有一个“灵”字,右手掌上有一字“耀”,取名为三眼华光天王,灵耀。第四世:“五通”共化为一胞胎,一粒肉球,在中界南京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九月二十八日子时投胎转世,剖开肉球现五兄弟,其排行第五大帝萧显德,就是世所崇敬之五显大帝。①[明]余象斗:《南游记》,云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明代福建人余象斗写有一部小说《南游记》,又名《华光传》,即《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写的就是五显大帝的故事。基于此,笔者共收集到三个与菇业相关的传说。
一是祈求大帝保佑,免除火灾,造福于民。在古代汉族传说中,华光大帝是火神,有三只眼,故又称三眼华光。菇民在菇业生产中需要用火来焙干,菇民在菇山作业时所居住的“菇寮”,结构简陋,极容易诱发火灾,况且菇民的生产生活处处用到火,理应对火神极度敬畏,为其盖庙塑像,香火朝拜,符合宗教信仰发展规律。
二是根据浙江菇帮所在地龙泉、庆元、景宁菇民的传说,香菇的人工种植技术创始人为春秋周灵王时期的商人五显。据说他做生意事业亨通,财运“像火把一样旺”,想做一桩亏本的买卖也不成!他即使是反季节地冬天卖凉扇、夏天卖火笼也因天气骤变而赚钱。于是,无可奈何之下,他买来树木伐倒,砍上花纹,扔在山里腐烂,心想这次总能亏本,没料到漫山长满香菇!加之其身怀三角金砖,为菇民求子求财无所不灵。所以,不仅是菇民尊他为菇业始祖,我国许多地方也把五显大帝奉为财神。
三是五显大帝作为汉族客家信奉的守护神,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五显”又称“五通”,“五通”常以“蛇”的姿态显形。家蛇能捕鼠,具有猫的作用,但不需饲养,也不像猫那样“偷食”而产生邻里纠纷。菇民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1省种植香菇,从而“入乡随俗”信奉五显大帝,朝拜“师傅柜”祈求守护,顺理成章。传说菇民回浙江时其山寮无人留守,但本地的乡人不会靠近,是因为菇民离开时做过法,留有蛇镇守。菇民身回家乡,心仍牵挂菇山寮房,所以除把蛇留在菇寮镇守外,还把那个菇民山寮中共同的五显神祇迎回家乡供奉,成为菇民的精神纽带和支柱。在汉族客家民俗中,他是由神到人、又由人到神的神灵。传说玉皇大帝封其为“玉封佛中上善王显头官大帝”,并永镇中界,从此万民景仰,求男生男,求女得女,经商者外出获利,读书者金榜题名,农耕者五谷丰登,有求必应。
二、菇民宗教信仰的差异化表现
走访龙泉、庆元、景宁、瑶里等地,综合对各地菇神信仰、菇神庙研究,笔者发现,从神庙的形式划分,菇民宗教信仰分为三类:一类是契约化的,即菇民利用合同确定生产协作关系,通过菇山神坛的形式建立合作纽带;一类是组织化的,即由全体菇民的共同组织“菇帮”修建的大型神庙;还有一类是非组织化的,即信仰活动存在的个体化状态,菇民自发建设的村落神殿。三者都是通过神灵信仰,祈求神灵保佑平安。不同点在于:一是前两者注重成员之间的沟通,后者注重与神灵沟通;二是前两种组织善于挖掘宗教信仰的实用价值,将神权与人权结合,后者表现为纯粹的神灵崇拜;三是前两者注重宗教信仰仪式,成员间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后者表现为自发的个人信仰,通过祭祀来保佑事业顺利、家人安康,祭祀形式也更为简单。笔者选取江西瑶里、浙江龙泉两地为考察对象,分别描述契约化、组织化、非组织化三类信仰模式对菇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契约化信仰——以瑶里菇山神坛为例
瑶里镇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地处皖、赣两省和安徽祁门、休宁,江西婺源、浮梁四县交界处,瑶里地形多为海拔600—900米的山地,全镇森林覆盖率高达94%,气候温润,雨量充沛,自古便是栽培香菇的优良菇场。
菇民上山前,由同村或亲朋好友5—7人结成一伙,彼此以伙计称,在山上搭建一两个菇寮。每一伙实为一个核算单位,入伙人各自参股。①张寿臣:《中国香菇栽培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每个菇场会专设0.5股,名曰“大帝爷股”,包挣不包亏,其他的股份由集体协调分配。“大帝爷股”乃是维持菇庙日常开支的经费,菇民朴素的宗教信仰观认为,神来参股必然保佑风调雨顺、财运亨通。此外,采取股份制能让账目清楚,出于对神的敬畏,菇民不敢在账面上动歪脑筋。无本钱而有技艺之菇民则以雇工身份参加,取得工钱而不参与分红。
菇民上山后,会使用柴刀、锯斧等工具搭建一座安全结实的菇寮。菇寮建好后,便由众人推举的祭祀师傅于寮外不远处磊一方山魈位,于寮内设神坛安放随身携带的神像。在菇山劳动时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要虔诚祭拜。神位设在菇寮中央,面朝东方门口处,神坛左右及上方要张贴对联长条,长条内容大致为:赐封五显灵官大帝之神位。菇山香火榜之神佛排列,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菇民大体一致,但亦有所差别。正中长条亦有写:南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玄天真武大帝之神位,但均写有吴三公与刘伯温。此类菇寮门口一般尚有对联及横幅。对联大多用:“闹天京英雄第一,震地府孝义无双。”横幅为“威震南天”,或对联为“菇乃良材生百宝,菇神坐镇授神术”“蓬在青山重重进,厂放香菇叠叠生”等。②同①,第55页。
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③[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菇民作为外乡人到中国南方十一省从事香菇种植和销售,往往有“强龙”与“地头蛇”之虞。菇民为了生产经营中的顺利和安全,除了习武强身、加强防范,还创造了信息传递过程中自己的独特暗语“山寮白”——“山寮”即种菇人居住的草房,“白”即语言。
按照宗教信仰规定,菇民一旦进入菇山便不能再说方言,必须统一使用菇山用语“山寮白”,这不是一种完整的语言,因为它并没有文字,读音也与三县方言迥异。据语言学家分析,这类语言脱胎于特定时期的方言用语,该语言很可能是前秦时期的南方方言遗存,为早期菇山作业统一用语。与此相呼应的菇民传说似乎也能印证这种说法,传说五显为周灵王时期人,香菇栽培技术是他的家族专利,秦征百越后,当地贵族式微,有帮工将香菇技术透露出来。为避免技术泄露,菇民约定使用特殊语言传播,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农业领域唯一的专类用语。
菇民的香菇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在大山的自然环境中种植香菇也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偶然性。香菇种植作为经济活动,如租场地建立种植基地、产品转移运输活动、香菇价格变化、生产和生活物资采购等等,生产活动如不同时段的劳作内容和技术术语,其经济和技术信息需要保密,所以有一套内部交流的信息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宗教信仰还同时禁止菇民起床至上工的这段时间说话,据说是怕惊扰山林的神鬼。按现代观点看,清晨起床为一天中最慵懒的时段,这种做法旨在避免菇民闲聊影响效率,能够帮助菇民快速投入生产。此外,宗教信仰还规定宅眷不能上菇山,不能单独走夜路,甚至对服饰的穿戴、吹奏的乐器都有硬性要求。农历每月初一、十四于菇寮举行祭祀活动,称为“过旦”。“过旦”由菇民推举的祭司主持,被选为祭司的菇民这一天不必上工,安心筹备夜晚的“过旦”仪式。到了晚饭时间,众菇民虔诚端坐于餐桌四周,只见桌上摆满了可口的山蔬野味,吉时一到便由祭司念祷告文,举行酬神仪式,内容多为感激神灵庇佑,祝福风调雨顺的话语。这一天,所有菇山禁忌全消,允许菇民喝酒吃肉,吹拉弹唱。菇山神坛的设置,体现了菇民坚定的宗教信仰,菇民信奉的教条确能保证菇山作业的有序化、高效化,同时兼顾了集体利益。
(二)组织化信仰——以浙江龙泉凤阳庙为例
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浙、闽、赣边界,是浙江省入江西、福建的主要通道,素有“瓯婺八闽通衢”“译马要道,商旅咽喉”之称,历来为浙、闽、赣毗邻地区商贸重镇。
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菇民宗教信仰的组织化形态,主要通过菇帮体现。菇帮的成员是龙泉、庆元、景宁三县所有从事香菇生产的菇民,人数最多时达数十万众。从事一种职业的人要结成一个有组织体系的帮派,首先是成员间对外有共同的利益关系,菇民在南方诸省山区种菇行走,免不了遭遇山贼劫匪,为抵抗外界力量侵犯,小到一个乡,大到几个县,小到几十人,大到几千人的菇民结成一帮互相照应,形成了菇帮早期雏形。
中国菇民千百年来一直分散在偏远的深山密林中作业,没有一个朝代的官府能将他们妥善地组织起来,给他们以物质和精神的援助;同时,以孢子繁殖为核心的砍花法栽培香菇是一种极度分散的、带有很大风险和人身危险的项目,而更多贫苦菇民缺少文化知识,离开了群体,他们将更加艰难,依靠至高无上的神权殿堂以协调和维护自身利益,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当外出人数增加、各种矛盾显现后,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来总体协调,同时又要极力避免他人染指利益,利用宗教信仰组织菇帮成了菇民最好的选择。于是,龙泉、庆元、景宁三县交界的凤阳山周边十八方村镇菇民,筹建了凤阳山五显庙,一方面供奉菇民信仰,一方面团结菇民,协调帮派秩序。
凤阳山神庙坐落于三县交界处。菇民信奉的五显大帝为五显大帝四世化身萧家兄弟五人,凤阳庙大殿正中五位天神依次列坐,敬受菇民的朝拜香火,与其正对的是一座戏台。庙堂左侧供奉的是土地公,右侧供奉的则是两位深受菇民爱戴的历史人物——吴三公、刘伯温。顺着右侧大门而出,则是一处偏殿——观音堂。大殿左侧设十八间厢房,供十八方村民歇息。每年农历七月初一到初七,十八方村镇菇民尽数聚于凤阳山庙庆贺,由于山高路远,沿途人烟稀少,进山男女便搭棚吃住于山上,为进山菇民服务的小食店绵延数里,不下百余处。祭拜高潮时,庙内庙外人群如潮,鼓乐喧天,夜晚烛光点点,构成一幅密林深处特有的画卷。①张寿臣:《中国香菇栽培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1.庙戏
菇民世代在深山作业,不少菇民自七八岁开始随长辈远涉异乡,在菇场生活,年年如此,竟不知世间春节与元宵。②同①,第63页。因此,每年的菇神庙会便成了菇民演习作乐的大好时机。所以,大凡菇神庙都有一个十分精致的戏台。而在庙会期间,戏曲表演更是彻夜不停,连唱七天七夜大戏是凤阳山庙会的特色与传统。
2.检查镇庙之宝
各大型菇庙都备有镇庙之宝,他们或被藏于庙内,或匿于指定菇民家中,在凤阳山庙会期间,这些珍宝需交付菇帮领袖检查。镇庙之宝或为金银玉器,或为稀世古玩。笔者研究分析认为,镇庙之宝的产生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为灾年做准备,菇民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培养了菇民的危机意识,若遇到灾年,菇帮可将宝物变卖,帮菇民渡过难关;二是菇民久居深山,与俗世社会交集有限,加上技术保密需要,菇帮更愿意将部分财富寄存于菇庙而不是银商票号;三是菇帮领袖长期外出带领菇民种菇,财富寄存于菇帮大本营中既能防备遗失,亦能通过神权来约束人心贪念。
3.菇帮会议
庙会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联络三县菇帮首领,菇帮凤阳庙议事是在庙堂神权下建立的菇民权力机构,用以处理日常纠纷事务。各县另设分支机构,比如景宁英川庙设有“三合堂”和“菇帮共厅”,用以处理本县菇民事务。涉及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菇业发展重大事宜,则在一年一度的凤阳山庙会时由三县菇帮领袖共同商议,以维护菇民利益和菇业生产秩序。此外,还负责对菇民纠纷做出调解,对严重违禁行为给予制裁,等等。如1924年龙泉菇民叶耀庭《菇业备要》出版,有人认为属于严重泄密,反映到菇帮。后经菇帮领袖审议,认为此书泄露部分种菇知识,但未泄露菇山暗语及砍花法口诀等核心技术。于是,庙会决定罚叶氏在菇神面前跪三日,罚金五十大洋,外加收回已刊印书籍,全部烧毁;处罚承印者龙泉印刷厂做庙戏三天。当时回收书本的力度很大,因此《菇业备要》存世极少。而类似菇民权益受损的案例常发生于全国各地的菇场,衙门是无法干预审判的。因此,菇民在“三合堂”内做出的审判,自然亦获得官方认可。所以,菇民领袖一般与地方官吏均有密切联系,无形中亦成为社会统治的一种辅助手段,相对地保持了菇业的稳定。至于其对菇业的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因为这些菇民领袖人物大都为菇民中的富裕阶层,对占菇民人数80%以上的贫穷阶层,不可能做过多考虑。最为明显的,是所有菇业史料都未见规定占菇民人数最多的雇工的基本权益,也未对雇主侵犯雇工利益的行为做出有力裁决,但其终不失为中国菇业发展史上一种利于行业规范的有效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菇帮上层的领袖人物的士绅,大都受到冲击,“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虽然菇民生产经营活动尚在,但当时菇帮组织机构瓦解消亡,凤阳山庙也被毁坏。改革开放以后,菇民们重操旧业外出种菇,凤阳山庙在菇民们的努力之下重修,但菇帮没有重新组织,庙会活动靠香客捐助得以延续。
(三)非组织化信仰——以龙南乡安和庙为例
龙南乡,位于浙江省龙泉市东南部,面积212平方公里,辖33个行政村、98个自然村,由建龙、建兴、义和、龙南4个管理区组成,2014年人口21742人,工农业总产值5505万元,人均收入1551元。辖蛟垟、麻竹坑、上田、安和等33个行政村。西南有凤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龙南乡安和庙祭祀作为民间信仰活动,主要集中在农历六七月举行。以2014年7月20日(农历六月廿四)在安河村举行的祭祀为例,此时菇民均从菇山归来,人力、物力较为充足,具备举行祭祀的条件。菇神庙内供奉的神祇除了传统的五显大帝外,还供奉着大禹等传统农业领域神祇。这是由菇民半耕种、半种菇的生产习惯所决定的,菇民一方面希望菇神庇佑平安、香菇丰产,另一方面也渴望禹神保佑年年都能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
村社祭祀是一种非组织化的信仰,民众以个体的名义自发到菇神庙进行祭拜,祈福献礼。为避免菇民在“上头香”(民间习俗认为第一个上香的人能拔得头筹)上产生矛盾,一种约定俗成的“迎神礼”应运而生。这类迎神仪式在菇民区大小村落普遍存在,凡是举行“迎神礼”的家庭即获得第一个祭拜菇神的权力,这种权力每年以家庭为单位轮换以求公平。“迎神礼”的家庭当年必须准备一头猪,择吉日宰杀放血,是夜由家庭成员或帮工将整猪抬入神殿,其他人坐于庙堂听专司祭祀的长者诵读祈福祭文,吟唱神灵史诗,整个过程至天明方歇。其他村民在仪式后方可入神庙祈福,举行“迎神礼”的家庭还需烹饪祭祀猪肉,设宴款待全体村民,宴席通常持续三天以上。
三、菇民宗教信仰的社会功用
(一)支撑菇民精神的重要方式
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一到“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时,菇民就已成群结队地背井离乡。他们忍饥受饿,眠霜拥雪,匍匐于深山神坛,期盼神灵庇佑,靠信仰来维系与故土的一丝关联。而当菇民上山后,“菇区内家家户户人去屋空”“在原地被他们留下的一群老幼,境遇可怜,也有于此时散布各处,行乞于寒冽朔风,唯盼来年枫树抽芽,传来佳讯”①张寿臣:《中国香菇栽培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面对残酷的生活环境,菇民唯有将命运希冀于神灵救赎。菇民祭祀菇神,传诵菇神恩典,其本质是传达自己的心愿,希望菇神能帮助他们免除灾祸、平安顺利、财源滚滚。他们在贫苦环境下,于大大小小的山区村落间兴建庙宇,足见菇神信仰在菇民心中的地位。此外,菇民宗教信仰所延伸的庙会作为菇民年节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和载体,传递了菇民丰富的内心情感,每年一次的凤阳山庙会,成为菇民满足精神需求的平台。在庙会中,菇民可以祭祀菇神、品尝小吃、娱乐玩耍、观看表演等,这些活动为菇民的情感释放创造了条件。
(二)增强菇民认同感的重要手段
宗教信仰对菇民有增强认同感的作用。对菇民而言,宗教信仰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家积极参与祭祀活动,菇神就成为团结菇民的媒介。在深山菇场,菇民依靠一纸“大帝爷股”同菇神关联,于深山荒寮兴建神坛并严格遵循教条,以“过旦”的方式祭祀菇神。这种宗教信仰认同感帮助他们加强协作、减少矛盾、发展生产,集中力量防范山野强盗,打击偷菇贼。在下山之后,宗教信仰又促使他们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利益团体“菇帮”,以神的名义团结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菇民,合理分配资源利益,有效处理生产生活中出现的各类矛盾,行使世俗权力。也正是这种宗教信仰认同感,减少了人性贪婪的杂念。同时,庙会的举办、村落神殿的建设使妇孺也参与宗教信仰仪式,增强了家庭认同感,确保菇民上山后家庭的和睦稳定。
(三)对整合地方资源、保障菇民利益的重要作用
首先,菇民宗教信仰以及延伸的菇神庙是地方社会整合文化资源的重要媒介,庙会将信仰、贸易、美食与民间艺术相融合,将菇神信仰与香菇文化传播到各省份。其次,菇帮作为与菇民宗教信仰捆绑的权力机构,披着神灵的外衣,以神的名义行使裁判权,维护菇业稳定——菇帮掌控着香菇的定价权,严禁香菇贩售以次充好,菇民外出生产需向当地山林主“判山”,订立契约,菇帮提供基本合同范本。若合同交涉出现矛盾,往往需要菇帮出面协调,遇上特大事件,菇帮甚至能聚集上万菇民的力量。据龙泉文联主编的《龙泉》2009年第2期记载,清朝时期因菇业捐税过高,菇民无法生存,在菇民密集的江西发生了菇帮组织九千菇民大闹九江府的大事件,足见菇神信仰在维护菇民利益、协调菇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四、结 语
“信仰、思想和意见也始终表现于被改造的环境中。”①[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5—96页。换而言之,人类信仰的产生依赖于周围环境和生态,环境决定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影响人类的信仰、思想和意见。浙西南菇民的宗教信仰萌芽于菇民同恶劣环境的抗争中,伴生于菇民对香菇栽培技术的探索,又在菇民艰苦卓绝的候鸟式迁徙中逐步发展壮大,最终深远影响了菇民区乃至南方诸省香菇主产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沟通模式,衍生出多样的信仰形式。菇山神坛与大型神庙的产生源于一种文化迫力,即“一切社会团结、文化绵续和社区生存所必须满足的条件”②同①,第96—97页。。而村落神殿的形成可以说是个人动机的驱使,即“社区分子所自觉的直接而有意识行为上的冲动”③同①,第97页。。虽然形式有所差异,其本质均无法背离菇民朴素的宗教信仰思想。
任何习俗和信仰的形成发展,均受制于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居住、生产的自然环境深刻影响着菇民宗教信仰,独特的半农耕、半种菇模式决定了宗教信仰内涵的多样性。在南方11省菇场,菇神庙以合伙集体为单位建造,以缔结契约的形式分配利益,成员将菇神庙作为彼此互相信任、互帮互助的纽带,构成了一个相互团结、有共同诉求的生产团体。而菇民区既存在以个
体为单位、信众自发修建用来上香酬神的村落神庙;又存在以菇帮为单位、组织化修建的大型神庙。菇帮依靠神权媒介得到菇民拥护,宣示权力的正统性,最终作用于地方社会,对整合民众诉求、传播地方文化、促进菇业经济繁荣起到了巨大作用。
① 杨震山,浙江师范大学文学分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指导老师:毛竹生(1961-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