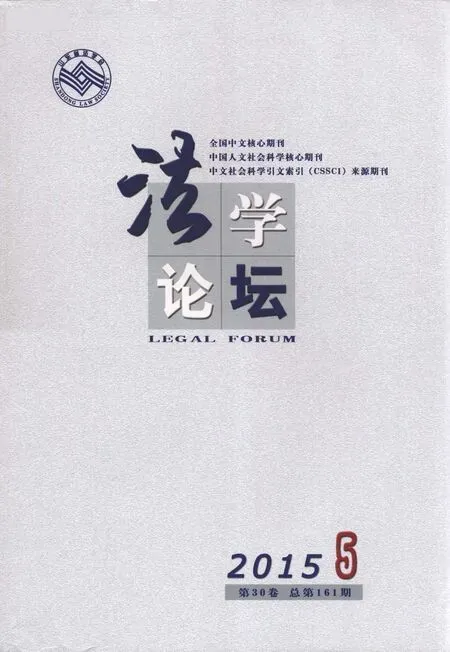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为视角
彭文华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为视角
彭文华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将危险驾驶行为予以入罪的必要性是相关的危险驾驶行为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行性是对相关的危险驾驶行为在认定与取证上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能确保其受到惩罚。《刑法修正案(九)》将“双超”入罪限定为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双超”的做法是欠妥的,不应将从事公路货运“双超”排除在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之外。将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予以入罪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但仍有空白之处。将毒驾、怒驾行为入罪不具有可行性,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范围不宜过于扩张。
危险驾驶;追逐竞驶;毒驾;怒驾
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完善刑法规定,已成为我国刑法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常态化、规律化特征。就历次的刑法修正案来看,扩大犯罪圈无疑是其典型特征之一,这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就刑法修正案扩大犯罪圈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二:一是降低犯罪的入罪门槛;二是增设犯罪的行为方式。前者是在不改变犯罪行为方式的情形下,将原本不构成犯罪的行为纳入犯罪圈;后者是在原有的行为方式之外,通过增设新的行为方式扩展犯罪圈。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圈,采用的就是上述第二种方式。现行《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是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机动车,《刑法修正案(九)》将其扩展为四种行为方式:追逐竞驶;醉酒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不难看出,后两种行为方式是新增设的内容。另外,《刑法修正案(九)》还明确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那么,如何评价《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罪的修改呢?本文将以危险驾驶罪增设以来的适用效果及其立法价值和功能等为视角,拟对《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加以深入分析。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罪修改的立法背景
危险驾驶罪本为《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罪名,其所确立的两种行为方式有其特定的立法背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辆数量和驾驶员人数猛增,无视交通管理法律法规,酒后乃至醉酒驾车的违法犯罪也日益增多,给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在醉酒驾驶层出不穷的同时,“飙车开始在国内一些特大城市出现。一些人将汽车作为宣泄的工具,将道路作为嬉戏的场所,追逐竞驶,严重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0页。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是将频繁出现的醉酒驾驶与追逐竞驶入罪的决定性因素。应当说,《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罪新增的行为方式,即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以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也不外乎于此。
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通常被称为“双超”,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违反公共交通管理制度的行为。在我国,“仅 2011年,因超载超限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就达91811 起,造成25864人死亡,106370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4.4亿元。”*余秋莉:《超限超载入刑的理由与路径》,载《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正是由于超限超载频发,社会危害性严重,不少省市纷纷出台规制措施以期惩治这类行为。例如《安徽省治理货物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30条规定,未经批准驾驶车货总重超过75吨或者车货总重超过规定标准100%的货运车辆的,由公路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进行相应的处罚。2012年 7月22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研究推动将严重超限超载行为入罪,以便追究驾驶人的刑事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双超”入罪在情理之中。
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同样如此。受危险化学品的特性所决定,运输危险化学品一旦发生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与“双超”相比有可能要严重得多。虽然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不是运输危险化学品造成事故的唯一原因,但显然是主要原因。例如,有学者经过对所收集的64起泄漏事故加以研究发现,运输车辆和装载体不合格是主要原因。*参见张炎:《浅论危险化学品运输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对于如何规制这类行为,有学者认为应从以下四方面入手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源头的安全管理:一是强化车驾源头常态化监管;二是强化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社会知晓率;三是强化路面检查管控不放松;四是建立全国性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车辆及从业人员的信息互动平台,为危险化学品运输及管理工作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参见张景晖:《让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转“危”为安》,载《道路交通管理》 2014年第2期。为了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肇事行为的惩治,制裁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显然是必要的。2014年9月16日,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六部门联合制定了《集中整治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旨在严厉打击该类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将相关行为纳入犯罪之列,正是其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以及频发的现状使然。
由上可知,《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以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的。这些类型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且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十分严重,在其他法律制裁不足以有效遏制这些种类的行为后,动用刑罚是不得已的选择。
二、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危险驾驶行为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点是学界公认的。但是,关于其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究竟是何种状况,换句话说,其入罪的必要性究竟是什么,在学界则存在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当行为人在有车辆与行人的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时,他就制造了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撞击车辆和行人。正因为行为人是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才说他制造了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因为在行为人正在驾驶的道路上总是可能出现其它车辆与行人。”*冯军:《论〈刑法〉第133条之1的规范目的及其适用》,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抽象危险与具体危险的范围,因而会导致处罚过于膨胀和严厉。如果行为人在醉酒驾驶的整个过程中,没有车辆和行人出现(当然,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形极为罕见),就不应当认为有抽象危险;只要在此过程中有车辆和行人,就应当认定具有抽象危险。*参见张明楷:《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6期。不难看出,这两种观点尽管存在争议,但均认为对危险驾驶是否造成抽象危险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均肯定危险驾驶会造成抽象危险。只不过,第一种观点认为道路上无车辆和行人时,则危险驾驶造成了抽象危险,否则就造成了具体危险。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只有道路上有车辆和行人,危险驾驶才会造成抽象危险。还有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区分应以实体性的危险程度为标准,前者只要实施了类型化的行为即视为存在危险并构成犯罪,后者还要求给具体的规范保护对象造成现实紧迫危险。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抽象的危险犯,前者存在被允许的危险,其违法性低于后者。”*张克文:《也论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张明楷两位教授商榷》,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这种观点则将危险驾驶作为类型化行为,并认为当然会造成抽象危险,只是在违法性上低于以危险方法造成的抽象危险。笔者赞成此种观点。
抽象危险是一种观念的、概括的危险,其与具体危险的现实性与具体性存在明显不同。例如,非法持有枪支具有抽象危险,但这种危险只是对公共安全的一种观念的、概括的危险,并不是说一经非法持有枪支就会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具体的危险。既然如此,那么发生在公共交通道路上的危险驾驶,所造成的就只能是抽象危险,因为这种危险主要是观念上的、概括的。也就是说,只要在公共交通道路上危险驾驶,就会对公共安全产生观念上、抽象的危险。否则,就无法解释《刑法》为什么将该类行为限定在公共道路上,而不包括非公共交通道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意味着,不是用于公众通行的非公共道路,不属于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因此,在非公共道路上危险驾驶的,不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只要是在公共交通道路上危险驾驶,就应当认为造成了抽象危险,与道路上有没有车辆和行人无关。只要有驾驶常识的人都知道,公共道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只是即时的概念,并不排除随时出现车辆和行人。*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例如在珠三角一些城市,夜生活的习惯使得凌晨驾驶车辆出没十分常见。而凌晨的道路往往难见车辆和行人,司机开车往往速度较快,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在司机看来,几乎没有车辆和行人的路况容易使其驾车飞驶,而公共交通道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只是暂时的,事实上随时都会有车辆和行人意想不到地出现,从而酿成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假如公共道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也只是一时的,出现车辆和行为则是随时的,这意味着公共道路上出现车辆和行人有时具有不特定性,而这正是公共安全的典型特征。因此,无论公共交通道路上有无车辆和行人,都应当承认存在公共安全,只要危险驾驶就应当认定造成了抽象危险。
正是由于在公共交通道路上危险驾驶会造成抽象危险,为危险驾驶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提供了现实根据。当某类危险驾驶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时,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概率就会上升,从而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和不良影响。为了防患于未然,将危险驾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消除在萌芽状态,就有必要将该类行为入罪,即使其只是一种单纯的行为而没有造成任何现实危害后果。这便是危险驾驶入罪的必要性。问题在于,在将行为入罪时不应当仅仅考虑惩罚的必要性,还必须考虑惩罚的可行性问题。如果某类行为虽然频发且危害严重,但是在运用刑罚加以制裁时,充满不确定或者难以有效查出事实或者获取证据等,导致存在惩罚上的不力与缺漏,乃至于不能有效惩治该类行为,那么,将这样的行为入罪,不但起不到预想的效果,还会严重损害刑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可谓得不偿失。醉酒驾驶与追逐竞驶就是很好的例证。醉酒驾驶与追逐竞驶均有入罪的必要性,但是在可行性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导致两者入罪后所产生的效果绝然不同。
尽管对醉酒驾驶入罪存在争议,但其入罪以来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却是有目共睹的。“据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醉驾入刑’3年来(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累计查处酒驾127.4万起,醉驾22.2万起,同比分别下降18.7%、42.7%。同时,依法对酒驾行为实施行政拘留1.1万人,暂扣驾驶证84.2万个,吊销驾驶证15.8万个,一次记满12分89.3万人。其中查处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酒驾并抄告纪检监察部门的达1400余人。”*张洋:《醉驾入刑有效果 法治入心显力量》,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0日。当然,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在我国不宜将单纯的醉酒驾车行为入罪,理由在于:“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全部等待和依赖于刑法典的修正,更为可行和负责任的方式是对刑法典进行与时俱进的扩张解释。因此,以‘增设罪名’、‘立法完善’作为学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普遍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推卸责任之嫌:一切责任均推之于立法,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均是等待立法的修正,而放弃了根据生效的现行法律如何去解决问题的思索。对于交通肇事罪也是如此,不能习惯于‘截弯取直’式的增设罪名,但是完全套用国外的立法模式也未必可取。”*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刑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载《法学》2009年第9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惩治酒驾的效果,关键在于执行的力度而不是严厉的方式,依靠行政制裁也能有效遏制醉酒驾驶。行政权重效率,司法权重公正,以刑罚方式惩治多发但危害不大的危险驾驶行为反而不利于遏制该种行为。*参见王政勋:《危险驾驶罪的理论错位与现实危险》,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进而有学者提出,通过对现有的行政法进行修改来惩治醉酒驾驶是一条重要途径,如提高醉酒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的罚款数额、在行政法的范围内可以规定相关的剥夺资格的行政性处罚措施、对危险驾驶者应当明文规定强制其学习的内容、增加与醉酒驾驶行为者有关的其他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等。*参见周详:《民生法治观下“危险驾驶”刑事立法的风险评估》,载《法学》2011年第2期。
上述第一种观点本质上并非否定醉酒驾驶入罪,而是认为通过立法修改的方式增设危险驾驶罪有所不妥。第二种观点则明确反对醉酒驾驶入罪,应当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司法实践中,通过其他方式如加大查处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即使不用刑罚也能起到遏制酒驾的作用。例如,从2009年8月5日开始,公安部对酒后驾车行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活动进行了为期 3个月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导致死亡人数降幅达33.3%,其中城市道路上酒后驾驶肇事导致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41.7%。*参见黄明儒、余运红:《醉驾入罪,就能管住醉驾吗?》,载《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24期。不过,在笔者看来,采取行政手段惩治醉酒驾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对于从事公务人员的处罚力度相对有限。以行政处罚的力度,往往不足以对公务人员形成真正的震慑力,这之中原因多种多样。事实上,在醉酒驾驶入罪之前,恰恰是采用行政处罚。上述试图修改行政处罚的种种措施,其实在实践中并非不存在,而是其效果在各种因素介入后变得无疑形同虚设。醉驾入罪后,由于犯罪关乎到公务人员的“饭碗”,其遏制效果十分明显。而对公务人员行为的遏制,向来在社会上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其对普通民众的示范与警示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对醉驾入罪的积极作用不应否认;二是醉驾入罪不仅仅是为了遏制该类行为,更主要的是改变人们长久以来的观念。我国的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今朝有酒今朝醉”可以说深入某些人的骨髓。而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显然需要重大的转变才有效,普通措施恐怕无能为力。对醉驾以犯罪论处,可以说教训足够深刻,能够起到基于重大变故改变观念的效果;三是,醉驾入罪在操作上简单、便捷,具有可行性。在司法实践中,对醉驾行为的查处,往往是在案发现场,采取的是酒精测试的方式,操作上具有及时性、便捷性等特征,司法成本低,获得证据容易,行为人也一般心服口服,效果极佳。相对来说,在运用行政制裁时,对危险驾驶者明文规定强制学习的内容,增加与醉酒驾驶行为者有关的其他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则操作起来复杂、繁复,成本会较高,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醉驾入罪还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刑事立法较为成功的个案之一。
与醉酒驾驶相比,追逐竞驶的认定则要难得多。有学者认为,追逐竞驶以具有抽象危险性的高速、超速驾驶为前提,单纯的高速驾驶或者超速驾驶,并不直接成立本罪。行为的基本方式是随意追逐、超越其他车辆,频繁并线、突然并线,或者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等。*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37页。有学者认为,“所谓追逐竞驶,就是平常所说的‘飙车’,具体包括在道路上进行汽车驾驶的‘计时赛’,或者若干车辆在同时行进当中相互追逐等,既包括超过限定时速的追逐竞驶,也包括没有超过限定时速的追逐竞驶。仅有一辆车在道路上狂奔的飙车行为,也包括在内。”*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77页。不难看出,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追逐竞驶是以特定对象为目标的追逐或者超越,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追逐竞驶即飙车,不需要针对特定目标加以追逐或者超越。还有学者认为“追逐”与“竞驶”含义不同,“当然从词义本身看‘追逐竞驶’,有相互展示、炫耀速度、技能之意,如只是单独一车,在行进中的高速行驶,或者在车辆行进中穿插行驶的,语意上不是‘追逐’,而只能是‘竞驶’。”*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从语义上看,“追逐”与“竞驶”强调的是“追”与“竞”,这是需要有一定的对象或者目标才能成就的。换句话说,如果是独自开车而超速行驶等,就没有“追”与“竞”,因而谈不上“追逐”与“竞驶”。此外,追逐竞驶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地步,才能以犯罪论处。如何认定为情节严重,追逐或者竞驶到何种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其界限并不容易把握。
追逐竞驶入罪不但存在认定难,而且取证也十分不容易。对醉酒驾驶由于采取拟制的量化标准,因而认定起来简洁、明确,不存在疑问与争议。追逐竞驶则不然,其取证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认定追逐竞驶的目的难。认定行为人具有追逐竞驶的目的,显然不能依赖于行为人的一面之词,而是需要有追逐竞驶的目标或者对象佐证,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取证工作。一方面,被追逐或者竞驶人不一定知道自己被他人追逐竞驶,另一方面,被追逐或者竞驶人通常很快驶离现场,难以查找、问询;二是追逐竞驶是一个行为,更是一个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形成与发展很难获取可资证明的客观依据;三是情节严重取证难。追逐竞驶的情节严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为人追逐或者竞驶的“度”。这个“度”包括追逐竞驶行为本身的程度以及相对于追逐竞驶目标或者对象的程度,而对此显然是不容易获取证据的。因此,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的发案率极低。其发案率不但与醉酒驾驶无法相提并论,就是与一般犯罪的发案率相比也相形见绌。有司法机关曾对2011年6月至2013年5月漳州市各基层人民法院共判处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858件 860人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所有的犯罪人之发案,皆源于醉酒驾驶,无一例系追逐竞驶。*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危险驾驶入刑的调研分析——以福建省漳州市十一个基层法院为视角》,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期。这倒不是说司法实践中鲜有追逐竞驶行为,因为那样的话刑法是不会将之入罪的。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该类行为认定、查处与取证难,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基本上差不多。如果刑法对入罪行为不能加以有效制裁, 那么刑法规定则形同虚设,这将无法发挥刑法的规范作用,严重影响刑法的权威与公正。对于这样的行为,与其入罪还不如不入罪。更何况,在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行为种类多样,无论是社会危害与影响,还是惩罚的可行性,追逐竞驶都不及某些行为。因此,将追逐竞驶入罪无疑是刑法立法的失败例证之一。追逐竞驶入罪的不成功表明,危险驾驶行为入罪除了考虑社会危害性外,还必须考虑认定与取证上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确保惩罚的可行性,应当成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决定因素之一。
谈到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必要性,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危险驾驶的行为性质。事实上,危险驾驶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某一驾驶行为是否对公共安全造成抽象危险,有时要取决于危险驾驶本身的危险性,这涉及到危险驾驶的行为性质。说到危险驾驶的“危险性”,有必要区分危险驾驶性质与危险驾驶的危害程度(在刑法理论上常被称为罪质与罪量)。以醉酒驾驶为例,对其罪质与罪量问题,在理论上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醉酒驾驶是严重的酒后驾驶行为,后者本是交通违法,前者是对‘醉酒’程度的严重交通违法犯罪化——此种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立法衔接关系表明,醉酒驾驶不能适用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同时作为抽象危险犯的醉酒驾驶,抽象危险的认定全凭行为,即达到 ‘醉酒’程度的‘酒后驾驶’行为就证明存在抽象危险,足以构成犯罪,至于其中的危险大小区别,至多影响量刑。”*夏勇:《作为情节犯的醉酒驾驶——兼议“醉驾是否一律构成犯罪”之争》,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9期。另一种观点认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王逸吟、殷泓:《醉驾入刑再考量》,载《光明日报》2011年5月15日。依据这两种不同理解,在定性上显然是不同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凡是醉酒驾驶一律构成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即使是醉酒驾驶也要考虑其他因素。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第一种观点将饮酒驾驶认定为驾驶行为,认为醉酒就是行为的危害程度,无疑是正确的。而第二种观点认为醉酒驾驶是否构成犯罪还应当考虑其他因素,也是合理的。但是,两种观点均存在缺陷与不足。第一种观点认为醉酒驾驶一律构成犯罪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而第二种观点将醉酒驾驶理解为特定行为,都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醉酒只是从饮酒的程度上为饮酒驾驶入罪确定了标准。问题在于,决定饮酒构成犯罪的情节,显然不能仅仅限定为醉酒,一切与饮酒驾驶有关的主客观因素,都可以成为影响饮酒驾驶入罪的因素。据此,醉酒驾驶是否构成犯罪,应当这样来认定:其一,如果醉酒驾驶且不存在其他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情节,那么醉酒驾驶应当一律认定为犯罪;其二,如果醉酒驾驶且存在其他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情节,那么醉酒驾驶就不应当一律认定为犯罪,特别是当存在其他足以降低醉酒驾驶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因素时,综合判断醉酒驾驶没有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就不宜认定为犯罪。
由上可知,在将行为入罪时是必须要考虑罪量要素的。一切与行为有关、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主客观因素,在决定行为入罪时均应予以考虑。任何纯粹根据行为之质入罪的观点,都是荒谬的。然而,理论上却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主流刑法思潮已经逐步摆脱了对犯罪进行实质评价的理论窠臼,转而从犯罪的形式定义出发研讨犯罪的含义,因此以‘社会危害性’的存在与否作为‘毒驾入刑’的正当化理由,至少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包涵:《论“毒驾入刑”的正当性诉求——兼议“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和取舍》,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言外之意,定罪可以不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只根据行为本身,这显然是对《刑法》规定(第13条)的曲解,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实不可取。即使是毒驾入罪,相信刑法也不可能将任何吸食毒品的行为人定为犯罪,否则必将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刑法评价
(一)“双超”行为的入罪评价
在司法实践中,“双超”既包括客运超限超载,也包括货运超限超载。对于“双超”,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目共睹,主要表现为:超限运输严重破坏公路设施;对公路桥梁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对执法人员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等等。*参见周鲁奇:《超限超载的危害及治理对策》,载《管理观察》2013年第20期。因此,对“双超”入罪应该不会引起太大争议。另外,依据现代技术对超过限定时速与超过规定标准搭载进行查处,通常不存在认定难与取证难的问题,因而“双超”入罪还是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的。
不过,《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双超”是指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的超限超载,不包括货运超限超载。这意味着,《刑法修正案(九)》侧重保护的是客运公共安全。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货运“双超”也会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公共安全,只不过这种公共安全不是源自货运本身,而是源自公共道路交通上。但是,其性质与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中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公共安全不存在任何区别。另一方面,就事故发生率及社会危害性来看,货运“双超”并不亚于客运“双超”,甚至通常超越后者。例如,“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2010年全国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占总量的32.0%和42.9%。其中,……7.0%的事故死亡人数系营运客车肇事导致,29.8%的事故死亡人数系一般货运车辆肇事导致。”*肖跃秀、张万安:《货车超限超载问题研究》,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可见,将公路货运“双超”排除在入罪之列,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事实上,不少省市甚至国务院也将一切超限超载行为均纳入专项规制,而并不限定于公路客运超限超载。例如,海南省相关制度规定:“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公路、公路桥梁和公路隧道行驶。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车辆确需超限行驶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超限运输许可。”*成军:《我省立法治理“超限超载”》,载《海南人大》2013年第12期。国务院办公厅2014年11月28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求加大对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车辆驾驶人、车辆所有人、运营管理者及货物托运人的处罚,研究推动将车辆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列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见:《国务院: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将追刑责》,载《专用汽车》2014年第12期。因此,《刑法修正案(九)》没有理由将公路货运“双超”排除在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之外。
(二)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入罪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包括生产储存安全、使用安全、经营安全、运输安全等。毫无疑问,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主要是指违反运输安全而言的。问题在于,受危险化学品的特性所决定,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所具有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危险,明显与醉酒驾驶、“双超”等不同。这是因为,醉酒驾驶、“双超”等所产生的危险源自行为本身,因而只有发生在公共交通道路上,才能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则不然。无论是发生在公共交通道路上还是非公共交通道路上,危险化学品都有可能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因此,在构成犯罪的要求上就可能不一样。例如,甲驾驶汽车长途旅行,晚餐时饮酒达到醉酒标准,如果白天驾驶不符合醉酒标准,就不能以危险驾驶罪论处。但是,根据《条例》第48条第2款的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途中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运输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换句话说,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即使没有驾驶行为,也要保证危险化学品的安全防范,否则将构成危险驾驶罪。于是,关于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是否要求在公共交通道路上进行,就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即使不在公共交通道路上进行也能危及公共安全,但由于危险驾驶罪主要规制的是危险驾驶行为所具有的危害公共安全特征,而不侧重运输对象的危害公共安全特性,因而,将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纳入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予以规制,也必须要求在公共交通道路上进行。不过,这样做的消极后果是,在非公共交通道路上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即使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也不能以犯罪论处。又由于危险物品肇事罪的成立要求发生严重后果,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要求方法的特定危险性,在非公共交通道路上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显然不可以这两罪中的任何一罪论处,于是,在非公共交通道路上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就游离于刑法规制之外,由此留下遗憾。
(三)毒驾的入罪评价
近年来,随着吸食毒品人群的不断增多,毒驾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浙江省公安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5月,浙江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12.4万人,其中近四分之一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参见孙建国:《“毒驾”入刑,势在必行》,载《吉林人大》2012年第11期。在司法实践中,毒驾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形时有发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例如,2010年5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居民傅某吸毒后驾车失控,连续撞飞多个摊位,撞伤17人;2010年7月26日,出租车司机陈某吸毒后,在北京西四环主路青塔路段连撞21辆机动车;2011年9月26日,四川省成都市居民杨某吸毒后闹市驾车,造成1死4伤的严重后果。*参见张蕾:《应尽快将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范畴》,载《道路交通管理》2012年第7期。在毒驾频繁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形下,不少人呼吁将毒驾入罪。“‘毒驾如同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危险驾驶行为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威胁着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破坏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应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参见林思婷:《危险驾驶罪的未尽之意——略论吸毒后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载《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10期。事实上,从毒驾入罪的必要性来看,并不亚于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等,因而在毒驾入罪的必要性上,似乎不存在太多争议。
当前,学界对毒驾是否入罪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可行性上。肯定者认为,毒驾入罪具有可行性,主要理由在于:一是毒驾与醉驾社会危害性相当;二是毒驾入罪顺乎民意;三是有境外立法可资借鉴。*参见颜河清:《“毒驾”入罪可行性探讨》,载《学理论》2013年第28期。这种观点与其说是阐述毒驾入罪的可行性,不如说是论述毒驾入罪的必要性。否定说则认为,毒驾行为入罪后,难以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认定。因为毒驾入刑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很多难题,例如毒驾入罪标准难以确定,毒驾的检测方式不精确、不平衡,检测技术不可靠,缺乏严谨的执法程序,倘若盲目将毒驾入刑势必会超过人权保障的边界。*参见李琳:《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标准之确定——以质疑“毒驾入刑”为视角之分析》,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2期。应当说,目前在毒驾入罪上存在一些操作上的难题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一点即使主张将毒驾入罪的学者也予以承认。“从案件处理的操作层面看,当时对毒驾的检测,在技术层面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容乐观的客观障碍和实践难题。据了解,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与禁毒机构此前并没有实现‘无缝对接’,道路驾驶的例行检查也缺乏及时、有效的涉毒检测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匆忙将毒驾而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纳入刑事追究程序并给予刑罚制裁,确实也会带来诸多的司法难题。可以这么说,毒驾没有入刑,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是刑事立法审慎原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立场,无可厚非。”*游伟:《“毒驾”入刑的呼声应当正视》,载《法制日报》2013年3月7日。肯定说意识到毒驾入罪在操作上的难题,主张对“毒驾入罪”另辟蹊径。“在‘毒驾入刑’的立法技术层面,应当坚持使用概括加列举式的立法,在立法理念上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思维,同时也不会破坏《刑法》法典的体系。而从技术上看,‘概括加列举式’的立法手段,既满足了当时对于醉驾入刑的立法目的,又给‘毒驾’或者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的入刑提供了解释渠道,且这一解释依循的是语言的普遍文义,只要在以后的立法中坚持将此后出现的危险行为与‘醉驾或毒驾’等量解释,就符合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扩大解释方法,不会触碰类推的底线。”*包涵:《刑法解释界限与行为犯罪化的矛盾与消解——以“毒驾入刑”的正当性与立法策略为切入》,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5期。但是,这种观点无疑在回避问题,并没有解决“毒驾”入罪后的具体操作问题,因而并无说服力。
笔者认为,尽管“毒驾”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由于在入罪的可行性上存在问题,因而在没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和经验作为保障的前提下,不宜将该类行为入罪。“毒驾”入罪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世界各国立法存在差异。在立法较为先进的发达国家,规制“毒驾”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起初是“基于效果”法或“损害性毒驾”法,尔后相继进入自证法时代,适用零容忍法成为趋势,即便如此,处罚违法者也存在采取刑罚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鉴于目前我国检测毒驾的技术并不成熟、均衡,难以有效解决定罪标准问题,而采取零容忍确实不符合《刑法》相关规定(如第13条“但书”规定)的精神,故在对毒驾尚存行政规制的情形下,将“毒驾”入罪是难以达到刑法目的,甚至可能引起诸多消极效果的,导致得不偿失。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并且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虽然司法解释在此将酒后与吸食毒品后相提并论,但不能据此以醉驾入罪推断毒驾应当入罪。醉酒不同于酒后,而是体现了饮酒的程度和状况,以之作为认定危险驾驶行为的依据和标准,体现了《刑法》对行为入罪的罪量要求。由于依据现有技术难以检测不同毒驾,因而无法像醉酒入罪那样确定不同的毒驾入罪的标准,故司法解释的规定恰恰表明毒驾入罪在现有的条件下是不可行的。
(四)“怒驾”的入罪评价
“怒驾”即怀着怨愤、恼怒情绪驾驶车辆的行为。在不良情绪的作用下,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很容易失控或者失常,乃至于违反交通规则,酿成事故。“怒驾”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源自成都被打女司机事件。*2015年5月3日下午,成都市三环路娇子立交桥附近发生一起打人事件。卢女士在驾车前往三圣乡途中,因行驶变道原因在娇子立交被张某驾车逼停,随后遭到殴打致伤。事件视频在网络上发布后,人们先是对男司机张某下手之狠表示震惊。然而,当张某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被披露以后,舆论又转而谴责女司机卢某开车太没规矩、太危险。她先是在几秒钟的时间里连续变道两次,直接从张某的车前切了出去,又压着实线下了主路,明显系违章驾驶。事实上,“怒驾”是个老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抽取900位司机开展问卷调查,约35%的司机承认自己属于“路怒族”,在驾车时出现过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争道抢行、连续鸣笛催促前车等行为。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因“路怒症”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1月至2015年4月底,全国查处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强行违法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路怒”违法行为1.04亿起。据悉,交管部门将针对“路怒”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参见袁国礼:《“路怒症”引发肇事逐年上升》,载《京华时报》2015年5月9日。在成都被打女司机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呼吁将“怒驾”入罪。在笔者看来,“怒驾”入罪显然不具有可行性:首先,驾车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情绪在所难免,因而将某种情绪作为入罪依据,难以服众;其次,怨愤、恼怒情绪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入罪,也是一个问题;最后,对“怒驾”取证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人的情绪不像醉驾、毒驾那样可以即时稳固化、确定化,而是可以瞬间消逝的,因而要想证明行为人是在“怒驾”,除非行为人自己承认,否则几乎不可能。因此,将“怒驾”入罪显然是不现实的。
(五)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的入罪评价
除了上述危险驾驶行为外,对于其他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入罪,在学界亦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行为范畴较为狭窄,不利于规制该类行为,因而主张扩张危险驾驶入罪的范围。例如,有学者认为,“明知自己没有驾驶能力而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和驾驶明知存在安全隐患车辆的行为,其危险性也不亚于醉酒驾驶与追逐竞驶,实践中可能由于事故发生的概率没有醉酒驾驶高,普通民众所感受到的恐惧感也没有醉酒驾驶强烈等原因没有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对于这些情形,应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其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皮勇、杨淼鑫:《论我国危险驾驶罪立法的扩张》,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有学者提出,明知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明知是已报废的机动车辆驾驶,严重超载驾驶等等,应以危险驾驶罪来充分评价和处罚。*参见亓旭岩:《试析危险驾驶的罪与罚——以危险驾驶入刑为视角》,载《山东审判》2014年第1期。
上述观点虽有其道理,但值得进一步探讨。就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范围而言,不宜过于扩张,更不应盲目借鉴国外经验,忽视本国国情并不可取。一方面,不应当将一切对公共交通运输安全可能产生危险的行为都入罪,否则就会过于扩张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毕竟,一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都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都会对公共交通运输安全产生某种程度的危险。将这类行为一律入罪,恐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也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入罪不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即纯粹根据行为本身入罪,而不考虑其他要素或者行为的危害程度。否则,不但会大量增加司法成本,也会严重影响司法效率,且成效未必显著,可谓弊大于利。
笔者认为,就危险驾驶行为入罪而言,在必要性上必须坚持以下几点:一是危险驾驶行为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对于这种危险性,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于一般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造成的。只有在行为人自身丧失意识或者意志等可能导致行为失控,或者由于运输对象的特殊性,或者严重违反运输管理法规等,可能会对公共交通安全造成重大损害的危险驾驶行为,才能将之入罪;二是危险驾驶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某种危险驾驶行为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但在司法实践中只是个别的、鲜见的,也不应当将之入罪。因为,较少发生足以说明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严重,因而入罪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可行性上,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必须做到入罪的依据和标准具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取证时不至于过于困难,乃至于无法查证。根据这样的标准,对明知自己没有驾驶能力而驾驶机动车,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等,均不应当入罪。总之,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应当慎之又慎。对某类危险驾驶行为,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前提下,才可以考虑将之入罪。
[责任编辑:谭 静]
Subject: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Amendment IX to Criminal Law
Author & unit:PENG Wenhua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s far as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s is concerned, the necessity is that it has considerable degree of risk and the occurrence of the behavior has certain universality, and the feasibility is that there are clearness and operability in the determin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so that the punishment is guaranteed to be possible. It is undesirable for Amendment IX to Criminal Law to exclude the “double super” of road freight transport from the scope of th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It is feasible and necessary for illegal transport of dangerous chemicals to be criminalized, but regret still exists.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riving after taking addictive drugs and driving with anger is not feasible. The scope of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s should not be too expansive.
dangerous driving; necessity; feasibility; driving after taking addictive drugs; driving with anger
2015-08-30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罪量视野下的犯罪论体系诸问题之困境与出路》(11YJC820091)的阶段性成果。
彭文华(1972-),男,江西新建人,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D924.32
A
1009-8003(2015)05-00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