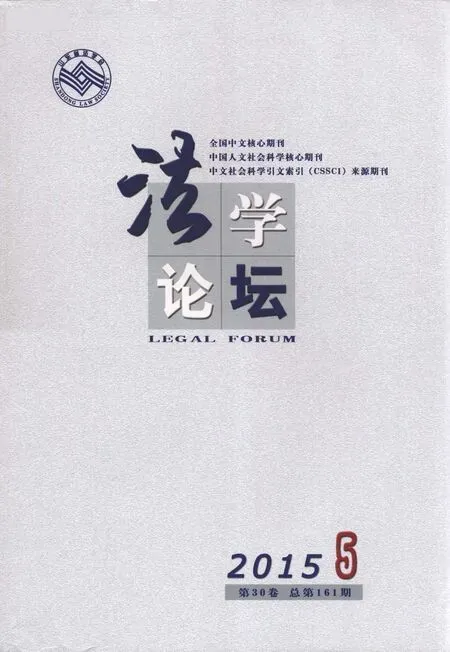言论抑或利益
——美国宪法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李一达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言论抑或利益
——美国宪法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李一达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在美国宪法的视域下,政治言论因其所具有的社会公益性而得到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保护。与之相比,仇恨言论、情色言论等则被视为“低价值言论”而只能受到有限的保护,商业言论作为一种商业活动的附属产物亦在此列。然而,以19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和本世纪初保守主义回潮为背景,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先后两次出现了应赋予商业言论以绝对保护的呼声。对商业言论给予绝对保护,本意是为了更加平等地保护多元的价值立场,从而促进社会公益。但是,由于商业言论与经济活动具有天然的亲缘性,金钱对言论效力的影响就很难得到有效的限制,进而加剧了价值立场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在自由与保守两极之间不断摇摆,司法决断逐渐侵蚀民主政治,广大美国民众日益沦为政治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
美国宪法;言论自由;低价值言论;商业言论;绝对保护
一、 引言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开宗明义地宣布了对言论自由的保护。*Wikipedia: “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Bill_of_Rights#First_Amendment, 2015年1月18日最后一次访问。但对于何为“言论”、什么是“自由”以及怎样“保护”这一系列问题,自该修正案被通过至今,依然莫衷一是。在这两百多年中,尤其是自上个世纪以来,围绕该修正案的解释逐渐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案例解释系统。简而言之,对我们所见所闻的各类“言论”,第一修正案将其区分为两个层级:“高价值言论”(high value speech)和“低价值言论”(low value speech),以此确立审查这些言论合宪性的不同基准。
第一修正案的上述言论保护分层观被认为奠基于以下两种理论:“思想市场论”(market place of ideas)和“自治论”(self-government)。前者出自霍姆斯大法官,在他看来,通向真理的最佳途径是思想的自由交流,如果将自由交锋的诸种思想存在的场域视为一个“市场”,那么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自然就成了判断某种思想是否接近真理的唯一判准。而言论自由便是创造这样一个能够自由交锋的思想市场的基石。*参见250 U.S. 616 (1919).后者则首先出现在布兰代斯大法官的判决附议中,这一观点不仅将公共讨论视为一项公民权利,更视为一种政治责任,视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因此,国家保护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在保护“人民自由、全面地发展”的可能,而这正是公共讨论得以开展的前提。*参见274 U.S. 357 (1927).在这条言论自由“金线”的衡量下,以政治言论为代表的高价值言论会得到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保护;而低价值言论则处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场域之外,或游离于其边缘,这其中包括仇恨言论、诽谤言论等等,商业言论也名列其中。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言论和非政治言论的边界日益模糊,诸如焚烧国旗等象征性行为作为非典型政
治言论大量出现,颠覆了人们一直以来对“言论”的认知,也冲击着第一修正案框架下的言论保护分层理论。*参见394 U.S. 576 (1969). 对该案的评述,参见臧震:《美国宪政精神下的表达自由——以焚烧国旗案为例》,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2期。作为低价值言论的一种,商业言论的最大属性恰在于其模糊性: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把对该言论的认知重心放在前一个词(commercial)或是后一个词(speech)上,它的意涵会变得完全不同。
本文关注过去的近50年中,作为美国政治“风暴眼”的美国最高法院,*参见[美]戴维·奥布赖恩:《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任东来、胡晓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关于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力,另参见[美]卢卡斯·A·鲍威:《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欧树军译,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版。一个通过案例史展示最高法院的政治角色的视角,参见Brest, Levinson, Balkin, Amar, Siegel,Process of Co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 :Cases and Materials(Fifth Edition) , Aspen Publishers, 2004.在给予商业言论以何种程度的宪法保护这一问题上的观念转换和立场位移,并尝试分析宪法变迁之下的政治分歧。*我国学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视域下的商业言论保护问题已有不少研究,但多数还停留在案例重述的阶段。这些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有:赵娟、田雷:《论美国商业言论的宪法地位——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赵娟:《商业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刘晖:《对美国商业言论宪法地位的探索以及对中国的启示》,载《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秦前红、陈道英:《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中的新课题》,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等等。这一考察不仅是以商业言论为视角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案”史重述,也是对商业言论本身性质为何的审视。考虑到当今世界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最重大特征之一便是经济活动的去国界化,这个过程更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形态与日常行为之边界日益模糊。本文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与剖析,想必能对中国的语境下重新理解言论自由的边界和商业活动的性质有所助益。同时,本文也试图通过对以最高法院为中心的美国宪法-政治过程的讨论,反思在国内学界已几成违宪审查“标准”模式的“司法审查”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我国学界经常将“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不加分辨地作为同一概念使用。对这一违宪审查模式及其正当性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张千帆:《认真对待宪法—— 论宪政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张志伟:《对美国司法审查正当性理论的分析与反思》,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3期,等等。对这一混用的批判与反思,参见: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田雷:《超越宪法的美国宪政史》,载《社会观察》2012年第4期。
二、利益即言论:商业言论的第一次“绝对保护”
商业言论的问题第一次进入最高法院的视野是在1942年,在判处仇恨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一个月之后,最高法院判决了瓦伦丁诉克里斯滕森案(Valentine v. Chrestensen,以下简称“双面传单案”),*参见316 U.S. 52 (1942).该案涉及的问题是,纽约市警察局长瓦伦丁禁止商人克里斯滕森在街面散发印有“政治性言论”的游览传单这种双面广告是否违宪。*在克里斯滕森所散布的传单上,一面印有某艘退役海军潜艇的展览广告,而另一面则是所谓“政治性言论”:抗议纽约市政府拒绝其使用码头设施进行展览的声明。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宪法不限制政府管制街头的“纯粹的商业广告宣传”(purely commercial advertising),而克里斯滕森的行为是试图将其传单置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以规避政府管制,尽管其广告传单上印有批评政府行为的言论,但其散发传单的本质目的乃是牟利,而没有形成思想的交流与撞击,由此判定该商人的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自此,最高法院开始袭用1937年罗斯福新政以来其所逐渐采取的保守态度:对国会有关经济方面的立法采用相当低的审查标准,即对此类言论进行一个“主要目的检验”(primary purpose test)的测试,如果这一言论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追求商业上的利益或者是获得商业交易机会,即这一言论更多地是一种商业活动而不是言论,如在双面传单案中该商人的行为,在法院的眼中便是“在街道上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差事”,那么它就满足了主要目的检验。*参见316 U.S. 52 (1951).被确认为商业言论后,这一问题就交由“立法判断”(legislative judgement)了。在1951年的布莱德诉亚历山大市(Breard v. City of Alexandric)案中,最高法院通过支持禁止发行商主动上门游说订阅杂志的法令,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准。
但20年后,商业言论重新进入了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核心视域。用保守派法学家柏克(Robert H. Bork)的话讲,在这一时期,能动的沃伦法院所判的一系列案子特别是与民权(civil rights)有关的案子使得第一修正案的“核心越来越软,边缘却越来越硬”。*参见Robert H. Bork, Coercing Virtue, AEI Press, 2003, pp.57.即是说,一系列的“低价值言论”在这一时期纷纷得到保护,如情色言论、污言秽语等,给商业言论以绝对的保护的论调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在最高法院中。
(一)作为公共议题的商业言论
在1975年的毕格罗诉费吉尼亚州案(Bigelow v. Virginia,以下简称“堕胎广告案”)中,最高法院以一份5:4的判决判处弗吉尼亚州对堕胎广告的管制违宪。*参见421 U.S. 809 (1975).卷入这起案件的毕格罗(John·C·Bigelow)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份周报的主编,他刊载了纽约市的一家堕胎诊所的广告,而弗吉尼亚州法院称这一行为违反了州一项禁止鼓励他人堕胎的广告的法律。主笔罗伊案的大法官布莱克门(Harry Andrew Blackmun)操刀法庭意见,第一次将商业言论纳入了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中。在该判决中,他写道:总体看来,广告蕴含了对于多元化公众具有潜在利益和价值的信息——不仅对于那些可能需要堕胎服务的读者,而且包括那些对于堕胎问题或其他州的法律具有一般好奇或真正利益的人们,以及寻求弗吉尼亚州堕胎法改革的读者。而且,进行广告的堕胎活动符合宪法的利益。——因此,在本案中,上诉人的第一修正案利益与一般公众的宪法利益恰好重合。*同①。
接下来,布莱克门对双面传单案确立的传统做出了限缩解释, 他认为,双面传单案裁决并不意味着,—州对于商业言论的所有规制都不可能受到宪法上的挑战;因为该案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即只有在作为“对于商业广告的分发方式的合理调控”的意义上,弗州的法令才得以维持。布莱克门因此总结道,广告的“商业方面”和“发行者的获利动机”不能“否定第一修正案的所有保护”,亦即,如果一项活动是合法的,州就不能禁止关于它的广告。
(二)作为公众利益的商业言论
堕胎广告案是最高法院第一次表明涉及到公众关心的议题的商业言论,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并对双面传单案塑造的判例传统做出限缩解释。然而,这种思路仍留有一个悬而未决的缺口,而这一缺口对商业言论的保护而言或许是致命性的:如果说,堕胎广告是因其“表达”的内容或思想涉及到公共利益或宪法保护的权力,因此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那么“纯粹的”商业言论是否在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内(事实上,如怀特大法官就将堕胎广告案视为一起堕胎案而非商业言论的案子)?不回答这一问题,商业言论就永远处在第一修正案的边缘地带。
从这个意义上说,1976年的弗吉尼亚药业协会诉弗吉尼亚公民消费者委员会案(Virginia State Board of Pharmacy v.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以下简称“处方药价格广告案”)可谓商业言论保护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件。*参见425 U.S. 748 (1976).该案最深远的影响是,它阐明了不包含“思想”、只包含“商业信息”、只是一种信息传播而根本不是一种表达的广告,即所谓“纯粹的”商业言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该案涉及弗吉尼亚州对处方药品的价格广告的一项禁令,该州的消费者团体认为州的此项禁令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州方则辩称这一管制有助于保证药品的职业标准,因此是合理的。
该案的判决依然由布莱克门大法官执笔。他指出,本案不同于之前最高法院处理的商业言论案件之处在于,如果涉案的药剂师们“……并不希望发表关于文化、哲学或者政治等方面的评论。他们也并不希望报道任何具有特定新闻价值的事实,或者是对于商业事务做出一般性的观察。他们通过广告所试图传达的观念仅仅是‘我将以Y价格将X 处方药品卖给你’。我们的问题是:这一交流是否完全处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外?”*同③。布莱克门首先分析了处于商业言论边缘的两种类型:劳资纠纷言论,和涉及重大公共议题(如堕胎)的言论,指出它们已经被纳入第一修正案保护范围,进而将问题引向商业言论的中心,即“纯粹的商业言论”。在此,布莱克门衡量了两种言论的价值,在他看来,即便做广告的人纯粹出于经济利益,但并不能因此就剥夺了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权利。因为“特定消费者在商业信息自由流通中的利益,即使不会超过,但也绝不会亚于他在重要的政治辩论中的利害得失。”
布莱克门何出此言?从判决来看,布莱克门并不否认商业言论相较于一般言论的特殊性——乏味、冗余,与其称之为“言论”,倒不如说是“信息”来得更为准确。但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承认美国的制度基础之一是一个以自由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那么大量的资源分配就将通过许许多多的个人经济决策来付诸实现。因此,就这些决策的整体而言,它们明智、博识与否也就成了一项公共利益问题。那么,商业信息的自由流通自然便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是,“第一修正案被认为主要是在民主政体中指导公众进行决策的工具,而信息的自由流通也正服务于这一目标。”*同③。由此布莱克门判决弗吉尼亚州的此项禁令违宪。针对州声称这一法律是为了将广告宣传置于更为专业的标准下的辩解,布莱克门称,州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声称如果人们“保持他们的无知”,他们会活得更好。
如果说在堕胎广告案中,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的保护是将商业言论尽量与政治性言论挂钩,模糊两种言论的边界,那么在处方药价格广告案中,布莱克门通过诉诸美国民众在经济领域的自治,使得商业言论彻底泛政治化,商业言论与政治性言论共享一个传统——自治(self-government),这一处理实际将商业言论的保护置于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即只要商业言论不是虚假的(untruthful)、误导性的(misleading),其便能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商业言论由此被区分为两种:真实言论和虚假言论,而前者与受第一修保护的政治性言论等没有什么不同,因而获得了被绝对保护的地位。
三、绝对保护的基础:“言论自由是绝对的”
不过,我们应当追问的一个问题或许是,商业言论是如何进入第一修正案的中心视野的?在1942年双面传单案的判决中,刚刚被罗斯福新政“规训”过的最高法院毫不犹豫地将涉案的广告定性为一种商业活动,然后交由“立法判断”。那么,在20年后,对商业言论的保护何以又成为了值得重新审视的第一修正案问题?更重要的是,布莱克门一直试图将商业言论与政治性言论挂钩,将他们共同置于美国人民的自治传统之上,以给予其绝对的保护,这种绝对主义的思路又是从何而来?
自布兰代斯大法官那份宣称公共讨论是一种政治责任的附议之后,教育家、哲学家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的两篇文章堪称“自治论”在此问题上最重要的文献。他写于1940年的《言论自由与自治的关系》,针对的是最高法院自1919年以来形成的、对第一修正案言论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审查标准,这一标准产生于申克诉合众国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中霍姆斯大法官的判决。*参见Alexander Meiklejohn,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s to Self-government,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11.米克尔约翰认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这一标准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搞清楚美国宪法涉及的言论有两种,即“公言论”(public speech)和“私言论”(private speech)。所谓公言论就是与统治事务有关、代表人们参与自治过程的言论,私言论则是与上述事务无关的言论。米克尔约翰写道:“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我们统治者有关思想和交流的活动的自由”,而所谓“我们统治者”(we govern),在其语境下就是美国人民,全体美国人民就是自治的主体。在文章他举新英格兰议会的例子说明道,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和决定各种公共议题,除了接受议事规程的调整外,其在议会中的任何发言都不受追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意见都有被倾听的机会,进行自治的人们才可以做出明智的决断。换言之,美国人民的这一自治首先基于言论的自治这一形式。因此,在公言论领域不适用“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公言论领域是一个“绝对”的领地,第一修正案所说的:“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这里的言论不是所有的言论,而是跟自治有关的政治言论。如果国会制定了约束人民发表此类言论的法律,那么国会就是制定了一个自我否定的法律,因为国会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人民的自治。
但做出如是界定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政治言论?政治言论的范围是什么?60年代后,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一样,陷入了一场“文化战争”中,种族、女人、反战统统变成了悬而未议的问题。那么,与这些议题有关的哲学、历史、文化等等这些所有言论到底算不算在政治言论里?在1960年的“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一文中,米克尔约翰对这一争议做出了表态。*参见Alexander Meiklejohn,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Vol. 1961 (1961), pp. 245-266.米克尔约翰认为,“投票”是一个自治的公民对于公共议题做出判断的正式表达形式,但一个合格的公民显然应当在投票前对所涉公共议题有所理解,才能真正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实现自治。因此,哲学、艺术、文学等等所有这些言论对塑造一个公民的政治认同都是有用的,都能使美国民众更好地成长为能合格地行使自治权的公民,所以这些也算政治言论。甚至不仅言论,那些“在人类的交流活动中,还有许多思想和表达形式有助于增益投票者的知识、智慧和对于人类价值的关怀,有助于增进他们做出明智、客观判断的能力。这些活动的自由也是不可限制的。”这样一来,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就变得无所不包了。
在米克尔约翰写下这篇文章4年后,也就是在《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通过的同年,最高法院判决了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ian,以下简称“《纽约时报》案”)。*参见376 U.S.254 (1964).在这一案件中,大法官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根据1942年双面传单案确立的商业言论保护原理,本案中涉及广告是否不受宪法保护?撰写法庭意见的自由派大法官布伦南(William J.Brennan)否定了这一思路,他指出在本案,言论尽管采用了商业广告形式,但完全是政治言论,“它传播信息,表达意见,陈述委屈,抗议所谓的权力滥用,为某种运动寻求财政支持,而该运动的存在和目标是属于最高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务。就本案关注事项而言,纽约时报为刊登广告而收费属无关紧要的枝节,如同出售报纸和书籍而收费一样。”他进而写道:“如果我们在此作出其他任何结论,都将阻慑报纸,使它们存有畏惧,不敢刊登此类广告,这会关闭一个本可用来传递信息和意见的渠道——对于那些不属出版界业内人士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能接近出版设施,却又需要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人来说,这是一条重要渠道。第一修正案致力确保‘来源不同和对立的信息能得到最为广泛和最大可能的传播’,(关闭言论渠道)就是桎梏第一修正案,使之无从发力。为了避免给表达自由造成上述障碍,我们裁定:如果(被上诉人)所称诽谤言论本应受到宪法保护,决不应由于这些言论的发表采取了付费广告的形式就失去这一保护。”*同②。
《纽约时报》案第一次明确广告因其内容所包含的思想而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广告本身只是一个媒介,重要的是其承载的思想,它是作为对一种意见的表达,作为“我们统治者有关思想和交流的活动”(米克尔约翰语)而存在。这一思路可以说完全贯彻了米克尔约翰文章的观点,10年后,最高法院几乎以同样的思路判决了堕胎广告案,从此,广告终于变成了“言论”。
四、商业言论的保护限度:四步分析标准
在1980年的中央哈德森电气公司诉纽约公共服务委员会案(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rp.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New York)中,鲍威尔的判决将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的保护彻底往后拉了一步。*参见447 U.S. 557 (1980).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纽约州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一项限制促进电力适用的广告的管制违宪。在该判决中,鲍威尔首先指出,1970年代的先例承认商业言论与其他类型的言论之间存在“常识性差异”(commonsense differences)。而这一“差异”便是商业言论涉及商业贸易,后者属于传统州管制的领域。因此,对商业言论的保护相比其他言论而言较低,这一保护的强度同时取决于商业言论这种表达自身的特征和管制商业言论所要实现的政府利益。鲍威尔由此指出,对商业言论的管制存在两种不同程度的审查:对虚假、误导性言论的管制,法院的审查比较宽松;对真实、没有误导性、与合法行为相关的商业言论,政府如果加以管制,必须经受法院对其管制行为的审查。
根据鲍威尔的判决,这一审查首先要求政府在这一管制中存在实质的利益,政府管制的手段与实现该利益应当是相称的,而在实现政府利益的过程中,对商业言论的限制必须十分谨慎。为实现上述要求,鲍威尔设立了两项判断标准:第一,这一管束必须直接推进了政府的利益;第二,为了实现政府利益而对商业言论进行的管制必须尽可能的小。
鲍威尔用这两个标准衡量1970年代以来最高法院在商业言论问题上的一系列判决,而将这些判决重新置于了他新确立的这一标准中,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法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关于商业言论的判决中,一个四步分析标准逐渐形成。这一标准是:
(1)涉案的商业言论是没有误导性的、合法的,即该言论是处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内。
(2)州的利益是“实质”的。
(3)州对该言论的管制能直接促进其所声称的利益。
(4)这一管制必须尽可能的小/有限。
为商业言论的绝对保护奠定基准的布莱克门大法官虽然赞同法庭意见的判决结果,但在附议中对鲍威尔确立的这一新标准展开了严厉的批评。布莱克门认为,尽管四步分析标准处理的只是商业言论管制的问题,但这类“通过将公众置于无知之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管制已经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表达”(expression)。 换言之,布莱克门和鲍威尔围绕对商业言论的保护程度展开的争论,大致可以还原为对如下问题的争论:商业言论所具有的、与其他类型的言论区别开来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商业言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它更多地是一种“言论”,还是“贸易行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商业言论在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诸言论的谱系中,究竟是不是一种“低价值的言论”,进而法院对加于商业言论之上的政府管制,要适用何种程度的审查。
五、言论即利益:商业言论的第二次“绝对保护”
对布莱克门和鲍威尔在最高法院的那些保守派大法官同事而言,上述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回答:商业言论当然是一种贸易行为,但它是与州对经济的管辖权密切相关的贸易行为。这样一来,商业言论所引发的争议就不仅关乎第一修正案,还同时在第X修正案的意义上具有了宪法意涵。随着斯图尔特和伯格两位自由派大法官相继离任,奥康纳和斯卡利亚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进驻最高法院,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内部逐渐转为攻势。在商业言论问题上,他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四步分析标准一概采取抵制态度;相反,他们通过对几个重要案件的判决,将该标准从一个严格审查标准改造成一个有弹性的标准,从而对州权实现了扩张。*如在1986年的波多黎各旅店协会诉波多黎各旅游局案(Posadas de Puerto Rico Ass. v. Tourism Co. of PR)中,保守派大法官们首次运用四步分析法,以一个5:4的判决否决商业言论的保护诉求。在对上述人的一条抗辩理由的回应中,伦奎斯特大法官指出,州有权州政府有权管制赌场这一“较大的权力”显然包含了州政府管制赌场投放的广告这一“较小的权力”。参见478 U.S. 328. 而在1989年的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诉福克斯案(Board of Trustees of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v. Fox)中,斯卡利亚大法官则重新定义了四步分析法的最后一个环节。他指出,只要政府所欲图达到的目的和其采用的手段相匹配即可,政府在诸多管制手段之中具有合理选择的权利, 而非必须选择最低限度的管制手段。通过这一修正,州权获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参见492 U. S. 469.
其次,国家审计人员应转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在实施审计时,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应通过审计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保持合理的职业谨慎,进行理性的、科学的风险评估与应对,以便将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从1994年到2005年,保守派占得了最高法院的多数席位,随着伦奎斯特(willian Rehnguist)升任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彻底奠定其保守主义的基调。但保守派大法官内部对商业言论的态度反倒出现了更为激进的变化,要求给予商业言论绝对保护的声音甚嚣尘上。正如宪法学者图示奈特(Mark Tushnet)在作于2004年的《分裂的法院》一书中所言,“如今保守派大法官们认为言论必须得到第一修正案绝对的保护而不能容忍任何例外,而他们的自由派同事们认为有关第一修正案的案子牵涉到许多要考虑的事实,因此必须仔细地平衡和审视每个事实。”*参见Mark Tushnet, A Court Divided: The Rehnquist Court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Law,W. W. Norton & Company, 2004,p.302.这一激进立场的代表便是托马斯(charence Thomas)大法官。自著名的44酒类市场公司诉罗德岛州案(44 Liquormart Inc.v.Rhode lshand,以下简称“酒品价格广告案”)开始,托马斯在几个涉及商业言论保护的案子中都表达了他对四步分析标准的不满;*参见517 U.S. 484 (1994). 在这个看似一致的9:0的判决中,却没能形成5票的法庭意见,而只有多数意见,针对该案法庭一共出现了三份意见书。在该案中,两派大法官仍以1986年的Posadas de Puerto Rico Ass. v. Tourism Co. of PR案为主要先例,将火力集中在围绕州权伸缩展开的攻防上。但以托马斯大法官为代表的保守派新观点已开始凸显。参见478 U.S. 328 (1986).在2001年的罗瑞拉德烟草公司诉瑞丽案(Lorillard Tobacco v. Reill,以下简称“烟草广告案”)中,托马斯在其撰写的附议中第一次完整阐释了其对商业言论的绝对保护的法理学。*参见533 U.S. 525 (2001).
烟草广告案涉及到两项对香烟广告的禁令是否违宪,一项是禁止在距离公共休闲场所与学校一千英尺的区域内设立烟草产品的户外广告,另一项管制禁止在销售香烟的地区以低于五英尺的高度打广告。法院以一个5:4的判决推翻了这两项禁令,这是一份基本按意识形态站队的判决,奥康纳代表法院多数撰写了法庭意见,斯蒂文斯代表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和苏特递交异议,托马斯又单独撰写了一份意见。在这份意见中,托马斯试图讨论一直以来困扰商业言论保护的两个基本问题:商业言论与非商业言论到底有没有区别?或说,商业言论是不是一种较低价值的言论?以及,对商业言论的管制因此应给予何种程度的审查?
在意见的开始,托马斯就指出,任何试图通过管束言论(truthful speech)的方式管束其所传达的思想(the ideas it conveys)的政府管制,都应当对其进行严格审查,无论这一言论是不是被称为“商业言论”。 他将70年代以来围绕商业言论保护的一系列争论一笔带过,指出从1976年弗吉尼亚处方药案法院开始保护商业言论起,从此商业言论的保护程度一直含混不清,这一含混性被集中体现在Hudson标准的一系列适用上。
托马斯认为,“商业”言论比“非商业”言论所包含的价值要低这种说法从来没有任何哲学或历史基础,想要清晰的区分这两种言论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任何宣传为了实现政府的某些利益而管束表达,将民众置于无知之地的政府管制,都要接受严格审查,无论这一管制的对象是不是“商业”言论。
托马斯承认,有些言论——如商业言论——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程度要比其他言论低;但他同时坚持,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这些领域就可以为所欲为。在他看来,“言论在这些领域内,是因其内容在宪法上受到禁止,所以才可施加管制。这和第一修正案也是一致的。”*同④。换言之,即便某类言论受宪法保护程度较低,政府也不能出于与该类言论之特征无关的原因,对其内容加以歧视。
托马斯也承认,商业言论的特性(“因其散播者而更易加以核实”,“并不会因‘恰当的管制而冻结’”)要求其必须满足特定的形式,包含特定的附加信息、警告和免责声明,以免对消费者造成迷惑。政府可以出于这种理由对商业言论加以管束,但除此之外,如果州禁止一种真实的、没有误导性的商业信息的传播而不是出于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这一目的,那么,没有理由不对该管制施以严格审查。在托马斯看来,无论联邦拥有怎样的权力来管制商业言论,或许都无法使用这种权力去限制商业言论的内容。*同④。在附议中,托马斯接连推翻了州诉称管制是为了保护儿童的利益和管制针对的是非法贸易行为(向儿童兜售香烟)这两条规避法院对管制的严格审查的理由,最后总结道,只有且仅当管制是涉及重要且正当的国家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时,管制才是被允许的,否则一切管制都要接受严格审查。
早在1994年酒品价格广告案的判决中,托马斯就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商业言论的双重属性带来的问题:只要承认商业言论存在不同于其他言论的“常识性差异”,政府就永远都可能对商业言论加以管制。于是,他抛弃了自己20世纪90年代试图将商业言论保护回归到1976年处方药价格广告案那个非常高的保护程度的努力,重新选择了另一种更为绝对的论证思路,这就是认为所有的表达(包括商业信息中)都包含了思想。借助这一思路,商业言论与非商业言论(主要是政治言论)之间难以抹煞的差异导致的,对商业言论究竟是否应当给予绝对保护的争论就彻底消解掉了:无论是商业言论还是非商业言论,其被保护都是因为其包含了一种思想,而法院所要做得就是保证这些思想在“思想市场”上畅通无碍地自由竞争,不到最后关头,政府应当放任思想市场自我调节那些虚假和误导性言论,而不是由自己来调控。
在这里,我们似乎又一次看到了80多年前霍姆斯大法官关于思想市场与言论自由的那份著名判词,只不过在托马斯手里,言论不再是作为思想的传播途径存在,而是作为特定利益的发声筒而存在,或者更绝对一点说,所谓“思想”无非是对特定利益的认知而已。因此,无论何种言论,最终都不过是对某种利益的主张,至于这个利益是公益、商益抑或其它,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表达从而应当受到保护的本质。于是,在纠缠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在托马斯笔下,商业言论的后一种属性(speech)终于不再和前一种属性(commercial)对抗,而是被后者“灵魂附体”了。
六、绝对保护的基础重置:两种共和党人和“大公司的宪法”*Mark Tushnet, A Court Divided: The Rehnquist Court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Law,"Big Business's Constitu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p.302-318.
随着以托马斯大法官为代表的商业言论保护激进派异军突起,保守派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也日益分化:斯卡利亚和肯尼迪两位保守派大法官在一系列案子的附议中也表示四步分析标准已经无法对商业言论给予足够的保护,而如伦奎斯特等保守派大法官出于保护传统的州权的考虑,更愿意维系承认州存在重大利益的四步分析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最高法院接连判了两起商业言论的案子,即前述烟草广告案和2002年的汤普森诉西部诸州医疗中心案(Thompson v. Western States Medical Center),两起案子涉及的都是共和党在经济上的利益所在(烟草和合成药),都是以5:4的结果判决对涉案商业言论的管制为违宪,保守派与自由派基本按意识形态站队,但两次都各有一名保守派大法官投反对票(苏特和伦奎斯特)。*参见535 U.S. 357 (2002).两起案子的法庭意见主笔都是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大法官,她依然坚持了其自1994年酒品价格广告案以来比较中庸的思路:一方面将Hudson案操作成一个更加严格的审查标准,另一方面抵住了更加右倾的托马斯等大法官的压力,勉力维持住了四步分析标准。
保守派大法官为何会陷入分歧?或者说为什么托马斯等保守派大法官会转而追求一种自由派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给商业言论以绝对的保护?如果跳出商业言论的视野,我们会发现保守派主导的伦奎斯特法院自形成以来,在一系列事关当代共和党根基的社会议题如堕胎、同性恋、平等保护上都举步维艰,共和党大法官们的分歧看起来并非是个人意见的相异,而更像是两种派性、立场的冲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保守派或者说共和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两种共和党人”问题。
两种共和党人可以在比较粗略的框架内区分为“经济保守派”和“道德文化保守派”,前者是更为传统的保守派的形象,在经济上坚持自由市场和小政府,而占据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流的则是作为对20世纪60年代“文化战争”反弹而发展起来的“道德文化保守派”,这两种保守派在共和党的旗帜下走到一起,但实际上却难以调和,两派因此更多地只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联姻。而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党逐渐执掌美国政坛,美国政治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大变化,即保守主义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在美国则已经成为处于守势的意识形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变同时包括两层含义:在经济上“市场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说压倒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主导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而“道德文化保守主义”则逐渐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46页。保守主义这两种在不同层面的意识形态扩张由此塑造了当代共和党人可能具有的三种特质:市场自由放任,联邦主义,道德文化保守。这三种特质并不兼顾甚至彼此并不相容,从阶级上看,前者主要是共和党上层,持后两种立场的则更多是中低收入阶层的选民;从地域上看,前者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传统共和党的阵地——重工业城市和华尔街,后两者则分布在南方各州;而在价值观上,前者虽然也支持“家庭、工作和邻里”等社群价值,认为“社群的规范”应当高于诸如性行为、色情和青年教育等议题,但当传统社区的需求与自由市场的需求相冲突的时候,这些人就变成了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参见E.J Dionne, Jr.,Why American Hate Politics, Simon & Schuster, 2004, pp.14.这就使得共和党内部逐渐分化成不同的阵营。
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商品市场如今已经完成了从政府管制到自由放任的转变,商业言论身上的金钱味道越来越浓,与传统共和党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大公司,尤其是烟草、制药、军工等大公司急切地想把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在政治上的优势,打破对自由市场的一切桎梏。于是上述共和党人内部的分裂反映到最高法院的6名保守派大法官内,便呈现出这样的情景:以托马斯、斯卡利亚为代表的“死硬的保守派”急切地想推进保守派在这方面的利益,推翻四步分析标准对商业言论施加的最后限制,而对传统共和党人更为关心的联邦主义问题不甚热心。正如斯卡利亚说过的那样,有时候联邦权力也是个好东西,例如它可以限制州批准那些干涉“自由市场”的经济管制的通过。而如伦奎斯特这般自20世纪70年代便供职于最高法院,一直试图通过扩张州权与激进能动的自由派对抗的大法官,必然是一个联邦论者,但他毕竟代表了被戈德华特和里根改造过的那种现代共和党人,对州权的伸张出发点更多地还是处于道德文化的考虑,这一点上他和奥康纳们又有不同。而奥康纳、肯尼迪和苏特则代表了更为传统的共和党人,他们更关心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和约束政府对经济的规制,反对新政以来国家干预州经济的种种“大政府”措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托马斯们利益一致,但他们传统上同样又是联邦主义者,赞成州为了其辖下居民的人身安全与福利而限制过于粗暴的市场逻辑和“合法但有害”(truth but harmful)的贸易活动,因此当自由市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在州范围内自生自发、甚至带有伦理意涵的那种小市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竞争的史无前例的大市场时,当大公司的利益开始挑战传统上属于州的治安权时,他们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七、余论
如上所言,商业言论的两种属性之间的张力,使得它始终难以完全取悦美国政治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在伦奎斯特法院末期,四步分析标准这一基于言论区分的有限保护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在2003年的耐克公司诉卡斯基案(Nike v. Kasky)中,面对“大公司发表在公共媒体上的公开信是不是商业言论”,进而是受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保护还是商业言论的有限保护这一问题,撰写多数意见的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束手无策,最后只能选择回避对该言论的定性。保守派大法官中,奥康纳和肯尼迪递交异议,而附议多数意见的3名保守派则未提交任何意见。*参见539 U.S. 654 (2003). 当然,着眼未来,本案的关键之处或许并不在于“什么是言论”,而是“言说者是谁”。参见秦前红、陈道英:《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中的新课题》,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该案似乎预示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派首创的、基于商业言论和非商业言论区分的一系列商业言论保护学说正在走进死胡同。
伦奎斯特之后,罗伯茨首席大法官(John G. Roberts Jr)执掌最高法院,而此时,奥康纳业已退休,如今的最高法院内部已经再没有能周旋于两派之间的“温和的共和党人”(Moderate Republican)了。罗伯茨法院的一系列动作已经毫不掩饰地向众人宣示,最高法院内的五名保守派要继续推动法院向右转。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纽约时报》的“驻院记者”亚当·里普塔克(Adam Liptak)指出罗伯茨法院“对判决涉及商业问题的案子越来越感兴趣”。*参见Adam Liptak, Justices Offer Receptive Ear to Business Interests, http://www.nytimes.com/2010/12/19/us/19roberts.html?_r=2&partner=rssnyt&emc=rss. 2015年1月18日最后一次访问。而一份来自芝加哥大学等院校的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的联合数据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五个庭期里,罗伯茨法院处理的涉及商业问题的案件在其处理的所有案件中所占比重达到了27%,这比伦奎斯特法院的最后5个庭期高了6个百分点。并且,在罗伯茨法院判决的这类商业案件中,大公司获胜的比率达到了61%;相比之下,伦奎斯特法院的相应比率只有46%。*参见Lee Epstein, 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Is the Roberts Court Pro-Business?, http://epstein.law.northwestern.edu/research/RobertsBusiness.pdf. 2015年1月18日最后一次访问。当然,数据无法完全反映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事实考量,但罗伯茨法院的判决越来越偏向大公司的利益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对商业言论的保护是否会完全右转,如20世纪70年代那样走向一种绝对的保护?在新的此类案件进入最高法院前,我们尚不敢下此断言,但从最高法院处理竞选资金等问题上的表现看,这将会是必然的趋势。*参见左亦鲁:《钱能讲话?》载强世功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287页。
然而这并非最重要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战争”时期,自由派大法官们将一系列不是言论的“言论”变成言论后,最高法院看起来又要在即将掀起的这场第二次言论自由绝对保护的风暴中走向分裂。柏克曾说过,“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 然而在两派大法官围绕言论自由问题的一次次斗争中,我们却并没有看到美国民主制度的主体——“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发出任何能影响自己生活的声音,他们更像是风暴中的枯叶,被一次次地卷起吹落。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最高法院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民意的代言的话,那么它的分裂就意味着美国民意的分裂。因此,陷入泥潭的或许已不仅仅是最高法院,还包括美国的民主制度。*R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pp.201-215.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民主已经不再是“寻求解决办法的政治”,不再寻求多种政治力量的整合,而是日益走向“两极化(polarization)”,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中上层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对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议题进行没完没了的隔空拳击,最终使选民对自己政党、对自己的政府越来越疏离,越来越“憎恨政治”*参见E.J Dionne, Jr., Why American Hate Politics, “introduction”, Simon & Schuster, 2004.。 或许正像前文提到的图示奈特那本《分裂的法院》(A Court Divided)标题所暗示的,随着司法过程通过违宪审查逐渐蚕食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又通过大法官提名逐渐渗透进司法过程,今日美国或许已经像内战前夜那样,又一次处在了“分裂之家”(A House Divided)的边缘。然而对越来越游离于政治过程和宪法决策的过程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选民而言,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尽快搞清楚一个最根本却也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究竟是谁在统治美国?“我们人民”的美国究竟往哪里去?毕竟,当下我们看不到又一个“林肯”出现的可能,他们能依靠的,只有他们自己。
[责任编辑:魏治勋 王德福]
Subject:Speech, or Interest?——a spectum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protecting for commercial speech
Author & unit:LI Yida(Law School,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In the realm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 while th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s political speech in term to its social public welfare, the protection for the low value speech such as hate speech and libelous speech is limited, and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commercial speech for its subsidiary position in the whole commercial system. Yet, by the clamor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since 1960's and the resurgence of conservatism at the start of the century, there were two claims for the absolute protection for business speech in the Supreme Court.The intention of the absolute claims is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freedom of different speeches more equally, and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But the commercial speech is naturally affinitive with economic activity. Money could hardly get effective restrictions on the validity of speech, and thus, exacerbate the inequalities among different value positions. Even more important, the swing of the Supreme Court between the liberalism and the conservatism leaded to the judicial decision gradually eroded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majority slipped into obscurity.
American Constitution; free speech; low value speech; commerical speech; absolutely protection
2015-07-06
李一达(1987-),男,山东莒县人,清华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理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宪法学。
D90
A
1009-8003(2015)05-0152-09
——从乔治·罗奇伯格的《和谐弦乐四重奏》研读他的《生存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