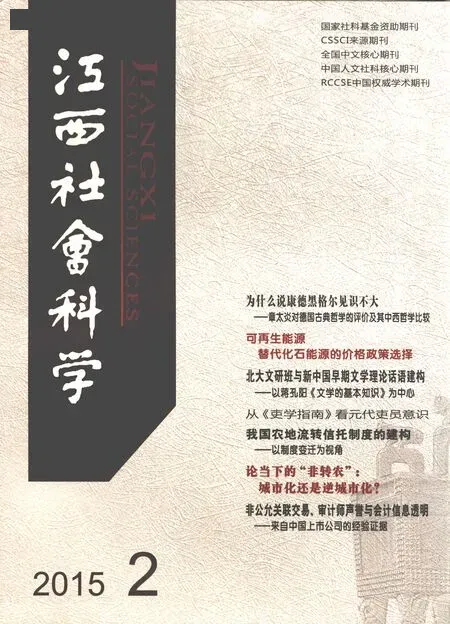邻避困境的反思与解决
——基于公平伦理与政策理性的双重考量
徐谷波 蒋长流
邻避困境的反思与解决
——基于公平伦理与政策理性的双重考量
徐谷波 蒋长流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及运营产生的邻避效应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新挑战。实质上,邻避困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社会与政治的博弈过程,因此,需要通过伦理规范考量邻避困境中的个体利益诉求。政策直接反映政府的价值取向,邻避困境的解决是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持续不断地求同存异、协调合作的过程,需要从信任与共识机制、第三方主体公正性、经济与伦理治理策略思维与执行力等方面着手。
邻避事件;邻避效应;伦理;公共政策
徐谷波,安徽广播电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安徽合肥 230022)
蒋长流,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 230601)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生产、生活垃圾和废弃物等的排量也在迅速增大,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厂、变电所、核能电站等城市基本配套设施应运而生,这些设施与火葬场、墓地、精神病院等设施类似,会给周边居民带来生理上、心理上乃至经济上的潜在危害,被称为“邻避设施”,即“邻居希望躲避的设施”,因这些设施的建设引发的群体性冲突被称为 “邻避效应”。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上海磁悬浮事件、大连反对PX项目事件、云南怒江水电站项目、四川什邡抵制钼铜项目及杭州余杭九峰垃圾焚烧厂等都是邻避效应的典型事件。
近几年,邻避效应也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他们分别从生成、规避、管理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探讨邻避效应,对应对邻避效应都有较好的指导意义。不过,任何成熟的理论都不是单一维度的,要形成完整而系统的研究体系则必须进一步拓宽和延伸研究视角。本文试图从公平伦理和政策理性的双重角度探讨邻避困境的根源,分析它的利益关系主体及逻辑关联,并尝试在一个多维框架内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邻避效应化解途径。
一、邻避困境的伦理反思
(一)环境正义与利益公平
公正原则是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它建立在利益基础上,并通过利益的实现客观地反映出来。公正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环境伦理是社会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它内生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之中,社会公正在环境方面的扩展和延伸即为环境正义,包含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理和公正等问题。[1](P254)邻避困境中伦理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利益关系调整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
依据受益对象的不同,利益分为公益和私益,公益和私益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它们往往成对出现,公共利益的实现有时以减少甚至剥夺私人利益为代价。在众多个案中,利益格局的分化、利益需求的复杂、“成本—效益”的不对称、社会信任缺失与风险沟通不足,都是产生邻避困境的原因,所以,邻避困境表面看是居民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一种抗争,实质上却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政治博弈过程,反映出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2](P26-37)具体而言,垃圾填埋厂、化工厂等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会不同程度地污染周边地区的空气、水、土地、建筑,从而危害居民的身体健康,戒毒所、火葬场、墓地的修建又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恐怖和“不祥”的心理暗示。当前,房产是城市居民家庭最重要的固定资产,一些邻避设施的建设导致的环境质量降低,会直接影响周边居民所持房产的经济价值,进而损害他们个人和家庭的财产总值。毋庸讳言,邻避设施的选址和建设往往倾向于弱势群体和贫穷群体的生活区域,这种带有歧视倾向的政策选择加剧了附近居民被孤立、被欺骗的感受,从而导致环境不正义的产生,弱势群体就成了环境不正义的首要牺牲者。
不可否认,邻避设施在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同时,其环境成本却集中转嫁给设施周围居民,这种利益不对称分配必然导致周围居民产生“邻避情绪”。邻避困境不仅从道德伦理上要求我们关注环境的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分配,更要求我们从更大的视角反思邻避设施带来的公益与私益的辩证统一,反思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环境责任、环境利益、环境权利的公平分配,反思受益大群体与邻避小群体的利益共担与分成。
(二)制度正义与理性诉求
如果说需要通过伦理规范考量邻避困境中的个体利益诉求,那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完善诉求的合理性,实现公共政策和个体诉求的和谐统一则需要制度的约束。制度是在特定社会范围内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规章等的总和,制度化就是把相对抽象的伦理原则和要求具体化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其决策首先要满足公共利益的诉求。公共利益是相对于共同利益群体内部少数人或单个人的利益而言的,公共利益既不是个体利益的叠加,也不是个体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少数人的共同利益。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公共利益始终是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人利益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公共利益,政策制定的合法性不足、政策监管力度不够、政策执行措施不完备等都会影响政策的合理性,在此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权益不对等、心理感受被误导等,都将直接引发个体或小群体理性诉求的形成和顺畅沟通的实现。邻避困境往往是在人们感觉到通过正常的制度程序无望解决纠纷,转而寻求其他“非制度化”途径时的直接表现。因此,邻避行动的产生不能简单归结为居民发自私利的非理性宣泄,它有更深层次的机制性成因。邻避行动的生成被韦伯称之为“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3](P56-57)。在这种情况下,正义作为制度的首要价值,必然成为制度建构的最基本伦理规范,义利相融、德得相通的实现只有依赖于制度正义。
就个体诉求而言,理性是有限存在的,个体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会最大化自己的偏好。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个体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会表现出拒不信任的非合作性博弈,邻避困境正是个体人组成的邻避群体在心理上形成“共意”并寻找“宣泄口”的必然结果。在这样一个由相关者组成的伦理框架内,实现制度正义与理性诉求的融合,需要设定几个边界。一是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个人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邻避困境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居民个体和群体,还包括项目所在的县区和街道、需动迁的企业和机构、项目运营主体等,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二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边界。要保证集体理性必须依靠制度,要获得个体理性也必须通过制度,在邻避困境中,吸纳民众参与、完善决策程序、设计更趋民主化,都是形成理性诉求的关键。三是制度最优与利益相容的边界。化解邻避困境,常用的方式就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广泛参与和直接民主,但实施过程却非常困难,制度形成的复杂性与制度功效的局限性,会造成在补偿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公共利益代表方在立场上虽能认可邻避设施受损,但在资金、政策和行动上却难具备协调进入政策程序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能力。[4]
二、邻避困境的政策理性与切入点
政策直接反映政府的价值取向,是对社会价值和利益做出的权威性分配,它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体现在经过伦理和利益的双重论证,制定和实施过程公正公开,最终利益分配结果让大多数参与者认同。
(一)协商理性下的利益界定
邻避困境起源于邻避设施的兴建,邻避设施的利与弊在空间上是分离的,即好处大家共享,但坏处却由少数人承担。[5]“为什么偏偏要牺牲我们?”“公共利益到底是谁的公共利益?”诸如此类的问题必然产生。当政府决策与民众诉求发生冲突时,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是缺乏理性和法治的表现。[6](Pl2-19)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基于政府公权力与居民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它依赖于特定的制度安排(比如民主程序与法治),也依赖于两者之间平等协商机制的产生。[7](P258-259)在我国,现行的政府决策模式在决策咨询空间开放度上已有较大提高,专家辅助参与政府决策的模式也被广泛采纳,但普通大众仍会习惯性地怀疑决策模式是封闭的,政府应当合理劝导难以有效规训的利益受损方,必然以伦理、经济、人文等更多层面的考量,改进单一管理职能体系去协调复杂利益关系。
(二)差异化认知下的风险认定
邻避困境中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对风险认知的差异。一般而言,当人们预感到设施会带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的危害时,必然会产生恐慌,这种恐慌是让普通人群演变成风险人群,风险人群演变为冲突行动者的根源。现代社会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唤起他们对潜在风险的防范。政府、专家和周边居民对风险的感知和推测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居民大多对高科技的数据标准知之甚少,他们只能基于自己内心的恐惧与担忧,或者根据道听途说的现实经验,本能地怀疑甚至否定专家的理性风险认知。[8](P67-77)邻避设施多属新兴环保行业,仅就技术而言,其风险远大于其他行业,如何协调利益相关方与利益中立方共同评估风险,如何制订风险应对策略和技术措施,均考验着政府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外部性视角下的补偿机制
补偿是最早用来解决设施设置问题的方法,虽然在居民获得满意的经济补偿时,邻避效应的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会降低,但政府财力有限、规章制度尚未健全、损失计算方法不完善等因素,还是会使补偿力度与受偿期望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基于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公益性项目补偿机制,邻避设施对居民造成的外部成本应该内部化,也就是根据环境影响情况,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影响谁受偿”的基本原则建立,补偿方案强调分摊成本、重新分配收益和体现公平公正。[9]
货币补偿是最通用的补偿方式。研究发现,货币补偿方式只能暂时缓解邻避现象,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产权、外部性以及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环境容量的货币定价困难,因环境权利衍生出的财产权利难以计算,更难以具体落实。[10]在政府实务操作上,补偿资金的缺位也是致使环境补偿机制不健全的重要原因。福利促进是解决邻避事件的另一重要方式,但不同的居民类型对公共项目的偏好不尽相同。
(四)信息不对称中的居民参与机制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居民参与邻避设施建设论证的主要目的是,深化利益相关者对项目全局的认知,增强居民和政府间的相互信任,运用科学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等。从我国现状看,居民参与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居民参与必须通过政府统筹安排,参与目标明确,参与模式设计要能满足不同参与强度的需求,形成合理的意见表达、反馈和理由说明制度[11](P30-35);二是居民参与的形式包括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基本任务是合理表达诉求,减少信息不对称,达成决策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均衡。
三、化解邻避困境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邻避困境的伦理考量与政策理性剖析,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邻避”看成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私的行为表现,无论从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看,邻避行动都有其内在运作的合理性逻辑,只有厘清邻避困境的产生根源和演变机制,从多元因素和多维角度思考对策,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一)信任与共识机制构建中政府角色定位与决策优化
邻避困境的治理过程不应仅仅看成是邻避困境的解决或消散,更应看成是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持续不断地求同存异、协调合作的过程。为了有效避免和治理冲突,首先要梳理和界定政府的角色职能。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看,在冲突困境的化解过程中,政府集公共利益的权威代表者、利益协调者、决策模式构建者、决策结果执行监管者于一身,因此,民众对政府有较高的依赖性。政府是制度和规则的最主要发出者,民众的这种依赖性是“别无选择”的,进而导致出苛刻的期望。其次,在处理邻避困境时,政府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和冲突点,培养风险理性意识,建立政治参与平台,创新参与模式,优化决策方式,通过有效的沟通建立信任并达成共识。最后,政府不能扮演“万能决策者”的角色,在项目审批、统筹协调、市场监管、政策制定等宏观管理事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反映公众诉求、咨询建议、科普宣传、规范维权等方面则需更多强化民间组织的合作伙伴功能。
(二)完善民众参与机制中第三方主体的公正性
罗尔斯认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首要要求就是公正。社会公正由“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共同组成。“实质公正”强调动机、目的和结果的公正,“程序公正”强调途径、程序和流程的公正。[12](P292)居民参与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减少决策执行的对抗性隐患、防范权力寻租的可能,是实现结果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必经途径。在邻避困境中,矛盾的焦点经常集中于居民和政府对风险评估、预测和损失计量等细节方面的认知偏差,政府不是专业的技术部门,居民也不是技术专家,双方在具体事件中都是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的利益相关主体,因此,即使有居民参与下的政府决策也并不一定是最科学的,完善民众参与机制需引入第三方主体。第三方机构与利益相关双方均无利益关系,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居民科学性、技术性的不足,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猜疑和恐慌,在认知层面建设相互信任的话语体系,找到利益相关者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最终提高政策的公信度。
(三)树立经济与伦理兼具的制度化治理策略思维
公共行政的核心要义在于“公共”二字。“公共”表达的是一种伦理诉求和道德取向。对公共行政而言,“绝对他者”意味着对“少数”、对“弱者”乃至对“伦理”的尊重,而恰恰是“差异”、“少数”、“弱者”成就了行政的“公共”质素。[13](P171-174)公共决策部门不能对经济与伦理进行分割式理解,理所当然地认为将邻避设施设置在社会弱势群体那里抵抗风险小、补偿成本低,而应在规划公共设施时,体现出人文关怀,避免制度性排斥。在决策论证时,摒弃“最小抵抗路径”原则,深度思考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在实现社会公平中的伦理意义,最大程度顾及环境正义和社会公平的逻辑关联。在化解冲突时,能关注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既不能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也不能以情感关怀替代制度正义。在治理策略上,把居民的价值情感诉求当作现实问题予以重视,构建面向城市弱势群体的政治吸纳机制。[14](P47-51)
(四)强化伦理约束与循法治理相结合的政策执行力
纯粹从主观的角度无法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化解邻避困境需要伦理的内在约束,更需要法律的外在约束,只有将公认的环境伦理法制化,违背环境伦理道德的行为才能真正消减。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但涉及邻避设施建设和补偿的法律法规甚少,很多地方以“办法”、“规定”、“实施细则”等处理邻避事件,一方面缺乏法律的硬约束,另一方面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制定的规则也不尽相同,难免会出现政策漏洞。因此,有必要在整合现有文件规定的基础上,出台国家层面的法律,只有将邻避困境预防和化解过程置于立法与司法的监督下,才能避免行政权专擅,真正提高居民参与民主的功效。当然,法制的完备并不必然就能避免邻避困境的发生,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必须相互配合、共同行使方能奏效,否则采取“体制外”的行动仍将长期以民众无奈而有效的诉求方式存在。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徐晴晴.城市发展中邻避困境及解决之道[D].济南:山东大学,2013.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汤汇浩.邻避效应: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居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11,(7).
[5]Woo Lai Yan,Lam Kin Che,Fung Tung,Lai Pong Wai,Lee Wai Ying.UnderstandingPublic Opposition to NIMBY Facilities: A Review.In: GlobalGeographers’Meeting.高雄,2007.
[6]张艳伟.“不要在我家后院”——国家自主性视域下的中国式邻避冲突[D].上海:复旦大学,2011.
[7]陈明明,何俊志.中国民主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9]R.Gregory,H.Kunreuther,D.Easterling,K.Richards.Incentives policies to site hazardouswaste facilities.Risk Analysis,1991,(4).
[10]Hong J,Jung M-J,Kim Y-B,et al.Analysis of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at the Environmental-Adverse-Effect Zone of a large-scale waste landfill site.Journal of Material Cycles and Waste Management,2012,(4).
[11]杨秋波.邻避设施决策中公众参与的作用机理与行为分析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2.
[1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伦理学[M].胡其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4]张向和.垃圾处理场的邻避效应及其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
【责任编辑:赵 伟】
D669.3
A
1004-518X(2015)02-0187-05
安徽省软科学课题(1302053072)、安徽省省级教学团队项目(2010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