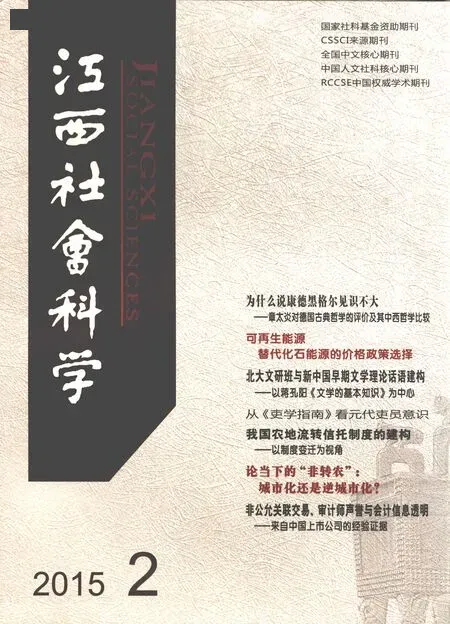陶渊明经典化过程的三阶段
郭世轩
陶渊明经典化过程的三阶段
郭世轩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生前在文学界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主要以隐士著称。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在去世很久之后才得以确立,而作为著名诗人乃至伟大诗人的美名是在宋朝确立的。可以说,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在经典化过程中,他的深刻内涵是逐步被发掘与认同的。道德、文章与境界分别成为陶渊明接受过程三阶段的关键词。
陶渊明;经典化;道德;文章
郭世轩,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皖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安徽阜阳 236037)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及其人生轨迹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自南朝以来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可以说,陶渊明已成为说不尽的永恒话题。之所以如此,源于陶渊明本人及其诗文创作的独特魅力。千百年来,能够赢得后世交口称赞的中国古代文人屈指可数,陶渊明则是其中的翘楚。
古人常常用“道德文章”来评价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名,这是一个尘世中人所能够达成的最高境界——圣贤境界。陶渊明以道德文章传世,被后世誉为“千古文人”[1](P119)。事实上,陶渊明无论是做人的道德还是传世的文章皆做到极致,无可挑剔。正如朱熹所言:陶渊明在官场自由出入,欲仕则仕欲隐则隐,毫无挂碍,一派天真自然,了无做作之迹。说不要是真的不要,不像晋宋时期的其他人物,犹抱琵琶半遮面。[1](P75-76)在陶渊明这里,既然不能成为官场的达人以兼善天下,那就只好归隐田园,独善其身。保身全性,身心自由,即使忍饥挨饿,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这种独立不羁的精神成全了他的自由人格和冲淡风格。陶渊明做人如此,作文也是如此!他以几近本色化的语言抒写田园生活,以质朴“无文”的形式表达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以边缘化的立场捍卫“田家语”的独特声音,以纯朴率真的姿态书写绚丽的人生华章。在这里,陶渊明是道德文章堪称一流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独立不羁的人格、独善其身的道德成就了“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1](P30)的文章,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诗意人生境界。正因为如此,道德、文章与境界分别标识着陶渊明经典化的心路历程。
一
道德文章在陶渊明身上是合二为一的。他始终以边缘者的立场成就田园写意的人生与朴实无华的文章。生前,他主要以隐士著称,成为江州地区知名的“浔阳三隐”[2](P333)之一。这虽与后世的文学史书写有很大出入,却代表着当时的文化界与文学场域对陶渊明的部分认同。其中有理解但更有误解,有发掘但更有掩藏。
在整个南朝,隐士身份是他的社会识别码,而作家的身份一直处于隐性状态。相比之下,道德脱颖而出成为凌驾于他文名之上的徽标。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隐藏着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极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门阀世族文化霸权所带来的压制与遮蔽。江州文学集团主要由下层文学、僧侣文学、田园文学所构成,其成员没有主流发言权和话语权。即使作为江州文学集团的优秀代表,陶渊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学地位。他只能与汇聚在江州柴桑的下层文人、归隐田园者、暂居者和文学过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交流也仅仅局限在下层封闭的小团体内进行,难以抵达京师上层文学集团和文化中心。来自于京师文学集团的成员颜延之也没有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看在眼里。按理说,他与陶渊明的交游主要集中在陶归居田园之后约五十三岁和六十岁的两个时间段内,前后约一年半左右。此时,陶渊明的主要创作及其代表作皆已完成。但在颜延之眼中,二人在江州柴桑的友谊仅限于饮酒,可以谈政治、性情等话题,就是很少谈文学。因此,在陶渊明逝世之后,颜延之的纪念文章《陶渊明诔》透露的主要内容就是身世、交情、性格、品行、操守和道德,关于他文章的评说仅有“文取指达”[2](P269)四字。
另一位宋代文坛领袖谢灵运来过江州、到过庐山,甚至还给慧远写过碑铭,与陶渊明近在咫尺,却擦肩而过,未有任何交集。如果说颜延之代表的是宫廷文学细密雕琢的品位,那么谢灵运则代表的是与之近似的模拟山水的贵族与名士文学的品格。他们都是陶渊明文学道上的歧路人。另外与陶渊明交往的江州刺史刘敬宣、王弘和檀道济等权臣皆不以文学名世,因此仅仅作为朝中高官权贵完成征召和礼贤的使命而已。无论是真正的欣赏与崇尚或者是职位使然,拜访陶渊明或与陶渊明发生交集并由此产生的逸闻趣事更加凸显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反而遮蔽了他那卓著的文名。
齐梁时期的文坛领袖沈约在他撰写的 《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纵论刘宋时期的文学家,却始终没有陶渊明的名字。这不能责怪沈约,主要还是与前代的历史书写、文学家传记书写的倾向性与资料性密切相关。齐梁之际对陶渊明有所倾心者有鲍照、江淹。他们分别从精神气质、文学风格等方面予以追和与模拟。
作为齐梁时代的文坛领袖,萧统出于仁者之心和被搁置的太子的压抑处境,为陶渊明的高尚美德所吸引。“读其诗,尚想其德”,“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精神境界恰恰能够安慰他那被压抑的青春之心,引起精神与心灵的共鸣。《文选》虽给人“高评低选”的阅读印象和审美偏向,但破天荒地将陶渊明收入文学家的名录。
与之同时,年长于他的刘勰和钟嵘的表现则呈现出天渊之别。《文心雕龙》呈现出文学史的视野,纵论作家数百人,时间跨度上千年,但唯独不见陶渊明的名字与身影。可以说,刘勰使陶渊明消失在文学史的迷雾之中,彰显出大家的盲视,成为后世龙学爱好者的遗憾与纠结。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复杂的,但文学趣味、政治倾向等的差异是其中不可否认的因素。钟嵘能够突破时代成见与审美偏见,名正言顺地将陶渊明收入诗人名录,并在《诗品》中给以中品定位。这在当时与后世都激起不同凡响的异样回声。可以说,钟嵘是在“辩论”中为陶渊明“正名”的,《诗品·宋征士陶潜》就是在为陶渊明一辩。尽管这种声音在当时是微弱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却为后世的研究者准备了足够重视陶渊明的资料。在后人看来,《诗品》美中不足的就是给陶渊明、曹操和曹丕等人的地位较低。
综合考量南朝的官方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南朝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集中在道德层面。这既与当世浮华绮靡的文风有关,也与朝野上下文人官员道德缺失的严重状况密切相连。因此,在南朝,陶渊明文名不显而德性彰显,足以慰藉时代焦虑、弥补道德缺失。
二
进入唐代,文人作家关注陶渊明的声音稍多,陶渊明的身份也主要由隐士转向诗人作家,关注的焦点也由道德层面转向文章层面。从时代论,隋代到初唐和盛唐时期,陶渊明受关注的程度逐渐呈递增状态。隋代诗人王绩对陶渊明初步认同,但主要还局限在道德层面、归隐田园上,具有过渡性。“初唐四杰”无暇关注陶渊明,其他的诗人更少问津。此后,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是主要关注者。孟浩然在文学风格、田园题材以及隐逸品格上对陶渊明予以极大认同。王维在田园诗风、田园趣味上有着一定的认同,但在隐逸志向上颇有差距,其中不乏指责声音。李白崇仙服道,过着诗酒剑侠式的生活,虽有强烈的功名利禄之心,但心中有着极好的把持,不能越过人格底线:折腰忍性,有辱人格。相比较而言,李白是从文学精神与人格独立上认同陶渊明的,属于深层认同。
进入中晚唐直至五代时期,由于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之久的军阀混战和晚唐时期的黄巢起义,盛唐如日中天的局面一去不返,日薄西山的悲观情绪和末世氛围始终笼罩着中晚唐诗人。整个时代精神也自然由“宁做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昂扬向上转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 《乐游原》)的消沉沮丧。杜甫具有初步转型期的中唐特征。他经历盛世与乱世、盛唐与中唐,生命体验更为丰富复杂。他处身盛唐具有很强烈的功名利禄思想和忠君爱国观念,同时饱经战患,寓居西南,虽远离政治中心,但忧国忧民情结浓郁。盛世成为他困境中坚守与憧憬的安慰剂,乱世使之忍辱负重期望大唐能够东山再起,隐居西南使之能够过上安居乐业、安时处顺的田园生活。因此,杜甫在卜居成都浣花溪之时,对陶渊明有着较为深入的认可。唐代在贞元 (785—804)和元和(806—820)时期,政治和文化全面转型。“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3](P256)白居易、韦应物、储光羲、柳宗元、李商隐、郑谷、司空图等人对陶渊明产生较为强烈的认同。
大致说来,中晚唐诗人主要从文章风格、田园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学习陶渊明,初盛唐铺张扬厉的南朝余风逐渐为深沉内敛、淡薄蕴含的诗风所取代。杜甫之所以成为江西诗派的鼻祖就在于它具有过渡诗风的气质与特征。同样,元和时期的元白诗派、韩孟诗派走的是实用化、平易化之路以实现诗歌对现实的干涉。尤其是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力倡古文运动的韩愈“以议论入诗”的倾向开辟了“宋调”之先声。在这方面,元和诗坛恰恰对陶渊明有较大认同。白居易走的是平易通俗之路,与陶渊明有着交集,并自认为是陶渊明的知音。储光羲、韦应物和柳宗元在风格与诗风上更接近陶渊明,因此赢得苏轼等人的好评。其他诗人虽声称学陶、尚陶、拟陶,但仅得其皮毛,遗神留貌,徒具形似。即使对于柳宗元来说,如果没有甘露事变而遭贬之经历,恐怕他也和其他唐代诗人并无区别。正是改革失败使之一再遭贬,从彩云之巅跌至万丈深渊。这种政治阶梯和人生境遇上的巨大落差,使之深刻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人生的崎岖、人性的险恶和名利的虚幻,从而淡泊名利、安时处顺、认同田园与边缘,使自己逐渐退去轻狂与张扬、学会低调与自安。正是这种人性的练达与诗性的体验才成就柳宗元的深刻孤独与人性超越,逐渐与陶渊明的境界靠近。至于晚唐时期的隐士诗人对陶渊明的膜拜更是趋之若鹜。
唐代诗人之所以聚焦于陶渊明的文章尤其是诗歌,主要源于如下因素:其一,两税法的实行拓宽了寒门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入仕之路,减少了魏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垄断性,士人与诗人更加切近贫民生活,对陶渊明更易产生认同。其二,李氏王朝引老子为上宗,力倡道家哲学,间或崇尚佛家,相对忽视儒家哲学,直接影响着士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建构,为接受陶渊明奠定思想基础。其三,在“外功”与“内养”失衡的语境下,陶渊明在士人心中若隐若现:得意时忘却,失意时亲近。其四,山水田园诗派队伍的壮大既源于寒门士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也在审美情趣与文学品味上逐渐靠近陶渊明。甚至在“立功”语境下壮大的边塞诗人一旦在现实功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仍然皈依老庄、认同陶渊明的审美趣味。总之,唐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集中在文章层面。“渊明鄙俗翁,未能达大道”[1](P18),这说明杜甫在道德与境界上未必能够理解陶渊明,在唐代很具代表性。
三
到了宋朝,政治军事与文化文学等方面皆发生极大变化。鉴于唐亡的沉痛教训,重文轻武成为宋朝开国君主的首选。赵匡胤 “杯酒释兵权”的高明就在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高的收益。这一军事策略不仅直接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与文化建构,还对宋朝的历史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政治上,削弱相权、剥夺将权和不杀文官,极大提高了文人的政治待遇和生活俸禄,使得宋代文人在高雅与通俗两方面皆得到极大的发展。广开入仕渠道使士人从政做官的道路更加宽广。文官队伍的扩大和俸禄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得有宋一代的哲学、史学、文学与美学等获得空前的发展,赢得后世著名史学家的高度称赏。开放、自信与创新的宋朝人不仅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深厚而丰富的精神文明。政治上的清静无为鼓励着文人士大夫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宋代理学广泛吸收儒释道三家的理论资源并加以综合创新,形成独特的新儒学,成为继魏晋玄学之后的第二个具有创新性的哲学形态,具有哲理性、思辨性、人文性和现实性等特点的宋学对宋代文学产生着重要影响。一改唐人注重外在事功和横向发展的模式,另辟蹊径的宋人则走内敛型和纵向型发展之路,由唐人的注重意象与感兴转变为注重意趣与涵养;文化品位也由青春阳刚、动态激昂渐入中年深邃、静态思量。这种文化语境极大地改变着宋代文人的思想与信仰。
陶渊明之所以获得宋朝士人的广泛认同,主要与宋代哲学和文学密切相关。宋六家对陶渊明都有很高的评价,尤其是苏轼最为明显。考之宋代诗人,凡是喜爱陶渊明者,皆在晚年时期。这一点从梅尧臣、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再到王安石、曾巩,直到陆游、朱熹,概莫能外。成熟期的宋代文学思想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崇尚清旷、追求理趣和老境美。由于时代语境和作家生存处境的关联,陶渊明在某种程度上与宋代文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遇合与共鸣。宋代文人的心态深受儒、道、释的影响。儒家使之高蹈济世、悲时悯世、期盼有为,道家使之注重全身自保、隐忍以行、厚德载物,释家使之心灵内视、精神充足、德性满溢、修身养性。而当壮志凌云的激情遭受打击与阻挠时,释家与道家的思想资源足以化解心灵的冲突与煎熬。从整体来看,除了宋初开国君主有心北伐之外,其余的君主皆忍辱自保、贪生苟安。整体主静、退让内敛的社会心态助长了主和派和保守派的气势。而志士仁人看到报国无门并遭受接踵而至的打击之时只能在内心化解,转向佛老祈求内心的宁静与平衡。因此之故,在宋代文人作家身上,豪放与婉约、入世与超世、外向与内向看似矛盾而又极其和谐的心态并行不悖地呈现出来。另外,宋代帝王对僧侣和道家的褒奖和优待,也极大地刺激了僧侣队伍和道士集团人数的激增。儒士之外文人队伍的存在间接诱发着士人的出世之想与心灵安慰。庞大的文官队伍和丰厚的物质待遇无须士人真正出世,公务之余也可做朝隐的“居士”。
在这种情况之下,陶渊明不愧为宋代文人的最佳选择:既能安慰心灵,也能享受高雅,更能在免受贫穷压迫的语境下抵达人生的至境:闲静淡远、身心安泰,简约生活,气定神闲。这种心态决定了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达到空前的盛况,在接受中加以深刻阐释与深度发掘,奠定陶渊明不朽诗人的地位。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陆游,无一例外。即使在宋代理学家那里,陶渊明的认可度也是极高的,从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真德秀,一致首肯。其中最突出者数苏轼和朱熹。这两位异代的学者在学术等方面对立但在对陶渊明的评价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也许是宋代文人浓厚的危机感、迟暮感、苍凉感与忧患感[4](P324-328)促使二人走向深度认同,超越集团偏见和门户之私,在境界与趣味上达成空前的同一。“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苏轼《东坡乐府》卷下)“神交久从君,屡见今仍悟。渊明作诗意,妙想非俗虑。”(苏轼《和陶咏二疏》)“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1](P35)事实上,苏轼不仅仅在评陶诗,而是在推崇其人生境界。“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1](P74)“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1](P35)“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1](P76)朱熹尚友陶渊明的是人格魅力与淡泊境界。由此可见,陶渊明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赠答诗》)的人生态度,“不戚戚于贫穷,不汲汲于富贵”的人生境界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诗学境界强烈地吸引着宋代文人学者,才产生人生境界的认同和审美体验的共鸣。
因此可以说,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语境和内忧外患的人生处境,使得学养深厚、忧患意识浓重的文人志士超越文章与道德层面直抵生命本质和人生境界,对陶渊明产生心灵喜悦与深情认同。正是宋人的独特视角才奠定陶渊明伟大作家与诗人的崇高地位,引后世无数学者文人的共鸣与崇拜。其中不乏过度阐释之嫌,却是内心纯正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化权威尤其是文学大家对陶渊明的极力推尊,极大地奠定了陶渊明伟大作家的经典地位,为后世陶渊明审美接受及心理定位提供了难以超越的范式。至此,陶渊明经典化历程已经完成。其后的金、元、明、清和现代文人在接受陶渊明的主题选择上无出道德、文章和境界这一藩篱。尽管每一时代由于政治环境、作家处境、文化氛围和审美风尚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接受主题方面基本在这三者之间徘徊:或偏于道德,或偏于文章,或道德、境界合论,或三者兼顾。金元两代作家在易代之际饱受家国存亡的耻辱之后,对陶渊明的接受着眼于道德、境界和人生出处的选择。“独立”、“真淳”、“明志”等成为评价他的常用语。“屈原之爱君,周子之明道,陶潜之明志,林逋之隘狷,能法四贤足矣,又何他求为耶?”[1](P122)“余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明君臣之义而已。”[1](P125)到了明代,汉人重新掌握国政。由于承平日久的盛世状况和宋明理学教化思想的全面控制,于是对真性灵和真性情的追求直接制约着文章的审美趣味。此时对陶渊明的接受倾向于文章、境界和理学 (道学)。“陶靖节诗,如展禽仕鲁,三仕三止,处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异于俗,而动和于道,盖合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1](P132)“陶公心次浑然,无少渣滓,所以吐词即理,默契道体,高出诗人,有自哉!”[1](P137)“靖节无一语盗袭,而性情溢出矣。”“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然已兆唐体矣。”[1](P153)清朝建立,满族入主中原,易代之际,民族气节和独立人格又成为突出的论题。加之清代文化上专制化与集成化的特征,因此,道德、文章、境界成为论陶的关键词,陶渊明接受呈现出综合集成的倾向。“抑文生于志,志幽故言远……千秋之诗,谓惟陶与杜可也。”“陶靖节诗……中多灵境。”[1](P180)“论隐逸者,不难于承平之时,而难于异姓之代。……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者,其亦以识胜也夫。”[1](P181-182)“靖节为晋第一流人物,而其诗亦如其人,淡远冲和,卓然独有千古。夫诗中有靖节,犹文中之有昌黎也。”“陶渊明世称诗圣。”[1](P260-261)“五四”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相互交战,境界、自然和性情成为论陶之主调。针对朱光潜等京派文人的“静穆”说,鲁迅提出强势质疑,并认为他“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 ‘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1](P286)。
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声名定位不仅仅取决于创作本身,还与时代的审美风尚、文人的接受心态以及政治文化生态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综合制约着对一个作家作品的评价与定位。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作家所创造的文本内涵与价值。因此之故,作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与奠定只能靠作品说话,这是超越时代地域与世俗权利的唯一确证。事实证明,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经典化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并在时空的考量中经得起考验。这也为当代作家的创作以有益启发:只有用心写作,深情体验,才能无愧于时代与人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应有的智慧与深情。陶渊明对今人的启示即在于此。
[1]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上、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王镇远,邬国平.清代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责任编辑:彭民权】
I206.2
A
1004-518X(2015)02-0092-06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晋宋时期的文学传播与陶渊明的经典化历程”(ahskf09-10d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