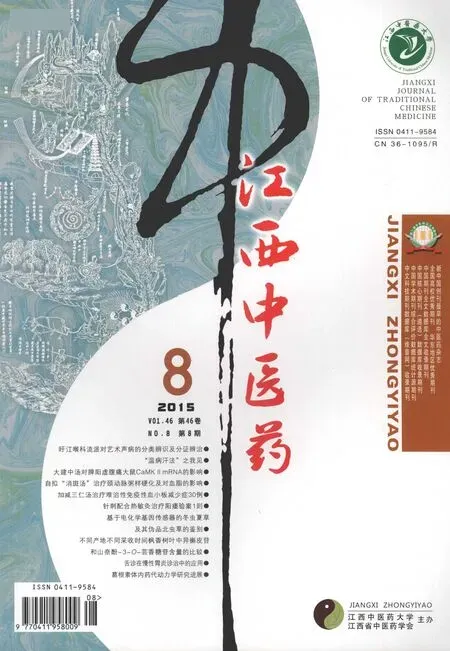关于血浊的理论浅析
★ 李茹 刘德山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03级硕士研究生 济南500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医科 济南500)
血浊与现代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随着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现代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血浊理论的提出,为中医临床治疗许多现代疾病如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痛风等疾病提供了思路[2]。笔者仅从血浊的定义、病机、及其与血瘀、痰饮、浊毒的相关性等方面进行论述。
1 血浊的定义
“浊”字的含义散在于古籍中,一是指不清、不干净,《释名·释言语》云:“浊,渎也,汁滓演渎。”《篇海类编·地理》云:“浊,不清也。”二是指混乱,《吕氏春秋·振乱》云:“当今之世浊甚矣。”不清、不干净讲的是液体的构成与形态,混乱讲的是指液体运动的顺序。血浊的含义,正如王新陆教授[2-3]所言:浑浊是血的物质构成发生了变化,混乱是血的循行发生了紊乱。血浊是指血液受体内外各种致病因素影响,失却其清纯状态,或丧失其循行规律,影响其生理功能,因而扰乱脏腑气机的病理现象。
东汉王充在《虚道篇》中说:“夫血脉之藏于身者,犹江河之流也,江河之流,浊而不清,血脉之动,易扰而不安。”可以看出血浊可以导致不同的疾病。血浊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4]。血浊作为病理产物,多是指饮食精微过剩(或因饮食过于肥甘厚味;或因脾气虚,不能散精),蓄积脉道(如糖浊、脂浊、蛋白浊、微量元素浊)。作为致病因素,多是指在血浊的基础上进一步生成和演化为血瘀、痰饮和浊毒。浊邪堆积超越了机体的自净能力,则发为疾病。如糖浊堆积可导致糖尿病,脂浊蓄积导致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
2 血浊的病机
关于血浊的病因,与当代人类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密切相关,关于病因在相关文献中已论述详尽,故不再赘述。血浊的病机可归纳气虚,关键是脾气虚。如祝谌予教授所言的“气虚浊留”[5],脾气虚弱,健运失司,无力运化输布饮食精微(糖、脂、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各归其所(脾不散精),精微蓄积过量而为浊,(糖浊、脂浊、蛋白浊、微量元素浊)[6]。脾虚,健运失调,精微物质不能被机体代谢,故蓄积脉道,血浊始成。另外,气虚鼓动无力,则气滞,气滞加重血浊,导致血瘀;脾为生痰之源,脾虚痰饮亦生。
3 血浊与血瘀、痰饮、浊毒的相关性
3.1 血浊是血瘀的前期状态 血浊、血瘀是一个逐渐发展的演变过程,血浊是血瘀的前期状态[4]。中医对血的认识分三类,一是血虚;二是血瘀,血瘀又包括血行迟缓、血行停滞和离经之血;三是血热迫血妄行。至于血浊一方面描述的是血行迟滞,血脉失其濡养功能,为血瘀形成前的一种状态。《医经原旨·脏象》言:“血浊不清而卫气涩滞也。”浊邪沉积血中可致气涩,气涩则血流缓慢形成血滞,血中有形成分黏聚,即可形成血瘀[7]。
3.2 血浊是痰饮形成的危险因素 血浊形成,蓄积脉道日久,可阻碍津液的正常输布,聚生痰饮,《景岳全书·痰饮》云:“津液者血之余,行乎脉外,流通一身,如天之清露,若血浊气浊,则凝聚而为痰。”痰邪又可加重浊邪的沉积,并可酿生浊邪,加重血浊。《张氏医通》云:“其饮有四,……始先不觉,日积月累,水之精华,转为混浊。”
3.3 血浊、血瘀、痰饮杂糅郁结为浊毒 血浊在脉道蓄积过多,不能及时有效地排出体外,如王永炎院士[8]所言:如有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体内的生理和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过多可转化为毒。痰和瘀在血浊的基础上进一步生成、演化和加剧,三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浊、痰、瘀均为阴邪,重着粘滞,易相互杂糅为病,其形成的复合物近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浊毒”之邪,其以血为载体,可以随血液运行到全身各组织器官,发生异位沉积,导致各种现代疾病,如肺纤维化、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非酒精性脂肪肝、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肾纤维化、多囊卵巢综合症等[9]。血浊逐渐从功能性病变转化为器质性病变。
4 临床应用
随着人类保健意识的增强和现代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诸多疾病在未出现典型临床表现时即被确诊,并给予生活方式或药物干预,其自然进程被打断,临床上出现了无症可辨的情况。如消渴病(此处特指2型糖尿病),起病缓慢,多数患者在偶然查体中发现血糖升高,并无“三多一少”及消渴病相关症状,现代医学中不同类型的降糖药和胰岛素注射液的普遍应用,血糖控制相对稳定,典型症状较少出现,疾病的自然进程被延缓;高脂血症,多无典型的临床表现,诊断依据为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实验室指标;这些情况的出现,对中医“病证结合”的辨证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导师刘德山教授认为“无症可辨,血浊为先”,王新陆教[10]授提出血浊的基本治法——化浊行血,并拟化浊行血汤(路路通、虎杖、荷叶、焦山楂、决明子、赤芍、酒大黄、何首乌、制水蛭)加减论治,用药体现了芳香化浊、苦寒化浊法。并根据临床辨证的不同,分别加以行气、清热、散寒、祛痰、补虚等药物施治。
5 小结
当代医家越来越重视“浊邪”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地位。但关于浊病、血浊、血浊病的病因、病机和治则三者是否有重叠部分,是否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论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另外,血浊与血瘀、痰浊、浊毒等相关性的表述也比较含糊。总之,血浊理论的临床适用性日渐凸显,通过血浊理论可以实现一部分疾病的“病证结合”。至于理论的完善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
[1]王新陆.关于血浊理论在现代疾病谱中作用与地位的探讨[J].天津中医药,2011,28(5):355-357
[2]王新陆.论”血浊”与”治未病”[J].天津中医药,2008,25(3):177-180.
[3]王新陆.脑血辩证[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25-28.
[4]王兴臣.再论血浊的病机和致病特点[J].山东中医杂志,2008,21(11):729.
[5]董振华,季元,范爱平.祝谌语经验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41,43.
[6]季春林,郭蕾,佟志,等.气虚浊留与浊病[J].中国医药指南,2009,7(18):38-39.
[7]韩萍,周永红,王新陆.血浊致病理论初探[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6):457.
[8]王永炎.关于提高脑血管疾病疗效难点的思考[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7,17(4):176.
[9]董志,王述文.试论浊病病机[J].光明中医,20111,26(3):421.
[10]王新陆.血浊证的辨证治疗[J].山东中医药杂志,2007,2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