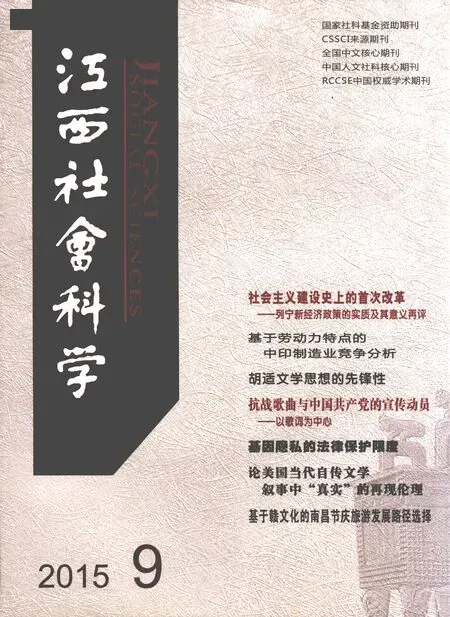从吴昌硕论书诗看其书学思想
■于 洁 吕金光
吴昌硕(1844—1927),名俊、俊卿,初字香朴或作香圃,后改为苍石,中年改为昌硕,别号甚多,常自署缶庐、老缶、苦铁、芜青亭长、五湖印丐等,浙江省安吉人。吴昌硕自幼随父刻印,通训诂之学,同治四年(1865)中秀才后,专攻金石篆刻,曾以幕僚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保举安东县令,一月后辞官,因此他自刻有“一月安东令”之印。光绪三十年,吴昌硕加入创始西泠印社的活动,七十岁时,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社长,晚年定居上海。著有《缶庐诗》四卷、《缶庐别存》[1]。吴昌硕的书学思想除了在其文章和书法实践中有所反映之外,其成就颇高的论书诗亦能从另一方面反映他的书学思想。
一、从论书诗看吴昌硕对碑学的继承
吴昌硕是继阮元、康有为、包世臣后的又一碑学重镇,相对于其书画印的盛名,很少有人从其诗歌的角度来对其书画印进行深入研究。诗歌能简明扼要地表达作者的意愿,也能表明诗人的文人身份,起到巩固其社会地位的作用。吴昌硕诗书画印中诗集最早出版。齐白石与吴昌硕一样重视诗歌,著有《齐白石诗集》。而被徐悲鸿尊称为“画圣”的任伯年,因为不会作诗,其艺术感悟虽不比前两位差,而其在艺术界的地位不及吴、齐,被归为画匠的行列。因此,任伯年的艺术成就直到“五四运动”、西学东渐、通过日本学西方的画家们掀起对造型的表现、对文人画的批判之后,才得到认可和提高。而林散之更是直白地在自己墓碑上铭曰:“诗人林散之墓。”在画中题诗才被列入文人画,说明诗歌是文人身份的标签,从论书诗入手阐释书家的书学思想,意义重大。
从吴昌硕的论书诗可以看出其继承了碑学家对帖学辗转失真弊病的否定态度:“黄庭禊帖无真本,小篆差能述相斯。兴发竟忘挥汗苦,素师蕉叶折来时。”[2](P103)诗中明确表明了他的观点:《黄庭经》与《兰亭序》都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质疑帖学鼻祖的地位,指出帖学的墨迹流传甚少;学小篆取法李斯还是可以的,北碑则是存留下来的原石,具有保存那个朝代真实书法风貌的优势。他承接了碑学奠基人康有为“即如《兰亭》《圣教》,今日之烂熟,致诮院体者”[3](P796)的观点。吴昌硕同样认为清代帖学的衰微与刻板的学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吟诗媿我力不足,饿隶还坐羲之俗。”[2](P111)《晋书·王献之传》 中将“饿隶”代指王献之,以枯瘦之状来形容王献之,将二王都列入俗的行列。对“二王”的评价之低,不言而喻。可见吴昌硕的碑学思想根深蒂固。
吴昌硕十分推崇从篆分入手的碑学大家何绍基:“蝯叟笔势高崆峒, 寸莛若撞 門音 巨钟。”[2](P194)吴称赞何绍基笔势险峻。诗中的“崆峒”是《庄子·在宥》篇中黄帝道广成子之所,可见吴昌硕将何绍基的书法当做追摹的对象。他也十分赞同何绍基的笔法。何绍基有论书诗《猨臂翁》:“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园空。以简御烦静制动,四面满足吾居中。李将军射本天授,猿臂岂止两臂通。……笑余惯持五寸管,无力能弯三石弓。时方用兵何处使?聊复自呼猨臂翁。”[4](P114)吴昌硕恨不能“耳聋足不仁, 蝯臂飞吾肘”[5](P315)。“唯蝯叟书天下褒,鲁公骨气淩秋豪”,“但愿蝯叟入梦兼鲁公”[2](P194),吴昌硕希望能够从何绍基处习到北碑的精髓,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创作中。
在清代,《石鼓文》受到碑学家们的追捧,康有为有言:“《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3](P785)而吴昌硕书法成就最高、功夫最深的就是《石鼓文》。吴昌硕把石鼓文作为第一法则,且不为法度束缚。他最初习小篆,参以秦石刻的原始气魄:“我藏泰山廿九字,自谓富比石季伦。此拓字数八十九,顾影遂觉南阮贫。”[2](P238)远取《泰山刻石》,近学邓石如、吴熙载、杨沂孙书法。在其四十三岁时得到潘瘦羊馈赠的石鼓精拓本后,《石鼓文》成为吴昌硕书法的主攻方向并以此为基变化出崭新的个人面目:
心仪文字十余载,思得翠墨悬环堵。瘦羊博士今斯翁,下笔欲剚生龙虎。谓此石刻史籀遗,伯仲虢般与曾簠。嫌我刻印奇未能,持赠一助吴刚斧。虽较明拓缺氐鲜,胜处分明露钗股。韩歌苏笔论久定,欧疑万驳辨何补。昌黎楮本今难求,有此精拓色可舞……清光日日照临池,汲干古井磨黄武。[2](P50)
吴昌硕对石鼓文字思慕已有十多年了,想得到之后悬挂在墙上观摩。相传石鼓文是史籀留下的,与《虢季子白盘》、《曾簠》不分伯仲。吴认为自己的印章不够奇崛,刚好通过石鼓文的摹写能协助他更深入地研究印学。最后两句是写吴昌硕临池学石鼓文很勤奋,将古井水汣干、黄武砚台磨破的情景再现。这版石鼓精拓本是1886
年瘦羊博士邀吴昌硕到虎阜,为倪云臞大令祝寿期间所见,使得吴昌硕亲身感受到石鼓文自然淳朴的气息,为其之后对石鼓文用功之深做好了铺垫:“倚汝作篆勿蹉跎,对十石鼓日摩挲,
蛇长蚓短功汝多。”[6](P227)吴昌硕对石鼓文下了很深的功夫,每天摹写,毕生精力尽瘁于此。吴昌硕对石鼓文书法的造诣极深,传承前人法度,但不袭陈规,逐渐形成气势磅礴、高古苍茫的独特风格,一扫碑学趋于僵化的颓败之风。
二、从吴昌硕论书诗观其“以碑入帖”的书学思想
相对于包世臣、康有为“崇碑抑帖”的碑学观,吴昌硕有其时代的进步性。吴昌硕倡导碑学,但并不排斥帖学:“羡君风格齐晋唐,书法遒劲张钟王。”[5](P281)他主张从帖学中汲取精髓,为书法自我风格的形成添砖加瓦:“明珠作花翡翠叶,平生不识蜂与蝶。寒香不散深闭门,伴我闲临洛神帖。”[5](P104)蜂与蝶指趋炎附势的小人,《洛神赋》为曹植名篇、晋代王献之书写,后人常常把洛神和水仙联系到一起。诗中表现了诗人与水仙为伴恪守贞操的性情,也是吴昌硕平日不排斥取法帖学的真实写照。他见到董其昌真迹,称赞道:“香光妙笔写此赋,如见骥足淩空行。字大三寸气凝练,墨池风雨腾匹练。遐想悬肘挥汗时,蹴踏乾坤走雷电。一卷传世三百秋,爱玩真迹逾天球。”[2](P145)董其昌《天马赋》墨迹淋漓犹如天马在空中驰骋,字大三寸气势凝炼。这卷书作已有三百春秋,真迹像天球(玉名)一样珍贵。以上是吴昌硕对帖学的态度,虽不代表其主流思想,但对帖学能客观认识。吴昌硕打破了碑学家对帖学的忌惮,扫除了清代碑学体系建立以来碑学家学帖的心理障碍,进行了碑帖的融合及以碑入帖的实践和创新。
吴昌硕最具进步意义的碑学思想体现于其以碑入帖,以碑学笔法写帖,给行草书带来了崭新的生命。他是较早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以碑入帖的书法家之一:“强抱篆隶作狂草,素师蕉叶临无稿。”[2](P194)指出要打破字体间的藩篱界限。吴昌硕以篆隶笔意作草书,开辟了碑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境界。这较之于处在碑帖融合有障碍的碑学发展时期的何绍基具有进步意义。而吴昌硕所处的晚清,碑学已经站稳了脚步,碑帖融合成为大势所趋。《流沙坠简》的发现,打破了碑帖界限,由于它既是墨迹又是出土发掘,被碑帖两家所尊崇。吴昌硕对帖学的态度转变,其本质上是时代的进步性所决定的。
吴昌硕行草书主攻黄庭坚、王铎。“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波磔一一见真相,直追篆籀通其微。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2](P191)吴昌硕取王铎书法中“突兀”“险巇”之势,以篆籀气融入其中,石鼓文的淳朴稚拙与汉碑的雄浑苍劲被融会贯通在他的行草中,线条老辣,笔势奔腾,古意盎然,其任意恣肆的行草书在柔美静和的书风外另辟势沉力雄之篆籀格调,正是吴昌硕以碑入帖从理论到实践的佐证,体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独到的胆识和创新精神。他的艺术作品中所着重表现的即是浑朴苍劲、古朴雄秀的风格取向。
三、从吴昌硕论书诗观其“以书入画”的美学实践
清代早中期,在考据学大兴、金石碑碣大量出土加之文字狱压迫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致力于考经证史,金石学始兴,碑学随之繁盛。碑学的异军突起与金石考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书法作品中追求金石篆籀韵味蔚然成风。金石气是相对于书卷气而言,以“不失篆分遗意”为宗旨,指创作中具有汉魏碑刻、钟鼎砖瓦中表现出的苍茫古茂之审美取向。吴昌硕即是金石大家,其号曰缶庐并作《缶庐诗》:“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俯将持赠情独厚,时维壬午四月九。雷文斑驳类蝌蚪,眇无文字镌俗手。”从吴昌硕论书诗中可以看出,其书画印无一不是根基于自身的金石学素养之上,“平生恨未多读书,刻画金石长嗟吁”[2](P36);“读书我未数卷破, 刻画金石徒好事”[2](P76); 题跋中也提道:“我庐缶声出金石,剪烛烹茶恣谈艺。”[6](P3)对金石气的偏爱表达了吴昌硕透过岁月沧桑、历史冲刷后领略的斑驳朦胧、稚拙自然的审美观,是其对金石气率真的追求。
吴昌硕的绘画受到任伯年悉心的指导,后从朱耷、扬州八怪、徐渭画作中汲取营养,将书法中的用笔运用到绘画创作中。他书法上的良好素养在绘画中得到自然流露,其论书诗道:“临橅石鼓琅琊笔,戏为幽兰一写真。中有离骚千古意,不须携去赛钱神。”[2](P350)充分发挥了自己书法上的优势,以书入画,以篆书笔法画兰叶,有别于纤丽隽秀之态。其笔下的兰花朴茂淡雅,空谷幽深,是其不入俗流孤傲品质的象征,形成了独特的浑穆质朴、古拙烂漫的风格。吴昌硕也将草书流畅的线条融入创作中,变化万端。吴昌硕在《王仲山草书》中说:“试演草作画,梅竹荷芙渠。”[2](P192)以草书流畅的笔触表达内心的情感。吴昌硕明确地将篆书笔意、碑学笔法作为绘画上的塑造手段,其对不加修饰的真实美的追求,通过饱满的笔墨将有力的线条呈现在画面中。
吴昌硕以篆隶笔法写梅兰,以草书笔意作梅竹,布局纵横捭阖,笔力老辣,从而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坛大写意中影响显著的一派。书法风格影响了吴昌硕绘画的内蕴:“闲尝自言生平得力之处,谓能以作书之笔作画,所谓一而神、两而化,用能独立门户,自辟町畦,挹之无竭,而按之有物。”[6](P235)艺术上的变革使传统得到延续,吴昌硕以简练浑厚的笔触表现深远的意境,所画作品面貌朴拙而内涵生动,抒发丰富的情感。大胆地将西洋红运用到绘画创作中,色泽古拙艳丽,画面单纯明快,生机勃勃,内藏金石韵味,达到了艳而不俗的艺术效果。吴昌硕在西方绘画侵袭中国传统绘画领域时,突破了思想上的束缚,矫正了糜弱的画风,引领了新一代的风尚。其画作显示出中国传统画作持久的生命力,使得艺术风格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吴昌硕的绘画思想不仅受到书法的影响,更多的是源于诗书画印的综合文化修养。他将诗书画印融为一炉,互为贯通,从吴昌硕逝世那年(1927)写的诗可以看出:“书画篆刻,供一炉冶。诗通性情,浪仙东野。竹头木屑,不风不雅。”[7](P218)吴昌硕终其毕生的精力将诗书画印相互融合,精益求精。吴昌硕将篆隶笔意移入篆刻中,使得篆刻富有书写意味。书法借鉴篆刻的布局,其石鼓文有左低右高之势:“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刻画金石岂小道, 谁得鄙薄嗤彫虫。”[2](P9)“武梁祠画日日相师承,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2](P157)吴昌硕的绘画借鉴篆刻的构图、书法的线条、金石的气韵,以势取胜,使得绘画作品极具张力。诗中自然地流露出文人的气质与情怀,与书画印相得益彰。吴昌硕以古拙沉穆的篆刻为素养、苍茫浑厚的书法为内蕴、渲染情感的绘画为形式、纵横郁勃的诗歌为灵魂,共同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高古深远。
四、结语
吴昌硕艺术造诣发轫于金石,取法高古,书画参照,诗印相通,而这些成就主要源于他的人生感悟。可以说,吴昌硕的诗书画印是其品行的自然流露。其论书诗中常谓:“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2](P8)“画当出己意, 摹仿堕尘垢。”[5](P170)吴昌硕法古但不拘泥于古,不受传统的拘束,敢于打破前人的藩篱,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是他在艺术上取得辉煌的主要因素,也是他典型自我意识的展现。吴昌硕主张以古为新,强调作画的独创性。“板桥肯作青藤狗,我不能狗人其宜。”[5](P222)吴昌硕不愿和郑板桥一样做青藤(徐渭)走狗,匍匐在人脚下,而要自立风格,表现了他勇于创新的胆略。
通过对吴昌硕论书诗的研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位碑学大师的书学思想。此篇为抛砖引玉之作,期待更多的学者对其论书诗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1]邹涛.吴昌硕《西泠印社记》疑为沈石友代作[J].中国书法,2008,(9).
[2]吴昌硕.吴昌硕诗集[M].童音,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康有为.广艺舟双辑[A].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4]何书置.何绍基书论选注[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
[5]光一.吴昌硕题画诗笺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吴东迈.吴昌硕谈艺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7]刘海粟.回忆吴昌硕[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何绍基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