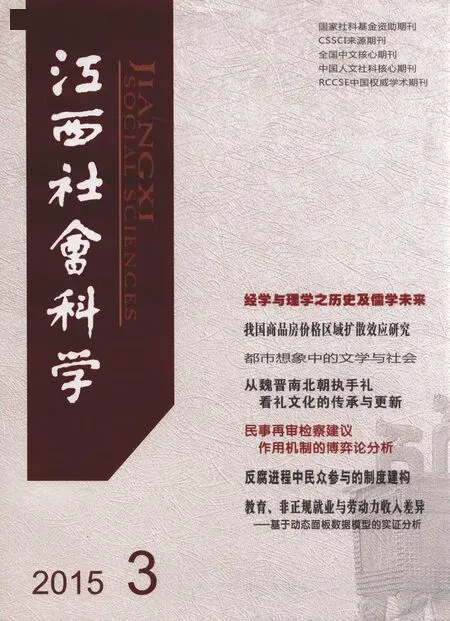比较文学“缺类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杜彬彬
比较文学“缺类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杜彬彬
“缺类”问题并没有在学理层面存在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缺类研究曾普遍关注的中国“无史诗”、“无悲剧”的问题,多是西方学者在研读中国文学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现象,也是近现代中国学者反思自身文学、文化传统的结果。当前国内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在对“缺类”问题的阐释过程中又将其消解,并不能与文化相对主义达成统一。另外,在当下语境中,文学类型划分理论所强调的历史性、反固定化,使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缺类”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索。
比较文学;文学类型;缺类;理论反思
杜彬彬,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上海 200234)
文类研究是中西方文学研究的传统。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开始,在经历古典主义对文类的固定化、浪漫主义对文类的颠覆,以及20世纪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理论对文类问题的关注之后,形成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类型及其理论。在中国,文类/文体①也无比繁复,风、雅、颂、骚、赋、诗词、传奇、话本、杂剧等,不一而足。当比较文学进入文类研究时,在理论上显示了其广阔的研究空间。在比较视野中,可以对不同文化语境中文学类型的内部发展肌理、审美心理等方面进行互释,寻找差异性和相似性。由于中西文类并不对等,“缺类”问题一直被中国比较文学界所关注,但是从21世纪以来的研究情况来看,以“中西文类比较”为选题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而以“缺类”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文章却很稀少。对“缺类”问题的研究在走过了“中国有无史诗、悲剧”的论题之后,理论和批评研究似乎式微。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比较文学进入所谓“第三阶段”之后,在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前提下,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缺类研究”?在考察“缺类”问题的提出、阐释策略和理论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考。
一、“缺类”问题提出的学术史考察与疑问
“缺类”问题并不是学者对比较文学理论阐发时所形成的学术共识。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来看,文学类型或体裁,是众多比较文学家不约而同关注的焦点,但对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学类型的“缺失”问题,却未给予太多相关论述。他们关注文学类型的问题,目的在于努力廓清世界文学类型划分方法的差异性,从而认识不同国家、民族文学类型的影响关系、演进规律和共同的存在方式。
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在他的《比较文学》中提出 “为什么法式悲剧不能在英国扎根”的问题。[1](P36)从表面上看,基亚提出文学类型的“缺类”,但实际上,基亚只是强调研究某种文学类型如何在另一个国家或民族中被接受、被改造的重要性,并没有明确“缺类”的概念。另外,法国的巴登斯贝格、布吕奈尔、梵·第根、布吕纳季耶,他们重在考察某种文学类型的历时性、共时性的跨越性影响,同样没有提到“缺类”。而美国韦斯坦因和俄苏学派对于文学类型和体裁的研究,或是希望达到建立一个总体文学意义上的“参照结构”[2](P120),或是探寻不同民族文学,包括文学类型,在诗学意义上“共同性”[3](P240),“缺类”的问题均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法国的克罗齐虽然提到“意大利没有悲剧”、“法国没有史诗”的问题,但他把艺术作品作为心灵和直觉的产物,反对刻意划分文学类型,从而也就否定了“缺类”问题。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并没有特意强调 “缺类”问题,而更多是他们在对中国文学的阅读、研究中所发现的现象。比如,黑格尔指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是因为中国人观照历史的方式是散文式的,而且中国人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史诗艺术的表现。[4](P170)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指出西方的历史和史诗都是按照编年的顺序结构的,是理智的;而中国历史学家却以抒情的方式对历史事实作分类和系统化,是感性和直觉的:这就是中国史诗不发达的原因。[5](P227-228)18世纪法国杜赫德以西方的文学观念为中心,认为在中国悲剧和喜剧也没有多少差别,目的都是劝善惩恶,并着重指出中国戏剧不遵守 “三一律”[6](P88),暗指中国悲剧文类是模糊不清的。至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没有足以在规模、精湛程度和形式灵活方面同西方悲剧相比的悲剧”[7](P172),虽是介绍“悲剧”词条时的一笔带过之言,但也认可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悲剧“不发达”的观点。这些对于某种文类“不发达”或“缺失”的指认,总体上是西方“自我中心主义”式的经验判断,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学理探讨。所以,华裔学者陆润棠在评论西方戏剧批评家穆勒所谓的 “中国人不可能产生悲剧”时,就认为穆勒只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而且“并没有表示这种缺乏是一种非常可惜的损失”。[8](P830-831)
但是中国学人对“缺类”的关注却比西方学者严肃得多。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进行全面审视和反思时,也在企图沟通中西文化,因此也就引起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9](P1)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指出中国古代无悲剧是由于未能表现“生活之欲”、“生活之苦痛”,其原因是“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10](P10)。这种“乐天精神”,致使中国戏剧“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没有“自律”的痛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一批学习了西方文化的学者,钱玄同、傅斯年、欧阳予倩、胡适、鲁迅等出于对救国救亡、推行新文化、批判国民劣根性,以文学为载体,进而反思我国民族文化和思想的薄弱,而“中国无悲剧”又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对残酷世界视而不见,创作者“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11](P122)朱光潜站在哲学和宗教的角度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就是世俗型的,比较注重伦理信念,对于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善恶自有因果,因此也就没有悲剧。[12](P191-192)
回顾这一学术疑问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学者所谓的悲剧不发达或缺失,只是基于思想文化层面的观照,更多地是以这个问题为载体,通过反思传统文化指出其疲弱之处,号召民众更新文化观念,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文类“本体”意义上考虑太多。19世中期到20世纪前期,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现实境遇,面对世界潮流的席卷之势,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国家落后,在他们讨论中国文学的“缺类”问题时,混杂着沉重的学术焦虑和文化焦虑。这种焦虑的表现内容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文学不能与世界对接,不能让中国文学在古代文论的论述框架中显示出普天同一的意义。[13]
我们可以推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比较文学学科之后,在比较文学理论中提出的“缺类”研究,是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对这一问题再次自觉、敏感性地把握,更是对前人学术疑问的继承。所以,从目前的比较文学专著来看,凡是谈到“缺类研究”的章节中,均会拿史诗和悲剧来作为例证,而诸如小说、散文、诗歌等文类所提很少或不提。
孙景尧和卢康华编著的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在明确提出“缺类”的问题之后,紧接着就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大规模叙事诗传统?为什么悲剧在中国没有希腊悲剧那种崇高地位?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有没有史诗?”[14](P181)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提出的“缺类现象研究”也同样是以中国有无史诗、悲剧的问题作为重要依据。还有,杜进主编的《跨文学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王福和、郑玉明、岳引弟编著的《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孟昭毅、黎跃进、郝岚编著的《简明比较文学原理》,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等也都是如此。
从中西文学类型的整体来看,如果把 “缺类”当作独特研究领域的话,悲剧和史诗的问题并不能代表其全部,但由于“缺类”问题恰恰缘于此,并且对这一问题的叙述多是一种经验式的,并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这就注定“缺类研究”不能显示其广泛性,更不能为其他文类的“缺失”问题拓展出相应的研究空间。所以,从对“缺类”问题的提出到目前比较文学教材、著作对“缺类”问题的描述,都有值得让人反思的地方。
二、“缺类”问题的描述现状及其消解
在当前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中关于 “缺类”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差异。一种认为,我们缺少了A,以及原因是什么;而另一种认为,我们缺少了A,或者我们有A的形式,为什么实质和表现形态和他国或民族的不一样。②第二种观点似乎包含着第一种,却存在着矛盾:既然叫作“缺类”研究,又何来“虽然在另外国和民族文学中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和内在的实质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呢?把某种“文类”在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表现形态也当作缺类研究,那么到底是“缺”,还是“不缺”?从词源角度来讲,既然是“缺”,就是没有、空额或不够,当然也就不会存在“虽然有”、“即使有”的问题。
从比较文学教材、著作中论述的“缺类”情况来看,缺类问题所引发的研究指向的是探析其产生的原因,但在论述过程中似乎又将缺类问题消解。
在当前众多中国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对“缺类问题”的阐释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也有悲剧”、“中国也存在史诗”、“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等的叙述。比如在杜进主编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中,为了说明缺类研究,从戏剧评论家穆勒提出的 “中国人不可能产生悲剧”的问题出发,引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和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的观点,以及钱锺书、姚一苇的相关论述,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中悲剧的“缺类”;但另一方面,又引用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有悲剧”的学理观念。那么这也就形成一个矛盾性的话语现状:到底中国有无悲剧,著者不置可否,它所激发的问题似乎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那么“缺类研究”到底要研究什么呢?以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为例,在本书“缺类”问题的相关章节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当比较文学研究从西方单一体系进入到中西文明对话的时代,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同一性研究逐渐被差异性研究所取代,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引起关注。比如说,中国古代有赋为什么西方没有?中国古代有没有大规模的叙事诗传统?”[15](P187)在他看来,“缺类”的存在是因为文明的差异,并涉及中国文学背后的社会意识、道德结构、哲学思维、美感经验、个人期望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似乎已经指明产生 “缺类”的原因,而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诸多方面”细化为具体的答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缺类研究”就是具体是指某种“文类”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中的表现形态及其文化的差异性研究,而“缺”这个词本身也已经变得无意义了。
一旦把“缺类”问题上升为文化问题,便会被大而化之,最后剩下“文化差异”这个宏大而具有复杂意义的答案。而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析,大多也只是基于文学经验的现象描述,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也不明确,总是纠缠在“有和无”的问题,而不去关注中西方在文类形态上的相互比较,虽然造成“缺类问题”的多声部讨论,却没有突破性的结果。对于中国悲剧和史诗的问题,其实有学者已给出答案③。对于“缺类”的问题,也有学者道出其中的矛盾和不可行性:
在上古时代交通隔绝的情形下,东西方各民族都以各自独特的智慧和审美体验创造出形形色色的文体,长短互异,不同之处比比皆是。倘须比较,必须通观全盘,深度理解,不能以某一个民族的文体模式去规范和评价另一个民族另具特点的模式。……对一些不可比较的特征,以一方为标准强作比较,生硬牵合,是否会给人削足就履之感?在平行比较中有所谓“缺类比较”,比如西方某些民族有史诗、有悲剧,中国古代没有或比较薄弱,那么是否也可以反过来提问一下,中国历史书中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典志体、舍委体、方域体、学案体,是否如此多的史学文体在西方哪个民族也那么完备?[16](P402)
三、跨文化、文化相对主义对“缺类”研究的困境构成
上引论述,已经点明文学类型的“缺类”问题不仅仅在于文类本身,而是其所承载的文学、文化传统差异性,这恰恰是当今比较文学“跨文化/文明”研究的内在要求。跨文化研究所提倡的 “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为了避免形式各异的文化中心主义,促进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设法去理解在这种文化中建立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不以另一参照系的框架去对之进行解释,而是要以“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的胸怀,来进行文化传播、接受、认识和感知。[17]但是当以这种宏观视野观照比较文学研究中的 “缺类”问题时,就使其陷入困境,也无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达成统一。
因为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牵涉的不仅是文学类型的名称、内涵和具体的文本指向,外在的文化场域及其生成机制也不可忽略,所以这种研究也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但是,我们对于“缺类”问题的敏感性指认,已经无形将我们的文类系统与“他者”摆在不平等的位置。他们没说“缺”,为什么我们“缺”了起来,难道我们的文类体系有先天缺陷吗?
中国古代的文类/文体丰富、庞杂,以至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分类。从汉代曹丕《典论·论文》中的“四科八体”,到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中对文体的三十四种分类和 《昭明文选》中的文体三十九种,以及宋代姚铉《唐文粹》划分的文体二十二大类……这些事实已经宣告中国文学自身文类的历史性、体系性。由此,再来反观所谓的 “缺类”,这似乎是对自身文类体系不自信的表述,带有对他者文类体系 “中心主义”的文化认同心理。赛义德认为:文化并不是仅仅用来标志一个人所属的某种事物,而是他拥有的某种事物,而在拥有的过程中,文化也指称一种边界,凭着这一边界,外在于或内在于文化的诸概念起到强有力的作用。[18](P14)具体到文学类型来说,它是生成于自身文化环境,每一种文学类型的定义或概念正是对这一文化、文学表现形态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并能够与自身文化相互印证。西方文学中的悲剧、史诗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 “边界”和文化上的“拥有”。如古希腊文化悲剧的产生与祭祀和歌队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古希腊人的科学和逻辑精神,使亚里斯多德对悲剧有了明确的定义;中国戏剧的产生则主要与民间说唱有关,带有娱乐的目的,悲剧和喜剧因素往往同时存在,因此我们没有对戏剧类型再作细致区分。“缺类”在如今看来,似乎并未考量中西方文类发展的时间性、不平衡性和文类传统的复杂性,而仅仅是在与西方文类的对照中得出的盲目性结论或定义,带有以“他者”为中心的色彩。这恰恰是比较文学“文化相对主义”原则所要克服的。
赛义德认为东方与西方在文化话语层面存在一种权力和统治关系。在他看来,东方并不是欧洲人的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是带有霸权意识的知识体系。[19](P6)要突破这话语统治力,必须建立一种适合研究的知识框架,如果粗枝大叶地忽视一切理论、体系和方法最终来源的条件,就会四处碰壁。对于文学类型研究来说,我们当然要在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前提下,实现文学间的平等对话,而“缺类”问题是与此相冲突的。它暗示着自我与“他者”的不平等性。厄尔·迈纳就曾尖锐地指出要避免“霸权主义的假定”,“认为西方的文学活动乃取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可以在另一文学中找出它的对应物,这种对应物有别于西方文学,足以证明它所处的从属地位”[20](P326)。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批判“缺类”问题,但认为寻找“文类的对等物”只能是相对近似,而不能绝对统一;只能是“比较的”,而不能是“相互对等”。因此,在跨文化视野中,在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文类比较研究重要的不在于是否“缺类”,而是要正视每一个文化系统中文学类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最终实现在文学内部的互动和文化差异性的认识。所以,“缺类”在跨文化研究的原则面前,处于一种困境之中,也显得没有意义。
四、现代文类划分理论不利于“缺类”研究
“缺类”的研究在当下难以进行,其背后隐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类划分理论的复杂性,使“缺类”问题的理论根基不牢。
西方文学类型从古希腊时期,就没有统一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文学类型划分的摹仿叙述、混合叙事、混合方式所依据的标准就不同:一种是叙事方式,一种是摹仿方式。黑格尔在浪漫型艺术中对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体诗的划分,依据的是人的内在观念表现的精神世界。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后,克罗齐、施莱格尔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文类划分,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属于一类。俄罗斯的卡冈又根据题材、认识容量、价值、形象模式对文学等艺术类型实行分类。[21](P391-405)这一事实说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文类划分的方法和依据不尽相同,所以整体上西方文学的文类传统从来没有统一过。
但是“缺类”研究的开展,意味着必须参照稳定性的文类系统。进入20世纪以后,文类划分理论的历史学、阐释学研究,使得文类的概念又处在“动态”之中,以此再来反观“缺类”,也就可以理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何难以开展。
美国的艾伦·R.科恩曾指出:“无论文类流传的时间是多么短,它都是历史的,它的文本存在于时间之流。一种文类的稳定性总是暂时的,因为一种文类中的不同样本或范例就可以改变它的目的。”[22](P191)法国的热奈特认为文学类型或体裁的划分都是每一个时期文学的内部机制作用的结果,是多元的,缺乏辩证性和完整性,而人们所发现的文类或体裁的“体系”虽然并非毫无用处,但充满了“虚假”和“空格”。[23](P34)即是说,类型或体裁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千变万化的,体系永远有照顾不到的地方——空格,在这些“空格”中可能会形成新文类,这也是文学类型划分不能固定的原因。
文学类型的划分在西方一直争论不休,并随着解构主义阐释学潮流,实施着“反固定”化做法。法国的让-玛丽·谢弗认为类型只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它与文本并不存在固定化的关系,因此文学的分类也没有一种“纯结构型分类”,并且文学类型的历史演化决定文本并不存在任何“种属”延续。而“类型”作为被下定义的词语,其外延是开放的,而内涵总是暂定的,不完全的,所以也“并不存在永恒的标准来确定一篇新的文本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类型”。[24](P424)这一解构主义、分析哲学式的阐释,使文本和类型的关系处在一种非固定化的动态关系中,就是说,任何类型的名称都是不必要的,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去界定某一特定文本的文类属性。从具体的文学作品来说,由于历史的发展使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不稳定的,作品、世界、读者以及和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也是变动的,另外文学作品的多维性也决定其属类的不固定。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就认为文学类型的存在决定于一种阅读的期待。比如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自然诗,经后世人的解读,发现了其中的生态思想,又被称为生态文学。所以,有学者就干脆提出了“文类是策略”的理论观点。[25]进入后现代时期,文学类型“超历史存在”更进一步消弭在生产方式、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谱系学当中,文学类型不存在特殊的护身符。如同文学类型的诞生,历史也常常宣判文学类型的瓦解,或者是部分地瓦解——只要条件合适。[26]
在这样的文学类型理论环境中,比较文学中的“缺类”研究难以开展可想而知。在文学类型处在“巩固与瓦解”、不断变动的情况下,“缺类”研究难以在固定的文类形态中进行,再加上理论的支撑难以取得,所以开拓空间就显得很小。
“缺类”这个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每个民族或区域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文化空间中都会形成特定的文类系统,每个系统生成的术语和概念以及所依附的思想体系、论证过程会有巨大差异,各种文类系统不可能一一对应,当然就不能冒然地说“缺”或“不缺”。例如在形式、结构、主题意义上,中国没有出现像西方文学中的悲剧文类,但是很多古代文艺作品中却蕴含着文人悲剧意识、英雄悲剧意识和女性悲剧意识。[27]这一部分作品其实也可以视为具有悲剧形态的文类。所以,中西文类“缺”或“不缺”并不是一个问题,而只是在文学类别的表现形态或存在方式的差异性问题。在当代语境中,比较文学的文类研究重要的是在文类特征、性质、身份、形态、生成等问题上,坚持跨文化研究原则,辨认其差异性和统一性,而“缺类”只是一个机械的、不合时宜的命题。
注释:
文体和文类,有具体而微的区分,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不再做详细的说明。在此仅指一般意义上文学的分类。
如王福和、郑玉明、岳引弟编著的《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认为“缺类研究”是指:“某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中所具有的某种文类,在另外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中却没有;某一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中所具有的某种文类,虽然在另外国和民族文学中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和内在的实质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另外,孟昭毅、黎跃进、郝岚编著《简明比较文学原理》认为缺类研究是:“研究一种文体为这个国家有,而在其他国家则没有,或者即使有这种文体的形式,而其实质或表现形式又相去甚远等。”这些观点,没有把“缺类”仅当作“为什么无”的问题,而是把同一文类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中的表现形态或实质的差异性研究也划入“缺类研究”的范围。
陆润棠在《东西悲剧文类比较》一文中认为,悲剧作为文类在西方本身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发展中的,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并不能按照西方的悲剧下定论。因此说中国戏剧史没有悲剧是武断的,只是追求一时诠释的方便而已。
[1](法)马里奥斯·法朗萦瓦·基亚.比较文学[M].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2](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史[M].四川:巴蜀出版集团,2010.
[4](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普实克.中国与西方的史学和史诗[A].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范存忠.《赵氏孤儿》在启蒙时期的英国[A].张隆溪,温儒敏.比较文学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7]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17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8]陆润棠.东西悲剧文类比较[A].约翰J.迪尼,刘介民.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9]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0]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77.
[11]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A].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13]林岗.二十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14]孙景尧,卢康华.比较文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5]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6]杨义,陈圣生.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7]乐黛云.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J].岱宗学刊,1997,(1).
[18](美)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M].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19](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韩少波,韩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1](俄)卡冈.艺术形态学[M].凌继尧,金亚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2](美)罗伯特·肖尔斯.结构主义与文学[M].孙秋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23](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4](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程锡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5]陈军.文类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07.
[26]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J].中国社会科学,2009,(4).
[27]朱志荣.论中国美学的悲剧意识[J].文艺理论研究,2013,(5).
【责任编辑:彭民权】
I106.9
A
1004-518X(2015)03-0088-0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三十年民族神话研究学术史”(14BZW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