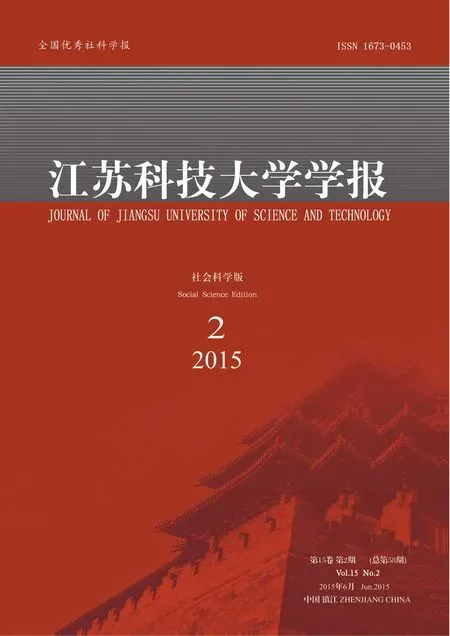《神秘的河流》中的“河流”书写
尤丽娜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外国语系,安徽 马鞍山243000)
凯特·格伦维尔(1950— )在澳大利亚享有盛誉。她的小说《神秘的河流》运用宏大叙事,真实再现了19世纪初英国早期殖民者在澳洲开拓疆土时与当地土著之间的矛盾与内心的道义冲突。该小说在2006年获得英联邦作家奖和澳大利亚克里斯蒂娜·斯泰奖,在国际上反响强烈。国内外对《神秘的河流》评论屈指可数,大都集中在种族、殖民、女权主义主题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王丽萍的《评凯特·格伦维尔的新历史小说》,她采用批判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方式来揭示《神秘的河流》的殖民意识形态。
《神秘的河流》既没有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情节,也无浮华铺张、瑰丽旖旎的语言,颇具极简主义文风。小说以类似圣经般的简洁语言描述了主人公索尼尔跨越英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度的生命历程:从幼年时期的贫困拮据到老年时期的功成名就;其间索尼尔经历了偷盗犯罪、流放赎罪以及在澳洲异域的艰苦创业。其中值得探究的是贯穿小说中的河流意象。因此,从个人心理空间的投射、社会历史的承载以及精神家园的构建三个角度来阐述河流意象的多重涵义,是揭示小说主题的必要途径。
河流意象至始至终贯穿文本,它既象征着人生历程,也象征历史发展犹如长河。河流是阿卡狄亚风情的诗意栖居地,是阿卡狄亚作为田园牧歌远离尘嚣的重要媒介。“河流来源于自然,它荡涤污垢,同时也是仙界与凡尘的交界。在神话故事中河流也是神居住的地方,是人类与神灵交往互联的通道。”[1]“阿卡狄亚不再是维吉尔牧歌中歌声缭绕的潘神之乡,而是一个新阿卡狄亚,田园牧歌也是那个幸福时代的最后余韵和不完美的替代品”[2]。
《神秘的河流》中的修饰语神秘,是指人对未知世界非理性的感知而引起的内心陌生体验,使小说透出远古阿卡狄亚气息,河流成了心醉神迷的福祉之国的代名词。神秘也有掩饰罪恶的意义。总体来说,小说中神秘的河流具有多重含义。在美学意义上,河流是远离尘嚣的重要媒介;在现实意义上,河流起到掩饰殖民者罪恶行径的作用;在哲学意义上,河流作为阿卡狄亚神话的象征来对抗现代文明启蒙。“神话时代的人类接近自然的方式是匍匐于自然脚下,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是人力所不能把控的,因此为了自我持存,他们采取的是顺从和模仿;而启蒙时代的人类以实验科学的方式来揭开自然神秘的面纱,他们得以愈来愈能够驾驭自然,为自己谋取福利。”[3]409启蒙不仅“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而且始终“带有极权主义性质”[3]409。神秘的河流在小说中是一个流动、开放的多重意义空间。河流更是化身为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牧歌对人类为中心的文明启蒙进行无限解构。主人公索尼尔毕生追寻的功成名就,实则是在世俗欲望中挣扎。因此《神秘的河流》既具备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牧歌元素,又有着天国与尘世的悖论,这使得小说与圣经形成异质同构的互文关系,充满文学张力。本文将把“河流”放在个人心理、社会历史、文化三个层面予以解读。
一、河流作为个人心理的投射与人生历程的象征
河流意象是主人公索尼尔的心理细节投射,河流挟带着索尼尔的意识呈现出不同景象。格伦维尔以小说主人公索尼尔为原型,塑造出开拓异域的英雄形象。荣格认为:“英雄原型的改变与救赎包含三种形态:一是英雄在经历长途跋涉(Odyssey)的考验中履行任务(quest),二是英雄在历尽苦难从无知成长(imitation)为完美的角色,三是英雄为了集体的利益成为牺牲的替罪羊(scapegoat)。”[4]242随着米德尔顿夫妇的离世,索尼尔夫妇生活陷入拮据,“索尼尔久久的坐在布尔码头,在汹涌的河水背后是另一种力量——大海……良久他心中的忧伤慢慢失去知觉,被忘却了。一切都能如此轻易破碎,还有什么好指望的呢?”[5]9这段文字从心理层面上描绘索尼尔梦想破灭后幼年心理创伤复现的情景。成年的索尼尔不计后果盗窃木材,表面上是想与萨尔过幸福生活,事实上是为了填充幼年心理创伤所引起的“碎片我”与“理想我”之间的鸿沟。索尼尔妄图在“熟悉与陌生,非家与家”的悖论中构建出完整的自我人格,以弥补幼年时期的心理分裂[6]。在索尼尔的潜意识中体现为“忘却式记忆”:“幼年压抑的情绪在不经意的记忆中以一种无意识的、隐秘的方式复现。”[7]巴塔耶认为:“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欲望一直就处在主体和符号的掌控之下,它才能够得到设想的地位,无论主体是根据意识和理念得到设想还是根据无意识得到设想,欲望一直是渴望填充,渴望再生产的残缺之物。”[8]索尼尔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英国社会的显赫身份、地位和名誉,毕生都在世俗世界的欲望机器中挣扎,成为尘世欲望的牺牲品。
河流意象也是索尼尔人生历程的象征。《神秘的河流》以主人公索尼尔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涵盖了索尼尔晦暗悲惨的童年、艰辛漂泊的青年与异域发迹的成年。从伦敦的泰晤士河,到澳洲的不知名河流,河流陪伴索尼尔一生。弗莱认为,“河流原型象征着死亡与重生、救赎、时间的流动、生命的阶段、意识的流动”[4]263。格伦维尔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贫民窟的悲惨生活。河流对岸的风景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冰冷无比,感觉不到上帝的仁慈”[5]10。河流意象在这里不是神灵的化身,更不是具有救赎洗礼功效的天国圣水,而是索尼尔晦暗童年的写照和生命历程的惨淡开端。格伦维尔笔下的河流不像马克·吐温小说中浪漫唯美的世外桃源密西西比河。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贝利乘坐木筏逃离丑陋衰败的陆地,来到象征着宁静自由的密西西比河,河流对哈克贝利进行灵魂上的救赎与洗礼。《神秘的河流》中的索尼尔因为贫困和饥饿产生求生欲望,铤而走险偷盗木材从而锒铛入狱。索尼尔青年时期在河上做雇工,贫困使得他“像只野兽耷拉着脑袋,自己像是断了手臂,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空虚感,憎恨的对象只能是河风和潮流了”[5]46。索尼尔和妻子萨尔因盗窃罪被英国政府流放到悉尼,开始了他们在异域的艰辛创业。这是索尼尔的成年阶段,河流也逐渐变得明朗宽阔:“亚历山大号抛锚在一片波光粼粼的水域,水面上波光点点,明亮炫目。”[5]71由于妻子萨尔的努力和英国政府的赦免,当索尼尔看到澳洲的河流时,“他用手拭去脸上温热的眼泪,道道光线照得他眩晕”[5]71。与青少年时期在英国伦敦看到湍急的水流、瞬息万变的潮汐相比,索尼尔名利双收的晚年时期看到的河流变得平静开阔:“天色已晚,风停了,河面平静的像一块玻璃,山崖在河岸边耸立着,倒影在水面飘散开来,交相辉映,宁静而完美。”[5]328河流意象的运用,不仅为索尼尔看似圆满的人生历程增添了历史沧桑感,而且与行文中的阿卡狄亚风情形成异质互文关系。
二、河流作为社会历史空间的承载者
在《神秘的河流》里,河流意象除了象征时间流动和个人心理意识流动外,它还代表着对时空的穿越。作者以索尼尔的人生历程来构建历史话语移动空间,索尼尔从英国伦敦到澳大利亚的空间旅程湮没在河流之中。格伦维尔以去中心的态度来解构英国主流社会话语,同时建构作为“他者”的非主流社会阶层。索尼尔在与米德尔顿签下立约学徒时就与河流结下不解之缘。当索尼尔跟随着米德尔顿先生来到水运人员大楼时,他觉得“模糊地理解了人们的排列方式,一个在另一个之上,从最底层的索尼尔一家这样的人直到最高层的国王或者是上帝,每个人都站在别人的头上,又被别人踩在脚下”[5]25。这是索尼尔最初对社会分层的朦胧感知。接着索尼尔接受政府官员的盘问,“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来回答。由于米德尔顿经常让他划船,他的手掌还没有消肿,不过不流血了。他一言不发的伸出双手”[5]26。这是索尼尔处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失语状态,他的生活轨迹只限于泰晤士河,对于上流社会人士来说,“船夫不过是自然风景的一部分”[5]26。索尼尔因盗窃木料被流放至荒凉的悉尼湾,经过艰辛创业开始在悉尼湾拥有自己的领地和船只,并且开始雇佣仆人。当索尼尔面对来自英国本土押送犯人的职员萨克林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自尊顿时被击得粉碎。接着萨克林“挥着手把索尼尔往后赶,好像索尼尔是条狗”[5]166。索尼尔作为土地主的满足感顿时荡然无存,“转瞬之间,杰克逊港口所有的荣耀又一次变成了监狱,中心附近的城镇变成他幼年时期的恶臭之地,他的心中一处旧患开始隐隐作痛”[5]166。这是索尼尔又一次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幼年心理创伤的复现。在宗主国盗窃入狱的污点随着河流延伸至澳洲的悉尼湾;过去的创伤不经意间在各种当下复现。索尼尔的失语状态,是由英国本土社会的压抑造成的,日后在澳洲如幽灵般复现。这种心理以一种忘却式记忆方式隐秘的存在。时刻感受到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是幻觉投射在索尼尔微观心理的一种感受。
河流意象除了具备穿越空间连接英国泰晤士河与澳洲悉尼湾的功能,还赋予其解构功能。当索尼尔以罪犯身份乘坐“亚历山大”号来到悉尼湾的临时居住地,“叫喊声冲击着他的耳膜,他从未想到有如此毒辣的太阳,他有了晕船的感觉,觉得脚下的土地在不断地膨胀,太阳敲击着他的头骨”[5]76。悉尼湾上嘈杂的声音与混乱的场面,预示着索尼尔日后在澳洲的命运。索尼尔怀着梦想来到澳洲,就像清教徒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他们企望按照圣经的意旨恢复失去的天国,在荒野中缔造伊甸园——上帝之城。”[9]索尼尔的最初理想被残酷现实撕扯得支离破碎。随着索尼尔开拓领地的深入,他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陷入道义与事业的两难抉择境地。特别是索尼尔举起屠杀当地土著的枪时,他就陷入了永远的道义谴责。索尼尔在澳洲煞费苦心缔造的天国实质上是建立在对当地土著居民的驱逐、迫害、屠杀基础上的。“启蒙是人类借助理性和科学从迷信、愚昧、神话世界的魑魅魍魉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走向澄明、理性和开放,使人们由此而逐渐摆脱恐惧与困惑。”[10]英国政府在澳洲宣布悉尼湾“成为忠诚的拥护者英王乔治三世的扩张领地”[5]71时,高高飘扬在澳洲的英国国旗,实则是殖民地扩张与掠夺的标识,也是对人文底线的破坏和对阿卡狄亚神话的解构与颠覆。格伦维尔用下层殖民地的非主流话语和去中心的姿态,对英国上层社会主流历史叙事话语进行了解构。在索尼尔对当地土著进行一场血腥屠杀后,公报上刊登文章来粉饰这场血腥的屠杀:“当地黑人们掠夺和残暴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当地发生骚乱,居民们把黑人们都赶跑了。”[5]317英国公报把索尼尔的血腥暴行粉饰成保卫领地的正义之战,索尼尔后来试图以英国的语言、服装来教化当地土著注定以悲剧告终。霍克海默认为:“与神话相比,启蒙是更为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他的目的是使自然完全失去魅力,彻底变成可供主体意志投射的对象,致使启蒙走向了新的巫术,更走向了同化、统治、独霸。”[11]格伦维尔通过“边缘叙事”手法形成一个沉默、错乱的跨界(in—betweeness),以此解构英国主流话语,把殖民地非主流话语纳入到英国历史时空下,从而揭示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启蒙是对以河流为代表的田园牧歌神话的彻底消解。
三、河流作为精神家园的构建
河流意象在小说中也是精神栖居地的象征。格伦维尔创造性地把个人欲望和精神家园杂糅在一起,用家园文化来对抗英国与澳洲殖民地异质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压迫,通过带有阿卡狄亚元素的河流来质疑、消解文明启蒙所宣扬的由理性、知识、主体构建的天国理念。奔腾不息、穿越时空的河流意象具备了多重意义:悲伤与欣喜、认同与质疑、自我与他者。河流成为格伦维尔书写精神家园的意象。
在《神秘的河流》中,精神家园分为两类:一是索尼尔和他妻子萨尔的爱情家园;二是以索尼尔为代表的殖民者与澳洲土著黑人的家园理念。索尼尔与萨尔之间的爱情有着田园牧歌表征。在索尼尔初识萨尔时,河流呈现出阿卡狄亚的唯美景观:“天高云淡,有一大片水域,还有水鸟的叫声,他喜欢那里的空旷,喜欢被微风吹拂的感觉。”[5]18从伦敦的泰晤士河到澳洲的悉尼湾,索尼尔和萨尔的爱情如同河流一样平静,偶尔会溅起一些水花。这与阿卡狄亚神话中唯美浪漫的爱情如出一辙。但是河流宁静的表面下面却是暗流涌动,索尼尔与萨尔婚后被流放至澳洲,索尼尔与妻子萨尔发生了冲突:萨尔希望攒够钱就回伦敦,而索尼尔把自己的理想天国定位在了澳洲异域:“他和萨尔会为了后半生日子不停进行无谓的争执,萨尔不会留下,他也不会离开。这就像就绳子上的死结,拧的像个攥紧的拳头那么结实。”[5]295最后直至索尼尔参与了一场对当地土著居民的血腥屠杀,才彻底解决了他与萨尔的根本矛盾:不会有黑人再来惹麻烦。索尼尔在澳洲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甚至拥有自己的领地,却与妻子萨尔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和萨尔的关系有了莫名的微妙变化:“丈夫和妻子之间出现了一个沉默的空间,有些事情谁也不愿意提,这些事情就像一团阴影。”[5]318虽然他们依旧恩爱,依旧像伊甸园的古朴爱情,但是在这个他们无法表达的沉默空间中,“就像河边的无花果树盘在岩石周围扎根一样,他们俩的生命围着这个空间慢慢生长”[5]319。澳洲殖民地的开拓过程,也是妻子萨尔逐渐被父权社会压抑直至失语的过程。萨尔在英国伦敦营救丈夫索尼尔时还是一个聪明、活泼、勇敢的姑娘,但是到了索尼尔事业越做越大的时候,萨尔的生活区域却逐渐缩小至家庭范围,接触的人也只限于孩子与自己的丈夫,直至成为一个失语的影像。阿卡狄亚田园牧歌式的爱情几乎都是以皆大欢喜为结局,而《神秘的河流》中索尼尔与萨尔的爱情无疑是对阿卡狄亚牧歌爱情的揶揄与嘲弄,也是阿卡狄亚神话祛魅化的过程。索尼尔对澳洲的开发过程,也是对女性的征服过程。索尼尔对当地土著黑人女人更是如此:“当那个黑女人摇晃着往外走,索尼尔看到鞭子抽到她的背上。她站在那里,手里举着拴在脚上的锁链。”[5]245-246英国白人居民把黑人土著女性视为与自然界类似的、被动的、低劣的、非理性的群体,理应服从富于理性的男性。殖民者缔造出来的伊甸园女性与自然界河流,都遭到父权制的压迫与物化。
在《神秘的河流》中,殖民者不仅对女性与自然界的河流进行贬抑,而且对当地黑人部落同样充满歧视与压迫。作者借索尼尔之眼描述了黑人们在营地“聚会狂欢”的情景:“火光让他们看起来很不真实,就像一堆舞动的网状光线……他身上的肌肉强壮有力就像水流中的鱼一样舞动,他双脚跺地的声音就像土地脉搏,歌声悠长回转仿佛是这片土地血液中的声音”[5]238。格伦维尔通过陌生化手法,描绘出自然精灵般的黑人在营地舞动的阿卡狄亚景象,与英国白人冷酷的等级制度和贪婪自私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狂欢的精神内核,“其一是重视对话,其二是多重性,其三是强调相对性”[12]。狂欢化的内涵与阿卡狄亚神话如出一辙。格伦维尔运用阿卡狄亚神话的作用有三点:其一是对白人叙事话语进行消解,重新审视一直处在失语、边缘状态的黑人;其二是重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多元对话;其三是格伦维尔对启蒙教化行为持否定态度,并且对英国殖民者开拓澳洲的历史进行解构。格伦维尔采取不偏不倚的暗恐式叙述,努力还原那段隐秘的殖民历史。她通过对土著黑人在营地里面狂欢景象的描写,以对抗被西方文明所掩盖的殖民行为。小说以河流领地为中心,以白人殖民者与当地黑人土著对于家园理念不同的诠释为线索,以黑人土著黯然离开自己领地而告终,白人殖民者最终将英国文明启蒙思想带到澳洲来构建他们所谓的天国。索尼尔在澳洲建立起自己的领地并获得当地人尊重,但是他的非家幻觉依然如影随形。这种感受使得索尼尔在澳洲建造酷似家园的景观,大至伦敦的建筑,小至屋内摆设,包括花园的植物。这些都是他家园意识投射到流放地的类像,并且这些类像会无穷无尽地复制。因此,索尼尔毕生追求的理想家园也只可能无休无止地在天国与尘世的理想类像中替补。
综上所述,《神秘的河流》既拥有历史厚重感的后现代写实小说特质,也具备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牧歌元素。其河流意象展示出万花筒般的多维空间:个人心理空间的投射、社会历史空间的承载以及文化精神家园的构建。个人心理空间的投射解构了阿卡狄亚式的开拓异域英雄原型,揭示出世俗世界的欲望机器是埋葬个人理想的坟墓;社会历史空间的承载消解了现代社会文明思想启蒙功能,展示出文明启蒙是对田园牧歌神话的彻底清算;文化精神家园的构建颠覆了白人精神栖居地理念,批判了英国与澳洲殖民地的异质文化对性别、种族的压迫。这种解构性的河流书写,不仅对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牧歌特征进行了嘲讽,使得文本与作者意图形成悖论诗学关系,充满美学张力,而且揭露出西方人文主义启蒙思想蜕变成极权统治的本来面目。格伦维尔以此反思殖民扩张的思想根源,质疑白人中心论,提倡性别、种族的平等对话。
[1]孙胜杰.原型批评视角下文学作品中“河流”的救赎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3(12):106-107.
[2]杨宏芹.牧歌发展之“源”与“流”——西方文学中悠久文学传统 [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6-25.
[3]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JUNG C G.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4):263.
[5]凯特·格伦维尔.神秘的河流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6]NORTHROP F.Anatomy of criticism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287.
[7]JAMES S.“The uncanny”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J].London: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1981:156
[8]GEOGE B.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M].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187.
[9]HENRY N S.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76.
[10]DAVID R.Art and enlightenment[M].Nebraska: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2.
[11]MAX H.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M].New York:Seabury Press,1974:9.
[1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