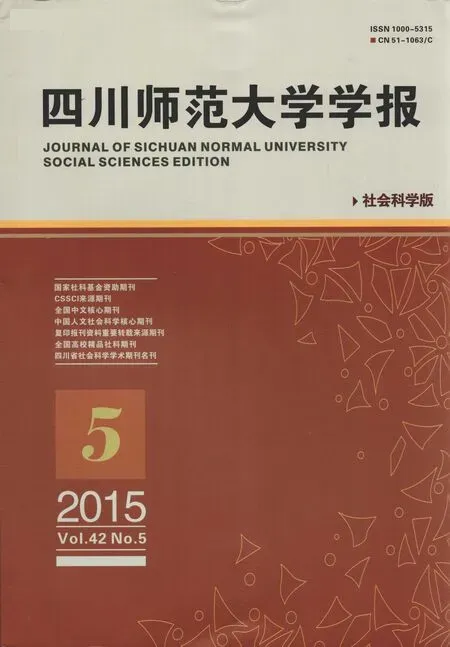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
徐 碧 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
徐 碧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后期最重要的学说。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从“人生在世”即“人活着”这一事实出发,以“实践”、“行动”(“做”)联结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度的智慧和来自西方马克思的实践观念,把一种本是纯西方的学说(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一脉即儒家哲学相结合,构造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即“情本体”理论。情本体成为实践美学最终的落脚之点。“情本体”理论的思想基础仍是实践哲学。它一方面是对李泽厚80年代的“内在自然人化”、“心理本体”学说的具体化和深化,另一方面又吸收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关于仁-孝的思想。它的主旨是探讨个体面对强大的不可预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如何把握自己的偶然性,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本文主要以《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论语今读》、《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哲学探寻录》等论著为主,对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的内涵进行一些梳理和分析,从五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情本体的生活实践基础:“做”的哲学与“度”的本体性;二、情本体的世界观:“巫史传统”与“一个世界”;三、情本体的伦理内涵:礼仁分疏与两种道德的建构;四、情本体的核心:人性情感的塑造;五、情本体旨归:“立命”与个体主体性的确立。
关键词:情本体;李泽厚;实践美学
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后期最重要的思想。从“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的美学到“儒学四期”说,到“情本体”理论,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从“人生在世”即“人活着”这一事实出发,以“实践”、“行动”(“做”)联结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度的智慧和来自西方的马克思的实践观念,把一种本是纯西方的学说(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一脉即儒家哲学相结合,构造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即“情本体”理论。“情本体”概念在李泽厚的论著中首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系列提纲,但真正对之展开阐述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哲学探寻录》、《论语今读》、《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等论著之中。“情本体”的思想基础仍是实践哲学:一方面既是对他80年代的“内在自然人化”、“心理本体”学说的具体化和深化,另一方面又吸收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仁-孝思想的内核。从早期的实践美学强调工具本体和群体主体性的决定性作用,到情本体理论以个体主体性为中心,探讨个体面对强大的不可预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时如何把握自己的偶然性,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李泽厚的美学完成了由外而内、由社会的物质性实践向个体的心理情感层面的拓展和深化,回应了他在《美学四讲》中“回到感性”的呼唤。关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理论来源、核心概念“实践”、“自然的人化”、“人自然化”、“主体性”、“积淀”等问题,笔者已有过专著和多篇论文探讨。这里,笔者试图主要以《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论语今读》、
《哲学探寻录》等论著为主,对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的内涵进行一些梳理和分析。挂一漏万,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请李泽厚先生和学界同仁批评。
一 “做”的哲学与“度”的本体性——情本体论的生活实践基础
李泽厚认为,与西方哲学强烈的思辨性不同,儒家学说是在人生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去体会或践履的。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不是“太初有言”,而是“太初有为”、“太初有道”,即中国哲学强调在实际行动、践履过程中形成人对世界的把握:“中国是‘太初有为’‘太初有道’(行走),因‘此道’而有‘情’:情况之情,情境之情,如周易所言‘类万物之情’。由此客观的‘情’‘境’而有主观的‘情’(生活感情)‘境’(人生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主题脉络。”[1]183人与世界在这“为”的过程中相遇,从而产生了主客两方面的“情”:客观方面的“情境”和主观方面的“情感”。因此,对于儒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理论的抽象,而是行动。一部《论语》,便是孔子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处理客观的“事情”所形成的主体对此事情的应对和“情感”的记载。对待同一个问题,孔子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境和对象而有不同的回答,显示出强烈的实用理性和智慧。而这一点,正好与马克思强调人在实践过程中塑造自身、社会在实践过程中完成建构的思想相吻合。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费尔巴哈提纲》等著作中反复指出,人的“类本质”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自由自觉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人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2]273-274。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在自由自觉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这一点,中国学术界曾经反复讨论并达成了共识。在这里,无需再多说。也许正因如此,李泽厚早期多引用马克思的论说来证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性,说明美的本质属于人的本质,美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而后期,当进入“内在自然人化”,具体论述作为“内在自然人化”的成果的“情本体”时,李泽厚更多从传统儒家学说中获取理论和思想资源。
由此,李泽厚赋予《论语》中的“学”以一种实践性的内涵。在他看来,“学”在《论语》中并非单纯学习知识或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为人”、学“做事”,亦即是一种人生实践的学习和践履,因而,“学”与“做”实际上便是一回事。并且,因为人生本是在学习与践履即“实践”中展开的,知识、经验、技能、交往等亦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因而,这个“学”便具有了指向人生本体的性质。“我强调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有不同于神性和动物性的人性(human nature),人之所以拥有动物所没有的各种能力情感,是人类自己通过历史和教育创造出来的,人造就了自己。人之所以能如此造就,是因为‘学而第一’。”[3]9
由此,李泽厚对《论语》首章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作个体独存也。‘人不知而不愠’,则虽群却不失个体之尊严,实在与价值也。此三层愈转愈深,乃‘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作为《论语》首章,不亦宜乎。”[1]29-30此处似确有过度阐释之嫌,却不无深刻与启迪。杨伯峻《论语译注》释“习”为“实习”,亦即实际去操演、练习作为当时社会生活中重要内容的礼、乐、射、御:“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学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讲为实习为好”[4]1。这种“实习”便是践履、行动、“做”。
因为人生在实际的“做”之中完成,它永远是一个“学”的过程,因而如何“做”就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在人生实践过程中,掌握“度”的分寸,无过无不及,允执厥中,恰到好处地处理人生各种问题与难题,便成为重要的智慧。正是在大量的操作实践中,人们把握了“度”。在对度的把握中,人作为操作行动的主体与对象之间产生了韵律、节奏、对称等等造型力量上的感应与契合,从而产生了内外两方面的美:外在方面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所产生的“自然的人化”,内在方面则是由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的人化产生的“内在自然的人化”,即情本体。由此,“度”成为实用理性的关键词,具有了“本体性”。
“度”是无过无不及,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它首先是人在操作——劳动——生产中为实现目的应用规则而达到的成功,从而维系、延
续了人的生存、生活、生命。但在这成功的操作实践中,人的主观心理上所相应的感受,却不仅是目的达到的成功愉快,而且还有与个体运动紧相连接的肢体感受的愉快。……正是在这种有节奏、有秩序的操作实践中,人开始拥有和享受自己作为主体作用于外界的形式力量(forming force)的感受。这即是说,节奏等等形式规则成了人类主体所掌握、使用的形式力量,这就是所谓“形式感”(the sense of form)的真正源起。……从外在能力说,这是人类由使用——创造工具所获得而拥有的技艺,即“度”的工具——社会本体力量在诞生和扩展;从内在心理说,这是构成人性能力的心理——情感本体力量的诞生和扩大。这便是人的“自由”的开始。[5]2
由此,李泽厚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智慧契合无间地结合在一起,以实用理性的度的智慧诠释了实践美学对美和美感的本质的理解。在这个解释框架下,人生在世(“人活着”)成为理解的起点。由这个起点出发,人的实践活动(“做”、“行”、“学”)便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由这一基本事实生发出人对世界的掌握——“度”的智慧。“度”在客体方面是一种形式力量,在主体方面便是“形式感”。“形式感”正是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产生或形成的,它不但减轻了主体身心的劳累,而且因主客体的契合而逐渐形成美与美感。比如劳动号子使劳动成为一种有节奏的过程,这种节奏使得劳动不再是单调的疲累与折磨,在某种意义上,它使劳动变成了一个美的创造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美学坚持美起源于人改造世界的劳动实践活动。换言之,正是人主体方面的机体和对象世界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一种“融会吻合”,使得主体的机体在节奏、韵律、对称、平衡、顺序等等方面产生形式美感。这样,情的两个方面,客体方面的“情境”、“事情”,主体方面的“情感”,便成为相互联系的自然人化的内外两方面的体现。
二 巫史传统与“一个世界”——情本体论的世界观
与西方明确区分出现象与本体、尘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的“两个世界”观不同,在中国,天、地、社会、个体本是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之中,即所谓“天人合一”。西方自柏拉图开始,就设立了一个位于现象世界之上、之外,与现象世界相隔离,并且是现象世界的本源,亦是其本体的理式(idos)。这种现象世界与理式世界相互隔离,且理式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使得西方自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向基督教的一神教转化顺理成章。自中世纪以来,上帝(God)、绝对精神、物自体、Being、Logos等等成为西方哲学中世界的最终的依据、最后的解释,人间世界及其道德准则的根源——亦即哲学的“本体”。在长达千年的一神教统治下,关于超越于人世界之外、之上,支配人间的神的思想,成为西方根深蒂固的深层思维模式。即便启蒙运动大力宣扬无神论和唯物论,关于上帝创造世界、死后的永生问题、天堂与地狱等等观念仍十分有市场。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一个超越性的神成为生命与生活最终的价值与意义的依据。人不但向神奉献,还可以吁求神的保护与救赎。李泽厚把西方文化的这种世界观称作“两个世界”,即神和人分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系统。人间世界受神的支配与统治,人要服从于神。另一面,神也保护人。人哪怕处在最孤苦无依时,也可以通过祈祷神恩救赎来获得内心的平静,从而得到心灵的慰籍。
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在中国,文明的源头处,一开始,就存在着强大的巫术传统。在这种巫术世界观里,人可以某种方式沟通自然(天)与人(社会),宇宙、自然、社会、人处在一个系统中运行,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整体。人与神、天与地、自然与社会都处于同一法则规律的统治之下。因此,不存在某种与人隔离的超越性的神灵,人有大小事情也勿需求告某个看不见、感受不到的神祉庇佑,而是通过自己的德行与智慧、以自己的实践作为去顺应天地自然的存在,从而赢得自己的幸福。
在中国,也有“天”的观念。儒、道都讲天。但中国的“天”不是高高在上并且支配人类命运的“上帝”(God),而是一种“天意”、“天命”。所谓“天意”、“天命”,一方面是宇宙自然的某种法则、规则,独立于人而存在,但另一方面,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实践、道德、智慧去理解、把握并进一步利用这种“天意”,从而使得“天意”与“人意”处于一种奇妙的互动状态。人如果能自我修养、自我克制,品德高尚,配得上“天”,“天”就必然会眷顾人,照应人,便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反之,人如果强作妄为,逆天而行,就会受到惩罚,地震、火山、干旱和洪涝等灾害便是上
天对人的警示。另一方面,人的意志、行为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还可以干预“天命”,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因此,“天”与“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截然两分,而是就在一个相互联系、影响、作用的系统里。
李泽厚从不同角度多次论及中国的“天道”观念与西方“上帝”观念的区别。
“天主”是唯一神,即使强调不能有人的外在形象,却总有拟人的意志、语言和教义,祂全知全能,发号施令,创造世界,超越经验,统治一切。它是超人类经验的实体或本质存在。“天道”则不然,它虽拥有不可预测难以违抗的功能、神力,却从不脱离人世经验和历史事件,而成为某种客观理则但又饱含人类情感的律令主宰。始终没有发展或接受全知全能、至高无上、人格性唯一神的天主(God)信仰,却产生和延续着含有规律性、律令性、理势性意义在内的“天道”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思想史上最早、最重要也最具根本性的心理成果。[6]403
他总结中国的天道有三个特征:“第一,‘天道’即‘人道’。因为‘由巫到礼’和‘礼’作为‘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天’‘道’‘天道’的宗教性也就与作为‘人道’的政治、伦理直接攸关。”[6]404-405“第二,与此相关,‘天道’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就是包容性和灵活性。由于‘天道’具有‘神’的无限法门而又朦胧含混,便可以作出多种可能性的解释。”[6]406“‘天道’的第三个特征是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直接昂扬。……由于没有绝对的极端畏惧崇拜的对象,没有不可变易的铸定命运威吓,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从而便可以更主动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现实生存和世间生活。”[6]408-409
天地自然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行,四时更替,万物生灭,气韵流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什么超越性的神可以依恃,没有来自自身之外的超越性力量的神恩救赎或依靠,一切全靠自己,从而形成中国文化独有的悲凉特色。不是忧乐圆融,而是一种深刻的忧患与豁达的乐观精神。所以有乐感文化。更进一步说,既然没有一个超越于人之外、存在于人之上的神为人安排、引导,人活在天地之间便须自强,并且反过来“为天地立心”。这个“心”,在李泽厚看来,并非某种狭隘意义上的道德,而正是一种审美:“‘为天地立心’之‘心’,非道德,非认知(理性),乃审美:鸟飞鱼跃,生意盎然,其中深意存焉。……其实,正因为无上帝信仰,中国传统才建此‘乐生’的宇宙观,以为支持,以求奋进;日日新,又日新,以积极乐观之态度对待生存、生命和认识。”[1]183-184
这种有情的宇宙观与西方神圣的宇宙观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天道”“天命”的理势性、规则性使得人可以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它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又使得它可以作多方面解释。正如李泽厚所言,它使得历史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天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是“天道”;梁山造反是“替天行道”,“汤武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都是“天道”;“正由于‘天道’不是‘天主’,没有明确的人格、形象、语言、意志、教义,可以随着不同情态、环境、事件、人物而作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说。从而它的时代变易性也就非常大”[6]407。由此,人的地位固然因此而变得很高,但没有明确解释的“天命”律令却也极易为那些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如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为正史所肯定的“汤武革命”,还是被否定的“王莽篡权”,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流民造反,都是打着“天命”、“天道”的旗号实行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或目标,而以人生活、生存本身作为信仰或是目的,便极易踏入所谓“造化的陷阱”。的确,我们可以说,在“生”之中,主体与客体、自然与心灵、个体与社会一体两面,心灵体验到生机勃勃的宇宙自然之盎然生意,而外在自然则以其日新月异来给予心灵之滋养。但是,若无道德上的自律,“生”之本体并不必然导致真正高明的审美境界,反而易滑入得过且过、苟且偷安之泥泞。且人生之悲苦并不必然导致道德上的高洁,反而极易突破人生底线,所谓“饥寒起盗心”是也。这里的问题在于,情本体论作为一种审美哲学依然需要某种形而上来支撑。否则,它便易堕入空洞,甚至滑入泥泞。李泽厚先生曾提出“人与宇宙的物质共在”作为情本体论的形而上依据。这样一来,情本体哲学作为“没有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也终于走向了新的形而上学。
三 “礼仁分疏”:两种道德的区分——情本体论的伦理内涵
情本体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实践美学的内在自然人化理论。内在自然人化是一种理性的积淀,由社会性的理性内涵向感性形式的积淀。具体来说,有作为理性内化的自由直观的认识、作为理性凝聚的自由意志的道德和作为理性融化的自由享受的审
美。李泽厚严格区分了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伦理(Ethics)指外在的制度、风俗、规约、习惯等等,道德(Morality)则指内在的心理,如意志、情感、观念等等。关于道德,历来有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绝对主义把道德看成是一种先验的“绝对命令”,道德命令犹如神的指令,即使无理可说也必须绝对服从。有了它,人便无所畏惧,处变不惊,一往无前。而恩格斯则强调道德的相对性、历史性和社会性,认为道德是随着时代、社会的不同而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李泽厚认为,一方面,道德确实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具体的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变化,比如某些原始部落有杀老的习俗,而中华民族则以尊老为美德;另一方面,人类的确又存在某些共同的道德规范或准则,比如人们对于宁死不屈的敌人,在现实层面很痛恨他,但在内心深处却对他怀着某种尊敬,前者他称为“社会性道德”,后者他称为“宗教性道德”。
由于中国文化源于巫史传统,导致了它的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宗教、伦理和政治的三合一:“远古巫史文化使中国未能发展出独立的宗教和独立的政治,而形成以具有神圣巫术——宗教品格性能的礼制(亦即氏族父家长制下的伦理血缘关系和秩序)为基础的伦理、宗教、政治三合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1]79
宗教、伦理与政治三合一的礼制,在心理上形成儒道互补,在政治上则成为儒法互用、外儒里法。对于原典儒家来说,一日三省、检视自身、修养个体心性与建立外在的功业本是并重的。但孔子之后的儒学各有侧重,而以孟子一派心性论成为主导,发展到宋明儒学,更几乎完全忽视事功一面,使得心性论成为唯一关心的论题而忽略社会政治、国计民生问题。
这种“三合一”的礼制导致了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被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两种道德混淆的结果是,在理论上以私德代替公德,以道德的要求代替实际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上则导致治国无良策,只知道以空洞的德行来回答如何治国的问题。这一特点其实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已露端倪。《论语》中弟子问政多次,而孔子多答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之类言语,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从而达到社会的不治而治。
进一步说,这种“三合一”的理论与体制,不但导致政教不分,公德与私德相混,在历史上还演变成一种泛道德主义,这种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求、心灵完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混同、融合、统一、组织在一个系统里。在这里,形式原理即是实质原理。从孔、孟开始,由汉儒到宋明理学,一直影响到今天”[1]49。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开来,“此所以假道学、伪君子、马列主义老太太永远以绝对律令的伦理主义而横行天下也”[1]49。
情本体理论一方面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论为基础,另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以儒学为主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转化性创造”,便是要把三者分理,使其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在伦理学上,把现代社会性的公德与宗教性的私德分梳,使其“分途而治”。宗教性道德属于私德,主要关涉人“安身立命”,即信仰与心灵归属,看似具有绝对性,其实它属于个体选择,无法绝对强求。所以对于信仰问题不能干涉,不能以行政力量去强求人秉持某种信仰。而社会性公德则属于公共道德,看似各个时代有所不同,但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却是要求必须遵守的,具有一定强制性和约束力。
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基础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其实质上是一种公共理性,是公民共同遵守的准则。“随着形式正义、程序第一、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理性化的社会秩序在发达国家中的历史性地独立和稳定,这些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基本命题随着历史经济的进程日益广泛地在全世界传布开来。尽管有各种曲折困难,以及与各种传统道德或宗教的严重冲突,但它似乎总能最终冲破各地区、种族、文化、宗教的传统框架和限定而‘普遍必然’,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记之一”[6]62-63。
李泽厚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现代社会性道德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工业化生产的基础之上,是现代社会生产的必然要求。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话来说,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相一致。这些现代社会性道德包括“形式正义、程序第一、个人权益”等等内容。它们并非如西方启蒙学者所言建立在“原子个人”的理论假设上,而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是由历史必然性而转为普遍必然性,因此,它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这便是所谓“西体”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铁则。因此,“形式正义、秩序第一优于实质正义、内容第一,将成
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6]63。
宗教性道德关乎个体的信仰和终极关怀,关乎个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看起来是一种绝对命令,却恰好属于个人选择。李泽厚认为,两种道德虽然应该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区分,在现实中往往不可能完全分开来。宗教性道德往往会通过习俗、文化、社会意识等等影响社会性道德,甚至影响立法。如西方许多国家关于堕胎的立法遭到教会人士强烈反对,至今在某些国家堕胎仍属非法,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宗教性道德可以对社会性道德起一种范导性作用,调节、软化人际关系,使冷冰冰的理性注入温暖的人情。从中国传统来看,“天地国亲师”经过改造当可成为这样一种宗教性道德:“由于与重生命本身的根本观念直接攸关,亲子情(父慈子孝)不仅具有巩固社会结构(由家及国)的作用,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培育了人情至上(非圣爱至上)的特征。我认为它就可以在现代社会性道德中起某种润滑、引导作用。……‘亲’如此,‘天’‘地’‘国’‘师’亦然。‘天、地’既可以是自然界,也可以是一切神灵的代称;‘国’是故土、乡里、‘祖国’,它是亲情的扩展、伸延和放大。”[6]78
情本体理论区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力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宗教、伦理、政治(是否还有哲学、认识?联想各种对天文与人事相关的臆测,哲学和认识似乎应包含其中)诸多因素合一之综合混沌之中条分缕析,廓清它们之不同领域,并从中发掘对现代世界仍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将“天地国亲师”“转换性创造”为现代宗教性道德,以此作为中国人的信仰和情感寄托。这一思路,深具启发性。特别是当今中国,公德损毁,私德亦不存,这种理论上的深切反思与创造性的前瞻眼光更具现实意义。
李泽厚在不同地方对现代社会性公德和宗教性私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和讨论。在《论语今读》中,他对“忠恕”进行了现代性阐释,把“忠”释为私德,“恕”释为公德。“是否可把这个‘忠恕’分别释之为‘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前者作为个体对天地神衹以及君长父兄某种无条件的绝对律令的服从;后者则是维持社会群体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114在《“说巫史传统”补》中,他从法律、道德、政治和日常生活各方面对之进行了探讨,日常生活中的“里仁为美”、“守望相助”,政治上把“以德化民”和“以法治国”结合起来,“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斧斤以时入山林”的生态保护,“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反科技异化、使人不成为机器附件或奴隶的思想,等等,这些都将成为人类学本体论所将继承来范导和建构当前的、局部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里,他提出以“仁学三合一”代替传统的“礼教三合一”的设想:“总之,舍弃原有‘三合一’的具体内容,改造其形式结构以注入新内容,使‘礼教三合一’变而为‘仁学三合一’,即建立在现代生活的‘社会性道德’基础之上,又有传统的‘宗教性道德’来指引范导而形成新的统一,以创造出新形式新结构的‘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它就仍然可以承继‘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焉’的传统精神,这便是对传统的转换性创造。”[6]401
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所有这些当然有其意义。但是,所谓“仁学三合一”却显得有些奇怪。它的提出本身似乎正好说明了传统“三合一”思维的强大与顽强:连清醒、深刻的李泽厚也要追求新时代的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他明明一直在论述这种三合一所造成的危害,在现代社会性道德尚未建立之时却又提出所谓的新的“仁学三合一”,不仅会导致理论上的混乱,亦会招致实践上的灾难。在当今,首先是要建立自由、平等、法治的“历史、社会性道德”,而非急急忙忙去搞一个理论上既难以说清、实践上更难以操作的所谓“仁学三合一”。
李泽厚还提出以中国传统的“和谐高于正义”作为情本体的政治学内涵,以此作为宗教性道德对现代社会性道德的范导,作为纠正现代原子个人社会的孤独、冷漠的人情关系的偏弊:“所以我说,‘人类视角,中国眼光’。人到底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中国这么大的时空实体能生存下来,到底道理在哪里?这一巨大的时空实体能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吗?例如,在政治哲学上,能否提出‘乐与政通’、‘和谐高于正义’,即不把理性的最后审判而把身心、人际、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不是理性而是情理结构)作为最后的制高点呢?”[3]30-31但我认为,无论在什么社会,“和谐高于正义”都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设定的高远目标,不可能成为现实。也许,对于某一小范围的时空来说,比如一家,一族,甚至一村,一乡,也许可能的确和谐比正义更重要,因为在一个狭小的时空共同体中,人际关系的和谐远比弄清是非对错重要。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理性的裁决,正义的要求,一定应该高于所谓和谐追求,否则就会变成
如李先生自己所说过的,回到古代那伦理、宗教、政治的三合一,在各种美丽的口号之下杀人——以礼杀人,以主义杀人,以和谐维稳的名义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等等。
四 以“仁”释“礼”——人性情感的塑造:情本体论的核心
内在自然的人化,建设心理本体,塑造人性情感,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泽厚一直强调的中心,也是他的实践美学关于个体主体性和情本体的一个主题。李泽厚塑造“人性情感”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传统儒家美学的仁—孝学说,即通过教育、训练和各种社会性的礼仪、典礼建构人性心理的情—理结构。
人性情感的建构,在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中,主要在于以“孝—仁”为核心,建立起一种理性化的情感结构。不是性——自然欲望,不是理——离开自然心理的道德规范,而是既包含了自然生理欲望又包括社会理性和道德伦理的“情”,成为人生和社会的本体。自然欲望论放纵自然生理欲望,使人成为自然欲望的俘虏;道德论则以道德伦理压抑合理的欲望,变成伪善的泛道德主义。情本体论既承认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又不沉沦于此,而是以理性的积淀改造自然人性,使之脱离纯粹动物性而变成人的心理。“‘情’是‘性’(道德)与‘欲’(本能)多种多样不同比例的配置和组合,从而不可能建构成某种固定的框架和体系或‘超越的’‘本体’(不管是‘外在超越’或‘内在超越’)”[7]188。情的自然基础是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孝,其核心是由社会规范、礼仪内化而来的仁。“仁”不是脱离心理情感的自外而来的道德规范,也不是单纯的自然情感,它由外而内,由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成为自觉的心理要求。
仁不是自然而然就具有的,而需要由外在的社会行为、实践、仪礼来建构、塑造。因而,要塑造以仁为核心的心理结构,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礼。礼是一种规矩、仪式,是对外表、行为的规范与约束。礼来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祭祀活动,到了孔子时代,原始氏族社会的祭祀仪式、音乐等制度或规范已被打破,不但原先只能由天子方能从事的祭仪被各国国君僭用,而且许多礼仪在社会生活中早已废弛。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许多时候,遵循古老的礼仪便显得有些繁琐可笑,甚至滑稽(《论语》第十章记述孔子在上朝、祭祀、宴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举止、仪态、言语等。有时候便显得有些古板滑稽)。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仪式之所以重要,在于通过这些仪式、典礼和各种繁文缛节,让人们把礼的各种内涵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心理要求,由外而内地塑造人们的心理习惯和心理结构,把本是外在的社会性的道德律令、戒律命令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心理要求。这个过程是通过乐来实现的:
乐无关知识,技艺,而直接作用心灵,陶冶情性。即使当时之礼制规矩,虽或失之琐碎,然正在此具体举止、态度、行为、言语的教导训练中,才能建立人的情理结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立于礼,成于乐”,均此之谓也。具体礼乐之内容,细目均可随时代、社会而大有异同,但此教育学之文化心理的“形式原则”则永在常新,即非人文(human culture)不足以成人性(human nature)也。[1]179
这也是为什么先秦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礼教和乐教对于塑造人的情理结构皆不可或缺。礼的规矩、制度、仪式,固然有时显得迂腐可笑,甚至束缚自由与想象,限制天才,但它在构型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性本如水,没有定型,如何教育便塑成什么样。如装水之器具,器具方则水方,器具圆则水圆。因此不可小看礼之作用。古代是礼,今日是仪式。所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各种仪式是非常重要的。当今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进入“少先队”,在国旗下宣誓“时刻准备着”;美国学校的中小学生在听到广播里演奏国歌时也要起立致敬。这便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训练。这种训练使得“祖国”这种抽象存在通过日常生活的仪式变得具体,并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孩子们的心理结构,成为深层次的心理情怀。
五 “立命”与个体主体性:情本体论的旨归
如果说,李泽厚早期的实践美学主要致力于奠定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人类历史实践活动中发现作为人类“类存在”和“类活动”的美的本质,因而特别注意和强调美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强调作为审美主体的群体主体性。那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他的重点便由群体主体性转向个体主体性,由外在自然人化转向内在自然化,即确立美感作为内在自然人化的心理本体的内涵,也就是情本体的内涵。即他的美学的重点,由确立美学的实践基础转向为个体生存建构一种心理—情感本体。早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在整个社会尚未意识到个
体生存问题时,他就已谈到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未来生活中将具备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8]528在《美学四讲》里,他提出:“寻找、发现由历史所形成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如何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自觉地塑造能与异常发达了的外在物质文化相对应的人类内在的心理—精神文明,将教育学、美学推向前沿,这即是今日的哲学和美学的任务。”[9]465在《哲学探寻录》里,他明确提出情本体是未来哲学的方向:“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7]187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早期以“自然的人化”为核心的实践美学到晚年以“孝—仁”为中心的情本体理论,李泽厚的目标都是要确立个体主体性,要为个体在去宗教化、去主义化的21世纪寻找一种“安身立命”的归宿。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两个对谈里,李泽厚谈到,情本体哲学是要承续海德格尔哲学,要探索一条“后现代之后”人类的心灵之路。海德格尔提出人是“向死而在”,强调人必须面对死亡而“活着”这一境遇,这是他的贡献。但是,海德格尔把“本真”与日常生活的“非本真”完全分开,只强调自我选择、自我决断、走向明天,但怎么走呢?所以他的哲学很容易为纳粹所用[3]73。而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本真”就在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无限就在有限中。情本体论正是要在海德格尔哲学终止的地方开始走,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本真”,在有限中寻求无限。从而,所谓“安身立命”也就不是在日常生活之外找到某种神灵来主宰个体,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塑造属人的心理、摆脱个体“被扔入”到世界上这样一种让人不豫的处境,通过个体存在的偶然性建立自己的“必然性”:“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的每个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中,来参与建构这个本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性和必然性。这里就不是必然主宰偶然,而是偶然建造必然。”[7]239
“命”通常被解释为某种必然性,某种注定如此、非人力可抗拒的定数。与此相反,李泽厚认为,中国传统儒学所谓“命”,恰恰指的是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人是偶然间“被扔入”这个世界上来的,因此,如何摆脱这样一种偶然性,让本是偶然间来到世界上的每个个体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赋予本无意义的生命以“意义”,这便是儒家所谓“立命”、“正命”。在他看来,儒家的“立命”就是为个体建立内在心理机制,通过仪礼、仪文、仪式,把原属于社会性的外在的礼制内化为自觉的心理要求,建立以孝—仁为本体的情理结构,从而使得个体身心俱安,在世界上从容而诗意地活着。
由于一个世界的世界观以及理性与感性、抽象思辨与情感想象、客观认知与主观判断融为一体的巫史传统,中国人没有超越性的神可以依靠(思维上也没有一种超理性的绝对认知作为参照),而生存之不易,生活之艰难,生命之短暂,又使得人们必须理性地面对自己“活着”这一事实,并以绝大的勇气与智慧,在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积极交往和交流中生存。因而,积极进取,豁达乐观,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调,即乐感文化是也。“乐”非浅薄的知足常乐,非庸俗的短视之乐,非驼鸟似的逃避危险或痛苦之自我麻醉之乐,而是在积极事功(子张、荀子等儒学所倡导)、学习知识(学之乐)、践行道德(三省吾身等)、改造社会和自然之中培养起来的道德—审美境界,或者是超道德的形而上境界。所以,乐在这里带有形上性质:“此‘情’此‘乐’又并非低层次的审美感觉,而是溶理知、意志于其中的本体感悟。此感情之所以为‘乐’,则中华文化之特征。人生艰难,又无外力(上帝)依靠,纯赖自身努力,以参造化,合天人,由靠自身树立起乐观主义,来艰难奋斗、延续生存。”[1]159
这便是情本体理论的旨归。实践美学以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原典儒学的现代性阐释,“转化性地创造”出“人类视角,中国眼光”的情本体理论。这种理论立足于中国传承五千多年的文明所塑造的心理文化结构,赋予巫史传统、一个世界、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度的智慧等传统文化资源以现代性的内涵,提出现代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相互区分而又以“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对前者进行范导,以经过改造后的孝—仁为基础建构现代心理结构,以对“人生在世”的充分肯定和现实中的温暖人情来填充“后现代之后”的人类的巨大的精神空白,使建基于“一个世界”之上的“情本体”真正成为一种审美形而上学。情本体理论有历史唯物
论的坚实哲学基础,立足于深厚的中国哲学传统,其内涵无比丰厚,其学说能够自圆其说,成为继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后最具有创造性和现实感的哲学理论。当然,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还有诸多问题,包括审美形而上学在解构形而上学之后是否成立,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的双重本体或多重本体问题,所谓
注释:“仁学三合一”的理论假设是否成立,所谓“十三亿人的巨大的时空实体”作为情本论“登场世界”的基础等等,都需要更多的讨论、质疑、分析,但毫无疑问,情本体理论是值得关注和深入探究的、最富创造性和启发性的哲学理论。
①参见拙作《美学何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另见《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情本体——实践论美学的个体生存论维度》,《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从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到个体生存论——再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美学》第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学争论中的哲学问题与学术规范——评“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从人类主体到个体主体——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观念》,《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新中国实践美学六十年》,《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5期;《从“自然的人化”到“人自然化”——后工业时代美的本质的哲学内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自然美、社会美、生态美——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之二》,(《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等等。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李泽厚,刘绪源.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李泽厚.度与个体创造[C]//美学:第1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6]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7]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0.
[责任编辑:张 卉]
●书讯
[9]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Emotional-Ration Substructure of LI Ze-hou’s Practical Aesthetics
XU Bi-hu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emotional-ration substructure is the LI Ze-hou’s most important thoughts in his late period.LI Ze-hou developed an original,creative and innovative system of ideas which is based on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stemme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ct of “human’s being alive”.In his theory of emotional-ration substructure(ERS),LI Ze-hou exami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ragmatic reason,the measure-based wisdom and the Marxist notion of practice.Thus he combined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onfucianism.Therefore,ERS became the final purpose of his practical aesthetics.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still the basis of ERS theory which is,on the one hand,a reification of notions of “the humanization of inner natures”and“the psychological substructure”and on the other hand, an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thoughts of Ren and Xiao.The principal purpose of ERS discusses
how one can grasp the chance or control one’s contingency,settle down and get on with one’s pursuits in the world when facing strong unpredictability and inevitability.This paper focuses 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LI Ze-hou’s theory of emotional-ration substructure from his works such as Pragmatic Season an d Optimistic Culture,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Five Speeches in Jimao,Seekin g of Philosophy,and so on.The paper discusses LI’s thoughts from five aspects,namely,the practical basis of the ERS:the philosophy of“doing”and the essentiality of the“measure”;the world view of the ERS:the idea of “one-world”stemming from the idea of“shamanism rationalized”;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the ERS:the distinction of the Li and Ren,and their constructions;the core of the ERS:the conformation of the humane emotion and the purpose of the ERS:grasping the chance to establish oneself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Key words:motional-ration substructure(ERS);LI Ze-hou;practical aestheticse
作者简介:徐碧辉(1963—),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美学。
收稿日期:2015-06-30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0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