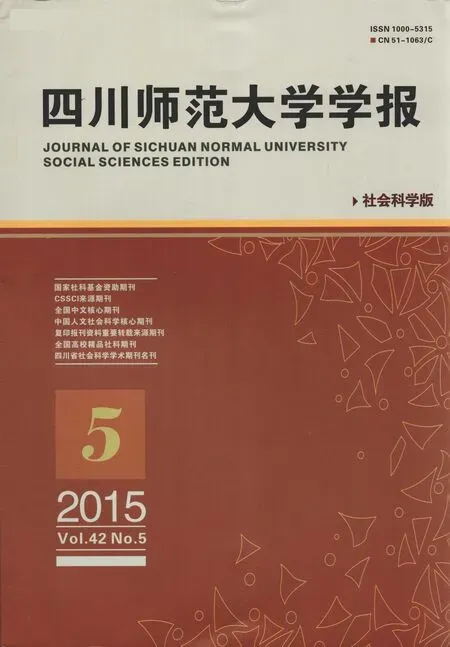论胡适诗学中诗性的衍化历程
曹万生,王 方(四川师范大学.诗学研究所,.文学院,成都610066)
论胡适诗学中诗性的衍化历程
曹万生a,王 方b
(四川师范大学a.诗学研究所,b.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叔永)之论辩,表面是文言与白话之争,本质却是白话诗的诗性之争。胡适在初期白话诗学中主张用白话,强调清楚明白,强调用白话写的即是诗,忽略诗性,论辩中的任鸿隽、梅光迪主张重视诗性。1918年后,胡适逐渐改变关于诗性的看法,重视音乐性、具体性。他关于现代汉语多音节词的理论创新,为新诗的音乐性作出了初期的理论贡献。胡适的“影像”(意象)概念,源于意象派理论,同时也体现了胡适1919年以后对新诗诗性反思的成果,标志着胡适诗学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胡适;白话诗;诗性;音乐性;影像
王方(1973—),男,安徽淮北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诗学。
初期白话诗学是由胡适奠基的,胡适的白话诗理论即现代新诗理论的第一时间形态,这个形态的内容与意义是文学语言革命,这个形态的问题与缺失在于汉语诗性衰减。本文拟研究胡适白话诗理论的诗性阙失及其后衍进的问题,以期对中国现代诗学史的诗性历史构建基本的轮廓。
一 初期胡适白话诗学中诗性的阙失
中国现代诗学,是从胡适的白话诗理论开始的。胡适白话诗的“八事”①认为,凡用白话写诗,均是诗[1]。其后他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上将某些条序、条文稍作调整、修改后称为“八不主义”②[2]。此“八事”与“八不主义”,一直被公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也是白话诗的基本主张。加上他后来补充的“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3]790,“话怎么说,就怎么写”③,构成其初期白话诗学的基本形态,即白话诗的美,就美在白话。也就是说,在“白话”与“诗”这两个因素中,强调的是“白话”,而不是“诗”。这也是胡适奠定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诗学理论。
这个理论的意义在于,对传统汉语诗歌的诗体与语言进行革命,这一点学界并无争论。这个理论的阙失是什么呢?学界关注却不够。因此,有必要真实回顾并研究一下白话诗学诞生时的论辩。胡适白话诗学,一开始就陷入了理论上的悖论:用白话写就是诗;用白话写,不一定就是诗。为了辨析的方便,现就争论的两个点(文言与白话、诗性与非诗性)列出两对、四种可能性:
第一对:白话
第一种:用白话写出有诗性的白话诗,就是诗;
第二种:用白话写出没有诗性的白话诗就不是诗;
第二对:文言
第三种:用文言写出有诗性的诗,就是诗;
第四种:用文言写出没有诗性的诗,就不是诗。
如果选择第一对,显然,用白话写的诗,不一定都有诗性,用白话把诗写得有诗性,这才是诗。但胡适强调的只是用白话写,强调的是“清楚明白”,他“八事”的价值中心就是“清楚明白”,这就是胡适诗学理论的问题。换言之,就白话诗而言,胡适的革命价值在用了“白话”,缺陷在于忽略了“诗”,即导致了诗性的衰减。而第二对,正是他的论敌们坚持的观点。
胡适与梅光迪等白话诗论辩的实质,是白话诗性之争,包含两个内容:第一,用白话写诗是否就是诗;第二,怎么才是诗。
(一)用白话写的是否就是诗
胡适这一层面主张用白话写的就是诗,仅强调在白话语言的层面。我们拟以评述的方式客观呈现历史原貌。
首先,“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胡适1915年9月21日日记记录了他20日与任鸿隽(叔永)赠酬,首次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口号:“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3]790“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是胡适后来宣布的白话诗革命的宣言,也是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回顾文学革命时所津津乐道的[4]7。作诗与作文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作文不用有诗性,作诗一定要有诗性。用白话作诗像作文一样作,这种主张当然遭到了任叔永、梅光迪诸人的反对。胡适三个月后的日记再次记录了他们反对的情况。
其次,“不像诗”。胡适以说话方法写诗,同学群都认为“不像诗”,对胡适这类白话诗作出批评:“近来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而张先生甚不喜之,以为‘不像诗’。适虽不谓然,而未能有以折服其心,奈何!”④[5]838这是当时争辩的基本论点:一是胡适认为他“作诗颇同说话”到了一种进境;二是同学群均认为他写的“不像诗”即没有诗性;三是互不服气。这个分歧,为后来五四白话诗论争埋下火种。这段记录表明,他们的分歧不在语言,而在诗性。
再次,根据周作人回忆,胡适强调“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要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独抒性灵’。……要想表达现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6]100-101这是一个佐证,可以证明胡适诗学在当时的影响与被接受的情况。在五四新诗界,新诗的写法就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写下来的结果就是,诗可以有真情,但诗不一定有诗性。丁西林20年代独幕剧《一只马蜂》剧中人吉少爷谓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旁人莫名其妙”[7]60,自己非常乐道之说法,很有代表性。
最后,被明代大诗人杨升庵嘲笑的唐人张打油“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8]1063这类打油诗也被胡适挖出来,作为用口语写诗的例子来证明“作诗如同说话”。张打油诗的问题不在用了俚语,而在写了废话,写了不是诗的韵文,胡适当时心仪此例,说明胡适当时对诗性是忽略不计的。
(二)白话诗怎样方有诗性
这个问题,是胡适与同学群当时辩论的中心。根据他们辩论的信件往来,双方有如下不同的见解。
首先,梅光迪主张用“诗之文字”作诗,不用“文之文字”作诗,其内涵在强调汉语的诗性层面。“觐庄尝以书来,论‘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截然为两途。‘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以其太易也。’”[9]845胡适重心在于,主张诗可以“诗之文字”,也可以“文之文字”入诗,但以不避文之文字入诗为主,他还例举历史、现实例证证明“文之文字”入诗的好处。这里“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即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之谓。散文之语言即他主张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中的“话”,包括俚语俗语等。汉语诗歌创作实践证明,汉语诗的语言宜用有意境、有音乐性、有节奏感、琅琅上口、精炼悦目的语言为好,这是诗人与诗学的共识,这也是保证汉语诗歌诗性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古代诗歌之所以形式精美,就在于诗人主动创造并维护语言的诗性原则。
其次,白话作诗,诗性太少。这是梅光迪等人对新诗的误解。梅光迪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10]981“白话俗不可当。”[11]965这是梅光迪等人对文学革命保守之铁证。文学革命的重心就是文学语言的革命,而文学语言革命的最后一关就是诗歌语言的革命。在20世纪10年代以前,由于近代诗文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文体革命的发展,白话小说、散文、戏剧已被普遍接受,
“诗界革命”只革掉了诗的境界,使用了翻译新词,并未改变近体格律,更未废文言,就是因为古代汉语诗性桎梏之制约。现代汉语是可以有诗性的,这已为后来创作所证明。这也正如卞之琳所回忆的:过去许多读书人,还是读到了徐志摩的新诗才感到白话新体诗真像诗,基本原因在于“能显出另有一种基于言语本身的音乐性”[12]。梅光迪等人只看到文言诗的诗性,看不到白话诗可能寓于的诗性,这是梅光迪们的短视。
再次,梅光迪认为,用白话作诗,要有“教育选择”和“锻炼”淘洗。梅光迪还认为,诗的语言有一个“教育选择”与审美选择(“锻炼”)的问题,有一个历史上的锻炼精炼最后得到认可的问题。他说:“一字意义之变迁,必经数十百年,又须经文学大家承认,而恒为始沿用之焉。”[11]972-973梅光迪的这个观点是对的。这样来理解,就明白梅光迪反对胡适白话诗语言观的真实意思。也就是说,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主张是错误的,这“话”里的“新的语言”,有一个历史选择的问题,有一个由粗到细、由不美到美的过程。新诗由20年代到30年代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个过程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梅光迪说得这样残酷和神秘。
由是可见,梅光迪没有看到白话的诗性,只看到文言的诗性。这是梅光迪的误述。他看到的白话,只是俗的白话,不是诗性的白话。徐志摩等创造的诗性的白话,证明白话是可以有诗性的。因此,统称白话写诗没有诗性,是缺乏远见的。这是梅光迪的问题。当然,梅光迪所言当际,的确没有诗性白话的杰作。
最后,认为白话诗,除了白话与韵,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这个主张,在任叔永的主张中体现得最为完备。任叔永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盖足下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
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
……余自倡一种高美芳洁(非古之谓也)之文学,更无吾侪厕身之地。[10]983,984
今天看来,在这一方面,任鸿隽的主张最为妥当。白话诗之有无诗性,不在于是否白话,也不在乎是否押韵,仅有白话与韵不一定是诗。诗之为诗,除此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这里的“和谐之音调”,指诗的音乐性,含诗的押韵、节奏等外音乐性,以及内心情感的波动即情感的旋律即诗的内音乐性,这两方面有了,才有“和谐之音调”。其次,所谓“审美之辞句”,显然含诗歌语言营造的意象、意境的美,以及诗歌语言本身的美,换言之,这强调的是白话诗语言的诗性。如果当时胡适的白话诗能写到后来徐志摩那样具有这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当也就合于任叔永之白话诗的诗性要求了。
但任叔永仍然认为白话写诗没有诗性。任鸿隽是在集体误述与误读中展开论述的,但他的重心在诗性而不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
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的白话诗论争,学术界至今认为是白话与文言之争。这种陈识,既受限于胡适与梅光迪的误述,同时也有学术界的无视与误读。胡适的误述是对白话语言的误述,认为白话写的就是诗。梅光迪、任鸿隽的误述是对诗的误述,认为只有文言写的才有诗性,白话写的没有诗性。言不尽意构成双方的意的曲述与史的误写。而学术界的无视与误读是以胡适为圭臬,以胡适所反对为历史之反动,其学术意义可疑。
建国以后,学界的这种以白话文言论英雄的说法,遮盖了胡适与论敌之间诗性的各自得失,这是现在应该加以清理的。当年朱自清也曾点出过胡适的问题:“胡适之先生及其他的白话诗人”“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13]。
二 胡适论辩的中心主张及其后来的变化
如上所述,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之论辩的表面是文言与白话之争,论辩的本质却是白话诗的诗性之争。
胡适反对梅光迪、任叔永上述论点,并在论辩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观之胡适的主张,其核心论点:主张“质胜于文”,内容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用“文之文字”,泛化了“诗之文字”,从而解构了白话诗的诗性。文学革命后,主张反对为白话诗定规则,即仍然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当然是革命时期的必然,即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919年后,由于反对初期新诗的人,不再是主张用文言写诗的人,
而是写新诗的人,因此,他开始改变不谈文、不谈形式的一贯态度,开始谈新诗的外形式问题。历史与逻辑地看,即仅从诗学逻辑上讲,胡适的贡献与失误起码是不分伯仲。
胡适的主张从历史维度细分下来,有如下几点可再示。
(一)1915年论辩始,他主张用白话写就是诗。
首先,在论辩中,胡适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即主张用白话写即是诗。在白话与文言的论题上,胡适主张白话写诗,梅光迪主张文言写诗。
其次,在诗歌写作上,梅光迪、任叔永主张白话诗的语言和写法要有诗性。胡适的白话诗主张没有包含诗性,梅光迪、任叔永反驳的是胡适主张的白话诗无诗性的一面。梅光迪认为文言诗才有诗性,白话诗没有诗性;任叔永重心不在文言还是白话,重心在驳胡适的白话诗论没有诗性。
(二)1916年论辩中,他对白话诗诗性不自觉的矛盾表述。
胡适的上述主张,在论辩中发生了变化,接受了梅光迪、任叔永的一些建设性看法,逐渐体现出诗性上的矛盾性,同时又非常坚定地主张“质胜于文”。
在论辩中的这个矛盾性体现为:一是接受梅光迪的“锻炼”说,接受任叔永和谐的音调与审美的辞句说,但对音调与审美的理解有分歧;二是实际上到后来意识到诗性表层层面的重要性,如音乐性、节奏的意义等,开始谈论这些问题了,但对用诗之文字写诗是一直反对的,这个反对当然体现了胡适的内容主张;最后,他更明确地主张“质胜于文”。
首先,胡适在与梅光迪的论辩中,勉强附和了梅光迪来信中的“教育选择”与“锻炼”说了。这种附和,明确都写在1916年7月22日《答梅觐庄——白话诗》一诗中[11]965-974,这是对他1915年9月21日《寄绮城诸友》一诗中“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3]790的某种矛盾的表示,这是有进步的。但这个进步,并非自觉的,而是论辩中自圆其说的一种说法。
其次,对任叔永回信时的回应,自辩其诗也达到了“和谐之音调”与“审美之辞句”,但从文中看,不是自觉的理论意识,而是应对任评“失败”的自辩。“足下谓吾白话长诗为‘完全失败’,……适意颇不谓然。吾乡有俗语曰‘戏台里喝采’,今欲不避此嫌,一为足下略陈此诗之长处:……”[10]985显然,这是对任叔永批评其长诗“完全失败”的自辩,这种自辩不能理解为对诗性理论的修正。
(三)1917年文学革命后,他提出“质胜于文”的中心论点,这是胡适白话诗诗性缺失的根源。
文学革命开始以后,胡适在与陈独秀通讯中,面对诗学革命的反对派,提出“文学堕落之因在于‘文胜质’”:
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14]4
胡适的逻辑是:第一,旧文学(应读做旧诗)的堕落,在“文胜质”;第二,新文学之新,在质胜文;第三,反驳孔子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第四,提倡有“物”即可,“文”无所谓。就诗学层面来看,整个思路是革命的,不是建设的,即摧毁旧诗;至于新诗如何建设,建设成什么样的新诗才有诗美,则是不关心的。他的第三层推理也是有问题的,“言之无物”只是一种选择,若“言之有物”呢?他没有讨论这一点,他关心的只是有无“物”的问题,而“文”的问题,即诗的诗性的问题,他是不管的,他只管诗是不是用了白话,是不是说了“想说的话”。这说明,在与梅光迪等论辩后,胡适的诗学观并没有改变。
(四)新诗革命后的1918年,进而反对为白话诗定几条规则(保证诗美的诗性规则)。
从逻辑上讲,这一点,是胡适白话诗革命中最有问题的一点。从历史上讲,1918年新诗革命已经没有大的反对力量,这时与新诗人谈这个问题,有极大的理论误导的意义,导致后来闻一多等人的批评。
诗性问题,胡适直到1918年尚没有觉悟,新诗一诞生就遭遇诗性解构的历史缺陷与逻辑缺陷,是胡适一手造成的,是胡适诗学思想一手造成的。胡适作为新诗革命的旗手,他的言论影响太大,大到以致连周作人这种领袖人物当时都有些模棱两可。所以,穆木天认为,胡适是新诗的第一大罪人[15],梁宗岱讲胡适是新诗的第一个“罪人”、是“反诗”[16]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1918年7月14日,胡适写信给朱经农。这封信不再有试验期时的谦虚与恭敬,也不像前一年朱经农裹进新诗潮时胡适写谈朱经农的诗那样的兴
奋⑤,而是一脸严肃、一本正经地反对朱经农很有建设性的建议。他说:
来书又说,“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这是我们极不赞成的。即以中国文言诗而论,除了“近体”诗之外,何尝有什么规则?即以“近体”诗而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的律诗,又何尝处处依着规则去做?我们做白话文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还有—层,凡文的规则和诗的规则,都是那些做“古文笔法”、“文章轨范”、“诗学入门”、“学诗初步”的人所定的。从没有一个文学家自己定下做诗做文的规则。我们做的白话诗,现在不过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做白话诗的规则。且让后来做“白话诗入门”、“白话诗轨范”的人去规定白话诗的规则罢![17]72
胡适的这段十分武断的话,洋溢着几分成功的得意,这也是胡适文学革命时期偏激思想的再现。这段话的问题太多。一是,“诗体的解放”指对旧规则的打破,这与新规则是否应有是两个概念。二是,“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不是写诗的方法,这是作文的方法,这是胡适一贯的概念不清的问题,也体现了胡适对诗性解构的思想。第三,白话诗的规则并不是《诗学入门》、《学诗初步》的问题,而是对白话诗的根本主张的问题,是白话诗是否是诗的问题,怎么保证有诗性,这是规则之要,这远不是一般作法的问题,胡适对这两个相近但不相同的问题的混淆,也体现了他没有诗性观念的价值根本所在。
(五)1919年《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后,胡适开始谈论白话诗性问题,这表明胡适开始自觉意识诗性问题,并开始衍进其白话诗学。
1919年以后,批评新诗的已不只是一些写新诗的新诗人,一些不写旧诗、也不写新诗的读者也都在批评新诗的粗糙。面对这种情况,胡适开始改变态度,开始谈论新诗的外形式问题。这就是他发表于1919年10月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就诗性而言,他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新诗的音节,一是新诗“具体的写法”,即用形象的方法做新诗的问题。
首先,谈新诗的音节⑥。《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的音乐性问题有三个理论层次:一是新诗有“音节”,但不是旧诗的“音节”;二是关于新诗“音节”的定义;三是什么是新诗的“节”,什么是新诗的“音”。他的关于现代汉语多音节词的理论创新,为新诗的音乐性作出了初期的理论贡献。
其次,胡适提出了要用“具体的写法”即形象的方法做新诗。他使用了“影像”的概念,这个概念既源于意象派理论,同时也体现了胡适1919年以后对新诗诗性反思的成果,体现他关于新诗应使用具体的写法即形象的写法,与文的理论概述不同,诗应有诗的形象的美。关于此点,后文拟详论。
(六)1920年,胡适仍然坚持“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1920年,胡适在《尝试集·序》里说道:“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编)和第一集(编)的不同之处。”[18]39
以上变化说明,胡适关于白话诗主张,总的是在走向诗性的道路上发展,但也不时地有徘徊与矛盾。
三 胡适诗性衍化的第一路径:音乐论⑦
胡适1919年10月发表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系统清理和修正了他对新诗音乐性的看法。文中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新诗要有自己的“音节”(现通行称为音乐性),二是定义新诗“音节”,三是具体解释其“音”其“节”。第一、二个观点强调,新诗自有其“音节”概念,且与旧诗音节之不同;新诗之音节概念在于其“语气的自然节奏”,即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
第三个观点意义最大,强调了新诗的“节”与“音”是不同的概念。
“节”是胡适音乐性有理论贡献的论述。“白话里的多音字比文言多得多,并且不止两个字的联合,故往往有三个字为一节,或四五个字为一节的。”[19]
胡适敏锐地看到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相异的以多音节词为主的现象,提出了新诗诗学中新的读音单位即“多字为一节”的概念,这是胡适的首创。为后来闻一多的“二字尺”、“三字尺”、“多字词理论”理论作了铺垫,也是后来从闻一多到何其芳的“顿”、卞之琳的“拍”理论的起源。
“音”即“诗的声调”,胡适从语言的演变指出,白话平仄已变,故新诗不再用平仄而只能讲押韵,这也是他的贡献。至于押韵与否,他强调以自然为上。
四 胡适诗性演化的另一路径:意象意境论
胡适诗学中关于诗性的衍进,还体现在意象意境论的演进上。这个衍化,有先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后来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两个时段的区别。仔细研判,可以见出胡适诗学的变化与发展。
(一)胡适与美国意象派理论
20世纪10年代,正是美国意象派盛行之时,胡适以中国白话诗革命为鹄的,急借时热的意象主义理论,遮蔽性地引进了西方意象主义的相关学说,以作为其文学改良刍议之“八事”部分内容。由于目的的差异,因此,把意象这个最重要的要素阉割了。
首先,为文学革命寻找理论根据而急引。
1915年到1917年,胡适在美国与梅光迪、任叔永关于白话诗论辩的过程中,思考了有关中国白话诗革命的问题,时也正是美国意象派理论创作最为活跃的时候。胡适写于1916年12月26日以后的二则日记即《藏晖室劄记》之十五卷中序十九、二十则⑧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
1916年12月26日的“十九”则的日记所云“近作数文,记其目如下/(一)文学改良私议。(寄《新青年》)”[20]1070该文即发表于《新青年》2卷5期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所谓“近作”,即日记之前一段时间所作⑩。该文刊出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十九则日记后并列的第二十则日记则为英文,文后标有“From the N.Y.Times Book Shechor”[21]1073,内容为意象派主义主将洛威尔所谓意象派六条宣言。该则日记最后一句系中文:“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21]1073这里的“我所主张”,即胡适在与梅光迪、任叔永论辩中提出的用白话写诗、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清楚意象派六条⑪:“去运用普通语言的文字”、“去创造新的韵节”、“去允许明白、质胜于文,自由体”等,还有“八事”中的八个主张。
中国新诗学最早引进西方意象派理论的文献就是发表于《新青年》2卷5期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引进目的是借意象派的理论反对近体律绝体,提倡白话诗。这就形成西方意象派理论引入时的变异。胡适引进时没有明确说明源于西方意象派。上引《胡适留学日记》公开出版是1947年,但这一事件从1 9 2 0年代就有梁实秋⑫、赵景深⑬、梁宗岱⑭等诸多学者揭櫫。胡适自己在1947年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12月26日后的日记中记录了意象派的六条主张,说明“此派(即意象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21]1073。
其次,意象派的六条宣言的核心主张是“意象”,而胡适文学革命时期的主张及“八事”阉割了这个核心主张。
胡适抄录了美国诗人洛威尔所写,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栏的取材有“绝对的自由”、“去呈现一种意象”、“去写出坚硬与清楚的诗”、“相信思想是诗的要素”(此采邵洵美的汉译)[22]883。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八事”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讲对仗。七曰,不用典。八曰,不避俗字俗语。”[1]
第一,胡适文学革命与白话诗语言的基本主张,即白话诗与“八事”中的二、五、六、七、八条共“五事”,与他所借鉴的意象派六条宣言的第一条相同。胡适白话诗革命的总主张,即“用白话写诗”以及“八事”中的第二、五、六、七、八条:“二曰,不摹仿古人”;“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讲对仗”;“七曰,不用典”;“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与意象派六条宣言的第一条“去运用普通语言的文字”相同。这也是“八事”与意象派理论相似最大的一点,首先从数量上讲,八事中的五事就对应意象派六条的第一条。胡适把意象派六条宣言的第一条“去运用普通语言的文字”,改成了中国白话诗歌用语这种“普通语言的文字”在反对文言文诗歌时的若干内涵的体现。
第二,“八事”的一、四条共“二事”,与意象派六条主张的第六条相同。“一曰,须言之有物”,“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与意象派六条宣言第六条“相信思想是诗的要素”相同。胡适在文中论述“言之有物”时,就明确地提出了“我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二)思想”;并明确指出,当时正是“文
胜于质”形成的“文学衰微”,“此文胜之害”,“宜以实救之”[1]。所以,他在论述中对意象派所主张的“思想”特别激赏。
第三,胡适白话诗革命的口头禅“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与意象派六条宣言的第二条“去允许取材有绝对的自由”相同。
第四,胡适八事第三条“须讲求文法”以及他关于白话诗要“明白清楚”的主张,与意象派主张的第五条“去写出坚硬与清楚的诗”相同。
第五,胡适主张白话的自由形式,与意象派主张的第二条“去创造新的韵节”有类似之处。
显然,胡适文学革命时期关于白话诗的主张以及文学革命“八事”的八条主张,与意象派宣言六条中的一、二、三、五、六共五条相同。胡适恰恰抛弃了意象派最核心的主张即第四条“去呈现一种意象”。
意象派的六条主张是反对浪漫主义滥情的产物,是与象征派并行的讲究诗的情感的客观对应化倾向的产物。这个体现,就是意象的强调,收敛情感于意象,同时讲究反情感的清楚明白。但胡适只吸收其“清楚明白”,把最重要的核心“意象”扬弃了,就离开了意象派的本旨,学了个皮相。
胡适这种引入与变异,以白话诗革命及文学革命服务为目的。在革命中,他反对的是文,主张的是质,所谓“质胜于文”,所以对意象派最文的一条即“去呈现一种意象”完全割弃,这也正是他白话诗主张白话的一面,但削弱诗性的一面的必然。
(二)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提出了新诗影像即形象化的理论
文中提出的“影像”概念并“具体的写法”是胡适关于新诗诗性转向的最重要的理论标志。
这是胡适1919年开始增加和加强新诗形象性努力的重要转向。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新诗诗性增强的思考,也就是说,对初期引进意象派六条宣言时忽略的意象这重要一条的重视:他已经在《谈新诗》里使用了当时对意象的翻译“影像”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他的引进与解释,同时建立在明白清楚的基础上,这又是与后来的象征派不同的地方。
第一,诗是否“好”的标准。他提出的是诗是否具有意象(影像)的特征。这是他第一次从理论上强调诗的意象。他说:“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19]。这种看法比起他发难期只强调白话的“说话”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飞跃。
第二,他明确正确地解释了具体性的内涵,这个具体性,就是意象(影像)的内涵。他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这指的是意象(影象)与抽象的区别,也是诗与非诗的区别。那么,什么是意象(影像)的呢?在他看来,第一,“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19],就是意象(影像)要具体可感;第二,要生动感人并且含蓄精炼,即该意象(影像)要让人产生“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做到了以上,他认为“这便是诗的具体性”。在这里,他已经近乎论述了意象派的基本要义,即意象是一种象,生动饱满且包含了诗人的感性力量,同时凝炼新颖,要求是要“明显”,要“逼人”,要引致读者产生“一种或多种影像”。
第三,他强调了“具体性”的诗学意义:“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这里的具体性,就是上述的意象(影象)的程度性,越是意象程度明显,就越具有诗意诗味,这是他衡量诗性的最高尺度,这显示了他诗学的巨大进步。
第四,这个进步,当然是意象派影响的结果,是他对“八事”遮蔽了的最重要的一条意象派理论即“意象”的补充引进。因为他所说的“具体的”写法,就是他使用的“影象”的概念,是当时他输入意象派理论时对意象的翻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曲里有十个影像连成作一片萧瑟的空气,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天净沙·秋思》也是意象派举的经典例证。”[19]胡适从英美意象派借鉴的影像概念在这里不断出现,是补足其八事之删之阙,以匡其正。这正如梁实秋当年使用影像一词来究胡适原引所说一样⑮。
第五,胡适提出了各种具体性的概念,一是眼观的,二是耳闻的,三是浑身感觉的。他认为,“一叶夷犹”四个撮口呼的双声字,却有着“读的时候使我们觉得身在小舟里,在镜平的湖水上荡来荡去”[19]的感觉,这已经不是诗学的分析,而是接受美学、心理生理学的分析,但基础是诗学特别是语言诗学的分析,就是四个撮口呼的双声字。这是从丢弃旧诗以来胡适对旧诗的形式吸收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是难得的。
第六,抽象的题目与内容,要用具体的写法去写。这种朴素的说法,与毛泽东“诗要用形象思维”
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强调诗的形象感。形象感是诗性的表征。胡适在这一段话里,用“具体”来强调可视、可闻、可联想的感觉。
胡适由提倡白话诗的强调白话的一面,逐渐向诗性一面的转向,对于他个人来讲,这条轨迹是清晰的,但对于整体诗歌史特别是影响来讲,前者的影响要大得多,这就是第一印象与第一符号的效果。所以,在新诗史上,到20年代中期,穆木天还怒气冲冲声讨说:“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15]到了30年代,梁宗岱《新诗的十字路口》[16]讲胡适是新诗的第一个“罪人”,也是不为过的,他还认为胡适的主张是“反诗”⑯,认为“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的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的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等等,指的就是胡适白话诗理论第一符号的影响。因此,才有20年代中期新月派对胡适“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形式论上的革命,象征派对胡适“清楚明白”的表现论的革命。事实上,胡适从1919年就开始修正自己的初期错训,今天我们还原历史,在于修正上述情绪性言论遮蔽的另一面事实,这于历史才是公道的。
注释:
①胡适所言“八事”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②“八不主义”即为:“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字俗语。”
③转引自: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100—101页。原文为:“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即加增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要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独抒性灵’。……想要表达现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④此则原题为1916年1月29日《和叔永题梅任杨胡合影诗》。任鸿隽(叔永)的诗为七绝:“适之淹博杏拂逸,中有老梅挺奇姿。我似长庚随日月,告人光曙欲来时。”胡适和诗为五古,按梅光迪、杨杏佛、任叔永和他自己先后为序,每人一首,以口语入诗,似在实践他的“要须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见:《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37-838页。
⑤胡适《答经农》云“寄来白话诗很好,读了欢喜不得了”,见《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032-1033页。⑥为了论述的方便,凡是胡适使用的概念,文中仍沿用“音节”说法,但著者论述时,均使用“音乐性”说法。
⑦胡适关于新诗音乐性的理论,作者在《论20世纪20年代诗学的音乐论》(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有系统全面的论述。此处从略,只列要点。
⑧见《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第1070-1073页。十九则为1916年11月6日至1917年3月20日之作《藏晖室劄记》之十五卷中序十九。十九则、二十则均未有日期,十九则为1070-1071页,二十则为1071-1073页。
⑨版权页标的出版日期为1917年1月1日。
⑩19则共记了四篇目录,两篇中文,两篇英文。胡适日记时断时续,时一日记多事。此前记为12月21日。
⑪胡适1 9 1 6年1 2月2 6日至1 9 1 7年1月1 3日之间所写的署为二十则,见《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第1 0 7 0-1 0 7 3页。日记摘录了“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即意象派六条宣言(These six principles of imagism are from the preface to“Some Imagist Poets”):
1.To use the language of common speech,but to employ always the exact word,not the nearly exact nor the merely decorative word.
2.To create new rhythms——as the expression of new moods——and not to copy old rhythms,which merely echo old moods.We do not insist upon“free vrese”as the only method of writing poetry.We fight for it as for a principle of liberty. We believe that the individuality of a poet may often be better expressed in free verse than in conventional forms.In poetry a new cadence means a new idea.
3.To allow absolute freedom in the choice of the subject.
4.To present an image,(hence the name“Imagist”.)We are not a school of painters,but we believe that poetry should ren der particulars exactly an d not deal in vague generalities,however magnificent and sonorous.
5.To produce poetry that is hard an d clear,never blurred nor indefinite.
6.Finally,most of us believe that concentration is of the very essence of poetry.
⑫梁实秋:“美国英国有一部分诗家联合起来,号为‘影像主义者’,罗威尔女士佛莱琪儿等属之。这一派惟一的特点,即在不用陈腐文字,不表现陈腐思想。我想,这一派十年前在美国声势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响:试细按影像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见: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第6页。
⑬赵景深在1934年据一些说法也说:“胡适的诗受美国意象派诗的影响。”见:赵景深《现代诗选·序》,北新书局1 9 3 4年版,第1页。
⑭梁宗岱在1933年写成而发表于1 9 3 5年的《文坛往那里去——“用什么话”问题》一文中甚至说:“胡适之先生从美国的约翰·尔斯更(John Erskine)处抄来的‘八不主义’差不多都具这”,在文学中提倡用“白话”的“意义”。见: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⑮梁实秋:“美国英国有一部分诗家联合起来,号为‘影像主义者’,罗威尔女士佛莱琪儿等属之。这一派惟一的特点,即在不用陈腐文字,不表现陈腐思想。我想,这一派十年前在美国声势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响:试细按影像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见: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第6页。
⑯也就是非诗的意思,即无诗的形式。
参考文献:
[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5).
[2]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8,4(4).
[3]胡适.依韵和叔永戏赠诗[M]//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4]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G]//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
[5]胡适.和叔永题梅任杨胡合影诗[M]//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6]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M]//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
[7]丁西林.一只马蜂[G]//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等.独幕剧选: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8]胡适.“打油诗”解[M]//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上海:商务印务馆,1948.
[9]胡适.与梅觐庄论文学改良[M]//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上海:商务印务馆,1948.
[10]胡适.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M]//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上海:商务印务馆,1948.
[11]胡适.答梅觐庄——白话诗[M]//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上海:商务印务馆,1948.
[12]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J].新文学史料,1982,(4).
[13]朱自清.中国诗的出路[J].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1931,1(4).
[14]胡适.寄陈独秀[M]//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J].创造月刊,1926,1(1).
[16]梁宗岱.新诗的十字路口[N].大公报,1935-11-08(12).
[17]胡适.答朱经农[M]//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胡适.尝试集·序[M].尝试集.2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19]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J].星期评论,1919,(“双十节特刊”).
[20]胡适.近作文字[M]//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21]胡适.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M]//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22]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J].现代,1934,5(6).
[责任编辑:唐 普]
作者简介:曹万生(1949—),男,湖北黄冈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诗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现代诗学流变史”(04XZW007)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20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16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