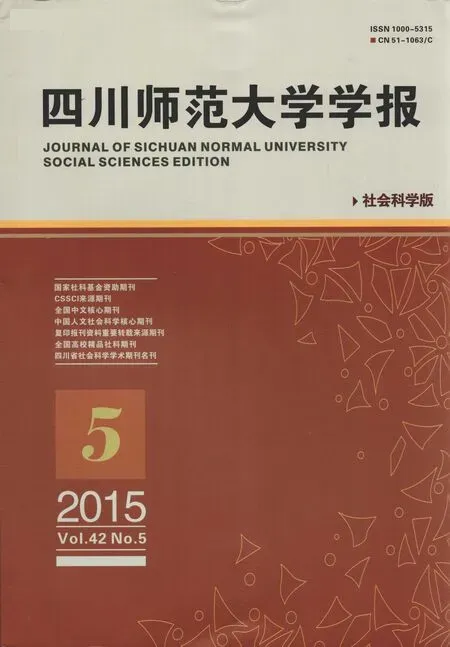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以《刑法》第十四、十五条为切入点的分析
石 奎,胡启忠(.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成都60039;.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成都60074)
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以《刑法》第十四、十五条为切入点的分析
石 奎1,胡启忠2
(1.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成都610039;2.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成都610074)
摘要:对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认定,一些学者基于各自的理解,构建了相应理论,但均无法自圆其说。笔者以《刑法》第十四、十五条为切入点,指出争议的根本症结是对主观罪过理论的不同理解;争议的实质是违背《刑法》总则精神来构建理论;认定的难点是该罪罪过处于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之间的游离状态。鉴于该罪罪过之性状,可行之路径是切实恪守罪过形式的“一元性”原则,以危害结果为考量点,并结合所掌握的证据进行具体分析。唯此,才能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能彰显人权保障的精神。
关键词:《刑法》;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刑法语境
胡启忠(1957—),男,四川达县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刑法。
回顾《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以来,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以下统称“危险驾驶罪”)的关注度并未因其入刑而有所减弱;相反,还因对其主观罪过的界定(是故意、过失,亦或两者兼而有之)所引发的争议而备受关注。从刑法解释学的视角切入,这种争议的实质可归结为如下最基本的追问:出现分歧的根本症结何在?问题的实质何在?认定的难点何在?破解司法认定的瓶颈如何?
一 主观罪过争议的梳理及其评析
(一)由酒驾引发的争议
在现实生活中,酒驾的情况很多。比如,甲某与乙某同为酒后驾车,甲某在驾车过程中遇到交警例行检查,经酒精测试达到“醉驾”的处罚标准,检察机关以《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提起公诉,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对甲某定罪量刑;乙某在驾车时因未及时避让路人,将其撞成重伤,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法院鉴于其“醉驾”事实和严重后果的考量,以交通肇事罪对其定罪量刑。
上面两种情形的裁判结果可能引发以下争议:按照学界通行的观点,甲某犯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故意;而乙某犯交通肇事罪,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过失。这难免让人感到不解和疑惑:有实害结果是过失,无实害结果却是故意。这不仅有违常理常情(醉酒开车显然是故意,为何能界定为过失呢),而且与主观恶性认知理论相悖(故意犯罪比过失犯罪更严重)。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认定引发的困惑,已受到学界部分学者和实务界的关注,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二)理论争议梳理
当前,针对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认定,我国学界形成了“故意说”、“过失说”和“故意过失说”三种代表性观点。1.“故意说”。该观点认为:“危险驾驶罪就
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的危险驾驶行为会给公共安全造成一定的危险状态,却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一危险状态的发生。”[1]27,1512.“过失说”。该观点认为:对故意的“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应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未遂)论处,只有过失的“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才符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2]。还有学者从否定故意的角度来肯定过失的合理性,其理由是:“如果将危险驾驶罪确定为故意犯,会产生罪刑关系明显失衡,相关《刑法》规范的适用丧失妥当性,导致许多人丧失职业的不良后果,也没有填补《刑法》的漏洞”[3]。3.“故意过失说”。该观点认为:“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4]
以上三种代表性观点在论述上尽管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结合《刑法》十四、十五条,我们认为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1.将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认定为故意,与《刑法》总则第十四条存在矛盾之处
(1)根据我国刑法学理论,“故意”可界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而区分两者主要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来把握。从认识因素来看,直接故意对结果的发生是有充分认识的,而间接故意对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要弱于直接故意,表现为对可能发生的结果的不确信,即可能亦或不可能。从意志因素来看,直接故意是通过自身的动作而积极追求法律评价的结果,而间接故意则体现为“不主动、不干预”的放任态度。就危险驾驶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而言,尽管醉酒驾驶者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明知”的,但对这种结果到底是持“希望”还是“放任”主观心理,则有待于进一步考量。就拿本文开始列举的甲某与乙某醉驾情况来看,甲某与乙某在驾驶车辆时,其实都持有相同的主观心理:都不希望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从人性的趋利避害来看,亦是如此),因此,这里应排除直接故意的认定。
(2)当前“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已得到学界一致认同。那么,如何来认定危害结果呢?有学者认为,应以实害犯的罪过标准来衡量危险犯,由此演绎出“结果就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的结论,简而言之,危险亦结果[5]118。依据此理论,醉驾者的主观罪过是以醉驾者对其醉驾行为引起侵害公共安全危险的态度作为判断标准,其结果是醉驾者的主观心理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结合现实生活,希望造成侵害公共安全危险的直接故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谁都不愿意自找麻烦。但在现实中,也不排除存在放任的间接故意。如醉驾者李某遇到危急病人求救而暂时无法找到其他人帮忙的紧急状况下,选择驾驶车辆送病人到医院,其途中被交警查获的情形。在处理中,李某的主观罪过假如被界定为直接故意,可能有违同类解释规则。显而易见,放火、决水、爆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行为,与李某的醉驾行为在性质上并不具有等价性,而李某的真实想法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谨慎驾驶而救人。这里把李某的行为界定为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可能更为合理。
(3)用“危险状态”取代“危害结果”与《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立法原意不符。首先,从两者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存在差异。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危险状态的认定关涉判断材料、判断时点、判断标准以及具体判断因素等,因此,该问题就成为刑法理论中复杂且颇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并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具体约定;而危害结果(又称犯罪结果)作为“刑法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司法实践中无法绕开的现实问题,这从近几年学界围绕该问题展开的研究就可见一斑”[6]。据此判断,两者(危险状态与危害结果)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就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从价值取向来看,《刑法》的偏好在危害结果。其次,从两者的逻辑关系来看,危险状态是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一种持续状态,当危害行为从量变演变为质变时,危害结果出现,危险状态也就停止。从刑法评价所遵循的原则来看,其考量点在危害结果而非危险状态。因为依据常识,实害结果显然甚于危险状态,并且评价实害结果足以囊括到危险状态。综上分析,应排除了直接故意的可能。而“故意说”将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笼统的界定为故意,而不做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分,则有失偏颇。
2.将主观罪过界定为“过失”,同样值得探讨
一是与常理常情不符。如果将危险驾驶罪定性为过失犯罪,站在受害者家属及普通人角度,则难以让人接受。交通事故,特别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如果还将当事人的行为界定为过失,可能会遭到受害方以及主流民意的诘难:明知自己醉酒还要驾车并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明显是故意行为,怎能谈得上是过失呢?面对质疑,无论如何辩解,可能都难以让人信服。这种情形与高楼抛物致楼下行人受伤事件具类似性:任何人基于常识和经验都知道高空抛物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果在发
生伤人事件后,当事人还自辩为过失,可能于情于理都难以自圆其说。回过头来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成为驾驶者的戒律。如果主观罪过认定忽视这些现实,可能会引发舆论的讨伐。成都“孙伟铭案”①就是例证。鉴于此,在信息社会,基于常理常情形成的大众价值取向,立法者和司法机关不应漠然视之。
二是对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界定,既要尊重《刑法》条文本身的立法原意,也要顾及刑法价值体系的完整。“过失说”部分持有者采取从否定故意的角度来肯定过失的合理性,而未结合《刑法》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进行深入探讨,其实质是脱离《刑法》文本来谈文本,其论证也自然缺乏说服力。
3.“故意过失说”看似合理,实则与《刑法》总则精神不符
我国《刑法》总则将罪过明确地分为两种(故意与过失)四式(故意与过失分别具有两种具体形式)[7]。这样,同一法条的同一罪名的罪过形式只能是单一的,即故意,亦或过失。而且罪过是否确定也关乎司法实务中界定罪与非罪的客观要求。尽管有学者在借鉴德日《刑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但在中国刑法语境下,该学说既未得到学界的认同②,也未得到立法者的切实回应。这样看来,该理论并不能解决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认定面临的难题。
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认定引发的以上争议,笔者认为,其共同缺陷是既有悖于《刑法》总则精神(即《刑法》十四、十五条对故意与过失的界定),也未切实尊重《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立法原意。基于这样的境遇,下面我们将以《刑法》第十四、十五条为切入点,并结合中国刑法语境,对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做深入探讨。
二 争议根本症结:主观罪过理论存在争诉
对于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的学说之争,我们认为其根本症结在于将危险驾驶之实施行为和行为导致之结果分别进行考量,从而得出实施行为是故意,行为导致之结果为过失,而依据的理论是德日刑法主观罪过理论中对行为和行为导致之结果的“二元”评价体系理论。考虑到德日刑法与我国刑法的语境差异,我们认为,对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分析不能脱离中国刑法语境。刑法语境是一国社会制度、法律文化、行为风俗等长期博弈的产物,对其立法、司法、执法都产生深远影响。针对危险驾驶罪在理论上出现的争议及司法认定中的困惑,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没有厘清中国刑法语境与德日刑法语境的关系所致。
(一)从《刑法》文本的规制形式来看,我国刑法与德日刑法在关于主观罪过认定的立法规制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对故意与过失(如《刑法》第十四、十五条)采用了条文明示的规制方式,这显然是刚性立法模式。而德日刑法对主观罪过却未明示,即对故意与过失未作严格的内涵界定,而体现为柔性立法模式。这是我们理解和认定主观罪过需把握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对个罪主观罪过认定,必须依据我国《刑法》第十四、十五条之规定来严格探讨其违法性认识或危害性认识;并且理论研究不应该撇开中国《刑法》文本另设理论,而应尊重《刑法》文本所蕴含的精神。这是引入德日刑法理论时,应特别予以重视的问题。
(二)从故意与过失的内涵来看,中国《刑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制得非常清楚和全面,逻辑清晰,一目了然;而德日刑法理论虽然未明确规制故意与过失,但提出了“违法性”概念。在理论探讨中,许多学者主张将“违法性”这一概念运用到犯罪的主观认定上。这样极易导致对犯罪主观行为的认定脱离《刑法》第十四、十五条的立法原意,引发理论认识的困惑和司法认定的混乱。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境况,除了无视中国刑法语境外,更重要的是对引入的德日刑法术语缺乏深入认识。就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违法性”理论在德日刑法中本身也面临诸多争议,这集中体现为从不同角度去界定其内涵,如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之分类,或者分为形式违法性、实质违法性以及实质违法兼形式违法性等三种。形式违法性就是前述行为对法规范的违反,而实质违法性则更多指向法规范的实质即法益侵害。而危害性认识并没有像违法性认识这样有形式与实质之分,学者对危害性认识的不同理解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前提性知识。解决好违法性认识与危害性认识的概念,才能进一步分析它们在犯罪故意认识当中的作用及其利弊。纵观近年来中国刑事立法进程,德日刑法理论大量渗透到中国刑法之中,对传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形成了一定冲击,于是一部分学者提出:中国刑法中的四要件已不适应现实需求,应引入德日的三要件理论。针对这些主张,我们认为:重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宏大工程,这不仅要考虑到我国犯罪体系的承受度,更应结合我国的政治制度。因此,不顾刑法语境的差异,不探究其真实的内涵,就无法实现理论的有效“对接”,也无益于解决刑法面临的问题。
(三)从刑法解释学来看,对《刑法》条文的理解应
在《刑法》文本之内进行探讨。刑法学是严谨、科学之学,刑法学的解释应该是借助一定的方法、规则而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反对和抵制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以及脱离中国刑法语境法律文本的任意解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处反对的类推解释是法外之类推,而非法内之类推。在目前的法律条文中,存在内涵包容的法内之类推,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条中对“放火、决水、爆炸”等重大破坏力的行为,归纳演绎出不能穷尽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行为,就属于法内之类推。这种法内之类推,既契合了中国刑法的立法现实,也顺应立法技术的内在要求,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结合案例对主观罪过的理论之争作进一步分析,如前面提到的甲某和乙某醉酒驾驶情况。如果将甲某的主观心理认定为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似乎缺乏说服力;但如果界定为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则存在这种可能。既然甲某没有出现刑法上所评价的结果(危害结果),只能转移到对其行为进行考量,自然得出行为之故意的结论;而乙某同为醉酒驾驶,但发生致人重伤的结果(出现了刑法意义上的评价结果),而这种结果又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处罚标准,其主观罪过就顺理成章被认定为过失。但这样的认识似乎与人们对犯罪中不同主观恶性——故意犯罪显然重于过失犯罪——的评价相距甚远,而此案裁定所昭示的结论是:交通肇事罪导致的血淋淋惨剧或生命的陨落比不上实施某种行为却未发生实害结果严重。这种判断无疑与社会公理和公序良俗背道而驰。究其原因,这一方面由于引用的德日罪过理论不慎所致,同时也与立法时本将拟制为过于自信过失的犯罪,但基于其他考虑,刑罚参照的却是间接故意犯罪的司法习惯有关,其中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最高法定刑达到15年就是最好的佐证[]。
可见,个罪中主观罪过应界定为故意或是过失,除了对德日刑法理论的理解与适用不慎所致,同时也与基于中国刑法语境下主观罪过的考量点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三 争议实质:忽略了现行《刑法》是以行为导致之结果为考量点
对中国刑法语境下的犯罪构成理论,储槐植教授曾做过精辟论述,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一种适应阶级专政需要的、静态反映“犯罪规格”的平面整合结构模式[9]3。在这种模式中,刑法的价值偏好在于其惩罚机能而非预防功能,因此,危害结果就作为考量主观罪过的唯一依据。
(一)对故意的界定体现了以结果为本位的偏好
结合《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制的内容来看,犯罪故意的核心要素为“危害社会的结果”,这表明“结果本位”是犯罪主观罪过的考量点。在此基础上,依据故意犯罪意志控制的心理特征,又将故意进一步解构为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即学界统称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细酌两者的逻辑关联,都表现为以“结果”来考量其认知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句话中有两个关键词需厘清:一是所谓“明知”,从刑事立法学和刑法解释学来看,是指以一般人的认知水平作为判断依据,这包括普通民众的认知水平、知识结构和心理活动对犯罪行为规制的行为中具有犯罪构成要件意义上的具体事实的一种判断和认知,这可理解为刑法对社会民众的一种义务苛求;二是所谓“会”,从法哲学的角度讲,是指一种应然状态,而非必然。易言之,只要实施了该行为,这种危害结果就能被民众所认知,而并非一定是实害结果。
而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区别,也主要投射到对结果的意志控制上,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是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何为“希望”和“放任”?这是厘清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关键点。对于“希望”,有些学者指出,它只是一种心理活动,是一种愿望。在我们看来,“希望”必定是意识控制之下的身体动静,即通过积极的身体动作促使应然之结果转化为实然之结果,即实害结果发生;缺乏了意识或身体动作,都不能称为“希望”。何为“放任”?“不加约束,任凭其发展”是其应有之义,归演到刑法语境,其内容和范围甚广,可认为是“希望”之外的一种概括和模糊界定。现实中,主观罪过表现为间接故意的情形鲜有出现,即便存在,也是在以放任某个犯罪结果的发生而实现某个意图或目的之场合。因此,有学者指出,决定间接故意能否成立的一个重要考量点,就是危害结果是否实际发生[10]56。
(二)对过失的界定也体现了以结果为本位的偏好
从《刑法》第十五条来看,“应当预见”的对象是“危害社会的结果”。从意志因素来看,“行为导致的结果”是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的共同考量点。可见,过失犯罪也体现了“结果本位”。因此,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是以行为导致之结果作为《刑
法》的考量点。厘清这一点,对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该罪认定的难点:介乎于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之间
既然中国刑法语境是以“结果本位”来认定主观罪过,那如何判断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呢?我们认为,这需要结合现实进行分析。大量生活事实表明,在醉驾案中,醉酒后驾车大多出于对自己驾驶技术的自信而放任自己的行为,或是自信自己谨慎驾驶就能避免结果发生。而这两种心理要确定为是间接故意或是过于自信过失,往往又囿于证据,无法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源于理论上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适用边界难以厘清。德国刑法学者Welzel就曾感叹,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界限是刑法中最难界定和认定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难在意欲是一种原始的、终极的心理现象,却无法从其他感性或知性的心理流程中探索出来,因而只能描述它,无法定义它[11]43。这样看来,主观罪过是否会突破“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二维逻辑,而形成第三种结论“即此即彼”呢?
(一)介乎于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之间的游离状态是该罪罪过之性状
要厘清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之间的界限,在现实中确实面临诸多困难。一是认识因素难以区分。从《刑法》第十四、十五条来看,间接故意是“明知…会…”,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应当…可能…”,其中“明知”和“应当”都是一种义务苛求,其涵义具有等值性。而“会”和“可能”所致的结果也具有交叉,“可能”包含“会”的内容。二是两者的意志因素趋同。具体表现为对结果发生的态度是不希望。三是两者以追求结果的发生为构成要件。可见,理论上的分歧必然投射到实践领域,其结果是有些案件认定面临争议与分歧。如杭州“胡斌飙车案”③。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是事后认定胡斌当时行车的可能速度。从胡斌的驾驶技术、汽车制动性能、看到行人后的反应以及事后的补救措施等客观因素来看,胡斌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判断。因为单就车速控制来看,如果车速在每小时84.1公里,采取紧急制动,伤及路人的可能性更小,其主观罪过更倾向于过于自信过失;如果车速为90公里或101.2公里,当事人的主观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是否转化为“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呢?这一方面与汽车制动性能有关,也与路面的粗糙程度、个人驾驶技术等因素有关;加之驾驶技术、应急处理技巧和经验、距离判断等,很难予以客观量化和准确描述,势必影响到主观罪过的认定。可见,判断其主观罪过,需综合考虑当事人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环境等具体因素,一旦某些变量发生改变,则结论就很难确定。
(二)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界限难以区分两者的界限
1.意志因素的区分难以自圆其说
学者们试图以对危害结果发生持何种心理(放任或轻信能够避免)等意志因素作为主要依据予以区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但在实践中,则面临操作局限。众所周知,理论上的区分容易表达,但如果外化为客观实践,则难以量化和操作。为此,一些学者试图突破抽象的价值衡量,寻求具体的司法操作办法,如德国的弗兰克公式④、陈兴良的“回避容忍说”⑤等。但究其本质,我们认为,这些学说仍未脱离主观判断的界域,并试图借助意志因素来界分两者之关系;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均难以自圆其说。
2.认识因素的区分也缺乏说服力
既然意志因素无法解开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死结,那能否另辟蹊跷,从认识因素上寻求路径呢?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两者存在多处交叉点,具体表现为:过于自信过失不仅包括间接故意所认识到的、与犯罪有关的已发生事实,还包括防患于未然的事实和条件。当然,仅从立法解释学的角度切入,其论证略显单薄。若以刑法理论为进路,能否寻求理论依据呢?有学者指出,认定主观上具有过于自信过失,理论上是以一系列假定前提为基础。比如:假如要认定过于自信过失,需要以行为人认识到的各种不利因素全部出现时,才能出现刑法上的危害结果,但现实中,这些因素同时出现仅仅是小概率事件,基于这样的判断,行为人更有自信认为不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会更多些,或者认为依据个人的小心谨慎或个人能力能够进行避免。而与过于自信过失不同的是,间接故意中,行为人对刑法上的危害结果的理解是直接的,也是现实的。并且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如果行为人按照这种方式行为,完全可能将应然中的危害结果转化为实害结果,此处并不存在过于自信过失中的假定前提条件,易言之,该危害结果完全由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所导致。有学者对此作过精辟概括:间接故意是明知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轻信过失是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假定可能性[8]。
然而,这种认识逻辑在遭遇疑难案件(如前面提到的胡斌案)时,与传统以致害可能性的大小来认定罪过的司法惯例不期而遇,但寄予通过认识因素来区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界限之构想却无法得到实体法的有效回应。
3.司法实务中难以认定
理论争议的困扰必然扩散到司法领域,这是刑法运行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司法实务中,主观罪过必须外化于客观实际,而客观实际需人为拟制为具有说服力和科学依据的系列数据和相应结论。由于受科学技术和客观环境的影响,数据的采集和结论的获取不一定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就拿司法鉴定结论来说,可能由于方法的差异、技术人员业务能力高低不同等影响,其结论也具有差异性。再加之危险驾驶行为的性质、程度、情节等各有差异,对主观罪过的量化和判定难以界定,从而增加了认定的难度。据笔者的统计,与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认定类似的情况,在《刑法》条文中并不少见,如第一百二十九条丢失枪支不报罪,第一百三十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五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七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一百四十二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一百四十五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卫生器材罪,第一百八十六条违法发放贷款罪,第一百八十八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第三百零四条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第三百三十二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第三百三十九条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这些个罪在司法适用中已引发了不小争议。可见,主观罪过介乎于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之间的情形已不是个别情况,理应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三)争议关键之所在:主观心理难以厘清
由于受科学技术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人类对心理活动的把握是有难度的。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科学认知中,对心理活动的把握一方面通过人的手势、面部表情、语言等方式获知,另一方面依据经验法则进行推理,从而使认识活动实现从主观到客观再到主观的升华。就刑事司法而言,可能掣肘于现行苛严的证据制度与规则,客观存在于人脑中并形成影像并为我们主观思维所过滤和确信的认识,受人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等影响,可能遭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尴尬,亦或囿于现行证据拟制,也无法以合法的形式予以采纳,结果是主观罪过认定缺乏统一的确证标准和认定手段。
加之在前面分析中,我们已指出,一个人的犯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何时是间接故意,何时是过于自信?可能连涉事者本人都难以判断。人的心理活动变幻莫测和游离徘徊,恰恰契合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渐进性和连续性。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认识过程,从而使认识活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随着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把握,人们往往意识到事物并非都是以前认为的那么简单(是与非)和精确(以前可能认为是类似于1或2这样的确定值),还可能是介乎一事物与它事物之间(1.2或1.7)的游离状态。因此,主观心理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模糊状态也就具有现实可能性。
五 主观罪过认定可行之路径:以危害结果为考量点,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主观罪过表现形式的不确定性(可能表现为确定性,也可能表现为游离状态),不仅与现行《刑法》“罪过的一元性”理论相冲突,也对诉讼中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构成实质性影响。对于主观罪过认定,现行通行的模式是利用间接证据(即主观心理作用下表现的客观行为)来进行证明,其主要方法是归纳、演绎等推理方法的综合运用。考虑到推理之结果存在的或然性和危险驾驶案件在现实中的差异性,对主观罪过认定有必要以危害结果为考量点,而综合个案中的相关证据进行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情形之一:在危害结果上,如果一次性出现了多人重伤、死亡以及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且主观上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认定适用于《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为宜;如果一次性未造成严重后果(人员重伤或死亡)和公私财产重大损失且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以《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定罪量刑为宜。以上两种情形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应界定为间接故意。下面再以“孙伟铭案”为例做一个分析。
该案中,我们认为涉事者的行为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把握:一是无证驾驶;二是酒后驾车;三是超速行驶;四是肇事逃逸;五是在人员和车辆密集区域连续与多辆车相撞并引发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仅从前四点来看,孙伟铭定为危险驾驶罪或交通肇事罪,并无多大问题。但关键是第五点,在人口密集区越过双实线先后撞向四辆车,直至该车不能动弹,才被迫停下,其结果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果此时仍定罪为危险驾驶罪或交通肇事罪,则为法理、情理所不容。那对于这个案例该如何认定呢?我
们不妨参考法院的两次判决。
该案一审结论认为,现有证据表明,孙伟铭对自己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是明知的,但仍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并放任这种严重后果的发生。所以认为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依据这种主观罪过的考量,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4]。
对于一审判决,当事者孙伟铭不服,便提起上诉。在二审中,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经过法庭的举证与质证,二审法庭认为,上诉人孙伟铭在未取得合法的驾驶执照的情况下,多次无证驾车,并多次违章,尤其是在本次事故中,孙伟铭以超过限速二倍以上的速度驾车,并在车辆、人流密集的道路上穿行逃逸,违章跨越道路黄色双实线,冲撞多辆车辆,造成四死一伤、公私财产损失数万元的严重后果。现有证据表明,孙伟铭完全能够预见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虽然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的证据不明显,但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证据是非常明显的,其间无任何避免的措施,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规定,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15]。
通过两份判决书的对比,可以看出,二审对学界和媒体比较关注的定罪问题做了回应,也指出了孙伟铭主观罪过,就是间接故意。下面,我们不妨做进一步分析探讨。
首先,从认识因素来看,孙伟铭在喝酒前对醉酒驾驶可能导致的危害结果是有充分认识的。依据之一是孙伟铭之前已有多次无证驾驶、多次违章的违法记录,这足以引起他的警戒和自律;依据之二是孙伟铭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对醉酒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是有充分认识的,并且也应认识到在醉酒状态下开车是非常危险的。其次,从意志因素来看,孙伟铭的行为表现为虽然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也是一种放任态度(既不积极追求又不设法避免)。这在第一次肇事后的表现(未及时停车,而且选择继续逃逸,并先后与四辆车相撞)就可见一斑。因此,此处界定为间接故意似乎并无不当。但有学者可能质疑,为什么不是直接故意呢?我们不妨举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例子来说明:某人因被他人陷害而入狱,刑满释放后由于在应聘工作中受到歧视,便萌发报复社会,于是开着大卡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导致10多人伤亡的结果。从这个案例来看,与“孙伟铭案”的确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从结果来看,都造成了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从手段来看,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具有同质性。而最大的区别可能是主观罪过,该案是预谋已久,并且是明知这样的危险行为会导致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仍积极实施该行为,这符合直接故意的特征。仅凭这一点,我们认为,它与“孙伟铭案”是有区别的。这样看来,孙伟铭的主观罪过定性为间接故意,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也是该案二审中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的主要原因。
情形之二:如果危险驾驶行为一次性造成了实害结果(无论是否严重和财产损失大小)并且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无认识,则应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定罪量刑,其主观罪过应界定为过于自信过失。我们再以杭州“胡斌飙车案”为例。
此案一审认为:被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其理由是,该行为人客观上驾驶的机动车辆严重超速行驶,并导致一人死亡,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从主观心理来看,胡斌案发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肇事并致人死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严重。综合案件事实,我们发现,胡斌有开快车的习惯,并且开车技术较好。据媒体报道,他曾获得全国F2比赛冠军。由此看来,胡斌驾驶技术非常娴熟,对驾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状况的应对也具有自信心理。从胡斌飙车时的心理活动来看,依据对自己技术和车况的自信,认为不会出现意外,所以即使在繁华的街区也未降低车速。从发生事故后个人反应来看,胡斌在撞伤谭卓后,并未逃逸,而是马上刹车,查看伤情,并积极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从这一系列行为可以推断,胡斌当时对其行为并非是“希望发生”或“放任发生”的故意心理。从这一点来看,胡斌案与孙伟铭案有明显区别,孙伟铭发生第一次事故后并未停车,反而加速逃逸,结果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如果孙伟铭也做了胡斌的选择,那么认定为交通肇事罪无可厚非,但他并未做这样的选择,导致了其行为向间接故意的转化。可见,这一点是决定这两个案件走向的重要关节点。
这样看来,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就成为区分以其它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节点。而主观心理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通过行为人的行为方式、手段、措施等进行综合把握。
情形之三:如果危险驾驶行为只存在抽象的危险,未造成实害结果,应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定罪量刑,其主观罪过应界定为间接故意。下面
我们以“徐某醉驾案”⑦和“彭某竞驾案”⑧为例进行说明。
从“徐某醉驾案”来看,徐某明知醉酒不能驾驶,而在婚礼过程中大量饮酒,并在醉酒的状态下开车送醉酒的朋友,导致与电动车发生了轻微碰擦。从徐某的主观心理来看,饮酒不能驾车,这在饮酒之前已有明确认知,但出于帮助朋友的善意,认为凭借自己的小心慎重不会出事,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放任这种行为发生的心理,所以应界定为间接故意。
而“彭某竞驾案”中,彭某与他人因为误解而斗气,不顾道路上其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长时间相互追逐、相互别挡,给道路行车安全带来了较大影响,其行为理所当然构成危险驾驶罪。从两人的主观心理来看,是泄愤心理支配下的行为,而并非是积极追求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因此,应界定为“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比较合理。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对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把握,应牢牢把握《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内容,特别是其第二款的规定,以危害结果为切入点,依据不同的情形,作出符合实际的认定。
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认定的分歧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践中一些司法实务部门呼吁将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驾驶不具备安全性能的车辆、高速公路或单行道逆向行驶、单行道超速行驶等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但我们认为,刑法固然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过于夸大刑法的功能,则不仅不利于刑法的科学发展。
注释:
①2008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为了给父母祝寿,在并没有取得驾照的情况下,驾车将父母载至一酒楼。席间大量饮酒,当日17时许,孙伟铭在成都成龙路口与一比亚迪轿车相撞发生事故后,驾车立即逃离,在高速逃离的过程中,所驾驶的车辆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一长安奔奔轿车、奥拓轿车、蒙迪欧轿车及奇瑞QQ轿车,直至孙伟铭的别克车不能动弹,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此后被公安机关挡获后,经血液抽样检测,被认定为醉酒驾车。
②对于复合罪过理论,学界多持否定意见。如有学者指出,复合罪过“混淆了故意与过失的应有区别,并与《刑法》的谦抑精神相冲突,故其存在的合理性令人质疑”(见:向朝阳等《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法学评论(双月刊)》2005年第3 期)。亦有学者指出,复合罪过“混淆了生活事实与《刑法》规范的关系,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胡东飞《复合罪过形式”概念质疑——以对滥用职权罪为视角》,《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年第6期)。
③2009年5月7日晚,被告人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与同伴驾驶的车辆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当晚8时8分,胡斌驾驶车辆由于疏忽,没有注意到行人谭卓,结果导致谭卓被撞飞,落下时又与挡风玻璃相撞,再次跌落至地面,致其死亡。事故发生的路段标明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经过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应该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④弗兰克公式:以行为人对构成要件的实现具有明确的认识时,是否仍然实施该行为为基准,如果仍然实施该行为,则属于容认。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⑤陈兴良观点: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相比较,过于自信的过失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采取回避态度的,而间接故意则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容忍的态度。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⑤摘自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⑥参见四川省高级法院判决书,网址:http://news.qq.com/a/20090908/001504.htm,2015年5月25日访问。
⑦2011年5月1日是醉驾入刑正式实施的第一天。家住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镇的小伙子徐某于5月1日晚上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席间喝了不少酒。后徐某决定开车把喝醉酒的朋友送回家,途中与一辆电动车发生了轻微碰擦。徐某在交警到来之前与电动车车主进行协商,并赔给对方100元。正当他准备开车离开时,被巡逻民警发现。经酒精测试,驾驶人徐某有酒后驾驶的嫌疑,于是委托苏州大学司法鉴定所对徐某进行血液鉴定。经鉴定,徐某的血液中酒精含量达98mg/100ml,已经超过80mg/100ml的警戒线,被认定为醉酒驾驶。
⑧2011年5月11日中午,彭某驾驶桑塔纳轿车在北京市密云县密西路一路口红绿灯处,因侯某(另案处理)所驾宝来轿车挡住去路,两人驾车在密西路上追逐、相互别挡,两车在别挡中同时撞上停在路边的帕萨特轿车,造成3车损坏,之后彭某抄起砖头将宝来前挡风玻璃砸坏。
参考文献:
[1]赵秉志.“醉驾入刑”专家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冯军.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范目的及其适用[J].中国法学,2011,(5).
[3]刘宪权,周舟.危险驾驶罪主观方面的刑法分析[J].东方法学,2013,(1).
[4]谢望原,何龙.“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究[J].法商研究,2013,(4).
[5]〔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M].东京:有斐阁,1972.
[6]徐祝.论我国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3,(4).
[7]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刑法理论对现行刑法内含的新法律现象之解读[J].法学研究,1999,(1).
[8]冯亚东,叶睿.间接故意不明时的过失推定[J].法学,2013,(4).
[9]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高铭喧.刑法学原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苏雪梅]
[11]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The Subjectiv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14th and 15th Articles of Criminal Law
SHI Kui1,HU Qi-zhong2
(1.Humanity College,Xihua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39;2.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Sichuan 610074,China)
Abstract:Many researchers have constructed corresponding theories based on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n the subjectiv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in the 133rd article of criminal law; however all of which are unable to be justified.The author takes the 14th and 15th articles of the criminal law as the starting point,noting that the fundamental crux of the dispute lies i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theory of subjective crime.The essence of the dispute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riminal law;the difficulty of crime determination is due to the free state of the crime between indirect intentional faults and self-confidence fault.Giv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ime,the feasible path is to strictly follow the sole principle of crime forms,take the result of the crime into consideration,and analyze the specific case based on proofs.Only in this way can we implement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but also guarantee human rights.
Key words:criminal law;dangerous driving crime;subjective crime;criminal context
作者简介:石奎(1978—),男,四川旺苍人,刑法学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法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基础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项目“刑罚模式对犯罪界域的制约关系——以罚金刑为视角的分析”(11BFX113)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4-06-10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1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