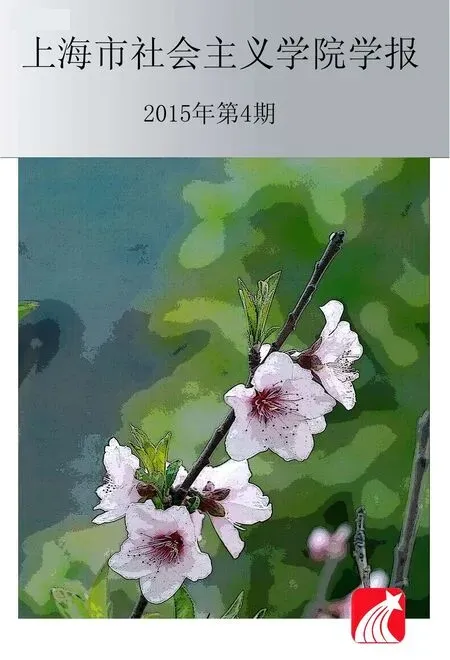第一国际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及现实意义
郭芷材(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第一国际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及现实意义
郭芷材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第一国际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联合组织,它在加强工人组织性和提高工人觉悟上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列宁所说的,“第一国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在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史上是永存的”[1]。第一国际在处理同各国工人组织的关系时坚持了国际合作上的联合统一与各国工人运动中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在统一联合的基础上恰当地处理了第一国际内部不同工人组织和各种流派之间的关系。第一国际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及其处理党际关系的实践,对我们当前处理党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国际;党际关系;原则;独立自主
一、第一国际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
1848年欧洲革命后,世界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壮大。在1857年从美国开始逐渐蔓延到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国际工人运动出现新的高涨局面,这为欧洲各国工人组织走向联合创造了条件。第一国际的成立系由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压迫的民族起义直接促成的,“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2]266。起义唤起工人热情,促进各国工人相互团结。1864年,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圣马丁教堂的小礼堂正式成立,“它是当时欧洲的两个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即英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工人阶级协商一致的产物”[3]4。马克思受邀出席大会并被选入主席团。经过国际内部长时间酝酿,根据当时工人运动的现实状况和协会内部不同流派的意见,马克思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以下简称 《章程》),说明了第一国际的组织形式,并确定了第一国际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体现了马克思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策略灵活运用的统一。
第一国际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国际性的群众联合,它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联合,更不是国际共产党。马克思称呼第一国际为“协会”、“联合”和 “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首先,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看,当时西欧各国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力图通过第一国际使工人群众明白,必须用自觉的大规模的行动来代替孤立的、分散的、时断时续的、爆炸性的行动”[3]3。第一国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把广大工人和无产阶级团结到第一国际的旗帜下,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推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第二,协会内部有众多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且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在 《宣言》和 《章程》中作了让步和妥协,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明确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阶级,更没有使用 “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协会的指导思想。
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为民主制。这是协会性质所决定。协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的群众联合,由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思想和不同阶层的工人组成,需要民主协商才能更好行动。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民主,民主包含必要的集中,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进行战斗。第一国际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记录等都体现了民主制原则,例如,“中央委员会是互相合作的各国协会之间的一个国际机构……凡遇有适当时机,中央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组织或地方性组织提出建议”[2]18。这表明,总委员会不是高度集权的指挥中心,只是沟通和协调各国工人组织的国际机关。它的日常工作是向各支部通报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组织调查欧洲的社会状况,讨论一国协会提出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和向各国提出建议等等。在后来的会议上,总委员会的权利有所扩大,突出表现在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 “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4]。但无论如何,总委员会只是一个执行机关,各支部和会员仍然享受充分的自由。
二、第一国际同各国工人组织的合作与实践
第一国际成立后,它同各国的工人组织既有思想认识上的争辩,又有组织形式上的合作。它之所以能够在团结各国工人阶级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原因是它在处理与各国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上坚持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在国际合作上的联合统一与各国工人运动中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是由第一国际的组织性质和组织形式决定。第一国际内各国工人组织具有独立自主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不违反 “共同原则”的基础上允许各支部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纲领和组织形式。马克思认为协会可以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属于自己的理论纲领。所以,第一国际成立之初,内部就存在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在英国,工联主义、欧文主义和宪章派占统治地位;在法国,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占主导地位;在意大利,马志尼主义占主要地位。《章程》规定一切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加入第一国际,但加入的条件就是承认协会的章程和协会主要目标,即“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5]17。也就是说协会不仅承认组织会员,也认可个人会员。第一国际内部不仅有工会、合作社、互助会、教育团体等组织,还有宪章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个人会员。协会还规定,“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兄弟般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5]18,规定 “任何独立的地方组织均可与伦敦的中央委员会直接通信”[5]18。
第二,各国支部拥有领导本国工人运动的独立性。第一国际只是规定一个 “总的范围”和 “总的原则”,第一国际并不要求每个支部统一执行。各国工人组织完全可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策略。因此,日内瓦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第一国际的职责是联合工人阶级,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各种死板的制度,代表大会只应当公布若干共同原则,不应推行某种具体的合作制度,就像马克思说的 “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着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6]。
第一国际在处理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事件上始终坚持 “国际合作上的联合统一”这条根本原则,毫不妥协。马克思在与 《世界报》的记者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公认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需要”[6]。“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它就失掉被称作国际的权利”[6]。在当时,巴枯宁想把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打入第一国际,企图从内部分化并取代国际,以争夺领导权。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行为破坏了第一国际的统一团结,他指出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7]1873年5月,总委员会把巴枯宁分子开除出第一国际。
三、第一国际处理内部纷争和组织关系的策略与实践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大会时选出的32人总委员会中,真正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也只是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两人。马克思在起草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 《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后,实际上就掌握了协会的领导权。如何处理好与协会内部各种非社会主义流派的关系,马克思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在坚持国际团结的立场上运用了以下策略:
第一,承认彼此之间有分歧,先团结后引导。针对协会建立之初,各国工人发展水平很不一致,他们又容易受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马克思采用 “形式上温柔,内容上坚决”的表述方法起草了带有各派都能接受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 《宣言》和 《章程》,虽然 “一切党派都接受和满意,并不等于说,它们都理解了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实质”[8]。马克思为了国际工人运动大局,承认彼此分歧,耐心说服教育,尽量把他们都融合到第一国际之中。法国工人代表托伦和弗里布尔出席了圣马丁堂成立大会,他们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却并未与他们直接交锋,当 《宣言》和《章程》英文版出版后,马克思就把它们寄给了托伦和弗里布尔,希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去影响托伦,他还向巴黎方面询问 “他们在组织支部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9]。拉萨尔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德国工人的机会主义思潮,它对德国的工人运动起到了消极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传播的障碍,也是德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绊脚石。马克思希望通过第一国际来影响德国无产阶级,使德国工人摆脱拉萨尔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第二,以理论斗争代替组织制裁。“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为确立一种指导整个运动的共同思想和制定一个包括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实现方法的纲领而进行思想搏斗的历史。”[10]143-144第一国际在对待内部非马克思主义流派时,起初并不是采取激烈的斗争,而是在会议和交往中逐渐等待各派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第一国际成立之初,马克思一方面团结利用英国工联组建第一国际,另一方面针对工联主义进行了思想理论上的斗争,他认为英国工人运动长期缓步不前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革命的理论作指导。1865年6月,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议上作了 《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这也是他在第一国际中作的唯一一次报告,报告给英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需要说明的是,工联领导人奥哲尔之所以被撤销第一国际领导职务,不是因为他坚持阶级调和和改良主义的观点,而是因为他坚持大国沙文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这与第一国际联合统一原则相违背。
如何正确对待第一国际内部不同国家工人组织的关系也是事关第一国际团结的大事。第一国际在处理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中既坚持了独立自主和相互平等原则,也反对第一国际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这对于维护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第一国际反对内部一个组织凌驾于第一国际之上,也反对内部某一组织利用第一国际谋取宗派私利。第一国际内部的蒲鲁东派反对马克思的正确路线,他们认为第一国际应当通过合作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想改变第一国际信条,把第一国际变为 “合作社”。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经过斗争,于1867年的洛桑会议通过了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决议,决议指出 “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不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绝对必须的措施”[11]。这个决议实际上否定了蒲鲁东主义者的主张,说明了蒲鲁东主义宗派活动的失败。
其次,第一国际在处理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时体现了一律平等原则。马克思积极支持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他认为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的堡垒,“一旦这个堡垒在爱尔兰崩溃,英国的这个堡垒也会随之完蛋”[10]196。19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和爱尔兰已经成立了一些第一国际爱尔兰支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支部有利于向爱尔兰人民传播先进思想。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第一国际内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爱尔兰作为独立的支部存在,主张爱尔兰支部应作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一个支部,接受它的管辖。1872年公民黑尔斯提出在英国成立爱尔兰民族分部违背共同章程和协会的原则,他认为 “在英国成立爱尔兰分部只能使长期以来不幸地存在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对立继续存在下去”[12]145。恩格斯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提案实际目的就在于使各爱尔兰支部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爱尔兰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且 “总委员会无权强迫任何一个支部或分部承认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的最高地位”[12]147。恩格斯的发言得到了绝大多数委员的支持,最后,此项提案未获通过,大会维护了第一国际内部各组织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四、第一国际处理党际关系原则的现实意义
第一国际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继起者,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活动家,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提高了广大工人的思想水平,并成功地把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摆脱了工人运动盲目自发和彼此隔绝的状态。第一国际所取得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领导,这更多地体现在第一国际正确处理工人运动中党际关系的原则和实践上。当前,如何更好地处理党际关系,第一国际给了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积极总结和吸取国际共运史上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长期以来,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党际关系的方针政策。第一国际成立伊始,就在《宣言》和 《章程》中规定了协会的组织原则和处理与其他工人组织的原则。我党第一个处理党际关系的文件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并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章程》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3]至此,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
第二,求同存异,尊重各国党派的具体实践。以往我们总是把党际关系理想化,总认为大家既然目标一致,就应该彼此统一合作,以取得共同目标的胜利,而对于彼此的矛盾和分歧,总是被忽视和掩盖,可当彼此矛盾爆发出来的时候,又往往以传统的思维指责对方背叛和变质。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和社会党 “分分合合”的关系中看到,这两类党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承认东西方的差异,总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有时甚至要把自己那一套强加给对方,甚至不承认对方属于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14]。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在处理与各党派的关系时应该坚持平等原则,不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不做凌驾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之上的“老子党”。
第三,积极与各国政党合作,取长补短,为我所用。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应该是开放的政党,这里的 “开放”指的是能够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当今世界 “一球两制”的局面将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社会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政党的关系已经不是革命年代的敌对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能把视角仅仅局限于政党之间意识形态是否有一致性,而是在事关人类共同问题和本国发展上大胆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合作,使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其他优势为我所用,加快自身发展,并在合作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最后,做好共产党自身党建工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一国际告诫它的继承者要珍视工人阶级队伍的国际团结。”[15]在第一国际诞生时,就指出了各国党支部独立自主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一个党的单独存在比它们形式上参加国际性的团体更为重要,这样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各支部发挥自身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党的建设好坏与否事关全局,“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16]。我们要根据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的党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更好地把握主动性。
[1]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年[M].时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徐宝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2卷):第一国际第五次(海牙)代表大会文献[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0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1.
[7]王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6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 (1868-1869)[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52.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1.
[9]巴赫,戈尔曼,库尼娜.第一国际(第一卷)(1870-1876年)[M].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251.
[10]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一卷)[M].杨寿国,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1]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M].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68.
[12]张文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6.
[14]黄宗良,林勋健.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84.
[15]巴赫,戈尔曼,库尼娜.第一国际(第二卷)(1870-1876年)[M].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584.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86.
(责任编辑:周凤)
10.3969/J.ISSN.1672-0911.2015.04.058
D11
A
1672-0911(2015)04-0058-05
2015-04-27
郭芷材 (1990-),男,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