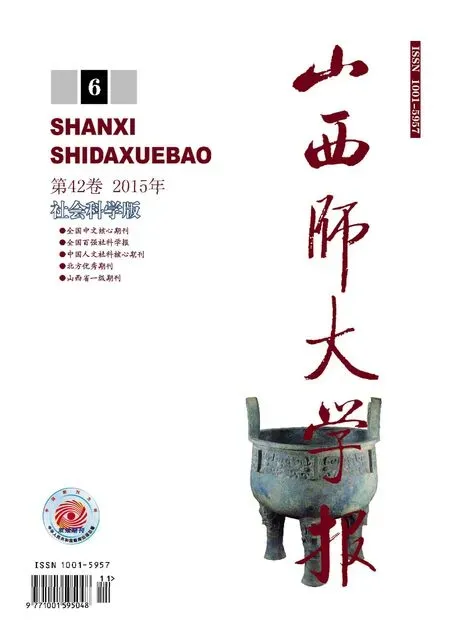个体化时代的文化拯救与诗意信仰
----小岸小说创作论
金 春 平
(山西财经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太原 030006)
新世纪之交以来,现代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悄然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城乡格局,城镇化和城市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发展的主导趋向,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社群化”社会开始步入“个体化”社会,所谓的“传统”意识形态,也正在被一切以“后”命名的解构性价值形态所取代。但传统“解构”的结局并非现代性的文化盛事,却是文化残局的真空,现代性的“建构”在中国仍然呈现为“未完成的工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初,全球化浪潮、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物质主义等多元价值理念在当代社会的蔓延,在带来国人感官解放和物质享受的同时,“人”却最终滑向了信仰扭曲的“心灵渊薮”和精神景观的“家园荒原”。城镇化进程引领下的个体化时代,人的现代化如何深入开掘,如何进行解构残局后的文化重建,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亟待解决的文化命题。70后女作家小岸,以其独特、沉潜、深刻的女性生命体验,对这一文化难题进行着个体化的诠释和探幽。同时,小岸的小说对“人”的主体性思考,呈现出超越传统现代性或第一现代性的文化特征,进行着第二现代性,即“自反性现代化”建设的趋向。
孤独与荒诞:无奈的自由和存在的游戏
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历史步伐,正击碎着传统乡土文明以家族本位为纲的宗法制伦理秩序,人开始由社会化和群体化的人上升为个体化和自由化的人。个体化、自由化,既是现代性的要义,也是现代性的期望。但是,个体自由权利的成熟和获取,却演变为“个体越来越受到自由之累,空有自由之身,渐成孤立之人,反而丧失了自主的能力”[1]之人。对这一隐秘、强大却又无法言说的精神状态,小岸以其敏锐的洞察、细腻的刻画、巧妙的叙事,谱绘出在灯红酒绿的城市景象和大国崛起的浮华和喧闹掩盖下个体之“人”心灵无以逃遁的“孤独”。
《比邻若天涯》中,朱文妮在摆脱无爱婚姻之后的人身自由,却无法弥补自我心灵的自由,与田云飞的邂逅和一夜激情是对孤独的反抗,但一切仍回归于爱与自由的失落和孤寂;《半个夏天》中的“孤独”女孩小莲对彭思阳的暗恋是她唯一慰藉孤独心灵的方式,但彭思阳的悄然离去只给这个女孩带来一场“爱情白日梦”;《温城之恋》以诡异的穿越结构,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人鬼情未了”,迟岩对美丽、单纯、近乎完美的蓝心的极致“纯爱”,在“穿越”到现实之后,仍然是不得不面对的残酷孤独;《水仙花开》以动人的情感笔触,叙述了水仙和张泽兴之间爱情契约的“失信”,看似充盈而丰富的个人日常生活,却始终满溢着忧伤,“孤独”的个体渴望着温暖的情感,却是以悲情结局;《海棠引》中海棠的生活轨迹,更像是萨特箴言“他人即是地狱”的验证,看似“圆满”、“和谐”的家庭,原来夫妻之间竟然隔着无以言表的孤独之河……
小岸的城镇叙事,摆脱了对宏大历史和时代政治漩涡中人的不自由审视,也不停留于传统乡土文明或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的禁锢或扭曲的凝望,人不再承受传统文化枷锁、阶级政治枷锁,甚至物质匮乏枷锁之重,人的心灵在城镇日常生活空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小岸并未执著于自由获取之后虚幻而肤浅的狂欢当中,却在其小说中先觉性地触摸到了人在解脱种种无形重负之后的“心灵自由”,实质是陷入了思想自由的“孤独”境况,“‘人’刚从传统文化和政治桎梏的‘不自由’当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世俗’和‘物欲’的‘不自由’当中”[2]。小岸笔下的孤独,源于对自我本真的清醒认知,也是人的自我权利或曰主体性的确认。它虽然伤感,却并不需要怜悯,“孤独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释放和驰骋,也是身体权利和伦理陈规的冲决。因此在其小说叙事中,可以一夜激情,可以友情聚散,可以家庭破圆,一切都是在自由的选择中开始和结束,与此同时,人也是从拒绝孤独中又最后走向宿命般的孤独。正因如此,小岸的小说创作已经迈开了对“当代人的现代化走向”这一难题的个体化言说步伐,并敏锐地感受到了个体的“孤独”和无奈的“自由”,恰是当前社会人类所不得不面对的“精神存在”,这也正是启蒙主义者和现代化号召者所始料未及的人的“现代性危机”的负面后果。这种现代性后果,既包含对现代性的合法性在个体化社会失效的质疑,也透视到了隐藏在社会转型中个体心理文化依托资源的失落,小岸直面着虚假喧嚣时代背后人文精神的败局,更审视着个体心灵的柔弱机理。
个体化,其基本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的高度分化,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分殊逐步进入层化、级化,甚至极化,其潜在的对比参照概念就是“整体化”。因此,孤独的个体已然失去了整体关系网络的多元化位所,哲学意义上的“荒诞”在文学生活空间当中就演变为人际和现实的“游戏”和“戏剧”。这是小岸对生活复杂的理路清理,是对“整体生活”与“个体之人”关系的深度刻摹。小岸搭建小说与世界之间的通道,始终试图走向“深度”的“尽头”。但这个尽头却是令人不忍面对的画面,每个个体都在积极努力地进行自我意义的赋予,但却普遍以“无意义”的“荒诞”、“困境”、“虚无”收场,个体之人终究无法逃脱命运之神的捉弄,只能走向心灵的孤独和精神的荒芜。
《你知道什么》当中,作者以嵌入式的叙事视角进行衍射,一场偶然车祸竟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般的心理连锁反应,将一群看似没有任何关联实则又是身处人际封闭圈内的所有人的美满毁灭。在小说中,几乎每个人都在不由自主中走向不可预知的黑色深渊,死亡、背叛、意外、欺骗……《梦里见洛神》当中,杜浩然与辛晓雪轰轰烈烈的婚外恋情,却因一个藏有两人大量私密短信手机的丢失而发生戏剧化的转折,杜浩然成为“网络红人”,仕途夭折、女儿高考失利、妻子离家而去,为了寻找人间的“真爱洛神”,却被虚拟的“网络厄神”玩弄,真实和虚幻恍如春梦;《车祸》当中的袁小月,在沉闷的日常生活漩涡中,并未放弃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执著和努力,一次阴差阳错的“被死去”却最终发现,自己的“死”不仅没有对人际之网和生活之海激起任何波澜,还让很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死亡”与“复活”、“灾难”与“幸福”,竟然奇妙地进行了颠倒、置换和错位,个体化时代的生命、生活和人性,最终裸露出的是不堪入目的“荒诞”和“虚无”。
这种令人“惊讶”甚至“绝望”的“存在”发现,显然是小岸对当代社会人类生存透视后的自我构建,更是小岸基于生活审视和生命体验的无奈总结:生活没有完美,生命没有圆满,但残缺和碎片,恰又是当代社会个体化转型当中个人权利获得高度自由选择的结果,后现代的隐忧不仅悄然成为生活的常态,原来,意义的消解、颠覆、解构,早已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当中。也正鉴于此,小岸在全国的同代际的作家群当中,显示出了相当的思想先觉性和先锋性。
家园与怀恋:重建的皈依和文化的追忆
个体化社会的转型结果是在破解权威、消解传统、颠覆经典之后,人也随之呈现出了异质化面貌,人的主体性发展开始进入更高阶段。但与之相随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自我的意义赋予如何获取?人在获得“自由”之后,如何构建主体觉醒、主体独立、主体完整的价值资源?而小岸则以“守望传统”的姿态,开始建构着当代社会个体人的精神家园。这种资源摒弃了第一现代性所提倡的民主、理性、科学等界域分明的实用型、政治型理念,转而以“退”为“进”、借“回归”为“化用”,对“传统文化”和“乡土文明”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和借鉴,以此来建构个体化社会当中,整合人的流变、多样、未定、异质的共享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小岸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拯救”或“文化救赎”的努力意识,内隐着以“传统文化”和“乡土文明”为基石的价值取向,这也成为贯穿其作品始终的灵魂。
首先,小岸的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个体之人在实现着现代性所倡导的人格独立、性别独立、主体独立,但精神家园丧失之后,以“恪守传统文化伦理法则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心灵家园”的“寻觅”和“重建”的温情景观。《回家》当中,家庭的形式组织并未真正蕴藉着“精神之家”的情感认同。但父亲的“宽恕”、母亲的“赎罪”、丈夫的“孝廉”,甚至路人的“亲善”,一个个因情与性的分离造成的情感悲剧,在“以和为贵”的“大爱”蔓浸之下,剥去了晦暗的面纱,展示出家园复得的温馨与魅力。流变中的孤独个体,在传统家族文化伦理的感召下,寻得安身的处所,觅得家园的复归。《杨杨的理想》当中,杨杨几乎苛刻和自虐般的存钱,都是为了她心中圣洁的“家”。传统文化当中的家族伦理信仰成为支撑杨杨不懈努力的心理动机,也正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当中,杨杨看似单调而平凡的生活也因而充盈和丰沛起来。小岸作品世界中的人物,都在努力地寻觅和重建着遗失的心灵家园,这种精神家园的构建,立足和扎根于本土传统文化和乡土道德伦理,它们不仅是个体化时代能够进行个体单元整合的文化粘合剂,同时也实现着对个体社会普遍的精神沉沦的文化拯救和精神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岸通过温情小说世界的打造,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嫁接和转换,并据此对现代性的“副作用”进行着审美式的批判。
其次,小岸对当代价值资源真空的文化救赎,还表现为通过“文化追忆”的“怀恋”来反观当下个体精神的溃败,以此实现对人类“文化精神家园”的“寻觅”和“重建”。人在从“人类化”到“个性化”发展到“个体化”阶段,并无法完全摆脱集体文化传统的制约。个体化阶段的“文化多元”,在肯定其对人的自由发展和思维解放的同时,却并未带来新的价值理念的有效整合;现代工业技术和物质财富的巨大进步,在带来个体现代化发展契机的同时,还未能形成整体的个人化历史的可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与自我主体性的独立,使当下人的经验图式、行动方式愈趋淡化,人和人更加难以复制出彼此的经历和体验。于是,对“非个体化时代”的“集体怀恋”和“文化追忆”,就具有了对当下个体之人进行“文化家园”“寻觅和重建”的意义。长篇小说《在蓝色的天空跳舞》中,作者将叙事时空设定为“过去”和“现在”两大情境。小说在追忆青春体验的同时,“青春叙事”更多蕴藉着“人”的文化追忆。苏娅与贾方方、常秀妮、罗小玲等同性之间的友情,在青春期羞涩懵懂的心理浮沉和细腻婉转中,却不失超越现实功利的“纯”与“真”;苏拉对苏娅的朦胧暗恋、苏娅对老师钟远新的执著暗恋,这场“暗恋”与苏娅和姜博键为了婚姻的“择偶”行为,恰恰是功利世俗“爱情”和美好本真“爱情”的对比式反讽;对“爱情”的渴望,以至于苏娅和卷毛的一夜激情之后,苏娅不惜悔婚也要赋予爱情结晶毛毛以生命权利,这是个体化时代女性主体性觉醒的必然。对世俗陈规的冲决,也是价值失衡年代对以爱情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理念的守护,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精神平庸和心灵单面的文化救赎。《比邻若天涯》中朱文妮与田云飞近在咫尺的回忆,田云飞与顾真真的初恋回忆,《温城之恋》中迟岩与蓝心的纯爱追忆,《水仙花开》当中水仙与张泽兴的羞涩初恋,等等,小岸的这类文化追忆和生命怀恋小说,绝非停留于存在主义层面的“再现”,而是不断通过回忆的叠加与当下现实的隐形参照,“表现”个体社会的一种文化认同和价值分享,以此来整合早已松散的文化碎片,重建价值虚空年代的文化基石。
神性与人性:诗意的生存和价值的信仰
个性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流动、独立、异质成为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人在获得了高度个体化自由选择的权利之后,“无根”与“漂泊”也成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自反性现代性,就是对信仰缺失、价值消解的反叛,它试图对人的存在和意义进行整体性的认知自赋,对现代性过程中人的个体化的过度“自由”和“多元”进行制约和整合。小岸的小说并不回避生活的复杂和残酷,凌厉的生活质感、戏剧般的烦恼人生、残缺不全的爱情婚姻,等等,都是小岸必须直面的现实存在。但是,在观照庸常人生与平淡生活之时,小说却始终有着“神性”和“人性”之光的烛照,以此来穿透个体化时代人的心灵沉钝与精神荒漠。是在心灵漂泊、灵魂躁动、生活迷茫、苦难随行的现实处境当中,“神性”和“人性”的存在,是人能够诗意生活的带有宗教信仰般的精神资源。
小岸小说中人物的“神性”,“是指不可企及的只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人性的完满性、理想性实现”[3],有着超越世俗、不染尘埃的“极致”的“天使之美”,这种神性的存在,是对当下俗世人生的参照对比,也是荡涤生活丑陋的上帝般的大智。《温城之恋》中的乡村姑娘蓝心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性女子,这个充满古典韵味的穿越式爱情故事,虽有着男权意识下对女性形象的期待和东方式的“蝴蝶情结”,但蓝心的“神性”更蕴藉着对个体化时代风花雪月、饮食男女、随意爱情和游戏情感的鞭挞,是对个体化时代“爱情自由”选择权利的警惕和反思。在《半个夏天》当中,小莲对彭思阳爱的执著与至真,恰是当下时代真情不在、爱情消解时代的悠远钟声,这种神性之圣洁,是对心灵尘埃的洗涤和净化,也是对现世功利爱情和婚姻无望破败现状的有力的文学性、想象性鞭笞,深隐着小岸对“理想”爱情和“古典”人伦回归的渴望。《水仙花开》当中,水仙这样的纯情女子,恰恰烛映出世俗纷扰和物质喧嚣年代个人生活的看似卑微,却包含着对人类精神的无法超越、遗忘永恒、拒绝记忆、不信爱情的“时尚”大众理念进行回击的力量,也正是因为有神性之光的存在,小岸的小说有生活的忧伤却并无生命的绝望。
小岸创作中的“神性”在投射于一系列女性形象之时,男性形象同样有着“神性”的伟岸光芒。他们以其神性般的璀璨和力量,化解着生活中的种种误解、悲情、低微和扭曲,是生活得以继续、圆满,是让个体之人不失追求幸福和诗意生存的动力源。在小岸的小说当中,一系列“父亲”形象,具备了神性之父的所有品质,隐忍、大度、无私、关爱、宽容、无怨……集体无意识当中“父亲”应具备的一切元素,都可以嵌入其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当中。《回家》中的“父亲”,用理解、宽容、博爱,原谅了母亲年轻时无奈的出轨,包容了儿子并非自己亲生骨肉的事实——只为了家的圆满。《余露和她的父亲》中余露的三次“恋父”情结,是对记忆中父亲神性的守候——因为父亲是为自己而殒命。父亲俨然成为余露心中的“圣洁”之人,这是一种信徒与教父般的虔诚关系,尽管隐藏着心理的危机和乖戾。
小岸小说中“神性”人物的存在,在带来精神馈赠的同时,脱俗与空灵也成为其作品的主要特征。生活的多元和复杂,固然需要神性的光芒,更需要以沉潜的姿态,触摸生活的质地,也更需要对人性复杂的深入理解。在当前的个体化社会当中,后现代理念的甚嚣尘上,使得对人性的内涵理解日趋多元,道德化审判已逐渐失效,“多元人性”取代了传统的“道德人性”,并成为衡量个体时代生活模态的基本价值理念。小岸的小说,正是对多元人性与复杂生活的勾勒,生活的“酸甜苦辣”被生活的“丰富多彩”所取代,人性的“善恶美丑”也被人性的“本真真实”所解构,一切在道德化的“不合理”审判当中,又呈现出“理所当然”的合理色彩。
《卡》巧妙地通过一张空白银行卡,串联起了四个家庭、五段人生。对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的心理和行为的审视,传统道德审判已经失效,更多的是人性元素的作祟使然。但无论是私吞、行贿、受贿、婚外情,都无法用传统道德伦理的“对错”来衡量,对与错已经没有界限,只有隐藏在所有行为背后的人性使然。《守口如瓶》当中,小岸设置了“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两大空间:现实空间当中,苏素、丈夫武修文、朋友唐叶,每个人承担着各自的社会角色,都是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个体,在生活之流中行进着。但是网络空间的链接,却让三个不同的个体灵魂有了慰藉和依靠的理由,原来“社会角色”和“本真人性”之间的错位和间离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守口如瓶”不是信守任何社会诺言,而是信守着角色重压下人性的纯粹与澄澈。
为了凸显出个体“人性”在残酷生活中对群体道德伦理法则的超越,小岸在《零点有约》中将“人性”与“法律”进行了尖锐的并置。因杀人而隐匿于山村煤矿的韩国强,怀着对广播节目零点有约主持人钟梅若的无保留信任,最终投案自首。生活的荒凉、世界的残酷、命运的不济,唯有人性,以及人性当中最宝贵的信任,才是这个个体时代和冷漠世界的情感纽带和温暖之火。小岸在《零点有约》当中,彻底完成了对道德化和理性化价值判断体系的扬弃,欺骗、犯罪、巧言,乃至杀人,这些传统道德法则当中惯常认为的“丑”与“恶”,早已被“人性之光”的妩媚和耀眼所遮蔽,人性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价值灵魂,构筑起了小岸小说人性化叙事的永恒命题。
以神性作为平庸现实的“理想彼岸”,以人性作为观照生活质感的“此岸切口”,是小岸小说和故事构筑的内在线索。在个体化社会信仰溃败的年代,“神性”和“人性”既成为个体自我反省的内在价值参照,也是个体之人获得意义确认和赋予的生活理由:“人性”成为小岸有意展示生活奥秘和复杂理解的基础体验和基础话语,而“神性”是小岸小说呈现昭示价值和意义重建的内在价值机体,这也构成了小岸“温情叙事”的文化命理,从而成就了小岸在山西文学界和中国当代同代际作家群当中的独特之质。
底层与女性:日常的表达和话语的重觅
个体化,意味着传统的金字塔形阶层固化模态逐渐被打破,个体成为社会网络关系当中的一个基础单元,“个体流动化”将成为个体社会的基本形态,底层这一社群时代的重要概念,也将成为一个相对性概念,底层话语的表达,即演变为日常化话语的表达。因此,小岸的小说,虽有一部分是以“小人物”在社会“底层”中的艰难与苦涩的生存图景为内容,但其“底层意识”,即对社会的不公、阶层的压迫、机制的弊端等领域的批判性并不十分显著,一切的悲苦都在“人性温情”的“大爱”之下走向消解。她的小说,一类关注于非个体化时代的“小镇生活”,以《水仙花开》《半个夏天》《车祸》《杨杨的理想》等作品为代表。这类作品当中,社群组织是其基本的社会机制,“底层”的概念还有着基本的界限归属,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之间的不对等,也因着地域、经济、文化、价值观等的阶层分殊而充满悲情意味。但由于有“人性”之“真爱”、“宽容”、“仁善”等作为调和,这类作品底层化叙事的批判锋芒已经被“真爱”温情所削弱,进而充盈着浓郁的日常化生活气息,人物也“安详”、“幸福”地享受着虽然清贫却又静好的岁月。另一类作品关注个体化时代的“城镇生活”,以《卡》《海棠引》《零点有约》《梦里见洛神》《你知道什么》等为代表,这类作品不着意于人物的社会阶层划分及其道德观照和社会批判,因为在这类作品当中,底层、小资、中产的界限渐趋模糊,所谓的身份和地位的随时转化和置换,已经成为个体化社会不足为奇的景观。即使有对底层悲苦和人性丑陋的展览、鞭挞和追问,但小岸的绝大多数城镇叙事类小说,阶层划分渐趋同构和平面,并通过诗意化的“人性叙事”,消弭了底层概念的界限,从而建构了一种个体化时代“底层的日常化表达”的新型话语。应特别指出的是,小岸关于女性话语权的表达,出现了本应独立却被长期遮蔽的“话语权回归”,即传统女性的话语由压抑和沉默,走向女权时代对男权的对抗和反叛,但在个体化时代又复归到性别同构、性别平等的两性相对性话语权,“小岸小说的女性意识打破了男女之间的尖锐对立,采取了另一种更合理的突围方式,与男性站在同一方位,共同去探讨人生境遇中的种种困境。”[4]
小岸的城镇叙事类小说,试图思考从“性”——“爱情”——“婚姻”——“家庭”等一系列生活图景在个体化时代的断裂、抵牾和分散的现实与困惑。按照社会学对“婚姻”的定义,婚姻作为个人活动结果的“生活实体”,其核心是:持续的性关系+共同生活(包括情感、经济、生育);但作为“社会设置”,其核心是:契约关系的“婚”+当事人家庭的“姻”(当事人的地位、角色、权利、义务);“家庭”作为“生活实体”,其核心是:实体婚姻+子女+生活共同体,但作为“社会设置”,其核心则是:血缘+供养+继承。[5]189—190个体化时代的到来,女性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婚姻和家庭当中,两性地位与角色在变化,传统性别的不对等关系正在被颠覆,稳固的、依托的、专制的性别模式,日益被流动的、平等的、民主化的性别模式所取代;个人的自由选择空间空前扩大,传统婚姻和家庭模式当中的“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传统婚姻当中夫妻的共同生活目标,正在被“后家庭时代”的“从需求共同体到选择性亲密关系”家庭理念所取代;传统的两性模式、爱情模式、婚姻模式、家庭模式之间高度统一,因为个体化的社会制度和自由理念的介入,阻断了四者高度统一的可能,更多呈现的是碎片化和分离化。小岸的情爱系列作品,全方位表现了这种个体化社会的转型对传统爱情、婚姻和家庭模式的解构,以及这种解构给当代女性所带来的“自由选择权利”和“传统角色瓦解”之间难以调和的存在、困惑和反思。与此同时,小岸也在其价值构建上,呈现出试图用“真情”和“大爱”来化解这一切残酷生活困境的文学超越性努力。
在小岸的城镇文学空间当中,性、爱情、婚姻、家庭的不协调是其重要的生活审视对象。维持“生活实体婚姻”的核心组件,即“持续的两性关系”和“共同的情感、经济、生育生活”出现分裂并开始走向分解——或者有“性”无“情”(《比邻若天涯》《你知道什么》《杨杨的理想》),或者有“情”无“性”(《海棠引》《你知道什么》)。“社会设置层面的婚姻”也开始出现分化——或者有“婚”无“姻”(《你知道什么》《车祸》);或者有“姻”无“婚”(《零点有约》《在蓝色的天空跳舞》《梦里见洛神》)。“生活婚姻”和“社会婚姻”的错位,最终导致了“生活实体的家庭结构”和“社会实体的家庭结构”构建的难度。因为,个体化时代对传统家庭模式的巨大冲击,或者使得作为生活实体的“家庭结构”(实体婚姻+子女+生活共同体)不再圆满而渐趋残缺(《回家》《守口如瓶》《梦里见洛阳》《车祸》);作为社会实体的“家庭结构”(血缘+供养+继承)也在步入碎片和坍塌(《回家》《车祸》《在蓝色的天空跳舞》)。生活实体层面的“婚姻和家庭”和社会实体层面的“婚姻和家庭”本应是高度一致或者基本一致,但是个体化社会“后家庭时代”的到来,使女性有充分的自由与异性进行“亲密关系”的建立,这也导致了两者高度的分离(《在蓝色的天空跳舞》)。在小岸的婚姻小说当中,“情”与“性”、“婚”与“姻”、“家”与“庭”之间的现实落差,是作品当中各个婚姻走向解体的直接原因,小岸通过一个个婚姻失败的文学注脚,反思着个体化社会女性在生活实体婚姻和社会角色婚姻当中,获取一定性别自主权后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角色、情感、责任和心理困境。
传统婚姻和家庭的解构,虽然符合现代性所一直倡导的人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实施预期,但解构的摧枯拉朽却忽略了“情感”“责任”“义务”的遗失,也直接导致了传统文学情爱叙事经验和道德伦理的尴尬处境和失效境地。而小岸的小说,试图从“人性”出发去建构一种在性、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处理当中的“利他型的个人主义”道德伦理——即以充分履行“社会设置层面”的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为前提,以不伤害社会设置层面的“丈夫”“妻子”“子女”为前提,但又充分享有生活实体层面的两性之间的“性”和“爱情”为目的,并辅之以 “宽容”“理解”“体谅”“平等”的“人性之温与善”,以此作为个体化时代,整合传统乡土爱情文学和新兴城市情爱文学的一种可能的有效经验。
综上所述,传统乡土文学向现代都市文学的转型,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潮,但如何构建都市文学的价值体系,如何构建都市文学的审美空间,如何让都市文学介入到当前社会和当下的人文精神领地,却是中国乡土文学历史惯性和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难题。小岸的小说同样具有70后作家不及老一辈作家的“先天不足”:“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作家不再可能有深厚的乡村经验”[6],但是,这代作家同样具有老一辈作家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他们有着充分的自我意识,他们没有强大的20世纪的历史记忆,他们更愿意去追随个人的生命旅程。”[6]与同时代的国内70后作家相比,小岸试图以其“城镇叙事”沟通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的内在价值理路和伦理法则,在看似柔性和温情的人性化叙事背后,则是以“自反性现代性”为内在基石,“与其说中国当代文学呼唤城市文学……根子里是我们未竟的现代性事业”[6]。她的创作不仅将文学的聚光灯聚焦于个体化时代和城市化空间当中的人的荒凉生存图景,而且创造性地借用“传统文化”和“乡土文明”对城镇荒漠的人进行“绿化”“惠泽”和“救赎”,并以“文化记忆”的方式,承担起了其他70后作家所普遍拒斥或者遗弃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反思权。虽然其文学探险有时也存在着理想化、封闭化的倾向,对正面人性的过高期望和宣扬,导致其对人性的复杂,以及对个体化社会运行机制的缺陷的审视,缺乏更为清晰和明确的价值判断,但这样的一种尝试和努力,恰恰代表着中国城市文学走向成熟、成就经典所必经的阵痛、考验和前锋。
[1] 熊万胜,李宽,戴纯青.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式悖论及其出路——来自一个大都市的经验[J].开放时代,2012,(10).
[2] 金春平.风景叙事与小说主体的现代性理念流变[J].当代作家评论,2014,(3).
[3] 傅书华.神性、人性与社会性的纠结[J].当代文坛,2013,(6).
[4] 赵春秀.何需杀死安琪儿[J].文艺争鸣,2013,(5).
[5]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 陈晓明.城市文学:弯路与困境[J].文艺争鸣,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