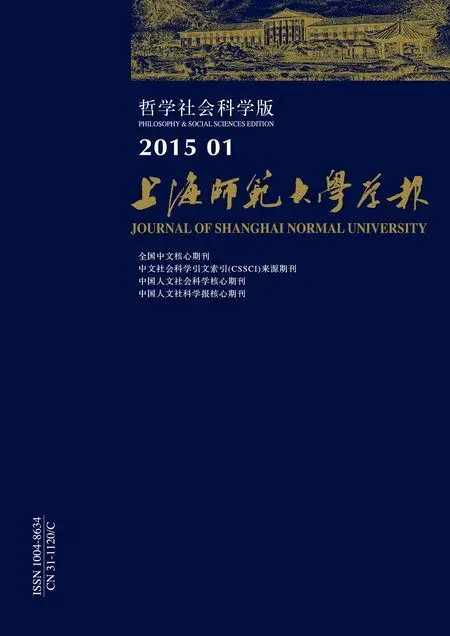明清话本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
秦 川
(九江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一、明清小说之文士形象与社会风习
所谓文士,泛指读书人,包括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各级大小官吏在内。“三言”、“二拍”以及李渔话本小说中的文士,遍布于明及明以前各代。具体来说,李渔短篇小说3个集子,去其复重篇什,计小说30篇。这30篇中,除《十二楼》中的《合影楼》《夏宜楼》系元朝至正年间事、《拂云楼》《鹤归楼》《生我楼》为宋朝故事外,其余25篇均为明代故事。而“三言”中120篇小说,其中只有21篇为明代故事,如《喻世明言》中3篇,《警世通言》中8篇,《醒世恒言》中10篇。其余皆宋以前故事,其中唐宋者居多,而宋尤突出。“二拍”中78篇,明代故事有26篇,分别为《初刻》14篇,《二刻》12篇。合起来看,明代故事约占3位作家4个集子总数的32%,而明以前的故事则占68%。通过对这些小说各类人物群像的梳理和分析,可以了解明及明以前人们的趋尚与社会风习之关系,而文人学士以及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读书人是小说人物群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诸篇中的知识分子,因各自所处的社会时代不同,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且心性各异,喜好有别,因而情况复杂,都充分体现了其所在的时代的气息和具体人物的个性特征。但作为在中华古老文明这个大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各代知识分子,其人生追求和风尚习气也有着明显的共通的延续性,以致形成小说戏曲中被今人所批评的“脸谱化”、“类型化”群像。
1.进入仕途的大小官吏与社会风习
清官、贪官是对比明显的形象概念,任何时代,无论是清明的王朝还是污浊的王朝,总少不了清官、贪官这两类人物,只是孰多孰少的问题。本文所及话本小说中正面描写的大小官吏,皆系为政清廉,且善于行政、知错就改的清官和能吏,而作为反面形象的贪官、庸吏,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手法间接透露出来的。这与《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以揭露为主的作品大异其趣,显然是要歌颂清官、好官,以寄寓作者对风清气正、公正廉明、造福百姓理想官场的深切渴望。
明清话本小说正面描写歌颂的好官、清官为数不少,如有为官清介、人称“鲁白水”的鲁廉宪①,正直清明一心想做好官、单吃任上一口水的县令石璧②、苏云③,少年得第、敢言善诤的县官虞继武④,“少年聪察,专好辨冤析枉”的陈廉御使⑤,大器晚成、官至抚台、“三番知遇”却三世报恩的鲜于同⑥,善察迩言、复多奇智、断案如神明的某知县⑦、汪大尹⑧,“到任未几,最有贤声”的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某刑尊⑨,知错就改、自求罚俸的某知府,有识人任贤、善于闻过、善听诤言的殷太史,急流勇退、追陶仿谢的徐州路总管詹碧峰。如此之类,难以遍举,现详举数例,以略展其概。
如《老门生三世报恩》中的鲜于同,系明朝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人氏,他“八岁时曾举神童”,才超董、马(董仲舒、司马相如),志类冯、商(冯京、商辂),但才高而数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举,岁岁观场,不能得朱衣点额,黄榜标名。然而他心态特好,因一心要中进士,一心要做好官,任凭他人耻笑、嫌憎,全不在意。真的得了科第,做了大官,又是那样淡泊名利。他处事公允,和讼有方,特别是对“恩师”蒯遇时的“三番知遇”,他三世报恩,更加受人钦敬。作者以欣赏的笔调写鲜于同的老运和感恩心理、报恩行为,一方面告诫世人“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以鼓舞后学;另一方面,借此以弘扬儒家尊师重道、知恩报恩、为官清正廉明的优良传统和浩然正气。
再如李渔《十二楼》之《三与楼》中的虞嗣臣,十七八岁得了科名,做了一任县官,考选进京,升授掌科之职,为人敢言善诤,世宗皇帝极眷注他。因母亲年老,告准了终养。他廉静居乡,不修宿怨,不仅为欺心谋产的仇家唐玉川说情保释,而且还将父亲的朋友,即那位老侠客暗赠他家的20锭元宝让给“仇家”唐玉川作为赎产之费,十分难能可贵。还有《无声戏》之《美男子避惑反生疑》中的知府,是位知错就改的廉官,他能将自己曾经审错的案子重新翻案,还受冤者蒋瑜一个清白,值得肯定。不仅如此,他还屈尊对蒋瑜道:“这都是本府不明,教你屈受了许多刑罚,又累何氏冒了不洁之名,惭愧惭愧”,颇为难得。与此同时,他还因审屈了这桩词讼而反躬罪己,申文上司,自求罚俸,实不多见。宦官的口碑向来不太好,但《喻世明言》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太监李公公却是此类人中的另类,他轻财重义,助人为乐,为玉成李英和善聪的婚事,侨情认李英为侄,还不惜资财,替善聪备办妆奁。又游说五府六部及府尹县官,使之各有所助,此事被传为佳话。时人有诗称道李公的好处:“节操恩情两得全,宦官谁似李公贤?虽然没有风流分,种得来生一段缘。”
上述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大小官吏身上所体现的修齐治平的儒家正统思想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官理念,已成为历代读书人普遍追求的共同目标,且进一步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为全民、全社会所推崇。这在社会历史中亦不乏其人,如《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在福建寿宁任上的赫赫政绩,一肩行旅两袖清风的清廉作风,至今为广大读书人所景仰。再如宋代的包拯,明代的况钟、海瑞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民间尚有“包青天”、“况青天”、“海青天”之美称,而进入《三言》中的还有描写善断案的包青天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况青天话本《况太守断死孩儿》,以及以况钟在苏州任上巧断冤案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加以改造而成的话本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亦可见冯氏对包青天、况青天等清官、能吏的崇敬和向慕。即使像从未做过官的李渔,常常是以大贤人、真义士、医国手的身份出现,充分体现为政理想。
2.未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风习
未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饱学之士,他们也曾一度热衷过功名富贵,但种种原因使得他们最终绝意功名。这类人物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名士”。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名士与《儒林外史》中揭批的那些“假名士”显然不同,他们都是些具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且个性突出的真名士、大名士。李渔小说《三与楼》之虞素臣、《闻过楼》之顾呆叟以及《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入话中的“乞丐”唐伯虎等,都是作者非常欣赏且热情歌颂的人物,其中《三与楼》《闻过楼》是学界公认带有作者自寓性质的作品,诸多人物言行亦可以视为作者本人的现身说法,而唐伯虎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进入小说中,则反映了李渔对唐伯虎的才华及其鄙视庸官的傲岸风格的欣赏。且看李渔笔下的名士:
《三与楼》的虞素臣,系舜帝重华后裔,“是个喜读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他绝意功名,寄情诗酒,有古董园亭之好。他对人生的理解是:人生一世,任你良田万顷,厚禄千钟,坚金百镒,都是他人之物,与自己无干;只有三件器皿(即日间所住之屋,夜间所睡之床,死后所贮之棺),是实在受用的东西,不可不求精美。所以他毕生精力、钱财均花在楼宇建造上,其“所造之屋定要穷精极雅,不类寻常”。体现一个高人达士对生活的艺术追求。但细察其意,似乎还有其更深层的含义。如“三与楼”自下而上分别题为“与人为徒”、“与古为徒”、“与天为徒”,从这上与天接,中与古通,下与人和的人间胜境中,我们可以遥想这位高人的博大胸襟和旷远情怀。
作为艺术大师的李渔,他曾精心建造的芥子园有“园中之王”的美称,蜚声海内外,与小说中的“三与楼”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其说“三与楼”是虞素臣的理想之所,还不如说是作者李渔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而《闻过楼》中的顾呆叟则明显有别于虞素臣,他虽然不做官,但他与官场联系密切,且关心朝政,常给官场人物提建议,出高招,是官场人物的诤友、畏友和高参。当他迁到远离尘嚣的乡间后,殷太史辈三番五次设套处他,目的是要他回到身边以便进谏。最终殷太史如愿以偿地将顾呆叟弄到事先安排好的“非喧非寂”的山庄安置,还在此间另建一小楼即“闻过楼”与他居住,以便府、县的官员前来闻过纳谏。李渔的一生,虽然也常与达官贵人接触,但他仅以一个文化艺人的身份给他们演堂戏打秋风,多为士大夫文人所不齿。而顾呆叟作为作者的自寓性人物,幸运地受到殷太史等官场人物的赏识,实为李渔“自己骗自己的梦”。
与文学人物顾呆叟的幸运相比,作者李渔的反差太大,他一生不被正统文人所看重,心中的委屈和不平沉积太深,而唐伯虎的傲岸与略带玩世不恭的滑稽便成为作者李渔排遣愤懑和寂寞的极好方式。且看作者笔下的唐伯虎:
一日,一个出使琉球回来的“显宦”经过苏州,慕虎丘风景之胜,特地泊了船只,带着几个陪宾来到虎丘山顶,开了一樽名酒,一边饮酒,一边作诗。当那显宦正在搜索枯肠却难以成句时,唐伯虎便化妆成乞丐前来讨扰。结果是不仅讨吃了显宦的名酒,而且还将那些陪宾尽情奚落了一番。作者也因小说中的唐伯虎成功演出了《六如山人乞食图》的好戏而获得情绪的释放和精神的快慰(《连城璧》第三回《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未入仕的知识分子除了上述那些大名士外,还有一些秀才及以下的小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明清话本小说亦有不少这类小知识分子群像的描写。他们常结社集会、会文讲学、饮酒作诗,如《连城璧》第十二回《贞女守贞来异谤 朋侪相谑致奇冤》中的马既闲、姜念慈等几个年少斯文,他们结为一社,成为地方的名流。但他们的日常活动中也有些低俗的行为,多表现为朋友之间的相互捉弄取笑,如该篇标题已充分证明了他们因讪笑而惹的祸端。还有《连城璧》第七回《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的费隐公为调教或整治一个妒妇而安排的一些闹剧,反映了那时的文人雅士也存在着一些低俗的趣味。这与明中后期文人世俗化倾向不无关系,正如袁行霈所云:“在作品内容市民化的同时,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时兴着一种世俗之趣。”[1](P6)
二、明清小说之商贾形象与社会风习
古代中国是个重农抑商的大国,商人属“四民”之末,加之商人趋利的职业特点和一些奸商的客观存在,所以商人在历代国民心目中的口碑不是太好,尽管事实上也有不少儒商分列于各朝,但人们一提到商人总习惯以“奸商”的恶名加之。
然而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已与以往不同,有不少重义轻财的商人形象在作品中频频出现。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商人蒋兴哥,以十六箱贵重衣物作为“出轨”妻子王三巧的再嫁妆奁,他这样重情轻财的举动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失千金福因祸至》中的秦世良和秦世芳,皆是重义轻利的典范,受到时人的尊重和后人的向慕。值得肯定的还有该篇中那位曾因经商于海上历风波之险,不得已打劫秦世良货物做本钱的年轻商人,作者以颇为欣赏的笔调写他,不仅在于他侥幸成为朝鲜国驸马之后,仅矢志要加利奉还世良钱财,而且在于他那份深厚的民族感情。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的文若虚等也都是本分做生意。如叫张乘运的,小说写他“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即便如文若虚,也是个忠厚志诚的生意人。他原本是个极不幸的人,人称“倒运汉”,但在张乘运及其诸朋友的帮助下侥幸做了两笔大生意,便成了众人中的焦点人物。特别是无意拾得的那个鼍龙壳,当那个识货的买主诚心要出高价购买时,他没有漫天要价,而是接受张大出的5万两银子成交。他还对众人说:“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众人都道:“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而那个买主也是个“存心忠厚”之人,他虽得了这笔便宜货物,但他心里总有点过意不去,所以一直非常礼遇文若虚这帮生意人,并千方百计予以补偿。
值得称道的商人还有《喻世明言》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那个南京应天府上元县的黄公,他以贩线香为业,兼带卖些杂货,惯走江北一带地方。因他买卖公道,所以人皆唤他作“黄老实”。黄老实死后,其幼女善聪化名张胜继续女扮男装,与同乡做线香生意的青年李英结为异性兄弟,合伙生理,甚相友爱。从此,两人轮流往南京贩货,一人留在庐州发货讨账;一来一去,账目毫厘不欺,体现传统儒商友善、敦厚、诚信的美德。像黄老实及其幼女善聪和李英这类雌雄结义“兄弟”合伙经商的故事,还有《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和他的义子义女刘奇、刘方。小说中的刘德,夫妻两口,六十多岁,无弟兄子女。住在河西小镇上,自己有几间房屋,数十亩田地,门首又开一个小酒店儿,过着亦耕亦商的生活。他不仅买卖公平,而且还极肯周济人的缓急。“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银,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掏取。因此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他为刘长者。”其中接济救助方老军及其幼子(实为幼女)的情节极为感人。故事讲述的是方老军及其幼子冒着大雪严寒,一步一跌来到刘德小店时,刘公为他俩备了一碟小菜、一盘牛肉,还暖了一壶酒。当方老军父子只把小菜下酒,牛肉全然不动时。小说有这样一段对话:
(刘公)问道:“长官父子想都是奉斋么?”答道:“我们当军的人,吃什么斋!”刘公道:“既不奉斋,如何不吃些肉儿?”答道:“实不相瞒,身边盘缠短少,吃小菜饭儿,还恐走不到家。若用了这大菜,便去了几日的口粮,怎生得到家里?”刘公见他说恁样穷乏,心中惨然,便道:“这般大雪,腹内得些酒肉,还可挡得风寒,你只管用,我这里不算账罢了。”老军道:“主人家休得取笑!那有吃了东西,不算账之理?”刘公道:“不瞒长官说,在下这里,比别家不同。若过往客官,偶然银子缺少,在下就肯奉承。长官既没有盘缠,只算我请你罢了。”老军见他当真,便道:“多谢厚情,只是无功受禄,不当人子。老汉转来,定当奉酬。”刘公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小东西,值得几何,怎说这奉酬的话!”
不但如此,刘公还为老军延医诊治,后来还收留了刘方为义子。小说中的那位太医,也是个有德性、肯助人的良医,当刘公拿出一百文钱给方老军付药费时,他坚辞不受,说道:“些少药资,全为利市。”此类故事无不感人至深。
而刘奇、刘方这对雌雄兄弟自从刘公死后,把酒店收了,开起一个布店来。因他两人少年志诚,物价公道,因而盛名远播,四方客商皆慕名前来买货,挨挤不开,以致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比刘公时多了数倍。
经商牟利是商人的本等,但当利与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当以义为重、以情为重的儒家道德原则,便成为全民全社会所关注和崇尚的原则。因此,推崇公平交易,讲求诚信为本,倡导重义轻利的商业道德已成为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上述所及商人们的道德行为,也被进一步凝成一种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为全民特别是市民所推崇。相反,那些诸如“三言”中梁尚宾那样的市侩、奸商,只能是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消失。
《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一篇,作者以同情和欣赏的笔调写商人八老的遭遇和奇逢,写出商人的艰辛和时刻惦念娇妻幼子的情状,与白居易谴责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大相径庭。小说如此写道: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
明清小说的作者之所以如此关注商人生活,对他们行商的艰辛予以同情,对他们的商德予以肯定和赞赏,这与明清后期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商人地位逐渐提高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圈中,一些未入仕途的平民文人人数众多,相当活跃。其中不少人本来就出身商人家庭,一些缙绅士大夫弃儒经商或涉足文化市场的也属屡见不鲜”。[1](P5)
三、明清小说之僧尼形象与社会风习
真正的僧院尼庵,是为佛门净地,最为庄严神圣。而正宗的佛教信徒,他们出家是出于修心养性,因而出家人又叫修行者。佛教讲因果报应,讲三世轮回,其理论依据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佛教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存善因得善果,存恶因得恶果;因缘改变,结果也会随之得到相应的改变,是为不易之定律。既然因缘是可以改变,因此命运也就可以改变,所以佛陀反对算命,因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命运。李渔小说中的蒋成、秦世良等,其命运原本不好,就因为他们的善心善行而改变了因缘,进而改变了命运,随后一生顺风顺水,得到善终。这正是佛教因缘和合理论的充分体现。
然而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僧尼,多半是些奸淫偷盗、坑蒙拐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之徒。他们的不轨行为,不仅败坏了山门,而且还危害了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但最终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有一个不自食恶果的。最恶劣的要算“二拍”中的《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以及“三言”中《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简帖僧巧骗皇甫妻》等篇中的和尚、尼姑。这些僧尼,其图谋不轨的动机不外乎钱和色,或主要为钱,或主要为色,或兼而有之。他们常常与社会上一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惯于穿窬爬墙、攀花折柳的赌徒淫棍勾搭成奸,骗色骗财,导致人命官司。“其间一种最狠的,又是尼姑。他借着佛天为由,庵院为囤,可以引得内眷来烧香,可以引得子弟来游耍。见男人问讯称呼,礼数毫不异僧家,接对无妨。到内室念佛看经,体格终须是妇女,交搭更便。从来马泊六、撮合山,十桩事到有九桩是尼姑做成、尼庵私会的。”
这些尼姑不仅为那些淫棍做牵头,而且有时还趁着凑趣。如《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的卜良,作者说他“乃是虔州城里一个极淫荡不长进的。看见人家有些颜色的妇人,便思勾搭上场,不上手不休。亦且淫滥之性,不论美恶,都要到手,所以这些尼姑,多是与他往来的”。而该篇中的赵尼姑则把她的徒弟本空当作自己养的一个粉头,推给卜良陪他歇宿,得他钱财,而自己也时常来与卜良勾搭淫乱,只是瞒着人做。但最终因诱骗巫娘子与卜良成奸,遭到巫娘子丈夫贾秀才的报复而血洗尼庵,赵尼姑自己也成了贾秀才的刀下之鬼。
再如《醒世恒言》卷十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赫大卿,虽说是个惯于卖弄风流、寻花问柳、纵欲无度的色魔淫棍,其死于声色也是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下场,但非空庵的尼姑空照、静真等人的强留合奸也加速了郝大卿的死亡,特别是她们与郝大卿寻欢作乐时的绕膝挽颈、传杯弄盏、嗲声调笑时,无视众女童的存在而肆无忌惮地淫乱场面,所展示的是普通动物的本能,连一个普通人的廉耻心、羞耻感都没有,何谈出家人的清规和禁忌!让人深感肉麻和恶心。这样的师傅还能带出好的徒弟?所以该寺原本单纯的几个女童,在空照、静真的影响下,也混入其中淫乱凑趣。就因为她们轮流合奸,导致淫棍郝大卿的速亡。而极乐庵的了缘也与空照、静真无异,她竟把圆觉寺的小和尚去非勾引到自己身边淫乱数月,以致去非的父亲误以为儿子是被师傅害死了,若不是郝大卿的案发,去非的师傅还要屈遭官司,枉担恶名。此事结果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出乖弄丑,贻笑四方。小说如此写道:
那时哄动了满城男女,扶老挈幼俱来观看。有好事的,作个歌儿道:可怜老和尚,不见了小和尚;原来女和尚,私藏了男和尚。分明雄和尚,错认了雌和尚。为个假和尚,带累了真和尚。断过死和尚,又明白了活和尚。满堂只叫打和尚,满街争看迎和尚。只为贪那一个莽和尚,弄坏了庵院里娇滴滴许多骚和尚。
比之女尼,和尚都是些假托神道,哄诱愚民,奸淫良善的恶棍。他们不仅骗财骗色,而且还要欺世盗名,如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宝莲寺的和尚即为典型的欺世盗名者。小说如此写道:“惟有宝莲寺与他处不同,时常建造殿宇楼阁,并不启口向人募化。为此远近士庶都道此寺和尚善良,分外敬重,反肯施舍,比募缘的倒胜数倍。况兼本寺相传有个子孙堂,极是灵应,若去烧香求嗣的,真个祈男得男,祈女得女。”“因有这些效验,不论士宦民庶眷属,无有不到子孙堂求嗣,就是邻邦隔县闻知,也都来祈祷。这寺中每日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布施的财物不计其数。”可见,那和尚们虽然出家,利心比俗人更狠,再无个餍足之期。
宝莲寺的“好声誉”、“大影响”何由得来?而送子娘娘又如何那样灵验?小说做了详尽的交待:
元来子孙堂两旁,各设下净室十数间,中设床帐,凡祈嗣的,须要壮年无病的妇女,斋戒七日,亲到寺中拜祷,向佛讨笤。如讨得圣笤,就宿于净室中一宵,每房只宿一人。若讨不得圣笤,便是举念不诚,和尚替他忏悔一番,又斋戒七日,再来祈祷。那净室中四面严密,无一毫隙缝,先教其家夫男仆从,周遭点检一过。任凭拣择停当,至晚送妇女进房安歇,亲人仆从睡在门外看守。为此并无疑惑。……那净室虽然紧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钟声定后,妇女睡熟,便来奸宿。那妇女醒觉时,已被轻薄,欲待声张,又恐反坏名头,只有忍羞而就。一则妇女身无疾病,且又斋戒神清;二则僧人少年精壮,又重价修合种子丸药,送与本妇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发九中。那妇女中识廉耻的,好似哑子吃黄连,苦在心头,不敢告诉丈夫。有那一等无耻淫荡的,倒借此为繇,不时取乐。如此浸淫,不知年代。(《醒世恒言》卷三十九)
他们的恶劣行径,不仅造成山门失色,佛面无光,而且还长期影响到人们对正宗佛教的误解。但无论这些秃驴如何奸猾,最终难逃法网,像宝莲寺的贼秃淫僧终于被新任的汪大尹觉察了情弊,识破了机关,一举查处并火焚之,从此改变了浸淫已久的恶俗。
像这类恶僧的奸邪故事还有许多,如《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也是个典型的例子,故事中的和尚因设谋奸骗了皇甫殿直的妻子,后来又谋害这妇人性命,也落得以“杂犯”罪而重杖处死。典刑正法的那日,一个书会先生当场做了一首《南乡子》,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其曲云:
怎见一僧人,犯滥铺摸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状了,遭刑。棒杀髡囚示万民。沿路众人听,犹念高王观世音。护法喜神齐合掌,低声。果谓金刚不坏身。(《喻世明言》卷三十五)
出家人何以形成这些恶习?其原因既有僧尼自身的,也有社会的。
从僧尼自身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原本不是真心想出家,他们或因父母早亡,无人教养,送入空门;或是自己好吃懒做,又想坐享清福,故而出家。如杭州金山寺的至慧和尚,他自幼出家,自然不是自己的意愿,这从他怨恨父母的一段话中可见。如说:“当时既是难养,索性死了,倒也干净!何苦送来做了一家货,今日教我寸步难行。怀着这口怨气,不如还了俗去,娶个老婆,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团聚。”后来他果然还了俗。至慧和尚对佛门的清规戒律更为不满,他曾抱怨道:
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怎地剃掉了这几茎头发,便不许亲近妇人?我想当初佛爷也是扯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罢了,却又立下这个规矩,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我们是个凡夫,那里打熬得过!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员,你们做官的出乘骏马,入罗红颜,何等受用!也该体恤下人,积点阴骘,偏生与和尚做尽对头,设立恁样不通理的律令!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责杖?难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心,岂是捉缚加拷得的!”又想起做和尚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烧香吃茶,恁般受用,放它不下。
可见,至慧和尚出家明显与他好吃懒做的“本心”有关。尽管他后来还了俗,但毕竟放不下寺院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享乐生活。其心绪、行为极为矛盾。
万法寺住持觉圆的徒弟去非,也不一定是自愿去当和尚的,虽然书中没有明说,但从觉圆与其父的一些言语中也约略可知。然而可悲的是,去非没有像至慧和尚那样从容还俗,而是潜入尼庵与尼姑了缘鬼混,最终因违规犯科而被处之以徒刑。
至于非空庵的尼姑空照、静真以及极乐庵的了缘,原本就是个“真念佛,假修行,爱风月,嫌冷静,怨恨出家的主儿”,其所作所为显然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至于她们是如何来到庵中,小说也没有交代,但肯定不是自愿出家的。正因为如此,她们哪里能耐得住庵中的清净和寂寞?
从社会原因来说,其一,一些地方“信巫不信医”,“故此因邪入邪,认以为真,迷而不悟”,把妻女送到寺里来,给这班贼秃图谋不轨、奸邪淫乱提供了机会。其二,普通人的爱财好占便宜的心性也为不法僧尼和市侩淫棍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女道慧澄为藤生牵线,用珠宝勾搭上狄氏,后来成奸。恶棍妖尼正是抓住狄氏这个弱点或嗜好,投其所好,致使入其彀中。于此,作者有一番深刻的议论:
原来人心不可有欲,一有欲心被人窥破,便要落入圈套。假如狄氏不托尼姑寻珠,便无处生端;就是见了珠子,有钱则买,无钱便罢,一则一,二则二,随你好汉,动他分毫不得。只为欢喜这珠子,又凑不出钱,便落在别人机彀中,把一个冰清玉洁的弄得没出豁起来。(《初刻拍案惊奇》卷六)
此可谓僧尼淫邪之事屡屡得手的深刻原因之所在。
由此可见,明清话本小说之文士、商贾、僧尼等人物群像,其生活行为习惯与社会风尚习气之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这些人物群像的各种行为习惯而逐渐形成的社会风习,既有良好的,也有不良的,因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有着正面和负面之分。良好的社会风习对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方面的建设,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并进而形成一种优良的民族精神;而坏的社会风习则相反,它对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方面起毁坏作用,进而形成民族文化之劣根性习俗。因此我们在评价古代文学作品时,要把它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分析,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因为“用西方文艺理论分析古代小说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和局限:西方文论唯美主义文艺观与中国古代小说重教化的传统相矛盾,忽视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的纯形式主义的分析有明显的片面性;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古代小说重国家、重集体的传统格格不入,以现代人的观念去评判古代小说人物,往往脱离历史语境,过分苛求;西方文论的哲学化和高度抽象的演绎牺牲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造成解读文本的无效性”。[2]
四、明清话本小说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所蕴含的文化史和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是近现代人的学科概念,它是研究社会人及其相互关系之现象的一门科学,古人对此虽未曾做出学科的概括,但社会学现象在历史文献和文学文献中却随处可见。明清话本小说所展示的各类人物群像及其与社会风习之关系,充分体现明清话本小说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重度关注,蕴含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史和社会学意义。
1.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关注人性与道德的平衡
所有明清话本小说作家皆可称之为社会心理学家,他们不仅对书中人物做深入细致的心理分析,而且还将那些人物的心理现象、心理发展过程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使得小说作品的情节、细节以及人物形象皆明显体现出社会心理学特点。
人性最突出的莫过于“三欲”,即权势欲、金钱欲和情欲(或叫色欲),其中金钱欲和色欲遍及所有人群。仅以情欲而言,由于宋明理学对于人性的过度压制,曾引起人们的广泛不满与强烈反抗,于是像李卓吾、汤显祖等思想家和文学家便起来针对宋明理学的灭绝人性,做理性的或艺术的批判,他们的思想、著作在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从社会现象的实际来看,矫枉总难免过正,像西门庆(《金瓶梅》)、严嵩严世藩父子(《十二楼·萃雅楼》)以及金海陵(《醒世恒言·金海陵纵欲亡身》)的贪欲和滥欲,皆损害了他人,危害了社会,甚至威胁到朝政,于是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又开始出来对社会公德、人欲合理做理性反思,以为情欲的满足要以不损害他人的情欲为限。换言之,作为社会人,其欲望的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皆要受到社会和道德的制约。明末清初的小说家冯梦龙、李渔,皆用文学形象表达了他们对人性与道德间相互矛盾与平衡的新见解。对于情欲与道德的矛盾,作者首先是肯定人的合理情欲,但情欲的宣泄又不能违背道德规范。所不同的是,冯氏终其一生是在明代,他对这两者的平衡是采取道德为先,通过道德的自律与调和,最终实现情欲的合理满足,像《喻世明言》之《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醒世恒言》之《陈多寿生死夫妻》《刘小官雌雄兄弟》皆为此类典型的篇章。而李渔一生跨越明清两个朝代,前半生在明末,后半生在清初,他对明末的社会混乱、朝政腐朽,以及清初君王的励精图治、程朱理学的复兴等,都有亲身的体验。因此,在对于情与理的问题上,李渔是采取折衷的态度,既肯定人的情欲,又主张道德自律,强调群体公德。他的这些思想在其小说、戏曲中得到充分表露,如娴娴的心理描写(《夏宜楼》),珍生、玉娟、锦云的害相思与大团圆(《合影楼》),以及段玉初生离时的从容誓诀、生还合卺时的精辟议论(《鹤归楼》),皆体现了作者努力平衡情欲与道德的折衷主义理想。
2.从社会伦理学角度关注社会文明
社会伦理学是关于社会道德秩序的学问,而古代中国的伦常秩序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如父子、兄弟、夫妇等,皆为家庭关系,在传统的五伦中占了三伦,故有“家庭小社会”之论断;再扩大到君臣、师友,业已进入社会关系的范畴,是真正社会学的意义;再进一步扩大到自然界,又有“天地”的概念出来,于是“天地君亲师”的民间祭拜风俗得以形成,并且延续至今。天地虽属自然界范畴,但却是社会存在的重要依托,所以社会人必感恩天地以敬畏之。至于对已故“君亲师”的崇敬和祭拜,显然是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所致,因为早在《国语》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并对民与父、君、师间的重要关系做了简要的阐述,说:“民性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而《荀子·礼论篇》中则将“天地”融进君亲师而加以阐释,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精辟地概括了民与“天地君亲师”五者之关系。
明清话本小说所反映的社会伦常秩序是根植于儒家思想观念的,儒家的忠君、孝亲、尊师重教、重然诺、讲义气等传统道德观在小说中有大量的描写,体现此期小说家们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以及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如李渔自称“觉世稗官”,其小说《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冯梦龙亦将其三部小说集分别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皆体现为明显的社会学意义,若给他们冠以“进步的社会学家”的称号,也毫不为过。
再从小说的具体内容来看,无论是写家庭亲情还是写朋友邻里友情,抑或写师生情、君臣义,其人物形象也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皆能让人感觉到,明清话本小说作家是在有意识地导引人们去恶向善,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谐与文明。如小说中的清官能吏、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等人物群像,无不给人以榜样的力量,使读者从中受到感化,如鲁廉宪、苏知县的清廉如水,鲜于同、蒋成的尊师与感恩,秦世良、秦世芳的重义轻利,等等,无不感人至深;而相反,一些贪官污吏、乱臣贼子、奸猾小人等人物群像无不让人反感和厌恶,特别是他们的恶报下场皆给人以心理的震慑,如严嵩父子的贪婪残暴而被弹劾,恶船家的谋财害命而遭法网,郝大郎、金海陵的纵欲无度而身亡,等等,皆遭恶报而无一善终。这里需特别说明的是,李渔虽为清初作家,但他的小说基本上是写晚明的现实,而晚明的各种社会矛盾皆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所以从明末的冯梦龙、凌濛初直到清初的李渔,其作品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晚明的社会生活。由此可见,明清话本小说中那些正面人物群像,反映了作者的人文理想追求,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而那些反面人物群像,所体现的是作者对丑恶现实的极端憎恶和无情鞭挞。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人物群像,对于匡正祛邪、净化人性、营造社会良好习俗都有着警诫和教育作用。
3.从社会遗传学角度关注民族精神的扬弃
遗传学本为生物学中的二级学科名称,它是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科学;而社会现象中亦存在着“遗传”现象,故此借用来指社会现象的因承与变异情况,提出“社会遗传学”的概念。兹所谓社会遗传学,专指人物思想、言行、道德规范的社会性、延续性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突出表现,更多地体现为人间万象的社会性和民族性。笔者论及明清话本小说民族特征时曾用过类似的概念,即“文学的民族遗传基因”。而这种“文学的民族遗传基因”,“一方面体现为社会整体现象;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时代的连贯性……”[3]
然而,社会遗传学不单指遗传,同样也存在着变异现象。至于“遗传”的问题,诸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贞廉的道德原则,做人美德和精神品格等,是优良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文明进步史上代代传扬,这就是笔者所说的“遗传”,已在《话本小说的民族特征与社会风习》一文中详细论及,故此仅就“变异”情况做一简略概述,以为前文之补充。
明清话本小说所及社会的遗传与变异,亦可理解为小说中民族特征的演进变化,因为民族精神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丰富的,必定注入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时代精神。先就“孝”字来谈,儒家的孝道涉及面极广,如身体肤发皆受之于父母,不能随意毁坏,否则就是不孝,而最大的不孝是不能传宗接代,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章句上》)。明清话本小说所尊崇的核心思想当为儒家思想观念,但在“三言”中却有与之相悖之处,如《喻世明言》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和《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篇,虽突出了儒家的“义”,但又违背了儒家的“孝”。而这义与孝的矛盾,最终却在儒家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中得到解决,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为大仁大义的体现,当然也就是大孝的体现,蕴含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学意义。
再就“贞”字来说,“三言”“二拍”及李渔小说中亦有大量描写。但由于明代好南风(即同性恋,主要是男性)的风习滋生蔓延,自朝廷直达民间,南风现象便成为这个特定时代的热点。因此在冯梦龙、李渔的笔下不仅津津乐道其事,而且还做具体细致的描写,竟还用“守贞”、“贞节”等字眼来肯定当时的同性恋行为,显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这种现象只能理解为畸形社会在文学作品中的畸形反映,属特定时代的产物。
总之,文士、商贾、僧尼是明清话本小说描写最多的文学群像,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都与社会风习发生密切的关系。而由各种行为习惯逐渐形成的社会风习,既有良好的,也有不良的,因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有着正面和负面之分。明清话本小说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民族精神,用艺术形象诠释了他们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观点和见解,充分体现了小说所蕴含的广泛的社会性、深厚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我们通过阅读、分析、研究这些小说和各类人物群像,则可反观小说所及各时期的社会生活情况和各种风尚习气,为当今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以及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这可视为此类小说创作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和社会学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喻世明言》卷二之《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②《醒世恒言》卷一之《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警世通言》卷十一之《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④《十二楼》之《三与楼》,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⑤《喻世明言》卷二之《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⑥《警世通言》卷十八之《老门生三世报恩》。
⑦《十二楼》之《三与楼》。
⑧《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⑨《十二楼》之《夺景楼》。
⑩《无声戏》之《美男子避惑反生疑》,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
[2] 齐裕焜.学理、学科和问题意识[J].明清小说研究,2013,(3).
[3] 秦川.明清话本小说的民族特征与社会风习[J].明清小说研究,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