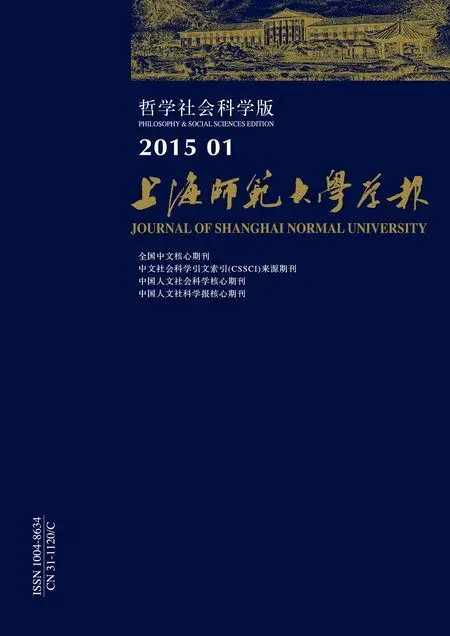明代“文人结社”刍议
李时人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结社”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名目繁多,历史悠久。“文人结社”则是近古以来在特殊的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定人群的特殊社会活动形式。“文人结社”发端于诗社、文会,亦以诗社、文会最为大宗,当然首先与文学有关,但随着“文人结社”的发展,使其不仅成为一种影响文学发展的活动,更成为一种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成为我们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鼎盛时期,故明代“文人结社”理应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一、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最为兴盛的时期
在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有一个萌生、发展、衰落的过程,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大略而言,虽然汉代淮南王刘安“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辞赋”(《汉书》卷四十四);梁孝王刘武聚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于梁园,即景咏乐,染翰成章(《汉书》卷五十一),都还谈不上“文人结社”。但至魏晋“竹林七贤”、王羲之兰亭修禊之会以及南齐永明间“竟陵八友”,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似已有后世“文人结社”之雏形。隋唐以降,由于科举选官制度的推行,“科举士子人群”的出现,文人雅集、诗酒交游较之往古为盛,故“文会”“诗社”“吟社”“诗会”等话头开始在诗中出现。①司空曙《岁暮怀崔峒、耿氵韦》有“洛阳旧社各东西,楚国游人不相识”语,已明说其与同属“大历十才子”的崔、耿两人实为同社诗友,文献中亦有白居易组织“洛中九老社”的记载。故说“文人结社”兴起于唐应为有据;虽然较之后世,其数量还不是很多,规制也较小。两宋“文人结社”似已成普遍,据有关研究,仅诗社已近百家,[1](P129~136)著名者有贺铸“彭城诗社”、徐俯“豫章诗社”、叶梦得“许昌诗社”、许景衡“横塘诗社”、冯时行“成都诗社”、王十朋“楚东诗社”等。尤其是杭州西湖一时成结社之胜地,先后于此结诗社者就有杨万里、许及之、张镃、费士寅、史达祖、陈郁、杨缵、周密、汪元量等。至元统治时,仍有文人沿袭旧习,结社吟咏,以抒情愫。如南宋义乌令吴渭,退居浦江吴溪,延致方凤、吴思齐、谢翱等,共创“月泉吟社”,选与社280人中前60人诗作共74首编次成集,刊为《月泉吟社诗》,其诗多隐含追怀宋室之意。与其同时者尚有“龙泽山诗社”、“明远诗社”、“香林诗社”、“越中诗社”、“武林社”、“山阴诗社”等,②亦多有遗民色彩。元泰定以后,战乱再起,文人多取避世远祸之态,又陆续出现了昆山顾瑛诸人之“玉山社”、松江陶宗仪诸人之“真率会”、嘉兴濮乐闲诸人之“聚桂文会”、广州孙蕡诸人之“南园诗社”、苏州高启诸人之“北郭诗社”、莆田方朴诸人之“壶山文会”等,一时也蔚然成为风气。
至有明一代,“文人结社”则达到空前的兴盛。20世纪40年代,郭绍虞作《明代的文人结社年表》一文,辑考出“明代文人结社”达176家。③2003年,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中提出明代“文人结社”已“超过三百例”;④至其2011出版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又稽考出“明代文人结社的个案(含元末)”680余家。[2](P9)李玉栓2006至2009年从我攻读博士学位,所撰论文《明代文人结社考》在前哲时贤的研究基础上,大量翻检明人诗文集、明人年谱、地方志乘以及相关的史料、笔记、杂传、墓铭等各类文献资料,共考得明代(不含元末、含南明)“文人结社”530多家,毕业后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增补至710家,另有社事时间难以确知的220家作为附表列于书后,凡得930家,而据其所言,明代“文人结社”的总量实际应当在千数以上。[3]十余年来,我一直在编写《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为此翻阅了大量有关文献。根据我的印象,明代“文人结社”的确还不止此数,只是有些因为没有明确的记载,故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除了数量,明代“文人结社”的种类也很繁多,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将其大略分为“研文类结社”、“赋诗类结社”、“宗教类结社”、“怡老类结社”、“讲学类结社”和“其他类结社”,而最末一类所含甚广。至于明代各种结社体制之完整、规模之巨、活动内容之丰富、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也都超过往古。如宋代“文人结社”的规模一般是几人、十几人,元代的“龙泽山诗社”“聚桂文会”“月泉吟社”等规模开始扩大。明代中期以前仍然延续着这种态势,到了明代后期文人结社动辄几十人、上百人。如阮自华大会词人于福州乌石山之邻霄台,“时入社可百人”(谢兆申《谢耳伯先生全集》卷一)。朱承綵开大社于南京,“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张凤翼)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当陈(陈子龙)、夏(夏允彝)《壬申文选》后,‘几社’日扩,多至百人”(杨钟义辑《雪桥诗话续集》卷一)。而张溥诸人立“复社”,更是达到数千人之众(杜登春《社事始末》),姚澣“大会复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几二千人”(吴翌凤《镫窗丛录》卷一)。
明代“文人结社”的内容非常丰富,赋诗、研文、讲学、参禅、冶游、宴饮、清谈,乃至赏曲、狎妓等,常常集于一社之内。如方朴诸人结“壶山文会”,“月必一会,赋诗弹琴,清谈雅歌以为乐”(《明诗纪事》甲签卷十五)。阮自华大会词客于邻霄台,“丝竹殷地,列炬熏天”,“梨园数部,观者如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公安“三袁”结“蒲桃社”,“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十六《潘去华尚宝传》)。闻启祥修复月会,“上之讲道论德,既足祛练神明,次亦咏月嘲风,不失流连光景”(闻启祥《重订启》、《月会约》)。吕维祺立“伊洛大社”于洛阳,“讲学于程明道祠,以初二、十六为期,又以初三、十七为文会”(施化远《明德先生年谱》卷四)。由于社事内容的繁富,导致许多结社的性质很难确定,同时具备文学性、学术性、宗教性、政治性、娱乐性中两种或者以上性质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由于结社之风盛行,除赋诗类、研文类、怡老类、宗教类、讲学类等正统的结社以外,明代文人不论何事,亦常聚众结社,如谢肇淛创“餐荔会”以品啖荔枝,张岱设“斗鸡社”以赌博字画,沈德符结“噱社”以说笑逗乐,黎遂球诸昆弟立“怒飞社”以放鸽为戏等,可谓五花八门。由此亦可见“结社”之于明代文人,已经成为一种风习。
二、明代“文人结社”是与经济、政治、思想等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
明代“文人结社”的繁盛,说明其不是历史的偶发事件或社会个别现象,也不仅仅是一种影响文学发展的文学活动,而是一种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
明代“文人结社”与经济有关系,应该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从宏观来看更是这样。结社虽然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但必须有经济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明代“文人结社”的实际情况也说明“文人结社”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据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明代社事地点可考的 “文人结社”有645家,这其中除南、北两京外,其余以府为单位统计,前十二名为:苏州府76家、杭州府50家、松江府50家、广州府43家、常州府33家、徽州府22家、福州府22家、嘉兴府22家、宁波府18家、河南府(洛阳)18家、绍兴府17家、湖州府16家。除广州府、福州府分别为所在省政治、经济之中心,河南府(洛阳)为传统的中州经济文化中心,其余均在南直隶和浙江经济发达地区;其中环太湖的“江南核心五府”的中心、也是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府“文人结社”,甚至远超南京(应天府)的55家和京师(顺天府)的41家。
从纵向看,明代“文人结社”的发展亦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关联。同样据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明代文人所结之社大致时间可考者有710家,其中明前期(洪武至成化)的120年里,有结社66家;明中期(弘治至隆庆)的85年里,有结社131家;明后期(万历至崇祯)的72年里,有结社397家;南明(清初)时期的38年里,仍有结社119家。这与明代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大致上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其中明后期结社的特殊繁盛,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明代至万历时经济发展达到顶峰,尤其是江南地区,较之全国,经济更显高度繁荣。如苏州府,元末明初因战乱曾一度“里邑萧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宋元旧观,到成化时已开始给人“迥若异境”之感(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嘉靖以后更成为“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乾隆《苏州府志》卷二十一)。当时苏州府的赋税数居全国各州府第一,占全国税粮数的十分之一,应该不完全是朝廷的随心所欲,在很大程度上应与其富甲天下有关。故邑人王世贞敢于说苏州“亡论财赋之所出,与百技淫巧(手工业)之所凑集,驵侩诪张(商业)之所倚窟”,都堪称天下第一雄郡(《弇州山人续稿》卷二十八《送吴令湄阳傅君入觐序》)。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高度发达,不仅造就了苏州这样主要因经济原因而形成的大城市,还造成了大批农、工、商紧密结合的中小城镇——据研究,仅苏、松、杭、嘉、湖五府,万历间的市镇总数就有200余个。⑤其中苏州府吴江县领六乡之地,其时已有17个市镇,彼此距离不过数里。这些星罗棋布、掩映于河湖交错的江南水乡的小城镇是江南经济普遍繁荣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为社会文化的普遍提升,包括读书人口的增加、科考的投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苏州府“文人结社”盛于其他州府,而嘉靖、万历以来更盛于先前。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州府万历以来“文人结社”频繁,且往往规模很大,亦与江南经济的发达有关。清人赵翼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这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明代“文人结社”与政治也有密切的关联。这其中,显而易见的是有些“文人结社”与政治局势变化、文人官场得失有直接的关系。
朱元璋击败群雄建立明王朝后,对文人采取高压政策,文人要么被征入朝或担任郡县之职,为专制政体服务;要么遭受无情打击,如高启因为魏观作上梁文而被腰斩,孙蕡、王行因蓝玉案坐死,徐贲下狱死,张羽自沉龙江。凡此,无疑影响了当时的文人结社——虽然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仍有文人坚持结社,如休宁江敬弘谪濠梁,与同时谪居濠上的众多文人相与结社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钱塘凌云翰坐谪南荒,举“清江文会” (凌云翰《清江文会诗为崔驿丞赋》);福清林鸿为躲避政治风险归隐山林,赋诗结社(《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五《礼部员外郎林鸿传》)。“靖难”事起,一些文人逃归林下,如永乐二年(1404),太平林原缙与丘海、何愚诸人“会里之花山,修白香山故事,称花山九老”(《明诗纪事》甲签卷三十○);永乐七年至二十一年间,长乐陈亮“结草屋沧州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终其身不仕”(《明史》卷二百八十六);会稽漏瑜“靖难后不复出,侨寓乌镇”,至“宣德中,在乌墩为九老之会”(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六)。也有一些得势的文人雅集于朝,如永乐七年大学士胡广就邀请翰林院同仁“会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后,酒酣,分韵赋诗成卷,学士王景为之序”(黄佐《翰林记》卷二)。但总的说来,洪武、永乐数十年,较之元季的文人结社并无大的进展。
自明宣德始,社会逐步稳定。至明正统年间,明朝国势一直呈上升趋势。国力的强盛,文人地位的提高,大大增强了文人的自信心,结盟会社又渐成风气。宣德时杨荣掌翰林院事,首创馆阁之聚奎宴,众皆赋诗;正统初复举“杏园雅集”,“赋诗成卷,杨士奇序之,且绘为图”;后“三杨”又“倡真率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黄佐《翰林记》卷二)。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土木堡事件,英宗被俘,次年方得释还京。此事对明朝国势产生一定影响,但并未动摇明王朝的统治根基,经景泰、天顺、成化至弘治时期是明王朝的承平之世。虽然政治和社会危机逐步加深,但由于前期奠定的基础,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其间,文人结社也逐步兴盛,并在全国范围内渐渐形成了南、北两京以及南直、浙江、闽中等几个结社最为活跃的地区。
正统时,明朝出现了“国事浸弱”的迹象(《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正德、嘉靖两朝,武宗、世宗长期怠政,宦官刘瑾、权臣严嵩先后擅权,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一些正直敢言之士被罢官放黜,因得借结社以自遣。如正德初,刘瑾乱政,杨守随因抗疏致仕,与其乡之耆旧以诗酒相娱,结社于甬上;刘麟因不谒谢刘瑾而被黜为民,流寓湖州,结“湖南崇雅社”,“与吴琬、施侃、孙一元、龙霓为‘湖南五隐’”(《明史》卷一百九十四《刘麟传》)。嘉靖中,张时彻以忤严嵩擅归里,结社聚士,领甬上风雅达二十余年(余有丁《张司马先生时彻传》)。
万历时,由于首辅张居正为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多采用强制性手段,与之同朝的不少文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打击,一些人也因此退而结社,借以消磨闲暇。如万历五年(1577)“夺情”议起,张居正嘱张瀚留己,瀚弗听,居因“嗾台省劾之,以为昏耄,勒令致仕”(《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张瀚致仕后,“与同乡诸缙绅修怡老会,会几二十人,一时称盛”(《武林怡老会诗集·序》)。万历八年汪道昆亦因与张居正不和致仕,归乡后组白榆诗社,与者二十余人,皆一时才俊,钱谦益称其“谼中主盟,白榆结社,腥脓肥厚之词,熏灼海内”(《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天启间,闽人曹学佺因著《野史纪略》,忤权宦魏忠贤,削籍归里(《明史》卷二百八十八),遂与陈衎、徐火勃诸人修阆“风楼诗社”(《静志居诗话》卷十九)。同时顺德梁元柱以劾魏珰削职罢归,“与陈子壮、黎遂球、赵焞夫、欧必元、李云龙、梁梦阳、戴柱、梁木公开‘诃林净社’”(《番禺县续志》卷四十),“每花晨月夕,招邀朋旧,饮酒赋诗”(《粤东诗海》卷四十五)。
明社倾覆后,遗民结社甚多。其中或眷怀旧国,如“惊隐诗社”、“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等;或借之抵抗新朝,如杨廷麟“结连赣抚李永茂,立‘忠诚社’于赣,招致四方义勇”(《明诗纪事》辛签卷六上),全美闲“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巨室子弟为‘弃纟需社’”(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八《族祖苇翁先生墓志》);或躲避世乱,如吴与湛“结诗社于江枫庵”(《国朝松陵诗征》卷二),章有成“与同邑赵淳、吴鲲、范开文为诗酒社,吟啸以终”(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三十一)。这类结社也主要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如清人杨凤苞所云:“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文人结社”不仅受政治影响,也难免被卷入甚至直接介入政治,从而从另一方面与政治产生联系。这方面以“复社”最为典型。成员数千且遍及十余省六十余府的“复社”,首先是一个为了应对科考、研习五经和制义之文的研文社,但其首领张溥在立社之初就强调立社的宗旨为“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又以“倡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相标榜(杜登春《社事始末》),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实际上成了明末一股政治力量。《复社纪略》中收有张溥、张采驱逐顾秉谦的檄文,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立场。崇祯三年,张溥乡试夺经魁,四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按说张溥不过是初登仕途的一个进士,但由于其“复社”领袖的地位,竟然得以干预朝政。此即《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本传所谓 “声气日广,交游通朝右,品题甲乙,颇能荣辱”。复社甚至直接介入了朝廷党派之争,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出任首辅,就与张溥、钱谦益、吴昌时等复社成员的密谋有关,是复社力量和意愿在政治上的反映。在以后晚明的政治纷争中更多次看到复社力量的展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复社已由揣摩时艺之研文社发展为带有政治性的社团。
不过,明代“文人结社”与政治的关系还不仅如此。因为“文人结社”在中国古代的兴起、发展,包括其在明代的兴盛,从根本上说与中国古代,特别是近古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我们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历史演进形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的不再是“分封制”,而是一种中央集权下的郡县管理体制,担负这种专制体制运行任务的主要是各级官吏。而为了满足这种政治体制的需要,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士。特别是唐代实行“科举选官制度”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往古、以“科举”为中心的“读书士子人群”——这是除了东亚一些模仿中国,亦实行科举制的国家如越南、朝鲜外,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科举选官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尽管其本身存在种种弊端,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亦是有利有弊,但其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了社会成员上、下层之间及“知识精英层”内部流动的“规则”,又使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负起整合社会关系体系和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成为保证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正常运行的一种调节机制。中央集权(皇权)、郡县统治、科举选官应该说是中国近古以来政治体制的三大基石。从唐代开始,以“科举”为中心的“读书士子人群”既是这一体制的产物,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李玉栓将他的这本书命名为《明代文人结社考》,上举在此之前有过的一些同类著作,如郭绍虞的《明代的文人结社年表》,何宗美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和《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以及近年来发表的不少论文,都在标题上使用了“文人”与“结社”两个概念。由词义看,这两个概念并非并列,前者应是对后者的限定和说明。但综观这些著述、论文,对“结社”之事,或考或论,大多倾注了作者的努力,成果显著;然于“文人”一词,则大多语焉不详,甚或不置一词。其实,要理解或者解读 “文人结社”这一历史现象,似乎首先要从对“文人”的解读开始。因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结社”的兴起、兴盛以及衰落,与中国古代文人——即中国古代知识人群的历史变迁有很大的关系。而从唐代开始,直至这种皇权至上的专制政体被推翻,中国的“文人”实际上主要就是以科举为中心形成的“读书士子人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从一开始就与“科举”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明代“文人结社”的兴盛,显然与明代“科举”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
曾翻阅几种“科举史”著作,几乎无不称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的“鼎盛时期”,从各方面看,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明王朝建国之初,由于急需各级官吏,故在短时间内曾经荐举、科举并举,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以后每三年一科,子、卯、午、酉年乡试,次年丑、辰、未、戌年会试,终明一代,遂为“永制”。宣德年间,荐举废置不用,后来更明确规定,所有文官必须由科举而进,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的人不得进入内阁。通过一系列制度和举措,包括科考内容、形式的确定,“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程式的确立,分区域配额取士制度的制定,特别是将学校纳入科举体制——所谓“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造成了明代科举的高度制度化、规模化,从而达到了超越往古的空前兴盛。
明代科举的一系列制度和举措,造成了读书人口特别是“科举士子人群”数量的庞大和稳定增长。明代自洪武十八年(1385)起共有89科进士考试,登科总人数为24000多人;⑥有明一代乡试所取举人,总数约在70000人左右。⑦特别是每年固定在校(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的诸生(秀才)就有50000人左右。⑧这样由“童生”、“诸生”组成的一般读书人,举人、进士,以及举人、进士出身的各级官员,就在整个社会中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读书士子人群”。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读书士子人群”,就不可能有明代“文人结社”的兴盛。
由于参加科考的人数众多,每次乡试、会试期间,大批士子集聚一地,为结盟立社提供了契机。如江南乡试在南京举行,遂使南京不仅有陪都的官员和当地文人的结社,也成为南直隶所辖十四州府应试考生结社之地,“南京,故都会也。每年秋试,则十四郡科举士及诸藩省隶国学者咸在焉,衣冠阗骈,震耀衢术。豪举者挟资来,举酒呼徒,征歌选伎,岁有之矣”(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七《国门广业序》)。如天启七年(1627),江南乡试,艾南英诸人倾盖定交结“偶社”,徐介眉、顾重光、吴圣邻、曹允大诸人结“因社”(艾南英《天佣子集》卷十四《偶社序》)。崇祯三年(1630),“因社”诸子再集南京,增之为“广因社”(艾南英《天佣子集》卷十三《国门广因社序》)。是年“复社”也集合参加南京乡试的生员召开金陵大会,隶于“复社”的“国门广业社”首举社集(《楼山堂集》卷十七《国门广业序》)崇祯六年“国门广业社”举行第二次社集;崇祯九年“国门广业社”举行第三次社集(同治《嘉兴府志》卷五十三);崇祯十二年“国门广业社”举行第四次社集(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陈定先生墓志铭》)。“广业社”前后共有过五次大的集会,除最后一次由于国事变更的影响外,其余四次均为乡试之年。而诸社所以能这样连续于乡试年举行社集,乡试录取率不高,许多应试者往往要连考数科,应是一个重要原因。⑨
除了因应试而结社,科考中式者也结社。因为“同年”在官场和社会生活中都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士子们也有意识地借结社来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如天顺间,罗璟等为同年宴会,于春、夏、秋、冬之节会举行宴集赋诗活动(《翰林记》卷二十“节会唱和”),成化四年(1468)何乔新等11人举同年会(何乔新《椒丘文集》卷九《同年燕集诗序》),成化十二年李东阳等41人举同年会(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二十六《京闱同年会诗序》),弘治十六年(1503)李东阳复举同年会(《怀麓堂集》卷六十三《甲申十同年诗序》)。李东阳《怀麓堂集》中尚有《两京同年倡和诗序》《翰林同年会赋》等,说明李东阳经常通过结社与同年保持联系。
另外,科考内容和形式也对“文人结社”有影响,或者说正是科考内容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明代“文人结社”的发展。明自洪武始,“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史》卷七十《选举二》)。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产生的大量“研文社”正是为了应付这种考试而产生的。万历四十一年(1613),白绍光署常熟教谕,“立五经社、分曹课试”(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三《常熟县教谕武进白君遗爱记》)。张溥等人的“应社”最初成立时亦名“五经应社”(计东《改亭文集》卷十《上吴伟业书一》)。而由于明代科考在形式上采用八股文体,在规范化的同时,也简化了繁复,降低了科考的难度,急功近利者因不再沉潜经典,更多的是摹拟名家,揣摩文风,甚者仅仅记诵若干篇,以应考试。于是不仅“研文社”以习作八股文为要务,旨在为参加科考之人记诵、摹拟乃至剽袭提供便利的程墨、房稿、社稿等在社会上也非常风行。崇祯二年(1629),松江名士杜麟征、夏允彝等倡立“几社”,就是以切磋制艺、研习古文为号召,次年即刊行了《几社六子会义》,收杜麟征、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与陈子龙制义之文,崇祯五年又刊《几社壬申合稿》二十卷,收社友11人所作骚赋、乐府、古近体诗及序记之文。
如果考察一下明代许多著名文人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们大多有参与各种“结社”的经历,无论是考前,还是为官期间和致仕以后。也就是说,对于以科考为生活轴心的明代文人而言,“结社”不仅是一种风习,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文人结社”不可避免地与明代文人的思想观念,包括儒学的流变建立了联系。
儒学是汉代以来中国文人尊崇的核心学说,儒家思想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宋明理学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但明代的情况又不同于宋代。宋代儒学发展的过程,是由北宋提倡“通经致用”的“宋学”各派逐渐向强化专制统治的南宋“理学”转化的过程,并使后者在以后数百年间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不过,程朱理学权威的真正确立却是在明初,明代永乐十五年朝廷颁行《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府、县学,并将其定为科考的内容和士人的思想、行为规范,朱熹的“集注”和宋代理学家的言论才真正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只是由于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不久即有人对程朱学说产生怀疑,至明中叶,终于出现了陈献章和王阳明,各自提出了一套与程朱理学本质不悖而思想方法却有很大差异的儒学新体系。特别是王阳明“良知”、“致良知”学说的问世,很快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王阳明“心学”始终未被官方承认,但其思想,包括其二传、三传弟子所创立的各种思想观念却流播广泛;直至半个世纪后“东林学派”重新倡导以程朱为学,开启明末清初朱子学复兴之端,才逐渐消息。值得注意的是,中晚明思想的流变,无论是王学崛起,还是朱子学重振,在表现形式上都与 “讲学”有关,以至于著书立说所起的作用还在其次。王阳明曾身体力行至各地讲学,其卒后,讲学活动在嘉靖中后期达到鼎盛,江右、浙中及南京附近都成为讲学活动兴盛的地方。以后随着阳明后学门户纷立,流弊渐多,“讲学”活动始向程朱之学转变。虽然明代“讲学”活动主要在书院,通过“讲会”等形式进行,但无论是书院、讲会都与“文人结社”特别是“研文会”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文社之风与“讲学”之风可以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举一个例子:万历间“东林学派”以讲学于“东林书院”著名,又因其参与晚明政治斗争,被称为“东林党”,但其源起却在“东林社”。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原为北宋杨时于政和元年(1111)所建,因时代久远而荒废。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廷推阁臣忤旨,革职归乡,遂“偕同志修东林之社”(顾宪成《明故孝廉静余许君墓志铭》),因“弟子云集,邻居梵宇僦寓都遍,至无所容”,遂建“同人堂”为“东林社”讲学之舍(《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至万历三十一年始倡议重修东林书院,次年,“移同人家社于丽泽堂,月课多士”(《顾端文公年谱》)。“东林社”不惟讲学、课文,亦时有赋诗、和诗之举。万历四十一年,钱一本受邀至东林讲《易》,会罢,赋诗纪之,参与和韵之人前后有13人、赋诗五十余首(《东林书院志》卷十八)。万历四十年八月,“东林党人”公奠顾宪成,参与者“同年、同社及后学门生于孔兼、钱一本、吴达可……四十余人”(《顾端文公年谱》)。后世多注意“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和“东林党”的政治活动,却忽略了“东林社”实为两者之基础。再如,天启元年(1621),吕维祺归新安,次年立有“芝泉会”(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二十一《芝泉会约二》),本为研文之会,但同时也为“讲学”之会,以“扩良知之传”为己任(施化远《明德先生年谱》)。后崇祯十年(1637),吕维祺在洛阳立伊洛大社(又名伊洛社、伊洛会),亦集讲学与文会于一体,从游人数达二百之众(《明德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甚至有因为学术观点不同,希图通过结社论辩,澄清问题,如崇祯四年,刘宗周不同意陶奭龄“圣人非人”之论(《证人社约·社约书后》),反对以禅诠儒,遂于越中立“证人社”,邀请陶氏赴社,“分席而讲”,希望通过讲学证之(《南雷集·子刘子行状》)。至清初,黄宗羲又复举“证人”讲席于甬上(全祖望《鲒埼亭集》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明代“文人结社”不仅与儒学有关系,与佛学也有关系。有明一代,从朱元璋起,除世宗、思宗等少数皇帝有过禁佛、排佛举措外,多数都崇信佛教,在对佛教进行整顿和限制的同时更多地是保护和提倡,因此明代佛教屡屡出现兴盛局面。明中叶以后,特别是万历以降,佛教诸宗,不仅禅宗、净土宗,就连沉寂已久的华严宗、律宗,甚或几近失传的法相宗,都有所发展。如被称为“晚明四大高僧”的祩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前三位都主要生活在万历年间。他们主张三教同源、诸宗融合,关注民生社会,积极践行大乘佛教精神,许多士大夫都与他们有所交往,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由于当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信拜宗教,读书士子也出现了亲近佛教的现象,以致《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有如下记载:“缙绅士大夫亦有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戒律,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思想对文人的思想必然产生影响。早在正德时,“心学”的创始人王守仁,就曾遍访佛刹,求教名僧,“出入于佛、老者久之”(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其创立“格物致知”之说多少曾受到佛教“明心见性”思想和运思模式的启示。王守仁辞世后,王学分流,王畿等主张“四无”,认为良知“当下现成,不假工夫修整而后得”(《明儒学案》卷十二),更类于禅。被称为“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罗汝芳诸人亦多与释家过从,深受禅学影响,时人目为“狂禅”。李贽更是出入儒佛之间,交结僧侣,酷好禅宗,晚年去冠薙发,号居士,居禅院,立言护法,与真可和尚并称“二大教主”(《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其所倡导的“童心说”,与禅宗“心性论”亦有密切关联。后来“公安三袁”学禅于李贽,受其影响甚巨,不仅向心净土,撰《西方合论》,而且在李贽“童心说”的启迪之下,还提出文学的“性灵说”。
明代这种儒、佛交结的现象,与文人、僧人的社集有一定的关系。自晋慧远修“莲社”以来,历代都有一些士子与僧人共社的现象,不过多数都是文人参与僧人结社,在本质上尚属宗教结社。如明代汪道昆的“肇林社”仍然如此,虽然其规模很大,听经者百人以上,但入社的缙绅学士仅有十余人(《太函集》卷七十五《肇林社记》)。宋元以后,僧人开始介入文人结社。至明中叶,文人开始自行结社,有时邀请一二僧人加入,有时入会者则纯粹是文人。如冯梦祯所主之“澹社”,“每月一会,茗供寂寞,随意谈《楞严》、《老》、《庄》,间拈一题为诗,后期薄罚,以督之”。(《武林梵志》卷三“理安禅寺”条引吴之鲸《澹社序》)。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三十年(1602)间京师“蒲桃社”也纯为文人所结,社中17人皆为文士,活动方式却以“静坐禅榻”(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十六《潘去华尚宝传》)、“食素持珠”(《珂雪斋前集》卷十六《石浦先生传》)为主,此时社事已经完全由文人主盟,文人禅社至此趋于兴盛。如焦竑与李贽“往来论学,始终无间,居常博览群书,归心于佛氏”(黄毓祺《居士传》卷四十四《焦弱侯传》),尝在南京立“长生馆会”,“每于月之八日,与客游栖,听僧礼诵”(《隐秀轩集》卷八《长生馆诗引》)。再如明季杭州“读书社”本来宗旨为读书研理,由于主创者张秀初为虞淳熙之婿,“丛林称为仁庵禅师”(《南雷文约》卷二《张仁庵先生墓志铭》),社中成员闻启祥、严调御、严武顺、丁奇遇、冯悰、邵洽皆出自虞氏门下,后俱逃之于禅,故黄宗羲谓“武林之读书社,徒为释氏之所网罗”(《南雷文定后集》卷三《陈夔献墓志铭》)。明代受佛教影响而结社最多的当数“公安三袁”。从万历二十年(1592)至四十一年(1613)间,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先后参与或组织过“南平社”、“蒲桃社”、“香光社”、“青莲社”、“堆蓝社”、“华严会”、“金粟社”等数个涉及宗教内容的结社,这些社事集僧俗于一体,儒佛合一,或者谈禅论学,或者念佛诵经,或者参禅悟道,间以徜徉山水、诗酒吟咏。正是因为结社,进一步沟通了文人与宗教的关系,加速了佛学与儒学的交融,并因此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流变。
三、明代“文人结社”是研究有明一代文学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视角
关于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以往人们关心比较多的是“结社”与明代文学发展的关系,这无疑是重要的。在我看来,文学史意义上的“明代文学”有四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同时发展,雅俗交汇,同时文学人口(作者和读者)大量增加,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往古的、带有一定近代气息的文学景观;二是表现出与时代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同步的态势,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所占份额增大,更多地体现了文学的职能、价值和意义;三是出现了文学创作与理论探讨齐头并进、相互影响的局面,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文学的独立与自觉;四是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表现出古代文学终结期的特色,庞杂混乱的表象下充满了指向未来的张力。而这一切与明代的“文人结社”都不无关系。
明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曾主盟或参与过结社,如高启之“北郭诗社”、孙蕡之“南园诗社”、杨士奇之“真率会”、顾璘之“青溪社”、郑善夫之“鳌峰诗社”、王世贞之“六子社”、张时彻之“甬上诗社”、梁辰鱼之“鹫峰诗社”、汪道昆之“北榆社”、茅坤之“西湖秋社”、陈际泰之“新城大社”、袁宏道之“蒲桃社”、曹学佺之“石仓社”、张溥之“复社”等。其他如林鸿、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守仁、李维桢、归有光、汤显祖、冯梦龙、田汝成、王思任、艾南英、谢肇淛、祁彪佳、谭元春、黎遂球、钱谦益、张岱等在文坛上卓有影响的人物也无不参与社事。可以说明代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形成的每一个文学流派,以及各个阶段、各个流派的领袖人物,都或多或少地与当时的“结社”有关。如诗歌中的“后七子”复古派、公安派等,都是借助于结社,甚至是以结社为基础形成的文学流派。
结社往往通过集体活动激发参与者的创作,使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名列“南园后五子”的黎民表“偕友人结社于粤山之麓”,“旦夕酬酢,可讽咏者至千余篇”(黎民表《清泉精舍小志》卷首),是为典型。许多结社成员还将他们的社集作品编裒成集,刊刻行世,如“海岱诗社”有《海岱会集》、“西湖八社”有《西湖八社诗帖》、“小瀛洲社”有《小瀛洲十老诗》、“白榆社”有《白榆社草诗》、“淮南社”有《淮南社草》、“萍社”有《萍社草》等。在结社过程中,文人们为扩大影响、延邀声誉或者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常常开展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探讨,有的因此进行诗话创作,如“六子社”中王世贞著《艺苑卮言》、谢榛著《诗家直说》,“青溪社”中朱孟震著《玉笥诗谈》;这些诗话在记述社事活动的同时也阐述了自己或者诗社的文学观念,甚至创作理论。有的编纂诗文选本,如“闽中十子社”高棅选《唐诗品汇》,“西湖秋社”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石仓社”曹学佺选《石仓十二代诗选》等。有的进行文学评点,如“青溪社”顾璘批点《唐音》,“秦淮社”潘之恒评论《牡丹亭》,“复社”成员评点《新刻谭友夏合集》等。通过编选、评点古人或今人的作品来宣传自己和诗社的理论主张,都充分证明明代文学理论的繁荣与结社有关。
毫无疑问,对明代“文人结社”进行研究,对于我们考察、研究明代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流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明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关于这方面,前人已经有过很多成功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文人结社”研究对明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还不止于此。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明代文学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重点:一是作家作品研究,一是“文学史”研究。前者是对历史上文学现象“点”的研究,后者则重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线性”研究。这种点、线结合的研究,强调了文学的时间性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的空间流变;强调了名家名作的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文学现象的整体观照。其实,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文学也是在“时空”范围内发生的现象,因此,文学不仅是一种时间现象,也应该是一种空间现象。古代文学研究中,只有既注意时间又注意空间的多维研究,才能真正描绘出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立体的、流动的图像。在这个意义上,对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对于考察研究有明一代的文学生态,考察研究明代文学发展的地域因缘与空间形态,肯定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可以深化和推进我们的明代文学研究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文人结社”不仅仅是一种影响文学发展的文学活动,也是一种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对繁盛的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就不仅对我们研究明代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是观察、探究有明一代全部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注释:
①如“泛湖同逸旅,吟会是思归”(孟浩然《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孟郊《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三年文会许追随,和遍南朝杂体诗”(李群玉《寄长沙许仕御》);“沧洲诗社散,无梦盍朋簪”(戴叔伦《卧病》);“前朝吟会散,故国讲流终”(李洞《叙事寄荐福栖白》);“好与高阳结吟社,况无名迹达珠旒”(高骈《途次内黄马病寄僧舍呈诸友人》)。
②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下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③郭绍虞:《明代的文人结社年表》,载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原载《东南日报·文史》1947年第55期﹑第56期。
④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一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⑤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二章《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市镇网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86页。
⑥明代进士登科人数各家统计不一,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统计为24831人,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统计为24636人,然总数在24000人以上则无疑。
⑦洪武三年(1370)规定全国各地乡试一科录取举人500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一《科试考》)。以后不断有所增加,如正统元年(1436)下诏增加乡试录取名额,规定每科录取740人(查继佐《罪惟录》卷十八《科举志》)。后又有较大增加,如洪熙元年(1425)规定“南国子监及南直隶”乡试取80人(《明宣宗实录》卷九),但实际上景泰元年(1450)取202人;四年取205人;从景泰七年至万历四十年(1612)53科,每科135人;自万历四十三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10科,每科取148人(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三十《选举志》。因明代乡试资料不完整,故此70000人中举之数属于估算。
⑧“宣德中定(学校)增广之额: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成化中定卫学之例,四卫以上军生八十人,三卫以上军生六十人,二卫、一卫军生四十人,有司儒学军生二十人,土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无定额。”后又不时有增补,所谓“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又据《明史·地理志》,除羁縻之府、州、县不计,明代共设府140、州193、县1138;又有两京都督府分统都指挥使司16、行都指挥使司5,下设卫493。故初步估算其每年在校诸生在五万人左右。
⑨如弘治五年(1492),应天府“就试者二千三百余人……得士凡一百三十五人”(王鏊《震泽集》卷十《应天府乡试录序》),录取率为5.8%。嘉靖七年(1528),浙江乡试“就试者二干八百有奇,预选者九十人”(陆粲《陆子余集)卷一《浙江乡试录序》),录取率为3.2%。嘉靖十三年江西乡试,“所选士三千有奇,而三试之,得中式者九十人”(李舜臣《愚谷集》卷五《江西乡试录序》),录取率为3%。故有人估计明代乡试总录取比例平均仅有4%(参见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1] 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 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