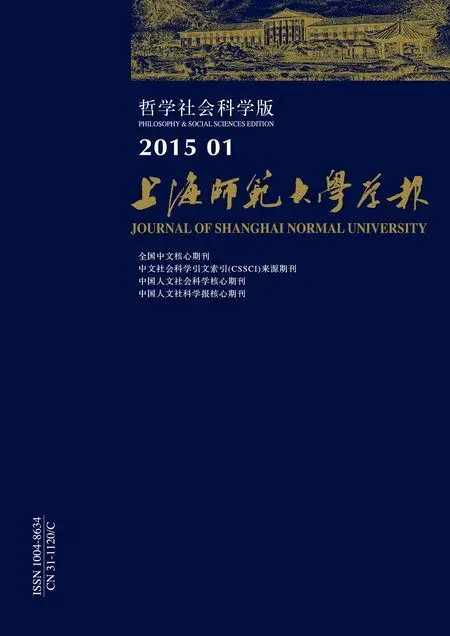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后现代道德
汪小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上海 200083)
作为二战后美国“纽约派”诗人的杰出代表,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 1926—1966)十分关注日常都市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和意识形态。他的作品通常指涉个体的亲身体验和生活经历,成为一种反思性的人文关怀。从无限丰富且又多样化的日常生活碎片中采撷现代人类道德所应有的生命力,并以真诚的个人体验为参照依据,发掘面向世界意义的生活伦理资源,这是诗人奥哈拉后现代道德观的思维模式和根本标志。本文将探讨奥哈拉城市诗歌所展现的后现代道德的个体性、多元性和生活性等三方面的属性,论证奥哈拉城市诗学中的后现代道德观,揭示出后现代道德“与生活共沉浮”的趋势和规律。
一、个体性
奥哈拉的城市诗歌真切地反映了诗人对后现代个体道德经验的关注和重视,其诗歌艺术中的道德旨趣也在诗中描述个体的日常感受中得以呈现。他的许多作品,如《喜欢》(Like)、《今天》(Today)、《诗》(Poem)、《音乐》(Music)中的道德风貌和人伦秩序正是借助于个体复杂生活的特殊体验来凸显的。诗人笔下消费场域中的欲望支点、建筑地缘中的人性异化、都市丛林中的孤独况味,也唯有通过日常生活体验的现代真切感受才能迸发出至诚至真的心灵火花。尽管以往的西方后现代伦理学说素来专注于道德知识论的客体化分析和抽象化考证,然而奥哈拉诗歌中的道德属性和内在规律却是由多样化的个性生命连缀而成,共同反映了后现代道德自身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趋势。
当今的纽约社会, 后工业机械时代的消费制度和技术理性日益成为人类道德思想的实际操控者。人们在热点追踪文艺繁荣的同时还发现,都市人群的道德生活在现代科技高歌猛进的过程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之中。在《喜欢》(Like)一诗中,繁忙与喧闹的纽约中心港地带被最具都市意味的商务景象所占据。它就像一面高扬在纽约城上空的“叛乱”旗帜,专供诗人拨响心弦、宣泄欲望。奥哈拉的《今天》(Today)也细腻描绘了错杂变幻的、如“万花筒”般的都市消费风貌:“袋鼠,金币,巧克力苏打!/ 你们真美!珍珠,/ 口琴,胶糖,阿司匹林!/ 他们总在谈论所有这些物品。”①[1](P105)在诗人创作的诗歌中,购物主题和消费场域往往是现代人生存的天堂。这里,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调控着人们内心的道德力量:“一道道铁栏杆紧紧地 / 圈住我们的心脏。”[1](P159)公共场所的风华世态随时随地都处于摄像机的监控之下:“在加拿大上空被相机抓拍。/ 贷与烦恼和愤怒,爱的分支。/ 那是他的国际领地。”[1](P141)甚至连人们依场合而定的“制度化微笑”[1](P143)也变成了“都是正常的模样”[1](P143):“啊!微笑,快活而节制。”[1](P145)现代技术的理性规则过度关注着“每天和我们在一起的这些事物”,[1](P151)抽掉了个体内在本能的人类丰富情感,直接促成了后现代道德体验对生命个性和差异的遗忘。难怪诗人奥哈拉会在《同性恋》(Homosexuality)中写道:“哭喊着去迷惑勇敢的人 / 这是个夏日,我渴望被需要胜过世上的一切。”[1](P121)他的《七九七》(SevenNineSeven)也通过某种具体的、背离了世俗生活的编码规则,而彰显了人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情感和日常性真理。“沥青战栗的天空、采石场、树叶、石油、车道”仅仅是外在的理性规训或技术控制力, 注定无法发挥其应有的道德规则作用,更不能够解决人们内心情感的回应难题和缺失现象。所以,后现代道德情感的钝化和制度化——“这一天 / 怕就要这样相安无事地度过了”。[1](P156)——随之成为一种现代性的日常体验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人性而言, 原生性的个体道德永远比外在生活变迁的理性规划更为重要,因为“没有一种规则制度能够取代生命多样态的弹性和适应性”。[2] (P59)所以,奥哈拉的城市诗歌才会诉诸个人体验的生存本能和道德情感,并以多元思维和开放想象的艺术力量去弥补后工业时代理性规划的机械意义与僵硬模式之不足。诚然,在“纽约城”这片冰冷的金属都市疆域,无论何时何地, 丧失了主体真实经验和丰富内涵的作品都不可能还原出真正的道德本色。
诗人奥哈拉重视植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个体生命体验,与当代都市人群对后现代道德生存的本质理解有关。费瑟斯通曾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必须努力表达、体验和享受这个‘唯一’。”[3](P23)生活层面上的存在理由给生命本身以生存下去的勇气和超越生存的力量。因此,城市文本的美学旨趣应当尊重和关怀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具体欲求和不同感受,才能使美国后现代的道德生活世界重新走向人性化。尽管《走着去工作》(WalkingtoWork)、《又是一个戏迷》(YetAnotherFun)、《1951》(1951)中的个人体验蕴含着现代生命活力的原初性道德本能和本根性道德冲动,“但这些忧虑 / 依旧浓郁,成为 / 心灵深思熟虑的 / 伤痛之地”。[1](P160)这些诗作中的道德生活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较为普遍的自发性原则和多变性依据,成为人类最本真的个人体验表达方式。而不以任何道德体验为辩证基础的文本实践,充其量只是理性的文字游戏,无法表达出日常生活现实的真挚价值和朴实情感。
此外,发自个体内心深处的体验是自发而快乐的道德,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压抑性道德。奥哈拉在《圣塞西莉亚》(OdeOnSaintCecilia’sDay)中所描绘“最后的空想忙于追寻快乐”[1](P235)的字句,便是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情感体验色彩的快乐道德之例证。因为在日常生活的生命体验中,唯有找到精神依托和生活目标的人,才能在社会行为中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从日常生活的个体生命体验中获得的道德快感,常常是道德本能的自我呈现。如同“白日的霓虹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1](P99)一般,在这里,快乐体验不仅是诗人对自己生活态度的一种自我褒奖,也是生命本质对道德真诚行为的一种持续性原动力。不可否认,具有某种“游戏性”的后现代快乐道德乃是回归人类道德本真性的诚挚之途,并非是相对主义的道德虚无化。从严肃的高雅文化中走出来,摆脱道德规则的制度化束缚,用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娱乐话题去毫不修饰地探究个人本能性的道德冲动之源,使发自内心的道德真诚成为每个人原生性的自觉自愿的践履目标,这就是奥哈拉的城市诗歌所笃信的后现代道德理念。《死亡》(Death)、《同性恋》(Homosexuality)、《我亲吻你的圣餐杯》(IKissYourCup)、《在医院》(InHospital)中的都市生命细节,立足于“小叙事”的种种旨趣,远离“宏大叙事”的理性主义道德,直视生命之真的快乐本质和欣慰原色,审视以个人体验为基点的后现代道德观念赋予人类存在意义的精神基础和内心法则:“无须想象永久地生存在这世上。”[1](P226)
奥哈拉对纽约日常生活的道德审美,因为强调个体经验而触碰到真实自我的人性问题,使得美国城市诗歌对新价值、新体验、新语词的审美欲求上升为对道德生活伦理意义的追求,形成了个体审美与道德实践的水乳交融:“我猥琐地 / 走进你 / 我们所做的事 / 就是我将你吞噬。”[1](P227)由于当代社会中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和评判无法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道德手段来进行,道德生活的精神价值业已超越了单一的伦理层面而转向个人的生命体验。对奥哈拉而言:“而我在这里,/ 在所有美丽的中心!/ 写这些诗!想想我多么出色!”[1](P214)他的自我陶醉和对个人主义的不懈追求,是后现代艺术发展的方向。在这里,审美沉浸移情于道德诉求,伦理感受高于审美需要,原始性道德冲动的生命本真欲望呼之欲出:“我想他们昨晚做过爱 / 但是谁又没有呢?”[1](P219)
由此可见,以奥哈拉为代表的美国纽约派诗人在道德层面上形成了相对开放的诗歌路线,将个体的道德体验融于充满激情的即兴诗行中,并感受审美其中的快乐:“在所有五彩斑斓的灯光闪亮之前,我的梦但愿有益!”[1](P132)抓住个体经验,秉持转瞬即逝的当下,这是奥哈拉的城市诗歌捕捉后现代道德灵感的一瞬。个体创造性的生活过程是道德生命力回归本真的不懈追求过程。在此意义上,奥哈拉诗作中的个体性道德体验是美国后现代道德的生存动力和基本模式。
二、多元性
由于个体的多样性,奥哈拉作品中的后现代道德生活图式是多变不定、模糊不清的,显示出后现代道德多元纷呈的特点。《距离他们一步之遥》(AStepAwayFromThem)、《城市之冬》(ACityWinter)等即景式短诗的艺术主题往往取自平淡中的人和周围的事,且与诗人当时存在的具体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去播撒种子以唤醒我心”[1](P111)的道德情感和知觉努力,注定摆脱不了生命意志的自由性本质,以想象、直观等非理性因素呈现多元化规律,这是后现代道德生活的现状。科学技术和理性规划无论怎样宽广,都不能冲破自身的限度而挣脱人类固有的生物环境的牢笼,即离不开“以人为中心”[4](P189)的生命体验范畴而走向独断与专权。像《华盛顿越过特拉华河》(OnSeeingLarryRivers’WashingtonCrossingTheDelawareAtTheMuseumOfModernArt)中的内在诗境一样:“瞧,我们多自由!”[1](P138)这种直面人和事的“去中心化”立场,通过人类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而一跃成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心。
毋庸否认,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急剧变迁时代,纽约城里的公共秩序或个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理性和制度的维系与规范。但是,都市生活跳动节奏中的理性和制度并不能澄清生活本身的一切重大意义,自然也就解决不了人类心灵荒原的自我救赎难题。奥哈拉的诗歌尝试从一个反传统的视角拨开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迷雾,以期重建人类道德的阐释力和生命力。在他那篇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实验作品《第二大街》(TheSecondStreet)中,建立在虚幻经历之上的每一件事情描绘的都是独立自主的都市生活意象。这些看似支离破碎的散漫细节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本表象整体,小心翼翼地开挖着生命个体的超验性和神圣性,洞察着纽约都市生活的深刻性质。《纪念日1950》(InMemorial, 1950)中的科学实验和进步技术固然拥有猛烈性的破坏力量,但其间的规范化理性制度根本就不能穷尽整个世界的全部意义和生命内涵,就只能借助于诗人对个人道德经验的直面感受,去追寻隐匿于鲜活的人类生命背后的那道看不见的善良之光:“战争结束了,那些事情熬过来了/ …… / 艺术不是字典 / …… / 我爱的又失去了。”[1](P145)在日常生活的生命体验中,“我们将拥有我们希冀的一切”[1](P134)的感性世界,只能是一种无意义的幻觉。道德规则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成效也需要谋得个人体验的内在历练与逻辑支撑:“因为费力正流着汗且又充满柔情蜜意的爱的坟墓临近的地方 / 不会再有死亡。”[1](P134)因此,对于奥哈拉而言,发掘个人生活的道德旨趣等同于对世界宿命意义的探索和对理性之外生命多重意义的印证。
其次,奥哈拉还充分意识到单一的语言符号,根本就不可能表达出后现代道德文化和生活风格的无限丰富性与多种可能性。要纠正后现代生活的偏失与无奈,必须为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等级消弭提供一个共时存在的合理性空间。《音乐》(Music)里的时代特质就呈现了一种潜在的、有点超现实味道的政治文化大拼盘内涵。诗中曾经象征着英雄主义的“五月花”和“古罗马战车”,在这里表达的却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凡夫俗子的物质消费生活:“在五月花商店停下来吃一块肝肠三明治 / 那位天使好像把马牵进了伯格道夫购物中心。”[1](P210)这些字眼成为诗人对地方性道德和纽约人固有生活习惯的一种讽刺和批判,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美国历史道德记忆的一块“活化石”。至此,长期被降温的美国历史道德记忆,如今也被诗人奥哈拉纳入诗歌的创新实验,在这个物质因素无所不在的消费世界中进行着独特的、“赤裸裸”[1](P211)的披露和解读。从前掌握在上层建筑和知识精英手中的道德话语权、如今也逐步复归于芸芸大众的原始欲望。曾一度被贬为原始、落后的传统道德观念重新受到关注, 人们对道德文化的世界价值也予以了新的评判。在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奥哈拉的眼里, 单一目标是希望的刽子手,目标本身不再重要。既然每天都是一样的、无目标的一天,那么“怎么做都行”[1](P235)的道德准则就是生活的全部;换言之,那就是“很少将做爱看成是十恶不赦”。[1](P235)当“爱 / 已失去 / 星星出现 一把破椅子”[1](P214)诗行中的丑陋淫欲(性的描写)也被冒险地卷入“道德文化”的大众普及行列时,原本神圣权威的高雅文化就毫不留情地遭到了摒弃。“一切皆可入诗”的创作理念使奥哈拉的诗歌创作之路深入世俗美学的大众领地,他所持有的反理性、反权威倾向也把美国社会的道德文化资源由专享变为了共享。
当然, 奥哈拉任何一首诗作中的道德生活秩序,都是普遍的道德体验和具体的生活感受的统一。这种天然的统一,与理性主义者旁观生活的冷峻态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正如《收音机》(Radio)、《忧郁的早餐》(MelancholyBreakfast)、《简在家里》(ChezJane)、《音乐》(Music)中的后现代道德要求一样,只有凭借着大众文化所特有的居于生活底层的日常意蕴和持久道德情感,才能推动艺术家们主动深入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探寻和挖掘多元鲜活的道德生命和特殊多样的道德冲动。
三、生活性
奥哈拉的诗歌创作,在内容上倾向于生活化的具体事件和短暂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不断与自我进行对话的道德体验,显示出很强的后现代道德的生活性特点。“激动的实现了的愿望 / 正在和诗的洞察力 / 缔结终生的婚姻”,[1](P253)这一愿望并非是人类外在的非理想性的终极关怀,而是以日常性的情感体验为道德探究的基点,并对具有偶然性和外在性的个性化感官体验加以关注,以便凸显出美国后现代道德生活所具有的明确“另类”特征的典型例证。不过,诗人奥哈拉的后现代道德观并非仅为倡导一种单纯化的简单生活,而是旨在鼓励人们要努力去体验正在经历着的生活,即“让后现代成为生活自身”。[5](P61)尽管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诸多道德经验对个人而言具有某种先在的善恶冲突性,但它能够引导着人们的生存视野由发展走向超越。所以,“一件完美的事 / 就类似于人类的一只手 / 真的是这么回事”。[1](P251)其中的生命状态挣脱纯粹一致性的理性枷锁禁锢,向着尊重和反思体验的道德生活方向前进。这个向道德批评前进的诗学方向,同时也意味着统合了混乱和模糊质素的后现代生活经验对理性规划主义的颠覆与反叛;但它并非是人类生命的唯一存在方向,而是“一件真正恰当的事”。[1](P252)在诗人奥哈拉看来,以“事实之真”为前提的“道德之善”必须要以非平庸的视角在“重复之中”发现不同,才能认清后现代道德生活的绝对优先权和主要目标:“深夜独自一人 / 在这潮湿的城市 / 乡村的风趣 / 容易被忘记。”[1](P260)“白色的飞机轻盈地 / 在地平线上漫游 / 你的羽翼敲打 / 到地面 并将我们的斑点 / 捻进珊瑚和草场。”[1](P259)这其中的物质客体和心理倾向是诗人认识事物多样性的一种特殊方法,它是后现代艺术家从差异中对道德本质规律的必然性探讨和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理智把握。至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强调个人体验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直觉对人类生命而言同等重要。从个人道德动机的自主性体验中读出生命本身的道德蕴含,实现向个人旨趣的复归,这就是美国纽约派诗作获得道德话语权的思想前提。
“在充满不确定性、多样性和流变性的后工业时代,面对生活中各种复杂的道德冲突矛盾,无法诉诸某个固定的道德实践模式,去操控个性化了的具体的人的道德行径。”[6](P95)正如“你的手如同天鹅 / 砣在乌龟的背上 / 优雅地在海上漂浮”[1](P259)那样,个人必须以个性化的方式把握自己的道德命运,完成自我,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学会主宰自己的生活。《走着去工作》(WalkingtoWork)、《又是一个戏迷》(YetAnotherFun)中的日常生活复杂体验,不仅是个人审美体验与道德情感的统一追求对善恶的超越,也是真诚的自我对生活之美的向往。“谁又从无足轻重的人那里无所挽救?我正在变成 / 街道。/ 你在和谁相爱?/ 我?/ 背着光直接穿越”[1](P259)这样的诗句中,依然可见后现代道德生活之丰富性的活力表征逻辑。在奥哈拉的城市诗歌中,后现代道德对本能、欲望、享乐等深层道德情感因素的重视,不过是引导道德回归生活本位的非理性接纳过程。事实上,“倘若我孑然一身 / 尚能去爱,/ 这严肃的声响,这任务的恐惧”[1](P261)并不意味着情感因素的无度放纵和无限消解。况且,即使是生活化的道德规范,也无法穷尽生命自身的全部情感意义。只是城市诗歌为了标明当代文化脉搏对生活现实的控制力,往往将后现代经验世界的道德问题细节化、城市化、生活化,以便可以借助语言的本体功能而把握生活意义的优势。因为“所有的屈服都投向 / 众明星和闪烁他们名字的灯光牌”,[1](P261)这些生动体验的直觉式意念往往依赖于都市人群对特定的、精确的物质形式样态的本能反应。其实,由历史深处向历史表层的当下道德生活复归,势必会导致诗歌个性化、生活化的时尚性重塑。
自文艺复兴以来,从世界意义的发现到个人生活的关注,从卓越风格的模仿到大众旨趣的回归,文学艺术和哲学命题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多样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诗人奥哈拉将后现代道德种种现象置于个体灵魂的生活框架内加以审视和观察是睿智的。毕竟,“道德在本性上包含有某些非道德的心理因素”。[7](P105)“没有对道德和生活的亲身体验关照,生命的灵魂便无立足之处。”[8](P118)历经生活侵蚀的道德流变,并时时受到生活沉浮的驾驭,才是人类道德的真实命运:“从现在起 / 天将大亮。/ 出去,你们所有的人。”[1](P258)奥哈拉回归大众生活,“与生活共沉浮”[8](P126)的路径,厘清了美国当代诗歌未来的道德走向。它将作为“风向标”,推动美国诗坛向都市更为开阔的伦理空间延伸、拓展。
四、结论
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后现代道德显示出巨大的生命活力。在他的作品中,都市生活的各种即兴事件不仅是对真切的个人体验的多元呈现,也是对真挚的个体道德的直接考验。作为奥哈拉城市诗歌中后现代道德活力的最终源泉,都市生活的日常体验在某些特殊时刻的特殊境遇之下,往往如火山般迸发出来,能瞬间击中人性深处最敏感、最隐蔽、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的最本真道德神经,如被埋藏已久的原始性爱冲动、城市生活的无奈心理规律或其他重大的生离死别情节等。当代美国的物质社会反复传递着影像刺激的凌乱感和震荡感,它们在奥哈拉的城市诗作中传达出纷乱杂沓的审美效果和情感风格。正是借助于这些逼真的视觉冲击和发达的媒体技术,因个体生命存在而辉煌的不同个体间的道德冲动和共识才能给现代人的心灵以抚慰和冲击。因此,奥哈拉的城市诗歌不仅阐释了后现代道德的基本属性,在揭示人性伦理的深层意义上也必将影响深远。
注释:
①本文中出自《弗兰克·奥哈拉诗歌选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Frank O’ Hara)的引文均为作者自己翻译,不再一一注明。
[1] Donald Alle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Frank O’ Hara[M].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2] Blum L A. Moral Perception and Particular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ies[M]. Oxford: Blackwell,1995.
[4] Hans Bertens. 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A History[M]. London: Routledge,1995.
[5] Robin Gill. Moral Leadership in a Postmodern Age[M]. Edinburgh: T. & T. Clark,1997.
[6] Jonathan Dancy. Ethics without Principle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7] MacInture A.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M]. London: Duckworth,1985.
[8] Jerrold Lebinson. Aesthetics and Ethics: Essays at the Inter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