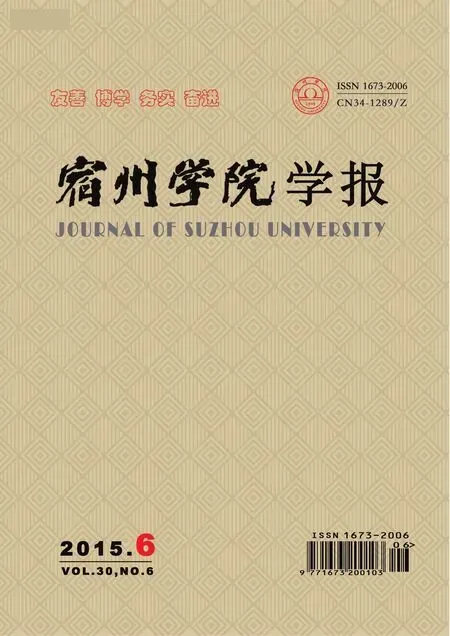一个自由的存在
——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觉醒》中的埃德娜
杨玉萍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一个自由的存在
——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觉醒》中的埃德娜
杨玉萍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读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中的主人公埃德娜。运用存在主义关于“人的存在”和“自由选择”等理论探讨埃德娜这一人物形象,并结合小说情节以及埃德娜的心路历程来分析她从觉醒到追求自由,再到捍卫其“本质”的过程。将《觉醒》作为一部存在主义小说来解读,艾德娜已认识到她的“自在存在”不过是丈夫的附属品。通过“自为存在”,她决心要做一个有自由选择的人,宁为自由死也不愿苟且于世。小说昭示:埃德娜的存在是一个自由的存在。
凯特·肖邦;《觉醒》;存在主义;自由;存在
19世纪著名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名噪一时,然而,她的巨著《觉醒》曾一度被埋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受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影响,人们才打开了尘封一个世纪的《觉醒》。小说中女主人公庞太太即埃德娜的形象,一反传统,被肖邦刻画得栩栩如生,仿佛一首奇妙的乐曲拨动了万千读者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
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存在主义最著名和最明确的倡议是让·保罗·萨特的格言:“存在先于本质”(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存在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由他在完全自由的选择之下所做的一系列活动构成的,构成的这个东西可以称之为人的本质(essence)。存在主义强调自由选择,但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1]74。
在《觉醒》这部小说中,埃德娜是否自由地选择并为此负责呢?她所极力维护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在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中,捍卫个人本质的人不在少数,却罕见埃德娜这样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因此,仅仅探讨埃德娜的觉醒与自由是不够的,还要深入研究她的生与死。死亡这一命题是人类永远无法解开的迷,因为死去的人从来没有告诉活着的人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活着的人永远不知道死后为何物。
以往有关《觉醒》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主义或女性成长的历程,本文从存在主义视角探讨埃德娜是如何作为一个自由的存在,造就了自我并誓死捍卫自己的本质(the essential)的;并以死亡作为探讨埃德娜本质的一个时间界点,结合其做出自杀这一决定的缘由揭示埃德娜所捍卫的本质,进而指出埃德娜通过死亡走向了另一个自由的存在。
1 埃德娜的觉醒
斯蒂芬·恩萧(Steven Earnshaw)曾对一个人的觉醒过程做了系统的总结。恩萧认为,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主人公通常是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
[27]王士元.语言、演化与大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9
[28]Zatorre R J,Evans A C,Meyer E,et al.Lateralization ofphonetic and pitch discrimination in speech processing[J].Science,1992,5058:846-849
[29]Siok W T,Jin Z,Fletcher P,et al.Distinct brain regions associated with syllable and phoneme [J].Human Brain Mapping,2003,18:201-207
[30]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75
[31]Strange W. Cross-language studies of speech perception:a historical review[M]//Winifred S.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Issues in Cross-language Research.Timonium,MD:York Press,1995:3-45
(责任编辑:李力)
而后一系列关于存在的问题便会随之而来。比如,主人公会问“在这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意义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应当对谁负责?”他指出萨特认为“一个觉醒的自己旨在对自己负责,做一个真实的自己”[1]18。
小说中,埃德娜的觉醒也是如此,她首先意识到了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她突然意识到了自我,自己不是别人的附属品,而是真实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自己。小说一开始,埃德娜就是已婚之妇,并有了两个孩子。埃德娜逐渐忍受不了这种平淡无奇、索然无味的婚姻家庭生活。于是在一个深夜,当她的丈夫雷昂斯把她从沉睡中叫醒并督促她去看孩子时,她终于哭了。她觉得“在她意识中不熟悉的某个地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给她带来模糊的痛苦并充满她的整个存在(her whole being)”[2]7。从那时开始,埃德娜就模糊地意识到了她的生活现状带给她的压抑和痛苦。“简而言之,庞太太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是作为一个人,意识到她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及她与世界的关系”[2]15。与传统的女性形象不同(她们听从自己的丈夫,把自己当作丈夫的私人财产,她们的生活就是相夫教子),埃德娜开始敢于违背丈夫的意愿和命令。又在一个深夜,雷昂斯回到家中发现埃德娜躺在吊床上,便要求她回到卧室睡觉。这次,埃德娜没有顺从丈夫,而是固执地呆在外面,直到身体上的睡意侵袭她,她才回到屋里。“不,我就待在外面,”她说,“雷昂斯,去睡觉吧,我就想待在外面,我不想进屋里,我不打算进去。不要再像那样跟我说话,不然我是不会回答你的。”[2]36这是她第一次勇敢地跟丈夫抗衡,并以胜利告终。
萨特指出,对于人来说,“存在先于本质”[1]74。这一学说成了萨特作为存在主义大师的经典名言。人们说到萨特,便会想到“存在先于本质”。值得说明的是,萨特的这一学说是在不考虑上帝的前提下,即在无神论的范畴内。因为,倘若考虑上帝,那么上帝造人也是预先想好了人的功能与意义,而后再创造人。这么一来,人也就同一把剪刀一样,是本质先于存在了[1]74。所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可以说是一种无神论思想。或者说,萨特的哲学必须“从主观开始”。萨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3]6小说中,有一次埃德娜在做弥撒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这时,她想逃离教堂那令人窒息、无比压抑的氛围,跑到室外那辽阔的天地里去。于是,她来到了安东尼夫人家里,并在一张床上第一次爱抚自己的身体,她发现自己的身体竟是如此美丽。埃德娜这一逃离教堂的举动,似乎暗示了她内心深处对于宗教、对于上帝的无视与冷漠。相反,埃德娜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并有思想的“人”而存在着。
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埃德娜开始遵从自己的内心,做真实的自己,也即追寻自由。
2 追求自由
萨特认为人的行为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因为我宣传自由,就具体的情况而言,除掉其本身外,是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的;而当人一旦看出价值是靠他自己决定的,他在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就只能决定一件事,即把自由作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这并不是说他凭空这样,这只是说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为,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3]27
人们常说“三岁看老”,埃德娜从小时候开始就对自由有着朦胧的幻想,暖暖的海风使埃德娜“想起在肯塔基的一个夏日,一个小女孩正在穿越一片浩瀚如海、比自己腰际还高的大草原。她一面走一面游泳似的将双臂平伸出来,像在水里拍水一样拍着高高的草原。”她说:“我一定觉得自己可以永远往前走,仿佛这片草地永远都没有尽头。”[2]18-19可见,埃德娜小时候是多么享受在浩瀚的草原上自由地穿梭,并且希望那份自由永远保持下去,她似乎沉浸在了自己虚妄的梦里[4]93。
从开始反抗丈夫的命令,到后来搬到鸽舍自己居住,这些都是在做真实的自己,也即追寻自由。“当埃德娜终于一个人时,她如释重负地深深地叹了口气。”并且,埃德娜为自己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而高兴,“现在,她的时间完全属于她自己了,她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2]85-86。埃德娜的自由选择集中体现在她离开雷昂斯的豪宅,独自搬到鸽舍去住这一举动当中。她说“我就知道我会喜欢,喜欢这种独立和自由的感觉”[2]94。她不仅想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还要有空间自由。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自由为埃德娜更加自由的行为提供了便利。她与阿勒宾私通,她自由地出行,悠闲地漫步于林荫小道。
她还曾幻想:“一个女人在夜里和她的情人乘坐独木舟向远处划去,再也不回来了。他们将消失在岛屿中,自此将没有人会再发现他们的踪影。”[2]83埃德娜对爱情也抱有绝对自由、远离尘嚣的幻想。甚至到小说结尾,她决定溺死在大海,这一举动也是自由的选择。
3 自由与责任
然而,自由也意味着痛苦。因为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不能撤销的,并且一旦选择就会对自己乃至自己身边的人或环境产生相应的影响。就如同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他写的诗《未选择的路》中所感慨的那样,人不能同时选择两条路,选择其中一条就必须放弃另一条。况且,时间是一维的,是线性发展的,一旦逝去就无法追回。所以人无法同时过两种生活,即使这个人有精神分裂,他的两个自我也不可能同时存在。并且,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性给人带来痛苦。倘若人的生命是无限循环的,那么人做的每个决定都可以被推翻,人的每个选择都可以重新来过,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痛苦和承担责任了。所以,人应当慎重选择,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是摆脱不掉的:他的选择牵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3]25有自由就有责任,萨特的“责任”来源于自由,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5]152。所以尽管埃德娜的选择是自由的,她的选择以及由此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所牵涉到的不止是她自己,还包括她身边的人。不管怎样,她始终处于一个社会环境中。那么,埃德娜就要为她的选择承担责任。小说结尾,埃德娜选择将自己溺死在大海之前,为什么还要去找维克多, 并说打算和他们共进晚餐呢?在此之前,埃德娜曾被拉夫人警告“埃德娜,想想你的孩子们吧!想着他们,记着他们!”[2]131而紧接着,在埃德娜与医生的交谈中,埃德娜无意间就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顾虑:“然而,我还是不应当摧残幼小的生命。”[2]132显然,这里的“幼小的生命”指的是她的两个孩子。由此,笔者有理由推断,埃德娜在自杀之前之所以去找维克多,是因为她不想给她的孩子带来母亲自杀而死的心理阴影,所以她要把自己的死伪装成偶然的溺水事故。试想一下如果埃德娜明目张胆地自杀了,那么人们会用怎样的眼光看待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在这种处境中,埃德娜这一做法是明智的,她既自由地选择了死亡,又很好地承担了这种选择的责任。
4 誓死捍卫本质
小说中,埃德娜多次说到“我可以放弃非本质的东西(the unessential),我可以给予金钱,我可以为我的孩子们牺牲我的生命,但是我不会给予我自己。”[2]56埃德娜把金钱和生命都视为是非本质的东西,而把“她自己”(herself)视为本质,显然这里所说的“她自己”并不等同于她的生命。那么“她自己”,也即这本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存在主义认为,人在完全自由的选择下所做的一系列活动形成了他自己的本质(essence)。“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是他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3]19所以,埃德娜所在乎的本质即是由她在自由选择之下所做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而构成的她自己(也就是她所说的“herself”)。埃德娜所做的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在追寻自由,是在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然而,这个“总和”该从何算起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性”使得存在主义关于“自由”“痛苦”和“虚无”的概念成为可能。所以,“有限性”在存在主义哲学中具有极大的意义。只有勇敢面对死亡,人类才能理解自我和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死亡,所谓的“可能性”才具有意义,因为它使得“选择”是不可逆转的,这也正是痛苦的根源[1]18。“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意图上才存在,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3]18“死总是——不管有理还是没有理,这正是我们还不能决定的——被看作人的生命的终端。”[6]645所以,从宏观上来看,一个人的死亡,即生命的有限性,极好地诠释了这个“总和”。死亡在最大程度上,最彻底地诠释了一个人的“本质”。
小说中,埃德娜所极力捍卫的本质和自我正是在她死亡的那一刻得到了印证与说明。她热爱自由,享受自由,并沉浸在自己“虚妄的梦”里。然而,孩子的牵绊让她痛苦,她觉得“孩子们像是能够压倒她的敌手,他们已经压倒她并且企图将她的余生硬生生地拉进灵魂的奴役中。然而,她知道有一个方式可以避免他们。”[2]136不难发现,埃德娜的方式便是选择死亡,来避免灵魂被奴役的悲剧。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在他的《西绪福斯神话》中就死亡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探讨,他认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7]86有的人死了,是因为他认为人生不值得活下去;而有的人却因为达不到本真的生存而选择死亡,加缪称后者为“生的理由同时也是绝好的死的理由”[7]87,显然,埃德娜当属后者。恰恰是她对自由的、本真的存在的追求让她选择了死亡。所以说,埃德娜的死亡极大地诠释了她所捍卫的“本质”——自由的存在。
5 走向“自由的存在”
在存在主义那里,存在指“being”或者“existence”。在《觉醒》中,肖邦多次提及埃德娜的存在,用的词语便是“being”和“existence”。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里,“存在(existence)”指“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之间的关系。“自在存在(the in-itself;being)”指的是“我是什么(The thing I am)”。“自为存在(the for-itself;consciousness of being)”指的是“思考自在存在的一种意识”[1]81。由此,埃德娜觉醒并追寻自由就是归功于她的“自为存在”,她意识到了自我,思考自己存在的方式以及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存在的认知也慢慢浮现。小说中的瑞兹夫人爱好音乐并弹钢琴。而音乐对于勾起埃德娜对自身的存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似乎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愫,可以让她的脊背为之颤抖,“第一次,那不变的真理触碰到了她的存在”[2]30。当罗伯特将要离开埃德娜去墨西哥时,埃德娜又感觉一个新的觉醒的存在悄然升起。在瑞兹夫人家中看到罗伯特的信时,音乐再一次穿透了她的整个存在,像光辉一样照亮并温暖着她灵魂深处最黑暗的地方。埃德娜对存在的认知伴随着她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慢慢地浮现,并照亮她的灵魂,指引着她追随自由的生活。在埃德娜追寻自由的一生中,孩子与婚姻在无形中成为了她为自我而存在的一种牵绊,于是婚外情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追寻自由爱情的需求。罗伯特的退缩让埃德娜失望并心灰意冷,埃德娜觉得除了自己的内心,似乎没有什么能成就她的自由的存在,她希望远离这种烦恼,她希望会有一天罗伯特会从她的思维中消失,远离她的存在[2]136。存在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个人主义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同传统的个人主义不同的地方……是把孤独的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出发点。”[8]27埃德娜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往往陷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在小说中的体现便是凯特·肖邦对埃德娜大量的内心独白的描写。埃德娜似乎习惯于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她去追求音乐对灵魂的洗礼、去追求自由与存在、在她对爱情失望的时候,也是诉诸于自我而非他人。外在的束缚使她痛苦,使她挣扎,但最终还是没能让埃德娜屈服。埃德娜最终选择死亡来解决她不堪的现状,去获得自由的存在,这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至此,回顾埃德娜的一生,她从小就向往自由自在,长大了又逐渐开始意识到自我,她与丈夫抗衡并有婚外情,她开始追求自由,她想摆脱牵绊,誓死捍卫本质。通过自由选择,埃德娜的一生印证了“存在主义”理论关于“自由”“责任”“本质”和“存在”的思想。埃德娜不愿做丈夫的财产和附庸,追求自由并勇于承担“责任与痛苦”。虽几经风雨,埃德娜还是通过死亡迈向了更高层次的自由,也捍卫了自己的“本质”,最终成就了一个自由的存在。
[1]Steven,Earnshaw.Existentialism: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2]Kate,Chopin.The Awakening and Selected Stories of Kate Chopin[M].New York:Penguin Group,1976
[3]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孙胜忠.分裂的人格与虚妄的梦:论觉醒型女性成长小说《觉醒》[J].外国文学,2011(2):89-96
[5]魏金生.人本主义与存在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7]加缪.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M].郭宏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许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李力)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6.017
2015-01-30
杨玉萍(1991-),女,安徽阜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074
A
1673-2006(2015)06-00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