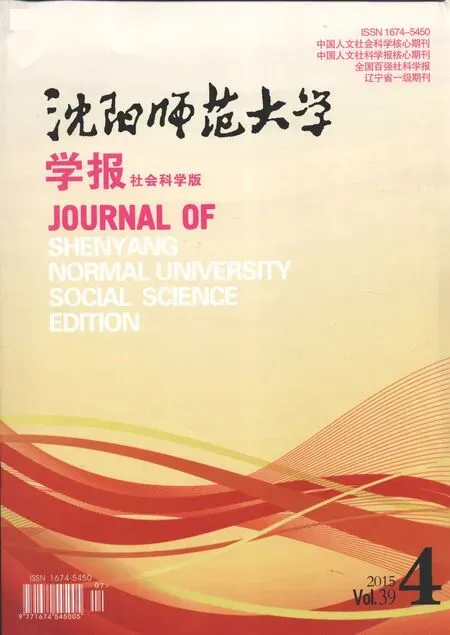日本“异端”作家女性审美取向的民族性
张晓宁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日本“异端”作家女性审美取向的民族性
张晓宁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泉镜花、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三人是日本近代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他们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初登文坛之际就以各流派的代表或骁将受到文坛的瞩目,更表现为在日益西方化了的日本近代文坛上,他们以日本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分别塑造了“诡异”“妖艳”和“悲凄”的女性之美的经典系列艺术形象,三人以此表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物哀”文学传统和审美理念。
异端之美;女性审美取向;物哀审美理念;民族性
泉镜花(1873-1939)、谷崎润一郎(1886-1965)和川端康成(1899-1972)三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杰出作家。他们在初登文坛之时,就分别以“浪漫派”“唯美派”和“新感觉派”的代表或骁将受到了当时日本文坛的瞩目。他们的杰出之处尤其表现于,在西方文学思潮仍在不断地涌入日本且又不同程度地主宰了日本文坛之时,当众多的作家还在致力于效仿西方文学思潮之际,他们却能自觉地对日本的民族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和反省,最终以独特的表现形式守护了日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尽管期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西方文化的迷恋与不舍。三人的文学主张与审美取向颇为相近。他们追求艺术至上;将表现“美”、尤其是“女性之美”视为艺术的使命;尤其擅长在“丑与恶”的事物中挖掘和表现“美”。因为三人与崇尚实证精神,重视取材于现实生活,反对“虚构与幻想”的日本近代主流,和正统文学相抗衡,且挖掘和展现“美”的形式与众不同,为此三人被视为“异端”。然而,他们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分别塑造了“诡异”“妖艳”和“悲凄”的女性之美的经典形象,以此向世人展示的是被日本近代文学遗弃了的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物哀”这一文学传统和审美理念。他们以女性、悲哀、异界、变态、非常态的情与爱等日本传统文学中最能表现“物哀”审美的要素,以此塑造女性的“极致之美”。其创作宗旨即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让读者获得感触和感动”这一日本传统文学的创作宗旨。
一、“诡异”“妖艳”和“悲凄”的经典女性形象
泉镜花整个生涯中有40余部是描写神秘与怪异的作品,这些神秘与怪诞的作品代表了泉镜花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其中的《高野圣僧》(1900年)则代表了泉镜花文学的最高水准。《高野圣僧》中作者对女主人公形象的成功塑造堪称是其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高野圣僧》讲述的是高野圣僧年轻时一次奇特的云游经历。故事情景荒诞离奇,却十分引人入胜。高野圣僧在途经水蛭、毒蛇、蚂蝗等出没的诡异森林之后,投宿于深山中一独户人家。此宅中的女子风姿卓绝,美艳倾城。不仅如此,她还魔性十足,能在夜半时分,自如应答来此骚扰喧闹的各种鬼魅禽兽。当日夜光之下,此女趁替高僧擦拭脊背之机对高僧暗施色诱,幸而该僧幼年受戒,秉性质朴,最终免遭此劫难。与泉镜花此类其它作品相比较,《高野圣僧》的女主人公不仅美艳倾城,还同时兼备有神力和魔力两种力量。她能以山间河水治愈被毒蛇、蚂蝗蛰咬得遍体鳞伤的高野圣僧,还能将对其欲图不轨的男子变成各种鸟兽。《高野圣僧》在塑造女性形象上的特殊意义在于,作者泉镜花超越了此前日本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美表现的既成模式与局限。他将年轻女性那带有体温的、富有弹性和触感的丰满的肉体以及通过肉体酝酿出的情感完美地再现了出来”[1]278《高野圣僧》中的女主人公皮肤白皙,体态风韵。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透过薄薄的衣裳,年轻女性乳房的轮廓若隐若现。作者透过女主人公体貌传递出的年轻女性独特情味,带给了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如此饱满、浓重的笔触表现年轻女性赤裸裸的肉体之美的范例,在日本此前日本的《万叶集》、《源氏物语》、甚至井原西鹤的作品中都不曾出现过。作者泉镜花堪称是“史无前例地将女性的肉体的本质的东西带入了日本文艺这一特殊世界”的人[1]278。这也正是是泉镜花“异界中的魔女”经典形象创作的一个独到之处。
与泉镜花相似,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同样也展现了对女性美的绝对忠实。但与泉镜花“异界中的魔女”形象不同的是,谷崎的经典女性形象是以自身的“官能魅力”为武器对男性颐指气使的、异常的、妖艳的恶魔般的女性形象。1910年24岁的谷崎发表的短篇小说《文身》,描绘了文身师清吉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在一个年轻美女的背脊上汶上了蜘蛛图案。美女入浴时苦痛难忍,然而清吉却在晨曦映照下的美女的背脊上感受到了异常的妖艳之美,竟然被自己创造出的妖艳之美所倾倒。由此自愿拜倒在美女的石榴裙下甘受其命。这篇早期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谷崎追求异端之美的审美情趣。此后,谷崎的作品《麒麟》(1910)中的南子夫人、《恶魔》(1912)中的照子、《痴人之爱》(1924-1925)中的娜奥密、《春琴抄》(1933)中的春琴等等,都是凭借女性官能魅力和野性让男人们放弃了底线甚至生命的。如《痴人之爱》中的女主人公娜奥密容貌超群,性情奔放,将男主人公河合“弄得神魂颠倒”,让她骑在自己的脊背之上自甘受虐,对如此跋扈的美女奉献一份“痴人之爱”。此外,通过异常的情爱表现对女性肉体美的绝对崇拜这也是谷崎润一郎创作的独特之处。尤其在其晚年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极致,如《钥匙》(1956)中的丈夫为了追求异常的情爱甘愿将第三者引入自己和妻子的婚姻中,因此丢了性命都在所不惜。
与泉镜花和谷崎润一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川端康成的创作完全体现了对女性美的执着。川端近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完成了一百多部以女性为主要人物的作品。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女性的“美丽”和“哀愁”。“悲凄的美女”堪称是川端康成女性形象中的经典。早期的代表作《伊豆的舞女》(1926)中的女主人公“熏子”是其笔下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为构筑其系列的下层少女——艺妓、女艺人、女侍者的形象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舞女“熏”与当时日本首屈一指大学的预科生“我”的美好爱情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川端从编织舞女“熏”令人悲叹的境遇开始,再透过“熏”对男主人公的纯情与执着,来反衬其内心的感伤与哀愁。这种心灵深处的“悲伤”与现实中真实的美景、真情交融在一起,创作出一种川端独特的“悲哀美”的抒情世界。川端康成中期的代表作《雪国》(1935-1947)中的女主人公——驹子与“熏”同样,也是欲爱不能、郁闷悲凄的美丽少女形象。她认真地对待生活和感情,保持了乡土少女的朴素、单纯的气质。她深知同有妇之夫的男主人公岛村的关系“不能持久”,却又无法自拔地迷恋于他。不仅“熏”“驹子”如此,川端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具有令人哀叹的个人境遇和情感,她们沉溺在内心矛盾以及与家庭、道德、社会的纠葛之中。他以表面优美、风雅,而内在却蕴藏着悲伤的“悲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增强女主人公形象内涵的深度和艺术的感染力,表现了最鲜明、最柔和的女性的极致之美。
泉镜花作品中异界美女的魔力与色诱、谷崎润一郎作品中以官能魅力为武器的女主人公们的跋扈与变态、川端康成笔下美丽女子们那悲凄哀婉的爱与情、以及三人笔下男女间异常的性爱的表现,如此这般在非常态的事物中挖掘和表现女性之美的审美取向,很难为不同民族的读者所理解。但是如果以日本文学的传统为视角来审视这样的审美情趣,会发现它颇有只属于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特质的东西。泉镜花、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三人的“异端”女性审美取向,从《古事记》的创世神话、到平安时期的和歌和物语,以及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中都可以寻找到其根源所在。三人以让读者叹为观止的女性之美的经典的形象,向读者展示了以“物哀”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学审美传统和理念。
二、异端之美与“物哀”
从本质上讲,“物哀”是包括日本自上代、中古、中世以及近世的日本传统文学的思想核心。围绕日本传统文学的创作宗旨的探讨,日本的学者们从《源氏物语》产生的平安时代开始,直至今天从来没有中断过。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开始,对其研究和争论也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结果莫衷一是,但在众多主题争论中,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始终被日本以及我国评论界视为比较权威的论断。本居宣长在《源氏物语》的研究专著——《紫文要领》一书中明确指出,《源氏物语》乃至日本传统文学的创作宗旨、目的就是“知物哀”[2]66。“物哀”一词是日本的固有词汇,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曾从词源学角度对“哀”(あはれ)、和“物哀”(もののあはれ)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结论是“哀(あはれ)”该词与中文的“悲哀”一词意思并不完全吻合。日本《大辞林》也以《源氏物语》为例对其做了解释[3]2048,中文的意思是:“物哀是代表了平安时代文学的一种文学理念,也是审美的理念。是当外界的事物与人的自身情感相一致时所产生的调和的情趣世界。本居宣长指出,《源氏物语》则是表现物哀的集大成之作。”“物哀”一词除了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释之外,还包括哀怜、怜悯、感动、感慨、同情、壮美的意思。我国学者叶渭渠在《物哀与幽玄》等著作中针对“物哀”这一日本传统文学思想也有专门论述。叶渭渠[4]73在该著中将“物哀”作为日本传统的艺术美的形态之一论述了它的形成与发展。叶渭渠为代表的我国学者还主张将“物哀”一词直译成汉语的“物哀”,因为相应的其它汉语词汇都难以完整地表现出其中的微妙蕴涵。此外,我国学者王向远以日本传统美学的视角对《源氏物语》的主题作了具体阐释[5]9。本居宣长的“物哀”理论强调阐释了作者写作的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观察、感受与感动,如实地表达出来并与读者分享,以寻求审美共鸣及心理满足。此外,没有任何说教等功利目的。泉镜花、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三人对“物哀”理念的理解和继承各有侧重,如川端对“物哀”中“悲哀”的色彩尤其青睐,他的作品多以“悲哀”的元素来感知“物哀”,从而唤起读者的感触和感动。他从早期的《伊豆的舞女》、中期《雪国》、直到晚年的《一只胳膊》、《睡美人》,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具有令人哀叹的个人境遇和情感,她们沉溺在内心矛盾的纠葛之中。最终都没有逃出悲剧的命运。尽管泉镜花、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三人对表现“物哀”的主题元素各有侧重,但相通的是,他们选择了女性、异常之美、非常态的情与爱等共同的元素,以此塑造了形式各异的极致之美的经典的女性形象。而这些元素在日本文学的传统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好色”与“知物哀”
首先,围绕女性写小说这也是日本文学的一贯传统。本居宣长对此的解释是: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好色者”即是最能感知物哀者。而“好色”自然离不开女性。日文中“好色”一词于与中文意思不尽相同,它是一种美的理念。是一种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它包含肉体的、精神的、与美的结合,是灵与肉两方面的一致性的内容。《源氏物语》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好色”者,同时,他们也被认为是最能感知“物哀”者。以女性为主角目的是为了在“爱恋情趣”中更好地感知“物哀”。在此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古典具有“好色而不淫”的文学传统,川端就十分推崇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纵使放荡,心灵也不应是龌蹉的”文学主张[6]150。三人都是这一日本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尽管他们的作品中女性之美往往以“异端”的形式出现,但生理上的肉欲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他们的观念中,女性的价值在于她所承载的美,而“美”所具有的令人倾倒的崇高力量能令读者自觉地、深层地感知“物哀”之所在。
除了“好色”一词之外,日本传统“物哀”理论中对“善”与“恶”有其独特的理解和定义。它以“知物哀”者为善,以“不知物哀”者为恶。主张从自然人性出发的、对万事万物的包容、理解与同情。它与儒教、佛教的善恶观有明显区别,与中国文学中的理性文学、理性文化也迥然不同。既然写作目的是感知“物哀”,那么如何在作品中更好地表现“物哀”呢?对此《源氏物语》这部被视为典范之作的作品告诉我们,就是要尽可能地让作品“有趣”。而所谓“有趣”即是能让人更深刻、深层地感受到“物心人情”。那么什么素材最能让读者感受“物心人情”呢?本居宣长通过对《源氏物语》的剖析后总结概括出了核心与精髓,那就是要通过展现非常态的事物,让读者最大程度地获得感动,最大限度地感知“物哀”之所在。因为异常的事物能给人们带来的感触和感动是超乎寻常的。这点也正是泉镜花、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三人执着于在异常事物中挖掘和表现女性美的的宗旨所在。他们将最能表现“物哀”的主题元素做到了独到的诠释。将污泥浊水蓄积起来,并不是要欣赏这些污泥浊水,而是为了栽种莲花。三人通过对女性极致之美的塑造,就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所谓“物哀”之花。
相继出生于明治时代的三位作家,他们在被西化了的日本文坛之上,从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成就了各自不可替代的艺术特质,塑造了“诡异”“妖艳”和“悲凄”的女性之美的经典形象,以此展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物哀”审美理念,也以此守护了日本文学的民族传统。
[1]胜本清一郎.泉镜花的异神像[M]//谷泽永一,渡一.泉镜花论集成.东京:立风书房,1984.
[2]本居宣长.紫文要领[M]//日本物哀.王向远,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66.
[3]松村明.大辞林[M].东京:三省堂印刷株式会社,1988:2048.
[4]叶渭渠.物哀与幽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5.
[5]本居宣长“.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代译序[M]//日本物哀.王向远,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9.
[6]叶渭渠.川端康成传[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160.
【责任编辑詹丽】
I106.4
A
1674-5450(2015)04-0085-03
2015-03-23
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W2010390)
张晓宁,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