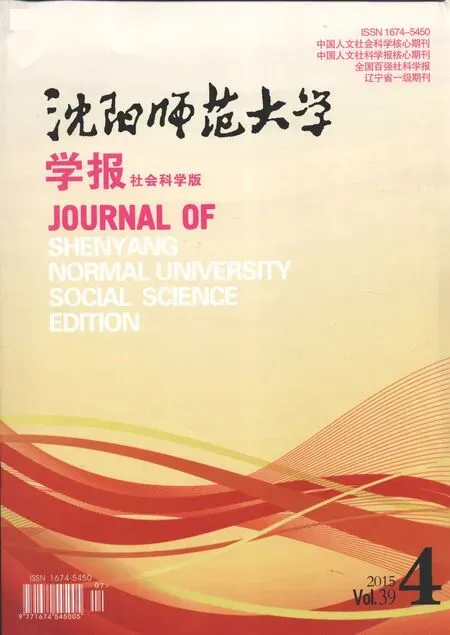满族女神神话精神内核探析
孙博,李吉光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
满族女神神话精神内核探析
孙博,李吉光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作为东北地区的原住民族,满族在母系社会形态停留的时间较长,女性崇拜的影响深远。这种环境下诞生的满族神话,女性角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实与神话相互影响,赋予了满族女神独特的民族气质和魅力,是满族的民族精神与审美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满族女神;崇高;民族精神
神话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神话的真实性不是事件的真实而是精神的真实。神话所体现出的精神便是民族在相应的历史阶段的真实状态。按照发生顺序,本文选取满族神话中非常重要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先知神话加以分析考察,透过神话的描述,尝试探究满族先民的精神内核。
一、创世神话中满族女神的不屈精神
(一)创世女神的英勇斗争
满族口述神话中,《天宫大战》汇集了一切重要的神话元素,如造物、牺牲、复活等,又称为“神龛上的故事”。故事描述了阿布卡赫赫、巴那姆赫赫、卧勒多赫赫的诞生及天地人三界创世的过程,其中世界和地球、宇宙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造天造神运动是如何产生的?“天宫大战”都作了详尽而生动的解答。这是北方先民又一重要的创世说,在北方神话学与民间口碑文学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天宫大战”讲述了创世之初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存在与毁灭两种势力的激烈抗衡。萨满教观念认为,人类创世之初,必有一番两种针锋相对的殊死搏斗,最终以光明获胜,万物才真正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与可能。阿布卡赫赫是女神,是整个自然势力的化身和代表,包罗万象,神威无敌;而以耶鲁里为一方的恶神,还有各种疠疫、疥疮、厄难、罹祸,以及自然界骤生的地陷山颓、风电海啸的职司恶神,其中耶鲁里为万恶之首,能够自我繁殖,暗示着上古时代灾祸无穷无尽。阿布卡赫赫、巴那姆赫赫、卧勒多赫赫在与恶魔的斗争中相继牺牲而后复活,直到战胜恶魔,暗示着人的生生不息,最终将获得生存的胜利。斗争的过程中,创世女神以坚定的意志面对几乎不可战胜的邪恶力量,表现出人性中不屈的美,正是这种精神带领我们从洪荒走到现代,实现了生存与发展。三位女神在战斗的过程里,接连牺牲了生命而又复生,直到最后将恶魔彻底消灭。在人的本质力量被强大的异己力量压抑、排斥后,最终通过审美实践得到人性的充分张扬,这可称之为崇高。而在《天宫大战》中,光明与黑暗的抗争,正义与邪恶矛盾双方的冲突对立,衍生出万物生灵和满天星辰,矛盾推动了世界的前进和发展,而在神话的恢弘描述中,女神的身上显现出令人惊心动魄的美。人神合二为一,赋予创世女神以崇高。这种崇高既体现为神心灵的伟大与神秘,也表现为改造自然、救赎苍生的责任与担当。在美学意义上,创世女神的崇高又体现为形象的壮美与审美主体道德完善的结合。这种形与质的融合,兼顾了世俗口味与理想标准,为人性的健全发展提供了美学目标。就如蒋孔阳曾经说到的那样:“美向着高处走,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提高和升华,以至超出了一般的感受和理解,在对象中形成一种不可企及的伟大和神圣的境界,这时就产生了崇高。”[1]
(二)恩切布库的事业
《恩切布库》是满族传统说部之一,是满族著名创世神话《天宫大战》的一部分,后独立成章。其名源自满语“enduri buku”音译,意即“神跤手”“与神摔跤的英雄”。全诗完整叙述了恩切布库从生到死的过程。恩切布库的神力可与创世三女神媲美,为了封印恶魔,她将自己投身于火山。天宫大战万年之后,阿布卡赫赫又将她召回人间,历经辛苦与磨难,将人间变为一方乐土,成就了累累功勋。《恩切布库·序歌》讲到:“恩切布库妈妈的故事/已传讲了数百余年/她是萨哈连黑水女真人/家喻户晓的尊贵的女神。”[2]恩切布库因此被世代满族人虔诚纪念。在与恶魔的斗争中,她为人民做出了诸多贡献。恩切布库教人们使用火,“恩切布库女神不但教野人们会用火/认识各种各样的火/还教他们怎么保护火/怎么抵御火/怎么驾驭火/怎么保留火种/从此/野民们不再为怕火而惊遁/野民们不再为缺火而烦愁/他们成为使用火和保存火的主人/成为大地上最无敌的人/生活远超过百禽百兽。”这使人类不再茹毛饮血,成为万物的灵长。恩切布库教会人类耕种生产:“舒克都哩艾曼的人们/又采集田野中的藤豆籽粒,并将野葱野蒜也种到艾曼/艾曼有了自己的葱、蒜,有了瓜、果、豆、蔬/鸡犬相闻,万里生机!”[3]这种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使人类有能力抵抗自然界的天灾巨变。同时也开展畜牧业,“恩切布库女神最早捕捉野兽,训养叫‘古鲁阔’/捕捉野狗,训养叫‘音达浑’/舒克都哩艾曼的族众/又在山外见到了一种/叫做‘莫林’的怪兽/……恩切布库将这种莫林怪兽叫做‘莫林马’/命族众习学骑术”[4]。这是满族人民第一次使用自然界的力量为自己劳作,从此成为大地的主人。自恩切布库从火山返回人间,她的形象已从女神渐渐变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在某种程度上,恩切布库是满族人的民族信仰之神,支撑着满族人更有信心和力量挺立在世间。这个过程让人体会到斗争的壮怀激烈,进而唤起人们生存的勇气、进取的力量与激情,实现悲剧之于人性升华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悲剧的确具有启迪民智、开化社会的教化作用。而恩切布库的传奇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冒险和牺牲,广阔的想象空间,给了她更多表现自我的机会,也赋予她震撼人心的悲壮情怀,她的牺牲,她的奉献,她对敌人的宽容和仁慈,呈现出不输于《伊利亚特》般的悲剧史诗特征。在满族人民民族意识萌芽的时期,通过说部这样的口头诗歌传颂形式,将满族人对世界所抱的宗教概念和朝气蓬勃的精神融于英雄的业绩之中。这一部伟大的史诗,就是满族社会最形象的民族历史,这样一种悲剧的意味,让恩切布库的形象伟岸雄壮,超越了性别的界限,将阴柔的女性之美和阳刚的崇高情感合为一炉。女神的牺牲和苦难,是走向崇高神坛的一级级台阶,进一步说,因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类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拥有神力的恩切布库处于乱世,注定了有更多的责任去承担。而当黑暗笼罩大地,无论是作为救世者的恩切布库,还是作为被拯救者的满族民众,都参与了崇高女性的塑造。拯救人间的伟大行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心灵激荡和情感起伏,充分折射出审美主体的正义、良知、舍己救世、不屈不挠、坚强顽韧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崇高的道德美和人生境界。
二、英雄神话中满族女神的牺牲与奉献精神
创世神话之后便是英雄神话,英雄的神话的主角是神力没有主神那么强大的小神或被神化了凡人,往往是部落首领、宗教领袖,体现在满族神话中,就是火神、完颜妈妈等一系列英雄形象。
(一)从突姆火神到彻库妈妈
创世三女神用自己的无边神力与恶魔耶鲁里对抗,不时落入下风,这时不畏牺牲的许多小神便挺身而出,加入与恶魔的战斗。火神突姆的故事广为流传,“巴那姆赫赫还将长在自己心上的突姆火神,派到天上卧拉多赫赫身边,用她的光毛火发帮助赫赫照路。天上常常见到的旱闪,便是突姆火神的影子,天上常常掉下些天落石,便是突姆火神的脚上泥。九头恶魔耶鲁里,闯出地窟,又逞凶到天穹,它要吃掉阿布卡赫赫和众神,耶鲁里喷出的恶风黑雾,蔽住了天穹,暗黑无光,黑龙似的顶天立地的黑风卷起了天上的星辰和彩云,卷走了巴那姆赫赫身上的百兽百禽。突姆火神临危不惧,用自己身上的光毛火发,抛到黑空里化成依兰乌西哈(三星)、那丹乌西哈(七星)、明安乌西哈(千星)、图门乌西哈(万星),帮助了卧拉多赫赫布星。然而,突姆火神却全身精光,变成光秃秃、赤裸裸的白石头,吊在依兰乌西哈星星上,从东到西悠来悠去,从白石头上还发着微光,照彻大地和万物,用生命的最后火光,为生灵造福,南天上三星下边的一顺闪闪晃晃、忽明忽暗的小星,就是突姆女神仅有的微火在闪照,像天灯照亮穹宇,后世人把它叫做“彻库妈妈”,即秋千女神。后来人们用高高的秋千杆架子,吊着绳子,人头顶鱼油灯荡秋千,就是纪念和敬祀突姆慈祥而献身的伟大母神。(竿上天灯)后来人类的部落城寨上和狍獐皮苫成的“撮罗子”前,立有白桦高竿,或在山顶、高树上用兽头骨里盛满獾、野猪油,点燃照天灯,岁岁点冰灯,升篝火照耀黑夜,就是为了驱吓独角九头恶魔耶鲁里,也是为了缅念和祭祷突妈妈母神。”(天宫大战原文)为了对抗恶魔,小侍女突姆火神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力量,谱写了催人泪下的救世挽歌。就像是屠格涅夫笔下的小麻雀,虽然貌似弱小但内心强大,勇敢地抗击猎犬,具有无惧恶势力的抗争精神。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其视为称崇高的对象。突姆火神的反抗斗争,让人产生紧张和不安的感觉,不由自主地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然后她舍身成仁,并且在生命的尽头还在想着为生灵造福,悲剧性的结局,转化为令人愉悦的自豪感、敬佩感,目睹整个场景的我们,能不为她的行为而深深触动么?此刻的她,比那些浴血沙场的男子汉更让我们感动和震撼。对于突姆火神来说,牺牲是新的开始,是她崇高信仰的最好诠释,火光毛发的失去,化为白石的悲哀,从那点点发出的微光里,是我们仰望星空时的泪水,突姆火神死后而已,那种舍弃自我造福人类的精神,依旧焕发着灿烂的光彩。人格的伟大与悲剧精神联系在一起,因为集体的利益引出的牺牲成全了女神的大义和大爱。但并非只有死亡就代表着悲剧,神话中的女神由一个美貌的女子,变成一块白石头,显现出悲剧精神,也展现了突姆女神的不朽。读者感悟悲剧性的故事,得以涤荡心中的自私和人性局限。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相符。这是满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伴随着故事的流传,世世代代的满族人灵魂得以净化。
(二)盗火女神托亚哈拉
火的发明,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使其告别茹毛饮血的野兽时代,令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恩格斯曾高度强调火在支配自然力、区分人与动物方面的重要意义。摩尔根所定义的中级蒙昧社会,也以火知识的获得作为重要的划分依据。火的发明极大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促进了人种的完善与更新。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民族,在原初阶段都有过采火、盗火等“火神话”。满族人民的火是怎么样被发现和使用的呢?是托亚哈拉女神,是女神的牺牲换来的,这是一则发生在《天宫大战》中的插曲,既是大战的尾声,也是人类文明的开端。托亚哈拉故事,主要源于《天宫大战》,她是另外一个火神,是为人类谋福的神明,相比于突姆女神,和人间走得更近。托亚哈拉的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创世神与邪魔力量的斗争。斗争行将结束,从阿布卡恩都力头上的红瘤中诞生出盗火女神——托亚哈拉。仁慈的托亚哈拉,勇敢无私地盗火下凡,为人间送去火种和光明。而她却失去了原来的美貌和神间美好的一切,变成了一只怪兽。这就是创世神话末期的一段悲剧。只有简单的只言片语,却呈现出女神的伟大。满族民众用自己智慧的想象和美好的道德,赋予了托亚哈拉女神以崇高的神性。虽然在康德等西方哲人眼里,“崇高”更多是与雄性相连。但在满族人的审美观念中,崇高与托亚哈拉这位女性、女神的距离却并不遥远。同时,满族人这种“女神崇高”的形容,与康德关于“崇高”的定义也并不矛盾。在康德看来,想象服从于理性才构成“崇高”的条件。而托亚哈拉的盗火之举,已经超越了理性,是为了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冲动”行为。这就不能按照康德的“理性——崇高”予以判断。我们或可以称之为“感性的崇高”。既然如此,康德关于“崇高”的雄性话语似乎也可以移植到托亚哈拉身上。诸如“强而有力(Powerful)”“活跃(Active)”“震撼(Overwhelming)”“驾驭(Dominating)”和“控制力(Masterful)”等,这些都可在盗火女神身上看到:“其其旦女神见大地冰厚齐天,无法育子,便私盗阿布卡恩都力的心中神火临凡。怕神火熄灭,她便把神火吞进肚里,嫌两脚行走太慢,便以手为足助驰。天长日久,她终于在运火中,被神火烧成虎目、虎耳、豹头、豹须、獾身、鹰爪、猞猁尾的一只怪兽,变成拖亚拉哈大神,她四爪踏火云,巨口喷烈焰,驱冰雪,逐寒霜,驰如电闪,光照群山,为大地和人类送来了火种,招来了春天。”[5]
三、萨满神话中满族女神高尚的道德精神
(一)闻名东海的第一萨满
在说部之中,曾经高高在上的神明,走下了凡间,成为了行走在人间的神使,这就是萨满的由来,她们身披神明的外衣,帮助世人走出困境,打败作恶的妖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萨满就是走出了神殿的神明,开始密切与人类的沟通,庇佑人类不受外界的伤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流传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的说部《乌布西奔妈妈》了。从她开始,便有了人间大萨满的传说。乌布西奔的故事是颂扬1416—1487年间,锡霍特阿林(山)麓、近东海海滨一带原始母系氏族部落中,声名显赫的乌木逊部落女首领乌布西奔的光辉一生。原本是赞美女首领英勇事迹的故事,但是在传承中被后人进行美化和加工,演变成满族人民虔诚敬仰萨满,神化祖先的传说。乌布西奔也变成了神女下凡,位列东海妈妈神群之中,成为行走在人间的神女。摩尔根将文明社会开始的标志定义为人类财产欲望的产生。他说:“对财产的欲望超乎其他一切欲望之上,这就是文明伊始的标志。它不仅促使人类克服了阻滞文明发展的种种障碍,并且还使人类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建立起政治社会。”[6]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免不了有自私和专权的倾向,如果战胜这样的人性弱点,便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巨人,可以称之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乌布西奔就是这样一个超越了人性劣根缺陷的人,她的存在便是为了其他人更好的生活。从故事的开头,乌布西奔就舍弃了天籁的声音,一门心思来到人间帮助凡人,远离了高高在上的神仙宝座。塔其乌离欣然说:“是的,我可将/咽喉声音,留给你们/我奉降人伦,只想扪心苦劳,话语尽可少用/我再求援海鸥代劳学语,朝暮喧叫海上,襄助你们传报好时辰。”[7]海神的身份没有了,却仍然牵挂着自己的责任。将声音奉献,俯首甘为孺子牛。实干者不打诳语,话语不多,却造福人间。岂止后来因为无法说话,乌布西奔蒙受了何等的不公和轻视,但是她并不在意这些,部族乡亲的平安幸福才是她心中不变的中心,而在她的一生中,接连打败了作恶东海的魔女,征服了专吃人脑的野人霍通,用强有力量的双手,庇佑东海的满族人,又依靠着双脚踏遍了东海的不平之事。超越了个人欲望的东海女神,不论是神责还是人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就像是一根燃烧的光亮红烛,点燃了自己,带来了光明和安宁,却没有时间去为自己着想,享受世间的美好。她的心,献给了人间的子民,也让后世的萨满以她为榜样,学习那种奉献和勤劳。
(二)神化的完颜女英雄
《苏木妈妈》属于满族说部中的给孙乌春“乌勒本”,讲述了千年前的满族先祖女真人的一位著名的女英雄,相传是完颜阿骨打的夫人——苏木格格。她不但从小就能文能武,智勇双全,而且有神权加身,是一位善于计策卜卦的大萨满。依靠着苏木的超凡能力,完颜部发展壮大最终成功地一统草原。功成名就之时,也殚精竭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逝去在阿骨打称帝之前。虽然伊人远去,但是英明永存,后世的女真人因为对她的怀念和感激,将很多神性赋予在苏木的身上,敬称她“苏木妈妈”,并在传统的灯祭中对她进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在这一天欢庆歌唱,传颂苏木的事迹。因为崇高包含一种粗犷质直的感性形态,豪壮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英雄之举令人心潮澎湃,进而受到鼓舞。苏木妈妈的神化过程,从侧面反映出满族先民对她英勇行为的认可和感激。在某种程度上,苏木不但是行走在人间的大萨满,播撒智慧和生存技巧的种子,更成为女真土地上维护和平的幸福使者。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善了女真部落人民的落后生活,同时结束了连年的战乱纷争,让完颜部成为女真最强大的部族。在她充满挑战的一生中,用自己的刻苦和勤奋,成就了自身的功业,也成功地令女真族人心生敬仰,从而在死后被神化和崇拜。崇高的形象来源于英雄的悲壮经历,苏木处于草原混乱时期的女真人,眼看着家乡受到战火的蔓延,怀揣一颗向往和平统一的心,这样的她,代表了无数死于战争的普通生命,那些为了统一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人们,把自己最美的一面投射到苏木身上,完善了女神的崇高神格。苏木所拥有的女神形象,是真挚情感、崇高精神,英雄行为,圣洁使命的化身。作为一个仁爱子民的女真贵族,她并没有安于富足的现状,反而认真学习各种知识,发展生产,传授生存的技巧,心甘情愿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部族的强大和进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完颜阿古打功成名就的时刻,苏木已经逝去,为了人民的幸福,她终于将生命燃烧到了最后。纵观她的一生,苏木妈妈身上凝聚了人类的崇高美德,成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不仅参与了伟大的事业——助完颜部统一女真,又体现在平凡实际的生活里,更彰显于天塌地陷的灾难中。此种力量,一旦于人的心灵中生根,就会释放出耀眼光华,催人奋进,锻铸出真善美之魂。
满族女神神话,其意义不但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传承,而且向现代人展示了原始人类对环境的真实体验。埋藏在传说深处的寓意和象征,传达了意味深长的初民呓语不论是神话所表现出对女性的权利的尊重,还是女性角色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都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和借鉴的。总的来说,满族神话中的女神具有的独特文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展现了女性不输于男性的力量和气魄,从侧面反映了当今社会所缺少的对女性的尊重和重新审视,是我们当今政治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所需要的民族精神。
[1]蒋孔阳.说丑——《美学新论》之一[J].文学评论,1990(6):31.
[2]富育光,王慧新.恩切布库·序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2.
[3]富育光,王慧新.恩切布库·传下了婚规和籽种[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120.
[4]富育光,王慧新.恩切布库·魂归天国[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142.
[5]富育光,邢文礼.天宫大战·玖腓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75-76.
[6](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
[7]鲁连坤,富育光.乌布西奔妈妈·哑女的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24-25.
【责任编辑詹丽】
I106.4
A
1674-5450(2015)04-0015-04
2014-06-12
孙博,男,吉林人,长春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