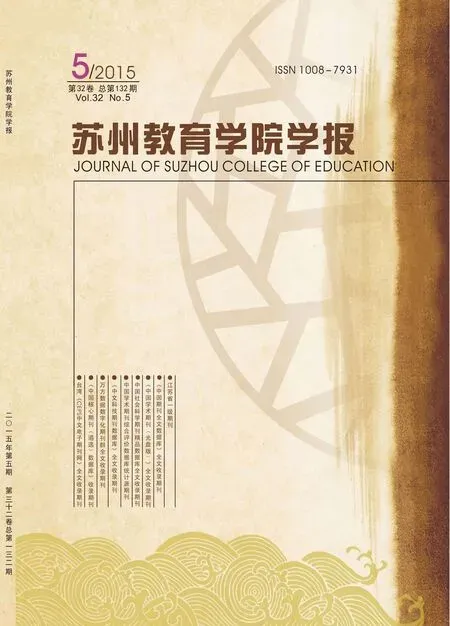萨默尔斯眼中的“他者”
—劳伦斯《袋鼠》中的殖民意识
廖春周(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萨默尔斯眼中的“他者”
—劳伦斯《袋鼠》中的殖民意识
廖春周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1922年,因西方传统价值观的瓦解而深感失落的劳伦斯,自我流放于澳洲。身为来自大英帝国的知识分子,劳伦斯借助《袋鼠》中的主人公萨默尔斯来表达自己对旅澳生活的失望情绪。萨默尔斯对“他者”的表征,也即对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社会环境、当地人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表征,流露出了植根于作者内心深处的殖民意识。关键词: 劳伦斯;《袋鼠》;他者;殖民意识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1]在文学批评中,他者被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广泛地运用于分析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中。本文运用后殖民视阈下的“他者”概念,对劳伦斯的《袋鼠》进行文本分析,以探讨劳伦斯的《袋鼠》与大英帝国殖民意识的共谋性。
一、在对自然景观与社会环境的描写中表现出的殖民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深了劳伦斯对西方文明的失望以及因西方传统价值观的瓦解而感到的失落。在《袋鼠》中,劳伦斯借主人公萨默尔斯表达了他的这种失望情绪。萨尔默斯深深地感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人类的内心变得更加压抑和扭曲。他对西方文明彻底绝望,渴求在澳大利亚寻找到一方未受污染的净土,这就是他自我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原因。
不过,在澳大利亚,萨默尔斯总是以一副唯我独尊的姿态彰显身为大英帝国国民的优越感,尽管他对原始的大自然心驰神往,但不知为何,面对眼前广袤而人烟稀少的土地,却感到十分惧怕:“森林死般寂静,鸟儿好像淹没于沉静之中。等待,等待……灌木林好似永久地等待着。没有人走近它,它在等什么呢?”[2]9他认为:“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国家前,要有人用血来浇灌它。这儿的土壤植物好似都在等待着。”[2]79祝远德教授在论述康拉德小说时指出:“作为帝国话语一部分,他的地理他者凸显出来的是荒蛮、原始和充满诱惑力的原始状态,为西方人对它的占领制造了理论依据。”[3]劳伦斯在《袋鼠》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殖民意识。
面对澳大利亚的社会环境,萨默尔斯彰显出了作为大英帝国国民的优越感。他总是不满于澳大利亚“狗窝样的小屋”,认为“一切都糟透了”[2]8,嫌弃肮脏污秽的乡下,抱怨废弃生锈的罐头盒的气味,甚至连门号上的名字如“艾略特” “特列斯帮” “天使之家” “贝特奥尔”等他都不满意,他希望能看到纯澳大利亚的门号。其实,这些英式的门牌,正说明澳大利亚带有英国的影子,具有英国味。当萨默尔斯郁郁寡欢地漫步于悉尼街头,想起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考文特公园、圣马丁巷时,他竟差点流下眼泪:“在环状码头,他思念起伦敦桥。这里不是伦敦,却完全伦敦化。唯一缺少的是伦敦所具有的古老而迷人的魅力。这个南半球的伦敦本身是瞬间建成的,但以假乱真。如同人造奶油替代黄油一样,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伦敦。”[2]16在萨默尔斯看来,澳大利亚只是对英国伦敦蹩脚的模仿,悉尼只是伦敦的仿制品,缺乏真正的内涵。由此可见,萨默尔斯难以摆脱欧洲殖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清楚地折射出埋藏于劳伦斯心灵深处的殖民意识及其优越感。
二、在对“男性气质”的刻画中表现出的殖民意识
殖民意识、欧洲中心论等观念,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英国的作家及创作,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殖民意识的痕迹,比如萨克雷的《名利场》、勃朗特的《简爱》、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等等。正如张中载教授所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作家也难以摆脱长期积淀下形成的集体意识,即白人优秀、欧洲中心的意识。”[4]劳伦斯笔下的萨默尔斯,总是用剥夺澳大利亚男性气质的方式来否定他们的人性,从而将澳大利亚人女性化、动物化以及植物化。
刚到澳洲,萨默尔斯就感到这里的人都“缺乏教养”,似乎都是野蛮人。这一点,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基尔南所说,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总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东方形象”—野蛮人,“人们奉希腊人为导师,借取灵感,相信自己的文明和野蛮正相对峙;却一点也不操心这里所谓的野蛮究竟是哥特式浪漫主义的野蛮、原始文明的野蛮、东方的野蛮,还是退化的野蛮”[5]。萨默尔斯认为自己是受过英式教育的正统的英国人,有别于其他芸芸众生,在他看来,澳大利亚的人都不具备“人格”。当看到一个澳洲青年在干沙里打滚时,萨默尔斯觉得“他像一头动物仰卧在阳光里”[2]23;当孩子们天真地玩耍时,他认为“如同无忧无虑的负鼠般玩命地折腾着”[2]23。1922年6月13日,劳伦斯旅澳期间,在给他大姨子埃尔斯的信中提及澳大利亚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总是这样庸俗地、毫无意义地生活下去。这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的空虚,毫无意思,这使我感到讨厌。他们都很健康,但在我看来他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6]因此,在劳伦斯笔下,澳大利亚这一民族成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劣等民族;而对澳大利亚动物化的描述,正是劳伦斯的写作手法,也是西方建构殖民地—“东方形象”—的常用手法。
在劳伦斯所生活的年代,男性气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家长式的男性气质代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在小说中,萨默尔斯多次消解邻居杰克的男性气质,使其缺乏统治权力,显得懦弱,从而弥漫着女性气质。萨默尔斯的语言更充满歧视:“考科特绷着嘴唇,瘦削、理光胡子的脸上呈现苍白色,他的嘴唇直到咧开没动一下。这是他们殖民地人的样子,他像原始人那样深邃的眼睛里有一种神秘感。”[2]29就个人层面而言,胡子是男性气质的代表性特征之一,而杰克干干净净的脸庞,在萨默尔斯看来,缺乏的正是男性气质;就国家层面而言,萨默尔斯嘲讽澳大利亚当局没有权威,一切都很随便,不负责任,这其实是将澳大利亚政府女性化,缺乏维护当局权威的能力。由此可见,萨默尔斯在将澳大利亚人物化、非人格化及女性化的过程中,充满了殖民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其意在说明: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政府毫无能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因而需要英国的帮助。
三、在对日常生活的叙说中表现出的殖民意识
作者的殖民意识,不仅体现在对澳大利亚自然景观和社会环境的描写及男性气质的消解上,而且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繁杂琐事的记述上。例如,当澳大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向萨默尔斯收取8先令车费时,妻子哈里埃特抱怨说:“星期六在伦敦只需要两先令。”[2]5萨默尔斯更嘲讽道:“他敲诈我,可你在这个自由国家,这里的人可以随意要价让你付,你不得不付给他们。这是自由!他们漫天要价,而你不情愿也得照付不误。”[2]5其意在说明澳大利亚人毫无原则可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漫步于悉尼港口的萨默尔斯,看着南半球夜空的美景,却深感孤独、恐慌与不安,他觉得这里的一切与当初的预想有着天壤之别。这表现出萨默尔斯的矛盾心理:当初他带着爱恨交织的心理离开英国,来到“崭新的”澳洲,而到了澳洲之后,他又感到很失望,认为澳洲毕竟只是英国的殖民地,无法与他的祖国相媲美。他回到家中时,妻子哈里埃特已将晚饭放到桌上,并说“肉是唯一真正便宜的东西,这块大肉只要两先令,要是能变的话,咱们肯定能变成野人和食肉兽”[2]11。显然,在哈里埃特看似幽默的话语里,也透露出她的殖民意识。待在这个殖民国家,哈里埃特生怕自己会变成被殖民者的同类—“野蛮人”。事实上,萨默尔斯也不无这样的“担忧”,以至于他不想和妻子哈里埃特以外的人说一句话,他们都害怕自己高贵的血统在同殖民地人的交往中被稀释掉。这已将萨默尔斯、哈里埃特夫妇的帝国情结、殖民意识及其自我优越感表露无遗。
综之,由于对西方传统文明的失望,萨默尔斯及夫人来到澳大利亚寻找希望,然而,由向往到失落,由希望到失望,再到最后离开,这一切无不说明,不论是劳伦斯对“他者”的表征还是消解,都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意识具有共谋性,映射出了作家潜意识里的殖民意识和帝国的优越感。
参考文献:
[1]张剑.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9-127.
[2]劳伦斯 D H.袋鼠[M].戴景海,谢毅斌,田树云,等,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
[3]祝远德.他者的呼唤: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9.
[4]张中载.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小说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89.
[5]维克托 基尔南.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M].陈正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
[6]戴维 赫伯特斯.劳伦斯书信选[M].刘宪之,乔长森,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463.
(责任编辑:毕士奎)
“Otherness” in Somer’ Eyes:
Colonial Ideology in D. H. Lawrence’s Kangaroo
LIAO Chun-zh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In 1922, Lawrence was depressed with everything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values, which is the cause of his self-exile in Australia. As an intellectual from Britain, Lawrence conveyed his own disappointment with Australia by the virtue of the protagonist Somers. What he represented in his novel is distorted and prejudiced. The representations of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al sceneries, social settings, residents and daily life in Australia reveal Lawrence’ s deeply-rooted colonial ideology.
Key words:D.H.Lawrence’s;kangaroo;otherness;colonial ideology
作者简介:廖春周(1990—),女,江西新余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15-09-06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5-0098-03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1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