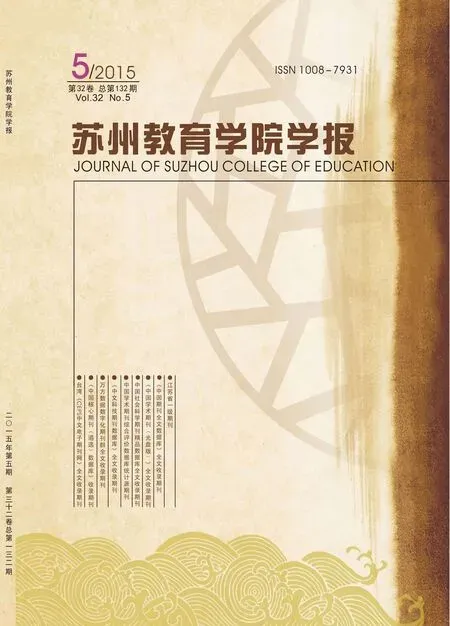来自民间的解构力量
—狂欢诗学视角下的《娜娜》
李依宸(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来自民间的解构力量
—狂欢诗学视角下的《娜娜》
李依宸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主要包括狂欢式世界感受的两个方面,即平等自由的精神以及更新和更替的精神。左拉的小说《娜娜》展现了一个狂欢的时空,从狂欢诗学的视角观照《娜娜》,可以充分领略左拉以民间世界对抗和解构官方世界的意图,从而显示出《娜娜》所蕴含的强大的民间解构力量。
关键词:《娜娜》;狂欢诗学;民间;官方;解构
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是巴赫金狂欢诗学的核心,它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即平等自由的精神以及更新和更替的精神。这两个方面都强调民间世界对官方世界的抗争与解构。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以主人公娜娜为线索勾勒了以剧院、马场、宴请聚会为主体的狂欢时空。来自底层民间的“娜娜”们,以狂欢式的生活吸引和聚合法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但最终让高高在上的官方世界走向分崩离析,这充分显示了民间世界巨大的解构力量。本文将运用巴赫金“狂欢式世界感受”的诗学理论,来剖析《娜娜》所展现出的民间世界对官方世界的解构力量。
一、自由和平等
等级秩序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一方面促进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异化了人类文明。“在现实生活中,等级制、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姿态和语言,不同等级的和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1]141从司汤达到巴尔扎克,法国文学家对等级秩序一直怀有强烈的冲破藩篱的冲动。左拉也是如此,只不过在小说《娜娜》中他采取了与前辈不一样的反击方式。
在小说《娜娜》中,左拉描述了一个以剧院、马场、宴请聚会为主体的狂欢时空。在小说展现的人物世界里,王子贵族也好,社会精英也罢,抑或剧院小丑,当他们彼此穿梭在娜娜之流的宴请聚会、剧院餐厅中时,每个人都沉湎于狂欢的世界里,整个小说呈现出一种狂欢节的氛围。在左拉的“狂欢节”上,狂欢式的生活消融了民间与官方的界限,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社会的人,都共同演绎着生活的狂欢。“狂欢节”所特有的平等意识让置身其中的人物褪去严肃的社会身份,王公贵族可以庸俗不堪,平庸之辈也可以光鲜亮丽。身处底层社会的萨丹,对上流社会的厌倦直言不讳;“娜娜”们鄙视贵族妇女的虚伪矜持;博尔德纳夫更对王子作出了“他归根结底还是有点像个没有教养的人”[2]171的评价。反过来,王子、伯爵、侯爵以及众多社会精英们对娜娜却迷恋追求,将娜娜捧到神坛的高度,法国社会甚至一度以娜娜的行为举止作为时尚的风向标。
与平等相伴随的是自由。人们为摆脱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而自由狂欢,而且它不仅仅表现为人人自由狂欢,更重要的是,狂欢式的生活能够让人正视真实的自我,享受人性的自由。“人回归到了自己,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3]12在娜娜们的生活圈子里,她们不会因为自己身份的低微而自卑,敢于蔑视官方意识的权威,承认自己,并自由自在地操控自己的人生,展现自己的人性。然而,对于王公贵族等上流人士来说,繁琐的清规戒律时刻束缚着他们的心,正如密尔所描述的那样:“信条之存在竟像是存在于人心之外,其作用只在把人心硬化和僵化起来以挡住投给人性更高部分的一切其他影响。”[4]米法,自幼饱受宗教道德的压抑,神圣不可侵犯的背后隐藏的却是痛苦不堪的灵魂;公爵夫人萨比娜,长期处于婆婆严肃恐怖的铁腕统治下,刻板的生活禁锢着她自由的生命活力。而在狂欢的世界里,这些作为社会道德化身的上流人士,他们的生命激情从官方正统的禁锢中挣脱了出来,受压抑的人性得到了自由挥发。他们逃匿于“娜娜”们的民间生活之中,褪去了规范严肃的外壳,撕掉虚伪的面具,直面贪婪的肉欲,暴露出他们真实的人性。因此在这狂欢式的生活状态下,两类人的自然人性都重获自由,尽情地释放着郁积的人情人性。
与“娜娜”们这些“低等级”人物获得自由的方式不同,萨比娜这些“高等级”人物的自由,则来自于“娜娜”们这些“低等级”人的拯救。米法等人代表的官方世界在娜娜们的民间世界的冲击下被淹没、解构。左拉说,娜娜“她把只许在老百姓中间发酵的腐烂物,带到了上层,使贵族社会随着她一起腐烂。她变成了自然界的一种力量,一种有破坏性的酵素,她自己虽然不自觉,但是她使巴黎在她两条雪白的大腿中间堕落,解体,她使巴黎翻腾”[2]226。可以说,娜娜这样民间的、原始的、自然的、野性的生命力,以其藏污纳垢的包容性,吞噬了上层冠冕堂皇的真理、价值规范,并最终解放了上层社会。
在这个狂欢的世界里,官方与民间之间的鸿沟、下层与上层之间的隔阂,由于不平等地位造成的畏惧、敬畏之情,都在狂欢的气氛下消解了。大家平等交往、尽情狂欢,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身份地位的禁锢烟消云散。巴赫金说:“狂欢式的生活则把人们从完全左右着他们的种种等级地位(阶级、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平等和自由。”[1]141于是造就了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等级关系恰恰相反”[5]161-162。
二、更替和更新
加冕和脱冕是狂欢节中最重要的仪式。巴赫金认为:“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和新生的精神。”[5]163《娜娜》在整个叙述中其实也演绎着这样的加冕与脱冕戏谑的仪式。
小说一开始首先设置了“娜娜是谁”的“谜”。妓女出身的娜娜在人们的纷纷猜测中,其身份在出场前即神秘化,并一步步炙热化。剧院老板博尔德纳夫巧妙地诱发人们的好奇心,让娜娜直到《爱神》的第三幕才出场,一出场就风头出尽。而在整个戏剧演出中,娜娜在观众的眼中不断地被加冕和脱冕。爱神娜娜一出场,乔治便发出“太美了”的稚嫩的夸赞(加冕),年轻绅士们则醉倒于“妙啊”的感叹中(加冕);也有的观众因为娜娜蹩脚的唱功和表演而不断地发出嘘声和口哨声(脱冕)。但是无论如何,娜娜都“巧妙地搔着了观众的痒处,能使观众不时产生一阵轻微的战栗”[2]18。随后的表演“掌声变得更热烈了”[2]18(加冕)。幕间休息时大家又开始议论娜娜,斯泰内对福什里说:“我准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我相信是在俱乐部里,她当时喝得大醉,让人家搀扶着……也许是在老虔婆特里贡家里吧。”[2]19米尼翁则说:“随便拿一个妓女来叫观众鼓掌欢迎,这真叫人恶心。”[2]20小说继而写道:“从第二幕起,无论她做出什么样的举动,都是容许的了:她可以在台上举止粗野,她可以连一个音符都唱不准,她可以忘记台词,这都不要紧,只要她转过身来嫣然一笑,便可以博得满堂彩声。她只要把她最拿手的扭腰动作表演一下,池座里立刻热情振奋,这股热情从一层一层楼座升上去,一直升到屋顶为止。”[2]24这一客观描述,既向我们展示了观众眼中加冕了的娜娜,又向我们指出,其实那原本就是个脱冕了的无才的宠儿。落幕之后,左拉还不忘通过德•旺德夫尔伯爵的口再次将娜娜脱冕:“这个娜娜,肯定就是我们有一天晚上在普罗旺斯街角遇见的那个……”[2]25-26当戏剧演到高潮即娜娜作为爱神裸体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娜娜被加冕的程度也达到高潮,裸体的娜娜在爱神的光环下将自己神圣化,而且是在观众的欲念下被神圣化,她从而控制了全场:“每个人都被娜娜迷住了”[2]32,“她的具有无限威力的裸体显得特别高大”[2]33。在最后谢幕时,“叫喊‘娜娜!娜娜!’的声音,疯狂般地到处轰鸣”[2]33。娜娜加冕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娜娜在这一被加冕和脱冕的过程中,由一文不名的妓女一跃成为红极一时的宠儿,这其中的滑稽不能不让人们质疑和唾弃上层精英们的审美及价值标准,他们道貌岸然及其所代表的官方世界的所谓正直、严肃和权威开始消解,而由此构建起来的统治体系亦在这种荒唐的价值追求中充分显示其虚伪和腐朽性。
值得一提的是,将娜娜加冕到最高头衔的是马场比赛中被命名为“娜娜”的小马获得冠军,并给娜娜带来了意外的胜利:“这个辉煌的胜利使她成了巴黎的王后。”[2]401整个马场上回荡着“娜娜!娜娜!娜娜!”的轰鸣,人们激情地高呼:“娜娜万岁!法兰西万岁!打倒英吉利!”[2]400娜娜被抬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狂热的激情甚至蔓延到激动的皇家看台上。小说还写道:“娜娜的宫廷越扩越大,她的胜利使迟迟不肯来的人也来了;人群的移动使娜娜的马车成了草坪的中心,最后竟使娜娜成为这中心里受人膜拜的天神,这是爱神王后受她的子民狂热拥戴的结果。”[2]402或因赛马的胜利,或因赢钱的愉悦,抑或是对娜娜这个女人产生欲念,这些都叠加在一起,人们已难以抑制狂欢的心情。因此无论是下层的还是上层的,统统臣服于她的裙围之下。
一个下层妓女,如同狂欢节上的小丑一样,却竟被冠以国王的荣誉,所以加冕的背后难以逃脱脱冕的危险。于是,左拉又让我们看到了娜娜的不忠和滥情:“各国首都都知道她的名字,所有外国人到了巴黎都指名要她;她用疯狂的放荡去招徕这人群里的显赫人物,仿佛这种放荡就是一个民族的光荣和最高的享受。”[2]460她身边的男人一个个沦陷,被吞噬在娜娜的深渊里。
纵使左拉不断地给娜娜脱冕,但他仍然不失公正地肯定了狂欢的娜娜所发出的反抗:“她为她出身的阶级报了仇,为乞丐和被遗弃的人们报了仇。”[2]485因为作者明白,娜娜置身的社会环境逼着她逃遁于狂欢的时空,并在无意识中开始她的解构。娜娜的一生从卑微贫贱的妓女到“巴黎的王后”,再由纵欲无度到最后寂寞死去。她既体现了上层、下层的双重身份,又体现了喜剧、悲剧的交替变换,从而引发人们深入的思考。“狂欢节(再强调一次,在这个字眼的最广泛意义上)将意识从官方世界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得有可能按照新的方式去看世界;没有恐惧,没有虔诚,彻底批判地,同时也没有虚无主义,而积极的,因为它揭示了……新事物的不可战胜及其永远的胜利,人民的不朽。”[3]318在此,上层已不再是单纯的高尚,下层也不再是单纯的粗鄙,他们的界限因娜娜的加冕和脱冕而变得模糊不清,官方和民间孰重孰轻、孰优孰劣亦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加冕和脱冕的表演者是娜娜,然而演绎的内容不仅仅是娜娜戏剧化的人生,而且还有官方世界的解构历程。
总之,以娜娜为中心的狂欢娱乐,虽具有生活糜烂、道德堕落的表象特征,但左拉在叙述这场盛大的狂欢的时候,其主旨在于解构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张扬以娜娜为代表的民间的强大的解构力量,从而突出了民间的自由和平等精神。
参考文献:
[1]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左拉.娜娜[M].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7.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毕士奎)
The Deconstruction Power from the Folk: Na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nival Poetic
LI Yi-chen
(College of Chines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Bakhtin’s Carnival Poetic theory mainly involves two aspects of the carnival world feeling, namely the spirit of equality and liberty, and the spirit of renovation and replacement. Zola’s novel Nana portrays the carnival time and space. A study of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nival Poetic can fully demonstrate Zola’s purpose to confront and deconstruct the official world with the folk world, so as to reveal the strong deconstruction power from the folk that is contained in Nana.
Key words:Nana;Carnival Poetic;the folk;the official;d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李依宸(1991—),女,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收稿日期:2015-09-12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5-01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