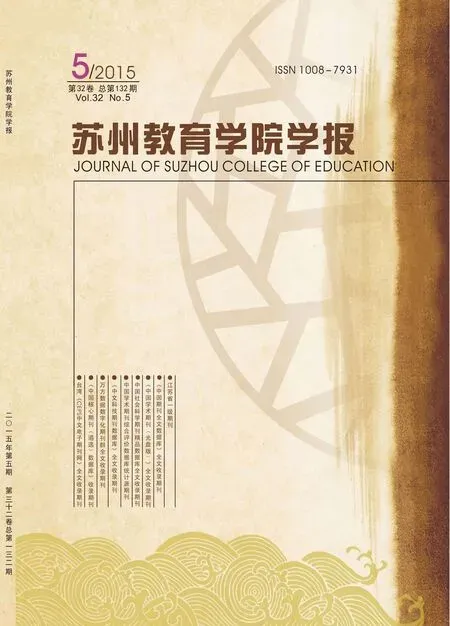超越马来西亚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创作
—以《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爱情书写”主题为中心
徐 榛,郑有轸(.韩国水原大学 国际教育系,韩国 水原 445743;.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韩国 首尔 3079)
超越马来西亚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创作
—以《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爱情书写”主题为中心
徐 榛1,郑有轸2
(1.韩国水原大学 国际教育系,韩国 水原 445743;2.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韩国 首尔 130791)
摘 要:马华文学作家朵拉,广受大众欢迎又长期受到文坛的重视,她所书写的关于“爱情”主题的微型小说,围绕着“男女两性”问题展开故事情节。她站在女性的立场直接指向女性问题,以都市男女间畸形的爱情来担起男女性别平等的老话题。在混乱的情感和极端的书写背后,朵拉自觉地承担起为女性寻找出口的担子。朵拉关注的不是男女游戏本身,亦不纠结于情感报复的闹剧,而是以极端化的出轨行为来追问如何寻得以正常的方式填充“第一性别”和“第二性别”之间似有若无的鸿沟。在朵拉的笔下,女性的身份地位表现出什么样的形式,她又怎样诠释和寻找女性改变的出口,值得关注。
关键词:华文文学;朵拉;《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爱情书写”;男女关系;女性地位
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阵容通常被学界分为五大版图,即台港澳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欧华文学以及澳华文学。[1]在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而且做专门研究的学者也不是很多,在韩国,这样的情况更为明显。当然,在韩国,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研究还是有的,但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目光还是更多地投向美国、欧洲地区的严歌苓、高行健等作家,而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相对较少①,因此,对东南亚华文作家及作品进行介绍和关注是很有必要的。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经旧文学②时期至20世纪初五四运动以后进入新文学时期,二战结束之前,主要是以启蒙与救国为主题,自1945年以后摆脱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趋于独立。如马来西亚1947年提出“马来西亚华文文艺的独特性”,于1956年提出“爱国主义文化”概念等,形成了基于双传统的独立文学传统。到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了“脚踏乡土看世界”的口号。[2]
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画家朵拉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祖籍福建惠安,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州副主席、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曾为马来西亚多家报纸杂志及美国纽约《世界日报》、台湾《人间福报》撰写副刊专栏。曾任马来西亚棕榈出版社社长,《蕉风》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清流》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等。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人物传记等29本。其作品被译成日文、马来文等出版[3]。朵拉以各种活动与作品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作品中微型小说的比重较大。微型小说的形式特征加上作者的个性,使朵拉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主要讲述了社会的腐败、上流社会(城市人)或下层阶级的生活等,书中男女爱情主题的内容占较大比重。[4]这些讲述爱情主题的作品,关注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比较现实的爱情,大部分显得晦暗、压抑,让人感觉沉重。笔者考察了其爱情主题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男女关系,通过细读文本,整理分类分析,考察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都市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类型,发现作者在继承传统爱情主题小说表现的两性关系类型的同时,又在创作时塑造和描绘了别样的两性相处方式。并且,笔者还分析了女性作家在两性关系中是如何塑造女性形象的,据此考察作家笔下两性关系的类型。通过这样的整理分析,考察作家以“爱情”为视角,对女性的认识和为女性的“抬头”提出怎样的话语。
一、马华文学创作的政治与文化语境
华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大量涌入马来半岛。大量华人在此时涌入马来西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殖民地统治集团需要大量的劳工开发这片土地,二是中国政治局势比较动乱,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马来西亚独立后,“外来者”的身份使华人在政治上无法与原住民争夺主导权,再加上华人比较热衷于经济发展,在政治场域缺乏谋略与远见,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华人的地位弱势越来越明显。反之,马来民族从建国初期就坚决地在这一多种族的国家中确立马来人主导的政治模式,他们的愿望在1969年种族流血事件后可以说完全实现了。安德森悲观地认为,这些国家所形成的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官方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保护的政策,是和维护帝国—王朝的利益紧密相连的。”[5]他们有效地控制了国家机器与话语,并在各领域中获取主导权,与非马来人形成了主流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局面。
“外来者”不能掌握政治的主导权,只有马来人才是合法的支配者。[5]马来人甚至认为,非马来人能够被接纳为公民,是他们作出了牺牲,也是马来人所给予的恩惠,因此非马来人应该接受马来人的主导地位以及马来人的特权。再者,他们宣称马来人在殖民时代是被剥夺及被侵害的族群,遭受殖民统治及华人经济的双重压迫,导致马来人成为贫穷与落后的族群。[7]原住民在政治上的特权和主权也就成为马来人民族主义文化霸权的出发点,从而也就很容易地形成或者说建构出一个以马来“知识—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语境。在这样的政治精英的文化霸权之下,自然会出现一种抵抗机制,马华文学就属于这种反对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文化抵抗机制下的产物。郑良树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形态具有三层结构:第一层是华人社团;第二层是华文教育、华文报;第三层是马来西亚有別于其他国家(大陆、台、港、澳以外)华社的重要活动—政治参与、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及文化演绎。他认为,第三层之能够开展是因为“中程阶段的完成”,特別是对华人教育底线的坚持。[8]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成为构建国家政治符号非常重要的参与机制,也构成文化语境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它可以成为国家政治和文化语境的高压手段;当然,它也可以成为个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文学成为了一个双重概念,集控制/反控制、深化/超越二元矛盾于一身,并且使矛盾双方互相转化。
如上所述,原住民构建的马来文学和国家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构建的文化语境自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于是,华人作家通过马华文学来表达对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政治文化语境的不满和反抗,马华文学就成为反映和反抗这种政治文化语境的话语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马华文学,可以发现如下一些内容:(1)华人在这个国家所受到的歧视与不满,如潘雨桐的短篇小说《一水天涯》;(2)对马来民族精英与官方集团的消极意识与防备心理,如黄锦树的短篇小说《天国的后门》;(3)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召唤[9],即对中国文化的怀念;(4)离散与再移民心理,如潘雨桐的中篇小说《烟锁重楼》等。这些都是对马来控制的政治和文化语境的反抗。
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之下,马华文学作家们多集中书写上述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朵拉在她的微型小说创作中,开辟了新的书写主题—爱情叙事,这里所谓的“新”并非指爱情主题是全新的主题,而是指相对于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新的创作。笔者认为,她在爱情主题的书写中,并没有很明显地通过男女爱情关系来讽刺,或者是反抗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痕迹,而是比较纯粹地、严肃地探讨男女之间的爱情。朵拉谈到自己爱情主题小说的创作时也表示,她也在寻找诠释男女爱情的定义或者方法、男女爱情相遇的时间点等问题,与政治无关。这就显得比较特别了—她能够跳出意识形态和固有文化语境下的宏大书写,从反抗政治书写,或者说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叙述,转向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这样的问题与政治无关,与文化语境无关。笔者认为,这样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具有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的无视和不关心,也可能是隐在的对抗,很有必要提出来,并加以分析。
二、传统和现代都市爱情主题小说的探索
要考察朵拉微型小说中有关爱情主题的小说,首先要考察中国传统小说和现代都市小说中的爱情主题书写。爱情是通过男女关系表现出来的,那么,朵拉所书写的男女在爱情中的关系与传统和现代小说中的书写相比,有怎样的变化,需要比较说明。
有关爱情主题的作品,《诗经》中就有,但鉴于是对小说的考察,于是将考察的范围和对象设定为具有代表性的、表现男女爱情主题的作家和流派。代表性作品表现为以下两大方面:在唐传奇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到比较传统的男女爱情关系;在鲁迅的小说和都市文学代表—新感觉派作品—中可以发现处于城市生活中的或比较现代的男女爱情关系。
唐传奇作品描述的爱情中,男女关系一般都是文人阶层的男子在无经济能力的贫困时期与女子建立爱情关系之后抛弃女子。男主人公指望科举高中而苦读,对于爱情一贯持消极态度。可以揣测出作家藏有批判当时男人对女性和爱情不负责的恋爱意图。女主人公比起男主人公身份更为多样,如妓女、已婚女、妖精(精灵)、大家闺秀等。这些女主人公的特殊身份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女主人公是引导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角色。诚然,当时也有女性不甘处于被压迫的情境下,对男性进行反抗—包括“千里寻夫型” “香消玉殒型” “死后复仇型”,等等,但一般看来,大部分女主人公还是处于对男主人公奉献或者等待的被动地位(次位)。其代表作有《任氏传》《莺莺传》,描述了女主人公以消极、顺从的形象来面对爱情,显示出女性次位的爱情关系。[10]
特别热衷于书写男女爱情主题的鸳鸯蝴蝶派是发端于20世纪初叶上海“十里洋场”的,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一个文学流派,最初热衷于言情小说,多讲述像鸳鸯和蝴蝶一样相爱且不分离的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呈现了“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11]的爱情关系。在大部分作品中出现的典型类型有男子背叛爱人的“抛妻弃子型”,有描述优秀的男主人公与美丽女子浪漫爱情的“才子佳人型”。作品的男女关系中具有主导权的也是男性,而男女性别关系主要表现为女性次位的形态。自20世纪60年代,以言情小说而活跃于文坛的台湾作家琼瑶承袭了鸳鸯蝴蝶派的特点。她撰写的被拍摄成影视作品的《还珠格格》中,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男女爱情以圆满结局落幕,可谓才子佳人型爱情,但要注意的是,其中女性是从平民走向贵族,即使在成为贵族之后,对自己的爱情和情郎也一直是处于等待和妥协的状态之下的,可以发现,这里的男女性别身份中,一直是男性高于女性的。
而现代文学都市小说中显示出的男女关系的内容与前者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坛,鲁迅热衷于关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存在。其实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到他对女性解放的认识和情绪,早在《我之节烈观》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只是对女性的爱情观少有表述。但细读鲁迅的作品,笔者发现,至少在两篇作品中均隐晦地谈及对女性情感的解放之认识或提出了方法。鲁迅的《伤逝》似乎非常隐晦而间接地表现了一点儿不同于传统的“男上女下”的恋爱意识,这样的恋爱模式超出当时社会认同或流行的范围,从而可以看出鲁迅也许在无意识间揭示出了男女关系新的形式。然而鲁迅揭示的这种男女关系,对传统男女关系中女性不得不为第二性别的社会原理无法认同,并且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还是显而易见的。两位主人公以近乎平等的男女关系开始恋爱而展开爱情,但结局还是因社会、家庭、经济的压力,男人选择抛弃(女人),女人仍然处于第二地位,即以男女平等的关系开始,但最后仍以女人次位的形式收尾。可在鲁迅的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又似乎可以看到揭示的女性自救的方法,处于次位的女性主人公通过“出走”获得自由(这种出走要求女性独立,也许是经济上,抑或是情感上)—似乎可以说是女性要获得解放,自身需具备独立性的较为隐晦的主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以海派文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都市男女关系的形象,其中特别塑造了女性的不同肖像。一般描述的男性人物的形象是“绅士”形象,女性人物的形象是“妖姬”。看上去像是上流社会的爱情关系,其实基本相似于传统的男女关系。男女关系的流动是按照“渴望—冒险—幻灭”的阶段展开的,还显示出对于性的开放意识,男女关系的纽带是由“性”来沟通的。尤其是海派女作家张爱玲描绘出的许多女性的肖像。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可以看出张爱玲也有过类似的爱情。在她的作品里,即便男女结为夫妻,大部分最终都因男人外遇或三角关系等导致分离。在相遇与离别的过程中,女性被描述得较为卑微。除男人离开外,也有女人离开的描述,女人的离开使读者感到是女人的反抗,但女人离去后男性并没有悲伤落魄之感,仍可以看出女人本质上卑微的地位。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小说和现代都市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大多男女关系还是处在“男上女下”的基本形态之中。即使鲁迅先生在其小说中隐晦地提出了女性如何处理情感问题的对策,但最终还是夭折于当时强大的社会背景中。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女性反抗的希望以“出走”的形式完成,只是这一希望是否能够达成还要再作讨论。那么,由此再来考察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朵拉微型小说中男女爱情的部分,可以发现作家对两性关系诠释和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继承表现传统小说和现代都市小说中两性关系传统书写的同时,她大胆地揭示和建立了更为复杂的男女情感,并且还尝试对女性的爱情关系和社会地位进行思考和改变。
三、朵拉微型小说中男女纠葛形态
由朵拉在微型小说中用很大篇幅来描述男女爱情关系,可以看出她对性别关系投入了很多思考。持续创作出爱情作品,可以看出作家在男女关系上对女性是很有期待的。作者在《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中说:“整个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是女人,不过,这50%的人口却被忽略,没有发言权,而且受到压抑、欺侮和冷落。两性关系从此成为我最爱探讨的课题。”[4]247朵拉并不是站在男性的立场,而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讨论男女关系。她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家庭,因为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所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想要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应从处理家庭关系开始,而且在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因此朵拉认为女性本身的问题首先要处理。于是在作品中朵拉对女性人物投入了特别的情绪与观照,虽然没有明确揭示出解决的方法,但可以看出作家在试图寻找解决的策略。因此,笔者将对朵拉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里描述的两性关系进行分类,并且以女性为中心,对作品中女性在男性话语中的表现和结果进行分析说明。首先,《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中有关男女爱情主题的两性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表现类型:
1.“男女平等”。共5篇:《礼物》《黑夜的风景》《岁月的眼睛》《电话响起》《绿叶子》。从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朵拉对男女两性平等关系的表现方式是很有趣的。女性在面对男性世界的时候,持一种莫名的冲动和不安全感,在面对和处理这种情感的时候,女性尽量以不再深入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即使这样的保护可能是一次误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性和男性一样,是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放开对方的;女性和男性达成了一种情感生活上的平衡。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女性选择离开男性,并且这种离开不是悲痛中的自我放逐,而是在有所感悟的认识中重新走向属于自己的生活之路,这是女性应有的觉悟,虽然这样的觉悟是在摆脱男性话语的过程中实现的;或者,女性通过自己的婚姻告别暗恋的男性,使有妇之夫的男性处于某种莫名的感伤之中,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平衡;亦或是通过自己和下一代的婚姻,面对同一个敏感的婚姻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男女两性在婚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家庭问题,其实男女两性的痛苦来自同一个原点。笔者认为这种男女“平等”,实际上是女性对自己的一种自我保护,是性别意义上的互相对立,并非是男女两性在社会意义上达到的平等。
2.“女性上位”。共7篇:《有一颗心》《会说话的墙》《心结》《咖啡约会》《自由的红鞋》《心焦如焚》《幻想电话》。女性几乎完全觉悟,了解男性和自身在社会生活中隐藏于背后的角色关系,并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动权而高度警惕和提醒自己;女性尊重和坚持自己独立的态度和私生活,认为完全不必为了顺从男性而作出让步,一切生活首先要建立在自己满意的基础之上;女性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爱意,并尊重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自我尊重的认识观;男性成为夫妻生活中“丈夫”这个角色的填充物,顺从女性的私生活,并成为为女性解决疑难问题的角色,男性成为顺从和等候的代言人。即使面临分手离别,女性也以豁达的态度接受分手这样的事实,不再以传统的悲情角色出现,变得更加率性。
3.“女性下位”。共13篇:《玛琪雅朵和法师》《重逢》《行李》《心碎》《病人》《有一首歌》《鸦片电话》《心事的花瓶》《病情》《虚拟之爱》《绝望的香水》《过时的信》《回家的猫》。“等待”成为女性在男权话语中的代名词。女性成为男性随意抛弃的物品,在被抛弃之后仍傻傻地等待男性回归,而等到的却是更多的沦陷;女性失去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在虚无的生活中苦苦等待男性的联系,在男性的世界中失去自我;女性在男性话语中处于弱势的地位,似乎没有办法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在配合男性的过程中消磨自己的生命。男性在女性以死亡结束与男权的对话中觉悟和懊悔,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女性在男权话语下不被重视的悲哀。
4.“女性上位”→“女性下位”。共1 篇:《纠葛》。女性受到一位男性的追求,但却沉浸于对另一个男性的回忆和幻想之中,女性在男性认识中处于期待和被忽视的双重矛盾中。
5.“女性下位”→“女性上位”。共1篇:《不解》。女性在两位男性之间表现出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在男权话语面前,坚持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又在男权面前处于失语和失去自我的状态。这样矛盾的冲突使女性沉溺于某种痛苦之中。
以女性在男权话语中的男女关系,从五个角度对朵拉相关微型小说进行分类分析,与传统小说及现代都市小说作品中的男女关系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个问题:(1)朵拉笔下书写的两性关系,或者说试图表现的两性关系是比较丰富和复杂的。从上文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她笔下的男女两性超脱了传统书写中女性绝对尊崇男权话语的书写模式,跳出了宏大的女性悲楚面貌的创作。(2)女性对男性话语的回应出现了新的呼声。正如前文所说,女性也在寻找自己在男性话语和男权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就是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或者是女性占据强势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强势又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脱离对男性的认识,只是从女性本身来思考和处理;另一种是以男性为参照对象,女性凌驾在男性之上。这样的回应也正表现了女性如何考察和思索男女两性问题。(3)女性下位,即处于男权话语霸权下,这种状况仍真实地存在,并且还是男女两性问题中的主流。女性无法从情感上走出对男性的依赖和期盼,而这种依赖和期盼也是女性无法跳出男性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男性可以更加轻易地掌握和调整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女性则毫无反抗力地在男性话语霸权下苟延残喘。(4)女性穿梭于男性之间,在男性话语下,表现出不同的性别言语面貌。女性在面对男性性别角色时,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即自我独立与依存于男权的二元矛盾中。这种以男性的对比表现出的女性自我认识,好像是一种混乱的,或者说是明知是矛盾的但回避不了的性别关系。从而我们可以发现,在面对男权话语时,女性的自我意识还是混沌的、不清晰的。
西方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对男女关系中女性正当化的方式提出三点看法:“1.男主外女主内的认识观;2.女性地位宿命论;3.神秘主义,即脱离人间爱情,投向宗教崇拜。”[12]此外在提到对独立女性的印象时,提出非经济层面的、从事艺术层面工作的女性在想象或是思想上保持自我独立性的情况。笔者认为,不管怎么说,波伏娃提出的“第二性”的观点,是将女性和男性分离开来讨论,并且即使提出女性的独立意识,也是从主观意识层面出发来进行讨论的。可以判断的是,这里呈现出来的女性,从本质上讲,仍然处于第二位的境地。社会关系中女性还是处于弱势地位,不管怎样,男女关系还是呈现在一种单一化的表现框架中。而朵拉打破了这一局面,她在微型小说中刻画了多种多样的两性关系,跳脱出了传统的男女关系的表现形式,尤其设置了女性的新的社会地位,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微妙变化。当然,这样的故事设置可能是很难令读者接受的,但这样的两性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确实是真实可见的。因此,这何尝不是作家对女性改变自身地位的一种焦虑或督促呢?
通过以上对朵拉“爱情”主题微型小说以“两性关系”的角度进行分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朵拉塑造的男女主人公在爱情的角逐中,充满着性别相异的二元对立,这种两性之间的对立成为亘古的话题,传达出了两性之间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朵拉的笔下,两性关系的和谐和冲突又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因为,作家不是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胜/负、压迫/被压迫、背叛/被背叛的二元对立关系之间作出绝对的选择,而是在“男性/女性”的背后,对隐藏的爱情生活的真相进行探索与反思。
身为女性作家,朵拉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观照和讨论女性问题自然不难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朵拉在描绘和塑造都市社会众生相的时候,她的性别身份并没有左右她对性别冲突问题的认识和反思,反而让她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挖掘潜藏的两性的弱点。正如朵拉本人所说:“女性抬头不表示超越男性,要求的是平起平坐,在这之前,先拥有自信自强自立,才有其他可说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人觉得重要,有人不。至今有此现象,是一种悲哀。而男性到今天,依然具有传统式的男性主宰女性的愿望,又是另一种悲哀。我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其实是对男权社会和女性自甘矮化的一种安静的反抗。”[11]247从朵拉的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作家想要表达的几层意思:(1)作家本身对男性性别霸权持有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无论是传统文学中关于男女性别的讨论,还是当代作家对男女性别对立的再书写,几乎都是对男性性别霸权的社会现象和体制进行批判和声讨,这一点在朵拉的微型小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2)对女性自身营造的性别弱势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朵拉在小说中对女性自身性别弱势放大化的现象表现出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正如她所说,女性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首先要改变自身的现状,在渴望和要求性别平等的呐喊中,又夹杂着“要求被保护,被呵护,被维护”的“女性是弱者”的精神面貌,这是朵拉感到困惑和滑稽的部分。笔者认为,身为女性,朵拉从女性的角度回归女性本身,提醒女性不要一味要求,而应该先反观自身,这样的抒写角度是比较特别的,可能也是朵拉作品与众不同的地方。
如果单从朵拉的这段表述来看,读者可能会有一种错觉:作家似乎只是对男性性别霸权进行批判和对女性自甘矮化表示悲哀和反感,好像只是停留在提出问题的阶段,还没有提出女性面对或者解决的办法。其实,仔细分析朵拉小说中的“两性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已经在尝试寻找平衡的“出口”。《东南亚华文文学史》对朵拉的小说评价道:“朵拉无论描写家庭生活的夫妻之情,恋人之爱,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品德的认可,如表里一致,坦诚,谦敬,不慕虚荣,不逐浮华等。”[13]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在具备了这样的优秀品德之后,可能会维系一种较为良好、稳定的男女关系,但是,笔者认为,朵拉选择的处理方式是极端的,是“极与极”的碰撞。如前文所考察的,朵拉寻找的“出口”都是脱离男性,由女性来完成的,可以发现的处理方式有:(1)女性性别男性化。即让女性选择学习男性的行为动作,以示以牙还牙,其结果则是让男性处于瞬间“第二性”的境地。(2)性别“平等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平等”不是要求男性给予性别上的平等认同,而是女性自身性别认识的转变要求,即认识上的“第二性”转变为“第一性”,或者说是和男性性别的社会认识合流。(3)女性社会生活多样化。即女性寻找到自己关注的方向,和男性在社会生活中保持必要的距离和独立性,先达到社会生活身份和意识上的独立,再走向经济和性别识别上的平等。(4)男女性别身份认同化。即男性和女性两性之间是在良好的、互相关心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生活活动。这和性别“平等化”的差异就在于,这是男女两性共同建构才可达到的目标,这对男性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诚然,此中作家朵拉探讨的方式也有从反面视角出发的,比如以女性性别男性化处理的方式来说,就是一例。笔者认为,作家其实并不是提倡用这种方式,而在于引起读者的关注,关注的不是男女游戏本身,亦不是纠结于情感报复的闹剧,而是以极端化的出轨行为来追问如何寻得正常的方式填充“第一性”和“第二性”之间似有若无的鸿沟。
四、结论
世界华文文学一直存在,可是一直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重视起来,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在韩国学界。现在,随着对华文文学的关注越来越多,华文文学也展露出它多姿多彩的一面,无论从主题、形式、叙述视角、故事编辑等方面,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欧美地区几位著名作家最为引人注目,如严歌苓(美国)、虹影(英国)、高行健(法国)等。朵拉不仅不同于欧美几位著名的女性华文作家,也与当地其他马华作家有所不同,她没有将她创作的主题进行宏大化处理,既没有回顾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包括抗战时期、文革时期等)宏大背景下发生的事件,也没有在马来西亚政治和文化语境下刻意为“外来者”发声,更没在自己的身世上大做文章,而是简简单单地将创作的命题确定于一个方向,即本文中提到的以爱情主题为视角的叙事,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朵拉所书写的关于“爱情”的主题,围绕着“男女两性”问题展开故事情节的微型小说,之所以备受大众欢迎,而又长期受到文坛的重视,是因为朵拉格外善于编故事,对同一主题的书写,她都能翻出新花样。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过朵拉的爱情主题小说:“朵拉抓住一个‘坚持爱情’的元素反复渲染,并在多处使这一元素爆出‘事与愿违’的遗憾。”[14]诚然,朵拉爱情主题小说的故事结局常常给读者一种“事与愿违”的无奈,但是,这样的评价还是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男女爱情故事发展的情节上,所以,与其说“坚持爱情”,笔者觉得讨论和思辨“爱情是什么”更为合适,在这样的问题意识背后,朵拉站在女性的立场直接指向女性问题,以都市男女间畸形的爱情来担起男女性别平等的老话题。在混乱的情感和极端的书写背后,朵拉自觉担起为女性寻找“出口”的重任,只是这出口有几处?在何方?这是值得读者深思的。当然,朵拉并没有局限于读者的思考空间,并没有给出一个定论,但也不是没有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想法。笔者认为这也是朵拉在重拾爱情话题时比较高明的地方。在给读者留白的同时,也在故事中从女性立场出发,隐晦地表达了内心深处最为原始的反抗和呼声。
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朵拉提出问题的落脚点不是男性应该如何去做,而是女性如何去做。这样的思考视角是值得关注的。朵拉没有失去理性而疯狂地向男权主义投出爆炸式的语言攻击,而是冷静地思考女性自我省视的重要性。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朵拉没有将自己的形象神圣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将女性本身神圣化。女性也有其软弱和报复的一面,所以作家毫不隐藏地将女性的这些小情绪表达出来,成为作家表达女性希望平等、独立呼声的一个出口和方式,这样的书写背后,不仅没有让读者反感作家笔下的女性,反而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女性真实的情感和追求两性平等的迫切感受。
参考文献:
[1]陈瑞琳.《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突破[EB/OL].(2014-01-24).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何与怀.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M]//刘中树,张福贵,白杨.世界华文文学的新世纪.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63-70.
[3]朵拉[EB/OL].(2015-03-24).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59570/10752112.htm?fr=aladdin.
[4]朵拉.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5]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159.
[6]MOHAMAD Mahathir, MELAYU Dilema.Diterjemahkanoleh Ibrahim bin Saad[M]. Kuala Lumpur: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2001:152.
[7]CHEE Tham Seong.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Malaysia[M]//QUAYUM Mohammad A, WICKS Peter C, eds.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a critical reader.Petaling Jaya:Longman,2001:46-50.
[8]毛策.郑良树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90.
[9]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M].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81-134.
[10]李字永.唐代传奇의爱情故事类型分析[M].首尔:庆熙大学校出版社,2008:43.
[11]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M]//鲁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01.
[12]波伏娃 西蒙.第二性[M].上海:东西文化社,2009:809-870.
[13]庄钟庆,陈育伦,周宁,等.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08.
[14]杨淑如.朵拉《野花草坪》[M]//杨松年,郑琇方.细致的雕塑:世华微型小说评析.唐山:唐山出版社,2007:245.
[15]변광배.시몬드보부아르저[M]//제2의성.坡州:Salimbooks,2007.
[16]엄가염저,박재우역.중국현대소설유파사[M].坡州:청년사,1997.
[17]박남용.중국현대诗의세계[M].高阳:학고방,2012.
[18]박재우.故乡为主题的华文散文:以黄河浪的《故乡的榕树》为中心[M]//再访故乡的榕树.香港: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2014.
[19]임춘성.홍콩문학의정체성과탈식민주의[J].中国现代文学,2004(31):337-359.
[20]박남용.许世旭시인의시가창작상의중국시학관념과중국이미지연구[J].中国学研究,2011(58):27-54.
[21]박남용.홍콩의梁秉钧시에나타난도시문화와홍콩의식[J].外国文学研究,2009(34):121-143.
[22]박남용.싱가포르화문시가(华文诗歌)의문화적정체성연구[J].韩中言语文化研究,2009(21):371-391.
[23]김혜준.화인화문문학연구를위한시론[J].中国语文论丛,2011(50):77-116.
[24]박길장.鲁迅의妇女解放에관한作品考察[J].中国人文科学,2007(37):501-523.
[25]지세화.중국의화문문학에대한연구동향과인식태도고찰[J].中国学研究,2008(49):161-181.
[26]지세화.海外华文文学研究에담긴문화적시각의性格考察[J].中国研究,2011(52):105-128.
[27]허근배,이난영.《伤逝》—鲁迅의여성과혼인에대한갈등[J].中国文学研究,2011(45):241-260.
[28]김명석.鸳鸯蝴蝶派小说의大众性[J].中国现代文学,1997 (12):25-60.
[29]김창규.근대중국지식인의연애의수용과고뇌:胡适과鲁迅을중심으로[J].历史学研究,2014(54):119-147.
[30]허세욱.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J].中国语文论丛,1996(10):201-212.
[31]이여빈.鲁迅의女性观研究:杂文을중심으로[M].光州:全南大学校出版社,2012.
[32]송정.鸳鸯蝴蝶派研究[M].全州:全北大学校出版社,2008.
[33]시시저,김혜준역.나의도시[M].首尔:지식을만드는지식,2011.
[34]하진저,왕은철역.멋진추락[M].首尔:시공사,2011.
(责任编辑:石 娟)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cend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Malaysia: Focusing on “Love Theme” Novel in Duola Author’s Conte Selection
XU Zhen1, CHUNG Eugene2
(1.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uwon, Suwon 445743, Kore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eoul 130791, Korea)
Abstract:In China, Malaysia-Chinese literature writer Duola is widely welcomed by the public, and also has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the literary world. She had written about “love theme” in her novels, and their storyline revolves around “gender” issues. Through stories of abnormal love affairs between urban men and women. She candidly describes gender issues from a woman’s perspective, and deals with gender equality which is a classic topic. In the background of confused emotion and drastic descriptions, Duola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suggest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with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t is not about love game or farce of emotional revenge, and what she focuses on is describing the insurmountable gap between “the first sex” and “the second sex”. By categoriz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Duola novel’s character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ender confli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identity of women is described in Duola’s novel and how the thoughts and situations of women are described, and also the way Duola finds for women’s liberalization. Through this study we can understand how Duola’s novel transcen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Malaysia.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Duola;Duola Author’s Conte Selection;“love theme”;gender issue;women status
作者简介:徐 榛(1986—),男,江苏大丰人,助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郑有轸(1988—),女,韩国首尔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韩国外国语大学BK21事业团项目
收稿日期:2015-06-02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4-0068-08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2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