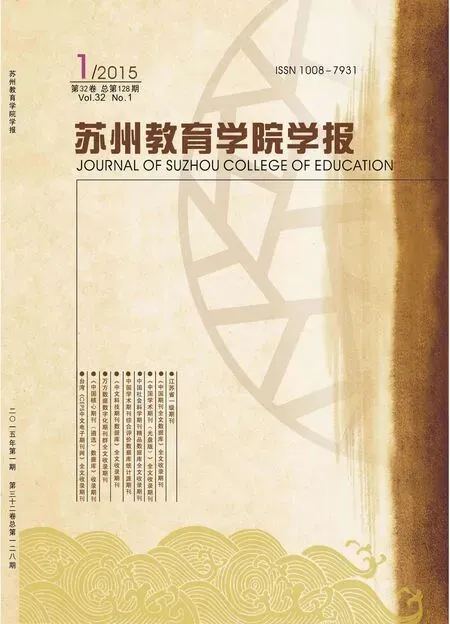保守主义:吴地现代报人的文化选择—以1920年代的《晶报》文人群体为中心
李国平(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保守主义:吴地现代报人的文化选择
—以1920年代的《晶报》文人群体为中心
李国平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以1920年代的《晶报》文人群体为中心,对当时吴地报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探讨。此时期的《晶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撰稿人群体,这一群体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文化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于“名士风度”和“才子风流”的追慕。在其小说、诗词唱和、小品札记中,类似的名士情趣流露得都颇为充分。
关键词:《晶报》;保守主义;报人;吴地;吴文化
近年来,作为现代通俗文学重要阵地的报刊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却是,这些报刊上较为出色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在连载时就曾引起读者注意的通俗小说大多已出版单行本或被收入各种选本,而那些已经被历史遗忘的作品绝大多数乏善可陈。于是,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报刊研究的价值何在?报刊研究又该如何进行?
或许,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那些报人(包括报刊编辑及其小说、诗文作者),借由他们来探讨现代通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创作主体的某一侧面。本文即拟以1920年代的《晶报》文人群体为例,对当年吴地报人的生存状态略作探讨。①之所以选择1920年代的《晶报》,自然是因为堪称海上小报“巨擘”的《晶报》存在时间长,在小报中发行最广,对其他小报的影响也最大。《晶报》于1919年3月3日创刊,1940年5月23日后被迫停刊,总计出报4 157期。最高发行量达到5万份,为上海小报之最。同时,《晶报》的风行还开创了上海小报史上的“三日刊时代”。另外,1920年代《晶报》的作家队伍大体比较稳定,而到1932年10月10日《晶报》改为日刊(此后为其后期)以后,新作者时有出现,但多昙花一现,为《晶报》长期撰稿者较少。《晶报》后期作者群更为庞杂,如捉刀人、周天籁、冯若梅等小报文人相继登场,包天笑、徐卓呆等资深通俗作家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甚至不时刊登郭沫若、曹聚仁等新文学作家的文字,所以其思想观念也更多歧异,缺乏基本近似的文化特征。
一、1920年代《晶报》文人群体的基本构成
1920年代的《晶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撰稿人群体,当时甚至有论者认为《晶报》不用外来的投稿,“不很情愿有新名字见于报上”[1]。尽管此说并不确切,但是当时的《晶报》很少采用外来稿件倒是实情,因为外来稿件“多不能十分贴合小报体裁,所以不能不加以改削,或者改做”[1]。相比之下,《晶报》的长期撰稿人则有着大体一致的思想与行为特征,他们的稿件往往更契合《晶报》的主旨与体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撰稿人视为一个具有大致相似的文化观与文学观的文人群体。综观1920年代的《晶报》作者,他们大多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轨道,所谓“新”的因素(现代的、“洋场”的气息)微乎其微,他们都属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关于前期《晶报》的基本作者,有这样几份大同小异的名单:一是《晶报》出版广告所列的特约撰稿人,二是《晶报》多次启事中所列基本作者的名单,三是1919年《晶报》国庆增刊上各位作者的签名。这几份名单大体可看作前期《晶报》的基本阵容。①1919年5月12日起,《晶报》刊登《爱读本报诸君鉴》,称:“本报出版以来,承小凤、小百姓、独鹤、钝根、老谈、微雨、漱六山房、飞公、欧阳予倩、癯蝯、生可、丹翁、瘦鹃、能毅、寄尘、小梵等诸名家分担小月旦、俏皮话、燃犀录、小说、莺花屑诸作,马二先生、凌霄汉阁主、张豂子诸剧家担任歌舞场及剧界消息,泊尘、丁悚二氏担任社会插画……另加李涵秋、卓呆诸家小说,可珋之插画……”其中所列作者与出版前广告大体相同。而1919年10月10日刊出签名的作者包括小凤(叶楚伧)、(姚)鹓雏、(徐)卓呆、(欧阳)予倩、漱六山房(张春帆)、(李)涵秋、老谈(谈善吾)、(冯)小隐、(钱)生可、小百姓(包天笑)、荒者(陈飞公)、沦泥(沈能毅)、微雨(刘襄亭)、(张)碧梧、剑云、老孙(孙癯蝯)、(胡)寄尘、(张)豂子、(周)瘦鹃、之光、(姚)民哀、霁庵(管际安)、(沈)泊尘、丁悚、马二先生(冯叔鸾)、丹翁(张丹斧)等(包括漫画作者)。这些作者以《神州日报》撰稿人和上海报界、文艺界人士为主,大多为余氏和钱芥尘主持《神州日报》时所结识的。除余氏、钱氏外,被前期《晶报》倚为台柱的包天笑自晚清以来先后编辑《时报》及《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星期》等刊物,结识并提携了周瘦鹃、范烟桥、毕倚虹、江红蕉、张毅汉等作家,这些作家中有不少也加入了《晶报》作者行列。由这几份名单不难发现,《晶报》文人群体以吴地作家为主,带有浓重的地域性色彩。他们囊括了近现代通俗文学中最负盛名的苏州派和扬州派,如苏籍作家包括包天笑、姚民哀、周瘦鹃、叶楚伧、徐卓呆、胡寄尘、江红蕉、黄转陶、范君博(范广宪)、管际安,扬籍作家则有李涵秋、张丹斧、毕倚虹、孙癯蝯、老谈(谈善吾)等。同时,由于《晶报》创办者余大雄为皖南休宁人,所以在《晶报》作者中还有为数不少的皖籍作者(如刘襄亭),其中皖南籍作者尤多,如张恨水、胡寄尘(胡怀琛)、汪优游(汪仲贤)、汪破园(汪洋)等皆是②除刘襄亭为安徽合肥人外,其他如张恨水(安徽潜山)、胡寄尘(安徽泾县)、汪优游(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汪破园(安徽旌德,汪为《神州日报》前期主持人汪彭年同乡)均属皖南籍,“皖南”历史上也是公认的吴文化区域。。此外,同属吴地的作家还包括常州籍的漱六山房(张春帆),嘉兴籍的钱芥尘和沈能毅,以及今属上海的松江姚鹓雏和青浦张豂子、王钝根、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等。
这些吴地作家大都是活跃于上海的报人和作家:老报人钱芥尘曾在余大雄之前主持《神州日报》,包天笑长期担任《时报》编辑并曾主编过多种通俗文学期刊,毕倚虹、江红蕉、沈能毅、刘襄亭都曾任职于《时报》,叶楚伧则长期担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他们的报人经历都为《晶报》的创刊准备了条件。这一点从后来余大雄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晶报》创刊之前,余大雄先向张丹斧、张春帆、张豂子、冯叔鸾、沈泊尘、丁悚、姚民哀等作家、画家“提出印行三日刊叫做《晶报》的方案。承他们担任基本撰述,都肯每期做篇稿子,或画张画,于是我再去托叶楚伧、包天笑、周瘦鹃、胡寄尘、沈能毅诸君帮忙”[2]。显然,余大雄最初是通过《神州日报》及其个人交际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作者班底,而这个班底就构成了后来的《晶报》文人群体。③部分作者是余氏通过私人关系所延揽,如当时已在演剧界崭露头角的欧阳予倩为余氏在日本成城中学的同班同学,当时二人还曾一同演出法国作家萨都的浪漫派剧作《杜司克》。
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
由于《晶报》文人群体大多由余大雄延揽,所以这一群体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文化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有研究者这样概括现代上海小报文人:“小报文人既不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也不是传统文化的守夜人,而是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职业文人。”[3]其实,假若我们细细考察的话,不难发现,所谓上海(吴地)小报文人绝非铁板一块,而1920年代的《晶报》文人群体则大多固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他们身上更多传统文人习气,其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也在在表现出典型的名士风流色彩。④不仅老一代小说家李涵秋、包天笑如此,即使一直努力顺应时代而不断前进的张恨水也未能摆脱传统名士文化的束缚,弄笔之余“听戏,看电影,吃小馆子”,还期冀能够“收买旧书,尤其是中国的旧小说”,“收买小件假古董”,“跑花儿厂子,四季买点好花”。见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在前期《晶报》文人群体中,思想最保守者当属李涵秋。他把“五四”以后逐渐兴起的新思潮一概视为“洪水猛兽”,常常发出“世道日衰,人心不古”之类的感叹[4]。他讽刺“一班文明朋友提倡甚么禁止早婚的办法”不过“是拾人皮毛”,既不切实际又于事无补。“在我看,大家不如留点精神,且放着这事,留待二三十年后再提倡罢。”[5]对于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李涵秋尤为不满。在《新三纲》中,他讽刺“今日文明朋友”讲究的是“新三纲”,即“臣为君纲,妻为夫纲,子为父纲”。他给出的理由是:现在是男女平权时代,男女双方都有随时结婚或离婚的自由;同时,现在又是家庭革命时代,“儿子呢,可以教训老子;老子呢,不可以管束儿子”[6]。在批驳“公妻”问题时,他再次对提倡男女平权者予以讥讽,认为“即使这男女的权,已经平的了不得,惟有那女人生产,不知谁有这本领,也叫男子同他一般,平了这权去生产,不使女子独受这生产的苦痛,我就佩服他”[7]。至于当时青年学生极力争取的男女合校问题,李涵秋也极力反对。他认为那些提倡者不过是要遂其男女一起“热闹热闹”的私心,根本不必“拿那些装饰门面的话来掩饰”[8]。很显然,在提倡晚婚、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男女合校等一系列问题上,李涵秋的观念都是与新思潮根本对立的,其保守主义立场不言自明。
与此相应,李涵秋对诸多社会活动的看法也是比较保守的。尽管其代表作《广陵潮》《侠凤奇缘》等小说对晚清革命者的英勇行动、无私精神多有赞誉,其《战地莺花录》甚至以浓墨重彩表现了“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但在《晶报》刊载的小说与笔记中,李涵秋却对学生运动采取了鄙薄乃至敌视的态度。在长篇小说《爱克司光录》第二回中,苏州一所新式小学的教员邵二壁虎竟然开导学生们,说所谓抵制日货不过是一个幌子,并不是要“真个同人家闹起正经交涉,一味实心爱国……我们尽管用这样旗号,内容变化,全要见机行事。大家如若表我同情,哼哼!我们吃喝嫖赌,包管从从容容的,不至有拮据之叹”。如何见机行事呢?随后,他对其兄长邵瞎子道出了其中内幕,原来所谓“查禁日货”不过是一种借机敛财的手段,“是虚张声势恐吓人的。只要那些开铺子的老板,识得我们诀窍儿,一经见了我们打着这样旗帜,只须哑没声儿三百、五百向我们袖子里一塞,还管他什么日货不日货呢?”至于那些不识其中诀窍的,或是虽识诀窍又舍不得出钱的,“哼!那就不能容情了!我们眼目又多,手脚又快,一声吆喝,果是日货,固然掳掇而去,即不是日货,亦可以顺便掳掇而去。随后拣出一两种不值多钱的,把来焚毁些,抛弃些,其余早替他一古拢儿收藏起来,或是暗中兜售给人”。第二天,上海商人罢市的消息传来,苏州各店铺“也就随声附和,不去开张了”。只有一个向来不留心时事的小店主鲁二混懵懵懂懂地照常营业,被邵二壁虎率同学生“将店中所有货物,收拾得干干净净”①涵秋:《爱克司光录》第二回《抵日货小百姓抄家 起风潮众商人罢市》,《晶报》1919年7、8月间连载。。小说中揭露,鲁二混的店铺被查抄并非由于其店中确有日货,而是因为他在几天前拒绝了邵瞎子强行借款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的这一段在《晶报》刊出是1919年7、8月间,正值席卷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方兴未艾之际。而李涵秋对学生运动的偏见无疑也暴露了他与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的隔膜。
不仅是小说,李涵秋的杂感笔记同样对学生们的行动充满了偏见,常常给予冷嘲热讽。比如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中日间种种交涉迟迟未能解决,通告全国学生一致罢课。李涵秋大发议论:“这一次学生罢课风潮,据外边人讲起来,都像不满意学生似的。不但不去帮助学生,而且啧有烦言。”幸灾乐祸之意不言自明。5月12日,扬州学生因查禁日货遭到船户殴打,学生们提起诉讼,要求“准许他们查货自由”。对此,李涵秋又揶揄说,无论是贩卖日货还是用日货都应该被查禁,所以不但这些船户们应该时刻准备听候学生们检查,“以后还须得叫那些住户居民,三更半夜,不许关门睡觉,听凭学生检查,才是彻底的办法”[9]。显然,李涵秋对学生们的行动充满了敌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已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
对李涵秋这些明显过于落伍的论调,即使是在当时的《晶报》文人群体中也有人并不赞同,比如著名的剧评家马二先生就公开批评他“头脑太旧,不脱冬烘本色”,而其笔记作品“不是讥骂新思潮,便是些龌龊不堪的琐屑语”。故此,马二先生希望《晶报》主持者余大雄以后不要刊登李涵秋的稿件,以免使《晶报》“大损名誉”。[10]不过,由于李涵秋的言论颇能代表社会上那些保守人士的思想,所以在前期《晶报》上,此类文字仍不绝如缕。
三、“名士风流”:《晶报》文人的社会活动与生活方式
当然,在《晶报》文人群体中,类似李涵秋这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同样落伍的并不多,他们中多数人都如包天笑所说“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11]391。或者借用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说法,他们“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2]。
在文化方面,《晶报》文人群体的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于“名士风度”和“才子风流”的追慕。《晶报》文人多为吴地作家,而吴地自古尚文重教,文人辈出,又有结社习气,因此《晶报》文人中有不少都曾经参加过当时的旧派文学社团南社、星社、青社。②《晶报》文人群体中参加过南社者有包天笑、周瘦鹃、叶楚伧、姚鹓雏、孙雪泥、汪破园、范君博、姚民哀、管际安、曾延年、周越然等。其中包天笑、姚鹓雏都堪称南社的中坚(包曾在1910年南社第三次雅集中当选为庶务,而姚氏则被誉为“南社四才子”之一)。一说张丹斧为南社成员,但查郑逸梅《南社丛谈》、柳亚子《南社纪略》,未见记载。20世纪20年代,包天笑、孙东吴、江红蕉、黄转陶、徐卓呆、严独鹤、孙筹成、姚民哀、江小鹣、范君博等还参加过比较活跃的通俗文学团体星社。同时,包天笑、周瘦鹃、何海鸣、胡寄尘、江红蕉、徐卓呆、严独鹤、王钝根、毕倚虹、李涵秋等又参加过另一个著名的通俗文学团体—青社。而这几个社团在文化方面无一例外地都带有浓重的保守主义色彩。以南社为例,其成员颇多保持着“名士”风度。③南社成员郑逸梅就认为南社“一般社友,未免有些名士习气”。见郑逸梅:《南社丛谈》,《郑逸梅选集》第1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南社历史上曾先后举行过18次雅集、4次临时雅集,除前两次雅集在苏州虎丘和杭州西湖外,其余各次均选择在清末民初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上海,其中仅在当时名噪一时的著名私家园林—愚园—就多达12次。在时间上,南社的雅集多选择在春秋佳日或传统节日(如朔望日、重九节、上巳日等)。如南社第十次雅集就特意选择了1914年3月29日(农历三月三日,即上巳日),追慕前贤之意不言自明:“上巳之辰,古称佳日”,“兰亭流修禊之觞,华林驰校射之马”。①匪石(陈世宜):《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南社丛刻》第九集(1914年5月)。“修禊”为古代民俗,多于上巳日(农历三月三日)临水为祭。《韩诗章句》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最著名者当属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山阴兰亭之会,王羲之作《兰亭集序》记雅集之盛况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自然,在历次雅集中,觞咏为乐、诗文酬唱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柳亚子在追忆南社雅集时曾不胜感慨地说:“宿酒未醒,加以新醉,文人雅集,如是而已。”[13]比如前述这次雅集,“既茗话于名园,复飞觞于酒阵,赏心乐事,把酒论文”。茗话、飞觞、把酒论文,这样雅致的生活显然更接近于传统文人士子,而与此后的新文学作家大异其趣。正如《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中常常描写的酒令也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先是飞“四书”相连数句,遇“口”字者饮;接下来又改成“第一句古诗,第二句词曲牌,第三句诗经,要贯串,佳者各贺一杯,不贯串者错误者罚三杯”②匪石(陈世宜):《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随后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九集则刊发了本次雅集的合影,并刊登《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予以纪念,第十集又刊载了多位作者盛赞此次雅集的诗作。
星社的活动与南社大同小异。星社最初的雅集是不定期的茶话,后来才改为酒集,同样是定期假座苏州各园林举行,而且“每一次雅集,总有社友记录下来,在报纸上发表”③天命《星社溯往》,见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207页。《晶报》也常有《七夕星聚记》之类的纪念文字刊出。。这种定期举行雅集的活动方式以及他们在雅集中的活动表现,实则是一种更接近于传统文人的名士风度。
具体到创作方面,尽管《晶报》刊出的诗歌数量并不多,但同人之间你来我往的诗词唱和仍不绝如缕。比如袁寒云就常常同林屋山人、毕倚虹等人诗词唱和。其中袁、毕二人相互推重,寒云对毕倚虹的小说更是赞誉有加。1922年,毕倚虹称赞“洹上寒云字似拳,雄遒苍劲落鱼笺”。他邀请寒云到杭州一游:“何当来作看山计,酌取西泠一勺泉。”寒云随即以诗谢之:“十年怀慕结拳拳,忽接清光拂玉笺。湖上婆娑思俊文,天涯跼蹐有高贤。耻为黄歇三千客,漫续虞初九百篇。一卷销魂入浊世,冷然疑对在山泉。”[14]二人惺惺相惜,彼此引为知己。同样,《晶报》主笔张丹斧也常有“戏拟××赠寒云”之类的打油诗。再如1923年4月,剧评家张豂子以诗作寄怀《晶报》主持者余大雄:“世局如斯不忍闻,闭关且自赏奇文。颇知海上价增纸,忍见中原事执薣。隔地悽惶同哭母,克家惭愧不如君。江南空有风光好,无日还乡望白云。”[15]余大雄随即和诗一首,戏谑道:“北京大有风光好,何必还乡望白云?”当然,类似的唱和并不多见,更多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创作一些主题相近、旨趣相投的游戏诗。比如1921年10月,天笑的3首《改杜诗赠〈晶报〉》刊出之后,寒云、马二先生等人也纷纷以“戏改《秋兴》赠《晶报》”之类的仿古拟古诗予以回应。这些诗作当然显示出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同时更表露出其根深蒂固的名士意识,因为旧诗词的交际往复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标识,是交接的双方能否在灵魂的平台上对话的基本条件。
在《晶报》文人的小品杂记中,类似的名士情趣流露得更为充分。他们谈天说地,品酒论诗,处处显示出一种优容有度的生活方式。最典型的当属袁寒云的小品。作为袁世凯的次子、“民国四公子”之一,袁寒云不必为衣食奔忙,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任情任性的生活。他喜欢金石书法,擅长填词制联,乐于冶游嫖妓,不时粉墨登场,而这些在他发表于《晶报》的诗文中都有反映。袁寒云在《晶报》上有为数众多的闲适文章,比如他的《食货小志》记载各地的饮食,《雀语》则谈麻将牌的种种消遣法,《斝斋杂诗》中常常论印石的制作,而《货腋》和《谈邮》则谈钱币与邮票的收藏。袁寒云还常常与友人交换藏品,在得到满意的藏品时又总是难捺兴奋之情,为文记之。张丹斧有“五代王氏割据闽疆时其臣郭氏所制”的面牌,方地山有宋高宗时军中所用的临安铐牌,寒云分别以明代袁氏嘉趣堂仿宋《世说新语》及徐天启小平泉一品易之。因为双牌均为“人间孤品”,“又同出自师友之惠”,[16]袁寒云作《双牌记》并填词《双调水仙子》向师友致谢。同样,因撰写《辛丙秘苑》,袁寒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熹平元年朱书匋瓶,“作《易瓶记》,永志斯缘”[17]。1921年2月,因《辛丙秘苑》纠纷,袁寒云与张丹斧反目成仇,在《晶报》上相互詈骂。直到两个月之后,袁寒云换得张所藏西汉赵飞燕遗下的玉环,两人的友谊才得以恢复。袁寒云喜不自胜,作《梦燕记》“以记艳”[18]。此外,袁寒云还多次在《晶报》上刊登启事,征求纸牌、纸币、世界货币图谱。他甚至刊登广告,希望读者能以邮票奇品、古泉或英文书报及明信片来换取其书画。这种闲情逸致,自然是不需为稻粱谋的名士才能享受的。
当然不仅是袁寒云,《晶报》其他作者中喜谈古董考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在1921、1922年间,张丹斧一方面常常和袁寒云互换藏品,另一方面也常在《晶报》上大谈其收藏。同时,《晶报》还连载余大雄的《泉鉴》、丁福保的《古泉杂记》,津津乐道于钱币收藏;人称“邮票大王”的周今觉则在《晶报》上连载《邮话》。由于此时的《晶报》每期都有至少一篇文章谈收藏,余大雄后来甚至认为《晶报》有一个“颇注意于考古”的时期。[19]
足以表明《晶报》作者传统文人身份的还有他们对于人生哀乐的咏叹和多愁善感的缠绵情致,因为“自伤身世”本来就是传统士子惯常流露的情绪。姚鹓雏在《白下杂事诗》中一再慨叹:“青袍瘦马淮南道,暮雨潇潇已可怜。” “宣南旧事今谁忆,惟有章郎记梦尘。”他追忆“宣南旧事”和沪上“文酒妓乐之盛”,更为“今不可复得”而惆怅不已。这种旧梦难追的今昔之感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诗人刻意营造“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情感氛围,其悲观的心态不言自明。而且,姚当时还不满三十岁,却感慨“三十功名意已灰,白门真为看山来”,有不胜悲凉之感①梦湘阁(姚鹓雏):《白下杂事诗》,《晶报》1919年11月9—21日。。这里,显然留下了传统文人士大夫多愁善感的心性的影子。
更多时候,《晶报》同人把对自身遭际的哀叹寄寓在悼念亡友的诗文中。1923年李涵秋去世后,毕倚虹不无感慨地说:“李先生年才五十,遽归道山,其故以撰著太繁,心血呕尽。吾人感于李先生之死,能毋联想卖文生活之凄苦?李先生既为此刻苦撰写之牺牲者,劬苦之小说家,或引以为戒乎?”显然,毕倚虹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也意识到“逾量之勤苦,心灵闭隘,体质孱弱,既戕其身,复害其文。久而久之,且损其名,甚可畏也!”[20]但是,这种生活一经选定就很难解脱,三年后,毕倚虹也因贫病而英年早逝。对此,《晶报》同人既感到痛惜同时更感无奈:“倚虹之死于钱,复死于子女之累。”他们深感毕倚虹之所以早逝是由于家庭和子女之累。因为子女众多,毕倚虹一直陷于经济困顿之中,被迫“朝夕运笔著作,卖文为活,嫌不敷,复充律师”[21]。也正因此,《晶报》同人感慨人生多苦:“行乐适自苦,多营得小休。”[22]他们甚至羡慕逝者“结束人间地狱,抛却烦恼家庭”[23]。显而易见,他们是要借咏叹毕氏的病亡来寄寓自我对于人生的感慨。如此一再渲染人生的“苦”与“哀”,刻意夸张自我的“穷”与“愁”,显然迥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激进主义者,而与古典诗文中“悲秋”的传统更多联系。
在“名士风度”之外,“才子风流”也是《晶报》文人们倾心追慕的一种生活状态,而“花”则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诗酒风流着意夸,银筝檀板送年华。闲寻玉软珠温馆,门巷琵琶第几家?”[24]“英雄迟暮惟耽酒,才子心情总爱花。”[25]因此,“载酒征花”也是《晶报》同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在《晶报》小说中,姚鹓雏的《夕阳红槛录》、包天笑的《一年有半》、娑婆生(毕倚虹)的《应时的〈人间地狱〉》等都是带有比较浓重的自传色彩的,表现的也正是他们饮酒看花的风流韵事。在《夕阳红槛录》中,主人公邵湘秋等人前往新世界游乐场,正赶上“花国总统选举”,于是与新世界主人章伯和一起征妓侑酒。他应招到杭州,仍以混迹官场为苦差,每天与上司、同事一道饮酒赋诗。辞职回到上海后,他终于恢复了诗酒风流的惯常生活。②鹓雏:《夕阳红槛录》,《晶报》1920年3月6日—7月6日。小说中的陈岫云、计蓉庵、花吴奴、邵湘秋分别以包天笑、毕倚虹、叶小凤、姚鹓雏等《晶报》同人为原型。饮酒赋诗、诗词唱和,这些似乎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无独有偶,在毕倚虹小说《应时的〈人间地狱〉》中,主人公柯莲孙和几位朋友从杭州来到上海,第一件事也是四处打电话约朋友吃花酒。显然,这种承袭了浓郁传统文化色彩的才子式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他们骨子里透出的也是一股旧式才子的风流韵味。
对《晶报》文人们而言,赖以表现其名士风度的诗与酒又常常是同“花”即妓女分不开的。换言之,作为其“才子风流”重要表现形式的狎妓冶游也是与其名士风度相辅相成的。近代上海被称为“中国的色情之都”[26],文人冶游也被认为是风流韵事。《晶报》文人也不例外,同样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最典型的当属包天笑,他曾有多次冶游经历,以至于张謇批评“天笑好嫖”[11]412。而在包天笑晚年的回忆录中,还记录了叶楚伧、姚鹓雏等《晶报》同人当时“吃花酒”“叫堂差”的事迹。在姚鹓雏小说《夕阳红槛录》中,一大批才子悉数出场,其日常生活同样离不开饮酒看“花”。参之以包天笑的长篇小说《一年有半》《新上海春秋》及前述《应时的〈人间地狱〉》等小说,有两点是颇值得注意的:其一,《晶报》同人的冶游很少单独行动,几乎都是与好友结伴同行,可见其冶游已经公开化,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的饮酒看“花”,谈及时自然也无羞涩之感。包天笑晚年回忆起这一时期的荒唐生活就并未为自己多作辩护,仅以轻描淡写的一句“交游既多,出入花丛,在所难免”轻轻带过[27]。同样,姚鹓雏的《白下杂事诗》记录自己在南京任省长公署秘书时的生活,17首诗中仅1首怀友之作,其余16首全部记述自己或友人与妓女的交往,或回忆往昔的“文酒妓乐之盛”①梦湘阁(姚鹓雏):《白下杂事诗》第11首附注,《晶报》1919年11月15日。。而在十余年后的《自叙诗二十四首》中,姚鹓雏再次回忆起当年的冶游经历,其中甚至提到当年“余家有时不举火,顾犹时时为狎游”之类不免荒唐的举动[28]。其二,《晶报》同人对于冶游已经习以为常,与妓女组织小家庭也不足为奇。在《夕阳红槛录》中,主人公邵湘秋几乎无日不到日新里的雏妓灵芝(以上海新世界第一次花选时当选民乐里都督的玲玉为原型)处。在现实生活中亦然,姚鹓雏和包天笑都曾与所恋的妓女组织小家庭。毕倚虹虽然未能如愿与所恋的妓女结合,却以这一段恋情为素材写成了包括其代表作《人间地狱》在内的多部(篇)小说。前期《晶报》另一位主干姚民哀大做花史。尽管他自嘲“背后总不免受人家咒骂:‘他说来说去,都是窑子里的事,真是丑表功了。’”[29]但姚并未因此而停止写作这类文字,前期《晶报》上的花稿几乎由他一人包办。
可以说,尽管《晶报》文人们并不尽如李涵秋那样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从他们的诗文、小品看,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自幼浸淫于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所以就其多数人来说,他们所接受的新思想更偏重于政治方面,并未达到更深的文化层次。因而他们更习惯于保守传统的文化文学观念,也更乐于以传统的、古典的方式去生活和创作。特别是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们都主张保守固有的道德观念,很难接受更不愿意去实践西方传入的现代观念。这样,他们“新”的政治理想与传统的伦理情感(尤其是孝道)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造成了他们思想深处“新政制”与“旧道德”的并存。这是1920年代新旧过渡的时代特征的投影。
当然,这种矛盾也不仅仅属于1920年代的《晶报》文人群体,不仅仅属于当时以吴地作家为主的通俗作家,即使是同一时期以激烈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人物如胡适、鲁迅、茅盾等人,也同样感受到了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感的力量,也只能在新旧道德的夹缝中寻求艰难的情理协调之心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坚守的也仍然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出于对母亲的“孝”,他们都接受了包办婚姻),寄希望于下一代,诚如鲁迅所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30]
要之,尽管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以1920年代《晶报》文人群体为代表的吴地报人也同样是具有“生存权”的,也同样是一种不容漠视的历史存在。
参考文献:
[1]林华.上海小报史[N].福报,1928-06-10(2).
[2]余大雄.二十年前的回忆[N].晶报,1938-03-03(2).
[3]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2.
[4]涵秋.吾志吾感[N].晶报,1920-04-06(2).
[5]涵秋.迟婚主义之商榷[N].晶报,1920-01-06(2).
[6]涵秋.新三纲[N].晶报,1920-03-21(2).
[7]涵秋.辟公妻[N].晶报,1920-02-03(2).
[8]涵秋.男女合校平议[N].晶报,1920-03-27(2).
[9]涵秋.船户打学生[N].晶报,1920-05-18(2).
[10]马二先生致余大雄书[N].晶报,1920-03-24(3).
[1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12]贝尔 丹尼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1.
[13]柳亚子.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
[14]倚虹寒云倡和诗[N].晶报,1922-05-21(3).
[15]豂子.读《晶报》寄怀大雄[N].晶报,1923-04-24(2).
[16]寒云.双牌记[N].晶报,1920-03-03(3).
[17]寒云.易瓶记[N].晶报,1920-12-21(2).
[18]寒云.梦燕记[N].晶报,1921-04-15(2).
[19]余大雄.纪念日回想[N].晶报,1934-03-05(1).
[20]毕倚虹.李涵秋先生的死后观[N].晶报,1923-05-18(3).
[21]听冰生.银灯毕命记[N].晶报,1926-05-21(2).
[22]丹翁.挽淞鹰[N].晶报,1926-05-18(2).
[23]庞京周.挽倚虹[N].晶报,1926-05-18(3).
[24]高旭.无题[M]//高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90.
[25]高旭.简刘三即次其《答兰史老人》原韵[M]//高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58.
[26]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20.
[2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145.
[28]姚鹓雏.自叙诗二十四首[M]//姚鹓雏剩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118-119.
[29]民哀.《晶报》的好戏目[N].晶报,1920-04-27(3).
[30]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0.
(责任编辑:时 新)
Conservatism, The Cultural Choice of the Modern Journalists in Wu Area: Taking The Crystal Literati in the 1920s as an Example
LI Guo-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Crystal literati in the 1920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journalists in Wu Area. The Crystal in this period had a relatively stable group of writers, this group has consistent mindset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is their conservatism of thought and culture. Their cultural conservatism is largely embodied in the “celebrities demeanor” and “romantic grace” of a person’s desire. In their novels, poetric responsory and sketch miscellanea, similar interest to celebrities is revealed quite abundantly.
Key words:The Crystal;conservatism;journalists;Wu Area;Wu Culture
作者简介:李国平(1970—),男,河南浚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
收稿日期:2014-10-10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1-0026-06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206.6;G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