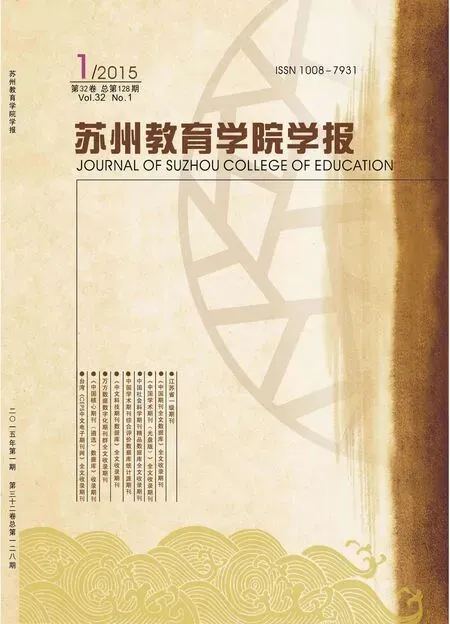张恨水副刊创作的新闻性修辞及其生成机制
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张恨水副刊创作的新闻性修辞及其生成机制
方维保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张恨水具有小说家与报人的双重身份,但在二者之间其本位在于报人。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新闻性,其新闻性修辞主要体现在隐喻性表达和直接陈述两个方面。其小说的新闻性及修辞特性,既与其报人身份有关,也与小说发表于报纸副刊密切相关。张恨水小说发表于报纸副刊,在传播上形成了受众与创作的紧密互动;在审美特性上具有社会性、世俗性、纪实性和时效性,因其独特的传播性而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张恨水的创作在审美性和新闻性的张力之中,大体做到了平衡。
关键词:张恨水;副刊文本;双重身份;新闻性修辞;生成机制;审美平衡
晚清时代的文学家和报人常常是二位一体的,他们共同寄生于当时发达的报纸和杂志等媒体之中。张恨水承续晚清到民国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人传统,他一直以报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现代文坛。他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既有小说、韵文,也有杂文时评。在小说中,既有传统题材的,也有时代题材的。在他的创作中,相当一部分小说和时评采用新闻性的叙述(修辞),这一方面与他的报人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小说发表于报纸副刊这一载体有关。其小说的新闻性修辞有着独特的生成机制,也有着独特的审美风貌。
一、报人本位副刊创作的受众鼓励机制
张恨水走上文坛之初,就在报纸新闻行业供职,他的文学创作也大多发表于报纸和杂志,尤其是报纸。张恨水的主体身份具有双重性—报人与小说家。
在报人与小说家这二者中,张恨水更看重报纸新闻的影响力,他不但从事记者这个职业,而且充当报纸的编辑和副刊的主笔。从1918年在芜湖《皖江日报》当总编辑正式开始记者生涯,到1948年辞去《新民报》的所有职务,张恨水从事新闻工作长达30年。曾任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益世报》助理编辑、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协助成舍我创办联合通讯社兼任北京《今报》编辑,任《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编辑,自办《南京人报》,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等,他的一生都和新闻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报人这一身份之下,张恨水更多是报纸副刊编辑。在北平,他先后主编过《世界晚报·夜光》《世界日报·明珠》《新民报·北海》;在上海,他又主编《立报·花果山》;在南京,主编《南京人报·南华经》;在重庆,主编《新民报·最后关头》等。张恨水的生命光华及报人才情主要体现在报纸副刊上。他自己也说过:“我的主要职业是做新闻记者,写小说不过是性之所好。”[1]事实上,文学写作对于张恨水不过是“副业”,他的终身职业是新闻记者,是副刊编辑和作者。
近现代报刊体制决定了报刊具有直接面对受众的特点,只有那些具有新闻性的报纸才能得到受众的热烈欢迎,报纸才能收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张恨水副刊创作的新闻性来源于副刊的新闻附属性
报纸副刊不同于正刊。正刊往往关注社会信息,而副刊则一般都具有文艺性,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作为新闻纸的“附件”,副刊(包括文艺副刊)也具有新闻性,这是由副刊的新闻附属性造成的。一般来说,报纸副刊多属报纸的衍生物或者说附属产品,依附性强。报纸是新闻纸,报纸的主角当然是新闻,这一点毫无疑问。特别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媒体中大量的新闻信息传播才是广大读者最为关注的。作为报纸的副刊,当然要紧紧围绕报纸的“新闻中心”来选素材,列选题,发作品。这是当代报纸副刊的正确选择。有人认为:报纸的副刊“必须引进新闻的新、快、活、短的手法和元素去打造副刊,创新副刊。对一些重大问题、事件和活动应有相应的呼应,副刊在新闻纸上的表现不可能一个劲地小圈化、私人化,她的主要读者群的定位一定要准确”,“与一些实时报道的新闻相配合”,“而且,一些杂文的针砭时弊也是有一定新闻要素的”。[2]
今天的报纸副刊其实也存在相当的独立性,正刊“风雨交加”,副刊“风和日丽”的现象也是有的。但是,晚清时代是中国现代报刊的发端期,新闻的时事性是它们得以萌生的理由。因此,晚清时代的报刊杂志对于时事新闻极为关注,新闻性当然也是本体性的。它的副刊虽相对独立,有时甚至与正刊“打架”,但它对于新闻事件也与正刊一样有着呼应的责任。张恨水所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副刊,在民国初年也继承了这种副刊体制,只不过副刊关注社会时事,与正刊关注的形式不同而已。抗战时期张恨水以“关卒”为笔名,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呐喊,以诗文、小说甚至漫画等形式来讽刺揭露汉奸的丑态,唤醒民众的抗战意志。对于新闻版面上不宜谈的事,张恨水就利用副刊文章旁敲侧击。
(二)张恨水副刊创作的新闻性来源于受众的新闻信息期待和阅读鼓励机制
张恨水报刊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实现了作者/作品与市场/读者之间的互动。他选择社会时事作为创作的题材,就是源于他自身对社会时事的敏感,也迎合了受众了解社会敏感事件的好奇心和阅读偏好。同时,他的创作以及对于社会时事的价值判断,又通过报纸及时送达受众。他的小说发表在副刊之上,这些作品被及时送到读者的手里,读者以及由读者所构成的市场也就能够及时作出反馈,小说的新闻性、市场的消费特性以及市场的营销特性,都最终反馈到作者那里,并获得了积极的回应,在叙述文本中体现出来。它与传统的文学观念阻断市场和消费的反馈渠道有着很大的不同。张恨水的报纸副刊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实现了一场阅读和创作的“革命”。
在这种互动之中,张恨水达到了干预现实的目的。张恨水的这些副刊小说显然不再是一个传统文人对于风花雪月的吟诗洒泪,而是密切联系着当时的社会现实。他把社会新闻集合到小说、时评中,使小说与新闻事件紧密交融,反映社会的最新动态及现实生活中的世态百相、人情冷暖。中国作家,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记者作家,更愿意以小说这种虚拟的方式吸纳、集合各种有趣的新闻,试图借此表达自己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张恨水借助于报纸这一传播渠道及时送达的特点,把自己对于社会事实的立场和观点迅速传达给了读者,从而最大限度也最快地影响了读者和社会公众。他做到了中国传统文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的小说显然具有了介入公共话语的权力。
在20世纪20年代,张恨水几乎囊括了北平各大报的连载小说;30年代,他又包揽了中国南北报业中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新闻报》的副刊连载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红极一时,以至于当时的读者为了追看张恨水当天的小说连载而在报馆门口排队等候买报。这种热烈的反应无疑给了他的创作以极大的鼓励。在文学场中,作者与受众之间是一种相互鼓励和期待的关系。张恨水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社会大众的阅读期待;而受众的热烈追捧也给予了他的创作以精神和物质的鼓励。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也符合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
张恨水副刊创作具有新闻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1.记者和副刊编辑出身这种特殊的职业身份;2.无论是时评还是小说大都载于报纸副刊。报人本位的创作原则使得张恨水在创作中对于时事新闻有着高度的敏感性,也使得他的副刊创作具有明显的新闻话语特征。
二、张恨水副刊创作的新闻性修辞
张恨水的报纸副刊文学创造了中国现代报纸副刊文学的辉煌,其主要的文体包括时评/杂文和小说两大类,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他在副刊上发表的连载小说。
张恨水的副刊文学创作无论在选题上还是遣词造句上都吸收了新闻话语的特点,形成新闻性修辞。张恨水早期的小说就有相当的新闻性,如《啼笑因缘》等。但一般的社会新闻多融合在休闲性的言情故事之中,“九一八”事变后所写的以抗战为题材的“国难小说”新闻性显著增强,如《虎贲万岁》就是以抗战中的常德会战为题材;《太平花》也是围绕着抗战爆发之初的抗战道路之争而展开的;《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暴行的中国作品;《巷战之夜》直接描写天津爱国军民反抗侵略、浴血奋战,收在《弯弓集》内,意在“鼓励民气”[3];短篇小说、电影剧本、笔记如《仇敌夫妻》《热血之花》《无名英雄传》以及小说《石头城外》《东北四连长》《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冲锋》《游击队》等,大多紧扣战争新闻,以真人真事为原型或直接以真人真事为素材,以纪实的笔法记录了战争中的人和事,报告文学的风格非常显著。这种选材和语言修辞在社会时评和杂文(甚至是韵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社会时评是报纸直接面对社会时事表明立场的短论,这些短论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杂文。作为报纸的创办人、主笔、记者和编辑,张恨水经常通过短评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些杂文所涉及的社会事实清晰,观点立场明确。抗战中,当“济南惨案”发生时,张恨水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就接连发表了《耻与日人共事》《亡国的经验》《中国不会亡国》等系列短评,直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进行了饱含激情的议论。他还把重庆《新民报》副刊命名为“最后关头”。他在1938 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写道:“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4]直接陈述的新闻性修辞,在张恨水的杂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张恨水的副刊创作使他特别喜欢用媒体的眼光看问题,较之于一般的书斋文学家,他更喜欢在小说中加入新闻元素,以小说介入社会热点问题,介入社会大众关注的时事政治问题;在小说叙述中融入新闻话语,达到新闻及时传达社会信息的目的。大体有两种方式:
(一)以隐喻的形式介入时事新闻
民国时代的新闻舆论一方面自由而开放,另一方面又危机重重。在军阀当政时,就有很多报人因为触犯军阀而被封报或被杀头。这种前现代化的舆论环境,催生了具有隐喻性质的副刊式修辞这样一种特殊的新闻修辞方式。
张恨水在副刊上发表的小说就常使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传达社会信息,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与评判。在谈到《春明外史》时张恨水曾说:“《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 《官场现形记》这一条路子。”[5]虽然《春明外史》最终没有成为《儒林外史》,但作家还是对现实生活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讽刺。所谓《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实际上就是黑幕小说的路子。这些小说运用晚清小说惯用的政治影射手法,“对政界、新闻界、军界、教育界、商界的各种‘黑幕’进行描写”[6]。
张恨水把大量的新闻事实、社会黑幕通过“改写”的方式融入小说作品的想象之中。早期的创作,无论是《春明外史》还是《金粉世家》,都存在着这样的“新闻改写”材料。《金粉世家》的故事背景设置为一个民国国务总理之家,无论是金铨还是他的子女们,都可以使读者联想起当时的某位国务总理及其家庭,有的故事就是当时所流传的某个国务总理的家事。《啼笑因缘》中所叙述的军阀刘国柱诱骗和霸占艺人沈凤喜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很常见的真实故事,这样的情节很容易引导读者与当时的某位军阀对号入座。这种事实的改写也引发了连带效应,那就是读者有的时候还会将作家虚构的一些故事也对号入座。这种“新闻改写”的创作方式,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十分常见,在张恨水的《魍魉世界》《纸醉金迷》《五子登科》《八十一梦》等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小说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新闻集萃,为了尽可能多地传达这些社会信息,作者甚至重新拿起了晚清时期黑幕小说重用的“串珠式”结构方式。
这些隐喻式的新闻性叙述,所切入的都是当时市民阶层所关注的公共话题,有的小说就是新闻材料的改写;有的人物就通过诸如名字、职位、长相、性格等方式,隐蔽地摹写了当时的政治人物;有的故事也是当时社会公众中流传比较广泛的社会事件,这些人和事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比较强的对应性,虽然作者并没有直接具体地写某个人或某件事,但读者在那样的语境中很容易对号入座。
新闻性的小说叙事一方面可以以虚构作为掩护,借助文学进行隐蔽的政治表达,比较自由地触及政治的敏感话题;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因新闻的对号入座而明确树敌,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避免因新闻造成的人事困扰;尤其是能够利用小说叙事的符号特征,将文学的触角伸入整个社会这一软性层面,扩大了小说的内涵,将新闻事件的具体涵义放大为社会公共的普遍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张恨水的许多小说也是比较成功的,比如《八十一梦》就借助梦的隐喻成功地揭露了抗战时期黑暗的现实生活,同时又躲过了当时严厉的政治审查。当然,这样的创作尤其如《魍魉世界》等作品,也模糊了“社会小说”与“社会新闻”的界限。
(二)以直接陈述的形式介入新闻时事
隐喻性的修辞介入主要提供的是类新闻的草蛇灰线,引导读者作现实联想,但是,也常常使得被隐喻的人和事有逃脱的借口。所以,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中也经常采用直接陈述的新闻修辞方式。
杂文是社会文化型的文体,直接表现社会时事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我们在张恨水的小说中也经常看到他采用直接陈述性的新闻修辞。在“最后关头”的发刊词中,他为这个副刊所规定的内容范围就体现了这样直接的新闻修辞观念:1.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2.游击区情况一斑;3.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4.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5.抗战韵文。从这一征文启事的内容可以看到,张恨水将所有的文类都定义为一种实用文体,无论采用什么文体,都必须及时反映抗战事实,直接表现抗战。“故事”当然有虚构的也有真实的,但是,他将其限定为抗战故事,也就是说即使是虚构也必须联系当时的抗战历史;哪怕是短篇小说也必须如故事一般记录抗战。而“游击区情况一斑”就是要创作新闻速写;“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也就是要创作生活的速写;甚至“抗战韵文”也只不过是以韵文的形式表现抗战历史而已。整个征文启事所强调的不是虚构性,而是新闻性、纪实性、生活性。
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中更实践着这样的理念,他经常直接将新闻时事纳入小说的叙事之中。如小说《虎贲万岁》中,张恨水一方面以纪实的笔调叙述了抗战中代号“虎贲”的五十七师的常德战役,把五十七师的抗战事迹以现场画面纪实的形式展现出来,使读者如临战场,亲身感受了战场血与火的悲壮。同时,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采用了“新闻事实+虚构”的叙述方式,即基本事件是新闻的,但过程的描写、悬念的设计、心理的揭示则有虚构。[7]下面是其中一段恋爱的场景:
婉华站在门口的一层石阶上,低低地叫了一声“坚忍”。他和她相隔不到一尺路,便转过身来,他站在坡子下的一层,两人正好一般高,便伸着手握了她的手道:“你还有什么话?”她沉默了一会儿,因道:“你看这整个常德城,多么清静呀,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坚忍道:“大雷雨的前夜,空气照例是这样一切停止的。你害怕吗?”她摇了摇头,但立刻觉得这星光下,他是不会看到什么动作的。便继续道:“我不害怕,不过这样清静的环境下,我情绪是不能安定的。”他把那只手也握了她的另一只手,两个人影,模糊着更接近了。约莫有三四分钟,他突然道:“婉华我告别了,祝你前路平安。”他立刻转身向前,皮鞋踏着路面的石板,一路扑扑有声。[8]
在这段叙述中,主人公及其恋爱场景是虚构的,但是,作者却利用主人公的对话将恋爱场景置于具体而真实的历史叙述中。作品对于历史场景的叙述则是一种直接陈述,作者直接将常德战役作为恋爱的背景,从而也使得虚构的爱情细节附着于虎贲将士的身上,使之具有了历史性。这种抗战罗曼司,特别容易使人想起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对于西班牙内战的叙述方法。因此,这种叙述的新闻性非常强,对于现实的表达作用当然也非常明显。
这两种直接的新闻修辞使张恨水的创作呈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场性,当然也使他的创作及副刊与社会新闻事件紧密配合,遥相呼应。把社会新闻事实融入小说创作中,使副刊具有文艺性的同时,也具有了鲜明的新闻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成为了后来包括文学,尤其是1950年代有关抗美援朝题材小说和报告文学新闻性写作的滥觞。
三、张恨水小说新闻性与审美性的平衡
张恨水的副刊创作除了一些古典题材外,大多具有现实主义的纪实风格,尤其是具有社会新闻的时效性。
这些创作受到报纸发行周期的影响,以及副刊新闻性的限制,都带有一定的时效性。张恨水创作中与报纸的新闻本性最为适应的文学文体是他的类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创作。长篇的纪实文学立足于真人真事,其文学性往往表现在细节和文字的修饰等方面。纪实性的散文,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及时点评,也是适合新闻性的文体。张恨水的创作由于副刊特性,与社会生活自始至终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力争“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新闻人的趋时特性,从文学想象的角度来说,显然增强了文学的活力,也保持了创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再者,报人身份几乎注定使张恨水要以新闻从业者的眼光来从事文学创作,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中摄入新闻元素,尤其将这些元素带入了报纸连载小说的叙述之中,使得小说创作濡染了现实性和世俗性。关注现实和传达现实的生活信息是报纸的特性,而以报纸副刊为载体的副刊文学,必然具有表现内容的世俗性和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特性。
但是,张恨水的副刊创作尤其是副刊小说由此也陷入了审美性和新闻性同场存在所形成的悖论。小说显然不是报告文学,它可能是以真人真事为背景,或者为原型,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除了背景地点和人物之外,大多数都是虚构的人物和事件,这是由小说的特点决定的。黑幕小说采用隐喻和影射的手法来表现,但是它与现实之间依然隔了一层,而且这种影射作用大多在当时的语境下生效。一旦时效性丧失,影射性也可能失效。张恨水早年也创作过黑幕小说,也采用了政治隐喻和影射的手法,甚至在后来的创作中,特别是《八十一梦》等作品中更是如此。这种隐喻手法的采用,一是迫于作者的自我保护,尤其是负面影射;同时也是因为作者屈从于小说的文体需要。但不管怎样,其中都隐藏着作者强烈的新闻冲动和对现实的干预冲动。这种新闻冲动与文学审美所需要的涵养性是有矛盾的。甚至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审美涵养的损害。将文学直接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用文学暗喻和影射现实,从而达到对现实或批判或鼓励的目的,这将带来文学现实目的性的增强,束缚文学表达。从审美中心主义来说,这样的创作,其审美性将大打折扣。
张恨水的副刊创作大多具有娱乐性。报纸副刊文学更强调其娱乐性,文学作品并不是没有娱乐性,而是娱乐性较少被强调,尤其在中国语境中。报纸副刊的文艺作品必须与正刊形成风格上的差异,以吸引不同层次的读者。因为正刊大多是新闻,且大多关涉较为沉重的现实生活,因此,副刊就要彰显休闲性的一面。张恨水对于新闻纸副刊特性的把握,使得他非常注重小说休闲的一面,诸如在创作中增强言情内容、故事性以及趣味轶事之类插科打诨的内容,等等,但这又必然导致小说的主线索和主导性审美凝聚点受到干扰,导致审美的稀释。尤其是这种休闲性,在新文化启蒙主义那里,因它不严肃而受到指责。
张恨水的副刊创作一般都有着较为鲜明的道德评判。在介入伦理方面,新闻强调的是道德评价的中立,而小说则充满了伦理的评判。相对于新闻来说,在小说中作家更易于进行道德的臧否。张恨水的小说不是自然主义小说,它不是如新闻那样只要把事实报道出来交给受众就行,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道德倾向性。相对于新闻来说,小说使得张恨水更易于发挥自己对于社会的道德评判。这可能也是张恨水在做新闻的同时选择创作小说的动机,同时,这也可能是当时的报纸在做新闻的同时又为小说提供版面的目的所在。当然,关于道德的臧否,对于副刊杂文是容易的,但杂文时评若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它显然又是一种边缘性的文体,无法承载审美功能。
总之,在报纸副刊语境中,新闻性与小说(文学)审美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在张恨水的某些副刊创作中,二者间存在着不平衡;而对于另外一些创作,特别是一些长篇连载小说如《啼笑因缘》等,却可以很好地把握二者间的平衡。因此,张恨水的副刊创作,既给现代副刊文学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提供了失败的教训。
参考文献:
[1]张恨水.我和长篇连载[J].新闻业务,1962(5):18.
[2]本刊编辑部.浅谈报纸副刊的新闻性与时代性[J].新闻世界,2010(10):57.
[3]张恨水.弯弓集[M].北平:远恒书社,1932:1.
[4]恨水.这一关[N].新民报(重庆),1938-01-15(4).
[5]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张恨水全集:6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34.
[6]温奉桥,李萌羽.现代报刊、稿费制度与张恨水小说—张恨水小说现代性的一个侧面[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6):36-40.
[7]刘文辉.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转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2.
[8]张恨水.虎贲万岁[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6-7.
(责任编辑:石 娟)
The Journalistic Rhetoric and Its Formative Mechanism in Zhang Henshui’s Supplement Works
FANG Wei-bao
( College of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Zhang Henshui had the dual identities of a novelist and a newsman, among which he based himself on the latter. Zhang’s novels have a noticeable touch of journalism, and the journalistic rhetoric was largely embodied in the two aspects of metaphoric expression and direct statement. The journalistic feature and rhetoric characteristic of his novel works have close relationships to his identity of a newsman and to the novels’ publication in newspaper supplements, which rendered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arget readers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social, popular, documentary and timely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aesthetics. The special communicative methods endowed the novels with the unique aesthetic tastes. Zhang Henshui had basically achieved the balance between aesthetic power and journalistic potency.
Key words:Zhang Henshui;supplement texts;dual identities;journalistic rhetoric;formative mechanism;aesthetic balance
作者简介:方维保(1964—),男,安徽肥东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安徽省重点学科建设重大项目
收稿日期:2014-10-11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1-0003-05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2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