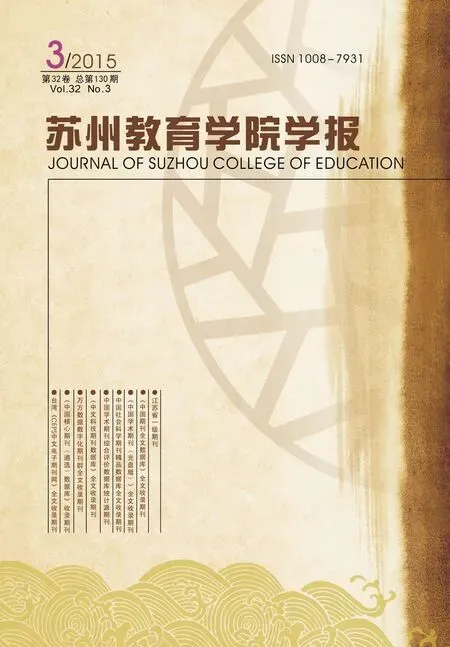余象斗和金圣叹的文化选择辨异
——基于对《水浒传》评改的比较
曾凡盛(湖南农业大学 期刊社,湖南 长沙 410128)
余象斗和金圣叹的文化选择辨异
——基于对《水浒传》评改的比较
曾凡盛
(湖南农业大学 期刊社,湖南 长沙 410128)
从编辑出版学的视角出发,对明末清初小说评点者余象斗和金圣叹评改的《水浒传》具体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概括余象斗和金圣叹的文化选择差异:“止录事实”和“始开生面”的文本差异,“愚夫愚妇”与“锦绣才子”的读者定位差异,“求其易售”与“名山事业”的价值取向差异。余象斗和金圣叹分别以“营利”和“艺术”为目的的不同文化选择路向最终导致了两者评改文本流传结局的大相径庭。
文化选择;差异;余象斗;金圣叹;《水浒传》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编辑的文化选择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令人惊诧的持续性,是编辑工作重要性的最有力证明。正是通过编辑的具体工作保证了文化的历史连续性。”[1]余象斗和金圣叹同属明末的小说评点者①余象斗(约1561—1637),福建建安人,明代嘉靖年间小有名气的书坊主,坊名“双峰堂” “三台馆”等,对古典小说的编辑、流传贡献甚大。金圣叹(1608—1661),江苏吴中人,明末清初著名小说批评家,对《水浒传》《西厢记》和一些唐诗都有评点。,他们对当时一些文本的选择、评改和刊行,无论从广义的精神生产、文化缔构、文化传播角度,还是从其选择、加工和整理的狭义角度,或是从他们所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性角色而言,都和现代意义上的编辑学属性有相通之处,因而产生了事实上的编辑行为②郭英德曾在《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福建建阳的某些书坊已不单是雕刻书坊,它们根据社会的需求,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编、刻、售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这既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生命力,又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作为福建建阳书坊主的代表,余象斗的“准编辑”角色自然毋庸置疑。关于金圣叹的“编辑”行为,拙文《通作者之意 开览者之心》和《金圣叹的编辑主体意识解读》已进行过一些论述。。在明末清初共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余象斗和金圣叹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选择对当时的《水浒传》版本进行了迥异的评改,产生了不同的文本和社会效果。为此,笔者拟从编辑学视角出发,对比其分别评改的《水浒志传评林》和《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文本,结合明末清初出版文化语境和评点者鲜明的个人特质,对余象斗和金圣叹在评改《水浒传》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文化选择进行辨异,以为当代编辑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
一、“止录事实”和“始开生面”的文本差异
据版本学考证,《水浒传》版本有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余象斗本属于简本系统的代表,是在对繁本大幅删节基础上形成的;而金圣叹本则属于繁本系统的最后一种。[2]对此已有大量文献进行了相关考证,此不赘述。现结合《水浒传》繁本中的“袁无涯本”[3],与《水浒志传评林》[4]和《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5]进行对比,可基本反映出余象斗和金圣叹的不同文化选择路向。
余评本《水浒志传评林》分为二十五卷,在其刊本《题水浒传叙》上方有《水浒辨》,内中云:“……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荃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陋,皆记上层。”[4]8清楚地体现了他的编辑观。余评本所述事件和繁本并无差别,其作为简本的内容主要少在哪里呢?经与“袁无涯本”进行比较,发现余象斗对重要情节和精微描写处进行了大幅删减。如《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回中,“袁无涯本”为:“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智深收受。长老又赐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监寺引上法座前,长老与他摩顶受记……”[3]60余评本则为:“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又赐法衣上法座前,摩顶受记……”[4]50改后缺乏主语导致语意不明。“袁无涯本”写陈抟处士听说柴荣让位于赵检点登基后:“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3]2而余评本则为:“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人问其故,那先生曰: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4]8余评本将繁本乱加删节,并将不属于老先生所言的语句嫁接到老先生口中,不仅弄得文句破碎,而且使“袁无涯本”中对老先生欣喜之余脱口而出的神情、心境的刻画失色不少。在《九纹龙剪迳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回中,“袁无涯本”用约200字详细描写智深如何跟老和尚们抢粥,如何吃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余评本则是寥寥数语:“见煮一锅粟米粥,智深把锅掇起来吃了几口粥。”[4]76将鲁智深跟老和尚们缠斗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精妙处消于无形。在《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回中,“袁无涯本”关于雪的描写多次出现,起着渲染气氛、刻画人物心理、揭示主题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但在余评本中,关于雪的描写只出现一次,“正是严冬天气,朔风渐起,纷纷下一天大雪”[4]116,将寓意丰富的雪景描写仅仅变成对环境的简单介绍。另外,繁本关于重要人物的出场浓墨重彩,大幅铺陈人物的外貌、装扮及性格特征,对人物刻画细致入微,但余评本中的人物出场却能简则简。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曾言:“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6]作为闽中知名坊贾的余象斗自然是可以将其对号入座的,他所删改的所谓“游词余韵”应是“尚足寻味”的“神情寄寓处”,这些精美的描写文字被大幅删节,直接影响了表达效果,使文本价值大打折扣。
金圣叹的评改则建立在深刻理解文本与作者进行精神对话的基础上:“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人是何心胸”,“读书尚论古人,须将自己眼光直射千百年上,与当日古人提笔一刹那顷精神融成水乳,方能有得”,“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5]4。金圣叹对繁本的精妙之处不但没有删削,而且还从一个出色的欣赏者的视角,在对文本原意深刻领会把握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结构、内容和字词等作了一些恰到好处的删改,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文本价值。金圣叹为突出“官逼民反”的主题,对繁本第70回后有“投降主义”倾向的部分进行了删除,保留了水浒英雄梁山聚义的精华内容,并通过文首的楔子加强了文本的连贯性。除了这个大的内容结构改动外,金圣叹还删掉了与文本情节和内容关联不大的诗词,使文本更加紧凑。另外,金圣叹对文本字词也有一些润饰,使文本增色不少。如第64回《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张顺悄悄开了房门,踅到厨下,见一把厨刀,明晃晃放在灶上”,金圣叹将“明晃晃”改为“油晃晃”[5]599,更加符合厨房的具体情境,而且与下文“原来厨刀不甚快,砍了一个人,刀口早卷了”的实际相合。再如《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回中,“一只快船飞也似上水头摇将下来”,金圣叹把“摇将”改为“急溜”[5]338,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船从上游而下之快速。这些改动说明金圣叹对文本介入和体验之深,在深刻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找到最适合作者之意的“那一个”,力求准确传神。因此,单纯从主题突出、逻辑严密、情节推进、语言表达等艺术表达的角度而言,金圣叹对《水浒传》内容、结构和字词的删改提升了其艺术品位,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廖燕在《金圣叹传》曰:“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7]刘廷玑《在园杂志》说:“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8]郑振铎认为:“第一,它已经包括了《水浒传》的菁华和主要部分;第二,在文字上也是一般地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些。它在近三百年来最流行,是有原因的。”[9]《水浒传》之所以今天能位列“四大名著”之一,与金圣叹关系可谓极大。
二、“愚夫愚妇”与“锦绣才子”的读者定位差异
不同的读者定位是余象斗和金圣叹不同文化选择的逻辑起点。正是他们各自读者定位和预设读者期待的差异,直接左右了余象斗和金圣叹对《水浒传》的选择和删改,从而表现出迥异的文化选择。
明嘉靖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及其市民阶层的扩大和文化消费欲求的膨胀,小说逐渐走向大众消费。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曾说:“夫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又以建安为盛,建安尤以余氏为最。”[10]作为经营书坊的商人,余象斗很清楚自己的目标读者群在于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市井细民,也就是当时同在福建的书坊主熊大木所说的“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11]。这些通俗小说虽然“文不甚深”,但毕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还是有点“言不甚俗”[12]。面临当时《水浒传》“坊间梓者纷纷” “何止数十家”[4]28的竞争压力,为了迎合更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余象斗开始着手对《水浒传》进行评改。针对所谓“愚夫愚妇”等下层民众文化水平不高,并不讲究精巧细腻描写的特点,余象斗略去《水浒传》繁本中的细节和景物描写,尽量“止录事实”,并删除大量的“失韵诗词”,其评点大多简略随意,不过是注音释义、解释典故等对内容作常识性的注释和评说,以排除读者在阅读时可能遇到的麻烦和障碍。余象斗还首创“评林体”的独特版式[13],每页分评语栏、插图栏、正文三栏。这种版式对文化水平有限的下层市井小民来说,有着很强的导读和启发作用,比只有文字叙述的“白头本”无疑有着更强的吸引力。
与尽量削弱《水浒传》的美学色彩来迎合下层民众的余象斗不同,金圣叹设定的读者对象却是文人儒士。他秉博学之才,试图建立一个包括《庄子》《离骚》《史记》《杜诗选》《水浒传》《西厢记》六部书在内的才子书系统,并把评点这六部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由于受“哭庙案”牵连被害,金圣叹最终只完成《水浒传》和《西厢记》的批注,并选评了一些唐诗,“六个才子书,只批两个半”。金圣叹把为当时才子士大夫所不齿的《水浒传》《西厢记》和其他典籍并列,足为惊世骇俗之举。为提升《水浒传》的地位,他明确将读者定位由“贩夫皂隶”变为“锦绣才子”:“旧时《水浒传》,贩夫皂隶都看;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①“不曾增改一字”并不符合实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金圣叹假托他所批改的《水浒传》为真正之古本。,却是与小人没分之书,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方解说道好。”[5]14王古鲁在《本书〈二刻拍案惊奇〉的介绍》中一语道破天机:“金的所以腰斩《水浒》修改《水浒》,为的是不愿‘贩夫皂隶’都看。”[14]金圣叹多次批评时人阅读《水浒传》的误区:“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5]13他指出,阅读不能仅仅停留在熟记故事即“事迹” “闲事”的消遣式的阅读,应进一步达到以“锦绣心肠”熟参作者结撰故事的艺术表现方式,从而向审美型的阅读转化。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一》中说,“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因此他评书的目的是“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5]2他曾讲到:“仆幼年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15]3为达到将普通的文人读者培养成新的“才子”的“金针度人”的目的,金圣叹对《水浒传》价值和意义的发掘也从社会教化转向了艺术审美的功能层面。评点形式也大大完备:正文前有序言、读法,各回都有回前总评、双行夹批、眉批,而且评点文字多有长篇大论、深入发挥者,切入了对作者创作才能、小说艺术特色的讨论,评点重心由以往强调小说社会作用转向重视小说艺术美的表现。也正因为金圣叹对小说的重视和对读者定位的变化,通俗小说日渐被广大的文人儒士所接受,其读者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求其易售”与“名山事业”的价值取向差异
余象斗是一个精明的书坊主,他自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其对《水浒传》的选择和评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商业色彩。余象斗之所以选择《水浒传》进行评点,其原始动机就是为了牟利。作为明代以来最流行的小说之一,《水浒传》的商业价值毋庸置疑。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书稿可供选择的前提下,如何在这部流行小说中做足功夫使这位精明的书坊主颇费思量。对评点这种形式的首创无疑使余象斗从中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最能体现其商业色彩的莫过于余象斗在《水浒志传评林》中加入“辨文”和“识语”,以精心打造书坊“双峰堂”的品牌形象。他在卷首《题水浒传叙》上端《水浒辨》中写道:“《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4]9作为书坊主的余象斗必须从成本角度考虑其刊本,以最大限度节缩成本,争取更大利润。胡应麟所谓“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显然是为了降低成本。清人周亮公也说:“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指《水浒传》)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①《因树屋书影》,据赖古堂刊本。“节缩纸板”的目的也在于降低成本,“求其易售”。高明阁在《论〈水浒〉的简本系统》一文中也表明了这一点:“它(简本)形成的原因本来很简单,是书贾为了牟利,既偷工减料又以‘全’为号召,对古典小说任意大删大抹的结果。”[16]刻本字数越少,板材、印刷所用的纸张以及装帧所用材料以及人工费都会随之减少,成本将会大幅降低。“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17]
与余象斗相反,金圣叹的评点刊刻却看不到任何商业的痕迹。虽然金评本《水浒传》在其生前已经刊刻,但从现存史料来看,其与以营利为要的书坊主并无交集。为教育子侄辈学写文章,金圣叹一直有将《左传》《国策》《庄子》《离骚》等书合刻为《才子必读书》的心愿,却一直因贫困未能实现。这在金圣叹的《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之“十四”中也得到充分印证:“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久欲刊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至今未就。”[15]5其堂兄金昌《才子书小引》记述了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闲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然则何不与坊之人刻行之?’又颦蹙曰:‘古人之书,是皆古人之至宝也;今在吾手,是即吾之至宝也。吾方且珠椟锦袭香熏之,犹恐或亵,而忍遭瓦砾、荆棘、坑坎便利之?惟命哉!’”[18]523金圣叹既无力私刻刊行自己的评点本,又因为恐作品“遭瓦砾、荆棘、坑坎便利之”而不肯将书稿轻易卖给书坊。他为人十分自负,号称“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才”,秉此方可“成就绝世奇文”,因为“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5]106金圣叹虽有才名,但几次科举未就,君子立言、穷愁注书成为其理想寄托。在《与任升之书》中,他一再吐露心声:“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18]41在《答王道树》中他说:“诚得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18]35金圣叹作的《葭秋堂诗序》中言及其选批的唐才子诗时曾宣称:“名山事业,敢与足下分任焉。”[19]其实,被金圣叹视为“名山事业”的不仅是其唐诗评选,《水浒传》评点亦当作如是观。《水浒传》的评语中曾留下他这样的感叹:“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5]127从传统知识分子追求“不朽”的角度而言,金圣叹以其“立言”完成了生命价值的转换,正如清末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所言:“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其人者。”[20]
四、结语
余象斗和金圣叹基于不同的读者定位和价值取向,对《水浒传》作了截然不同的评改,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选择路向。作为书坊主的余象斗,同时又扮演了一个准编辑的角色,对《水浒传》的一些情节和精微描写处进行了大幅删节,激发了下层民众阅读小说的欲望,致使“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手挟一册”②《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六。,在赢得巨大利润的同时客观上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繁荣。不过,由于余象斗自身文学修养有限,加之市场和读者的需要以及利润的驱使,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以降低《水浒传》艺术审美为代价去迎合广大下层民众心理欲求的道路,为后来的书坊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清初沈光裕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书肆邪刻,有百倍于画眉者,其迹近于儿戏,其见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习,祸且不可言。”[21]因此,在短短半个世纪后,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主粗制滥造大肆发行的书稿即遭社会唾弃。余象斗《水浒传》评本因缺乏艺术鉴赏价值,而今也只能供资料收存和研究所用,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金圣叹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编辑”,他以评点者的身份对《水浒传》进行删改也备受争议,但他所秉持的“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理念,以及在深度介入文本、润色修改《水浒传》中凸现的艺术至上的文化选择路向,却在无意中成为当代编辑的宝贵精神财富。经金圣叹评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成为有清一代的唯一通行本,也成为其版本变迁史上的最后一个版本,“……(《水浒传》)其书初犹未甚知名,自经金圣叹品评,置之第五才子之列,而名乃大噪”①王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卷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今天,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本仍然值得仔细品读和揣摩。作为当代的编辑,在面对尘世的喧嚣和市场的诱惑时,应尽量追求金圣叹所言“能令未作之书不致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5]3的理想境界,固守文化发展的定力,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1]李超.论编辑文化建构的选择与制约[J].理论界,2007(8):161-162.
[2]傅隆基.从“评林本”看《水浒》简本与繁本的关系[M]//中国水浒学会.水浒争鸣:第五辑.武汉:长江文艺版社,1987:86.
[3]袁无涯.水浒袁无涯本[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4]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水浒志传评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5]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437.
[7]廖燕.廖燕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02.
[8]刘廷玑.在园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83.
[9]郑振铎.水浒全传序[M]//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1.
[10]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57:42.
[11]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M]//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
[12]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56.
[13]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7.
[14]王古鲁,苗怀明.王古鲁小说戏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203.
[15]曹方人,周锡山.金圣叹全集(三):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十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16]高明阁.论《水浒》的简本系统[M]//中国水浒学会.水浒争鸣:第三辑.武汉:长江文艺版社,1984:222.
[17]郎瑛.七修类稿:卷4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05.
[18]曹方人,周锡山.金圣叹全集(四):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等六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19]曹方人,周锡山.金圣叹全集(一):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26.
[20]梁章钜.归田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4.
[21]戴不凡.小说见闻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291.
(责任编辑:时 新)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Selections of Yu Xiangdou and Jin Shengtan: A Case Study of Adaptations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ZENG Fan-sheng
(Periodical Department, Hu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adaptations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of Yu Xiangdou and Jin Shengt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ience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t elaborates different cultural selections of the two versio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cts and values; the different target readers of ordinary persons and gifted scholars; the different purposes of profiting and culture spreading. The distinct cultural selections determined by the purposes of the two versions lead to their distinct circulation.
cultural selection;differences;Yu Xiangdou;Jin Shengtan;Outlaws of the Marsh
I239.29
A
1008-7931(2015)03-0052-05
2015-03-12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2C0180)
曾凡盛(1973—),男,湖南石门人,副编审,硕士,研究方向:编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