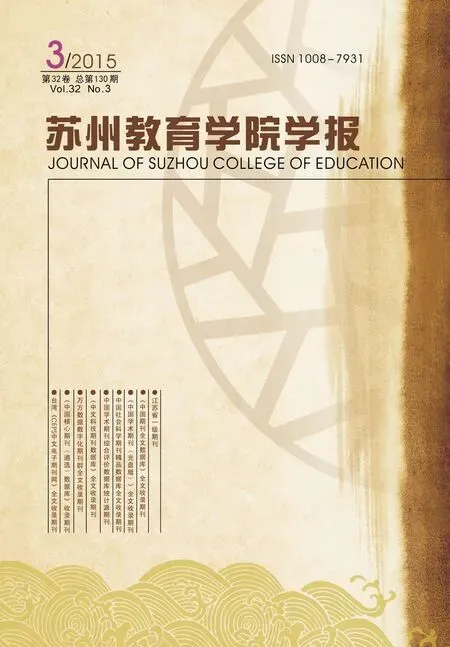试析神明祭祀与清代行会活动的互动与影响
——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孙 斌(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试析神明祭祀与清代行会活动的互动与影响
——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孙 斌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据碑刻史料记载,有清一代,苏州地区许多工商业行会都举办神明祭祀活动。行会不仅制定了专门的规约以保证神明祭祀活动的顺利举办,而且将许多重要的行会活动与之联系在一起。因此,祭祀活动的法制化与行会活动的宗教化是苏州地区工商业行会的一大特征,其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通过苏州地区现存的碑文可以发现,清代商人们认为神明祭祀活动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它能够保证行规的执行,进而维护商人们的利益与行业的发展。
苏州碑刻;神明祭祀;行会规约
阅读苏州地区的工商业碑刻,不难发现:清代的公所、会馆等都无一例外地供奉着神明。道光十六年(1836)《重修金华会馆碑》载:“乾隆初年始倡议募资于金阊门外南濠地,创构会馆,供奉关圣帝君,春秋祭祀。于是吾郡通商之事,咸于会馆中是议。”[1]360可见,商人们不仅于会馆中供奉神明,而且还常常举行专门的祭祀活动,这对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制定和秩序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神明祭祀的法制化
美国学者伯尔曼认为:“正如没有宗教的法律会丧失它的神圣性和原动力一样,没有法律的宗教将失去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变成为纯粹个人的神秘体验。”[2]68的确如此,因为倘若宗教活动不依靠法律的规范化来加以保障,宗教就缺乏可操作性而逐渐失去其社会性。清代商人们对此亦有深刻的体会,他们通过制定行会规约的方式来规范神明的祭祀活动,以保证敬神仪式能够得到长久的实施。
关于祭祀的费用,在行规中已有约定,即由成员共同捐助,但具体办法各行会的约定又有所不同。例如有的行会直接规定采用“抽厘”的办法,即从各商家的贸易额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光绪三十二年(1897)《兴复武林杭线会馆碑记》载:“会馆正殿,供奉武帝,一年圣诞两次及三节敬神。每年修理及看管之人,其费由杭庄扣除厘头。”[1]222有的行会祭祀费用的来源更广泛,不仅包括新开张店家的入会费用,还包括收徒、罚金等其他收入。道光二十四年(1844)《小木公所公议条规并捐户姓名碑》载:“议倘有私事,毋许开公所。如有私开,议罚。议外行开张吾业,先交行规钱四两八钱。议要带本地之徒,先交行规钱五两。议此钱入与公所,款神祝献公用。”[1]136有的行会规定更为灵活,例如置器业祭祀的费用并非事前议定,而是经由司年、司月等行会管理人员每次召开临时会议后再予分派。
神明祭祀活动在清代行会中已形成制度化,其具体祭祀时间一般有春秋二祭(清明与重阳)、神明诞辰或朔望日(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例如,苏州三乐湾蜡烛业的东越会馆就规定:“道光二年九月,公同捐资于吴邑十一都三十四图,建立东越会馆,供奉关圣大帝。逢诞恭祝,春秋设筵,朔望香供。”[1]267有的行会还详细规定了祭祀活动的筹备组织、参与人员以及具体仪式等。如立于苏州文衙弄的咸丰九年(1859)《吴县为七襄公所请官致祭给示碑》载:
补用同知直隶州署江南苏州府吴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甘,为据禀给示祭祀事。据司事监生黄杲等禀称,设立七襄公所,供奉关圣帝君神像。每逢春秋二祭,应请官为致祭。所需祭品猪羊,由生等公捐备办,于奉部颁祭之日,陈设祭祀。请颁示帛移祭,详请立案。等情。据此。除具详府宪立案外,所有执事人等,合行示谕。为此示,仰后开执事人等知悉:届期齐伺候本县儒学祭祀,毋得缺误。特示。
计开:猪户、羊户、礼生、读祝、吹手、亭头、结彩、炮手。
咸丰九年八月十一日示。[1]29
二、行会活动的宗教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2]3清代商人们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宗教信仰等力量注入行规中,从而将行会活动宗教化。
在工商业会馆、公所地点的选择及建造上,清代商人们会考虑以方便神明祭祀为原则。第一,倘若暂时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及适合的地点来建立会馆、公所,他们会将行会选择在庙宇中,直到条件成熟时再另作打算。同治三年(1864)《苏州府为剃头业借关帝庙权设公所给示禁约碑》载:“嘉庆年间,前人创设江镇公所,坐落吴邑北元二图马医科地方,供奉圣像……因遭庚申之变,公所房屋被毁无存……现已择于长境元二下图闾邱坊巷中关帝庙内闲房,权设江镇公所。”[1]296苏州剃头业于嘉庆年间所建的江镇公所,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全部被毁,李鸿章淮军克复苏州后,剃头业的商人们为了实现行业复兴,便在长洲县内的关帝庙中暂设公所,以应一时之需。第二,清代商人们于公所、会馆中建造专门的祭祀场所。商人们将行会设立在寺庙之中,多属不得已之举,一旦条件成熟后,即会建造神殿、戏台等以供祭拜、唱神戏等活动之用。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吴江盛泽镇续修济宁会馆碑》载:“正殿供奉金龙四大王神像……乾隆三十年乙酉,重修大殿。嘉庆十一年丙寅,重造戏台、山门。”[1]351这一方面表明清代商人们财力之雄厚,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对神明祭祀活动的重视。
与此同时,清代苏州地区的商人们总是将一切重大的行会事务都以神殿为中心来进行。孙丽娟教授认为:“敬奉神明的活动贯穿于清代商人社会的几乎全部社会生活之中。”[3]因此,苏州三乐湾的烛业商人们在关帝面前商定货价;闾邱坊巷的剃头业江镇公所在圣像前制定行规;而城隍庙的钢锯公所则在神明面前举行善举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意在使行会规约带有神圣色彩,从而具有更大的约束力。
三、神明祭祀对行会活动的影响
由上文可以看出,清代苏州地区的商人们已将神明祭祀与行会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者的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但对于精打细算的商人们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将神明祭祀作为一种手段,行会活动的顺利开展、商业利益的稳定获取,这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结果与目的。其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三种:
第一,神明保佑行会的发展。清代商人们普遍拥有一种神明崇拜心理,即他们认为只要定期祭拜神明,神明便会赐予福报。李乔先生指出:“从业者供奉行业神,是有着很强的神决定祸福、神左右生计的观念的。”[4]66人们常常有客观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某种愿望,但主观上又对其有强烈的诉求,于是便求之于一个先验的神灵,以慰藉自己无法满足的内心欲望。光绪二十三年(1897)《兴复武林杭线会馆碑记》载:“完竣之后,适增新店,补助经费,分上中下三等。公议酌捐,助入会馆。或蒙神佑,生意蒸蒸。将来抽厘愈多,尚可推广善举,成立义塾,或助同乡殡葬之费,或助同业婺恒之会。”[1]222“或蒙神佑,生意蒸蒸”,意味着商人们已将生意兴隆与神明崇拜联系在一起,即认为通过敬神活动便能得到神明的福佑;而在得到神佑之后,他们就会进一步推广义塾、殡葬、婺恒会等各类慈善活动,商人们通过更多积德行善行为以回报神明。这种人神之间交际往来的方式已被商人们所广泛认可,当然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他们更好的谋利。
第二,神威保证行规的执行。这也是基于商人们的神明崇拜心理,不过,它并非希冀神明直接保佑行会的发展,而是期望依靠神明的力量来惩罚、威慑违反行规的人。如上所述,清代工商业行会往往在供奉着神明的大殿中制定规约、执行行规甚至解决纠纷,故可以说清代商人们都是在神明的面前处理行会中的重要事情的。这一方面会使商人产生一种人事即神事的特殊而神圣的心理,另一方面也会在精神上承受一种压力,因而不敢轻易违反行规而亵渎神明,以免招致神明的惩罚。光绪十八年(1892)《药皇庙太和公所记》载:“每逢朔望拈香,集同业于斯,讲求采药之道地,考博炮制之精良,勿苟且而欺心,毋作伪面造孽。尽心尽力,利物利人。语云:‘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凡吾同业,谨守斯言,庶几生财有道,源远流长。”[5]太和公所是苏州药材业的行会,这一行会与其他行会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要为商人们生财进行谋划,而且还要肩负治病救人的社会责任。因此,药材商人们在定期举行祭祀活动的同时,还召集同业人来探讨药材业的各种工艺。无疑,这种做法很有深意,它使那些只顾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不顾药材质量的商人慑于神威而加以改正,并真心诚意地与同行进行交流、沟通,以提高药材质量。
第三,神明祭祀活动促进行业内外关系的融洽,以保证行会的长远利益。据嘉庆十八年(1813)《嘉应会馆碑记》载:
会馆之设,所以展成奠价,联同乡之谊,以迓神庥也……惟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亦聚,此不易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我五邑之人来斯地者,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人情可谓聚矣。则展成奠价生财之所,何可少缓须臾,而不亟为图谋乎?且会馆既立,五邑仕宦经过此邦者,皆得以瞻拜明神,畅叙梓谊。而在此经营者,每遇良辰佳节,衣冠济楚,旨酒佳肴,粢盛丰洁,以报神贶。则神听和平,降福孔皆,数千里水路平安,生意川流不息,皆聪明正直依人而行之明验也。[1]350
嘉应来苏的商人们认为会馆本身即为联络乡情并祭祀神明的场所,并且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神明祭祀活动可以有效地增进同乡商人、官员之间的联系,扩大关系网,此即所谓“人情聚”。而“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由祭祀活动而扩展的人脉,可以大大帮助其日后事业的发展,此又所谓“人情聚则财亦聚”。这也正如李乔教授所说:“各行业,特别是行业组织供奉行业神的重要目的和作用之一,是通过供神团结和约束同业或同帮人员,从而达到维护行业或行帮利益的目的。”[4]78
通过解读苏州地区有关工商业神明祭祀活动的碑刻可以发现,精明的清代商人们非常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的多种要素,利用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神明崇拜心理,为其在广阔的帝国版图中追逐最大利益的行为谋求某种合理性。内心的信仰与手中的利益相结合,出世的宗教与入世的法律相联系,这或许印证了文化底蕴与物质财富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苏州自古以来能够成为人文荟萃、经济富庶之地,想必在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此。
[1]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哈罗德 伯尔曼 J.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孙丽娟.清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16.
[4]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5]彭泽益.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175.
(责任编辑:毕士奎)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Worship Activities and the Activities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Guilds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in Suzhou
SUN Bin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tablet inscriptions, man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guilds conducted worship activities. These guilds established special regulations to safeguard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ship activities, and they related the guild activities to god worship. Therefor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worship activities and the religiousness of the guild activities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uilds in Suzhou, which we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reading the inscriptions in Suzhou, we can discover that the merchants thought the worship activities could prot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uild regulations by means of blessing, deterr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well-connected network, and then it could keep their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uilds.
inscriptions in Suzhou;worship activities;guild regulations
K206
A
1008-7931(2015)03-0030-03
2015-04-15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6)
孙 斌(1987—),男,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苏州地方法律文化与中国古代法律古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