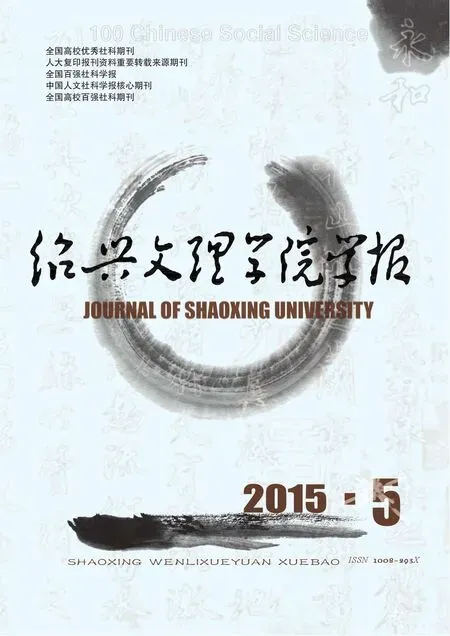刘履《选诗补注》陶诗注评议
王 文 张建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刘履《选诗补注》陶诗注评议
王 文 张建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绍兴人刘履《选诗补注》对《昭明文选》进行删补注释。通过对陶诗注解的分析,发现刘履对诗歌的注释,主要从诗歌中的难解字词入手,进行考证校勘,结合诗歌的创作年代与背景疏通诗意。刘履注诗的三大手法为以史证诗、以道学思想解诗、以赋比兴说诗,其结论既有求之过深的问题,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刘履;《选诗补注》;陶渊明;以史证诗
刘履,元末明初名儒,“字坦之,上虞人,入明不仕,自号‘草泽闲民’”[1]41。他有《风雅翼》共“十四卷传世,首为《选诗补注》八卷,取《文选》各诗删补训释,大抵本之五臣旧注,曾原演义,而各断以己意。”[1]40冯静淑认为刘履的《风雅翼》是诠释《文选》的作品中少有的一部“重五臣注轻善注”的立异之作。[2]王书才在《明清文选学述评》中,评价刘履的《选诗补注》说其“侈言比兴,发掘微言大义,多流于牵强附会”[3]67。
那么,刘履《选诗补注》的注释方法如何?有何价值呢?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诗人,刘履本人对陶诗尤为推崇,对陶诗所用功力较深。《文选》中共录陶诗8首,而《选诗补注》卷五全为陶诗,共43首①《停云》《荣木》两篇各按4首计算,因为每篇四章,而每章之下,刘履都有注解。。本文将以《选诗补注》中卷五的陶诗为例,说明刘履《选诗补注》的特点与价值。
一、以史证诗与分析诗意
《选诗补注》在注释中“以史证诗”的倾向明显,尤其表现在对诗歌年代的考订上。自《诗序》之后,“以史证诗”的方法便开始出现,尤其是到了宋代之后,由于宋代历史学大为发展,“以史证诗”的治学方法也明显开始兴盛起来。刘履的学术思想多承宋时的理学家,自然也继承了“以史实证诗歌”的方法。刘履注书的特点之一就是长于探讨诗作创作背景,以此发掘作者的创作动机。在《选诗补注》中也多处贯穿这种解析诗歌的方法,关于陶诗的创作年代与史实的推断,刘履大部分也都断定得相当准确,对于我们理解陶诗大有裨益。
例如,《赠羊长史》: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
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
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
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
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
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
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
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刘履注曰:
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伐秦,破长安,送秦主姚泓诣建康受诛。时左将军朱龄石遣长史羊松龄往关中称贺,而靖节作此诗赠之。其意盖谓平生慨念古昔达观世故,素有慕于四皓之风节矣,今天下丧乱,将有易代之祸,思欲与之同游而不可得,是以因松龄使次商山,使特为我谢之也,然商山之歌尚结于我之心,而商山之人则已乘世运而远逝,遂使我襟怀拥塞,言虽尽而意不舒也。[4]99
这一段对于诗歌创作年代的断定相当准确。汤汉在《陶靖节诗注》中注释曰:“盖南北虽和而世代将易,但当与绮甪游耳,远矣深哉。”[5]汤注仅“南北虽和而世代将易”几个字,无法解释清楚整个事件,而刘履的注释则根据“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一句,推断出该诗的创作年代,将史实原本呈现出来,说明了陶渊明作此篇时的历史环境及其缘由。
在对诗中的语词进行解释时,刘履将重点放在了一些历史名词的解释上,尤其是关于“四皓”的典故,他完整地注出那首“四皓”作出的《紫芝歌》①秦末“四皓”避秦共入商洛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而肆志。”,点明“四皓”与“紫芝”的艺术内涵,“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而肆志”[4],通过对“富贵”与“贫贱”的对比,陶渊明表明心志。刘履也站在同样的立场,对于陶死守善道的实践品格进行褒扬。
将诗中的“商山绮甪”的典故加以分析,再加上义熙十三年刘裕伐秦的史实,得出“将有易代之祸”的结论,“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伐秦,破长安”。巨大的事功,使得刘裕在东晋朝廷里的地位显赫,位在诸侯之上。“(当时的)刘裕经过两次北伐,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大片地区,都已经为刘裕所有。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刘裕令心腹鸩弑安帝,立司马德文为傀儡皇帝。元熙二年(420),刘裕迫使司马德文禅让,即皇帝位,改元永初,是为武帝,至此刘裕篡位成功。”[6]此篇作于篡位前四年,陶渊明虽身在田园,但始终关注政治局势,所以能够感受到“将有易代之祸”。笔者认为,刘履的结论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独成一家之言。
注者是将自己放在了陶渊明的角度和立场上,以己观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诗歌进行解读,由表及里,深入发掘出陶渊明的忠义精神。陶渊明虽然对国家统一抱有热切的期望,却又身处易代之际,他不仅是一个隐士,更是一位忠义之士,忠于东晋,不愿仕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
其实陶渊明这样的选择,也正是刘履的自我人生抉择。陶渊明这首诗作于易代之际,刘宋将亡,陶渊明愿效“四皓”,采紫芝以疗饥。刘履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元代行将就木,作为亲历元朝末世的学者,他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不仕即将成立的明朝,不做二臣。所以说刘履在注释的时候,重点点明注释中的用典,结合自身感情,对诗歌进行了恰当准确的分析解读。这种“以我观诗”的注释方法,因为注者与作者相似的人生际遇和价值取向,注者能从人性的角度更好地注出诗之内涵,为后世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野,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的心声。通过注释来隐晦地表达自我感情,寄托深意,刘履算是较早的一位,比清代学者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早了三百多年[7]。
王书才在《明清文选学述评》中评价刘履的《选诗补注》,认为其“发掘微言大义,多流于牵强附会”[3]65,这样的说法,最起码在论及陶诗时,是不准确的。
刘履注陶诗,虽不免会有一些牵强之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讲解是相当成功的。例如,刘履注《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篇,“此诗盖靖节彭泽退归后所作,故于首篇言误落尘网已逾十年,常如鸟恋旧林鱼思故渊,今乃归休田野而其景趣幽远闲静如此,正犹久在樊笼而复得返自然也。”[4]96只是敷衍原文大意,并无引申,反而将全诗更好地解读。
再如,在注释《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篇中,刘履评价道:“此诗凡十三首,皆记二书所载事物之异,而此发端一篇特以写幽居自得之趣耳,观其‘众鸟有托’‘吾爱吾庐’等语,隐然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则其俯仰宇宙而为乐可知矣。”“词虽幽异离奇,似无深旨耳”“愚意渊明偶读《山海经》,意以古今志林多载异说,往往不衷于道,聊为咏之,以明存而不论之意,如求其解,则凿矣。”[4]110自从汤汉注陶诗以来,往往都认为陶诗更有深意,再加上《山海经》本身比较离奇,汤汉注《读〈山海经〉》一组诗,注释得较为详细,但大都是对诗中的神话故事加以说明,后世注者却往往挖掘其寓意,与史实联系起来,可总是穿凿附会,难以自圆其说。刘履在注释之中得出“似无深旨耳”的结论,确实准确无疑,由此可见其对陶诗的把握还是有一定功力的,并非每一首诗都会“挖掘微言大义,牵强附会”。
二、以理学思想注诗
当然,刘履这种“以我观诗”的注释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对诗歌进行注释,最重要的就是站在诗作者的角度进行相对客观的阐述,而应避免注者因为个人主观感情而对诗歌肆意阐发。刘履由于其特殊的时代环境,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嫌。而刘履注诗,最大的问题就是求之过深。
刘履注陶诗,每每能看出一些道学情趣来。这明显受到了刘履自身的文化底蕴的影响。元末明初人谢肃在其《密庵文稿》壬集中的《草泽先生行状》一文写明了刘履的生平:“其先为沛郡人,先祖有仕于吴越者,葬于上虞,其子孙遂为上虞人。”[8]刘履的家族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刘履的高祖刘汉弼为南宋理宗朝侍御史,《宋元学案》中将其列属“西山真氏学案”一支[9]。刘履曾为其高祖编《忠公年谱》一卷。由此可看出刘履自身对宋明理学的推崇。刘履作《风雅翼》,本身就是为了理学教化。
例如在《饮酒》“羲农去我久”篇,刘履评曰:“西山真氏谓:‘渊明之学,自经术中来。今观此诗所述,盖亦可见,况能刚制于酒,虽快饮至醉,犹自警节而出语有度如此,其贤于人,远矣哉。’”[4]105真西山,即真德秀,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字景元,后更为希元,建之浦城人,[10]注有《大学衍义》一书阐释其理学思想。四库馆臣在评价刘履《选诗补注》时就说:“其去取大旨,本于真德秀《文章正宗》。”[1]王书才在《明清文选学述评》中,专列一节探讨刘履《选诗补注》对真德秀《文章正宗》的继承与发扬。
在注解《荣木》之时,刘履说:“言木之荣谢,则系乎时人之贞脆,实由于己能养之以福,则贞固可久。不能保养以取祸,则脆而易折,且祸福无门,莫不能自已。求之者,惟依乎道,则心常中正,敦乎善则德益加厚,此乃所以自求福也,舍是复何为哉?”[4]95更能体现作为理学家的刘履对于宣扬道德教化的文章的反复咏叹。刘履由于其自身的理学情趣及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往往能看到他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在注释之中,他极力宣扬理学教化及忠君爱国思想。
三、选诗与比兴说诗
在《选诗补注》中,最为特殊的一点就是以赋比兴体例说诗,这种说诗体例,四库馆臣寻其渊源说“其铨释体例,则悉以朱子《诗集传》为准”。由此可见,刘履注诗,仍旧是为了“诗教”一说,继承朱子遗志。谢肃在其文稿中收录有为刘履《选诗补注》所作之序:
惟穆清生人莫不有志,志之形于声文,斯谓之诗。诗于周为极盛而传者,止三百五篇。下此为楚人之辞,又下此为汉魏以降之五言,而诗风变矣。然三百篇则圣人所删,善恶毕备,以示劝惩。《楚辞》则朱子所校录,亦其发于性情,关于风教者,不则虽好而弗载。五言则萧昭明所选,编次无序而抉择不精,果能合夫圣人朱子删校之法乎?不惟不能合,夫删校之法,而诸家之注,果能合夫朱子注《诗》《楚辞》之法乎?况朱子尝欲抄经史、韵语、文选、古词以附于诗楚辞之后,惜其书不成。[11]
从这篇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履增删《文选》,选诗的标准不像是萧统那样更加注重文辞,“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12]。刘履注书就是为了实现其“诗以载道”的理学思想,对《文选》中的篇目进行增删评注,其实是他在向“先师”孔子学习。
刘履用赋比兴进行注释,这种注释方法与理学大师朱熹注释《诗经》《楚辞》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元代戴良为《风雅翼》作序说:“至其注释,则以(朱子)传《诗》、注《楚辞》者为成法。”[13]朱熹的《诗集传》每章先标出所使用的赋比兴方法,然后再对诗中个别难解字词进行解说,最后串讲全文。刘履《风雅翼》如出一辙,他将全书取名为《风雅翼》就表明了希望他所注之诗成为《风雅》之“羽翼”。
邓小军先生在《谈以史证诗》一文中讲:“《毛传》注重解释诗歌的赋比兴艺术。《毛诗》既注重以史证诗,又注重比兴艺术。《毛诗》的注释方法,实际上包括两种方法,从全体的理解到局部的理解(宋学式的方法),和从局部的理解到全体的理解(汉学式的方法)。”[14]很明显,刘履的注书方法是宋学的方法,从全体到局部去理解。但是,对于有切实历史背景的写实性诗歌来说,言说比兴的前提必须是对于史料的准确把握以及诗歌与史料的精确契合,“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15]。
但是,刘履言说比兴存在牵强之处,例如,《九日闲居》中“空视时运倾”一句解释为“易代之事”。再如,《拟古》“荣荣窗下兰”一篇中“初与君别时”一句,刘履认为“君”即是指“晋君”。这两例中历史背景考察均有争议,而且只根据文中的某些词句来断定比兴寓意是不合理的,也就是王书才所说的“侈言比兴”。
比兴除了严格要求诗歌与时代、诗人的密切关系之外,还必须使兴象与意义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只有这样才能在解读诗歌比兴时,使之能够了解兴象的暗示含义,体会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
《诗经》之中兴句,虽然大部分是譬喻,但是大多“兴义难明”。不同的诗经笺注对于比兴的断定会有不同,所以后世往往“比兴”连称,“兴”往往就是“譬喻”或者是“比”。后来的道学家认为“气象是道的表现,也是修养功夫的表现”,所以对“诗可以兴”加以扩充,读诗以“气象”而论,但是这样往往就会断章取义,误读诗歌[16]。刘履的注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选诗补注》中所论及的关于“兴”的诗歌,往往就是以比而论。刘履首选《停云》四章,每章分而论之,但是前三章都为“比”,而最后一章却为“兴”,关于比兴的划分方法,刘履亦未言明。其实刘履所说的比兴就是后世所谈到的“比兴连称”,其实就是“比”,而“兴义罕用”。但是刘履在注释划分比兴时,没有明确这一点而强说比兴,显然是不合适的。
刘履采用赋比兴注诗,对此持否定看法的居多。四库馆臣言:“至于以汉、魏篇章,强分比兴,尤未免刻舟求剑,附合支离。朱子以是注楚词,尚有异议,况又效西子之颦乎?以其大旨不失于正,而亦不至全流于胶固。”[1]41
从《选诗补注》卷五的统计可以看出,刘履注释的陶诗43首中,认为其中是赋的有30首,比有7首,兴2首,赋而比为4首。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刘履认定陶诗中“赋”占绝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比、兴说诗而求“微言大义”的弊端。可是刘履在论及比兴之时,往往容易产生误读。刘履认定为“比”的诗歌,大都断定该诗为政治隐喻之诗,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例如,刘履认为《岁暮和张常侍》一篇所用手法为“赋而比也”,分析其中的“飞鸟”一词有深意,“喻宋公阴谋弑逆之暴而能使人骇散也”。《饮酒》“道丧向千载”篇,整篇为兴,斥责当世之人不肯“适性保真”而徒恋世荣。上述两例中的本体与喻体之间都不具有相似性,而且对于诗中历史的界定也没有依据,所以论说比兴并不合理。
刘履的注释往往也是强说比兴以穿凿附会,印证自己的观点,但有时却难以自圆其说。例如,他认为《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篇为“赋也”,但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句很明显用了比喻,在后面的串讲全文中,他却说:“首篇言误落尘网已逾十年,常如鸟恋旧林鱼思故渊,今乃归休田野而其景趣幽远闲静,如此正犹久在樊笼而复得返自然也。”[4]96刘履的注释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言整篇为赋,但是后文的解释却是按照比兴来说。
再如,《拟古》“荣荣窗下兰”篇,首句“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一句,兼作比兴,而刘履单单认为此诗为比也。“兰与柳本皆易衰之物,犹且荣茂如此,以喻晋室虽弱,尚可望其有为。”[4]106但是写兰与柳,是为了写下文中的“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也是为了与下文中的“兰枯柳亦衰,”一句相互照应。实际上,陶渊明既然题之以《拟古》,这篇就是对于古代诗歌的模仿,真的是“拟古”之意。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集笺注》中认为“此篇确为拟古之作”,所仿照的篇目是《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并且列举该诗全文,从语言、声韵、意象、结构、主旨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17],这种观点明显更为合理。
综合以上几例可以看出,以割裂赋比兴的方法来分析诗歌是不合理的,汉魏以后文人文学创作更加多样化,以固守的眼光来看待新事物,将会不合时宜。正如四库馆臣所讥刘履之作为“东施效颦”“刻舟求剑”。因为刘履采用比兴说诗之法,才为后人所诟病。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得不说这是刘履注释书中失败之处。
结语
刘履也明白对于陶诗的鉴赏应该是灵活具体的,有与时局相联系的抒发愤慨的政治隐喻之诗,也有纯粹书写田园安适生活的农桑之诗。但刘履并不能很好地将二者划分清楚,因此才导致了注释之中的一些过分引申与牵强附会,过分关注作品的思想与作者人格,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而应有的艺术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并不高,批评《选诗补注》八卷,只是“取《文选》各诗删补训释,大抵本之‘五臣旧注’曾原《演义》,而各断以己意”[1]41。虽然刘履有一些注释加入较重的主观色彩,但是瑕不掩瑜,不能否认他的有些注释是十分成功的,能够探究出陶诗的深意,比如《赠羊长史》《归园田居》《杂诗》等几篇,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综上所述,刘履对诗歌的注释,主要从诗歌中的难解字词入手,串讲全诗,断定诗歌的创作年代与背景,方法主要为以史证诗,但不免有讹误之处。整个注释再加上对于诗歌的选择以及赋比兴的判断,这些都体现出刘履作为一个理学家的诗教观念。
刘履通过对陶诗的注释,从更深一个层次上挖掘陶诗的涵义,这对后世陶诗的解读具有深远意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陶渊明与刘履,同是处于朝代更迭之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而去,归隐南山下,写诗以发愤懑之情;而刘履编《风雅翼》,对《文选》中诗文的增删以及重新注释,通过这种隐晦的方法来表达对元朝的深厚感情。两人之间的共鸣使得刘履在注释陶诗时充满异代同悲之感,通过诗歌注释这一方式抒发了忠义之情,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注释中值得注意的重要类型①刘履之后,通过诗歌笺释寄托易代之思者,当属钱谦益《前注杜诗》,参见邓小军《红豆小史》,《诗史释证》第47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1][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P40[M]//万有文库:第3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2]冯淑静.《文选》诠释史上一部立异之作——刘履《选诗补注》论[J].理论学刊,2006(1):121.
[3]王书才.明清文选学述评:上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7.
[4][元]刘履.风雅翼·选诗补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9.
[5][宋]汤汉.陶靖节先生诗[M]//陶靖节先生诗注.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1988.
[7]张建伟.刘履《选诗补注》阮籍诗注评议[D].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元代文化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
[8]谢肃.密庵稿·文集·癸卷·草泽先生行状[M].《四部丛刊》三编本,P85.
[9]黄宗羲.宋元学案:第八十一卷,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2693.
[10][元]脱脱等修.宋史·儒林七:第1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958.
[11][明]谢肃.密庵稿·文集·选诗补注序[M].《四部丛刊》三编本,P85.
[12][梁]萧统.昭明文选·文选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8:3.
[13][元]戴良.九灵山房集·皇元风雅序:第5册19卷,P227[M]//丛书集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4]邓小军.谈以史证诗[M]//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1.
[15][唐]孟棨.本事诗[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3.
[16]朱自清.比兴[M]//诗言志辨: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2.
[17]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3:319.
(责任编辑 张玲玲)
I206.2
A
1008-293X(2015)05-0056-05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5.05.11
2015-06-29
王 文(1990-),女,山西运城人,山西大学文学院硕士。
张建伟(1973-),男,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