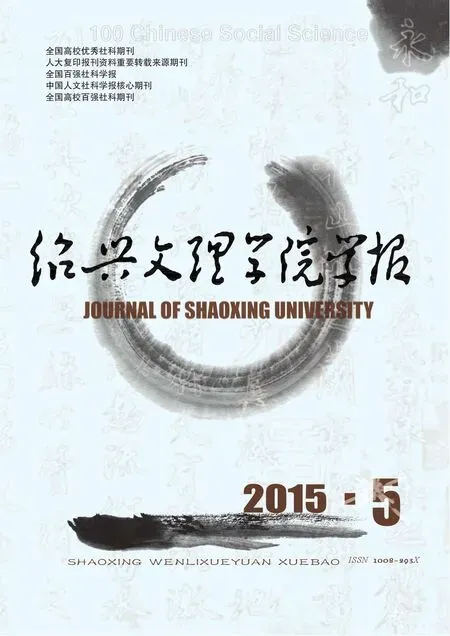浅析越地明清碑刻的治水理想
王晓亮
(绍兴文理学院 兰亭书法艺术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浅析越地明清碑刻的治水理想
王晓亮
(绍兴文理学院 兰亭书法艺术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绍兴是越文化的发祥地,这里保留着众多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的文字碑刻,其中,绍兴地区关于治水的碑刻有着较为突出的地域特征和文化价值。由所列举的几块碑刻来看,绍兴明清时期与治水相关的碑刻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绍兴人民以禹为师、防微杜渐、希冀长治久安的治水理想。
绍兴;越地;碑刻;治水
狭义的碑刻是指带有碑首、碑身、碑座基本组成的用以昭示丰功伟绩、建筑名称、墓主身份、立碑目的等作用的刻字石碑,如汉以后常见的“螭首龟趺”式的墓碑、功德碑、寺院碑等。而广义上的碑刻则是指包含碑、摩崖、造像题记、墓志、石经、石幢、画像石、墓塞石等所有在石质表面凿刻文字的物质文化遗存。绍兴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这里又是东汉以后,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的财货汇集和人文荟萃之地,自古而今,留下了大量的石刻遗存,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大量的文献史实,更是越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其中蕴含着越地文明发展的历史痕迹和越人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各类石刻之中,狭义上的古代碑刻,多为当时名闻一时的饱学之士和丹青名手所撰文书丹,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此外,更因其多为官方刊刻、所载事迹重大、形制完备、工艺细腻而尤具研究价值。
综合来看,绍兴碑刻文化特征包含了防治水患、保民安民;帝王手迹、恩泽地方;重文兴教、名士风流;三教共融、佛道名胜的诸多特征,但在这些文化特征中,绍兴碑刻治水安民的文化特征又最为突出,而这一特征的出现正是源于绍兴特殊的地理环境。由近现代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表明,宁绍平原所在的越地由于受历次海侵和海退的影响,平原陆地面貌曾有过巨大改变[1],最终形成了“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概况。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不同的气候、地貌和资源状况也必然深深地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先秦时期,管仲曾对越地环境和民风有过这样的描述:“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极而垢。”[2]可知在中原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春秋时代,越地还因为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而被视作“愚极而垢”之族的聚集之地。事实上,受山多田少、水网密布、地力有限、时有潮患所制,越人“断发纹身”的化外形象是经常出现在先秦的典籍之中的。且古人对越国民风的看法基本是“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3]。然而正是在这种并不算优越的地理环境中,越地百姓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将“原来的沼泽连绵、土地斥卤的穷僻之地,改造成湖泊棋布、土地沃衍的鱼米之乡;变上古以来的民风强悍、轻死锐兵的蛮夷之地,为文风鼎盛、名人荟萃、经济发达的文化之邦”[4]38。而这些变化正是在水文化的孕育之下逐渐形成的。
正如王建华先生所言:“无论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越地的文明史总是与水的治理史息息相关。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绕不开水的话题。一部越地文明史,从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如何与水环境共存并协调发展的历史”[4]22。绍兴历代关于水的碑刻包括了治水、驭水、护水、乐水、悟水等多方面的内容,此处我们仅以绍兴碑刻中与治水相关的明清碑刻为对象,考察越地治水思想的具体表现。
一、以禹为师、自强不息的精神
《史记》称越王句践为“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历代越国君主以禹后自称,绍兴会稽山为禹陵所在地,大禹陵自然成为后人凭吊先王、追忆功德的重要场所,历代在此修庙作祀,因而也留下了大量碑刻。现存较为著名的明清碑刻有《大禹陵庙碑》《禹陵重建窆石亭记》《重建绍兴大禹陵庙碑》等。
《大禹陵庙碑》全称《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清嘉庆五年(1800年)立,今在大禹陵景区禹王庙窆石亭旁,太湖石质,高205厘米,宽91厘米。碑首仿汉制晕首,有类于藏于西安碑林中的《仙人唐公房碑》形制,并在碑额下方中间凿浅孔模仿汉碑的碑穿①早期的碑,因穿绳綍的需要,会在碑身上中部凿圆洞,后人将这个洞称作“穿”,而碑的上部因绳綍摩擦会出现线痕。这些实用碑的特征,在刻字碑使用的东汉时期仍有所保留。即是如《仙人唐公房碑》《孔褒碑》的“穿”与“晕首”。,但碑座却是晋以后才广为流行的赑屃座,可以看出清人造碑时有意仿古,但未能尽合古意。碑额篆书“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3行10字,前2行各4字,第3行2字。碑文隶书,21行,满行33字,碑文记述了大禹得金简玉书、计功行赏、死后安葬之事,这些都与会稽山有关。其后,夏后帝少康之子无余,被封于会稽,以守禹祀。到了清嘉庆五年,大禹庙再次重修,浙江巡抚阮元来拜,颂扬大禹功德,后附四言颂诗。②有关本文所引碑文内容及介绍,皆参照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6卷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下文不备注。
同位于大禹陵窆石亭旁的还有《禹陵重建窆石亭记》碑,此碑立于明天顺六年(1462年)九月,太湖石质,高209厘米,宽88厘米,碑首高53厘米,两端刻云龙图案,中刻碑额“禹陵重建窆石亭记”篆书8字4行。正文楷书,25行,满行47字,正文四周亦刻绘祥云纹。碑文记述了彭谊由廷臣任绍兴知府后,拜谒大禹陵,见窆石亭因年久而倾覆,遂命重建,不久亭修成,府佐嘱乡贤韩阳撰文记之并立碑纪念。碑文的撰写者韩阳和书丹者曹南均是山阴人,曹南楷书深得唐楷三昧,风格介乎欧虞③唐初楷书大家欧阳询、虞世南的合称。之间。
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大禹治水神话广泛流传,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愿望。至于大禹治水成功的结果,则是海退以后,自然环境有所好转的客观反映。”[4]25
关于禹陵修整纪念的碑刻中还有一座民国时期的《重建绍兴大禹陵庙碑》,该碑现存于绍兴城东南大禹陵景区禹庙大殿东侧,太湖石质,高213厘米,宽100厘米,方首篆额“重建绍兴大禹陵庙碑”5行(“碑”字单列1行)。正文楷书19行,行37字,碑文记载民国建立以来,民智开启、移风易俗,各种祭祀活动逐渐被遗弃,惟祭孔与祭禹未歇的经过。然大禹庙因年久失修“渐”,民国十九年(1930年)冬,时任浙江省省长张载阳等提请重修,民国二十一年,由时任绍兴县县长汤日新主持修葺,历时16个月完工。文中对近代日本学界所称大禹治水为诬传的说法④碑文原话为“似东人以其国晚起,恶诸夏先进,则妄言治水为诬,尤清之欲宰中国则称岱宗为长白山支峰也。”进行了批判,认为“庙祀当与中国为废兴”。碑文指出,虽然重修禹庙的主持、督后、工程策划、礼制勘定者都是绍兴乡贤,是因为山陵处于越地,故越人从近而为,然而“后之功不局于一方,”且“苟中夏不灭,德广所及,桄于神州,百世莫得与比”。
此碑文中所述,不仅认为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不应遗忘,更将国人是否能够祭祀大禹作为国家兴废的象征。其中所涵盖的不仅是如何看待过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大禹精神的继承与否事关民族兴亡,这种大禹治水的精神就是于越百姓与自然抗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扩而广之,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二、防微杜渐、不忘忧患的意识
前文所述,越地早期的地貌环境与自然资源是较为恶劣的,后来经过历代先民的不断改造,终于变得逐渐适合生存,并越发富庶养民,但事实上,越地百姓始终都没能完全远离自然灾害的侵扰,尤其是水灾,一直是越地百姓挥之不去的阴影。从地方志和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找到“人相食”“溺死万人”“死者殆半”“饿死者十之八九”这种触目惊心的词句。“越地地理环境之危难万重,绝非今日一般人所想象总是风调雨顺、财富日积月累也易之情形;越地人民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曾经经历之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艰苦卓绝,由此亦可见一斑”[5]。也正是从这样的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一路走来,越地先民们积累了大量的治水经验,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应该是“防微杜渐、不忘忧患”的防治意识。
现存齐贤镇羊山石佛寺风景区《潮灾记》,是明崇祯三年所立的碑刻。会稽青石质,通高180厘米,宽85厘米,厚10厘米。碑首两侧钝圆,无碑额,仅在碑首处有16厘米宽的阴刻云鹤图案,碑身左右两边刻饰缠草文。正文楷书19行,行40字。碑文记述了崇祯元年(1628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受潮汐影响,风雨大作,堤溃洪虐,仅陶里一带,洪水就夺去了二百余人的性命的事情。逃过一难的幸存者因堤溃家破,处境艰难,多背井离乡。次年仲春,塘堤得以修复,逃离的百姓才陆续回归故土。该碑由里人俞应机撰文,江西安福县儒学训导俞应簠书丹,徐元刻石。碑文最后说道:“余谨陈辞,记之于石,使后人知我辰之潮患如此,与夫所以死中得生之故云。”可以说是对东南滨海之地的潮灾之患有着深刻的认识,故此立碑作铭以警示此后的历届继任者,勿忘水患,防治于未然。
历代水利工程督造不易,但随后常年的管理修整也至关重要,由现存有关清代三江闸修造的两块碑《重修三江闸碑》和《重修三江闸记》可以看出越地治水防微杜渐的意识。
《重修三江闸碑》立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碑额已佚,碑身为太湖石质,高188厘米,宽87厘米,碑文阴刻楷书23行,满行60字。碑文记述自明代汤绍恩肇建三江闸,后历任官员多有维修整治,“历有成规”,而时迁日久,到了清代乾隆末年,已“罅漏滋深”,乾隆六十年(1795年),浙江巡抚觉罗吉庆下令重修三江闸,耗时一月半有余,费资“缗钱九千八百有奇”,于是三江闸复还旧观,民亦安居乐业。
《重修三江闸记》立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青石质,高210厘米,宽81厘米。碑首方形,高42厘米,上雕二龙戏珠图案,中间龙珠内雕变体“寿”字,无碑额。正文楷书20行,行50字,首行竖刻碑名“重修三江闸记”,碑原在三江闸东南侧彩凤山西麓,现移至绍兴城区治水纪念馆内。碑刻文字近于柳体,用笔骨力强直,结体端稳,是清代较为出色的楷书碑刻。碑文记述古今治水有蓄泄二途,绍兴滨海,故水“易泄而难蓄”,并举古人治水用两法为例,东汉马臻蓄水源而为镜湖(鉴湖),虽有灌溉蓄洪之利,却因湖塘淤积难免“时有修筑之烦”①因湖塘淤积,加之围湖造田等原因,镜湖在宋以后的防洪治水功能逐渐退化。详见曾巩《序越州鉴湖图》,见中华书局1989年《四部备要》第75册115页,《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十三;而明代汤绍恩修筑三江闸,使得“三县之田,皆成沃壤”。可见撰文者是崇泄而否蓄的治水态度,三江闸虽好,但到了清道光年间,也因年久渗漏而防洪治水的功能日渐退化。时任绍兴知府的周仲墀召集三县士绅议修,用“网灰”法、“铅锡熔汁”法、“雁翅槛砌梭墩版鐶”法等修缮了三江闸,使之重新发挥了治水利民的功能。
以上两碑虽时隔仅40年,但分别立碑讲述过往,并记录当下所为,其目的除了有为现任记功外,也应包含了提醒后继者重视水利维护,护民于水患之外的意思在内。
三、取法于道、希冀长治久安的理想
有了治水的决心与自信,有了防微杜渐的意识,并不能保证治水效果,取法于道,才能长治久安。因为治水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中既有人财力投入和严格的监管,首要的还需有正确的治水方法,否则,如宋以后出现的鉴湖围湖造田之类为了一时之繁荣而损坏长远的发展的做法,可能令前人的辛劳与智慧付之东流。在这一点上,明清时期,绍兴地方官的一些远见卓识还是令人钦佩的,如明成化年间记述知府戴琥开设新闸的《山阴县新闸记》碑,和清康熙年间记载知府胡以涣捐献田产作为修复水利设施的常规收入来源的《捐俸置田添造三江应宿闸每岁闸板铁环碑记》颇具代表性,以下略作介绍。
《山阴县新闸记》碑,明成化十二年立,现存大禹陵碑廊。太湖石质、高190厘米,宽79厘米,碑额高40厘米,中刻篆文碑额“山阴县新闸记”6字2行,字外两侧刻云纹。正文楷书,21行,行52字,记述东汉马臻始筑鉴湖、宋代建斗门八所,民得其利,到宋熙宁后,围湖造田的百姓日多,以至“湖几废”,继而“萧山矶堰废”,郡中百姓又有“浸淫之患”的事情。而明天顺年间修筑的白马闸,本为解决灌溉之水源,却不料结果是“江愈浅”,因而时有暴涨之水患,冲决塘堤,水退之后,府县又需募工重修,扰乱百姓农务,导致了“民尤受弊”的反面结果。
成化十年,戴琥任绍兴知府,他以“兴利除害”为己任,“相地之宜。顺水于小江南北建闸四所,曰:新灶、柘林、扁拖、夹缝”,以泄山会二县之水。又在萧山建龛山斗门一所,以杀西水,工期历时年余。碑文先对鉴湖在宋代熙宁后被围湖造田所废,以及成化年间新修白马闸后百姓反受其害的反面教材做了批判,其后又对新开河闸的位置选择和功能规划做了介绍,将正反两面都展示给后人,警醒后来者治水不能仅顾眼前之利,亦不能只凭良好的初衷,必须有法有道,才能永利于民。
《捐俸置田添造三江应宿闸每岁闸板铁环碑记》现存绍兴城区治水纪念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月立,碑额已佚,碑身太湖石质,高192厘米,宽84.5厘米。碑文楷书阴刻,共分六段,每段满为24竖行,前五段记述了康熙十七年以来,因地方政府经费支绌,三江闸朽坏的闸板、铁环无法及时更换,已险象环生,知府胡以涣深以为虑,于是捐俸置田二十亩,同时山阴知县高起龙、萧山知县刘俨也各自捐俸置田五亩,将田产所得作为每年“缮补闸板、铁环之资”的事情。
从碑文内容可知,所载之事并不甚大,仅是父母官捐资修缮治水设施的一般善政,而此事却被镌刻于石碑,是否有些夸张,又或是地方官为己歌功颂德的贪名之举呢?实则不然,据《嘉庆山阴县志》所载,胡以涣于就任绍兴知府的第二年就曾“种万松于兴龙山上,一时远近作诗纪其盛”,足见其为官政绩不俗,而捐俸置田以田租作为修缮治水设备的经费来源,尤可看出其于善政之外,更重视政策发挥利民作用的持续性,设想如果仅是捐银维修,而此后年深日久,设施又将有朽坏之虞,因此他在碑中所言:“居民上者,安可不急为善后之谋乎?”胡以涣在捐俸置田之后立碑,并在碑文中明确规定了修缮标准:“板必本山松,厚四寸,阔倍之;环必福建铁,重十二两方为坚久,一遵旧式为之。”又规定所入多余部分,用以修汤公祠,以及给予闸工奖金,以促其勤,等等。归根到底只是一句话:“庶几旱涝各得其宜,有水之利而无水之害,于先贤之遗泽不无小补云尔。”可以说该碑正是绍兴地方官吏关注民生、希冀长治久安的实物记录,集中体现了绍兴碑刻治水保民的文化特征。
以上略举数碑,已能看出,明清时期绍兴有关治水的碑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于越文化中与治水相关的文化内涵尤其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于今日越人如何看待人与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林华东.浙江通史·史前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2][春秋]管仲.管子·水地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9:211.
[3][东汉]袁康著,吴平等译注.越绝书全译:卷八[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63.
[4]王建华.鉴湖水系与越地文明[M]//越文化与水环境国际研讨会组委会编.越文化与水环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潘承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0.
Analysis of Ideal of Yue Flood Control on Inscrip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Xiaoliang
(Lanting School of Calligraphy,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Zhejiang,312000)
Shaoxing is the core birthplace of the Yue culture,still embracing many tablet inscriptions which bear a historic literature value and cultural research value.The inscriptions regarding Shaoxing's flood control have more promine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value.Examining a few listed stone inscriptions,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nscriptions on flood control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pitomize Shaoxing people's(under the leadership of Yu the Great)flood control ideal that takes precautions against every possible leak,tiny or great,at the outset in the hope of a long period of stability.
Shaoxing;the Yue region;tablet inscription;flood control
G127
A
1008-293X(2015)05-0017-04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5.05.04
(责任编辑 张玲玲)
2015-07-25
本文为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基地重点课题“绍兴碑刻文化研究”(14JDYW01Z)的阶段性成果。
王晓亮(1981-),男,安徽阜阳人,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讲师,美术学(书法)博士,文艺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