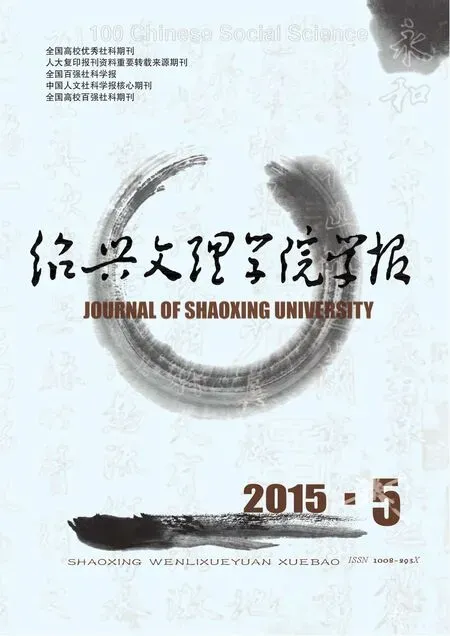重新发现风景
——论浙籍文人对“雷峰塔倒掉”事件的文学书写
陈丽军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241)
重新发现风景
——论浙籍文人对“雷峰塔倒掉”事件的文学书写
陈丽军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241)
风景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美,更具有文化的意义。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的风景颇具革命性的发现竟然始于“死亡”。一次偶然的“雷峰塔倒掉事件”使得“陈旧之物”重新显现。徐志摩、刘大白、鲁迅生于吴越、长于吴越,分享共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景观,但他们笔下的雷峰塔却极具个性和创造性。对于徐志摩而言,雷峰塔是爱与美的梦幻的化身;对于刘大白而言,雷峰塔与地域文化紧紧相连,如同阴阳,如同冷暖,如果说吴越文化是女性的,雷峰塔便透着阳刚的力量,“雷峰塔的倒掉”导致了吴越文化中英雄气质的缺失;对于鲁迅而言,雷峰塔腐朽、罪恶、带着过去时代陈旧的印记,是他所憎恨和批评的,于是,雷峰塔的倒掉也便预示着一种希望、一种新生的可能。
浙籍文人;雷峰塔;风景;重新发现;文学书写
引言
提到“风景”这个词,大多数人对其意义的了解源于字典,即“一定地域内由山水、花草、树木、建筑物以及某些自然现象(如雨、雪)形成的可供人观赏的景象”[1]329。从这个定义衍伸开去,便是一直以来美学领域对于“风景”的认知:“风景”属于一种客观的美,而观赏者作为外在的主体而存在。近几年,随着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诞生》、温迪·J达比的《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以及米切尔编选的论文集《风景与权力》等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中国文学研究界仿佛突然意识到“风景”另外的意义,“风景”不仅与美相关,同时也被意识形态所建构。或者换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而言,一方面,通过对世界的改造活动,人类将自己的情感、想象和风俗文化投射在“风景”上;另一方面,“风景”的存在丰富、甚至形成了人类对自身身份、记忆、历史的确认。这似乎又成了一个借助西方知识来实现我们本土观念突破的例证。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重返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在20世纪初,“五四”一代作家们眼中的“风景”已经离开了古典文学传统,具有了新的面貌。它不再仅仅与情感相关,而成为了某种现代精神,乃至文化的象征物。
本文围绕90年前的“雷峰塔倒掉”事件,以三位浙籍文人徐志摩①徐志摩(1897~1931),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现代诗人、散文家。、刘大白②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棪,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别号白屋。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好友。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史家。、鲁迅③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文学书写为例,来看一种故乡“风景”的消失引发了他们怎样不同的情感反应和文化想象,以及他们如何用文学来表现这种“震惊”体验。据记载,雷峰塔始建于五代北宋时期,因“雷峰夕照”的美景闻名于世。从南宋起,就常有文人墨客赋诗咏唱,或慨叹历史,或描摹美景,抒己之情;而在普罗大众中间,因雷峰塔而起的白蛇传说更是传播甚广。雷峰塔已经成为民族生活,乃至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人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或者说对它的审美想象定型化了。如果没有雷峰塔的倒掉,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古塔也并不会引起新文化人特别的关注,“死亡”事件,使得这陈旧之物重新显现。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徐志摩、刘大白、鲁迅生于吴越、长于吴越,分享共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景观,但他们笔下的雷峰塔却极具个性和创造性。对于徐志摩而言,雷峰塔是爱与美的梦幻的化身;对于刘大白而言,雷峰塔与地域文化紧紧相连,如同阴阳,如同冷暖,如果说吴越文化是女性的,雷峰塔便透着阳刚的力量,“雷峰塔的倒掉”在他那里意味着吴越文化中英雄气质的缺失;而对于鲁迅而言,雷峰塔腐朽、罪恶、带着过去时代陈旧的印记,这是他所憎恨和批评的,于是,雷峰塔的倒掉便预示着一种希望、一种新生的可能。
一
1924年9月25日下午,西湖名胜古迹雷峰塔轰然倒塌。两个月后,徐志摩在一篇介绍济慈及其《夜莺歌》的文章中说,“在我们南方,古迹而兼是艺术品的,止淘成了西湖上一座孤单的雷峰塔,这千百年来雷峰塔的文学还不曾见面,雷峰塔的映影已经永别了波心!也许我们的灵性是麻皮做的,木屑做的,要不然这时代普遍的苦痛与烦恼的呼声还不是最富灵感的天然音乐。”[2]479虽然短短数语,只是闲出一笔,但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刚刚发生的“雷峰塔倒掉事件”在他内心产生的震动。在他那里,“雷峰夕照”不是自然景观,而是“最富灵感的天然的音乐”,塔影与艺术相通,能唤醒人们荒芜已久的灵性。以前,批评家们在肯定徐志摩早期的白话诗创作时,往往注意到《雪花的欢乐》《破庙》《毒药》《婴儿》等诗篇,而忽视他的雷峰塔组诗。如果我们仔细地梳理和阅读后,就会发现,诗人和雷峰塔的精神联系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徐志摩在杭州读府中时,就常常去西湖边。从《府中日记》中可以看到,自1911年正月二十六到二月初八,除雨天和生病外,几乎每日都要去西湖游玩,要么拍照,要么划船,虽然没有文章记载当时他去过雷峰塔,但在西湖畅游,想来对于“雷峰夕照”应该并不陌生。徐志摩的笔下首次出现“雷峰塔”,要到1923年的《西湖记》,阳历9月29日的日记,补记与家人中秋节赏游雷峰塔的经历:第一次是远远看着,“那时我们便在三个印月潭和一座雷峰塔的媚影中做一个小鬼,做一个永远不上岸的小鬼,都愿意,都愿意!”[3]156-157下一天他们走近了雷峰塔,“我从不曾去过,这塔的形与色与地位,真有说不出的神秘的庄严与美,塔里面四大根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看着危险极了。”[3]157当时,轿夫还给他们指点白状元和白娘娘的坟。有人握着一丈余长的蛇,叫着放生,说是小青蛇,徐志摩掏了两角钱,看着那人将蛇扔到了荷花池中。“月下雷峰”“塔身形色”“白蛇传说”,这些正是容易打动和启发艺术家灵性的东西。一次夜间远眺,一次白日近观;对应这两次观雷峰塔的经验,徐志摩写下了两首诗歌,一首写于1923年9月26日,题名为《月下雷峰影片》,收入《志摩的诗》,一首写于返程途中,用杭州白话将白蛇的民间传说演绎了一番,发表时,题名为《雷峰塔》。表面看来,这两首诗截然不同,前者写景抒情,后者叙事为主;但实际上却共同指向了诗人的精神世界,诗人所崇尚的信念,一种对风景、纯粹爱情的绝对信赖。如果说沈从文通过湘西风物人情建构了一个躲避现代化城市的港湾,那么徐志摩便是利用自然和爱情树立了一种宗教。
《月下雷峰影片》中,第一节便是“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我”给“你”的不是金山银山,不是许诺和誓言,而是美丽的“雷峰塔影”“黑云与白云”“明月”以及“波心”。这些景物不光隐喻了诗人超凡脱俗的情感,而且景物的空灵、轻盈,造出了一个颇具宁静和清淡的空间。王国维曾认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4]30这段评语用来评价徐志摩也很合适。他是主观的诗人,能够沉浸于个体想象之世界,看到自然的艺术价值。在他那里,雷峰塔影已经不是自然景色,而是美的外在显现,是一个“完全的梦境”。是的,梦境,却指向世界之真。在另一篇名为《话》的散文中,徐志摩认为能够抵达世界之真的只有两种话语。
一种是诗人的梦话,“至于相对的可听的话,我说大概都在偶然的低声细语中:例如真诗人梦境最深——诗人们除了做梦再没有正当的职业——神魂远在祥云缥缈之间那时候随意吐露出来的零句断片。”[2]95虽然诗人的想象、神思看起来虚无缥缈,但超越了生活的表象,更接近存在的真实。这一点可能与徐志摩受印度诗哲泰戈尔的影响有关,诗歌和哲学在面对世界隐藏的真相时是相通的。
另一种是自然,“真伟大的消息都蕴伏在万事万物的本体里,要听真值得一听的话……现放在我们面前的两位大教授,不是别的,就是生活本体与大自然。生命的现象,就是一个伟大不过的神秘:墙角的草兰,岩石上的苔藓,北冰洋冰天雪地里的极熊水獭,城河边咶咶叫夜的水蛙,赤道上火焰似沙漠里的爬虫,乃至于弥漫在大气中的霉菌,大海底最微妙的生物;总之太阳热照到或能透到的地域,就有生命现象”[2]97-98。徐志摩是不信仰讲坛的演说,伟人的训导的。他相信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去观察和领悟自然的奥妙。这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分割,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人们已经发现了万物与人世的隐喻关系。
胡适曾经对徐志摩有过一个判断,说他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其中包括三个大字:一是自由,二是美,三是爱。如果说《月下雷峰片影》写的是自然之美,那么《雷峰塔》写的便是刻骨铭心的爱。《雷峰塔》以一个船夫的讲述,描绘了白娘娘“多情”的形象,这种“多情”在船夫和诗人看来是西湖上的佳话,然而因为情夫的糊涂,白娘娘被镇压在了雷锋塔下,距今已经一千年,漫长的时间和孤守的代价,本来最先让读者感觉到的是一个爱情的悲剧,但也正因为这无涯的时间倒更显出白娘娘对爱情的忠贞和永恒。雷峰塔的存在便是一个见证。联系这一时期徐志摩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想到,这似乎写的是诗人自己的心境。当时,他爱上了林徽因,不顾一切地要摆脱旧式的婚姻,与妻子张幼仪登报离婚,弄得沸沸扬扬。对徐志摩而言,这场爱情的追求中,要跨过的障碍,所受到的指责,并不亚于白娘娘与许仙之间的人妖之恋。梁实秋说,徐志摩一生所信仰的只有一个,那便是对“美妇人的追求”“浪漫的爱”。这怕是抓住了其精神的要害。徐志摩曾创造过“海砂上种花的孩子”的形象,海砂上种花,成年人知道那一定白费力气,无法成活的,然而孩子并不想这些,他只是觉得花很可爱,希望这可爱的花永远生长下去。徐志摩那“浪漫的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别人看来他活在梦境之中,他自己却并没觉得怎样,反而陶醉在爱的美好之中。
从上述两首诗以及《济慈的夜莺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除了发现雷峰塔本身具有的自然的艺术美之外,还展示了一曲爱的颂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可以触摸到徐志摩早期诗作弥漫的一种气质——单纯。然而在雷峰塔倒掉一年后,徐志摩又写了一首纪念的诗作《再不见雷峰塔》,情感却转为悲凉、激愤,已全然不见当年那两首诗中空灵、轻盈的柔美。开头一句“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大荒冢”的意象是荒凉的,没有了“团团的月影”,没有了“依依的塔影”,王子童话的世界坍塌,风月飘走,惟留寂寞。我们前面提到过徐志摩是一个主观的诗人,其诗歌的情调受制于个体的心境。1925年9月写作《再不见雷峰塔》时,徐志摩已经不是刚刚游学回国,志得意满,心存爱恋的纯情才俊,一方面他遭受了失恋的苦痛,与前妻所生儿子的死亡,以及重陷追求陆小曼的爱情困局;另一方面,社会也在巨变,五卅惨案给他的震动很大,他似乎在重新思考原先纯洁的信仰。这一切都能从《再不见雷峰塔》中体会得到。在诗中,诗人不断发出质问,雷峰塔的倒掉本是光阴流逝中必然的结果,为什么自己还要感慨?世上连爱情都不能永久呢,何况还有更多值得关心的事,比如那些“不应分的变态”。在诗尾给出了答案,“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雷峰塔象征了自己过去所有的寄托和美好,而如今就像雷峰塔的倒塌,掩盖的不止白娘娘爱情的传说,还有自我的历史和记忆。
二
1925年4月26日,雷峰塔倒掉的第二年,刘大白写下了长文《雷峰塔倒后》,此文发表于复旦大学校内刊物《复旦》杂志,当时,刘大白正在该校的文学院任教。从结构上来看,《雷峰塔倒后》一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列举驳斥迷信家、抱打不平者、古董收藏家等几类人对“雷峰塔倒掉”的言说和反应后,提出一个问题,“我呢,雷峰塔倒后的我呢”,“我”作为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记忆和经验的主体,又如何面对这一风景的消失,或者说于“我”而言,“雷峰塔倒掉”意味着什么?第二部分主要书写其记忆中的雷峰塔,在别人那里印象最深的是雷峰夕照,刘大白却能发现另外的美。他用抒情细腻的笔触,回忆20年前常去的三家茶店,一家叫藕香居,另一家是三雅园,还有一家名为仙乐园。重要的不是茶店的名气,而是坐在仙乐茶园一角,欣赏窗外美景的惬意,那真是赏景的绝佳位置啊,能将全湖景物尽收眼底,其中就有这雷峰塔。雷峰夕照也有,不过刘大白并不特别在意,他看到的是左边的保俶塔,右边的雷峰塔,一瘦一肥,各具美感。这种参差的美,就仿佛一个是玲珑的美人,一个是经过沙场的英雄。尤其让刘大白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偶遇,半雨半晴的天,他路过那里,一眼看到从保俶塔那里伸出一道云桥,一直伸到雷峰塔那里,并将其紧紧围住。那一刻,刘大白陶醉在那浓浓的虚幻的恋人情意之中了。而现在雷峰塔倒掉后,留下寂寞的恋人,形单影只。浪漫的爱情成为了一曲哀歌。这是诗人之眼的发现,能让别人那里的陈词滥调,千篇一律的景色,焕发出新的动人的美,但这还仅仅是个人记忆的描述而已,并没有深入到对于文化的思考。本文看重的是《雷峰塔倒后》的第三部分,正是这一部分,刘大白突破了自我经验的限制,将雷峰塔与浙江地域文化精神相沟通。
徐志摩虽生在浙江,但因天性浪漫,早年又游学欧美,与曼斯菲尔德、狄更斯等等名作家交游甚广,使其对诗人身份的认同远甚于其它文化身份。而作为绍兴人的刘大白,从其青年时代起,就与浙江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无法分开,除因反对袁世凯曾短期赴日本避难,以及1924到1927年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外,他的大半生为浙江的改变而奋斗。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方面,他与浙籍文化人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处于一条战线,著述作文,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刘大白又不仅仅限于文字上的鼓动,同时也注重事功,从绍兴师范学堂教员到《绍兴公报》编辑,从浙江一师学潮的引领者到浙江教育厅官员,将现代的理念和理想付诸故乡的变革。有很多研究者,将刘大白的历史地位定位在新诗的实验之上,这种结论,只看到了其作为现代文人的一面,从某种程度上,刘大白并不仅仅认同其文人的身份,作为清醒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人生选择与胡适、蔡元培保持着精神上的相通,兼具新文人和实干家的角色。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我们从其《雷峰塔倒后》一文就能够感受到。
在他看来,西湖的山“连绵委宛”,西湖的水“妥贴温存”,她整个的气质是女性的;这是西湖山水的美,也是她的单调和局限。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法兰德斯人的气质的确是在富足的生活与饱和水汽的自然界中养成的:例如冷静的性格,有规律的习惯,心情脾气的安定,稳健的人生观,永远知足,喜欢过安宁的生活,讲究清洁和舒服。”[5]57这种观点移至中国地域文化,也同样实用。越地山水的气象影响生活在其怀抱中人们的文化性格,所以杭州人的性情也是柔软的,就连生活在杭州的“寓公”也变得柔弱了。刘大白对于这种单一的文化性格是不满的,于是“雷峰塔”成了其想象中阳刚的男性文化气质的象征。
为什么刘大白会如此强调“阳刚”气质呢?这不能不提到五四一代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能够成功,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这些前驱者激进的革新精神。鲁迅曾感叹,“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6]171中国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这种文化状态利弊并存,好的方面来说,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会产生一种向心力和认同感;但同时也造就了另一层障碍,一种革新力量成长时阻力重重。正是出于这种历史文化的认知,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就呼唤革新者的“摩罗精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彻底的激进意识已经成为一大批文人所拥护的价值标准,尤其是浙籍文人团体。
刘大白将雷峰塔代表的英雄气质视为杭州人的另一种文化性格,这既是时代赋予他的意识,也是他自身的体验和观察的结果,突破了前人关于南方文化的刻板印象。早在《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区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地域风景与人情的关系。然而,一直到刘师培,还沿用历史上的看法,集中在讨论南北文化的整体性差异,“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主体。”[7]84此种思路到了当代转变为地域文学研究和城市文学研究,人们在谈论这些论题时,也没有脱离这种预设的框架。此框架的弊病在突出南北的地理和人文的差异时,却往往忽视南北各自内部构成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值得一提的是,无独有偶,同为浙籍文人的周作人也曾谈论过本地文化的问题,不过他集中在文艺方面的潮流,认为“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8]102飘逸与深刻,虽然是对浙江文艺特点的概括,但周作人用了两种人作比喻,一种是名士清谈,一种是老吏下笔,如果在现实中找对应,倒恰恰像以名士风度著称的郁达夫与被称为绍兴师爷的鲁迅。柔美、清丽与深刻、厚重,与刘大白对于杭州文化性格的判断很相似。从90年代起,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出版了众多的成果,影响较大的是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些研究在突出地域文化某些特点时,又压抑了另外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大白以雷峰塔为例,对杭州文化相辅相成的论述道明了中国地域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也由此为我们批判性地思考当前的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三
在我所考察的三位文人中,鲁迅的雷峰塔书写可能是最为人所知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来与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相关;二者《论雷峰塔的倒掉》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的重要课文。1924年10月28日,在雷峰塔倒塌后一月左右,鲁迅写下了《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文章无论情感基调还是文化抱负,都与徐志摩、刘大白的书写不同。在鲁迅眼里,雷峰塔并不是什么值得怀念和惋惜的美景。“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6]179这种否定性的情感构成了文章整体的批判立场。
如果仔细分析,《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否定性情感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发泄,而是出于更为久远的个人记忆。“我”对雷峰塔及雷峰夕照没有好感,起于幼年时祖母常常讲的白蛇传说,而且每次祖母总要指着那塔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6]179在白蛇传说的衍变史中,有很多个版本,最初起于南宋。明人吴从先《小窗自记》当是较完整的记载。“白蛇传后来形成一个相当充实而完整的故事,当推宋代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由明末冯梦龙编在《警世通言》中)。在那里,白蛇已经以白娘子的形象出现。但是,白娘子作为一个可怕蛇怪这一基本特点不但没有改变,而且由于作者的着意渲染,白娘子要比原先的蛇怪更令人憎厌。她缠住许宣不放,完全是为了满足她的情欲。”[9]144在这一系统里,白蛇是作为被警惕的形象出现的。而鲁迅的祖母所讲述的白蛇故事,据他回忆是来自清代陈遇亁的《义妖传》,这是另外一个系统,虽然还是以白蛇为主,但形象大变,已经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而法海则转化为多管闲事、无事生非的恶人。在儿童的认知中,虚构的故事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镇压白蛇娘娘的雷峰塔成了情感的投射物。于是,“我那时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6]179。
如果说童年的“我”,对于雷峰塔的“憎恨”是出于无法区分故事的虚构性,那为什么后来从书中得知雷峰塔为钱王的儿子建造,内心还是不舒服,希望塔倒掉呢?这与鲁迅追求个体自由的价值趋向无法分开。虽然白蛇传说是虚构的,但它却指涉到人间的问题,一个新文化运动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这是个体自由在伦理学领域的实现,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价值”中很重要一部分。“雷峰塔”不经意已经发生了转化,从镇压“白娘娘”的物体变成了礼教的象征。实际上,在大革命之前,鲁迅作品中同样的主题就不时闪现,比如《祝福》里祥林嫂的悲剧、《伤逝》中子君的死亡等等。在鲁迅一类的新文化人士的观念中,那些造成婚姻悲剧的个人性格被轻易地忽略或被淡化,而重点突出外在的社会及文化的压制。
1925年2月6日,鲁迅又写下了另一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虽然写作的对象还是“雷峰塔倒掉”事件,但此文与《论雷峰塔的倒掉》相比,其思想已经超越了五四新文化反礼教的主潮,而具有了个人的风格,属于国民性批判的范畴。从最初的起源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始于鲁迅偶然在2月份《京报副刊》读到的胡崇轩的通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胡文只是一个由头,鲁迅在意的是胡文中的一段谈话,“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6]201他由此生发,批判两个相连的问题。
一个是游客叹息“西湖十景”要缺一景了。在游客看来惋惜的事,鲁迅在文中却反其道而“有点畅快了”。他将游客言语背后的文化病灶展现出来,具体而言,就是几乎成为四万万同胞潜意识的“十景病”,不仅景色凑足十,点心要十锦,菜要十碗,音乐要十番,就连罪状也要十条。这种无意义的凑数,在鲁迅看来,怕是一种虚幻的完满,一种假的东西。现在,这种假的完满终于被破坏了,鲁迅的畅快便来源于此,但很快又觉得悲哀起来,因为民族的心理不会那么容易变化的,十景变九景后,未来总会有人再重建雷峰塔。这是鲁迅看待风景的方式,在这里,你看不到抒情,听不到惋惜,能领悟到的是入木三分的剖析,对你我灵魂的剖析。也因为他的这种文化批评,我们得以重新反思自身习以为常的观念。观念从自身出发,却指向整个民族灵魂,指向历史深处。
另一个是辨别“破坏者”的意义,以及探寻谁才是真正的“破坏者”?“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6]202这是很意味深长的话。文化要革新,要进步,破坏是第一位的。但在鲁迅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破坏者都具有革新的力量,所以他区分出三类破坏者:第一类是鲁迅一直呼唤的摩罗诗人,内心有理想之光者。鲁迅在1907年写过《摩罗诗力说》,其中有个主要的观点,中国文化要革新,缺乏的是摩罗精神的英雄人物。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孔子倒是有创新的精神,当人人崇鬼时,他能不妄谈鬼神;然而,孔子也终究是世故的,不敢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于是,最后成了圣人。“十景病”便在这样的文化偏向中得以生生不息。第二类破坏者是侵略者。像夷狄,像长毛,这类破坏者有破坏的胆量,也能够起到破坏的作用,但往往只有破坏,不能建设。因为他们志在掠夺,而非革除,所以经过这些倒扣式的洗劫后,只能留下瓦砾,并不会有什么新的气象。第三类破坏者便是如盗取雷峰塔墙砖的乡民,仅因蝇头小利,便去破坏,人数多,破坏自然极大,属于奴才式的破坏者。此类破坏者因身处的文化而产生,可能是四万万同胞中的任何一员,如同那“吃人”的人。鲁迅通过此类破坏者指向历史更深处的文化。
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开启了中国文化批评的滥觞,“如果从《科学史教篇》以及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读起,就不难理解‘不读中国书’包含的对于传统知识谱系的怀疑和拒绝;而这种怀疑和拒绝是和鲁迅对于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谱系中,嗅到了一种死亡和灭亡的气息。”[10]175鲁迅的文化批评并不局限在知识分子或是某个群体的文化,而是渗透在一切中国的人、事、物中,尤其那些带着历史气息的东西,往往能被他解剖刀般的敏锐思维捕捉到其中的不合理,然后加以分析和展露。
在鲁迅这里,风景的关照更像是一个由头,他总是能够由此生发,深入其文化层面。在现象的表面下,发掘更为深刻的东西。正如批评家张闳在答《钱江晚报》记者问时,重新提到鲁迅的这两篇雷峰塔书写的文章所言,“作为景观的雷峰塔乃至整个西湖风景区,也是传统的景观美学的集大成者。它们的残缺,符合鲁迅整体性反传统的立场。再者,西湖景观美学上的完满性,在鲁迅看来,乃是一个幻觉,实际上它们早已被蛀蚀一空,其背后是‘奴才式’的政治文化。雷峰塔倒掉只不过是这一政治文化的恶果,暴露出了那些华丽美景的真相。”[11]88-89
结论
对于生于我们之前的事物,尤其那种融入到民族个体生命、记忆之中的历史风景,总是容易让人产生永恒的错觉。但如果有一天,它突然从眼前消失,对人们心灵的震撼足以产生重新发掘其意义的动力。死亡带来的是一种重生。写作者凝视废墟,于是,新的风景诞生。雷峰塔作为西湖十景之一,千百年来被人们观赏,它矗立在那里,却是毫无风格的存在,人们走过,又视而不见。如果没有倒塌这样的事件,就算再敏锐的作家,对它怀有再深厚的情感,也很难对它有所发现。站在一堆的瓦砾前,浙籍文人徐志摩、刘大白以及鲁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重新赋予雷峰塔以生命与意义,无论是爱与美的象征,还是作为新的地域精神的想象,抑或成为旧文化的代表,在经过这些新文化运动前驱们重塑后,具有了文化革新的力量。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一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徐志摩.徐志摩未刊日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王国维.人间词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5][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M]//程千帆.文论十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8]周作人.地方与文艺[M]//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叶凡.《论雷峰塔的倒掉》的奇笔[J].上海鲁迅研究,2001,冬季卷.
[10]殷国明.鲁迅与中国文化批评的滥觞——鲁迅早期杂文的阅读札记[J].社会科学,2011(2).
[11]张闳.关于《论雷峰塔的倒掉》答记者问[J].上海采风,2015(3).
Rediscovering Landscape——On Writing of"Leifeng Pagoda Collapsing Incident" by Writers from Zhejiang Province
Chen Li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Landscape is both of objective beauty and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This revolutionary concept of landscape in daily life originated from"death".An accidental"Leifeng Pagoda collapsing incident"brought new life to the"antiquity".Xu Zhimo,Liu Dabai and Lu Xun were all born in the Wu-Yue district.They share common geographical,cultural and historical sights,but they describe the Leifeng Pagoda with their own 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To Xu Zhimo,the Pagoda is a dream of love and beauty.To Liu Dabai,the Pagoda and regional culture are closely linked as yin and yang;if Wu-Yue culture is compared to a woman,the Pagoda has a masculine force;"the collapse of the Pagoda"leads to the absence of heroic qualities of the Wu-Yue culture.To Lu Xun,the Pagoda,which he hates and criticizes,is corrupt and evil with the imprint of an old era;its collapse indicates the chance of a new and hopeful future.
literateur of Zhejiang province;the Leifeng Pagoda;landscape;rediscovery;literary works
I206.6
A
1008-293X(2015)05-0001-07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5.05.01
(责任编辑 张玲玲)
2015-07-2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文化语境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12BZW018)的阶段性成果。
陈丽军(1982-),男,山西忻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2013-2014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