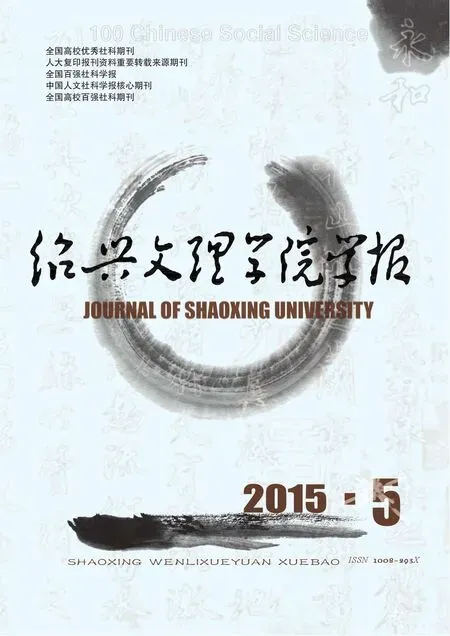从毛泽东对鲁迅形象的建构谈文学与政治
陈若晖 李广益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401331)
从毛泽东对鲁迅形象的建构谈文学与政治
陈若晖 李广益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401331)
没有人如鲁迅一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过如此浓墨重彩的痕迹,也没有人如鲁迅一般身上交织着文学与政治纷繁错杂的关系。从毛泽东的《论鲁迅》《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鲁迅在中国文坛上不容质疑的地位便逐渐形成,并愈发显示出一种与意识形态交相辉映的局面。此文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论述鲁迅的几部文本出发来讨论其对鲁迅形象的建构,从而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鲁迅形象;毛泽东;文学;政治
一、重塑:毛泽东对鲁迅形象的建构
鲁迅生前一直处于文坛论争的中心,树敌过多,得不到文坛多半的认可、也不可能得到认可。但他死后,悼念之文却铺天盖地袭来,不论是他的友人,还是他的论敌都来缅怀,似乎终于都认可了鲁迅在中国文坛的核心地位。竹内好[1]认为是鲁迅之死完成了文坛的统一,而事实上也正是鲁迅之死完成了中国文坛对鲁迅的神化。鲁迅死后,一切与他有关的争论都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褒奖之议和缅怀之音。不论是发自内心,还是做做样子,他们的赞扬和缅怀都使得鲁迅形象一步步得以神化。因此或许又应该说,是一代代人对死后鲁迅形象的建构成就了文坛的统一,这种形象在一步步建构的过程中,被不断神化、政治化、权威化,或许是连鲁迅本人也不愿看到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又不得不提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相关文章对鲁迅的评价。
毛泽东在1937年10月于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来被人整理成《论鲁迅》一文。该文明确地指出,“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2]9,强调的是“中国革命史”,而不是“中国文学史”。由此可见,毛更注重的是鲁迅在革命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而“革命”也成为了毛所建构的鲁迅形象中,比“文学”更为重要的所在。毛在该文中将鲁迅称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并总结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以及牺牲精神。但很显然,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甚至一等圣人的地位都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远见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看清了政治的方向”,才能“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从而“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2]10。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出了“鲁迅的方向”——“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2]16、“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2]15。不丧失自己的立场便是鲁迅的方向,那么自己的立场又是什么?前文提到,鲁迅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因此这一方向似乎就代表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大前提、中国革命的大方向之上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立场。但毛始终没有正面解释“鲁迅的方向”到底指向的是一种怎样的方向,而这种方向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则直接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划上了等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再一次提到了“鲁迅的方向”,称其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这一“新文化”,则直接指向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基础之上,而并非是单纯的文化及文学本身,坚持的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立场。由此,“鲁迅的方向”成为了一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一种政治纲领统领下的文化的方向,甚至是一种“毛泽东的方向”。
而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毛泽东再次将鲁迅拔高到无上的地位——“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有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是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2]31。而另一方面,毛对鲁迅“三个伟大”的论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奠定了之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对鲁迅评价的基调,成为之后几代人走进鲁迅、接受鲁迅时最直接的印象。而中国文学界多年来也正是以此来作为评价鲁迅的标准的。汪晖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中说得很对:“鲁迅形象是被中国政治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那以后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权威的要求成为鲁迅研究的最后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也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3],从而使鲁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某种先定的“神圣”或“绝对”的论证,斩断了鲁迅精神与生活的深刻批判性联系,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
由此可见,毛对鲁迅形象的建构是建立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之下的,尽管毛称鲁迅为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与思想家,但更看重的明显是鲁迅的“革命家”的身份,构建最多的也是鲁迅的“革命家”身份——“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等等。这种革命家身份的建构,正如汪晖所说,为的是树立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权威,带有浓重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气息。而正是这种明确现实目的的需求和限制,使得毛泽东对鲁迅形象的建构必然产生选择性与偏差性。
二、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选择与偏差
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选择与偏差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有着深刻的表现。在《讲话》中,毛首先对鲁迅的杂文笔法予以了否定,认为“鲁迅笔法”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统区、沦陷区使用是完全正确的,而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2]77的边区根据地,则“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2]77,对于人民不应嘲讽和攻击,而应保护和教育。鲁迅一直以批判国民性著称,但明显毛在此将“国民性”与“人民”的概念加以混淆、予以取舍,从而对文艺写作方式进行了限制。其次,毛在《讲话》最后引用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且将“千夫”指向敌人,“孺子”指向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从而扩大了他在《论鲁迅》中指出的鲁迅的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82。
除去这两点明显提到鲁迅的部分外,毛在这篇讲话中的其他内容事实上也是一种对鲁迅精神与思想的遮蔽与背离。就比如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鲁迅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个性主义思想的文学家,在实践中始终坚持文艺的个性与特殊性;而毛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必然首先强调的是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要求文艺能够适合广大群众的斗争要求,强调的是文学的党性、阶级性的存在。又比如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鲁迅从来都致力于用文学的笔来揭露社会的黑暗,极为注重其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仅是批判政府的黑暗,更希望以批判国民性来唤醒人民的觉悟;而毛则从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立场出发,将歌颂与暴露问题进行了二元对立,要求歌颂指向无产阶级、暴露指向资产阶级,人民内部的缺点应该教育与保护,而不是讽刺与暴露。而在暴露与歌颂这一点上,笔者私以为,是否接受暴露黑暗,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政党如果连接受他人批评的勇气都没有,而是一味地限制,不能暴露,只能歌颂,那么歌颂的东西未必是真的,赞扬的东西未必是好的;相反,其暴露的东西也未必是假的,批判的东西也未必是坏的。说到底,能不能暴露,并不是一个作家需不需要、或者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政党给不给、以及肯不肯接受的问题。
而正如竹内好所质疑的,“鲁迅的精神……与文学方面相比,是否更为政治方面所利用?”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鲁迅的文艺思想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契合,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契合的同时,鲁迅始终保持着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知识分子所要求具有的那种独立思想、怀疑精神与批判能力。毛在继承和阐发鲁迅精神时对其中一些思想,如人民为本位、文艺大众化、文艺统一战线等思想的时候都有着精确的论述,但大多数集中于文艺的人民性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而一旦涉及到文艺的党性、文艺与政治等根本性原则,毛则自动地进行了屏蔽。鲁迅始终坚持着自己文学家的身份,以文学启蒙人生;毛则从其政治家与革命家的身份出发来制定文艺政策,这种身份上的差异是导致二人差异的根本所在,它必然会导致毛在选择鲁迅文艺思想的时候对鲁迅精神与思想进行筛选,注重其与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相适应的部分,弱化、忽略甚至遮蔽其与意识形态相违背、或者无法与意识形态相整合的部分,从而重新塑造了一个能够融合于现有意识形态的鲁迅形象,其最终目的不外乎维护和巩固党对于文艺思想的领导和控制。或许这也就是霍尔所谓的“定型化”:忽略鲁迅精神与中共精神相违背的一面,而夸大其相适应的一面,从而将其定型化,把文化和历史建构的身份自然化。其背后隐藏着权力的逻辑,是一种表征的策略,为的是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权利关系。
而事实上,这种选择说到底就是一种对于话语权力的控制。将鲁迅形象神化,强调其有利、适应的一面并使之放大化,从而控制知识分子话语。钱理群在评论鲁迅时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对鲁迅进行改造,这是一个党和国家的权力发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知识分子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4]。通过鲁迅这一知识分子形象的改造,来完成对整个文艺界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这是毛泽东根本的目的所在。
因此,毛泽东对于鲁迅形象的建构,看似是一个“文学家”的形象,实则更多的是“革命家”的形象,这当中包含着意识形态的选择与遮蔽。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后来人、一个过往历史的观看者,在看到鲁迅死后毛泽东如此抬高鲁迅之时,经常提出类似的问题:“如果鲁迅一直活到了建国,经历过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么他那时候还会如生前一般响亮地发声?而毛泽东此时对鲁迅的评价还是否如今天一般?”鲁迅本人曾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有过这样的一句话:“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5]深谙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选择,那是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我们无法知晓。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鲁迅本人,还是死后所建构出来的鲁迅形象,都纠缠着政治与文学的难舍难分的关系。而文学与政治到底关系如何,文学界、思想界一直莫衷一是,从未给出过确定的答案。
三、破却中的统一:文学与政治关系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曾将五四运动——这一作为一个思想史范畴的现象,看成是启蒙(作为启蒙的思想运动)与救亡(作为革命的政治运动)的双重变奏,“两个五四”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在李泽厚这里,启蒙作为一个思想文化的范畴,它始终是与救亡,即现实政治相生相应,互相影响的。文学超脱不了政治,政治也隔绝不了文学。而在中国近代独特的革命年代,救亡的需要始终大于启蒙,政治也一次次地压倒了文学。特别是在《讲话》之后,文学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政治的附庸。从这一意义上看,反倒可以证实伊格尔顿那句对文学与政治的言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认为,任何阅读都不是清白或者没有任何预设的,根本没有纯粹的“文学”反应,所有反应,都与我们是哪种社会的和历史的个人深深交织在一起。而这其中,政治是一种最为核心的交织方式。我们根本不必把政治拉扯进文学理论,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而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不应该因其受政治学的影响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者无知。在伊格尔顿这里,政治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语和场所,即使艺术家或者文学家不去涉及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政治或意识形态也会隐藏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表现于他们作品的深层结构之内。就像萨义德在分析19世纪英国文学的时候提到的,尽管作家没有刻意去表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形态也已经深入到了作家意识和文学作品的骨髓当中。
伊格尔顿作为意识形态批评的代表,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作为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际的伟大实践者,他对于文学与政治的演说相较于伊格尔顿则更为深刻。伊格尔顿是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去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而毛泽东则是首先站在一个革命家、领导者的立场上去分析文学与政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有认识作用,是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革命性的工具效力,直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实践。而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着相同的特征。从这里出发,毛将文艺工作置于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将文艺视为政治军事斗争之外的第二条战线。而《讲话》则是集中表现了毛的这种思想。《讲话》从引言开始,就点明了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从整体上看,毛的《讲话》中所涉及的文学或文化的概念是与意识形态或政治密不可分的。他的整个文艺思想就建构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中,文艺必须服从于意识形态(政治)的总体要求。不论是他的群众问题、阶级问题、文艺批评标准问题,还是党内关系问题,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特征。特别是对于文学批评标准,毛鲜明地指出,文艺应当反映阶级斗争,必须将政治标准放第一位,艺术标准放第二位。应该说,毛的这种文艺观是在特定话语体系中,在特定的革命年代,以一个特殊的革命家的身份来言说的,它在特定时期确实能够起到较大作用,但将此观念带到和平年代,以强烈的政治规范对文艺进行控制,却是不利于文学的发展的。
到了80年代,当人们开始走出政治的阴影,开始重新思考鲁迅的意义、文学的意义之时,“纯文学”的概念恰逢其时地得以提出。这一“纯文学”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对抗一直以来形成的僵硬的文学教条,从而试图将文学从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纯文学概念的“衍生物”——“回到文学本身”,这一“文学本身”的概念,包含的就是类似个人、主体性、自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等的概念,而意识形态则是80年代时要从文学马车中卸下的首要之物[6]。但80年代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是片面的,仅仅将其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种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它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东西。而“纯文学”的概念就是过于逃避意识形态、过于强调“自我”,而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完善自己的概念,才在90年代逐渐失去了它的抗议性和批判性,陷入到“纯”的固定观念之中,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以文学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从而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因此逐渐地走入死胡同,发展为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就像薛毅在《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里所说的,“纯文学的观念本来应有对公众领域的关注”[7],文学不应该回避、也无法回避社会、政治的话题。
而相对的,竹内好在分析鲁迅的时候也涉及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竹内好尽管也不否认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却认为,正是深刻的文学性造成了政治性。文学只有将自己独立于政治,才具有真正的政治性。在他看来,鲁迅的根本文学观是“文学是无用的”,因为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产生了这种无力。游离于政治的,不是文学;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也不是文学。政治与文学不是从属或相克的,而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从来被政治所包围,产生文学的是政治,而文学又从政治中选择出了自己,所以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因此,在竹内好话语中的鲁迅,正是通过将文学独立于当时的政治,才获得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但另一方面,鲁迅以文学否定政治,却并没有因此否定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功能。文学之所以能够发挥政治作用,恰恰是因为它不从属于政治,因为它的独立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竹内好对于文学与政治的论述或许是更能够令人产生共鸣的。竹内好写的是鲁迅,在他的眼里,鲁迅是既不追随现实,又不回避政治,而是将文学破却在政治中,从而使政治也破却在文学里的。不论鲁迅是否真如竹内好所认为的这般,但我们尽可以把竹内好的鲁迅看成是他认为并追求的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对于文学与政治的态度。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文学的政治性。丁玲曾说过,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而人作为一个社会化的生物存在于社会当中,就无法避免会与社会、政治发生联系。但这是联系,不是从属,文学与政治可以产生密切的联系,但文学却不应该简单地从属或相克于政治。鲁迅身上有一种如孙中山一般的“永远的革命者”的意象,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与政治相关的,因此鲁迅的文学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子。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正是通过了对政治的绝对性批判才获得了文学上的独立和自觉。这种批判的精神在毛时代是难以做到的,在当代中国随着知识分子变成专家、变得职业化,或许也是难以做到的。但也正是因为难以做到,才使这个话题的讨论与意义变得经久不息。
而事实上笔者觉得,不论是毛时代以来政治统领文学的政策在80年代受到强烈抵抗,从而提出“纯文学”的概念,还是“纯文学”的概念在今天陷入了死局,沦为一种身体写作,关键都在于他们无法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政治与文学。毛时代以政治统领文艺,在革命时代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建设年代却禁锢了文艺的发展;而纯文学的概念在80年代推动了“自我”、主体性的发展,使文学冲破了政治的禁锢,但过度地局限于“自我”而无法将眼光落于现实,则又陷入了局限。因此,文学无法超脱于现实,无法回避于意识形态,但文学却可以在对二者的“破却”当中实现自我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J].文学评论,1988(12).
[4]钱理群.鲁迅:远行以后(1949-2001)(之一)[J].文艺争鸣,2002(1).
[5]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C]//集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11).
[7]薛毅.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J].上海文学,2001(4).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from Mao Zedong's Construction of Lu Xun's Image
Chen Ruohui Li Guangyi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Lu Xun,greatly involved in a world of both literature and politics,enjoys such high prestig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at he overshadows all the others of his time.In Mao Zedong's On Lu Xun,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cy,Speech Made in the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Lu Xun earns an unquestionable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world,and increasingly demonstrating a shiny reflection with ideology.Therefore,grounded upon several of Mao's works on Lu Xun written in the period of Yan'an,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Lu Xun's image,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mage of Lu Xun;Mao Zedong;literature;politics
I210.96
A
1008-293X(2015)05-0008-05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5.05.02
(责任编辑 张玲玲)
2015-06-03
陈若晖(1990-),女,浙江丽水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3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李广益(1982-),男,四川隆昌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