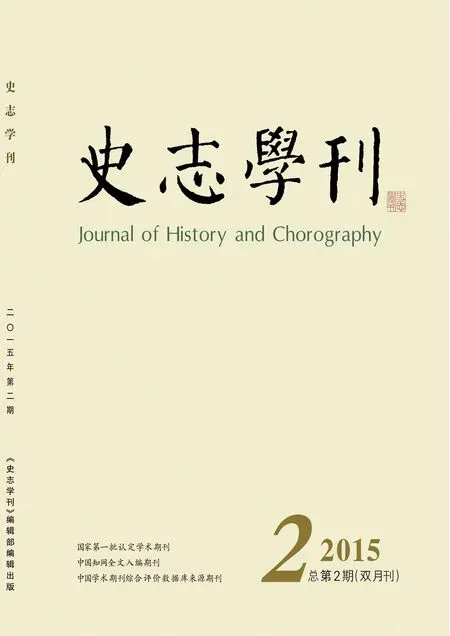葛洪交趾丹道之行考论
宇汝松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
早期道教的修炼法术主要有丹鼎派和符箓派之分。丹鼎派注重炼丹服食,习炼者多为富有、闲暇的社会上层。符篆派则宣扬神符禁咒,践履者多为一般的普通信众。越南自秦汉至十世纪中后期长期北属中国,道教创立后不久便开始南传越南。南传越南的道教主要是符箓派。王彦在《越南历史上的道教初探》中指出:“纵观历史上的越南道教,可以看出,越南道教受中国道教的影响很深,主要是符篆派道教,丹鼎派道教对越南的影响非常有限。”[1]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北大亚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247)越南有限的丹鼎派道教主要源于东晋著名的道教学者兼道医、丹鼎派创始人葛洪的交趾丹道之行。葛洪由于平贼旧功,东晋时再被举荐重任,但因道缘深厚,仰慕交趾富产丹砂和仙药而贱求勾漏令,在交趾“炼丹以祈遐寿”,从而推动了丹鼎派道教在越南的传播。
一、葛洪早年南行访道未及交趾
葛洪(公元283—343年)出生于丹道世家,其从祖葛玄曾是吴时著名的炼丹术士。葛洪对丹道仙学自幼十分喜好,其道术主要师承葛玄弟子郑隐,同时亦受到其“博究仙道”的岳父鲍玄[2]《太平御览》卷四一注引袁宏《罗浮山记》曰:“鲍靓,字子玄,上党人。博究仙道,为南海太守,昼临民政,夜来罗浮山,腾空往返。”的影响。《晋书·葛洪传》曰: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练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
葛洪一生至少两次南下访道弘教。葛洪二十岁左右平破石冰之乱后,本欲北求仙道异书以广其学,但由于当时北方正值“上国丧乱”,于是应广州刺史嵇含之邀而开始了他避乱南土的第一次南下访道之行。《晋书·葛洪传》曰:
太安中(公元303年),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
从本传记载的情况来看,葛洪此次南行一方面是应嵇含表请来广州帮助他打理军政事务;另一方面就是在交、广等地访道修学、弘传仙道。后者似乎是他更为主要的目的。其理由一是因为嵇含既是葛洪的故交,也是葛洪的同道,“嵇含实亦道教中人”。《抱朴子内篇·祛惑》云:“昔有古强者,服草木之方,又颇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许,尚聪明不大羸老,时人便谓之为仙人,或谓之千载翁者,杨州稽使君闻而试迎之于宜都。”[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P347)王承文据此认为:嵇含实亦道教中人。……据清嘉庆中孙星衍校勘本,“杨”当作“广”,“稽”当作“嵇”,实指嵇含。又据《太平御览》卷736引《抱朴子·内篇》佚文云李阿有弟子古强。据此,嵇含所崇重的道士古强曾师从孙吴时期李家道代表人物李阿。而嵇含撰《南方草物状》实际上也与魏晋道教服食有关[2]王承文.葛洪早年南隐罗浮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二是因为嵇含遇害,葛洪仍能停留“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似乎说明他此行潜心南修的真实旨趣。
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中认为,葛洪正是在此次停留南土多年期间去了越南交趾等地。即葛洪“光熙元年(二十四岁),往广州,遂停南土,当由日南(即今越南之顺化一带)往扶南(扶南国即今柬埔寨与越南极南部分)(其后因所闻见,记晋代南洋产砂之国,附于《太清金液神丹经》之后。)后返里。”[3]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P378)但从《抱朴子内篇》葛洪自述的情况来看,此说与史实多有不符。葛洪此次南行并未远及交州,只是止步广州,游学访道,为其垂名青史的道教经典写作收集资料。《抱朴子内篇·金丹》曰:
往者上国丧乱,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阅见流移俗道士数百人矣。或有素闻其名,乃在云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见,深浅有无,不足以相倾也。虽各有数十卷书,亦未能悉解之也,为写蓄之耳[1](P70)。
陈国符之所以认为葛洪此行南及日南、扶南,主要是因为他把《抱朴子内篇·金丹》中葛洪由北南下周游诸州的江州错认为是交州。陈国符说:
永兴元年(二十一岁),洪径诣洛阳,欲广求异书。正遇上国丧乱,北道不通,乃周旋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阅见流移俗道士数百人。光熙元年(二十四岁),往广州,遂停南土[3](P377)。
殊不知,东晋时江州正处于襄、广之间,而交州则在广州之南。《太清金液神丹经》所附《抱朴子序述》进一步证明葛洪交趾之行不是在他二十几岁,而是在他“年已及西”的垂暮晚年。
二、葛洪远赴交趾的丹道之行
《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抱朴子序述》曰:
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
奚自扶南、顿逊,逮于林邑、杜薄、无伦,五国之中,朱砂、琉黄、曾青、石精之所出,诸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实无求不有,不能复缕其别名也。称丹砂如东沤之瓦石,履流丹若甄陶之灰壤,触地比目,不可称量。而此五国,不见服用之方,莫知长延之道,贵无用以填宇内,遗灵石而不眄,竞雕玩之货,贱流丹之药,炼饵不加,真质长隐耳。混杂无亲,妙物不显矣。昔经眼校,实已分明也。
余今年已及西,虽复咀嚼草木,要须丹液之功而荏苒止足。顾死将切近,小县之爵,岂贪荣耶?洪所以不辞者,欲结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此之宿情,禄愿俱集,永辞坟柏,吾其去矣。
夫人大渴者,长愿临长河;大饥者,思托农圃。欲学道者,何不抱灵方游其地,则何忧丹石之匮乏也。意力之不集耶?奚为止足于贵竞之土,安身于纷争之邦,共其枯竭哉!……彼不贵用丹之术,则不贵我所为之事。是以我得安其所营,而心无怵惕,独贵所味而无钻仰,岂不尽理于内而如愚于外哉[1]道藏(第 18册).(P757,758)?
在此序述中,葛洪一是道出了自己年少就有游外学道的志向和梦想,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此即葛洪所言的“宿情”。二是,葛洪此次“因旅南行”是他在“年已及西”,即年事已高之时。三是葛洪之所以不顾荣华毁誉而贱求“小县之爵”,因为交趾“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实无求不有”,是服食丹液、“荏苒止足”的最佳选择。四是葛洪此行的目的主要因为“顾死将切近”,意欲服食交趾的丹砂、仙药以延年遐寿,“永辞坟柏”。五是葛洪对此行的自我感觉和评价是“禄愿俱集”“尽理于内而如愚于外”。
《晋书·葛洪传》亦有与此相互呼应的相关记载:
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练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
葛洪因早年平贼旧功,在东晋时得以封侯进爵。陈国符说:“洪之爵关内侯,当在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时洪年三十一岁)后。”[2]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P97)咸和年间又被举荐大任,葛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以炼丹服食以延寿。听闻交趾富产丹砂而贱求苟漏令,并最终获准。勾漏又名句屚、苟漏,系当时交趾管辖下的一个县。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说:苟漏位于“宁平省安庆县地区和南定省丰盈县、义县。晋时,道家葛洪闻交阯有丹(丹沙用以炼仙丹),求补勾漏县令。在现今安谟地区,过去称为九真山的石山中有许多山洞,其中著名的如蝙蝠洞、徐试洞,葛洪确有可能想来这里找地方炼丹”[3]陶维英.钟民岩译.越南历代疆域.商务印书馆,1973.(P61)。
本传随后说葛洪“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赴任交趾未能如愿成行。冯汉镛根据《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抱朴子序述》中所记载的印支特产、土俗和符箓变革等情况,确认葛洪此次印支之行不虚。
印度支那有许多外地缺少的特殊产品,对这些产品,葛洪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认识都相当深刻。甚至其深刻程度,还不是“见人撰南方之异同(《神丹经》语)”,仅据传闻就能知道的。尤其他所提到的特产,大部分都最先见于葛著,若非亲身目睹,就很难办到这点,从而表现出葛氏确曾去过印支旅行[4]冯汉镛.葛洪曾去印支考.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P59)。
葛洪游历印支似无可质疑,但不应是陈国符所说的,在他平破石冰之乱后的二十四岁左右,而应是在他年近晚暮之际。侯外庐等撰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确认葛洪封侯食邑是在建武元年(317),咸和五年以后再度南行,时年已有五十四五岁。
邓岳为广州刺史,在咸和五年(330)之后,葛洪再度南行到广州,当也在咸和五年之后了。则葛洪封侯食邑后在江南,也至少住了十四年左右(317—330)。也就是说,洪再度南行时,当在五十四五岁光景[1]侯外庐,杜守素等.中国思想通史(2卷).三联联合发行所,1949.(P785)。
王承文亦认为葛洪“第二次南适岭表在东晋咸和年间”,并引饶宗颐在《〈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中所言:“咸和六年(331)洪求为勾漏令”为证[2]王承文.汉晋岭南道教史考论——以“丹砂灵药”为中心.载李翀.论衡丛刊(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P257,261)。此时的葛洪也当在五十岁左右。
葛洪此行的主旨是“炼丹以祈遐寿”,这对推动丹鼎派道教在越地的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许永璋曾亦指出:“葛洪在这些地区活动,绝不仅仅是寻找丹砂产地,肯定会传播道教。”[3]许永璋.论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史学月刊,2002,(7).
三、葛洪交趾之行的历史意义
《抱朴子序述》否证了《晋书》本传说他到了广州为刺史邓岳劝留而止步罗浮山炼丹而终一事,确证了葛洪为了仙道理想,不顾俗鄙毁誉而远赴交趾贱任勾漏县令。其序述是道教史一份珍贵的史料,记载了当时印支半岛所富含的丹道仙药以及民人对仙道尚无识知的历史始况,对道教南传越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首先,对仙道丹术的满腔热情和矢志追求始终是葛洪惯行的弘道宗旨。《抱朴子内篇·金丹》亦曾印证他“少欲学道,志游遐外”的志向和个性:“余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有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P72)虽然葛洪以“才堪国史”的高贵身份贱求蛮荒之地的勾漏县令,饱受鄙俗毁笑,葛洪还是表达了他为了道教理想,此行“岂不尽理于内而如愚于外哉?”
其次,葛洪看到了当时的印支半岛确如听闻的那样,道教长生服食炼养的仙药品种多,藏量富,实乃无求不有。在“年已及西”,“顾死将切近”垂暮、危急之时,他对平时“咀嚼草木”的养生方法深感不足,渴望“丹液之功而荏苒止足”,因为在他看来,在所有修仙的药物中,还丹金液最为重要:
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
仙药之大者,莫先于金丹。
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4](P70,336,332)。
交趾富产的优质金丹仙药弥补了葛洪早年虽有炼丹之志、名师指点和丹经仙方,却长期苦无丹药的窘迫和抱憾。葛洪曾在《抱朴子内篇·微旨》中指出:“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费重,不可卒办也。”“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资无担石,无以为之,但有长叹耳。”[4](P124,71)如今的“小县之爵”终于可以遂愿他积压多年的宿情和心病。所以,葛洪认为,求任勾漏县令实是他人生明智而双赢的选择,即“禄愿俱集”矣。
再次,葛洪游历当时的越南中南部和柬埔寨等地,还不知长生延寿之道、没有炼养服食的意识和方法,徒把自然馈赠的灵石、流丹等贵重仙药视作无用之物,即“不见服用之方,莫知长延之道;贵无用以填宇内,遗灵石而不眄”。作为道教中人,葛洪一方面对此深感可惜,另一方面自然会向他们宣道传教。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洪所以不辞者,欲结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通过言传身教,推动道教炼丹服食在越南的发展。
再次,葛洪以亲眼目睹证明了包括越南在内的印支半岛确是修仙之福地,仙家之庭宇。《抱朴子序述》曰:“且南遐大境,名山相连,下洞潜霍,高齐青云,火州郁勃,香陵芳芬,岂唯杨楚之郊专有福地耶?……又丹经所言,既成而服,有升天之验,如仙人所传八遐,将一家庭宇耳。”[1]道藏(第 18册).(P758)这对道教南传越南无疑具有更大吸引力和推动作用。
最后,作为东晋著名的道士、道医兼道教学者,葛洪在赴任越南期间,通过亲身搜访和实地考辨,详细记载了当地富产的仙丹灵药,并对它们“混杂无亲,妙物不显”的乱象,进行了“眼校”,使其良莠可辨,症药分明。从而为丹道、医道等“将来君子,各搜德业,不以管穴别意,有所导引也。”[1](P758)为道教和医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即如冯汉镛所言:“他的这趟旅行,对中越等印支国家,都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更因葛也是位医学家,故在医学上所起的交流作用更大。”[2]冯汉镛.葛洪曾去印支考.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