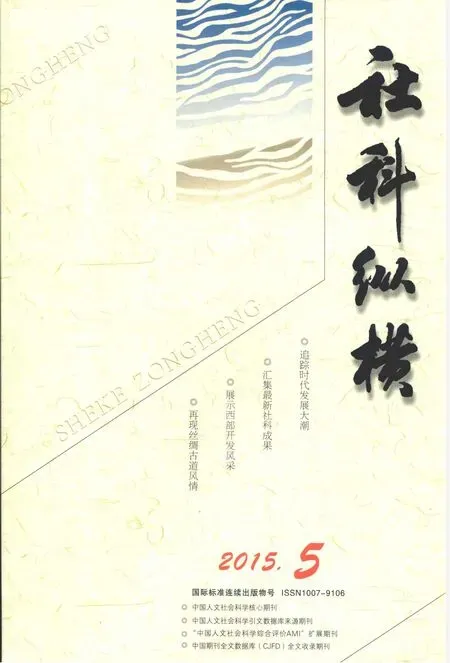论福泽谕吉对朝鲜壬午兵变的认识
董顺擘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作为日本“近代化的指导者”,利用出书、办学、办报大力进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宣传,抨击封建制度,阐释文明开化理论,为推动日本近代化进程起到了思想先驱者的巨大作用。但是,在其思想的中后期曾积极鼓吹对中国与朝鲜等亚洲邻国进行侵略的军国主义思想。
朝鲜壬午兵变作为近代中朝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近代中朝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无有关福泽对这一事件所发言论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对朝鲜壬午兵变的研究也相对薄弱①。考察福泽对朝鲜壬午兵变的评论,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福泽及其日本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福泽的朝鲜观以及中国观。
一、壬午兵变前福泽的朝鲜认识
“朝鲜”这一称谓在福泽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869年出版的《世界国尽》一书中[1](P29)。“朝鲜”只是作为一个国名在介绍俄国时被提及,称“支那②满洲一半已被并入俄国,俄国之实力已扩大至朝鲜边境”[2](P627-628)。明治维新初期的福泽根本没有具体论及朝鲜的情况,对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并不关注。
此后,福泽在多篇论著中承认“古代日本之文明来自朝鲜”,但同时又把只是记载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书中的神功皇后征服朝鲜的传说认定为历史事实,并多次提及丰臣秀吉攻伐朝鲜的实例。③由此可见,在福泽的意识中,认为古代朝鲜在文化上与日本相比处于优势,而日本则在军事方面处于优势[3](P395)。虽然福泽有时也承认“古代日本之文明来自朝鲜”,但福泽作为一位洋学者,对于朝鲜所信奉的儒学持批判态度,④已完全没有了江户时代文人学者对朝鲜文化的推崇[4](P194-201),意识中古代朝鲜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势逐渐消失。福泽在论著中更多地提及神功皇后征服朝鲜的传说与丰臣秀吉攻伐朝鲜的实例,更加体现出存在其意识中的古代日本在军事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优越感变得愈加明显,对朝鲜也就愈加蔑视。福泽立足于此的蔑视的朝鲜观,深深扎根于其思想之中,深刻地影响着福泽一生的朝鲜观。
1875年8月,福泽在发表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将社会的发展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这一文明观潜藏着鲜明的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倾向。福泽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观,“正是他所提倡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所必然导致的结论”[5](P39),体现出了西方殖民主义文明观的特点。⑤《文明论概略》发表后不久的10月7日,福泽在《邮政报知新闻》上发表了《与亚洲各国之和平与战争同我们之荣辱无关》[6](P145-151)一文。文中,出现了称朝鲜为“亚洲之一小野蛮国,其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日本”、称朝鲜人为“野蛮之朝鲜人”等蔑视的语句,认为朝鲜还处于野蛮阶段。次年11月1日,在福泽发表的《要知论》[7](P577-579)一文中,同样出现了蔑视朝鲜的语句,如“朝鲜人顽固至极”、“野蛮之常不值得奇怪”等。福泽虽然在《文明论概略》中将亚洲国家归为半开化国家,但不久之后在其所发表的其他论著中还是将朝鲜认定为处于野蛮的发展阶段。如果按福泽文明观中体现出的西方殖民主义文明观的特点,如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所宣称的那样“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8](P168),那么,处于半开化阶段并逐渐上升到所谓文明阶段的日本就应该压制处于“野蛮”状态的朝鲜,为日后日本侵略朝鲜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1875年9月云扬号事件发生后,福泽曾从“对日本经济之无益性”、“士族不了解朝鲜之野蛮状态”[6](P145-151)等方面来说明其反对征韩的正确性,希望以此来调和士族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然而,西南战争后福泽在《通俗国权论》一书中却明确指出,为了调和国内矛盾、唤起国民国权意识的最有效方法是外战,而外战的唯一对象只能是国力比日本弱小、路途又近的朝鲜[9](P641),为日后其积极倡导侵略朝鲜打下了伏笔。
1881年7月,福泽在《时事小言》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东洋盟主论”。福泽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东洋盟主”,以假设防止“延烧”⑥为理由,主张指导朝鲜、中国“文明开化”[10](P95-231)。
1882年3月11日,福泽在自己创办不久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论与朝鲜之交际》[11](P28-31)一文。文中主要论述如何与朝鲜进行交际,可以看出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福泽对外观中的具体课题。福泽把朝鲜开港时期日本同朝鲜的关系与日本开港时期美国同日本的关系相类比,由此认为日本在朝鲜具有“优越性”,并把它作为日本指导朝鲜“文明开化”的依据[12](P41-42)。
不久之后朝鲜发生的元山津事变⑦,为福泽提供了发表有关朝鲜问题言论的具体实例,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了《朝鲜元山津之变报》[13](P83-85)、《朝鲜与日本相似》[14](P87)和《必须要求朝鲜政府》[15](P96)等文章。文中,福泽希望日本政府派军舰常驻朝鲜、增加巡查等以武力保护日本的在朝侨民、扩大两国的贸易;并希望架设电报线,避免出现像元山津事变那样无法同国内及时地进行联系的状况。常驻军舰、增加巡查、架设电报线等内容都是对朝鲜国事的干涉,若这些都能实现,将为日本进一步“指导”朝鲜“文明开化”打下基础,同时这些做法也是日本实现对朝鲜的“东洋盟主论”的途径。在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认为其建议未得到实施是造成日本人“被害”的重要原因。
二、对壬午兵变的评论
1882年7月23日,朝鲜士兵因不满闵氏家族的腐败统治和日本人对朝鲜内政的干涉而发动了兵变。兵变中,朝鲜士兵杀死亲日派大臣并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致使公使花房义质逃归长崎。兵变后,清政府应闵妃一派的请求迅速出兵进行了镇压。期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评论。
(一)对壬午兵变的认识及对朝鲜政界的分析
7月31日和8月1日,福泽连续两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朝鲜事变》一文,通过壬午兵变发生后花房公使从长崎发至外务省有关壬午兵变的电报介绍了朝鲜壬午兵变的情况,[16](P243-244)并断定发动此次兵变的“无疑是所谓号称斥和党之顽固党一类”,指出:
当今之朝鲜国王乃持开国主义者,其父大院君乃主张斥和守旧之顽固主义者,其权势甚是强大。因此,当时在朝鲜政府一部分参与外交政略之人,按当时之情况不得已须乃持开国主义之人,其势力本不强大,常常因被斥和顽固党掣肘、压制,不能充分地实行其计划。然而政府外之普通社会,斥和锁国议论纷纷。或数百人联名抗疏极谏,或欲罢黜当今之国王,恢复锁国攘夷之政权,若概括今日之情况,全国上下几乎可谓乃斥和锁国党之大团结。[16](P245)
同时,福泽还指出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朝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称“在日本与朝鲜两国之间,7月23日之后其交往已经断绝,可谓已非和亲修好之交际,而成了战场相见之交际”。[16](P247-248)
对于壬午兵变后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福泽建议应该在朝鲜任命“国务监督官”,“由花房公使兼任朝鲜国务监督官,监督该国万机国务,至少应辅翼保护开国人士,委任于该国之政府”。[16](P249)“设置此监督官,监督全国政务改良期间,短则六七年,长则十数年,让一队护卫兵驻扎于京城,衣食住等须全由朝鲜政府供给。”[16](P254)设置“国务监督官”的设想也是福泽对朝鲜的“东洋盟主论”的实现途径之一,已经表现出了将朝鲜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意图,同时这也证明了福泽的所谓“东洋盟主论”的本质。
此后,福泽对朝鲜政界势力的分布进行了分析。他说:
今日其执政之大臣,大体上乃50岁以上至70岁左右之老者。其主义亦守旧,墨守周公孔子之道,仰视支那之广袤,保守本国500年来之旧物,未能前进一步,即以大院君为首,……仅李载完作为国王之从弟27岁,其余无一人50岁之下。此外,在朝在官之保守党繁盛如云,不能逐一列举。但是,另一方必定乃改进党。……其中,如闵泳翊、鱼允中、洪英植虽被称为壮年有势者,但政府全部之权利都掌握于十之七八之保守党之手,无实现改进主义之途径。但是,改进之幸在于国王一人,其30余岁,锐意进取,为采取改革进步之路,专门依靠改进党之壮年辈保持其地位,有时必须压制原来之老先生。……原本少壮之华士族中,虽说锁国论者甚多,但40岁以上之老者中可称为改进者之人屈指可数。[16](P252-253)
福泽还对保守党与改进党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并再次断定发动此次事变的是保守党。他说:
保守之老大执权者如脑,改进之年轻有力者如腕。虽说手腕因常活动而灵活,而下令支配其活动、左右其进退的在于政府之脑髓——老者之意愿。政治上如此之状态,保守(党)经常保守旧物可永远保持地位吗?改进(党)经常呈现其活力,定可压倒故老,谁能制胜,迟早会不可避免诉诸于腕力。[16](P253)
发动此次京城事变的乱贼原本与先前的(发动李载先之乱、元山津事变的朝鲜人——笔者注)乃同类,是以政府为目标举事?还是仅乃袭击我日本之公使馆?虽不知其详情,但若以政府为目标,明显的乃以政府中之改进部分为敌。若已经敌视改进,此贼徒不仅在朝鲜妨碍其国家之开明,且现已违背持改进主义之国王的旨意,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情面上都乃国贼,必须说乃王室之罪人。在此,我辈日本人若详查我敌之所在,可断定其敌不在王室,不在改进党,只在保守顽冥之类。[16](P254)
对作为保守党首领的大院君杀害王妃⑧、世子妃及其他保守党人士,福泽也阐述了其自身看法,认为“从《朝鲜事变续报》来看,大院君为了掌权,杀害了王妃、世子妃、李最应、金辅铉、闵台镐、闵镰镐与尹雄烈。原来此事变乃由朝鲜保守与改进之倾轧而产生,李氏以下五人中,除尹氏外皆保守主义者,保守党杀害保守者似乎不可思议。且大院君为了掌权杀害王妃与世子妃,在众人看来,骨肉之间杀害儿媳、孙媳在人情方面难于理解,但若详细了解他国20年来之情况,好像亦足可解开疑惑”。[17](P264-265)
而对于大院君一派为何未在兵变中杀害国王,福泽则认为“未杀害而是将国王囚禁,可推测乃为了利用其名使其虚有其位,乃今后以国王之命控制国内、以国王之名同国外进行交往之奸策”。[17](P268)
福泽还指出“如今之大院君政府正乃以这些暴徒组织而成,如其煽动者、指挥者立于新政府之朝廷,洋洋得意。加之,大院君本人亦非当日之指挥者,仅乃煽动声援之根本”,并认为此次在朝鲜袭击、杀害日本人的“一定乃大院君一派”。[17](P272)大院君正是在这次兵变中“利用士兵之不满而举事,其举动最活跃、其成功也最迅速”。[18](P288)
此后,福泽又发表《朝鲜政略备考》一文,对朝鲜的地理、风土人情、身份制度、科举制度、宗教、官职、租税、政府的腐败及官员的俸禄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19](P275-285)福泽对朝鲜政界的分析较为全面、准确,体现了其对朝鲜的充分了解以及对朝鲜非常高的关注度,同时这也是其分析朝鲜问题的基础。
(二)对壬午兵变中日本出兵的必要性的评论
日本政府接到兵变的消息后,于7月30日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日本政府一方面压制了黑田清隆等人提出的立即开战论,另一方面制定了以派遣军舰作为谈判的后盾,同朝鲜进行谈判的方针。
如前所述,在元山津事变后,福泽曾在“应在朝鲜三港常驻军舰”、“增加保护居留地的巡查”、“架设用于急用的电报线”等方面对日本政府进行过劝告。此时,福泽认为“若在元山津事变后4个月期间,早早地做好了如此之警备,可防患此事变于未然”。[16](P245-246)
对于处理壬午兵变的对策,福泽指出:
我政府传令海陆军,可做好军舰、陆军参加外战之准备。同时可任命遣韩特派全权办理大臣,委任其和战文武之全权,俟花房公使抵京,共同率军舰、陆军火速前往京城。然而,朝鲜暴徒之性质还不知其详,尤其是花房公使从韩国撤回后,情况完全不知。只有陆海军之兵力十分强大,才是万全之策。[16](P246)
并且,福泽指出实施朝鲜政略的“第一要务在于兵力”,[16](P255)对于政府关于壬午兵变的处理感到高兴。他说:
尤其乃用兵之时机一日亦不可贻误。这便乃我辈关于此次兵变根据一封电报便即刻讨论军舰、陆军进行对外作战准备之缘由。舆论对此毫无异议,政府之计划果然符合我辈之想法吗?三艘军舰已出发,井上外务卿既然从马关出发,小仓之若干分营兵应作为花房公使之护卫兵派向仁川。政府处置之迅速使我辈不胜欣喜。[16](P255)
福泽还批评了某些舆论者是“只管倡导和平,乃只要看到兵字就感到吃惊之人”,[16](P255)并再次指出日本向朝鲜出兵的“正当”理由:
此次把我国作为敌人的既非王室又非改进党,而乃他国朝野上下之保守顽固党,若政府出现一时落入顽固党手中之情况,非其国最上最贵国王之本意,又出现了改进党出于无力之情况,我日本既为了两国交际之情谊,又为了保护宇内之文明,暂时借我兵力扫除他国全面之迷雾,乃我国在道德信义上不可推辞之义务。[16](P256)
同时,福泽警告派往朝鲜的军队要遵守军纪,指出朝鲜的风俗习惯,如同女人接触、坐的位置等都与日本不同,因此需要注意,[20](P258)认为云扬号事件就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而引起的“误会”。[20](P258)福泽还认为朝鲜人之所以把壬辰倭乱称为“彻骨之恨”,也都是由于当时日本军队不遵守军纪造成的。[20](P258-259)福泽将侵略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将朝鲜人民对侵略的反抗归结于日本军队不守军纪,显然是其具有西方殖民主义特点的文明观的真实体现。
8月10日,接到日本政府训令的花房率领4艘军舰、3艘运输船及陆军一个大队开赴朝鲜。对于日本在处理此次事变中要具备强大兵力的必要性,福泽指出:
朝鲜之内乱与日本无关,今之逆徒非原来正当之政府,我文武全权办理公使视察他国之情况,欲尽量帮助其旧政府。旧政府果真毫无能力、不足以统治国内之人民,不能尊奉外部之条约,详查国家之实力全部归贼徒之事实,并非不能进一步承认它乃朝鲜之新政府并缔结新条约,当处理如此情况之时,无论是和、是战,不可或缺的在于兵力。并且,欲容易地解决如此之事情,需要迅速地利用战争之机会使兵力变得强大,因此我辈从最初就忠告出兵之事。虽说或许世间有议论,恐惧军队的通常乃书生,不敢责备。我辈希望的乃与永日地操练人数少之兵力相比,不如一时利用强大之兵力迅速地结束。[17](P269)
同时,福泽还为自己希望日本派兵的政策进行了辩解,称“大大地显示兵力,迅速结束谈判乃必要的。但如我辈本月四日之社说所述,派兵虽是重要的,但所希望的是不要误用。况且犹如此次兵力仅乃为万一之事变所准备,或者说不能实际使用”。[17](P273)
福泽又以英国为榜样,指出如英国因生麦事件与日本进行谈判时一样,壬午兵变必须以武力解决并取得谈判之抵押。他说,“总之,占据釜山或者江华岛以外之任何一个要冲作为谈判之抵押,紧要的是迅速地结束。在要求赔偿之谈判上,以武力取得抵押,实在乃通常之事情,无须感到奇怪”。[21](P290)
其后,福泽还指出必须出兵朝鲜的四点理由:一是要保护去朝鲜进行谈判的公使。他说,“上月23日暴动以来,朝鲜国内之情况无法详知。总之,朝鲜没有力量保护在韩之日本人。且若是大院君之政府,只是倡导虚饰外表的和平之说,出于遁词的一时之策,其内心想法不仅不保护我,可以明确乃要伤害我之人,这可通过此前事实来证明。要进入如此之国家商谈事情,作为我国政府之使者不可只身独步,这当然乃身经百战之心得,护卫之兵力不可少。”[21](P290-291)二是要保护在朝侨民和商人。他说,“在釜山、元山从事两国贸易之侨民甚多。然而,这些日本人完全乃从事商贸之人,乃身不带寸铁防卫之人,如今值他国暴徒正盛之时,无法预知有何等之变化。在已过去之3月31日,元山津之凶徒突然爆发,我侨民老幼、妇女有躲避灾难逃至釜山又回到长崎的。如此之暴乱,几乎都是无规律之时势,为了我国商人不可没有严格之保护”。[21](P291)三是为了保证谈判的进行。他说,“我问罪使在他国登陆后迅速展开谈判,袭击我公使馆、屠杀我人民的乃何人所为?指挥者又是什么人?教唆、煽动、声援的是些什么人?追究其事实,处死几名作为首领之人,对我被害者家属让其支付相当之抚恤金,并让其偿还我政府问罪之实际支出,犹如我国民在诉讼中须由败诉一方支付诉讼费用之惯例,关于如此之谈判可由我方介入罪人之处刑。抚恤之金额、问罪发生之实际费用,亦由我方计算其多寡要求之,限定时日要求其答复。若乃非常重要之谈判,依当时之情况,选择要冲之地以兵力占据,声明谈判不结束不归还此土地,就如把它作为谈判之抵押。若达到我方要求之目的,可谓乃和平之结局。否则,若他方无论如何亦无答应我方要求之意、更加无礼之时,不得已开启战端攻击其守卫之要冲,须迫使其签订城下之盟。”[21](P291-292)四是可以保证朝鲜今后不再攘夷。他说,“或和或战,以何为结局如今尚难预料。无论是和、是战,总之(不)答应我方之要求,一日不可结束。如其一时支付赔偿金一定会有困难,因此至其支付完了为止,兵力不可松懈,俟其结束乃紧要的。让其在精神上真实地悔恨此前之错误,只管以和平为主。若眼下仅乃由于似筹款无着而延期,我士兵驻在其土地亦无益处。通过我辈之臆测,决不能相信大院君之心中所想仅乃如此。若其对日本真有友好之意,推倒数年前国内建立之洋夷侵犯之石碑,并撤销国内攘夷之首领,大院君之政略今年今月改变一新之确凿证据明确宣告于国内,其必定会困窘。若以如此暧昧之政府为对手商谈事情,要有思想准备,其信义不可依赖,为加强其信义,必须使用我方之兵力”。[21](P292)
壬午兵变的发生,给了福泽进一步发表其关于朝鲜问题评论的机会。在评论中,福泽表现出希望使用武力解决壬午兵变的对朝强硬论,一直强调使用武力的重要性。期间,福泽为了达到反对清政府干涉日朝之间关于处理壬午兵变谈判的目的,还曾从历史形成上对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22](P62-64)
三、对《济物浦条约》的评论
8月20日,花房公使率兵抵达朝鲜京城后,立即向朝鲜国王提出了惩罚凶手、抚恤受害的日本人、赔偿损失、开放杨华津等地、驻扎保卫使馆的日本军队等各项要求,并限期3天给予答复。3天期满后,未得到答复的花房立即撤回仁川。30日,朝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通过该条约日本不仅获得了巨额的赔款,还扩大了在《日朝修好条规》中没有取得的侵略权益,特别是以保护公使的名义取得的驻兵权。该条约对于朝鲜来说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对于日本,则通过这一条约进一步加快了侵朝的步伐。关于《济物浦条约》,福泽进行了如下评论。
第一,福泽赞扬日本政府及其外交官在谈判中取得的“成绩”。福泽得到《济物浦条约》签订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喜悦,认为“首先,横在日朝两国间之杀气妖氛被以如此和平之手段一扫而光,对两国交情倍增、变得日趋亲密感到高兴。还感到高兴的是,此条约足以满足我日本国民之希望。最后,可见此次之处理同事先我辈所主张之意见毫无差别,我心中暗自不胜喜悦,听到此处理首先不外乎盛赞”。[23](P328)日本政府及其花房公使在“内有大院君一派之斥攘论,外有支那之嫉妒、猜疑,英美其他诸国军舰在近海来往”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花房公使之处境可谓非常之困难,活动不大自由”,[23](P328-329)“但克服此困难并迅速地解决,其结果之美好可以评为欧洲第一流之外交家,除了枝节问题之长短大小,不能给予一点儿之批判”。[23](P328)
第二,福泽认为谈判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兵力。福泽认为“外交上之事件莫不如说多数由背后兵力之精不精决定成败,如此次之谈判不得不说是最明显的”,并且,福泽还对在这次事件处理过程中军队的作用进行了说明,指出“在朝鲜事件发生之际,我辈就曾谈论过有必要派出大规模之军队。实际上若仅为保护公使一人之安全,本来不需要太多之士兵,但想要进行和平之谈判、得到和平之结果,对于朝鲜人要知彼知己,朝鲜之势力如何亦不能同日本敌对,此次之结局,不战则和,战则亡国,必须使其觉悟其祸不仅乃卖国之道理、形势。否则,由于其顽固、倨傲,再惹出什么事端,可谓会造成两国之交际不得已破裂。此乃用兵之第一着眼点”。[24](P329-330)对于条约的达成,福泽认为“不得不说完全乃日本兵快速到来促成了如此美好之结果”。[24](P331)“关于两国交际之错综复杂,应知道非用兵所能解决。或者说兵力之用途不只是在战争中,善于用兵不经常作战,紧要的乃将其放在不战之范围内,如佩戴杀人之刀不一定杀人一样”。[24](P331)福泽再次提醒日本政府为了避免“破坏两国之情谊”,注意驻朝军队的纪律,“此次特别地告诫士兵并在军队中下达特别之命令,以谨慎忍辱作为在韩国驻在时首要之注意事项,使朝鲜朝野人士第一次对我士兵之勇猛、对我士兵之谨慎与正直感到吃惊”。[24](P331)
第三,福泽提醒日本政府注意中国“教唆”朝鲜反对日本。他说,“此次关于清国政府之举动,我辈不能理解之地方甚多。一方面,称朝鲜为清国之属邦,试着胡乱地妨害日韩两独立国间之事;另一方面,在局外旁观,暗中忠告韩廷,以模糊暧昧之陈腐手段,如要瞒着其他人。在其心中仅认为日本有进行侵略之远大志向,欲逐步吞并邻国雄飞于东洋,结成一个疑团而不知解开,自家疑心之暗鬼被斥,可谓仅其自身在辛苦地奔劳”。[24](P332)福泽认为中国怀疑日本在汉城驻兵、在杨华津开设贸易市场、公使领事及其属员、家属到内地旅行,不仅自寻烦恼,而且“流言告密,倾尽种种手段教唆朝鲜人”。[24](P332)因此,福泽希望“我政府以及实地当局之公使等,对于中国烦恼之原因不可轻视,以我之赤心对待韩廷,广交韩人,提醒注意不能使清国政府之计谋得逞,可谓乃非常重要之事情”。[24](P331)
第四,福泽认为对于朝鲜的50万元赔款日本应该返还,用于朝鲜引进文明,日本监督其使用。福泽指出,“我政府要求金额之多少与我无关,只是让韩廷担负实际之费用,让其悔罪,进行惩罚,只是永远地维持两国间交际之意。但推查朝鲜财政之状况,只是要求朝鲜能够负担的、适当之少量金额,得到惩罚之实际证明足矣”。同时,福泽也对政府的做法表示了反对。他说,“推查如今朝鲜之国情,50万元之赔款,使他国国民胆寒,惩罚此举以儆将来,不可不亲近日本,不可不进行外交,革除旧弊,不可不推进日新月异之文化,人心一变,与我国之方向甚是一致,共同协作,会采取使东洋之面目一新之国策吗?”[25](P334)随后,福泽又分析了朝鲜国内的政治情况,认为如今的朝鲜持斥攘论的乃朝鲜人民,很难改变朝鲜人民的斥攘论,此次的50万元赔款对于朝鲜人民无关痛痒。[25](P335-336)所以,要使朝鲜和日本“一起共同走向日新月异之文明”,只能是让其引进文明之新事物。[25](P336)这次的50万元赔款,“一旦得到后,再把它赠与朝鲜政府,希望成为他政府引进新事物费用之一部分补助。但此补助金赠与后,为防止他政府滥用或用于其它无益有害之方面,我政府必须监督其对于此赔款之使用”。[25](P336-337)如果返还了此次赔款,福泽认为会取得一举三得的效果:“表明我政府之举乃为了义而非为了利;使朝鲜之朝野感到我政府之宽大,激起其共同开进文明之念;又乃使满清释然,消除其猜疑之权宜之计”。[25](P337)甲申政变前,日本政府确实返还了朝鲜的40万美元的赔款,[26](P201)但应该看到日本返还赔偿金只是为了缓和日朝之间的关系,实现日本自身的目的。
综上所述,福泽在壬午兵变前强调的日本在朝鲜的“优越性”及其后所主张的在朝鲜设置国务监督官等内容都体现了其基于文明观的对朝鲜的蔑视。福泽的文明观是其对外观的理论基础。壬午兵变前福泽基于其文明观所提出的“东洋盟主论”的实质就是,以指导朝鲜、中国“文明开化”为借口,使日本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正当化。福泽对壬午兵变的认识也无不体现出“东洋盟主论”的思想。此后,由于中法战争的爆发以及甲申政变的失败,福泽的亚洲观由“东洋盟主论”逐渐地转向了“脱亚论”。
注释:
①目前国内有关壬午兵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晓刚,国宇:《“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政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97-104页;沈渭滨:《朝鲜“壬午兵变”与中韩关系论述》(上、下),《韩国研究论丛》第2、4辑,第188-208页、第250-269页;南昌龙:《日本侵略朝鲜与壬午兵变》,《外国问题研究》1983年第1期,第85-93页等。
②“支那”一词是战前日本对中国带有贬义的称呼,为保持历史语境感及福泽原著的原貌,笔者在引用原著的过程中保留了“支那”及其略语“支”在文中的使用。
③如未发表的儿童读本《日本历史》初稿、《劝学篇》第9篇、《文明论概略》第5卷、《朝鲜非退步而是停滞》(载《家庭丛谈》,1877年2月4日)、《通俗国权论》、《时事小言》、《神官之职务》(载《时事新报》,1882年4月9日)、《日本人如何做才能满足如今之日本》(载《时事新报》,1883年8月2日至3日)、《天皇海外巡幸》,(载《时事新报》,1884年2月2日至6日),《御驾亲征准备之如何》(载《时事新报》,1885年1月8日),《不吞并土地也可改革国事》载(《时事新报》1892年7月5日),《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载《时事新报》,1894年1月1日)等。
④福泽在写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的19世纪70年代,对儒学及其封建意识形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较为全面且尖锐的批判。之后的1882年至1884年间和1898年两个时期,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批判儒学的文章,如《不知汉学主义无效吗》、《儒教主义之后果十分可怕》、《儒教主义》、《德教之说》、《排外思想之系谱》、《排外思想儒教之主义》、《儒教主义之害在于其腐败》、《儒教复活之责在于今之当局者》、《我辈勿宁是古主义之主张者》等。
⑤根据直接或间接的材料可知,福泽在撰写《文明论概略》时“参照了威兰德的《伦理学原理》、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穆勒的《议会政治论》和《自由论》等著作”。(参见远山茂树著,翟新译:《福泽谕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巴克尔、基佐等人的文明构建都是在西方帝国殖民世界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福泽的文明观必然受到西方殖民主义文明观的影响。
⑥福泽在《时事小言》中指出,所谓的“延烧”就是:“让我们看一下预防火灾。假如我一家乃石屋,房屋相连之邻居乃木造板屋之时,绝不可安心。若为了巩固好火灾之预防,防护自家并为近邻进行预防,救援发生火灾之时自不用说,平安无事之时同其主人商量,紧要的乃让其建造和我家一样之石屋”。“或者根据时机也可强制其建造。或者当事情紧迫之时,毫不客气地掌管其土地,可以我之手重新建造。这并非真正地爱护邻居,又非憎恨,只是担心自家被延烧”。参见「時事小言」『福澤諭吉全集』第5巻、186-187頁。
⑦1882年3月31日,日本的大仓组社员儿玉朝次郎、三菱会社的大渊吉威和本愿寺的僧侣莲元宪诚无视朝日两国的外交规定,擅自超出规定的活动区域,在朝鲜安边府遭到约二三百名居民的袭击,其中莲元宪诚当场死亡,儿玉朝次郎和大渊吉威身受重伤。这就是所谓的“元山津事件”。
⑧此时,福泽应该还未得到闵妃没有被害的消息。
[1]青木功一.福泽谕吉的朝鲜观研究[A].朝鲜历史论集(下)[C].东京:龙溪书舍,1979.
[2]世界国尽[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M].东京:岩波书店,1959.
[3]高城幸一.壬午军乱以前福泽谕吉的朝鲜论[J].韩国日本文化学报,1999(7).
[4]罗丽馨.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的朝鲜观[J].台大历史学报,2006(38).
[5]黄俊杰.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内藤湖南为例[J].开放时代,2004(3).
[6]与亚洲各国之和平与战争同我们之荣辱无关[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3.
[7]要知论[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9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2.
[8]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通俗国权论[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M].东京:岩波书店,1959.
[10]时事小言[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M].东京:岩波书店,1959.
[11]论与朝鲜之交际[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3.
[12]坂野润治.“东洋盟主论”与“脱亚论”——明治中期亚洲进出论的两种类型[A].佐藤诚三郎,R·丁克曼.近代日本的对外态度[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
[13]朝鲜元山津之变报[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14]朝鲜与日本相似(漫言)[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15]必须向朝鲜政府要求[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16]朝鲜事变[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17]朝鲜事变续报余论[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18]大院君之政略[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19]朝鲜政略备考[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20]朝鲜政略[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21]出兵之要[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22]董顺擘.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23]朝鲜事件谈判之结果[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24]朝鲜新约之实行[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25]朝鲜之赔款50万元[A].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
[26]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M].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所谓“退还40万美元”,当指壬午兵变赔款50万美元中尚未偿付的部分,免于偿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