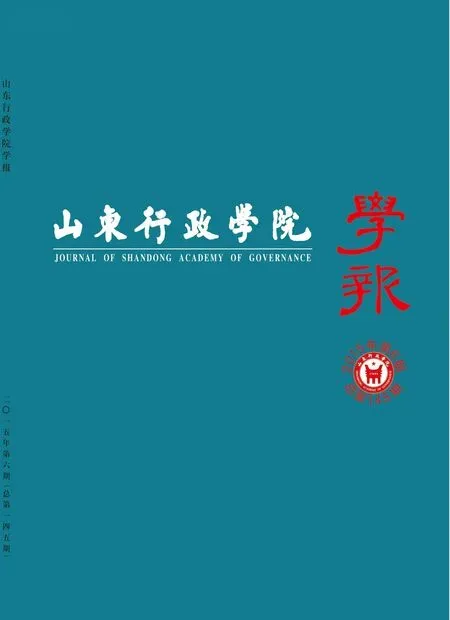浅析龚自珍矛盾的政治思想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龚自珍(1792年8月—1841年9月)是清代中后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作为当时第一个以衰世看待社会现实的士人,龚自珍继明清经世致用之学问,启近代图存变革之潮流,其政治思想之精华不仅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甚至对当代中国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1]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1)但诚如他生活的时代一样,龚自珍的政治思想批判与保守,现实与理想杂之,这不仅使他的政治思想难以呈体系化,削弱了其思想的作用效果,更使他本人及其思想如同堂吉诃德一样,一只盾牌掩护着旧世界,另一只长矛却刺向新世界,在自我矛盾中演绎着近代大门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完结的余韵悲歌。
龚自珍一生虽仕途坎坷,但著述颇丰,更在政治思想领域相继提出了治世、衰世、乱世三世循环与自改革,农宗平均和宾法君臣等宝贵思想,这都足以说明龚自珍是嘉道年间为数不多,不可回避的思想巨匠。但正如同龚自珍现实仕途坎坷与理想抱负远大的相向,他的政治思想也表现为批判满清统治者庸俗腐朽与强调忠君爱国相杂,这一现实写照的矛盾思想,一方面为早已消沉的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注入了生机活力,并为近代思想的异动和巨变谱写了序曲;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了没有摆脱传统士大夫固化思想束缚的龚自珍深陷传统儒学的迷茫与纠结。
一、政治哲学: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矛盾
龚自珍矛盾的政治思想的表现之一,即在政治哲学认知的模糊。“且吾与子何物?故曰:傈虫”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龚自珍视傈虫为人的本质,(2)“然而天地至老寿也,得傈虫而已”则进一步说明他所谓的傈虫贯穿时代世界发展的思想,(3)而“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的思想更凸显其看到了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和对理学崇尚圣人的质疑。(4)龚自珍将某种抽象的物质性的傈虫视为世界本原和注重众人之力的唯物色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为其批判五行之学,确立“先有下,而渐有上”的非传统天人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5)这在唯心主义的宋明理学占据思想主流的时代,应当说是十分珍贵的。但是,龚自珍又处处强调“自我”的决定性力量。“我性不齐……美丑之始……民我性不齐……是名善恶之始”,(6)龚自珍认为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文化伦理都是人自身的作用,并将“自我”作为世界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核心。龚自珍这一将“自我”作为世界原动力的主观唯心主义,对其政治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他虽然批判五行之学,对传统天命观有所怀疑,但无法看到传统天命观的要害,反而陷入既尊崇有批判的矛盾怪圈。正如“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7)龚自珍认为在人类形成之初,天人之间即是相通的,而“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更表现他承认上天与人一样是有意志的,客观上肯定了传统儒学天人感应的传统天命观。同时,龚自珍反复强调对鬼神要予以信服敬畏的态度,并十分看重鬼神祭祀的力量,“处处设立风神祠,泉神祠,岁时致祭,仰视上帝……颁祝文焉”可见他已将祭祀鬼神看作人性教化和地方治理的工具,(8)并认为鬼神与人的精神和魂魄是相通的,唯心色彩颇为浓厚,凸显了龚自珍对“自我”的过度强调。[2]
应当说,龚自珍的哲学思想颇似二元论,即王夫之的古代唯物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宋明理学等传统儒学相杂糅。(9)他既强调“自我”,又注重所谓“傈虫”,使其政治哲学思想陷入对立与矛盾之中。[3]这也凸显其思想缺少系统性,让他在矛盾之中无法对天命观有明确的认知,使他的思想依然在传统儒学的框架中修修补补,更使得其无论是对问题的发掘,还是措施的提出,大都简单落在人的因素上。[4]面对封建统治的危机,则大多归结于暴君专制,人才匮乏,提出的药方也都是君臣关系合一的宾法制,以德保民的开明君主政治等不彻底的改良,缺乏更加深入的对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批判与思想启蒙。
二、封建专制:批判与维系的矛盾
明清时代的封建社会已成衰落之势,而嘉道年间社会衰落的现实更已是不可逆转,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君臣关系日益恶化,文化思想暮气沉沉,流民流窜与农民起义更是如火如荼。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精英,龚自珍已敏锐洞察到当世“衰世”之照,并预料到“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他的诗歌创作和思想阐述,都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当权统治者的不满,而他对经世致用的重拾和对社会危机的反思,也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注入了动力。
龚自珍看到了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政治生态现状,并对君权予以“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猛烈批判,他认为当前的君主专制“去人之廉,去人之耻,震荡摧锄天下谦耻”,(10)压抑了士人阶层,出现“天下之子弟,心术怪而义理锢”的困局,(11)而龚自珍对满清封建统治者“得寻天下之私利”的本性揭露,(12)更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契合,表现了其对当权者腐朽专横的不满。同时,龚自珍利用天命观的思想,认为君主制度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宗法形式,直接否定了天理—君主的自上而下形式,触及到了传统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使其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深入到了新的层次。[5]
但是,天命观的保守和唯心又决定了龚自珍是一个尊君、崇君的坚定者,他认为君主“有父之严,有天之威”,(13)这凸显了其依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纲常伦教框架内。而“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更表现了龚自珍“君本”思想根深蒂固,(14)将尊君与尊天命相联系,与传统卫道士对君主威权的尊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龚自珍虽然强调君主对社会矛盾的产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认为“民之骄悍,不畏君上”也是社会危机形成的重要原因,(15)主张通过相平相齐的“君取孟焉,臣取勺焉,民取厄焉”的方式实现所谓平均。对待君主专制,龚自珍不乏对其黑暗的揭露和批判,但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旧时代士人,龚自珍无法真正突破传统儒学的君臣观、伦理观和天命观的束缚,并深受中庸之道的影响,这使得其陷入了对封建制度既批判又维系的矛盾中。[6]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也受君本思想的影响,强度和效果甚至都不及明清交际的黄宗羲等人。
三、思想精神:改良创新与保守传统的矛盾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而这正是建立在以“衰世”看现实的的基础上的,故而蕴含着丰富的改良因素。
(一)“私利论”的第二人
龚自珍的改革创新精神在于他的“私利本性”的思想。他认为“人之私,有功于私,无功于性”,强调现实中的性善道德,教化有美与本性并无关联,并以此作为“人必有私”的基础。在《论私》一书中,龚自珍多次强调私是普遍的,纯粹的大公无私是不存在的,认为“怀私者,人之情也”。(16)他又以“人尊其心”的角度批判理学压抑人的欲望的自然表达,颇有追求个性解放的抗禁欲主义色彩,更从人性的角度撼动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合理性。(17)
龚自珍的私利论与其主要居住生活地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有密切关系,并以此作为批判压抑人性,使士人充满奴性的君主专横统治的工具。虽然早在龚自珍200余年前的李贽已经提出 “夫私者,人之心也”的私利论,但在李贽之后再无人明确阐明私利论,虽然龚自珍的“私利”尚没有突破李贽的框架,但其敢于突破思想禁区,正视人的自然欲求,并将之作为批判现实士人与社会风俗败坏的武器,以凸显出其不拘泥于传统的勇气,作为倡导私利的第二人,在嘉道的陈腐时代已是超越现实的“异端”了。[7]
(二)首倡“宾法制”
龚自珍认为嘉道时期的君臣关系严重恶化,汉唐之际的君臣 “坐而论道”之朝仪制度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朝见常跪,夕见常跪之余,无此事矣”丑恶的主奴关系,(18)加之满清权贵的文字狱制造政治恐怖,不仅造成国家命运集君主一人的后果,更使庙堂之上尽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阿谀奉承的小人和按资排辈的迂腐之人。(19)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特别强调人的作用,认为人才质量和数量是区分三世的标准。面对政治社会腐朽现实,龚自珍认为必须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恢复“射策讽书”的形式。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宾法制,认为“王者正朔,用三代,天是以宾宾,宾也者”,(20)强调君主要更多地运用礼这一方式对待臣子,并试图通过这一法制,实现士人议政,对君主专权形成一种约束机制,最终实现君臣共治天下的目标。
仕途坎坷的龚自珍看透了封建官僚制的腐朽,创新性的提出了“以人才”为核心,“宾法”为手段的改良措施。[8]人才选拔与任用的不拘一格是宾法制的前提,而宾法制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保障,它们共同构成了其君臣合一的思想,而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思想家黄宗羲的 “君臣亦师亦友”的主张,这在当时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生态中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三)经略西北,严防外夷
龚自珍可谓博学,不仅精通经学、理学等儒家思想,同时深谙佛学、地理学、史学等多方面知识。他不仅提出了诸多切中时弊的理论思想,同时注重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而他的经略西北,严防外夷的思想正是这一 “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表现,是龚自珍对国防安全战略的一种改革构想,是其“自改革”思想在行政与军事上的体现。
乾隆中期准噶尔部问题的解决大小和卓叛乱的平定,新疆正式完整的纳入清朝版图,清朝统一全国战争彻底结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而统治者也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内政方面。但龚自珍认为国防安全依然十分严峻,当政者仍然有很多工作亟待处理。1820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通过研究沙俄对准格尔叛乱的暗中支持与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的历史,总结认为沙俄当局对新疆觊觎已久,西北塞防形势严峻,清朝虽设立伊犁将军等行政机构,但西北防务和行政架构远没有达到守土御敌的要求,主张新疆设省,改革屯田制,鼓励内地流民进入新疆,而使“公田变为私田……戍边变为土著”,(21)通过增加人力提升军力。同时,龚自珍在1823年就已看到了英国借鸦片侵略中国的野心,并认为侵略者会由海路进犯,为清廷提出了“曰得卒,曰得船”的治海之道,(22)颇具近代中国的“海防”思想。
虽然龚自珍尚没有对世界有着全面的认识,但在闭关锁的时代,他依然在努力地向外看,与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不知英国来自哪里,是否与俄罗斯接壤的清朝统治者和传统士大夫已经不在同一个层次。同时,他的这些思想蕴含着中国对外环境的理性认识成分,作为鸦片“严禁派”代表,他虽然强调对外夷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强硬立场,但认为中国面对俄罗斯,英国的侵略只能采取守势,这在他给林则徐的书信“非与彼战于海”中得到充分印证,(23)隐含着对中国军力落后的认识,但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龚自珍并没有对这一落后去做进一步认识。龚自珍对边防筹划的担忧后来大都不幸言中,但他的边防思想也为后人的塞防、海防构建提供了借鉴,正如李鸿章所说:“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24)
作为强调“自改革”的经世致用思想家,龚自珍站在了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前沿,其在诸多方面都有改良创新的精神,但作为长期受到儒家思想教育,在传统士大夫家族成长的知识分子,龚自珍依然没有摆脱自身阶级与时代的局限,诸多改革方式,或是缓解,或是空想,甚至以托古改制为原则,竭力维护旧的秩序。
(一)建农宗,现平均,以传统宗法维护封建土地所有
农宗和平均思想,是龚自珍基于农耕社会的现实在经济方面的主张,的确它们的立足点都有促进农业发展,缓和社会矛盾的成分,但农宗思想强调以古代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而这一宗法制在实际运用中必须通过以礼为核心的制度典章加以规范,应当说是一种变相的人治;而他所实现的平均更是有限平均,即只是缩小阶层的巨大差距,达到一种“贫不至于盗,贵不至于骄”的状态。
龚自珍认为上至国家政治制度,下到黎民百姓的社会风俗都是以农宗为源头,他的农宗与平均思想虽然有保民的成分,但其以血缘和等级色彩深重的宗法制为实现手段,可以说没有摆脱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更不会触及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龚自珍虽然讲求大小相齐,以此缓解严重的土地兼并给社会稳定造成的压力,但其以宗法制为手段实现农业发展的托古改制思想不仅不具有可行性,更违背了社会发展潮流,充分体现了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保守性。而龚自珍为实现农宗,更希望宗法制在社会各方面有所执行,强调重农抑商,抑制货币经济的发展,更是与明清交际的进步思潮有着一定差距。
(二)君本位,将一切改良限定在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前提
龚自珍虽然批判君主专制,揭露其压抑人性的种种弊端,但他并非要推翻君主专制,更没有对君主有否定之意,封建等级在龚自珍心中可谓根深蒂固。无论是宾法制,还是科举改革等政治改良思想,龚自珍的根本立足点是实现诸如汉唐盛世的开明君主专制,以求摆脱衰世之照,最终实现圣人之道的理想社会。同时,龚自珍认为现实社会衰落的责任不仅在统治者,还在“民之骄悍,不畏君上”,从而使社会风俗变坏。在表现其尊君崇君态度的同时,更蕴含着对广大人民的鄙夷。[9]正是由于龚自珍在尊君这一问题上的保守性,使得其对君主的批判更似对暴君政治的抨击,故而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也正是基于此,无论是农宗思想,还是政治改良思想,都没有摆脱传统儒学的框架,在根本上都在维护君主神圣权威与形象,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地主阶级士人阶层的利益最大化。[10]故而当我们全面审视龚自珍的政治思想时,会发现其思想精神充满着改革创新的批判性、先进性与保守传统的空想性、落后性的矛盾。
四、龚自珍矛盾式政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一)嘉道的太平粉饰与衰败没落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变化与特点是龚自珍矛盾思想产生的根本动因。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嘉道时代的评价颇为不高,并多以没落黑暗批判嘉道时代。但客观讲,龚自珍生活的嘉道时期并非晚清一般积贫积弱,虽积重难返,但仍有康乾盛世的余辉。首先,嘉道年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整体上尚未打破。经过川楚白莲教起义的结束和19世纪20年代新疆张格尔叛乱的失败,清朝地方战乱出现暂时低潮,而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官僚运作,还是地方政治、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表面上都依康乾之例。同时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龚自珍长期生活的江南地区,尚未经过大型战乱的影响,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依然较为繁荣,冶铁、造纸、纺织等手工业依然发展迅速,资本主义萌芽承接康乾盛世依然有所发展,而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世界50万以上人口城市江南地区占据半壁江山可表明,此时的中国农耕社会城市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25)龚自珍虽然以衰世之道看待当世,但他却认为这种衰世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是可以解决的,虽然龚自珍看到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统治弊端,但他却简单归为人的因素,甚至对满清统治者保有某种幻想,应当说嘉道时期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不能不对龚自珍的思想产生影响。
嘉道社会的危机四伏也是不争的事实。自乾隆末年的山东王伦起义(1774年)之始,康乾盛世已成强弩之末,并随时代的推进颓势愈发明显:1799年(嘉庆三年)权臣和珅查处自尽,其贪额之巨,房地之多深刻反映当时吏治的腐败混乱和土地兼并的严重,加之自然灾害的不断,地方起义更呈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1796年—1805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历史之长,涉及地域之广,耗费白银之多,严重削弱了清政权的统治力;1813年大乘教起义军攻入京畿重地,对清朝统治者给予沉重的心理打击;嘉道年间愈演愈烈的鸦片走私,使得白银外流,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主张经世致用的龚自珍早已感受到了当时万马齐喑、日之将西、木之将流的政治社会生态,并以衰世的视角对统治者、士人阶层的昏庸腐化予以猛烈批判,并试图以宾法制与农宗平均的自改革方式解决尚不为当时大部分人所注重的社会矛盾,并在这一过程中孕育了近代的思想元素,但衰世的没落与盛世的余辉让龚自珍虽看到种种社会危机,却难以正确把握他们深层次的原因,更无法预料到即将到来的乱世的疾风骤雨,反而其思想依然是传统的农耕时代观,并带有浓厚的盛世眷恋色彩。
(二)龚自珍的远大抱负与现实坎坷
当我们审视龚自珍的一生,其理想与现实差距甚大。一方面,龚自珍远大的理想抱负为其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人格基础。作为江南官宦后代,龚自珍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其天资聪慧,自幼属文,1814年(嘉庆十九年),年仅22岁的龚自珍著成《明良论》四篇,不仅突破了当时禁区,勇于评议时政之弊,更力图以此作为自己政治实践的指南。同时,龚自珍对改革家王安石推崇备至,虽然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其二度拜相,政治思想素以改革变法著称,并将自身政治理念践于国家施政,龚自珍自比王安石,甚至在科举中仿安石例行文,这也就不难解释其为何反复强调“一祖之法不足变,千夫之议无不靡,孰若自改革”的社会变革思想。(26)同是诗人的他,在情感自然流露的诗歌中也不乏展现慷慨激昂的呐喊,这些都无疑表现出其在政治仕途素有宏图大志,并在这种理想抱负中有着坚韧的变革决心和毅力。[11]
但另一方面,由于满清权贵长期奉行重满轻汉的统治政策和其自身性格原因,龚自珍的仕途可谓颇为坎坷。1829年(道光九年),历经六次会试自珍方中进士,但由于未能进入翰林,一直到其辞官回乡,一直担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等卑微官职。政治上的不顺使龚自珍更似以文人而非政治家的视角表现政治思想,他虽然认识到社会现实的种种黑暗与弊政,并提出了改良思想,但其部分思想措施不仅缺少现实可行性,更在某种程度是一种空想,经不起政治实践的检验。晚年于书院的自珍虽然对国事依然关注,并著《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但历经沧桑失意的他已将更多精力用于讲学、佛学和诗歌创作,而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其过早地暴亡,更使他矛盾的思想没有及时的整理和概括,在杂碎之中缺乏体系。
(三)理学的中流砥柱与异化腐朽
宋明理学自明朝成为官方哲学后,即确立了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并长期作为明清科举的重要考试内容,在嘉道年间仍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龚自珍出身官宦世家,读书文化气氛浓厚,20余年的科举考试生涯更使理学在龚自珍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了他汇百家之言的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龚自珍在现实中承蒙皇恩,不惜为清政府奔走效劳,为钦差大臣献言建策。同时,他阐述的思想大多实际却落脚于维系“有父之严,有天之威”的封建统治和“君取孟焉,臣取勺焉,民取厄焉”的封建等级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度,俨然一副封建士大夫卫道士的形象。龚自珍在自己的政治哲学中多次强调“我”的作用,“民我性不齐……是名善恶之始”等带有浓厚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观念,更凸显其思想深受陆王心学的影响。
然而,长期处于思想顶峰的宋明理学在嘉道年间早已丧失发展的活力,反而在成为专制统治工具后日益腐朽,不仅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仕途敲门砖,更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惨淡社会现实。由于龚自珍重要的启蒙老师,其外祖父师从清代著名理学批判家的戴震,龚自珍本人在学习宋明理学时也必然接触到对理学的批判思想,加之现世社会种种矛盾对其冲击,更促使他重拾明清鼎革兴盛的经世致用之学和对宋明理学的反思,特别是其“人性本私”的思想更是突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论调,彰显了他思想的闪光点和先进性。[12]但在宋明理学占据社会主导思想的时代,龚自珍的经世致用并没有对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有明显的超越,而对存天理,灭人欲有力批驳的“人性本私”思想也并未上升到对制度的构建和个性自由,社会民主及私有保护等思想深度,反而其大部分思想站在官僚儒学士大夫的立场,并诸如考据学,训诂学,经学等传统古学相融入杂碎,使其思想颇具保守成分,更使其改良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13]
结语
纵观龚自珍的政治思想,重拾了康乾盛世以来衰落的经世致用之学,称得上是当时社会的情侣表,正如日趋中落的嘉道时代矛盾突出,处于社会巨变的前夜,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也颇为矛盾。(27)龚自珍虽有唯物思想,但又强调“我”的唯心主义,并在现实失意中趋于佛学虚无的钻研,这也使得其政治哲学难以体系化,整体化;他虽然意识到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威胁,思想有一定的外向性,但却没有再深入探求其中原因和世界状态;他虽然对君主专制表现多重不满,但又主张尊君崇君,讲求君师合一,对君主政治充满幻想,这也使得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无法触及到制度本身,而只是在封建专制的大框架下修修补补,无法真正解决社会危机,虽站在近代的大门前,但无法预见近代思想的变革趋势。[14]而改良创新与传统保守的思想精神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虽能破旧,但远远达不到立新之效,更在杂碎之中难以有效实现思想解放与启蒙作用,伴随龚自珍暴死丹阳,他的思想也在近代的大门前戛然而止,在思想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28)
注释:
(1)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龚自珍思想“讥切时政,抵排专制”,颇使人“若受电然”;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释风[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28页.
(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释风[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29页.
(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壬葵之际胎观第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4页.
(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任葵之际胎观第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2页.
(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任葵之际胎观第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4页.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任葵之际胎观第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3页.
(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10页.
(9)王沛:论龚自珍思想的性质和评价[J],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沈论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20页.
(1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述思古子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参见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60页.
(1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沈论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20页.
(1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京师乐籍说[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17页.
(1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尊命[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3页.
(1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人笺八[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341页.
(1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68页.
(17)陈蕴茜,方之光:论龚自珍社会政治思想结构[J],《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1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31页.
(1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咏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471页.
(2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沈论四[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27页.
(2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00页—106页.
(2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定庵先生年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604页.
(2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70页.
(2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书番愚许君[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78页.
(25)西方史学家贝克罗经调查研究,认为清朝中国在1820年GDP占全球比重为28.7%,总量世界第一,后这一数据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引用,并认为农耕经济在当时仍处繁荣状态.
(2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七[M],台湾学者龙应台,朱维铮认为改革一词历史上最先即出自龚自珍之手.
(27)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J],社会科学,1993 年第1期.
(28)毛丹:晚清士的挽歌—重读龚自珍[J],杭州:浙江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郭延礼:龚自珍年谱[M],齐鲁书社1987年版.
[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3]陈铭:龚自珍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陈国庆:试论龚自珍哲学思想的学术价值[J],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3期.
[5]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平建东:龚自珍政治思想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
[7]冯天瑜,黄长义:晚晴经世实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8]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陈蕴茜,方之光:论龚自珍社会政治思想结构[J],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6期.
[10]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龙江:龚自珍变法思想研究[J],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4月.
[12]易梦红:关于龚自珍社会经济思想的评价问题[N],光明日报,1962年4月9日.
[13]吴松龄:龚自珍的政治经济思想有资本主义倾向吗?[N],光明日报,1961年11月3日.
[14]郭汉民,袁洪亮:近二十年龚自珍思想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