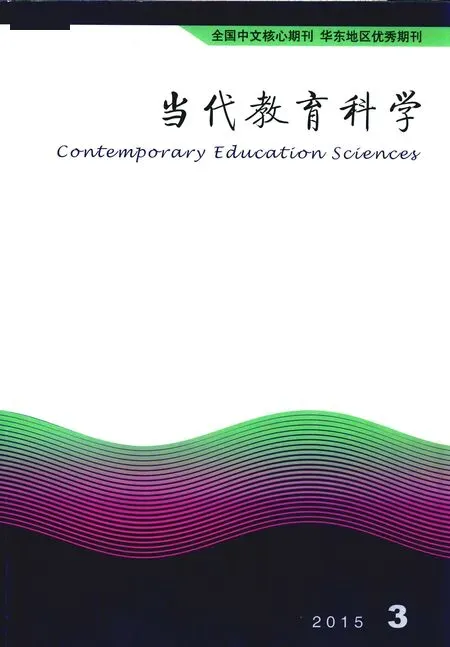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危机之始然与应然*
●阮朝辉
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危机之始然与应然*
●阮朝辉
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危机源自群体精神之爱的单一性、爱的迷乱以及因可量化而方可被认知世界观和对结果至上理论的误读,大学精神建构缺乏完整的先天基础。要重构我国大学精神就必须建基于大爱、大智、止于至善。大学存在的实事性是因为大学是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有机体。至善精神不仅是指导、引导大学物质建设和引领大学升向神性、人性的本己之力,而且具有净化、纯化社会及群体精神德性并趋向至善的引领功能。
现象学;大学精神;大学实体
现象学第二泰斗Max Scheler(舍勒)说:“大学是古老的、稳定的、已知的和经受住考验的存在,它是几百年来历史的产物;对国民的思想、本质、目标和组织产生深刻影响……是‘totum’(充满活力的)、整体的、包罗万象的,是代表着知识和教育的‘最高综合体’(Universitt)。”[1]该论断不仅发展了德国现代大学改革的鼻祖——洪堡(Humboldt)的大学的本质观念,而且奠基了现象学直观的现代大学本质及其精神的应然与必然。
一、我国当代大学精神之实然与始然
随着我国当代大学的快速扩张,不但呈现出大学(University)与学院(College)的功能相混淆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大学精神的严重危机——不少大学已经下滑成了“为了就业的职业培训机构”。所有人都希望接受大学教育,但所有人都在怨恨和怀疑当前的大学还是不是大学、大学教育还是不是大学教育本身。不少学者都深感我国当代许多大学的办学理念倍受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至上理论的影响,大学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看重知识技能传授忽视至善人格养育、推崇实证科学的应用价值轻视人文科学的精神建构、看重大学的规模效应而内涵发展亟待大力提高等等,导致近几十年来大师和杰出人才越来越少、整个社会德性欺罔、精神溃散、全民处于娱乐至死的恐惧之中……进行基于回到大学生活本身的现象学直观,也不难发现生成当前我国大学精神危机实然之始然。
其一,群体至善之爱的迷乱使大学精神建构缺乏先天至善的始基。
大学精神是一种群体精神,而西方大学精神建构之始基原本源自至善之爱——绝对之“神爱”,虽然经历了政教分离的中世纪、资本主义个人至上以及当代人本主义的发展,但其本源——精神至善之爱并未发生质变。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精神,在其生成之初,原本是脱胎于中国古代书院的明德至善——注重修身养性、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兼顾经济天下、实业救国等,但经过战乱洗礼和个人绝对崇拜的冲击,我国当代大学精神之爱之所爱者的始基发生了错乱——从至善人格、止于至善精神之爱为主导变成了物质、实证科学、宰制自然、救赎经济及愉悦肉身之爱为主导之爱。
爱是一切的原动力,爱的错乱必然导致行为及其结果的无序与失范。我国当代大学精神的群体之爱从止于至善之爱转型为人的生命、实体经济与宰制自然的救赎之爱,使我国当代(后现代)大学精神建构之始基在爱之所爱者本身就显得极为脆弱、极度迷茫——生命(肉身)、实体经济、宰制自然的物质化救赎原本就是此时此在的、快速变异的、发展的、永不满足的、自私的、甚至会毁灭的,不是群体共认共在的、永恒的、所在的。因此,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危机的先验始基就是因为爱的迷乱——只奠基于爱的暂时、自私、此在的物化样式,是摒弃了止于至善精神之爱为基础的纯物欲建构,而不是奠基于社会、群体、人格至善的爱的发展与升向永恒。简言之,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建构是抛弃了精神至善及其信仰的爱的先天基础的,或者说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建构是摒弃至善精神或重视不够之爱的建设。在群体精神的爱之所爱中,精神与物质至善之爱是有机统一的,而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建构之始基及其建构过程只强调物质之爱而忽视、忽略了精神之爱,这种以迷乱、单一而残缺之爱为始基的大学精神建构,陷入危机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其二,从绝对政治化向经济科技化转型,大学在功能转型中忽视了精神的建构。
我国在十年文革动荡期间,真正意义的大学已经名存实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开始恢复大学功能,重构大学精神;大学在弃绝对政治化的过程中寻找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大学之间的一个接洽点——培养经济社会的建设者、加快大学基础设施(物质)建设、加速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接洽点使我国大学从绝对政治从属机构转型为以科技、实业、就业为核心的人力资源培训中心。由于大学教育以科技、实业、就业为价值核心,使大学的资本化、实物化、功利化被强化;在赢得大学产业化的“欣欣向荣”的进程中,实证科学也在大学和整个社会中被推上了绝对优势地位。实证科学的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物化世界、物化观念快速弱化了人文科学、精神科学在人和大学生活之中的本真意义及其主导地位,使我国当代大学快速滑向了实物绝对化追求之中,这也就是公众怀疑和怨恨我国当代大学及其教化效果、大学精神残缺又一原因之所在。
其三,从物质困窘的人走向物质丰盈的人,使物欲化大学逐渐弱化了神圣化大学。
应用技术及资本化、娱乐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大学精神的嬗变——使仅有的至善精神正在被全民娱乐需求所取代。随着实证科学所带来的技术革命及其成果的快速生活化、娱乐化应用,实证科学的“繁荣”所带来的物质丰盈既使人和大学享乐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富足,使人沉浸于宰制世界能力的绝对自信和膨胀之中,也使人和大学原本的自然崇拜、至善精神的信仰转化成了对实证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商业经济等)以及量化世界的笃信和享乐主义的蔓延,也使大学培养工商业经营精英、实证科学技术人才、政经合一的行政精英的功能快速弱化了大学培养智者、政教合一的精英的功能——物化的大学精神逐渐主导了神圣的、理性的人和大学的精神,“象牙塔”的大学精神已经被物化世界彻底遮蔽和淹没。
大学和人一样,“既不是对象也不是物的存在,而是一个时刻在自己身上产生着的行为的秩序结构”。[2]人是唯一能把世界、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灵具象化的存在,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组织、知识的圣殿也必须是精神、灵性与物质的统一体,因此,不仅人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大学也必须有物质和精神建构的需要。但是,现实的大学却只关注了物质建设的快速推进,不自觉地使物质丰盈弱化着至善精神的建构,也就使大学成了“大楼林立的机构”,而找不到大师的身影——从大学的管理机构到大学的经营者、大学生等无一不沉浸在物质丰盈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愉悦的绝对自信之中;但又时刻迷茫、恐惧于至善精神的绝对空虚与无助之中。当然,正是这种物质丰盈与至善精神空虚的矛盾,才导致了有识之士对我国当代大学精神的追问、呼吁、探索、重构与再造。
其四,精神科学的非量化属性使大学精神难以进入唯科学主义的直观范畴。
实证科学、唯科学主义除了打着科学的旗号对人和大学的精神需求严加拒斥外,实证科学、技术生产本身并不能对人和大学的精神进行“量化”和“证实”,这就使得人和大学陷入了物质丰盈与精神空虚的价值迷惘之中——不仅迷失了人和大学生活的本真意义,也深深地陷入了实证科学的价值欺罔和发展创新的人性危机之中——既追求更大的物质丰盈,又抵制实证科学的非人性。胡塞尔在对欧洲科学危机进行现象学审视时早就说过:“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3]不仅如此,实证科学和唯科学主义的泛滥使得大学至善精神也快速地被“唯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所取代和遮蔽——一切似乎只有可量化、可证实、技术化才是可接受、可认同、有价值的存在,而那些对人来说具有真正意义的、又不可量化的精神质料就被忽视和遮蔽了。大学至善精神就在实证科学、技术之上的思想中迷失自己,养成了实证科学、技术化的世界观及其价值取向。
当然,不能完全归责于实证科学、技术至上的存在。实证科学和技术化不仅带来了物质的繁荣,而且也带来了人的“享乐精神”的无限扩展、无限未知,也使世界充满了前进的不竭动力。但是,大学作为精英人才汇集、养育的圣殿,因人的存在和发展是精神与物质的同构并升向至善,而使大学本身的精神性存在成为不可或缺。但是,精神知识、精神产品、精神存在本身就是不可量化也不可能量化的存在,在一切以因可量化方可被认知、被评价的价值观中,大学精神、人的精神也就自然不被纳入能评价方可被建设的范畴而不得不被漠视、被遮蔽。
其五,结果至上的误读与世界能量化理论的泛滥,导致大学精神的功利化趋向被强化。
教育人格养育和智慧技能培育的过程,接受大学教育也不是人存在与发展的结果,而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人的自我至善化的建构过程。但是,由于结果至上理论的误读和世界因可测量、可量化而被认知的理论的泛滥,虽然在数量上造成了大学产业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表象的“繁荣”,但从本质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是在校生、毕业生在数和量上的快速扩大,而是共认至善精神和至善人格的培育及其时代至善精神引领的普遍化、普惠化。大学教育,绝不是把人“生产成产品”或“艺术品”,人的塑造和成形与艺术和工农业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判定大学之在,绝不是能以其给社会或已经给社会输送了多少“教育产品”——大学生为价值尺度,而必须以其能为社会和已经为社会培养了多少“健全人格”(“全人”)的人以及对时代趋向至善发挥了多大引领作用为价值标准。所以,大学精神建构决不能曲解结果至上理论,更不能以结果至上理论作为大学精神建构、人才培养的哲学观念。
二、大学精神的应然
“精神是实事性(Sachlichkeit),是纯净和纯粹的现实性(Aktualitt),是可由事物的具体存在本身规定的特性。”[4]舍勒对“精神”的这一界定,不仅适用于人之为人本身,也适用于“大师之学府”的大学。
大学精神是一种群体精神,这一群体精神是在大学创建之初或转型的某个特定阶段,由大学校长及其领导团队、师生一起基于大学的本质而推崇、建构的实事性和纯粹的现实性,是由具体大学的所有师生员工共认并长期为之奋斗而养成的崇尚学术、真理、大爱、自由、止于至善、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担当责任等的价值追求与群体意识等升华之后的实事性和现实性。大学精神的核心即大学本身,既不是对象的存在,也不是物的存在,而是在大学发展进程中养成的(本质规定的)的秩序结构。这个秩序结构既来自社会至善精神及其价值的共认与推崇,也来自具体大学师生的自律、自觉与自信。正如云南大学的董云川教授所言:“大学精神听起来抽象,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亦即‘有而不在’之实在,而且在大学组织中无所不在,表现之一就在大学人的言语、眉目和举手投足之间。”[5]不仅如此,至善的大学精神对大学的世俗化、产业化、商业化等进程进行引导和控制,使大学的人(师生)和大学的物(大楼、图书馆、林荫道、实验室等)以及大学的理念、价值观念、理性思考、学术创新乃至整个社会进行观念的指导、引导,对民族及其个体的非理性欲望进行抑制(drangsale)和规劝。
大学精神是超时空的存在,是持续的、后延的、扩展的存在,是圣洁的、充满活力和感召力的存在。大学精神的超时空性是因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不因作为物质实体形态的大学的时空位移、师生变化而发生质变——这一群体精神始终高扬传承高深知识和指导、引导至善社会精神建构,担负起高深知识、至善精神、拯救社会的重任而不断扩展、建构自身的至善性。大学精神具有持续性、后延性、扩展性是因为作为群体精神的大学精神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的、固定不变的、先验的存在;大学精神的形成是对大学至善价值偏爱的一个长期养育、发展的过程,这种至善价值偏爱既可以促进大学精神的进步与发展,当然,如果对善之善者本身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这种价值偏爱也可导致大学精神的倒退或衰落(这似乎也是我国当代大学危机之源之一,甚至是根本性因素)。大学精神的圣洁性和感召力潜藏于大学精神对人和社会的无声、无形的感召引导之中,通过人的参与,通过人的投入和积极的认同行动,通过人分享大学及其精神的现实性,人通过对大学生命体的、物化形态的、人的活动展示大学精神无形而巨大的感召力、净化力、纯化力。
大学精神的产生与升向至善有着中西差异。西方大学精神建基于宗教,建基于神性的向往和人性自我原罪的救赎,即使经历了中世纪的神学至上、工业时代的技术理性与当前数字时代的人性至上等的变迁,大学精神的至善性的本质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因西方大学精神建基于人文(神、上帝)精神且超拔于政治理念和实证科学之上,因西方大学精神的向神性的本质,从而赢得了西方社会的推崇和扶持——为大学自治、教学自由赢得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建基于政治和国家实体经济建设之中,由于我国根深蒂固的集权文化,进而因各大学校长及其团队对大学精神实质的被集权化认识而呈现出不同大学精神在特定时期的不同的实事性——有的大学几十年来不仅有着让世人景仰的精神感召力,而且可量化的办学效果也让市民敬佩,但是有的大学几十年了也未让人认可其存在。因缺乏至善精神而成为一个缺乏活力的“人力资源训练机构”,这也正是我国当代大学教育危机的根本所在。
大学作为以培养至善人格为核心的“小社会”,大学是物质和精神有机统一的、具有灵性的实在。对大学精神的秩序结构的界说,目前学界也众说纷纭。四川大学刘莘认为大学精神表现为自由的公民精神、正义等,[6]复旦大学杜作润教授认为大学精神显现为创造、科学意识、独立意识、实践等[7]……事实上,基于回到大学本身的直观可发现,“大爱”、“大智”、“明德”、“止于至善”不仅是群体精神长青的实事性,也是大学精神秩序结构永恒的实事性。
首先,大学精神奠基于和扩展着“大爱”。大爱者,爱人、爱国、爱科学、爱自由、爱真理也。舍勒说“爱优先于认识”、“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之母……爱是宇宙和整体世界诸位格的中心”。[8]也就是说,有爱才有了大学,爱优先于大学存在,大学因师生群体的爱人、爱国、爱自由、爱真理而显现其实事性,在爱的建构中彰显、承载大学精神之实在。大学因为有爱,才为人和大学本身的生命注入了活力。可以说,谁把握了一所大学的爱的秩序,谁就理解了这所大学、理解了这所大学的精神之在(being)。以至爱建设物质和精神一体的大学,才有大学至爱之所在。
其次,大学精神承载和发展着大智慧。大智者,大师之智慧也。“大师,就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众人所尊崇的人。”[9]大学之大体现其“有容乃大”:不仅有不同的学科,关键在于有不同学术观点、造诣精湛的大师群;大学不仅是大师云集之地,而且是培养大师的场所。大师之大,不仅在于其学术造诣精湛和传授了高深学问,更在于其典范人格被尊崇和效仿。“大学必须把高深的学问转化为智慧,只有真正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按照人类的需要组合起来并满足人们的希望时,智慧就从知识背后呈现出来了。”[10]简言之,因大学精神有大爱,则必吸引、培育出大师;因大师有大爱、大智、大德,则必教化、引领才俊与科学技术、民族社会发展指向至善方向。
再次,大学精神传承和升华着明德。对现代大学而言,大学之道,在于大爱、大智,在于崇尚自由、追求真理、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学习自由(Lernfreiheit)必须自律、“慎独”、“毋自欺”。也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决定教育成功的因素,不在于语言的天才、数学的头脑或者实用的本领,而在于具备精神受震撼的内在准备。”[11]当代大学在反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限度中扩展其精神之在。“学术自由既要对社会进行谴责而与此同时又要对社会负责……应划清言论和行动的界限。”[12]当代大学的危机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人性的危机、精神信仰的迷失,尤其是大学之人(师生)至善精神迷失、无限的欲求与科学快速发展导致的人性与信仰的迷失所诱发的危机。
最后,大学精神承载和指导着社会至善精神的建构。“现代大学凭借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发挥着社会精神领袖的作用。”[1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大学不仅是高深学问的殿堂,而且是人类至善精神的圣殿。“止于至善”不仅是中国古今人格养育的最高追求,也是世界各国大学精神的共同的最高存在。舍勒说,“引发本能压抑的,正是精神。”[14]虽然精神本身并不能创造或消除任何本能,但是精神可以对本能冲动进行控制和引导。大学精神也是如此。大学精神并不能直接消除大学的此在危机,但是大学止于至善的精神可以控制和引导大学行动的无序、人性残缺的本能冲动,可以对大学的人及其观念和行动进行理性的指导、纯化、净化,最终促进大学至善精神的升华。在大学止于至善精神的感召、拉拢之中,大学师生以及整个社会都会不自觉地被其吸引、主动投入积极向善的未来,并在其中获得自我救赎。大学也只有超拔于绝对物化的世界、享乐化的世俗生活,回归其为了人和社会的至善,担当起引领社会集体向善的责任,才能扩展其至善性、彰显其人类灵魂净化的“象牙塔”的本质。
三、大学精神的实事性
康德说,“人是唯一必须接受教育的被造物……人是需要保育和塑造的存在。”[15]在大学教育已经世俗化的我国当代,大学已经是国人精神、政治、科技等文明的引领者;大学从其但是至今绝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播或研究机构,而是以人为中心的、为了人类及社会至善精神和生命有机统一的存在,其精神和世界的发展直接影响或救赎着人类及大学自身之在。
在多大程度上把大学止于至善精神的实事性实现在大学及人身上,并展示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欲求中,就在多大程度上使大学至善精神得以存在。作为最高教育机构的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和建构着至善精神与自我发展的完美结合,就在多大程度上趋近了它最高目标——止于至善的实现。换言之,大学精神是大学实体的观念化,只有大学实体把其止于至善的精神投入到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进程之中,并把该精神变成现实(无论是从最简单的知识传播行为,还是一直到完成最具精神意愿的人的培养上,都是如此的时候),大学实体与大学精神就最终真正展示了它的“大”之所在。
大学精神与大学实体的关系就如同人的生命与人的精神的关联,“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16]精神与生命绝不是“二元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生命是精神承载之基,而精神则使生命具有灵性,“生命的本能可以进入精神的法则和观念及意义结构之中;精神为生命指明方向。”[17]对大学实体与大学精神之关联也适用于该定论:大学精神引导和控制大学实体建构形态和范围;大学实体建构过程升华凝聚成大学精神,并承载大学精神的此在形式。
“大学精神是体现大学的智慧、气度、品格、信念、风范、操守等的核心文化体系。在大学的发展中凝聚、激励、导向、保障和熏陶等重要功能,对大学的思想、观念、制度、机制、行为等,具有全面统辖的作用和意义。”[18]因此,“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前提。守住大学精神,就保住了大学的‘根’和‘脉’”。[19]大学精神不仅统辖大学文化、置身大学中的人(师生员工),而且还引领群体、社会至善精神的建构。引领群体及社会观念变革的正是大学及其精神(在无神论哲学观念下的我国更是如此)——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通过其信仰、行为、观念、文化传承、学术研究、教育教学、科技发明等承载和显现大学精神之在;大学精神从置身其中的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学校文化建设等方面呈现出来,并扩展到社会各领域、各层级之中,也以其“有容乃大”的包容、吸纳世界之至善精神扩展其精神之在和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
从微观视角而论,大学精神的实事性就在于它统辖、指导大学的教风、学风、制度、建筑、师资、课程设计与实施、学术研究、科技创新等建设,并显现、扩展于其中。因此,一所守住了大学精神“根”和“脉”的大学,就为其校园建设、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师生的发展等实体建构寻找、构建了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超拔于职业训练及科学研究之上的文化。
总之,大学精神绝不是一个量化的存在,而是一个体验性的存在;大学精神的实事性寓于大学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指导、引导着大学可量化功能建构过程及其价值判断。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以养育至善人格为本和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就等同于大学没有灵魂;就会缺乏凝聚力、生命力和教育引领力;也就失去了大学存在的本己价值、实事价值、活力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对当代大学而言,是否建构起以养育之善人格为本和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是衡量大学乃至民族强弱的重要尺度。
[1][德]Max Scheler.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A.Francke AG.Verlag.Bern Dritte,durchfesehene Auflage 1980:p383-420,Universitt und Volksbocbschule.
[2][8][德]Max Scheler.舍勒选集(下)[M].林克译.刘小枫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338,751.
[3]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
[4][14][17][德]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李伯杰译,刘小枫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20,22,52.
[5]董云川,刘永存.再谈大学精神[J].大学,2012,(4).
[6]刘莘.哲学视野中的大学精神与文化自觉[J].哲学研究,2012,(5).
[7]杜作润.大学精神何处觅[J].高教论坛,2012,(7).
[9]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94.
[10][12][美]John S.Brubacher.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41,52.
[11][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09.
[13]徐辉,季诚钧.大学教学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92.
[15][德]Immanuel Kant.Band XI.Theorie-Werkausgabe Immanuel Kant,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2-193,Frankfurt am Main,1981,1.
[16][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24.
[18]蒲芝权.守望大学精神[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312.
[19]张晋衡.大学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122.
(责任编辑:刘丙元)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现象学直观的大学教学论”(11YJA880084)和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招标项目“‘致良知’与大学教学危机”(JD2013169)、贵阳学院重点支持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阮朝辉/贵阳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