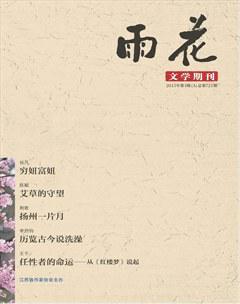苇叶青青
刘绍英
1
芦苇荡里的苇叶又青了。泥鳅和爹收完网,爹坐后舱煮饭。泥鳅望一河的碧水,有一丝儿风,水波就荡过来又荡过来。泥鳅,没事就把渔网晾起来,不放夜网了。爹把话从船尾递到船头。
就晾。泥鳅把话从船头又递过去。泥鳅瞅一眼爹,没挪身子。远处从芦苇荡里划出一只小船,船头船尾的红衣黄衣就亮丽了河面,亮丽了泥鳅的眼。
泥鳅说,爹,小苇和她娘来了。泥鳅爹一只手搭在额头,眼角的皱纹顿时密集成一
堆,脸就微微红了。捉个鲫鱼来。爹吩咐泥鳅。哎。泥鳅答得快,就动了身子,在舱里捉鱼。鱼有些
不安分,扑哧扑哧摆着尾,溅了泥鳅一脸的水。把你杀了,煮汤吃,看你还跳。泥鳅嬉笑着捉了一条
鲫鱼,交给爹剖肚。泥鳅爹,有饭吃啵?小苇娘隔老远把话送过来。泥鳅爹就答,有。刚打上来的新鲜鲫鱼。
小苇,俺娘俩口福好。娘看一眼小苇。小苇笑,不答。桨声咿呀,小苇娘就让船靠近了泥鳅家的座船。泥
鳅把小船的绳索绑在了自家的船上,扶一把船头的小苇,小苇上了座船,小苇娘也跟着过了船。
鱼丢进了锅里,小苇娘看着锅里的鱼说,泥鳅爹,明天我让小苇和王家的两个女儿出去打工,让小苇自己挣点嫁妆。回来就和泥鳅成亲。小苇娘说完,不再看鱼,看泥鳅爹。
泥鳅爹不说话,把眼睛投向泥鳅。泥鳅问小苇,决定了?决定了。小苇点头。吃过饭,小苇娘说,泥鳅,你就等小苇一年,过年小苇回来,就把你俩的事办了。泥鳅看着小苇的身子已过了
船,想跟去单独和小苇说会儿话,小苇娘把他拉住了。泥鳅看着红衣黄衣慢慢飘远去,才把心思收回来。爹,你说,小苇会不会变心?不会不会。那丫头我看着长大的。都说好了,她回来
就让你俩成亲。晚霞逐渐朦胧起来,偶有一两只沙鸥把河水弄出一点点响声。泥鳅闷闷地说,她要变心,我也没得法。不会不会。她娘同我讲过,你俩成了亲,她就与我搭伙过日子。就怕外面有人喜欢他,到时她不肯回来。泥鳅还是不踏实。屁话!小苇是那样的人?爹呵斥泥鳅一句,其实心里也没有底。两人的心思都装满了河。两人又任由一河的心思随岸边的苇叶摇过来又摇过去。爹说,泥鳅,你明天去送送小苇。给她打张车票。泥鳅就答应了一声。车子喘着气,留给泥鳅一溜烟就再也看不见了。泥鳅怏怏怅怅地回来。小苇娘的小船绑在自家的座船边。泥鳅在岸上咳嗽几声,泥鳅爹从舱里探出了头问,小苇走了?走了。小苇娘也从舱里出来说,泥鳅,你安心,小苇是听话的娃,我都交代了。她爹死得早,她不敢不听我的话。泥鳅笑了笑,不吭声。没有等到过年,小苇就和王家的两个女儿回来了。跟小苇回来的还有一个脸上长满青春痘的男人。王家的女儿说,青春痘家里有钱得很。小苇娘把女儿接上船也把青春痘接上了船。晚上,泥鳅爹划了只小船过来。小苇娘,小苇可是回来了?泥鳅爹边问边过了船裆。回来了回来了。刚回来。小苇娘眼里掠过一丝惊慌。小苇大大方方地从篷船舱里钻了出来说,大伯,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泥鳅爹心里有些慌,不自觉地就多看了舱内的青春痘几眼,又不甘心地问,还去?小苇看一眼青春痘说,还去。还想接我娘去。泥鳅爹不再说话,抽了支烟就过小船要走。小苇娘扯住他的衣襟说,小苇给你带了条烟,娃的心意。别的事,娃大了,我也管不了了。小苇娘说完叹了口气。泥鳅爹把小苇娘塞烟的手挡了回来说,这么好的烟我没福气抽,留给你家里的客人抽。说着,人过到了自家的船上。月色中,船和人拖着影子,一桨一桨地让船荡走了。泥鳅在小船上看岸上青青的苇叶,密密匝匝涨满心思。小苇娘悠悠的声音传过来。我不跟小苇走,我放不下你。泥鳅爹说,这事儿不好说了,我老了,我有泥鳅。小苇接你,你迟早也要走的。我不走,我服侍你父子俩。我不要人服侍。我泥鳅迟早还是要找婆娘的。你不留我?你还是走吧。老了都靠儿女。泥鳅爹说完,两行泪滴落下来。我送你回去。泥鳅爹起身。小苇娘抹一把眼泪就过了船。小船向茂密的芦苇荡深处划去。
2
芦苇以秋天的姿势在澧水中游滩头无语地站立。秋风起时,芦苇花的飞絮层层飘落在河面,只几天,就把芦苇荡吹成了一个白头老人。
爹卖完鱼,在集市上喝了口小酒,一路云里雾里地哼着小调回到了船上。
船上的篷杆上晾着泥鳅和爹的几件粗布衣。风儿一吹,那沾着芦苇花的蓝色灰色的衣服就左右飘飞。爹看了,就扯着公鸭嗓门喊了两声泥鳅。
高亢的声音在河面回旋,又飘远去。泥鳅从舱里探出头,不耐烦地说,晓得你回来了。
爹。那你还阴着不吭声?我在舱里钉扣子。扣子脱了。爹忽然觉得有些内疚。泥鳅娘死得早,这眼下泥
鳅也是三十左右的人了。那时指望小苇能与泥鳅成亲的,无奈,小苇出去打工就变了心,唉,是该给泥鳅寻个婆娘了。
爹上了船,放下了鱼篮,把一叠钱递给泥鳅,泥鳅数
了数,把钱收进了一个人造革的挎包。爹说,都攒着给你娶媳妇用的。中午,泥鳅和爹放了丝网,吃了饭,就缩在舱里休
息,泥鳅听见岸边有细细的声音在喊船老板。泥鳅从舱里钻出来。芦苇滩头,有一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正向他招着
手。泥鳅问,喊我?女子答,喊你。麻烦师傅渡我过河。爹听见了,对泥鳅说,泥鳅,你渡她过河,收点钱。
听口音是个外乡人。泥鳅松了拴船的绳索,把船一桨一桨地摇到了女子
站立的芦苇滩头。女子把孩子抱起,就上了船。泥鳅问,怎么从这里过河?芦苇荡里有好几里陂
地。女子说,不瞒师傅,带个孩子出来要饭的。家乡遭了水灾,不认得路。泥鳅一惊,想起爹要跟这女子收钱的事。那桨划动水面的声音就轻了许多。师傅,你船上有饭啵?孩子饿了。女子期期艾艾地说。泥鳅又一惊,连忙回答,有,有点剩饭。泥鳅扳了左桨,把小船调转方向,朝着座船划去。
泥鳅招呼女子和小孩过了船裆,把锅里的饭给女子和小孩各盛了一碗。爹不明白地一会儿望望女子和小孩,一会儿望望泥鳅。女子和小孩的确饿了,一碗饭只几口就扒完了。女子咽下最后一口饭,看了一眼空锅说,真是谢谢了。我们今天还没吃饭哩!
泥鳅说,没多的饭了,只能压一压。爹问,这小孩是你儿子?女子立刻红了脸说,我还没结婚。然后摸了摸小孩
的头,又说,邻居的儿子。是个哑巴。他父母都被大水淹死了。把他带出来寻个活路。
爹瞅女子和孩子可怜的模样,忽然动了一个念头:我泥鳅也三十左右的人了,何不把这女子留下?让她跟泥鳅过日子,白捡个媳妇和儿子。爹一下振作起来,向泥鳅使个眼色,就问女子,愿不愿意留在我们船上?
女子也看了一眼泥鳅,连连点头。泥鳅明白爹的意思,跟爹摆手说,不能咧,不好咧,爹。爹双眼瞪着泥鳅,骂一声,混账小子,莫不还惦记小
苇?泥鳅再无话。晚饭是女子做的。吃了晚饭,泥鳅把锚链搭在陂
地,让座船靠在岸边,跟女子说,要解手,就上岸。女子感激地点了点头。晚上,泥鳅点了马灯,和爹去收夜网。泥鳅和爹都
很兴奋,四周静得只有打上来的鱼儿活蹦乱跳的声音。爹以过来人的口气跟泥鳅说,女子虽是外乡人,不明底细,可你对她好,就能拴住她的心了。那孩子跟着我们,总比他要饭强多了。今后你们有了儿子,也算有个兄弟。
泥鳅说,这事情想着不像那么回事,爹。爹骂,又在想小苇?泥鳅不吭声了。丝网在父子俩不说话的时候就收完了。泥鳅用捞蔸
舀一下舱里的鱼说,怕有好几十斤咧,爹。爹把小船向座船方向划去。泥鳅把小船的绳索系在座船上,提了马灯,就过了
船裆。泥鳅把眼光投向女子和小孩睡的中舱,蓦然一
惊,那女子呢?女子和那小孩已不在船上。中舱一片狼藉。泥鳅爬到中舱,去看放钱的人造革皮包,皮包已不
翼而飞。泥鳅叫了一声爹,就瘫坐在舱内。
泥鳅爹望一眼岸上静谧漆黑的芦苇荡,女子和小孩的身影早被黑夜掩埋。一行泪水无声地从爹的脸上滴落下来。
天亮时,爹和泥鳅都没去卖鱼,父子俩呆坐在船头,任由秋风把芦苇花的飞絮吹落在头上和身上。太阳慢慢地升高,渔网上的鱼在阳光的晒烤下,逐渐散发出了阵阵臭味。
3
岸边的芦苇收割完毕,一捆一捆安静地卧在芦苇滩。澧水河日渐消瘦,苗条得像一条绿腰带。刷刷的一
阵秋雨过后,天气就凉了。
泥鳅和爹把几条丝网放在河里,整天都懒得收。澧水河的鱼安静地沉入了水底,只在阳光和好的时候,一两条浮出来觅食,就成了泥鳅和爹的下酒菜。
泥鳅看着爹皱着眉从嘴里吐出的烟雾,闷闷地说,爹,我去城里打点短工,要不,这个冬咋过?爹把望向空旷芦苇荡的目光收回,看了看泥鳅,点了
点头说,也好,反正也打不到鱼。泥鳅背包一打,就上了岸。泥鳅没费多少力气,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事做。
工地包工头扔给泥鳅两只灰桶说,一天20元钱,月底结工资。泥鳅默默地捡起了地上的灰桶。工地上,就有了泥鳅勤快忙碌的身影。
吃过晚饭,工地歇了。那些工友洗掉了一身的泥水,换上了体面的衣裳,在城里找各自的乐子去了。泥鳅上街买了两斤毛线,就回到了工地。
做饭的阿春看见泥鳅提了一袋毛线回来,就问,泥
鳅师傅,给媳妇买的毛线?泥鳅红了脸说,买给我爹的,我还没媳妇。那要请谁帮你织?泥鳅说,我自己织。阿春一脸愕然地看着泥鳅,像看个怪物。泥鳅又
说,我娘死得早,我就跟别人学会了织毛衣。冬天来了,我爹的毛衣早破了,不保暖。阿春看见泥鳅的手指,一针一针慢慢地上下翻动,显得格外的粗笨。
工友们回来的时候,泥鳅早进入了梦乡。泥鳅的床头摆着织了一小截的毛衣。一个工友高声咋呼,阿春跟这打渔佬钩上了,织的毛衣都忘在了床上。
另一个工友神秘地说,工头想搞阿春的,听说,都没上手。性子烈。一伙人把熟睡的泥鳅看了又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都咂着嘴,摇摇头,睡觉去了。
第二天,工地上的人就说,泥鳅和阿春睡觉了。泥鳅听见了这些闲言杂语,不吭声,只顾低头干活。中午去打饭时,泥鳅看见阿春,脸就不由自主地红了。晚饭后,工友们照例都出去了。泥鳅缩在工棚里织
毛衣。阿春洗刷完毕,风一样飘进了工棚。阿春看了泥鳅织的毛衣,说,织得还好,可是太慢
了。我帮你织袖子吧。泥鳅护住毛线说,别。人家要说闲话的。阿春嘴一撇说,嚼舌根的,随他们嚼,你怕什么?阿春从泥鳅手里抢过毛线,就又风一样地飘走了。月底结工资,泥鳅把几百元揣进了口袋,上了街。泥鳅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件大红的羊毛衣。泥鳅和大红羊毛衣一起进了阿春的房间。泥鳅把羊
毛衣搁在阿春的床上,跟正在织毛衣的阿春说,结工钱了,感谢你帮我织毛衣。阿春拿起惹眼的大红羊毛衣,笑了笑,就收在了枕头下。干到年底,泥鳅惦记在船上的爹,找到工头,要结工钱。工头阴沉着脸说,账不能结完,留到年后结。泥鳅嘴里咕哝,不是说好一天20元的,别人都结清
了,单要扣我的?工头不回答泥鳅,给泥鳅只结了部分工钱。吃过饭,很多工友都看见阿春一手拿把锅铲,一手
挥舞着菜刀,像个母夜叉在工地上和工头吵得凶。
泥鳅在工棚里默默清理背包,准备回家。阿春捏着几张钱,和已经织好了的毛衣,出现在工棚的门口。阿春说,回去,也不吭一声?
泥鳅说,我正准备去你那里,听说你和工头吵架了?阿春笑了笑,没回答泥鳅。阿春把钱递给泥鳅,说,你的工资。然后低着头,声音细碎得似蚊子叫:我想跟你回去。泥鳅瞪大眼睛,接了钱和毛衣,呆呆地看着阿春,慢慢地,红了脸,也把头低了下去。泥鳅带着穿着红羊毛衣的阿春回到了船上。爹不放心地把泥鳅叫到船头问,泥鳅,这回可靠了?泥鳅看一眼阿春说,是个好姑娘咧,爹。阿春正在伙舱边帮着生火做饭,袅袅炊烟飘荡在澧
水河上,又飘向静静的芦苇滩头,几只觅食的白鹭立在澧水河的浅滩,把一条鱼啄食得只剩下了一条骨刺。爹说,今年的春来得早,鱼已经出来找食了。
(特约编辑:王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