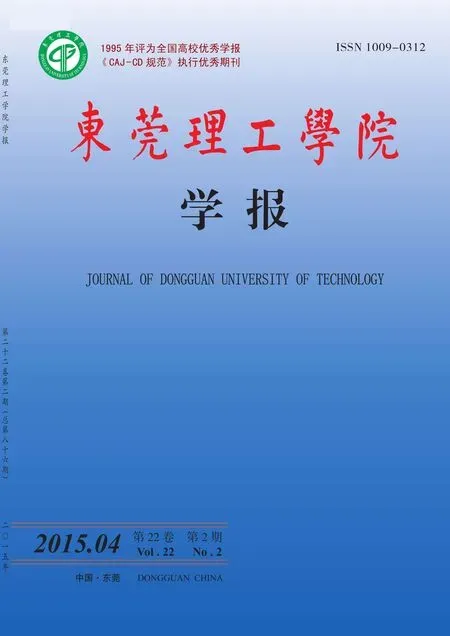渡边淳一《失乐园》中的差异性书写
黄海丹
(河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系,河南开封 475001)
关于渡边淳一《失乐园》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举凡其中极致忘我虽死无悔的纯爱意识,以肉体结合彰显生命的本源力量的性爱观念,对伦理秩序与价值规范的反思,乃至于其中日本传统文化的痕迹,都已经得到了不少的讨论。但学术界对于《失乐园》的研究,在久木与凛子的差异性考察这一方面,尚不尽如人意。一种情况以李小慧的《不伦恋歌》为代表。她在论述中只强调久木与凛子同为世俗常规的叛逆者,而不注重久木与凛子的差异性。另一种情况以冯羽的《渡边文学三议》为代表,他用“坚韧执着”[1]315与 “坚忍顽强”[1]315分别概括日本男性和女性对性的态度,但该文并未对这只言片语展开论述,于是这种差异性的论述显然既简略又模糊。还有一种倾向以于常敏的《荒山之恋失乐园——情感与传统道德的冲突》为代表。他在对创作过程的考查中,把久木和凛子之间的差别指认为作者基于社会理解与社会关怀的叙事策略;在对故事的考察中,把久木和凛子之间的差别指认为在婚外恋事件上,两个主体在主动程度上有所差别。这样就把久木与凛子之间的差别简单化,片面化了。
事实上,渡边对久木与凛子的角色定位与差异化书写,不仅深刻反映了日本当代社会的现实情况,也是《失乐园》表达深度与审美意蕴的重要基础,因此具有关注的价值。而无论在差异性的概括方面,还是从这种差异性出发考查其表达效果方面,学术界做得尚不足够。笔者尝试概括久木与凛子在这段婚外恋中所表现的差异性,并从此出发,赏析渡边在这样的差异性书写中的巧思妙笔。
一、久木与凛子的差异性
考据《失乐园》,笔者拟提出这样的论断来概括久木与凛子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久木是活在冰冷的现代社会之下,生活在功名利禄、世俗人情、逻辑理性之下,既挣扎其间又不能不受其影响,既被其宰制又被其抛弃的可怜生灵。而凛子则是一层薄薄的世俗外壳下,行为与身体、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合一的至情至性者。上述的差异性,深刻体现在这段婚外恋的进程当中。
对久木而言,这个进程一直是一个与现代社会的功名利禄、世俗常规、逻辑理性紧密相关的。久木恋上凛子,发生在从事业的高峰不可逆转地跌落的时刻,即使在久木与凛子感情已经十分深厚时,事业上的挫败仍然使久木在感情上再多走一步。在日本社会中,至少在《失乐园》营造的日本社会中,男子只要把握分寸,偶尔偷腥,几乎被作为一种潜在的在场而被社会所接纳——偶尔的偷腥被认知为一种实际上被纳入常规轨道中的伪越轨体验。久木一直有意识地运用自己在丰富的性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性技巧,借此不断使凛子与自己体验到性的极致快乐,也因此越来越深陷其中。在整个婚外恋进程中,久木一直在进行一种或是道德的或是逻辑的理性思辨活动。在该书的最后 久木决心赴死 也是经过深沉的思考之后的结果。 “久木虽然没有这样的梦幻,却清楚地知道,活得再长久,今后也不会有比现在更美好的人生了。”[2]413久木在婚外恋一步步加深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的功名利禄、世俗常规、逻辑理性,都一直发挥着作用。但他在这段恋爱中不仅被现代社会的功名利禄、世俗常规、逻辑理性所影响,更对这一切有着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有时候是一种有意识的个人选择。有时候,这种超越表现为感情的勃发全面逃出理性与常规的解释与掌控范围,如前所述的思辨活动,既然是为情感辩护,也就或多或少已沦为情感的同谋。最后,久木为着在爱的高峰以紧紧相拥的优美姿势幸福地死去,而周详地计划,缜密地布置,理性就更加沦为情感的助手了。于是,对久木而言,感情日益炙热的过程,就是始终在现实社会的影响下,或主动或被迫地疏离于世俗,情感自世俗常规与逻辑理性中溢出,理性日渐成为仅仅是情感的同谋的过程。
而对凛子而言,这个进程一直更多是与身体感觉、欲望和感情等非理性存在有关的。凛子最开始显得矜持 (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在种种细节中隐约表现出她的至情至性),而维系这份沉静与矜持的,就是一种依靠恐怖与厌恶约束人行为的感情—— “罪恶感”[2]31,及更重要的,足够美好的情爱体验的缺乏。于是凛子婚外恋程度的日渐加深,就是一种非理性对另一种非理性的超越,及一种情爱体验的唤醒与日渐生发。关于前者,罪恶感与爱情-性欲的同盟之间的“交战”一直在进行,在守灵之夜中,这次“交战”达到高潮。最终,“凛子已知道了身不由己这个道理,一旦承认了它,便无所顾忌了,飘飘然飞向空中那愉悦的花园去了。”[2]165至于第二点, “和丈夫之间从没有过这样快乐的感受”[2]29的凛子,终于被“久木你这个男人开发出了我沉眠未醒的快感。”[2]28于是凛子在这段婚外恋中,投入程度的一步步加深,基本可以看作是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内部运作的结果。
同样可以体现这种差异的,还有久木与凛子在这段婚外恋中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久木在这段婚外恋中所承受的代价,大多是处于世俗社会的维度之中的。这段婚外恋事件使久木的事业日渐衰颓。除了事业以外,久木与友人们也日渐疏远,婚姻与家庭最终走向破裂——虽然这婚姻早已没有爱情,但却为久木习以为常,因此无意识间绝对不愿意改变 久木付出的代价 就是日渐归于世俗社会之外,被整个现实社会所逐渐抛弃——这显然与被常态所抛弃互为表里。而凛子在这段婚外恋中所承受的痛苦,则绝大多数是情感方面的,非理性方面的。凛子受着罪恶感的煎熬。丈夫晴彦给予凛子残酷的精神折磨,其痛苦感基本不依赖世俗常规而存在,也在道德上不具有思辨价值。除此以外,凛子受到的另一层痛苦是在亲情方面:母亲对其失望透顶,凛子甚至失去了祭拜父亲的权利。久木在越轨中,受到了世俗常规的抛弃与折磨,而凛子在情感上因为这段婚外恋也伤痕累累。
在这种差异性的基础上,我们再次审视久木与凛子在婚外恋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发现,久木发挥的作用,可以总体概括为为情爱精心构筑一种充分施展的场域。这首先有着物质层面的意指:久木在大多数时候,负责物质条件的提供与保障。在情爱中,着意地,带有明显的审美观照地营造一种适宜于情欲迸发的外在环境的,往往是久木。要求“今晚就来它个月光浴”[2]82或者让凛子在下次见面时穿红色的内衣,久木都既带着几分淫邪又带着几分浪漫情怀与艺术气息地为情爱营造一个富有情调的氛围,最终既使自己“心旌摇曳”[2]84,又让凛子充分展现与抒发出自身的美与欲望。这种场域的构造还在于,从阿部定的案件到五郎与秋子的自杀案件,到《源氏物语》中六条妃子的命运到男体山的礼俗,从充斥全文的日本诗词到日本历史上的樱花与梅花之争,久木以其广博的知识发起话题,或者更精确地说,用知识与见闻构建某种可以讨论、阐发,也可以感性体认的场域。从物质经济的保证,到一个良好的情爱环境,到用知识与见闻构建话语场,久木为这段婚外恋精心营造了一个足够浪漫的,情爱能充分生长与抒发的良好场域。而凛子更多扮演的,是以无顾忌的至情至性,为这段感情注入激情、欲望冲动与非理性的角色。凛子迸发出骇人的情欲洪流,渐渐处于情爱中的主导地位。这种非理性冲动的注入,常常表现为凛子常常是久木的——也是这段婚外恋的——强心针与先锋队。当越轨的幅度逐渐增大的时候,尤当发生突发事件,已经完全超出理性可控制范围的时候,凛子“一向比久木要大胆果断得多”[2]380。同时,她因与自己的心灵同一,而常常率先体认到某种非理性的,时常有些骇人的感觉,当这种感觉被凛子坦率地表达出来时,常常让久木觉得不明所以,却最终往往得到久木理性的追认 于是凛子的直觉感悟成为了一种先知先觉,成为了两人爱情与命运走向的指向。
综上所述,在这段婚外恋关系中,久木是现代社会之下,生活在它的功名利禄、世俗人情、逻辑理性之下并始终受其影响,却又因现代社会的背弃与逻辑理性常规而走向反叛,最后苦涩地赢得了自由,却被整个“常态”所抛弃的可怜生灵。他精心地为这段婚外恋构筑了一个情感得以充分抒发的场域。而凛子,则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情感与欲望的,随着感情的日益浓重与欲望的日渐被激发,虽然承受着罪恶感的折磨和种种残酷的精神伤害仍然日趋坚定而沉迷地享受情爱的,行为与身体、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合一的至情至性者。她更多地为这段感情注入非理性,身上彰显着妖女般的情感与欲望洪流的妖娆妩媚的色彩。
值得提及的是,久木与凛子之间的差别及在爱情中的角色,既是个体性的,又可以认为具有男女情爱关系的普遍性。这不仅仅指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男女情爱关系的个例进行研究与阐释,更重要的是,《失乐园》中本来就有许多以“男人”和“女人”为指称的,关于男女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时而是叙述者的议论,也广泛见于久木与凛子、久木与友人的对话与渡边的自白中,甚至在叙述久木与凛子的情爱时,有时也直接以“男人”和“女人”指代双方。在久木与凛子的思维中,也即在渡边的创作中,两人的差异性以及他们的互动经常被纳入男性与女性的架构中进行考察。
二、差异性书写品读
之前的叙述,已经指认了久木与凛子在《失乐园》所描绘的婚外恋事件中各自具有的特性。那么,渡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差异性书写呢?这种差异性书写值得被关注的价值何在呢?
首先,这种差异性书写无疑深刻反映了当代日本社会的现实状况。当代日本,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规范”[3]在资本主义的现实情景中重新得到确认。男性无疑依然是家庭的顶梁柱和职场世界的主要参与者,自然更受现实社会与职场世界的宰制。而日本女性,正处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口,她们的自我定位与社会处境无不体现出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混合,她们一方面仍然受着社会性别分工规范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同时 又能获得良好的现代教育于是女性文化界对男女平等的呼唤、传统母性的厌弃与身体渴望的大胆承认与追求都会对其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职场上她们“倾向于打短工等比较灵活的非正规劳动方式”[3];在婚育上,“即便丈夫希望要孩子,也不一定能说服有经济实力和独立意识的妻子。”[3]以一种至情至性的方式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凛子,可以说是在思想观念上、经济上的日渐独立,却又终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与以职场为代表的现实社会有着太过严密的瓜葛的一批日本女性的典型。这种差异性书写体现了渡边对当时社会情况与男女角色分工精准细腻的洞察。
其次,这种差异性书写是构建该书思想深度与审美意蕴的重要环节——这正是差异性值得被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所在。上文已经对差异性有所指认,笔者尝试在此基础之上,观照这种差异性书写的表达效果。
在这种差异性的设计之下,久木与凛子之间的互动变得非常富有意趣。渡边与凛子是两个特性鲜明的个体,两者的思维方式甚至价值判断都不尽相同,于是互动中,便难免有互不理解的时刻。但许多时候,这种互动,在某种意义上依靠着巧合与误解进行——对话有时候依靠着语词上尚能相互衔接而得以继续。这表现为一段对话里久木与凛子说话动机与思路的不同,话题的断裂与歧出,但大相径庭的所指因能指能相互衔接而不至于阻滞交流,于是久木与凛子的对话总是充满着多义性的张力。而相互欣赏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某种巧合甚至误解。比如,久木因事业失意、“精神状态的确正处在低谷”[2]27而显得低调、慵懒,却被凛子视为久木的特别之处与一种“疲惫而忧郁的感觉”[2]27而珍而重之。在这样的书写中,渡边一方面冷冷地否认了完全意义上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却温情地描绘了灵魂相互契合与相互抚慰的部分真相:误解与巧合体现了两种价值体系、两种思维方式、两种关照视角的相互补充,而两者之间互补的严丝密缝何尝不是所谓“天作之合”的体现。于是久木与凛子之间的互动除了充满多义性的张力与巧思,更有一种写实的浪漫。
《失乐园》的主题之一就在于对现代社会残酷性的反思以及对包含性爱的绝对爱的呼唤。而对久木与凛子的差异性的设计扩充了这种反思与呼唤的深度与表达面向。通过久木的遭遇,对现代社会残酷性的反思能深入现代社会对人的限制与戕害的具体事实与内在运作机理之中,这些事实往往令人错愕,从中体现了渡边对社会洞察的高明与细节处理的精当。如,友人并不是谴责渡边有婚外情,从衣川到铃木到水口到中泽,久木的朋友们真正让久木感到隔阂与恼怒的地方,其实更多在于他们认为久木为爱情太过火,以及他们对这种越轨爱情的合理性的解读方式。久木既不能认同世俗对越轨的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包容性却极其想当然的阐释,也不能认同世俗对于这种越轨的行为的包容极限,也就是不仅仅不能被世俗的条框限制,也渐渐无法被世俗的延展性所容纳,这恰恰说明了不仅仅是世俗的条框,就算是看似人道的世俗的延展性,也是对人性的另一种宰制。又如,久木内心深处一度希望维持婚姻,妻子却主动提出离婚,这就又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层残酷性:当人决意在某些方面开始越轨时,即使他真心实意地尝试勉力维持某些领域的常态,却无法避免常态的崩塌。而凛子愈有着至情至性的色彩,就愈能由其在婚外恋中感受的苦楚体现出现实社会与世俗常规对人宰制的无所不在:现代社会与现实世界对人的宰制,既有着存在与现实社会的场域及思维之中的理性的手段,又有着直接给予人肉体或心灵的痛苦的。非理性的手段。于是这种宰制,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与职场世界保持距离,或者在思维方式上不受理性拘束就可以避免的。除了对现代社会残酷性的反思,这种差异性的设计也有利于对绝对爱的言说。这不仅仅在于逡巡在世俗常规之下的久木还是至情至性的凛子,最后都陶醉于炽热的情爱中不能自拔,也在于他们的差异性使他们在这种绝对爱的叙述中发挥着互补的作用。凛子是磅礴的情爱的活生生的展品。在对凛子的书写中,渡边一般采用一种旁观的叙述视角,让凛子尽情展现情欲的滋长、勃发、汹涌、诡异与不管不顾。而久木则承担着解释情感、理顺逻辑的叙述角色,这里他部分承担了本应由旁白承担的角色——事实上在《失乐园》里,何为旁白,何为久木的内心独白,常常是界限模糊的。从旗帜鲜明地为婚外恋辩护,到对无所不在的窥私欲望的深刻体悟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再到对凛子的非理性体悟进行各种理性阐释,作者借久木的内心独白表达着自己的理性思辨与对绝对爱合理性的理性辩护。借久木与凛子的差异性,作者的笔触既深入到现实社会对人的宰制的具体事实与内在机理之中,又展现出这种宰制的无所不在 同时用既展示炽热的情爱又阐释炽热的情爱的方法来书写、歌颂绝对的爱。
同时,这种差异性的设计在指认了久木与凛子、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性的同时,又同时确认了两个个性主体、两种性别特质的主体性与价值。在《失乐园》中,男性与女性都在被建构的范围之内,男性的局限性正如男性之外的局限性一样被书写——前者甚至被更多地书写——因而男性也与女性一样“本性则决定了他的行为,限制了他的思维”[4]11,从而实现一种男女的平等。而在此之上,渡边与凛子,男性与女性,在这段婚外恋的进程中,都既跟随自己的主观意愿而行,又受到对方的深切影响,都为这段感情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这种相互影响与对感情的贡献,于久木与凛子有侧重点的不同,在特定时段内,影响与贡献也有着孰大孰小的区别,但考察整个婚外恋的进程,则总体是两个具有鲜明差异性的主体的无分主次的携手合作。在《失乐园》以一次越轨行为为书写甚至歌颂对象的具体语境中,男性的主体性与价值的确认,与女性的主体性与价值的确认,在渡边的差异性书写中得以并行不悖,无分厚薄。当然,笔者无意在女性主义的维度上过分拔高《失乐园》,渡边对久木与凛子的差异化的书写绝不是某种“策略上的本质论”(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自觉尝试。从《失乐园》中许多以“男人”和“女人”为指称的,关于男女关系的讨论与男女差别的讨论来看,渡边对男女区别与男女关系的认识依然有着本质主义的局限性,也依然没有脱出日本传统文化的最源头处对男女两性的认识。虽然如此,但渡边的差异性书写既认可了个性特色与性别特征,又同时赋予两种性别特质、两个个性主体无分主次的价值确认,则依然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渡边的这种差异性书写总体是适度的:渡边虽然写出了特色鲜明的久木与凛子,但对他们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置却并不僵化。久木并非全然没有至情至性的一面,凛子也并非完全不懂现实世界,或完全不与久木一起解决婚外恋带来的现实问题。作为一个总体写实的小说,这样的处理使作品更富有真实性,也体现了渡边对人的多面性的深刻体察与塑造人物的高超技巧。
渡边在《失乐园》中对久木与凛子的差异性书写,除了深刻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实以外,本身也具有审美意蕴与叙述效果方面的价值:它使久木与凛子的互动非常富有意趣,具有一种多义性的张力与写实的浪漫 扩充了对现代社会残酷性的反思与对绝对爱呼唤的深度与表达面向;同时无分主次地确认了久木与凛子,男性与女性两种个性主体的主体性与价值,而且并没有造成人物塑造与情节设置的僵化。
三、结语
渡边创作《失乐园》时,“并不太注重构思完整才动笔”[1]309。尽管如此,渡边“回想着自己以往的强烈而充满激情地恋爱写这部作品,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情感与心写这部小说”[1]309,凭借着对爱情,对两性的热忱而深刻的体悟,渡边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恋爱状态”[1]309中创作的《失乐园》依然经得起推敲,对这段婚外恋的细腻精辟的描绘中,历历尽是作者对两性、情爱与人性的洞见。久木这个男人,在现代社会的功名利禄、世俗常规、逻辑理性中既受其束缚又被其抛弃,既决意逃离又始终受其影响,他用自己的知识 经验和缜密 构建一个浪漫的爱情场域也亲手策划埋葬了自己与凛子;凛子作为与感觉、欲望和情感等非理性直接统一的妖女般的至情至性者,敏锐地感应,勇敢地表达与展现自己的感觉、情感与体悟,使之充盈于恋爱之中,为这段感情注入一剂剂强心针,而看似诡异的非理性体验也成为了一种先知先觉。这种并不僵化的差异性书写,除了深刻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实以外,也使久木与凛子的互动具有一种多义性的张力与写实的浪漫,使对现代社会残酷性的反思与对绝对爱呼唤更为广博而深刻,又同时确认了两种个性主体的主体性与价值。上述种种,都不仅仅体现了渡边对婚外恋男女之间隐秘微妙却又互为补充的差异性的精准把握与深刻体察,体现了他对一切被僵化陈旧的体制与价值观念束缚者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体现了渡边高超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技巧,也可以超出《失乐园》的故事,超出婚外恋的范畴,为我们观照恋爱,观照两性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1]冯羽.渡边文学三议[M]//王守仁.终结与起点: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渡边淳一.失乐园[M].竺家荣,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3]赵敬.社会性别分工与当代日本女性的生活模式[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5):103-108.
[4]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