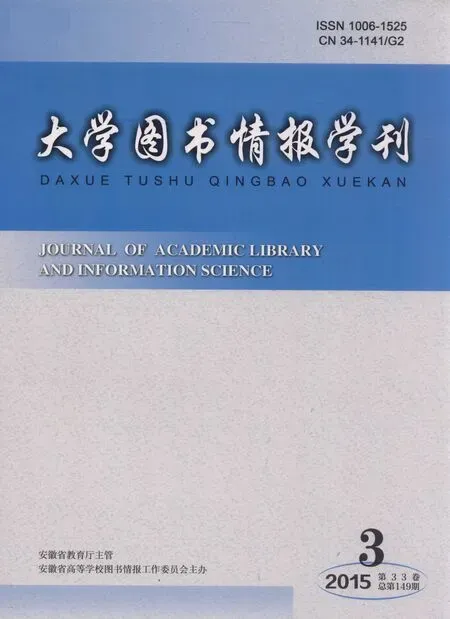关于信息弱势群体的若干探讨
关于信息弱势群体的若干探讨
李阳1,谢阳群2,张家年1,2
(1.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430072;2.淮北师范大学,235000)
摘要: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弱势群体逐渐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关注对象。界定了弱势群体与信息弱势群体的关系,介绍了信息弱势群体的几个相关基础理论。从大数据与智慧城市构建的视角探讨了新信息环境下信息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基于此提出了若干思考。
关键词:弱势群体;信息弱势群体;大数据;智慧城市;信息时代
中图分类号:G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73);国家自然科学
作者简介:李阳,男,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01-15
Probing into the vulnerable information groups
LI Yang1, XIE Yang-qun2, ZHANG Jia-nian1,2
(1.Wuhan University, Wuhan430072, China;2.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235000, China)
Abstract: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vulnerable group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ublic concern in information age. The paper frames a defi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ulnerable groups and information vulnerable groups, and introduces several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vulnerable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and smart city, it explores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the information vulnerable groups under the new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sheds new light on this.
Key words: vulnerable groups; information vulnerable groups; big data; smart city; information age
1引言
信息弱势群体(Information vulnerable groups)古已有之,从传统社会中的“愚民政策”、官民“信息占有”差异,到后来的“信息管制”以及“信息扶贫”等,都折射出信息弱势群体的种种现象和问题。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6.32亿,手机网民数也达到5.27亿[1]。可以说,相比过去,人们在信息交流、获取、沟通等方面已经大为便利。然而,对于信息弱势群体来说,信息的有效利用仍然颇为不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该是为全体公众服务的,但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信息“福利”的同时,扩大了信息利用上的差距,甚至分化出信息强势群体与信息弱势群体,而后者逐渐成为边缘化的社会人群。目前看来,信息获取渠道少,信息化技能低是造成信息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而从现实来看,为了融入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大环境,很多信息弱势群体迫切需要那些他们原本无法获得的信息服务。当然,很多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开展“民生工程”,希望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种信息弱势群体问题。然而,现实中这种由于各方面因素(政策、环境、生理等)导致的部分群体在信息利用等方面的差异化现象,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也难以被消除,信息弱势群体的存在俨然成为一种客观事实。由于信息弱势群体问题的日益突出,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目标下,有必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2信息弱势群体的基本问题
随着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信息弱势群体已经引起国内外政府、社会、学术界等普遍关注。从文献检索来看,目前专门针对“信息弱势群体”的研究还不多见。笔者以“信息弱势群体”为检索词,以中国知网文献为数据库来源,检索时间为2014年11月22日,检索范围设定为“不限”,共检索出相关研究文献107篇,内容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新闻传媒、互联网技术、投资、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下面从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概括、评述。
2.1 信息弱势群体与弱势群体
信息弱势群体是由弱势群体引申而来,弱势群体的概念范畴较广,研究也较为成熟。早在20世纪末,我国曾一度回避使用“弱势群体”这个词汇,一般称之为“困难人群”,这在早期的文献及报告中已经有所体现。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互通的,所谓的城市贫困人口、“困难人群”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弱势群体。朱镕基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及“弱势群体”,并表示对弱势群体要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2]。简单来说,弱势群体一般多是由经济贫困导致的,是指其个人及家庭生活达不到社会认可的最基本标准的困难群体,是依赖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自己目前弱势地位的群体,是需要他人帮助、支持甚至予以救助的群体[3]。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弱势群体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然而,国内有一些学者将“信息弱势群体”的研究等同于“弱势群体”研究,常常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实际上这并不正确。当然,对上述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界定,目前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争议。一种认为信息弱势群体包括弱势群体,它们是逻辑学的属与种的概念关系。相比较而言,信息弱势群体是信息时代特定背景的“产物”,是扩大化的弱势群体(当然,这种关系定位并没有考虑个别现象)。也就是说,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限制,某些群体在获得和利用信息技术(包括传统和现代信息技术)及信息服务方面就会处于劣势,这一群体的形成一般有其强烈的个人因素,而信息弱势群体的构成应该还包括一些信息知识与技能相对较低的高收入群体[4]。另一种观点认为,“信息+弱势群体”的解读方式能够更好地阐述出信息弱势群体的内涵与外延,这实质上就是认为弱势群体范围较大,而信息弱势群体范围较小。笔者认为,信息弱势群体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会随着社会文化、信息技术、政策法规等因素影响产生相应变化,弱势群体与信息弱势群体并不存在充分或必要条件,弱势群体并不一定是信息弱势群体,信息弱势群体一定是弱势群体,两者之间应该是有交叉与独立的部分。总的来说,弱势群体与信息弱势群体是密切关联的,至于具体的关系界定实际上并不影响信息弱势群体本身的研究。
2.2 信息弱势群体的划分与产生原因
实际上,信息弱势群体的划分也是在弱势群体划分的基础上引申而来的。信息技术发展对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行为(信息交流、利用、学习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弱势群体包括生理性信息弱势群体(如孤儿、残疾人等)、经济性信息弱势群体(如城市下岗工人等)以及新的信息弱势群体(如对计算机知识一无所知的人等),而对不同的信息弱势群体进行针对性的信息援助才能改变这种不利状况[5]。信息弱势群体一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经济收入少、社会地位低、信息素养不高等,人群结构上又分为老年人群、残疾人群、精神障碍人群等,这也是信息弱势群体产生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在信息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差异和个人能力的局限,在综合“差距”比较下,所谓的信息弱势群体就被“刻意”划分出来。有学者将信息弱势群体的产生系统地归纳为三个主要因素:技术因素、内容因素与个人因素[6]。技术因素主要表现在信息传输渠道以及信息基础设施问题上,内容因素主要是针对信息内容本身,因为信息弱势群体的获取与利用的对象就是信息,因此,信息的生产与提供、信息管制直接关系到信息弱势群体“接触”信息的“质”与“量”。个人因素相当于一个普适性因素,主要是指个人的信息意识与信息技能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的信息素养决定其信息“地位”。可以说,这三个因素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也体现出信息时代的独特特征。
3信息弱势群体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
信息弱势群体的研究虽然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其理论“溯源”问题受很多交叉学科理论综合作用,其相关基础理论涉及到社会公平、马太效应、数字鸿沟(信息鸿沟)、信息失灵、信息无障碍等。结合信息弱势群体来说:第一,社会公平理论强调每个社会的“信息参与者”应该是公平的,这种公平感不仅仅体现在劳动付出带来的报酬分配公平,还体现在信息福利的“非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会被忽略或排斥在现代信息源之外,尤其是网络信息源。第二,马太效应强调从侧面反映出信息强势群体和信息弱势群体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为信息的“贫”与“富”之间的差距,这与公平理论中的“信息平衡”之说应是相悖的,而信息弱势群体所反映出的马太效应问题一旦缺乏必要的纠正机制,这种负面现象只会愈演愈烈。第三,数字鸿沟(信息鸿沟)理论强调在信息技术服务上,一部分群体有最好的、最便捷的网络、计算机、教育技术等服务,而另一部分群体则处于不“幸”的一边,这种鸿沟到后来已经延伸为知识鸿沟,表现为因知识储备不足带来的信息技术服务差距。第四,信息失灵理论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准确、信息不充分[7]。信息不对称多强调信息提供者与信息拥有者之间在信息“量”问题上的差异;信息不准确则强调由于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信息错误等,信息弱势群体就常常因为信息的不准确导致在很多问题上频频遇阻;信息不充分对信息弱势群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上层(政府部门等)对下层的资讯信息公开、信息服务等存在信息“断裂”,很多信息往往不是不愿意传达,而是传达存在障碍,或是根本没有考虑信息弱势群体的特殊情况(需求)。第五,信息无障碍理论强调保障信息弱势群体获取信息的权利,认为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弱势”不仅源于其本身,而且源于信息服务各环节的设计、开发和管理等,甚至还包括国家法律、标准和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因素。
实际上,这五个理论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比如说,信息的“不灵”会给农民工在农产品的种植、销售等方面带来不利,但其本身又处于“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表现为信息获取上的“障碍”。总的来说,信息弱势群体的几个相关基础理论共同为信息弱势群体理论作理论支撑,成为其理论架构的重要部分。
4新信息环境下的信息弱势群体
进入信息社会以来,很多传统的信息交流、传递、沟通等方法、途径、模式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资源数字化、载体形式多样化、传播方式网络化、传播速度高速化、信息利用低廉化的新信息环境,这种新信息环境要求信息服务是非中介化、非专业化、非智力化,并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的[8]。如前所述,以往的信息弱势群体研究多集中在图书馆、社会伦理、政府公共服务等领域,实际上从一个更广义的信息弱势群体定义,新信息环境下的信息弱势群体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问题,本文简单介绍目前信息弱势群体研究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以及智慧城市背景下信息弱势群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两者具有交叉性,但视角略有不同,这些研究鲜有人关注或关注度还不够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4.1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弱势群体
近年来,与“大数据”主题相关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诚然,很多行业和领域都能从大数据中获益,但在本文中,我们撇开纯粹意义上的大数据概念及其思维,仅谈大数据给信息弱势群体带来的危害或弊端。大数据在弥补数字鸿沟的同时,也会带来数据垄断的危机,并催生出一大批形形色色的数据(信息)弱势群体[9]。大数据的本意是造福绝大多数人,并远离这种厚此薄彼现象,但实际上几乎很难实现绝对的平等。由于很多信息弱势群体对于信息的把握不足、认识不全、警惕性不够,大数据的“人肉”采集模式会给那些信息弱势群体带来不必要的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也就是说,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成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公平分享,会出现数据鸿沟、存在信息不平等问题,这势必对信息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危害,这种危害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及与其有关的服务、通讯和信息可及方面的失衡关系。比如说,某些群体在信息可及方面遭到了不合伦理和得不到辩护的排除。可以这么说,除了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安全等基本品以外,信息其实也是基本品,因此需要实现对信息的公正分配,以及对信息技术及信息的普遍可及[10]。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刻意地强调信息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将信息生态引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会导致社会信息系统缺乏应有的活力,而信息不平等实质上是可以发挥个体积极性、群体凝聚力,甚至可以反面提示社会层面的行为取向问题[11]。然而,对信息弱势群体而言,源于其本质特征,大数据时代的这种信息不平等只会加大、加剧这种不公平现象,很多大数据服务并不能覆盖到全部人群,尤其是信息弱势群体,他们就更难享受到大数据带来的种种技术成果。也就是说,针对这种特定人群,我们不应考虑其存在所谓的正负功能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弱势群体已经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苦难”。总的来说,存在不一定合理,但必有其原因,信息时代信息弱势群体的存在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由于各个行业的信息弱势群体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矛盾、纠纷以及难题,这就需要各个行业在开展信息服务时考虑有针对性的信息扶助。
4.2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弱势群体
大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引擎,为智慧城市的构建提供了技术和思维上的支撑和支持。智慧城市是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融合的产物。大数据时代,信息弱势群体没有享受到同等的信息服务,在现有的智慧城市构建背景下,很多也没有考虑信息弱势群体问题。智慧城市的构建本身就是惠民工程,需要帮助信息弱势群体,排除或者尽量减少信息弱势群体的存在,其本身实质上就体现出智慧之道,否则智慧城市也只是空话。当然,信息弱势群体的智慧之路又是异常艰难的。在本文中,我们列举几个代表性的问题,包括突发事件应急中的信息弱势群体、打的软件对信息弱势群体的冲击以及信息弱势群体在其他方面面临的挑战。
4.2.1 突发事件应急中的信息弱势群体
突发事件的发生会影响到城市的正常运转,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城市智能化建设的重要模块。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需要获取与突发事件相关的应急信息,对于信息弱势群体而言,在获取应急信息的资源和手段上都处于弱势位置,这里的信息弱势群体是指与突发事件相关的、受突发事件影响的群体。由于信息获取上的差异,信息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较弱。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应急状态下,信息弱势群体遭受的伤害、经济财产损失等相对更为严重。首先,信息弱势群体缺乏利用信息手段主动搜索感知应急信息的能力,更别谈参与突发事件信息的反馈交流,也就接受不到最新的灾情进展信息以及相关的应急资源的分配信息;其次,信息的不平等、不对称等问题已经让信息弱势群体落后于“信息”的起点,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信息弱势群体会处于茫然状态,极端情况下出现“乱投医”现象,以至于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一种现象是,信息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周围所处的群体多是相同背景的人群,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以至于突发事件发生时,这些被信息时代“边缘化的”群体无法及时获取、理解和有效利用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甚至被直接排斥在事件相关信息源之外。实际上,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信息弱势群体的应急信息需求不亚于其他群体,而通过采取相关措施提供应急信息支持,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救助不到位”现象的。考虑到信息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应采取适合群体的信息服务方式,如有学者建议建立相关的弱势群体紧急救助工作规程和应急预案,对他们救助实行分类管理、阳光操作,可以通过加强应急知识宣传,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培训他们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利用能力和应急技能,提高避险自救能力[12]。从大范畴上来看,公众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问题一直以来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关注问题,政府等相关部门也一直在尝试通过构建不同信息渠道来解决这种问题,但在实践中较少提及信息弱势群体的突发事件信息需求问题,致使应急处置出现各种意外偏差,而为了解决这种意外偏差,信息弱势群体的应急信息需求理应引起广泛关注,也是智慧应急的重要关注对象。
4.2.2 打车软件对信息弱势群体的冲击
智慧交通是基于实时交通数据,并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提供城市交通信息服务。智慧交通目前在城市交通管理与控制、城市智能公交等方面已经有了初步进展。可以说,智慧交通的发展给城市交通运输带来了便利,增进了社会效益,但也给部分群体带来了困难,最为典型的就是信息弱势群体。以前段时间兴起的打车软件为例(如“嘀嘀”、“快的”等),打车软件的应用和推广让出租车司机与公众之间有了更快捷的出租交易行为,降低了双方的发现成本,然而打车软件的应用是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对于没有使用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技术盲”信息弱势群体(如中老年人)来说,他们几乎被排除在打车软件之外,而原本属于他们的打车机会就被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抢单者”霸占,招手拦车屡屡被熟视无睹,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出租车属于公共交通,与社会化用车、私家车等不同,公共交通服务理应为信息弱势群体提供平等、优质的服务,公共交通服务应是承担相应社会功能的,而不是刻意追求经济效益。诚然,打车软件的推行符合整个行业智能化的大发展方向的,但由于其软件功能设置、技术运用等方面的不成熟,给社会以及相关行业监管带来了一些问题。鉴于打车软件给社会带来的种种负面现象,尤其对信息弱势群体带来的不良冲击,很多城市已经对手机打车软件下禁令、叫停或限制高峰期使用。实际上,针对这种问题,基于智慧城市背景建立相对应的打车呼叫平台,这个平台应兼顾信息弱势群体的利益,应向信息弱势群体倾斜,涵盖语音、翻译、导航等功能,通过电话的方式就可以享受到出租车服务。实际上,不仅仅打车软件,其他方面亦是如此,信息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是智慧交通之路上必须关注的问题。
4.2.3 其他领域信息弱势群体面临的挑战
实际上,除了上文中介绍的内容外,信息弱势群体的“弱”在各个领域都有体现。如在智慧政府的构建过程中,政府信息公开服务问题一直是核心问题,就目前来看,信息弱势群体在获取政府信息上存在不便与困难,对于信息弱势群体来说,这种不透明的政策环境无疑是不公平的。如在智慧企业的构建过程中,很多企业内部信息公开流程存在问题,在与客户的沟通与营销上也存在障碍,比如针对企业信息披露问题,一些投资者能够提前获取内幕性信息,而信息弱势群体(一般为中小投资者)则在获取和使用证券信息上存在滞后、信息不全等现象,造成了市场不公平。如在智慧教育的构建过程中,就教育资源分配问题,信息弱势群体不能平等地享受到教育机会、获取培训信息等,而他们本身的教育程度反过来又阻碍了他们对相关信息的获取。如医疗信息化成就了智慧医院,但就如何合理分类医疗资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尤其是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尤为重要,但信息弱势群体却很难获取重要的医疗信息资源。如在智慧图书馆构建过程中,很多公共图书馆与信息弱势群体仍然存在距离和隔阂,不能发挥人性化图书馆信息服务理念,如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等。总而言之,智慧城市在关注技术层面融合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用户层面的互动,智慧城市不是精英的游戏,而关注信息弱势群体是智慧城市构建道路上的重要课题之一。
5小结
信息弱势群体是全世界范围内共同面临的问题。本文从理论层面简单概括了信息弱势群体的几个关键问题,介绍了信息弱势群体的基本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几个基础理论。并认为新信息环境下,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理念的介入更需要我们去化解这种信息弱势群体中的尖锐矛盾。当然,解决信息弱势群体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而不是盲目跟风。归根到底,信息弱势群体的产生最终涉及到的还是信息资源的分配问题,从信息资源管理视角探讨信息弱势群体产生的信息技术原因,信息公平实现途径,信息分配、共享、服务方式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13]。一言以蔽之,要想促使信息弱势群体从信息“弱”到信息“强”,就必须对他们进行知识援助,让有效知识覆盖信息弱势群体,不能让信息弱势群体问题成为一种时代病。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EB/OL].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jcsj/,2014-11-28.
[2] 人民网.朱镕基报告中新名词弱势群体包括哪些人[EB/OL]. http://www.people.com.cn/GB/jinji/31/179/20020307/681536.html,2002-03-07.
[3] 严贝妮.扶助信息弱势群体跨越信息鸿沟——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知识河流”项目的思考[J].图书馆杂志,2008,(12):58-61.
[4] 詹晓阳.基层政府面向信息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0.
[5] 石德万.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弱势群体信息行为的影响[J].图书情报工作,2008,52(11):75-77,21.
[6] 江源富.面向信息弱势群体的政府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7] 应飞虎.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2.
[8] 贺西安,张小云,任虹,等.新信息环境与知识创新[J].情报杂志,2004,(12):137-139,136.
[9] 新华网.大数据时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3-07/25/c_116676037.htm,2013-07-25.
[10] 邱仁宗,黄雯,翟晓梅.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问题[J].科学与社会,2014,4(1):36-48.
[11] 赵玲玲,傅荣贤.基于社会功能理论的信息不平等研究[J].图书馆,2013,(1):18-19,27.
[12] 刘焕成.弱势群体的应急信息服务保障机制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3,(3):94-97.
[13] 丁邦友,靳晓恩.信息资源管理制度化建设与信息公平保障[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112-113.
(责任编辑: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