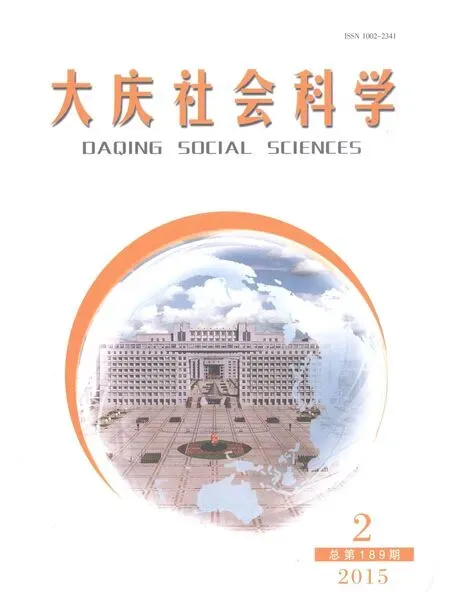关汉卿《窦娥冤》杂剧的“人民性”特征
张 硕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关汉卿《窦娥冤》杂剧的“人民性”特征
张 硕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窦娥冤》是我国元代伟大的戏曲家、杂剧艺术的奠基人——关汉卿的代表作。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元杂剧,历来受到后人的广泛关注。全剧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通过精练质朴的语言、简洁完整的情节,深刻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并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一反抗压迫的妇女的典型形象。通过对作品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作品的价值内涵,体会关汉卿在《窦娥冤》创作当中的人民性特征。
关汉卿;窦娥冤;人民性
“人民性”于19世纪首次被作为文艺学的一个范畴加以使用,俄国诗人、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在1819年给屠格涅夫的信里和1924年写的《古典作家和出版者的谈话》中,率先以“人民性”的标准评价作家作品。它是指在文学作品中流露或表现出来的人民的立场以及基于这种立场的对人民的同情、赞颂和提高的态度,也包括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人民的共同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的描述和向往的倾向。
关汉卿作为我国著名的戏剧家之一,生活在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代,他创作的《窦娥冤》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戏剧中的经典。明代戏曲家孟称舜评点《窦娥冤》说:“汉卿曲如繁弦促调风雨骤集,读之觉音韵泠泠,不离耳上,所以称为大家。……《窦娥冤》剧词调快爽,神情悲吊,尤关之铮铮者也。”[1]作家以精巧的构思和简练的叙事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深刻透露出作品中浓浓的人民性特征。
一、戏曲语言通俗质朴
戏曲是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有机结合,面对文化水平偏低的市民阶级,能够让他们听得懂曲词并激发他们的看戏热情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通俗的戏曲语言可以使复杂的剧情清晰化,提升观众的观赏趣味,但是想要达到戏曲创作通俗化这个标准是很难的,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提出戏曲必须“可演可传”(《曲律·论剧戏》);清代有名的戏曲理论家李渔认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贵浅显,重机趣”。可见通俗的戏剧语言是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关汉卿作为一位“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的戏曲家,深知作品能够获得广大市民阶级认可的重要性。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称赞这位语言大师的戏曲语言“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2]108王国维的对关汉卿的评价是高度赞扬的,肯定了他在戏曲创作中的贡献。同时也写出了关汉卿的戏曲创作特点,他对戏曲语言的把握和领悟,极尽能事,达到了戏曲创作的又一个高度。
关汉卿戏曲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俗自然,质实直露,评论家以“本色”二字概括其特色。如在《窦娥冤》中,蔡婆婆迫于无奈把张驴儿父子领回家,并告诉窦娥,自己将要嫁给张驴儿父亲时,窦娥丝毫不顾婆媳关系,埋怨说:“婆婆,这个怕不中么?你再寻思咱: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3]11不事雕琢的语言,有力地表达了窦娥对婆婆这一决定的不满。接着她又对婆婆唱道:“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3]12在知道婆婆已将自己许给张驴儿后,窦娥更加愤怒,直截了当地说:“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3]12虽然窦娥为封建社会的儿媳妇,但是面对婆婆的无理要求仍然能够据理力争,企图突破封建主义的枷锁,争取自由。关汉卿在戏曲中使用的语言符合人物个性,让读者(观众)有种身临其境之感,不由觉得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形间拉近了与读者(观众)的距离。
符合人物身份地位的角色语言也是关汉卿戏曲语言通俗化的显著特色。角色化的性格语言最能准确、敏锐地捕捉人物内心的感情变化,反映人物的性格本质。在《窦娥冤》当中,关汉卿塑造了很多具有高度性格化语言特征的人物,如窦娥在临刑前对婆婆说的一段话,语言平淡,却感人至深:“(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3]29-30这样朴素无华的说白,多么符合窦娥这个封建社会里小媳妇的声口。
语言的动作性将人物置身于情和境当中,可以使读者更加生动形象地解读剧本。关汉卿的动作语言分为舞台提示和曲白表现。显示舞台提示的,如在《窦娥冤》当中,窦娥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后,天色骤然变得阴沉,此刻作者用了“内做风科”来表现舞台氛围,这样的提示与剧情的发展是非常吻合的。在曲白表现中,激烈的言辞冲突可以使剧情推向一个高潮,如张驴儿误杀自己的父亲,嫁祸于窦娥,此时蔡婆婆愿意息事宁人,窦娥据理力争,张驴儿是泼户无赖,大喊大叫,表现得极为嚣张,语言也极富动作感,此段对话就具有曲白语言的效果:
“(张驴儿云)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做叫科,云)四邻八舍听着:窦娥药杀我家老子哩!(卜儿云)罢么,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吓杀我也!(张驴儿云)你可怕么?(卜儿云)可知怕哩。(张驴儿云)你要饶么?(卜儿云)可知要饶哩。(张驴儿云)你教窦娥随顺了我,叫我三声嫡嫡亲亲的丈夫,我便饶了他。(卜儿云)孩儿也,你随顺了他罢。(正旦云)婆婆,你怎说这般言语?”(第二折)[3]21-22
关汉卿的《窦娥冤》还具有一个明显的语言特征就是语言的民间化程度高,不仅吸收了金元时代少数民族的语言,还融会了宋元时代通俗文学中的口语,包括当时民间成语、谚语、歇后语等,语言形式丰富,贴近市民阶层生活,体现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人民性特征。王国维曾经称赞元曲的“最佳之处”时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能够达到第三条之境界实属不易,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使用的大量民间口语,如“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小的是念佛吃斋人,不敢做昧心事”。这些浓缩了人民生活经验和智慧的民间语言,使得关汉卿的《窦娥冤》在语言艺术的运用上独具姿态。
二、揭露社会黑暗现象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王朝,蒙古贵族吞并中原,统一中国,以凶残、荒淫、蛮横的手段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据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记载:“凤翔之役,太宗诏从臣分诛居,违者以军法论。……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听居民自出,日饿死不可记。”[4]由于蒙古族统治者始终奉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使得整个社会民族矛盾尖锐、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恶霸横行。关汉卿是生活在元代都市勾栏瓦肆中的剧作家,当然可以清楚地目睹市井中赤裸裸的社会黑暗面。他不畏强权,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大胆地在作品中对社会的不公和罪恶进行揭露。
如《窦娥冤》中的张驴儿,他就是元代社会孕育的一批无赖流氓的典型,危害社会的安危。清代戏曲理论家焦循说:“副净之名,见《窦娥冤》之张驴儿。”[5](《剧说》)足以见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特点。而关汉卿也是在剧中形象地刻画出了这样一批人物的典型代表。首先是对其语言动作的描写,反映出像张驴儿这样的一类人物的丑陋嘴脸。他对父亲说:“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里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儿,何等两便?”他以救了蔡婆婆性命做要挟,强行让蔡婆婆和窦娥给他父子做接脚,这是一副多么典型的流氓嘴脸。一进蔡婆婆的家门张驴儿就自吹自擂道:“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一副流氓腔。其次对张驴儿行为事件的刻画,生动形象,完全符合剧情发展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由里到外、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元代社会中此类地痞无赖的丑陋。张驴儿药杀蔡婆婆不成,反倒误杀自己的父亲,并且嫁祸于窦娥,他耍泼霸道,用花言巧语蒙蔽了糊涂的贪官,造成了窦娥的悲剧。赛卢医为了可以逃债,心生歹念,将蔡婆婆骗至郊外无人处,欲用绳子将其勒死,这种险恶的小人的存在以及对元代法律的无视都是在对整个封建黑暗统治的控诉。作者通过塑造这些泼皮、无赖形象,揭露了元代社会中那些强词夺理、混淆是非的恶棍们的丑恶嘴脸。我们可以看出,关汉卿在戏曲创作中饱含深情地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对待像张驴儿这样的人物,他写出了底层市民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的感情。
关汉卿的目光不仅停留在市井阶层,还大胆地撕开了上层权贵兴风作浪、残暴荒淫的外衣。元代的社会秩序混乱,法律政策不公,《元典章》卷三十九《不得法外枉勘》记载:“今之官吏,不思仁恕,专尚苛刻,每于鞠狱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辄加拷掠,严刑法外,凌虐囚人,不胜苦处。锻炼之词,何求不得?致令枉死无辜,幸不致命者亦为残疾。”[6]《窦娥冤》当中的桃杌就是昏庸贪婪的官僚阶层的典型。他说:“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钱;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7]足见他贪财的本性,他判案不分曲直,黑白颠倒,认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见来告状的就下跪,说:“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在这样一位昏庸糊涂贪官的错判下,窦娥蒙冤被斩。不知道造成了多少冤案的官僚,任满竟然升官而去,这也可见元代法律制度的黑暗。元代社会冤狱累累,屈死之人不计其数,关汉卿敢于正视血淋淋的社会现实,继承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用戏剧形象加以暴露,借剧中人之口加以鞭笞,由此可见作者进步的思想和作品深刻的人民性。
三、讴歌妇女高尚情操
在宋元时代,都市勾栏瓦肆中妇女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元代妇女对元杂剧的繁荣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给关汉卿的戏曲创作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视角。关汉卿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作为戏剧创作的重点,不仅揭露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和各种丑恶的人物,还用更多的笔墨抨击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的剥削压迫、蹂躏侮辱,并支持她们冲破思想和制度的束缚,讴歌她们不屈不挠、勇敢抗争的高尚情操。在描绘出元代社会富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百丑图”之后,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并没有因为这些贪婪、狡诈、无赖的邪恶势力而委曲求全,而是奋起反抗,毫不畏惧,表现出了女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光辉形象,这一鼓舞人心的主题意蕴也被后世所称道。
其中最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就是《窦娥冤》中的窦娥。她是一个感天动地、至孝至贞的艺术形象。她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陶冶出来被压迫妇女的典型,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只不过20个年头,却承受了现实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几乎一切苦难。她出生于贫寒的儒生家庭,3岁丧母,7岁成为“羊羔儿息”———高利贷的牺牲品抵押给蔡婆婆作童养媳。10年之后与蔡婆婆的儿子结婚,两年便守了寡,可见她命运多么悲惨。尽管她也曾哀叹:“窦娥也,你这命好苦啊!”但她又迷信“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被生招祸尤”因此她与蔡婆婆相依为命,安分度日。但是新的灾难随着蔡婆婆向赛卢医索要“羊羔儿利”朝窦娥扑来。张驴儿父子无意中救了将要被赛卢医勒死的蔡婆婆,哪知张驴儿是个泼皮无赖,听说蔡婆婆家还有一个守寡的年轻媳妇,恬不知耻地赖在蔡婆婆家,还提出要娶窦娥。蔡婆婆半推半就,软弱无奈,但是窦娥态度强硬,并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信条,并且谴责蔡婆婆说:“怪不得女大不中留”“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把人笑破口”“怕没的贞心儿自守”“你岂不知羞。”窦娥对待张驴儿的蛮横要求是严厉无情的,她对张驴儿的拜是“做不礼科”,并呵斥道:“兀那厮,靠后!”不留任何情面。面对张驴儿的嫁祸、威胁和恐吓,窦娥毅然选择与之对簿公堂,她说:“我又不会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没想到昏官桃杌不辨是非,贪赃枉法,决定问斩窦娥。这一残忍的现实悲剧将整个窦娥的满腔愤懑推向了高潮: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气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第三折)
此后她又发下三桩誓愿:第一是“血溅白练”,第二是“六月飞雪”,第三是楚州地区“亢旱三年”。她声明:“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元代戏曲理论家孟汉卿说:“霜降始知节妇苦,雪飞方表窦娥冤。”[4](《磨合罗》)她以这种惊天动地的斗争誓愿与黑暗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终于等到父亲归来为其翻案,才使得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
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妇女的典型。她性格中所包含的伦理精神和反抗意识也体现了广大妇女思想的共优性。关汉卿根据自己对元代社会生活的细微观察和对艺术作品的加工,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一不朽的形象。这一艺术形象,凝聚着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感悟,也从人民性的角度对窦娥的反抗精神作了最好的阐释。就其深层文化含义而言,无论于今日中华民族性格、人格、良心的再确立,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皆有不可置辩的意义。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这样称赞关汉卿的《窦娥冤》:“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137尽管元代社会存在种种问题和弊端,但是关汉卿的思想没有因此受到禁锢,而是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上,从抒发人民心声的角度进行创作,运用通俗质朴的语言,揭露社会黑暗现象,讴歌妇女高尚情操。钱穆指出:“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拥,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8]正是由于关汉卿在混乱的时代可以依然守护着文学的净土不被铁蹄践踏,我们今天才可以欣赏到《窦娥冤》中铿锵有力的人民性特征。
[1]袁有芬,李汉秋.关汉卿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3]顾肇仓.元人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李占鹏.关汉卿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翁敏华.关汉卿戏曲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张文澍.元曲悲剧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施邵文,沈树华.关汉卿戏曲集导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8]伍世文,伍世昭.关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5,(8).
〔责任编辑:李敬晶〕
I106.3
A
1002-2341(2015)02-0155-04
2014-11-19
张硕(1991-),男,江苏连云港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