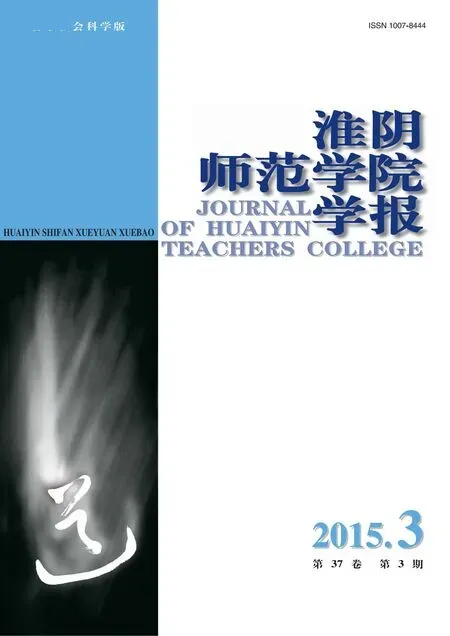论民国时期辑佚理论的讨论和创立
臧其猛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江苏南京211100)
南宋郑樵最早对古书存佚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书有名亡实不亡论”。此后明代胡应麟已经认识到类书保存古佚书的作用,而祁承提出三种求书购书的方法,其中第一种方法即为通过辑佚而得书。清儒重考据而轻理论,虽然他们辑佚成就巨大,辑佚工作也非常精密,但他们的辑佚思想缺乏系统性。因此,民国之前系统的辑佚理论仍未形成。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学者更加重视学科理论建设,再加上教学的需要,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辑佚理论就此创立并发展起来。概括起来,民国时期讨论的辑佚理论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典籍散佚的原因
典籍文献的散佚原因,历来是辑佚学者热衷探讨的问题,他们往往把文献散亡归结于“五厄”“十厄”。隋代牛弘曾谓书籍有五厄:“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1]1298-1299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又补充五厄,成十厄:“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2]172典籍“十厄”即为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五胡乱华、董卓之乱、侯景之乱、隋炀帝焚书、安史之乱、唐末战乱、靖康宋金战争、绍定宋元战争。
民国时期,对于文献散亡原因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张舜徽以秦世焚书为例,指出,没有禁止的医药、卜筮等书亡佚了,而焚毁的《诗》《书》等却流传下来。所以他说“书之亡佚不尽由于兵燹”。张先生认为书籍散亡的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古书散佚之原,盖不亡于公而亡于私”,例如孔子删《诗》;“不亡于憎而亡于爱”,如范晔《后汉书》修成,而前人所著东汉史书就亡佚了;“不亡于黜而亡于修”,如唐《五经正义》出,而六朝遗说亡佚。[3]62
陈登原对典籍亡佚原因提出“艺林四劫”[4]:(一)“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即在政治上统治阶级的禁毁。例如秦始皇焚书、隋炀帝焚毁纬书、清代大兴文字狱、修《四库全书》寓禁于修等。(二)“受厄于人事不臧而成其聚散”,即保管不善,水、火、霉烂虫蛀等毁书及书商窜改而使典籍残伪。(三)“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即历代战乱如典籍“十厄”,销毁了难以数计的典籍。天一阁、海源阁、振绮堂、寿松堂、江浙四库三阁、铁琴铜剑楼都因为太平天国战争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永乐大典》也在英法联军入侵及庚子联军入侵中被损毁。(四)“受厄于藏弄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即藏书家多珍秘其书,藏书秘不示人,使珍籍得不到传播而毁于一旦。
总之,民国时期学者对于书籍散佚原因的认识更加客观,并不简单归结于兵燹,也更加系统全面,归纳了兵燹、政治、灾害、优胜劣汰、传播困难等各种原因。
二、辑佚的定义和范围界定
(一)辑佚和逸书征集的区别。胡朴安、胡道静、刘咸炘、蒋伯潜诸先生将辑佚和逸书的收集分开讨论,蒋伯潜将两者作了比较说明,征求遗书“是指书籍之遗散于民间者言,全书是仍在的”。辑佚则是“书已久亡,绝对不能求得全书者,则不得不求之他书,考其佚文,掇拾补录,以存残编”[5]138。所以胡朴安认为辑佚应当是:“盖古书有久亡而绝不能访得其全书者,则不得不旁类以求,稽其佚文,亦期微言幸或不堕,鼎脔得以一尝。”[6]59
(二)后世辑编的文集、总集也是辑佚。对于现在还在争论的集部书辑佚问题,梁启超认为也是辑佚,例如晚明张溥之《汉魏百三家集》,清康熙间官修《全唐文》《全唐诗》《全金诗》,其性质实为辑佚,它们与《唐文粹》《宋文鉴》等书性质不同,《唐文粹》等是选本,立一标准以为去取,而《汉魏百三家集》等是辑本,见一篇收一篇,务取全备。刘咸炘先生也赞同把后世重新辑编的文集视为辑佚,他认为今本唐人小说文集就是最早的辑佚。萧一山先生也赞同这个观点:“康熙嘉庆间官修之《全唐诗》、《全金诗》、《全唐文》,皆属辑佚体。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搜辑极富,足为清代巨制。”[7]759
(三)辑学术宗派遗说也是辑佚。梁启超认为惠栋、余萧客辑汉儒遗说是清代辑佚的开端,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亦说:“《九经古义》甄明佚诂,亦符臧氏(臧琳辑佚)之书,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沈》,网罗放失,掇次古谊。”[8]197胡朴安、胡道静、蒋伯潜等均认同此说。
(四)补辑的界定。梁启超对补辑和校辑进行了界定:“亦有其书虽存而篇章残缺,据《大典》葺而补之,例如《春秋繁露》;或其书虽全,而讹脱不可读,据《大典》雠而正之,例如《水经注》。”[9]235陈钟凡对补辑的定义范围更宽,他认为古代典籍,有书成时就有遗漏失载或残缺不完者,如《汉志》不录萧何《律令》、叔孙通《朝仪》等文,《旧唐志》不著韩愈、柳宗元之文,正史中也有缺少表志者,“则补苴罅隙,又有赖于后之读古书者也”[10]54,因此,他认为对原书所缺部分的补充也是辑佚范畴。刘师培也认为对史书的补充也属于辑佚,他举例:“钱(大昕)作《廿二史考异》,并拟补辑《元史》,王(鸣盛)亦作《十七史商榷》,采掇旧闻,稽析异同,近于摭拾、校勘之学……(洪)亮吉旁治地舆,勤于摭拾,曾补辑《三国疆域志》、《晋齐梁疆域志》,即所辑汉魏晋,亦摭拾之学也。”[8]197-198
对于地方文献辑佚,例如《扬州文征》《浣湘耆旧集》等,梁启超认为性质亦为辑佚,是对于一地方人之著作搜采求备,“其宗旨皆在钩沉搜逸,以备为贵,而于编中作者大率各系从小传。盖征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9]275。
综上所述,民国学者对于辑佚的定义并不限于狭义的辑佚,即不限于以原有独立文献单位为对象的辑佚,而是达到了广义辑佚的定义范畴。民国学者还将具有辑佚性质的文集、总集,辑汇某一宗派的学说也作为辑佚来看待,这就扩大了辑佚的范围界定,对辑佚学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辑佚的起源
对于辑佚起源问题,民国学者有多种观点:
(一)起源于宋代王应麟说。章学诚首先提出[11],梁启超、张舜徽、胡朴安、蒋元卿等均赞同这种观点,如胡朴安在《古书校读法》中说:“溯蒐辑书之始,当源于宋王伯厚之《三家诗考》。”[12]47
(二)起源于宋代陈景元说。叶德辉认为应始于宋代陈景元[13]。蒋伯潜赞成此观点,他说:“从《意林》、《文选注》辑所引《相鹤经》,这便是搜辑佚文。”对于辑佚起自王应麟说,蒋先生表示反对:“章氏并以王应麟的辑郑玄《周易注》、《尚书注》、《三家诗考》,为辑佚之始……但上引《东观余论》所记辑《相鹤经》,当在北宋,又早于王应麟了。”[5]140
(三)其他学说。刘咸炘主张辑佚起源于宋人辑唐人小说文集:“宋时所传唐人小说及唐以上人文集卷数,多与原书不合,校以他书引,往往遗而未录。盖皆出于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辑佚之事也。”[14]18胡道静《校雠学》提出孔子辑史说[6];孙德谦则提出刘向在校理群书时也辑增了佚文,其《刘向校雠学纂微》中著有“增佚文”一节[15]。
总之,对于辑佚起源问题,民国学者是百家争鸣,但基本公认起源于宋代,对于具体起源于哪一人其实也没有必要继续争论,正如张舜徽所说:“总之,这几家的见解虽各不同,但辑佚的工作,毕竟是宋代学者开其端,这是大家所公认了的……我们今天也不必再纠缠于开始于哪一个人、哪一部书,作些不必要的争论了”[16]299。
四、辑佚的取材
对于辑佚的取材,梁启超概括为五点:(一)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二)以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例如《史记》《春秋繁露》等所引古子家说;郑康成诸经注、韦昭《国语注》所引纬书及古系谱等。(三)以唐人义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例如从《周易集解》辑汉诸家《易》注;从孔贾诸疏辑《尚书马郑注》《左氏贾服注》等。(四)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例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以下《史记》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五)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遗文之资料。如《文选》《文苑英华》等。梁启超所指出的五条资料来源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蒋元卿、张舜徽、萧一山都基本赞同梁说。
民国学者特别着重提出注和类书保存佚文的巨大功用。刘咸炘说:“辑佚者所取资最多者,曰三注、四大类书。三注者,《三国志注》、《水经注》、《文选注》也。四大类书者,《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也。”[14]18对于类书保存古逸书的作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中进行论述[17]51。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他指出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是文字记录史料之一,类书的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类书是分类编纂,更方便于学者之检索,故向类书中求史料,所得往往较多。[18]244张涤华《类书流别》中也论述了类书保存遗逸的功用:“陈编旧籍,时有散亡,后人生千载之下,每苦不睹往古之盛。若有类书,以撮其大凡,条其篇目,则原书纵逸,而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犹可资以补苴罅漏。世行《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辑佚家珍逾球璧,爬罗剔抉,不遗余力,而百千种佚书,遂缘以复见于世。此虽非撰集类书者始意所及,然亦由其体裁之善,有以致之,非偶然也。此类书之存遗佚,为裨四也。”[19]37
除此之外,胡朴安、胡道静、刘咸炘提出可以从同类之书中进行辑佚,例如郑康成之《郑志》虽亡,而见于孔颖达之正义者可辑也;《三家诗》虽亡,而见于秦汉人之著述者可辑也;真《古文尚书》虽亡,而见于司马迁《史记》者可辑也;汉儒之《易》虽亡,而见于李鼎祚之《周易集解》者可辑也。梁启超先生还提出从逸书同时代人著作中辑佚,例如从《孟子》《墨子》书中辑告子学说;从《孟子》《荀子》《庄子》辑宋钘学说;从《庄子》中辑惠施、公孙龙学说;从《孟子》《荀子》《战国策》书中辑陈仲学说;从《孟子》书中辑许行、白圭学说,等等。
辑佚取材也是辑佚方法论中的重要一环,民国学者对其论述较多,也非常详尽,特别是认识到类书中保存了大量的佚书佚文,这对此后学者从何处辑佚提供了指导。
五、鉴定辑佚书优劣的标准
梁启超认为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有四:“(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例如《尚书大传》,陈辑优于卢、孔辑;(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例如秦辑《世本》劣于茆、张辑;(四)原文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例如邵二云辑《五代史》,功等新编,故最优。——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何如,若寻常一俚书或一伪书,搜辑虽备,亦无益费精神也。”[9]241这些标准成为鉴定辑佚书的定制。此外,梁启超对有提要、小传的辑佚书大加赞赏,如《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两晋六朝文》每家各为小传,冠于其文之前,而马国翰于每种辑佚书之首冠以一简短之提要,说明本书来历及存佚沿革。这两部书都为梁启超所称赞。
刘咸炘《校雠述林》中有《辑佚书纠谬》一节,对辑佚书的弊病进行了总结,他将辑佚书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点:“漏”“滥”“误”“陋”,刘咸炘先生认为要消除这些弊病,辑佚者应该多考证订误,不能确定的应该存疑待考:“汪继培辑《尸子》,别录存疑一卷,叶德辉辑《傅子》,别为订误一卷,最为慎密,能以为法,庶几可免于诸弊矣。”[14]22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在论述清代学术时提出“摭拾”派(即辑佚派)的概念,提出清儒辑佚存在不辨真伪的缺失:“然功力至繁,取资斟别,或不知鉴别,以赝为真。”[8]166张舜徽也认为学者在辑佚过程中要进行细致考证,防止犯漏辑、滥辑、误辑、陋辑等错误。
辑佚书优劣的鉴定标准是辑佚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它为此后学者从事辑佚活动提供了一个标准和目标,确保学者减少漏辑、滥辑、误辑、陋辑等错误。因此,辑佚书优劣标准的确定规范了辑佚活动,也为辑佚学向正确方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辑佚中应注意的事项
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提出辑佚中应注意“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辑佚之难于别择”“辑佚之必须有识”“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四点。
我国典籍文献汗牛充栋,名称、内容、体例相似的古籍很多,有的还夹杂了大量的伪书伪文,而且书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字形接近,传抄或者写刻时就会发生错误。因此,张舜徽认为学者从事辑佚工作要先对辑佚对象进行研究,做好准备工作,“故学者苟有志乎搜辑遗书,首必究心著述流别,审知一书体例,与之名近者几家,标题相似者有几,皆宜了然于心,辨析同异,次则谛观征引者之上下语意,以详核之本书,庶几真伪可分,是非无混,别择之标或可寡过耳”[3]109。
刘咸炘也提出辑佚者应该对类书引用的同名书加以区别:“而三大书征引浩博,所列诸书凡一名叠见者,《太平御览》皆作又字,《文苑英华》皆作前名字,《广记》皆作同上字。其间先后相连,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缘此多录数十条也。”[14]18-19
民国学者还认为辑佚学家从事辑佚工作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因为尊崇某位古人圣贤,而将别人的著作辑佚到他的名下。例如清代学者普遍尊崇郑玄,有的辑佚学家把服虔的著作当成郑玄所作:“郑玄遍注群经,而独不及《春秋左氏传》。后之辑北海遗书者,率取服虔《左传注》以入录,盖据《世说新语》以为服氏注出于郑,即郑学也。”[3]110而事实上,服虔的著作早已流传。
张舜徽认为自己动手搜辑佚书,要在学问成熟以后再做,因为此前自己读书不多,见闻不广,虽然对辑佚有兴趣,但难免挂一漏万,加上这种工作做起来很费时间,耽误了读书的岁月,尤为可惜。辑佚要先打好基础,以学习研究现有书籍为基础,不能好高骛远,盲目崇古,以为最早就是最好,“要之学术有本末,而致力有先后,学者苟明于始终缓急之宜,则辑佚之事,非初学所宜言也”[3]112。他在《中国古籍校读法》中也说:“初学似不必在这里面投下太多的劳动,等到业务基础打好以后再谈此事,比较易着手。”[16]310
蒋伯潜也认为辑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如但见某书中有引此书者,按条钞录,便算辑佚,则只需几个书记,便可了事。这正和校勘一样,现在印刷所中的校对,把底本对校初印的样张,也不能说他们是校勘家。
刘咸炘提出类书中佚文有的也是辗转抄自他书,并不是原书佚文,有的已是二手、三手资料,而且本身也有讹误,所以也不可尽据。且类书在编排上将同名的书编在一起,难以区分,这就要求辑佚者认真抉择。蒋伯潜先生也提出辑佚必须细心参校。
由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民国学者对于辑佚中注意事项的认识趋于一致,他们共同提出并强调辑佚中要进行考证,辑佚要和校勘等其他文献学方法相结合。
七、辑佚的价值意义
对于辑佚,梁启超既有褒又有贬,他承认辑佚的价值,赞扬先辈的刻苦和成绩,“吾辈犹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20]55,“自清乾隆间编‘四库’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搜集之赐也”[17]51-52。郑鹤声先生《中国史部目录学》中也赞同梁启超的观点。
此外,梁启超认为辑佚对辨伪也是有功用的:“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已佚的书,后人伪造。若从别的书发现所引原书佚文,为今本所无,便知今本靠不住。”[9]228
陈钟凡、胡朴安、胡道静、孙德谦、蒋元卿、张舜徽诸先生对辑佚和清儒辑佚成绩也是大加赞赏,梁启超、张舜徽更是认识到不能盲目夸大辑佚的作用,不能放弃现有的书和文献资料,要对辑佚客观对待。“其余如钩沉、辑佚一类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的史料丢开不管。”[17]268
总之,民国时期学者在辑佚理论方面把历代学者的见解和采用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使辑佚理论系统化、条理化,使辑佚工作更具有规律性、科学性。民国时期的辑佚理论思想至今仍是辑佚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民国的理论研究也为辑佚学成为独立的学术门科奠定了基础。
[1]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四库全书本:8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张舜徽.广校雠略[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 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 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7]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0] 陈钟凡.古书读校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1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十[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2] 胡朴安.古书校读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13] 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4] 刘咸炘.刘咸炘论目录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15]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M].四益宦刊印,1923.
[16]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1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8] 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
[19] 张涤华.类书流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