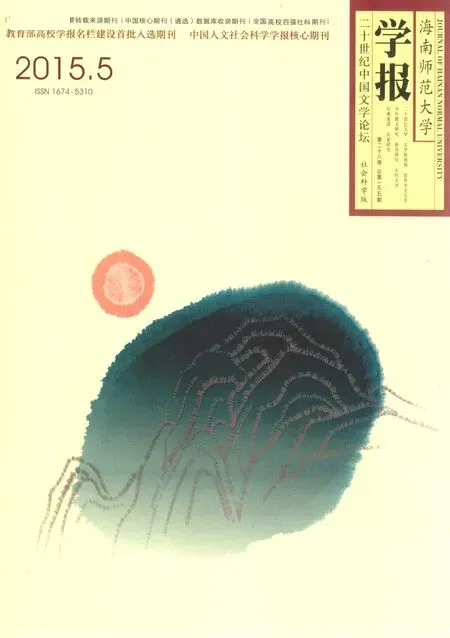家国情怀与个人伦理——叶问系列电影的比较分析
沈嘉达
(黄冈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黄冈438000)
2008年伊始,短短数载,叶问题材成了香港电影消费的宝藏。屈指算来,就有叶伟信导演的《叶问1》(2008年)和《叶问2》(2010年),有邱礼涛导演的《叶问前传》(2010年)和《叶问之终极一战》(2013年),当然还少不了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2013年)。需要说明的是,电影《叶问3》正在紧锣密鼓地制作之中。此外,还有50 集电视连续剧《叶问》。
叶问作为一代武术大师,生活阅历丰富,授徒甚多(最著名的便是李小龙),本身便已具备了反复消费的可能。笔者感兴趣的是,具备现实属性(真人故事)的叶问系列故事,是如何被各位导演演绎得风生水起?
一
20 世纪80年代,一部《霍元甲》及其后的《陈真》电视连续剧,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大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主题曲至今耳熟能详,民族英雄霍元甲、陈真的塑造让人记忆犹新。这并不难理解。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屡次为列强所侵略,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国人,通过霍元甲擂台痛击俄国大力士的强力举措而扬眉吐气,高涨起被阉割许久的民族情绪。往前追溯,李小龙1972年拍摄的电影《精武门》已经很好地将民族情怀与英雄崇拜结合起来了。电影中,得知师傅霍元甲为日本人所害,愤怒的陈真(李小龙饰)独闯日本武馆,砸烂“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匾,痛击日本武士。李小龙的激情演出,深深地烙上了国家和民族印迹。1993年,电影《精武英雄》问世,由李连杰饰演的陈真同样深入虹口道场,一脚踢飞了日本军官藤田刚扔过来的“东亚病夫”匾额,惊心动魄,最终击毙藤田刚这个日本“机器人”。颇有意味的是,“东亚病夫”的牌匾一再成了中华民族的耻辱记忆,在系列影视中,皆由身体强壮、武艺高超的中华英雄一雪前耻,让人热血沸腾,无比畅快!从李小龙到李连杰,从黄元申到甄子丹,他们演绎的英雄故事中,民族、反抗、牺牲等始终是被我们一再唤起的关键词。有意思的是,2006年李连杰重新演绎《霍元甲》,电影结尾处,霍元甲为了武术精神而宁愿被日本武士田中安野打死,这一情节“设计”不止是激起所谓的霍元甲后人提出强烈抗议,更是为诸多的国人所完全无法接受!我们的民族英雄,怎么会如此窝囊而死?附丽其身的家国情怀、英雄气概哪里去了?
说到底,霍元甲也好,陈真也罢,都是作为符号而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的。而这个“符号”的核心便是“民族英雄”。沿着这种思路,我们便不难理解,《武林志》《黄飞鸿》《醉拳》等电影为何不避重复,一再让东方旭、黄飞鸿们痛击东洋鬼子和西洋鬼子……
“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我,佛山四小龙!”这是《叶问2》中被日本鬼子枪击而疯疯癫癫的周清泉,在叶问擂台击败英国拳师龙卷风后,突然清醒时所吐的真言!在最初的叶问题材影片也就是叶伟信的《叶问1》和《叶问2》中,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导演让叶问再一次接续上霍元甲、黄飞鸿等民族英雄的豪气与血性,分别击败日本军官三蒲将军和英国拳师龙卷风。作为定性,外国列强依然是卑劣下作的,譬如日本人枪击比武后的中国武师廖师傅,英国人在叶问与龙卷风比赛时有意限制其使用脚功,狂傲的龙卷风在比赛铃声响过之后仍然偷袭叶问致其受伤等等——诸如此类故事以及细节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观众的民族义愤,从而也就使得叶问的擂台比武——看起来——为中华民族争光的色彩更加浓厚。
然而,细细体味叶伟信的两部《叶问》,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并不是导演所要真正表达的主题。至少,已经不再是《精武门》《精武英雄》等电影那样的民族主题了。
尽管两部影片的开始,都将故事背景定位在国家多灾多难时代——譬如《叶问1》设置为日本人侵占佛山时期,然而,我们很容易看出,在两部《叶问》中,“国家”并不是作为突出在前台的“实体”,换句话说,“国家”只是一种“虚拟”存在;导演所要展示的也不是危亡关头的民族救亡故事,而是着力于“国家”虚幻时代的个体生存。没有显在的“国家”,当然也就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民族正义与非正义。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渺小”的个人,“世俗”的个人。电影中的叶问是大英雄吗?是,又不是。所谓是,因为他打败了三蒲将军和龙卷风;不是,因为其行为并非明确指向为国争光为民族伸张正义(所谓阶级仇民族恨)。我们注意到,在《叶问2》中,导演有意设置了武师洪震南这一角色。洪震南与龙卷风比武,宁死不屈。何以如此?洪震南大义凛然地说:“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这里,武术与民族气节相关联。还有一个细节,龙卷风打死洪震南后,狂妄地弄了一根大香(很长很粗),叫嚣:“在这根香烧完之前,我会打败所有的中国师傅!”龙卷风上台比武之时,身上披着一面英国国旗,这也似乎再一次印证了民族仇恨——然而,随后上台痛击龙卷风并有机会打死他为中国武师洪震南报仇(也就是为民族复仇)的叶问,却并没有击毙龙卷风,而是“手下留情”放他一条生路。叶问在其后的答记者问时说:“今天的胜负,我不是想证明我们中国的武术比西洋拳更加优胜,我只是想说,人的地位,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人格,不应该有贵贱之别。我很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大家可以学会懂得怎样去互相尊重。”与此相印证的是,作为恶的象征的英国警察卫力,并不是由中国人处置(中国人善良而正义,应然出任这个角色),恰恰是由卫力的上司(同样是英国人)将其法办。也就是说,恶的根除,并不是完全、彻底地由中国人(这里就是叶问)来实施。诸如此类细节,不一一列举。由此可见,传统电影中的民族主义表现,让位于“世界主义”呈示。
在一般的电影电视中,我们会发现,民族英雄往往有一个“成长”过程。常常是这样的:“英雄”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英雄,相反,很可能是莽夫,是个人主义者;就其武艺来说,也往往是半生不熟,因之屡受挫折。我们经常见着这样的例子:张三(主人公)苦大仇深,有杀父之仇(或夺妻之恨),于是愤然复仇。然学艺不精,反被仇家所伤。后逃脱上得深山名寺,得遇高人指点,既学其武艺,得其精髓,又俘获其女芳心,二人练得鸳鸯腿、雌雄剑什么的,终于君子报仇,得雪前耻。这是屡试不爽的武侠模式。后来,电影中加入民族主义成分,让土匪恶霸与洋人相勾结,沆瀣一气,我们的民族英雄最终将其一网打尽——既报了家人仇恨,又一展民族情怀!叶问故事,完全可以依照此种模式塑造人物,在人物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处,完成性格塑造和伦理升华。就是说,随着国难的加重和民族情绪的高涨,英雄终成正果。可是,在两部《叶问》中,我们不能解读到这些,相反,叶问一开始就被定型,不是境界高远的民间大侠,不是心忧天下的正人君子,更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天地英雄,叶问,就是一介大时代沦陷下的草根小民而已。叶问的性格,并无上升(升华)的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消解了英雄属性。
岂止是叶伟信的两部《叶问》如此,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邱礼涛的《叶问之终极一战》,同样摒弃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化结构法则。《一代宗师》根本就可以说是在讲宫二小姐复仇马三的故事,充其量,叶问在这儿只是充当宫二小姐的爱情对象物,如果硬要扯上叶问,电影所表现的也不过是那种恩格斯所言的“老而又老的爱情故事”。叶问赖以立身的武功侠义,完全无法“对应”时代特征与民族诉求。电影中,民族热血只是在灯叔的身上短暂翻腾——当日本人侵占佛山时,灯叔慨然说:“南粤子弟火气旺,孙子才不敢杀日本鬼子哩,来一个杀一个。”然而,也就是说说而已,没有任何下文。必须指出的是,表面上看,马三在20 世纪40年代投降日本人,做了“奉天协和会会长”,因之,宫二小姐的复仇,似乎可以看作是家仇和民族仇恨一起算。然而,宫二小姐的复仇马三,在电影中被反复强调——只是宫二小姐“要拿回宫家的东西”,是为父报仇,清理门户,而无关乎国家与民族。邱礼涛的《叶问之终极一战》,黄秋生饰演的叶问,无论是出手救助歌女珍妮小姐,还是力战魏天霸等黑道人物,抑或与白鹤派掌门人吴忠的恩怨情仇——所有这些,都与民族、国家无涉。在《叶问之终极一战》中,我们感受到的叶问,更像是一个大家长,时时刻刻在呵护着他的弟子;同样,他的弟子们也都热爱、敬爱、尊崇师傅,共渡生活难关——这里,哪有什么以武报国壮怀激烈的情怀呢!
二
与“民族、国家”等相匹配的,当然是主人公的舍小家顾大家的英雄行为,是见血封喉风霜刀剑的天下大义,是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担当精神,因此,英雄人物的话语、行为、心理表现等,便带上了卓然独立的症候。
纵观这几部叶问题材的电影,生活化、世俗化、平民化是其共同色彩。
我们看到,叶问是一个深受传统伦理教化的习武者,在他眼里,家庭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譬如《叶问1》中,与廖师傅和金山找的咄咄逼人相对照,叶问是以吃饭的背影而出场(亮相)的——当廖师傅急切地要与叶问比试武艺之时,叶问拒绝的理由竟然是要“吃饭”!廖师傅一再催促,叶问仍然慢条斯理,还邀请廖师傅一起用餐。用毕后兴味盎然地问道:“今晚的饭菜还可以吧?”——叶问完全不把比武当回事!因为吃饭更重要。
吃——也就是饮食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一般意义上说,有闲有钱才能精吃,而这里,“吃饭”成了朝不保夕的芸芸众生实实在在的感受。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是为了谋生糊口。廖师傅是如何死的?为了多得几袋大米养家;曾经小康的叶问不也为了挣得一点粮食,而去煤场挖煤么?在《叶问之终极一战》中,再次凸显了“吃”的概念:1950年,叶问只身来到香港。已经名震广东的叶问遭遇他人要与之“切磋切磋”的挑战,这时的叶问回答道:“肚子饿,”“没力气比武。”女徒弟李琼闹罢工,被港府警察所抓,叶问找到同为警察的徒弟邓声,要求他想方设法解救李琼。邓声解释困难,这时的叶问一是答应教邓声某种绝招,再就是“请”邓声吃龟苓膏——深受感动的邓声才会尽力救出李琼。这里,还是“吃”!曾经辉煌半边天并帮助过叶问的李耀华老板,因为家穷,不得不狠心卖掉自己的第六个孩子,以养活夫妻二人和另外五个孩子。同样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叶问,感谢李老板的最好办法,就是请李老板“吃”一顿,以报当年李老板搭救自己之恩……
叶问怕老婆,人所尽知。叶问夫子自道:“这个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叶问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这里,实实在在的小家遮蔽了被虚化了的国家。用叶问妻子张永成的话说,就是“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我只知道,(一家人在一起)我现在很幸福”。与此类似,《叶问2》中,叶问就问洪震南:“洪师傅,你认为(比武)胜负重要,还是跟家里人吃饭重要?”家庭(老婆和孩子)自比“胜负”这些外在的东西重要,这一点,不言自喻。
真实生活中的叶问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历史上的叶问本就是广东佛山的旺族子弟,从小受到家庭严谨的儒学教育。16 岁时被送到香港圣士提反读书,接受英式教育。后返回佛山,任职佛山侦缉大队书记、广东防务稽查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等。解放后,发妻张永成过世,年近60 的叶问只身来港,娶得一名来自上海的女子为妾,全然不顾众多弟子的反对。由此可见,生活中的叶问本就是深受儒学熏染,以家庭为天下的“凡夫俗子”。系列电影中的叶问,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生活中的叶问的真实写照。
从香港电影艺术发展的角度看,系列电影中的叶问生活化、世俗化实不足奇。当21 世纪香港电影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之后,重新转向,开辟另一片天地,也是势在必然。20 世纪80年代的霍元甲、陈真等,应和的是国人改革开放要扬眉吐气的民族诉求,也就是说,国人需要那种大刀阔斧式的硬汉形象,需要那种血荐轩辕的民族脊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当一个时代需要英雄之时,就会创造出英雄来。当30年过去,现代性诉求压倒了当初的民族性诉求,个人性遮蔽了民族性,恒长性大于当下性,这时,电影电视中的新的叶问形象便应运而生。
譬如说,“武术是干什么用的”这样的命题有了新的答案。传统答案当然是保家卫国。这里,家国一体。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当外族入侵,家园失落与民族危亡总是连在一起,因此,擂台上痛打俄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等,既是为家,更是为国。有了这样的崇高境界,英雄形象自然超凡脱俗。然而,在叶问系列电影中,武术就是武术,武术的功能就是强身健体。习武之人,强调的是武德。这里的武德,可以理解为打抱不平,更可以看作是以武会友,以武止戈,点到为止。譬如《叶问1》中,要与三蒲将军比武的叶问宣讲的是:“武术虽然是一种武装力量,但我们中国武术里包含着儒家哲理。武德,仁也。推己及人,你们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个道理。”《叶问2》中,徒弟黄粱好出头动手,叶问曰:“中国武术,包含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还有修养。贵在中和,不争之争。”影片结尾,年幼的李小龙想要拜师叶问,理由是:“看到不顺眼的人,我就想去打他。”叶问意味深长地说:“等你长大了,再来找我吧。”表面上看,是嫌李小龙太小,实质上是说李小龙彼时并不懂得武术的精髓,因而拒收。
这种思想同样在《一代宗师》和《叶问之终极一战》中得到淋漓的体现。中华武术会长宫羽田为何赶走马三?就是因为发现马三锋芒毕露,容易“出鞘”,不懂得“藏锋”。甚至宫羽田命名之为“马三”,其寓意也就在做人要“言必称三”,不应争强好胜。在他眼里,“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第一阶段只看见自己,故热血沸腾,总想当天下第一;第二阶段,发现宫二小姐所言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便又上了一重境界。最终,习武之人以众生为重,怜悯众生便是终极目的。
笔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电影中的叶问始终不以武艺高强为喜,相反,总是感觉习得高深武艺并无大用。这一方面源于国家的残破与受辱,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们对武功的“解构”思想——在这里,武功再高强,也不足以匹敌已经具备现代化枪炮的列强,再也不可能像早期的李小龙电影,仅凭着三拳两腿便可无敌天下了。中华武术,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叶问,不就是靠它在香港谋生的么?《叶问1》一开始,鞭炮声中新武馆开张了,话语也随之响起来:“又来了一个争饭吃的……”武术,即便是中华武术,也是吃饭的家什。
三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主要功能还在于叙事,这就涉及一个叙事伦理问题。为何叙事?所叙何事?如何叙事?
《叶问前传》可以作为一个“症候文本”来进行分析。同样为邱礼涛所导演,同样是叶问故事,2010年出品的《叶问前传》与2013年的《叶问之终极一战》简直判若云泥。简单地说,《叶问前传》让我们仿佛回到了20 世纪80年代中期,影片一开始,黑白胶片呈现的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面貌,炮火连天,民不聊生。这是“前背景”,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基调”,因为电影马上转到了1950年的香港。叶问这时在港授徒谋生。接着,影片回到1915年,叶问来香港圣士提反学校读书,在与同学玩曲棍球时,遭遇一英国学生以中国人为“中国猪”及“东亚病夫”的侮辱。叶问主动出击,一身正气地用咏春拳狠狠教训了这个“外强”,显示了华夏青年的爱国热情。这只是个“题头”,故事的重点放在佛山。这有点类似于宋代话本里的“入话”。影片中,学成归来的叶问,在家里与义兄天赐一同习武。原来,这个天赐是父亲多年前好心收留的弃儿。天赐大婚,身在佛山的日本商人北野派人送来贺礼,当晚,正直的佛山精武会李会长被人残忍杀死。叶问受冤入狱,天赐却顺利地当上了精武会会长。后得副市长千金张永成相救,叶问查出真相,发现杀死李会长的竟是义兄天赐,而指使天赐的元凶正是日本商人北野。叶问出手,向天赐和北野索讨公理和正义,迫使天赐说出真相后剖腹自杀——原来,北野会长很早就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用影片中的话来说,就是利用商务活动之便偷渡日本儿童来中国,装作社会弃儿,打入中国家庭及社会机构内部,“执行渗透任务”。譬如天赐,就是北野的亲生儿子田中英杰,他12 岁遵循父训潜入中国,后成为“大日本皇军少佐”……
显然,《叶问前传》的电影叙事基于这样一种伦理: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是蓄谋已久、无孔不入且心狠手辣的。中日民族之间存在着绕不过去必须面对且应该时刻警醒的血海深仇。影片中,除了“输入”幼儿执行长期潜伏任务外,北野还“捐款”30万元给佛山精武会实则收买人心,让天赐当上佛山精武会会长,从而控制整个佛山武术界;其后,北野又让天赐杀死李会长并贿赂督察长栽赃叶问,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凡是妨碍我们的人,都要铲除。”——有了这样一种“预设”,故事的真实性、可行性就不再是必须考量的要素,民族情绪、集团诉求、政治倾向的表达就成了直接目标。从甲午战争开始,一直延伸到“七七事变”被其入侵的耻辱记忆和民族焦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叙事的逻辑起点和国家形象重新建构的终点。叶问的胜利,其实就是民族的胜利。中华武术击败大和剑道,寓意的就是民族正义的必然张扬和终极胜利。我们说,《叶问前传》中的叶问,与霍元甲、李小龙、陈真等一起,共同归入了民族英雄谱系之中。
电影作为艺术,要求电影人必须对其艺术属性葆有足够的“尊重”——不仅仅是对“艺术”之外的社会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间离,还在于需要建构起电影艺术的“个人伦理”。以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为例,我们要问:“这还是关于叶问的英雄故事吗?”答案是否定的。说到底,《一代宗师》讲述的是宫家的故事,准确地说,叶问不过是“视点”,由此来“观照”出宫二小姐故事而已。影片的重心应该是宫二小姐复仇马三的故事,捎带上宫二小姐见情见性的凄美人生。与此相一致,电影很讲究“如何”叙述故事,讲述的是“如何”模样的故事。这种典型的王家卫风格,别具一格。
还是邱礼涛,其导演的《叶问之终极一战》,让人眼睛一亮。电影多次变换叙述故事的视角—一开始是以叶问的儿子叶准的口吻来述说的,讲的是“我父亲”如何如何;中途荡开一笔,转换到工会主席梁双身上,因为此时的叶准并未来到香港,无法铺开笔墨,展开叙述;1960年后,再回到叶准那儿,重新讲述其父亲从前的故事。表面上看,电影覆盖的是1950年到1973年叶问因病去世的这一段时空,是“顺序”;实际上,整个故事却是“倒叙”,也就是叶准在回忆父亲往事。这样,叙述视角跳跃灵动,丰富了观众的想象,也使得电影本身避免了一览无余的毛病。
显然,《一代宗师》和《叶问之终极一战》已经偏离或者说已经疏离了类似于《叶问前传》这类电影的传统叙事伦理,也就是说,他们镜头下的叶问不再是那个霍元甲、陈真式的叶问,而是王家卫、邱礼涛(2013年)的叶问。谁是一代宗师?是叶问吗?叶问只是其中宗师之一。因为还有宫羽田,还有宫二小姐,他们以各自的生命阐释着对于“宗师”的理解。宫羽田大气、沉着、开明、正义,宫二小姐果敢、坚决、恩怨分明;甚至是一线天,也可以算作是一代宗师,他也有着对于武术、武林和武德的独到理解。而《叶问之终极一战》所叙“终极一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决斗,不是最后的家国情仇了断,恰恰是对“生活”、对“武德”的持续保卫战。我们在电影中无法看到诸如擂台一决雌雄、血雨腥风那样的场景,电影中体现的是生活流水线,是叶问个人“断代史”,是生活本身。这哪里是“最后一战”呢?
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第一次使用了“去魅”(deenchanted)这个词。他提醒人们:“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确然如此,在过去,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日月循环这些人们所无法理解无法掌控的现象成为了生活之“魅”,人们将自己的恐惧、猜想附加于这些之上,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着精神宗教,以有意无意地维持着这种“魅力”。科学的发达,让人们大量祛魅,看清了世界的同时也了解了自身。然而,科学的发达并不意味着“魅”的从此销声匿迹。“魅”不再是过去的神秘主义、巫术玄学、宗教体验等,而拓展到现实生活中的某种“集体无意识”——非理性思维和习惯性建构模式。本文前所述说的“言必称民族”、“武必造英雄”之定势思维及其重复实践,将英雄神化、固化、僵化,是不是一种时代之“魅”?就我看来,其“魅力”巨大,影响深远。考据叶问系列电影故事,《叶问前传》其实是在“复魅”;而其他几部片子,在很大意义上说,已然“祛魅”——它们已经卸掉了叶问身上的民族标示,还原了他的平民、世俗、务实等色彩。这,我们自可细细思量。
[1][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