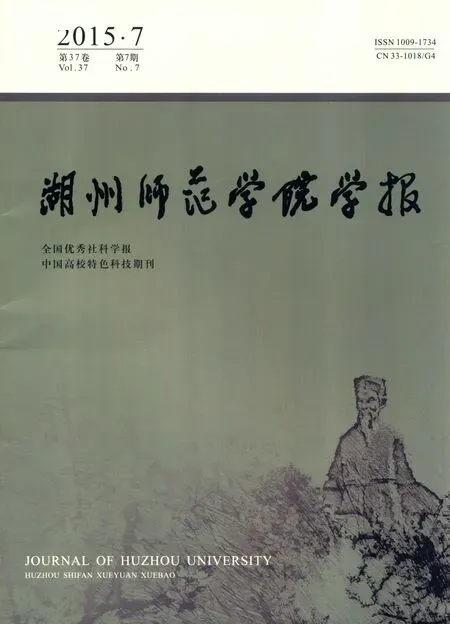艾伟《爱人同志》的叙述声音*
王昌忠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艾伟创作于本世纪初的《爱人同志》是一部有着相当艺术水准的长篇小说。作品真切、细致地书写了在中越战争中负伤的军人刘亚军与张小影之间艰难、困苦的爱情与生活历程以及悲剧性结局。正如吴义勤所言,作品“完成了对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历史变迁和精神变迁的独特阐释,其对于人与世界、人与时代关系的独特解读,对于爱情、人性、英雄等时代性词汇的解构,都赋予小说一种罕见的力量和深度。”[1]时事、命运、处境和情感、心性、精神的“变”与“拒变”构成作品的内在张力并使作品呈现出饱和、紧张的美学特征。除了内容厚实、饱满,思想深沉、犀利,文体精致、细密,结构匀称、齐整等艺术质地之外,《爱人同志》的叙述策略也颇为机巧、高妙。根据叙事学理论,作为叙事性文本,《爱人同志》只能是叙事的结果。着眼于阅读效应,《爱人同志》最典型和最具特色的叙事品格体现在叙述声音的设置和安排上。叙述声音属于叙述语态这一叙述学范畴,指的是作为“表达出构成文本的语言符号的那个行为者”[2](P8)的叙述者的声音,也就是“谁在叙述”中的“谁”的声音。叙述声音是叙述者的情感、思想的传达和反映;叙述性文本正是通过描述、阐释、评价等叙述声音实现“叙述干预”并由此服务、配合于作品的主题动机。叙述话语的叙述分为“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其叙述声音分别称为“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和“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是故事人物发出的声音,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则是置身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它们分别表征着故事内人物和故事外人物的情思意念。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和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的有机混融、恰适整合,造就了《爱人同志》的叙述声音的突出特色。这一叙述声音特色,使得作品的整体感、和谐感得到了有效彰显。
一
作为典型的叙事话语,小说的文本内容主要由四种叙述声音来承载:展示人物外在情形(事件、状貌、场景、行为、置身环境等)的声音,描述人物心理情形(情感、思想、感受、体验等)的声音,再现人物语言(对话、独白)的声音,阐释、评析(人物、事件、场景、情形等)的声音。这些声音既可以由故事内叙述者来承担,也可以由故事外叙述者来行使。也有不少作品,比如《爱人同志》,则通过作者的巧妙处理,实现了故事内叙述声音和故事外叙述声音的整合和混融。外在客观事象的叙述与内在主观心象的有机配置、交汇便是《爱人同志》实现故事内叙述声音和故事外叙述声音的方式之一。
刘亚军与张小影的婚恋经历、生存际遇构成了《爱人同志》的故事框架和内容线索。为了充分、有效呈现作品的外在内容要素,作品交叉运用了“讲述”和“展示”两种叙述技艺,其中既有省略、概述,也有场景、停顿。就第一叙述层而言,作品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也就是说,以“详尽、准确、‘生动’的方式”从而“程度不同地造成模仿错觉”[3](P109)地“展示”刘亚军、张小影的外在生命场景、生存情形的主要是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另一方面,虽然有着较强的故事性和情节性,但《爱人同志》并非以故事化、情节化见长,而是以心理性、感觉性取胜。整体来看,故事和情节不过是作品的支架和凭依,其间充溢、弥漫的是大量感觉、感受和情思、意念。在《爱人同志》中,细致交代遭遇、处境的文字,详尽描绘情形、场景的段落,以及精微刻画环境、氛围的语言,其实不是很多,几乎不能视为结构文本的主体。作品的话语主体当是人——主要是刘亚军、张小影——在特定情境、事件之中的感受、体验、感觉、情思,即心理内容。可以认为,作品中人的外在遭遇处境和行为举止只是机缘、触点,其作用在于引动、激发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空间。既然主要是故事人物刘亚军、张小影的心理内容,那么传达这些心理内容的叙述声音就主要是故事人物刘亚军、张小影的叙述声音即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了。
本来,任何小说文本都组织有外在的事象话语和内在的心理话语;像《爱人同志》这样的以第三人称故事外叙事为叙述主体框架的小说文本,也都是由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和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搭配、组合而成。不过,通常情况下,叙述事象的故事外叙述与叙述心理的故事内叙述是泾渭分明的,两种叙述主体也是并置“现身”的,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往往经由“他想”、“他觉得”等等故事外叙述者的中介声音“转述”出来。《爱人同志》中也不乏这种处理和安排。然而,《爱人同志》中还有一种独特、匠心的设置方式。那就是在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者的情形、场景叙述中直接穿插、引入第一人称故事内叙述者的情思、感受叙述,既没有“他想”之类插入语的衔接,也没有另起段落、运用引号之类的过渡,一气呵成,真正实现了故事内叙述者和故事外叙述者声音的“无缝对接”。例如:
有段日子,他想自学大学课程,他还叫张小影弄了几本大学教科书来,但没看几页就泄了气。因为看书简直不像是在做事,看书是远离人群的劳动,而他目前最大的问题恐怕是需要在人群中。所以,他想到社会上去工作。政府没有想到这一点,甚至连张小影也不知道他的这一需要。她只顾自己出风头,根本不体恤一下我的情感。就连来自社会的信息也要她来传达。刘亚军感到很屈辱,他是个男人啊,现在一切都得靠老婆。①论文所引作品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艾伟著《爱人同志》。
这段文字中,刘亚军(“他”)看大学教科书的经过和“到社会上去工作”的想法,以及“屈辱”的感受,是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者叙述的,刘亚军关于无人知道其需要、无人体恤其情感的心理事实,则是第一人称故事内叙述者(“我”)叙述的。显然,故事内叙述者的心理叙事直接组合、编织进了故事外叙述者的事象叙述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和衔接。在这里,故事内叙述者和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浑然一体、合而为一,显示出不分彼此、你我交融的叙事效果。事实上,在这段文字中,把“他”全部置换成“我”,或者把“我”置换成“他”,对文本没有丝毫影响。这样的叙述声音,表面上是故事内、外叙述者语气、语调、语义的相同,实质上两者是情感、思想、意识的一致,也就是精神心灵的同构。关于这样安排叙述声音的合理性,作家东西曾有过交代:“其实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说话某些时候是连成一片的,你根本用不着强调他说或是他想。”[4]《爱人同志》中经常出现的这种叙事模式,使得作品中具象、客观的场景、情形、事件总是涂抹、浸染上故事人物的心理色泽,从而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二
心理话语在《爱人同志》中不仅占有较大比重,而且也承载着积极的价值。其实,在小说文本中,由于心理话语与人物言语中的独白具有形态和性质上的同一性,故它们在以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为第一叙述层的小说话语中,都属于人物声音或者说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因而常常是被同样对待和处理的。然而,在以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为第一叙述层的小说话语中,故事人物的言语、心理活动,并非只能被故事人物直述出来,而是还能够经由作为“一个置于场景之后的作者的隐含的化身”、“一种自己的优越的替身,一个‘第二自我’”[5](P169)的隐含作者转述出来。也就是说,故事人物的声音其实是可以通过故事外叙述者“发声”加以叙述的。正因为如此,叙述学将叙述人物言语和心灵的话语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三类。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是最为常用的人物语言叙述方式,而且两者总是交互式地出现在小说话语中,以体现出故事内叙述者和故事外叙述者同时而又分别“在场”。《爱人同志》同样如此,其中既运用了大量直接引语,也采纳了大量间接引语叙述人物的口头和心理语言。与此同时,自由间接引语也不时登台、亮相于《爱人同志》的话语现场;不仅如此,经过机智、巧妙地编排、组合,自由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精当化约、恰适交汇,形成了人物语言叙述的有机统一。在这其中,最见机巧的是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的整合、融通。这一人物语言叙述策略,也是造就《爱人同志》故事内叙述声音和故事外叙述声音混融、合一的重要原因。
直接引语用引号直接引用人物语言,所引文字不仅客观记录了故事人物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还忠实呈现了故事人物所说言语寄寓的情感、态度。直接引语是由故事外叙述者援引的,因而引用文字前面一般会有起着交代、承接作用的故事外叙述者语言(例如:“刘亚军不回答张小影的问话,继续挖苦道:‘张委员,你这样来回奔波,我没拖累你吧。’张小影听出话里的话,她有点生气:‘你今天讲话怎么阴阳怪气的。’”中的黑体字,等等),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故事外叙述者对人物说话的情状以及说话内容的情感态度与评价。在间接引语中,人物语言不是由说话者本人表达出来,而是借由其他人转述出来。与直接引语相比,在表面形式上,间接引语没有引号,除了语句中指称说话者和受话者的人称代词发生了转换,如说话者由“我”变成了他(她)、受话者由“你”变成了名字等,更为明显的是说话者所说的言语常常经过了删减、压缩;在内里实质上转述语言不只是扼要阐明了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同时还含纳了转述者对说话者及其所说的话的认知、评价。例如:在“张小影过去把老头叫到一边,问老头那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老头开始不肯说,但后来还是……把刘亚军倒药的事情说了出来”里,“那天说的是什么意思”、“刘亚军倒药的事情”便是对说话人所说的话的概略性叙述,而“老头”、“还是”等语词则展显了转述人物语言的故事外叙述者的情感态度。
在存在上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同时,《爱人同志》还接纳有不少自由间接引语叙述人物语言,尤其是人物心理语言。自由间接引语由于不用引号,因而具有间接引语的外形。另一方面,自由间接引语又是对人物口头或心理语言的如实、客观、直接援引,是说话者声音的直接复制,因而又具有直接引语的质地;然而,自由间接引语的出场不需要说话人之外的叙述者的交代、承转,因此比直接引语显得灵活、自由。自由间接引语在传统小说中并不多见,而在《爱人同志》这样的以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者为第一叙述层的现代小说中较为普遍。《爱人同志》中的自由间接引语的独特之处,也是更富现代性的是:它们不是分割、独立的,而是自然、妥帖地与直接引语、间接引语交织、融汇成一体点缀、镶嵌于文本的言语情境。例如:
这件事也让她反思自己这一年来的行为。她认为她确实也有虚伪的一面。她意识到自己其实同她塑造的公众认为的那个张小影有很大的距离。我是有点儿装模作样的。这都是因为我说了太多冠冕堂皇的话的缘故,那些话比面具更容易隐藏你真实的面目。她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上有人们所说的城府,原来的那张单纯的脸只能到过去的照片里去找了。不过,这怪不得我,我变成这个样子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无法控制我变成这个样子。
在上述文字中,第二句、第三句属于间接引语,而接下来的两句显然就是自由间接引语。紧接着是一句故事外叙述者的情形叙述(其中也有间接引语的意味),然后又是自由间接引语。在这其中,自由间接引语自由、随意地穿插、游走于间接引语、故事外叙述之中,使得整个叙述被张小影(“我”)的叙述裹挟、拖动,流淌、散布其间的都是张小影(“我”)的情感、意绪,从而掩盖、遮蔽了故事外叙述者(间接引语的传述者和情境叙述者)的存在。经过这样的处理,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和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达到了高度吻合和和谐,不仅没有造成语义的障碍和理解的受挫,而且显得流畅、浑圆、通达。与此同时,读者的情思、意念也与张小影取得了一致并由此对张小影此刻产生的自责、反省和辩解产生情感的认同和共鸣。
三
一般来说,在以故事外叙述者为外层叙述框架叙述者的小说文本中,故事外叙述者都是叙述主体,其除了转述(间接引语)和承转(直接引语)人物语言,还是事件、场景、情形、环境等描述性叙事的主要实施者、行使者。不仅如此,故事外叙述者在描述的同时,还常常要对描述对象发出阐释、评价等“叙述干预”的声音。然而,随着叙事观念的更新和叙事实践的推进,于现代小说而言,在外围叙述层下的第二、第三甚至更低的叙述层中,无论是对事件、场景、情形、环境等的描述性叙述,还是对叙述客体的干预性阐释、评价,都可能出现故事人物也就是故事内叙述者的叙述声音。上述叙述技艺在《爱人同志》中有着较为普遍、突出的体现。对许多同类叙事来说,描述事象也好,评析事象也罢,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和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是截然分离的,既分属于不同的叙述层,也显现出未必一致的话语样态,如语气、语词、语调以及相应的情感色彩、价值指向。《爱人同志》与此不同,其中的故事外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者达到了混成和同一,不仅由于相融相汇而没有造成将两类叙述者分割于不同叙述层的感觉,而且也由于语气、语调、语词和情感意绪的一致而使人感觉两类声音是同一“发声系统”发声的结果。
他们说的没错,刘亚军确实在跟踪她。对此她感到不能理解。……张小影尽量把刘亚军照顾得更周到。但刘亚军还是跟踪她。现在,她走在街头时,她的耳朵总是飞向几百米之外的地方。她听到车轮吱吱转动的声音。那声音听来单调无耻固执不近人情。她甚至觉得这会儿刘亚军就像一条随时准备向她攻击的响尾蛇。
如果从人称代词等来看,上段文字属于故事外叙述者对刘亚军追踪张小影的情形和张小影被追踪的感受的描述。然而,从语气、语调和“确实”、“还是”以及“单调无耻固执不近人情”、“向她攻击的响尾蛇”等语词、语象的运用来看,这段话显然又是故事人物作为故事内的叙述者叙说出来的。在这段文字中,如果把“她”、“张小影”置换成“我”,语义和情感色彩不会有任何改变。这说明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达到了完全化合和高度一致。
我就像一只凭本能行事的动物,我很早以前就在为自己的最后归宿做着准备。刘亚军来到黑屋子的角落,那里有一只塑料桶,方形的,扁扁的,上面还有一只像夜壶那样的手柄。他伸手掂了掂那桶。他知道里面放着什么。那是柴油。……这桶东西变得醒目起来,成为我眼里决定我命运的物件。我打开桶盖,深深吸了一口气,我闻到柴油的芬芳。我感到自己热血沸腾,像畅饮了烈酒。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刘亚军发现柴油、打开桶盖的情形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在叙事学上显示了异常明显的叙述“越界”特征。作为一部以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为叙述框架的小说,至少在表征(突出地反映为人称代词)上对于外在事件、情形的叙述应该采用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但是在这段文字中,不仅故事人物刘亚军的心理活动是刘亚军本人(“我”)叙述的,而且故事人物刘亚军看、闻、吸、打开桶盖等行为举止也是由刘亚军本人(“我”)叙述的。与此同时,通过“刘亚军”、“他”等的运用,又表明故事人物刘亚军进屋、掂桶等动作又是由故事外叙述者叙述的。也就是说,这段文字是故事内叙述者和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混置、配备在一起叙述故事人物刘亚军在特定情形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在这里,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与第一人称故事内叙述之间自由组合、随意拼排,没有过渡语、转承语、衔接语。然而,读来不是感到牵强、别扭与突兀、生硬,而是流畅、圆融、自然,原因就在于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同化为了故事内叙述者的声音,两者的叙述姿态、立场和情感、意识整合、通约成了一体。
在小说文本中,阐释和评介文字是普遍存在的。在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为第一叙述层的小说文本中,起着叙事干预作用的阐释、评介既可以由故事外叙述者也可由故事内叙述者完成。通常情况下,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的阐释、评介是相互独立、区隔的,因为它们标识的分别是故事外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者各自的情感意向、价值尺度。在《爱人同志》中,像这样能够对阐释、评价话语的“发声者”给出故事内叙述者和故事外叙述者的指认的情况大量存在。不过,《爱人同志》中也有许多阐释、评介性文字的叙述主体,却难以作出故事外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者的明确、直接定位;也就是说,对于这些阐释、评介而言,其叙述者是故事内叙述者和故事外叙述者的合一、混成。例如:
张小影的这个想法让女记者有点吃惊。这个想法或多或少有点天真幼稚。以现在我们国家的气氛,人们肯定不会再对他们感兴趣了。现在可不是一九八零年。现在,全国人民想人民币都想疯了,谁还会对上一个时代的政治遗民感兴趣。但女记者为了安慰张小影,还是说她会试着写的。
女记者徐卉在时隔多年后探访张小影、刘亚军夫妇,身陷困境的张小影请求徐卉给他们“写一篇报道”以使他们再度“成为新闻人物”。上面这段文字即是对张小影这一要求的评析和议论。仅仅考虑上下文的叙述逻辑、仅仅着眼于没有运用“徐卉(或女记者或她)以为(认为、想道)”等过渡、承接语,这些评论的叙述主体当视为故事外叙述者。但是,结合女记者徐卉当时对张小影夫妇处境的情感态度和感受体认,又不难发现,这评价、议论其实就是出自故事人物女记者徐卉本人,即它们是故事内叙述者叙述的结果。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故事外叙述者(隐含作者)与故事内叙述者(女记者徐卉)对于张小影夫妇的处境遭遇以及造成这种处境遭遇的社会时世怀揣着同样悲悯、愤懑的情感意向,从而显示情态的一致性、心志的同构性,并以此“昭示”既指隐含作者也指作品人物的“生命个体”“在时代的变革和历史的错位之中……的经验与痛楚,欲求与挣扎”这一主题指向,彰显《爱人同志》“触摸到时代与个人、政治与人性之间错综纠葛的小说文本”[6]的审美质地。
[1]吴义勤.符号的悲剧[J].南方文坛,2003(4).
[2][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东西.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灵魂[M].林建法,徐连源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5][美]W·C·布思.小说叙事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刘婧婧.活在虚无与真实之中[J].南方文坛,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