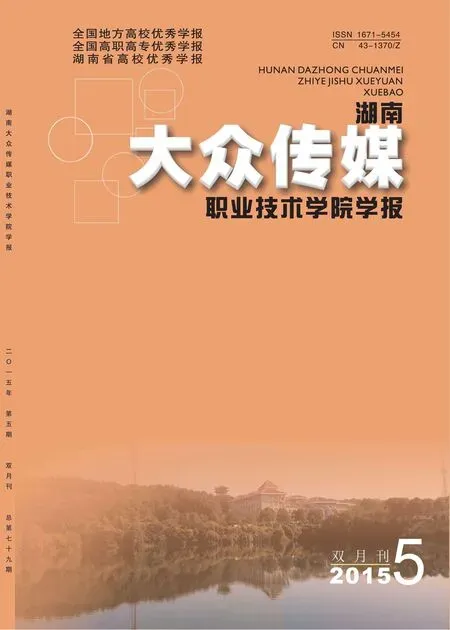许地山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
黄林非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许地山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
黄林非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摘要]许地山具有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其学术研究涉及宗教、文物、语言文字、历史等领域。许地山的宗教研究尤其是道教研究和佛教研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了解许地山的学术研究状况和学术思想,有助于人们深入解读其“复杂难懂”的文学作品并准确把握其“独异”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许地山;学术研究;文学创作
[DOI]10.16261/j.cnki.cn43-1370/z.2015.05.015
一
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学术研究也卓有成就。其文学创作除了为人熟知的小说、散文外,还包括剧本、杂文、童话、诗歌等数十篇。在学术著作方面,有《道教史》(上册)、《达衷集》、《印度文学》、《佛藏子目引得》、《国粹与国学》、《扶箕迷信底研究》等单行本面世;此外,尚有一些民俗学、宗教学及哲学论文未曾入集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许地山学术论著》汇集了许地山的学术著述约30万字,但仍有一些篇目未被收录,稍有遗珠之憾。许地山这位“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以风格独异的小说和散文名世,学界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不过,对许地山学术思想研究似乎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冷门,这与许地山巨大的学术成就很不相称。陈寅恪曾撰文专门论述许地山的学术研究:“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1]放眼中国,能让陈寅恪心悦诚服的学者能有几个?许地山学术水平之高、学术成就之大,似可略见一斑。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地山就已是中国文坛的一员闯将,但是,如果简略梳理其学术背景,即可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1920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又进入该校宗教学院学习并于1922年毕业,获神学学士学位,做过周作人等教授的助教。自1923年开始,许地山先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赴印度瓦拉纳西的印度教大学短期进修。在此期间,许地山获硕士学位,系统地研习过宗教史、宗教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希腊文、梵文、印度哲学等课程。1927年后,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并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师,担任《燕京学报》第一至第十七期的编委。他在燕京大学讲授文学和宗教学,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在清华大学、中山大学讲授人类学。1935年,由胡适引荐,出任香港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从以上经历可知,许地山并非只是一个作家,他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是一位学术视野开阔的有广泛影响的学者。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许地山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宗教、文物、语言文字、历史等四方面内容。
许地山在学术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当属宗教研究,特别是对道教与佛教的研究。他所著的《道教源流考》、《道教思想与道教》、《道教史》、《佛藏子目引得》、《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等篇,称得上是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的思想虽受宗教的影响,但他的宗教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上,采用的研究方法完全是科学的。茅盾曾评论过许地山的《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认为许地山在宗教研究方面,其用心与研究扶箕的迷信是一样的。在该书中,作者从扶箕的起源、箕仙及其降笔、扶箕的心灵学上的解释等角度,对扶箕迷信作了全方位的考证研究,全书引述古代文献中的扶箕故事多达132篇,并运用心理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理论加以阐释。该书指出,占卜是不科学的,它的构成是由于原始的推理的错误。“原始人的推理力和孩童的一样,每把几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络起来,构成对于某事物的一个概念,如打个喷嚏同时又听见鸦啼,就把那两件事来与明日的旅行联络起来,断定在旅途中会遇见不吉利的事情。”因此,占卜也可以被看成交感巫术的一种。[2]131许地山最为人称道的学术成果,应该是《道教史》。该书自1934年出版(商务印书馆)至今已逾80年,但一直被学界重视,今天的相关研究者,几乎没有人能够绕开它。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道教专史,它系统地梳理了道教发生、演变的历史,许地山因此被誉为现代中国道教研究的先驱者。
文物研究方面,颇能体现许地山学术兴趣之广泛。《香港考古述略》对香港附近发现的石器陶器、“广东文物展览会”所展示的一幅照片、新界的几块墓碑等进行考证,并加以推算、推断,从而回答“香港人何时从何处来的”以及“最初来港的汉人姓什么”等问题。《礼俗与民生》区分了“风俗”、“礼仪”、“风化”、“礼俗”等概念,并从考察“生活的象征”、“行为的警告”、“危机的克服”三者的演进入手,来分析礼俗与民生的关系。《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考证一件铜磬上所刻《心经》和《尊胜陀罗尼经》的刻文时代。《清代文考制度》依次考述“学校之设置”、“童生资格与入学”、“入学与入监”、“学校训育原则及待遇”、“考试”等涉及清代文考制度的方方面面,并附有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年间所颁“训士规条”。《猫乘》一篇,旁征博引,从神话、人事与自然三方面来谈猫,文章爬梳使用了大量中西文献,既严谨厚实,又很有意思。
语言文字方面,许地山有《国粹与国学》、《中国文字底命运》、《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较》、《中国文字底将来》、《青年节对青年讲话》等文章传世。许地山反对当时学界的浮夸之风、迷古复古之风,他的一系列关于语言文字的文章,不仅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发人之所未发,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曹聚仁曾评论说,“三十年前,许地山先生在香港大学任文学院长,他病逝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题名《国学与国粹》,刊在香港《大公报》上。我们对于读古书的态度,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曹文引述了许地山的一段文字:“中国学术不进步的原因,文字的障碍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我提出这一点,许多‘国学’大师必定要伸出舌头的。但,稍微用冷静的头脑去思考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国文字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到现在用的,还不是拼音文字,难学难记难速写,想用它来表达思想,非用上几十年工夫不可,读三五年书,简直等于没读过。繁难的文字束缚了思想,限制了读书人的视线,所以中国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曹聚仁在这段文字后面说:“这话说得平实极了。叫年青人读古书,尤其是读四书五经,便是要现代人用两千五百年前的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岂非自己开自己的玩笑?”[3]许地山看到了汉语言文字的改革方向,不仅在理论上做出了多方面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在实践中推动汉语言文字的改革。任职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他曾大刀阔斧地改革原有的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并力倡白话文,一举打破了文言文在当时香港各校中文教学中的垄断地位。
此外,许地山还在历史研究方面下过功夫,且有重要的成果问世。比如他曾编撰服装史,著有论文《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他的《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一书影响更大。该书是许地山留学英国时,受罗家伦之托,从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公文底稿以及旧函件等大量中国史料中摘抄整理而成。这本书被后世之史家反复引用,早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二
许地山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他善于整理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正如任继愈在《道教、因明及其他·序》中所说,“许先生在宗教学、社会学、新文学、考古学的开创之功是永远存在的”。[4]许地山的文学创作深受宗教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影响,这与许地山多年从事宗教学的研究工作不无关系。不妨先看看许地山在道教研究和佛教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
《道教史》是许地山最重要的学术专著。这部书的“绪说”开篇就直接谈“道”这个概念,认为上至老庄思想,下至房中术,都可归入“道”的名下。所以,“道”可分为思想方面的道与宗教方面的道,前者可称为道家,后者即所谓道教。许地山显然很看重道家思想,他指出:古初的道家是讲道理,后来的道教是讲迷信;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道家思想是国民思想的中心。在探讨“道家”与“道教”的区分时,作者先后引用刘勰的《灭惑论》、阮孝绪的《七录》、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张君房的《云笈七签》,分别讨论了刘氏的道家三品说(上品道、中品道与下品道),阮氏所谓方内道与方外道,马氏的清静说、炼养说、服食说和经典科教说,以及张氏将道教分为正真之教、反俗之教和训世之教的观点。许地山认为张君房的分法不尽如人意,训世之教应属儒教。不过,许地山将各种看法悉数罗列,有助于人们通过丰富的史料加深对“道家”与“道教”这两个概念的认识。
事实上,许地山的学术兴趣似乎更偏向“道家”,即“思想方面的道”,而非“道教”。《道教史》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中追溯老子、关尹子、杨子、列子、庄子等“道家”思想的缘起与演变,比较道家最初的静虚派、法治派、阴谋派、全性派的相互关联和不同主张,细致地呈现了“思想方面的道”的各个侧面。除此之外,许地山充分考虑到道教思想渊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他稽考《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深入阐释了道家的“养生”、“阴阳”、“五行”等概念范畴,并用两章的篇幅,分别论述“神仙底信仰与追求”和“巫觋道与杂术”。在对道家的文化源头和思想脉络的考察过程中,许地山着墨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应该是庄子。《道教史》花了较大篇幅考证庄周的事迹、辨析《庄子》三十三篇的作者,更重要的是,许地山深入发掘、阐释了庄子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
许地山说:“假若没有庄子,道家思想也不能成其伟大。”[2]57许地山于诸种宗教文化中,钟情于道家,于老庄杨列中,又注目于庄子。许氏论述庄子思想,头绪较多,其中有三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要点。一是他将庄子的齐物论概括为是非、物我和生死三个根本论点。他解释说,是非之辨,没有客观的标准:天地万物与我本属一体,故万象都包罗在里头,无所谓是非真伪。如果依人间的知识去争辩,那就把道丢失了。在物我的问题上,许地山指出,物我之见乃庸俗人所有。在这点上,庄周标出其真人的理想。所谓真人,便是不用心智去辨别一切的人。论及生死问题,许地山认为爱生恶死乃人之常情,而庄子以为现象界的一切所以现出生死变化,只是时间作怪,在空间上本属一体,无所谓来去,无所谓生死。因此,“真人”不知“说生”,亦不知“恶死”。二是许地山提出了庄子的至人思想的内涵。他认为《齐物论》、《田子方》、《外物》等篇中的“至人”,与儒家的“圣人”有很大的区别,至人没有政治意味,他有超越的心境,不以外物为思想的对象,离开民众而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三是他论析《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七篇,认为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脉络,即是返回本性的道理。而《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骈拇》、《马蹄》、《胠箧》诸篇,皆可作如是观。许地山认为,庄子视人性的本源是从最初的无有无名发展而来的,所以人应当返回那个状态,也就是返其性情而复其初。相比道教研究而言,许地山的佛教研究成果略少,但其学术影响不容忽视。他所主编的工具书《佛藏子目引得》旨在为学者研究佛教文献提供方便。他的相关论文主要有三篇:一是1928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的《陈那以前中观派和瑜伽派之因明》;二是1934年刊载于《大公报》的《观音崇拜之由来》;三是收录于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的《国粹与国学》中的演讲稿《宗教底妇女观——以佛教底态度为主》。
因明学专家郑伟宏曾评价过许地山的《陈那以前中观派和瑜伽派之因明》一文,他认为许地山的论文“依次评介了龙树、圣天(仅有生平)、弥勒、无著、世亲其人其书,理清了陈那以前中观、瑜伽派发展因明的线索,同时发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发表了一些新鲜见解”,并指证了许地山这篇论文的四个方面的主要贡献。郑文认为许地山的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一篇长达六万多字的因明史专论”。[5]许氏仅仅凭借这篇论文,即已在中国佛教因明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观音崇拜之由来》体现出许地山广博的佛教知识和扎实的梵文功底,文章采纳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并联系自己印度之行的切身经历,不仅揭示了“观音”一词的内涵,纠正了一些常见的误解,而且指出了观音崇拜的文化源头和时间起点。文末还列举了多达12种形象各异的观音,其中既有中国的观音,也有日本的观音。作者涉猎之广,搜罗之细,让人叹服。这篇文章篇幅虽小,但学术价值较高。《宗教底妇女观——以佛教底态度为主》主要阐述佛教的女性观,文章征引多部佛经中的相关材料,并参照基督教、印度婆罗门教的典籍,认为佛教对女子多持鄙薄的态度。许地山揭示了佛教给予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一方面考虑到男女的天然差别,另一方面又深究其社会根源。他客观地分析看待宗教的妇女观,认为“宗教没了解女子,乃是在立教时社会没了解女子所致”。他希望新的宗教不要再轻看女子,至少“也要当她做与男子一样底人格,与男子平等和同工底人”。[2]262这篇文章并未对宗教的妇女观提出过火的批判,态度公允,却也可以看出许地山对女性的深切同情。
三
许地山的文学创作受到道家、佛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显然与许地山多年从事宗教研究有关。他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中,就留下了明显的佛家文化印痕。“命命鸟”又叫共命鸟、生生鸟,出自佛经故事,《法华经》、《涅盘经》、《胜天王般若经》、《杂宝藏经》、《阿弥陀经》都有记载。在佛教传说中,这种鸟两头一体,命运与共。用佛经故事中的词语作为小说标题,既让人倍觉神秘,又显得新颖别致。小说女主人公有几句祈祷,也是地地道道的“佛语”:“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诸佛:我自万劫以来,迷失本来智性;因此堕入轮回,成女人身。现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恋天人,致受无量苦楚。愿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碍,转生极乐国土。愿勇猛无畏阿弥陀,俯听恳求,接引我。南无阿弥陀佛。”[6]99可以说,若不是许地山读过大量的佛经,就不可能信手拈来用“命命鸟”作为作品的题目,也不可能写出如此地道的一段佛弟子的祷告来。小说之所以笼罩着浓浓的异域情调和佛教气氛,自然与作者年少时曾漂泊至缅甸仰光有关联,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作者多年研究佛教,已被佛家文化深深浸染。
《空山灵雨》里有一篇作品《香》,写夫妻闲聊:“佛法么?一一色,一一声,一一香,一一味,一一触,一一造作,一一思维,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底爱不是佛法。”“你又矛盾了!这是什么因明?”[7]13作品中,一词一句,皆可见佛教经典的影子。再看《愿》里这几句:“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7]54这段话中,“宝华盖”、“普荫”、“世间”、“诸”、“有情”、“如意净明珠”、“普照”、“金刚杵”、“障碍”、“盂兰盆”、“无量数”、“那由他”等等,全是佛教典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七宝池上底乡思》写亡妻在西天极乐世界思念人间,思念丈夫。在这一作品中,几个关键词如“七宝池”、“弥陀”、“迦陵频伽”等,都是佛经中的语汇,都是有来历的。“弥陀”就是阿弥陀佛,“七宝池”、“迦陵频伽”可见于《阿弥陀经》,前者指极乐国土,后者是极乐国土常出现的奇妙杂色之鸟。还可以看看作品中弥陀的几句话:“善哉,迦陵!你乃能为她说这大因缘!纵然碎世界为微尘,这微尘中也住着无量有情。所以世界不尽,有情不尽;有情不尽,轮回不尽;轮回不尽,济度不尽;济度不尽,乐土乃能显现不尽。”[6]54作品中很多词汇出自佛典,字字句句散发佛光。这样的作品,如若不是对佛学深有研究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许地山谈论创作时,也常常是满口“佛语”。例如,《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一文说:“写出来底文字总要具有‘创作三宝’才能参得文坛底上禅”。他在解释“三宝”时又说:“创作底三宝不是佛、法、僧,乃是与佛、法、僧同一范畴底智慧、人生和美丽。”解释“四依”时,则引用佛教古德的话:“心如工画师,善画诸世间。”然后,他干脆借“佛家底四依”来谈文学批评之道:“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7]297这是谈论文学,还是谈论佛学呢?在许地山这里,文学和佛学已然融为一体。
道家文化对许地山创作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已不止于语汇和意象的借用。许地山在道家思想研究方面的学术观点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读者如果明白了此中奥秘,对照许氏的学术思想去解析其诸多“复杂难懂”的作品,会有贴心润肺般的到位之感。
如前所述,许地山对庄子的思想深有研究而且十分推崇,其文学创作也常常能体现他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和认同。例如,《暾将出兮东方》一文写道:“本来,黑暗是不足诅咒,光明是毋须赞美的。光明不能增益你什么,黑暗不能妨害你什么,你以何因缘而生出差别心来?若说要赞美的话,在早晨就该赞美早晨;在日中就该赞美日中;在黄昏就该赞美黄昏;在长夜就该赞美长夜;在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就该赞美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说到诅咒,亦复如是。”[6]40文章消解了常人惯有的“差别心”,提倡以庄子式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不齐,泯灭生活的差等。这段话简直可以看作许地山对庄子齐物论的阐释和评价。他认同庄子的看法,认为人可以通过齐生死、等是非、泯物我、一成毁,来获得内心的愉悦自由,在不一样的人生境遇中搭起一样的逍遥殿堂。《愚妇人》借樵夫的歌唱说出了庄子“方生方死”的观点,《山响》、《黄昏后》等作品则是对庄子生死观的形象化表述:生不足喜,死不足惧,死亡不过是人顺应自然、与时俱化的归本归真。
(责任编辑远扬)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316.
[2]许地山. 许地山学术论著[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3]曹聚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M]. 北京:三联书店,2012: 261.
[4]许地山. 道教、因明及其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
[5]郑伟宏. 佛家逻辑通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69.
[6]许地山. 许地山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许地山. 人生空山灵雨[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454(2015)05-0058-05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资助科研课题“许地山的学术思想与文学创作”(编号:14YJ07)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林非(1972-),男,湖南湘阴人,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