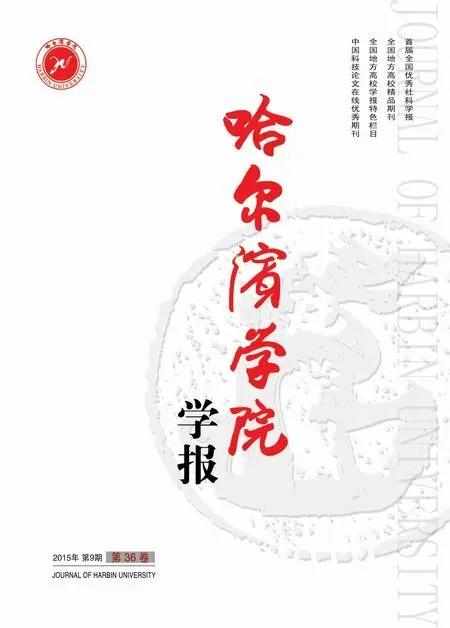对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探究
朱建芳
(福州大学法学院,福建福州 3 50108)
一、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的本质揭示
“不可抗力”是来源于《法国民法典》的一个法律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可抗力的范围也有所变化。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相关法律都将不可抗力界定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事实或社会现象”。同样,在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以及环境保护法规中也都将“不可抗力”界定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但是,不可抗力这一传统的定义并不能将其所涵盖的对象与范围阐释清楚,笔者认为还应探讨如下问题:
其一,采用何种判断标准来界定“不可抗力”内涵中“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才最能够体现立法者的立法旨意。根据对不可抗力的判断依据的不同,学界形成了主观说、客观说与折衷说三种观点。主观说仅从主观角度来评判,认为应当以侵权行为人的预见能力与防御能力来判断不可抗力是否能够预见,若侵权行为人已经在主观上尽了最大的注意义务,仍然不能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就是不可抗力。客观说不关注人的主观性,它认为不可抗力中的不能预见与不能避免是一种与人的主观意志无关的,客观的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无法控制的客观事实。但是,由于单个人的力量及其薄弱,绝大多数的自然现象与社会事件都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因此“一般人无法抵御”等限定性术语在客观说中被用以界定不可抗力,由此可见,客观说并不单纯的以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为要旨,将客观现象与“一般人”“理性人”的防范风险能力相联系,这就形成了折衷说。主观说,以人的主观状态为衡量标准,个体差异极大会造成一千个人一千个标准的无标准状态还会赋予法官超乎寻常的自由裁量权;而客观说则完全忽视行为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性,用同一僵硬的客观标准来量化责任,这也会导致一些专业技能或者经验丰富的行为人借此逃避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折衷说更为合理,折衷说对客观现象的判断原则是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而较高的特殊标准适用于例外情况。可见,折衷说既克服了主观说的过度差异无标准又弥补了客观说的僵硬性,不仅为法官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裁判规则,而且具有适度的灵活性保证了具体环境侵权案件结果的公平性。这与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初衷相契合。
其二,传统理论将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排除在“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的客体之外,其所定义的客体仅限于客观现象本身。笔者认为,环境污染损害中不可抗力的客体不应局限于客观现象本身,因为不可抗力不是自然学科上的概念,而是具有一定目的取向的动态的法律概念,其概念的界定必然关涉到人类生活,否则难以体现不可抗力在环境污染损害中保护环境受害者利益的目的性。如沙尘暴本身与法律无任何关系,只有当风沙弥漫湮没村庄导致他人损害时,才有必要讨论沙尘暴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由此,不可抗力在实践中作为法定抗辩事由的必要性之一就在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现象关涉到人的有价值的行为,特别是由客观现象造成的损害是关涉到侵权行为人的作为与不作为。可见,纯粹的客观事实并无法律价值,只有将客观事实对人类造成损害的评价纳入进来,不可抗力在环境侵权中作为免责事由才具有法律意义。
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需要秉持其内涵中的三个必备要素。第一,“不能预见”,它包括了人类在现有的认知水平下根本无法预知到,也包括了人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预见但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预见不可抗力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具体性、延续时间的长短以及影响范围的深广等。原则上“不能预见”是在现有技术水平基础上,以一般或者同行业或类似行业的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来判断;但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环境侵权行为人的预见能力高于一般人的预见能力,则应以行为人较高的预见能力为标准来判断。第二,“不能避免”,是指侵权行为人在事后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仍不能防止结果的发生。第三,“不能克服”,它是指损害结果的发生是人类能力所无法控制的,也就是在不可抗力发生之后,即使侵权行为人迅速采取了合理措施也无法阻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但是,一律要求不可抗力不能或缺上述三项要素任何之一,很容易出现结果不公的情形;因为在很多情形下即便环境侵权人能够预见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也没能够阻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在环境侵权中,针对那些侵权人行为人能够预见到但是无法防止结果发生的客观情况也可认定为不可抗力。特别是,不可抗力在具体的案件中,需要用利益衡量规则来甄定不可抗力是否构成免责事由,才能体现这一法律概念的旨意。
二、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的原因分析
(一)无法预见性
无法预见性是指人们无法及时、准确预见客观现象造成的损害结果。无法预见分为完全无法预见和无法准确预见。完全无法预见,如非洲的埃博拉热带病毒、广州的登革热、海啸、地震等;无法准确预见,要结合个案中不可抗力构成要件进行综合性的评定,比如在地震多发区,就应该在建造房屋时考虑到房屋的抗震等级,低级地震引发的房屋倒塌就不能完全用无法预见来对抗。由此可见,无法预见性还要求行为人即便是预见了也无法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这与刑法中“欲而不能”不归罪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无法避免性
无法避免性是指环境侵权行为人已经对不可抗力进行了有效的预知,并且采取了相应合理的措施,但是损害结果并不因采取了合理措施而减少或不发生。有的学者采取较高的行为标准,认为无法避免是侵权行为人在尽了最大的努力、采取了一切可采取的措施之后仍然不能避免灾难性的结果发生,这样的标准显然是对行为人过于严苛。虽说事实上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建造抗震等级极强的房屋和具有牢固防御功能的大坝可以对抗剧烈地震引起的房屋倒塌以及千年一遇的洪水引起的堤坝决堤,但是这样高质量高标准的规定并不符合我国当代的国情,而且如此巨大的耗资也不是任何一个开发商都能承受的了。
(三)客观事实性
客观事实性是不可抗力区别于行为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可抗力应是独立于人的意志外的客观现象。强调不可抗力的客观事实性,就在于不可抗力发生的客观事实切断了行为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不可抗力成为免责事由的主张得以成立。
三、对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的探究
将不可抗力有条件的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是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并经侵权行为人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环境污染侵害的发生,侵权行为人免于承担责任”,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海洋污染防治法》中都有相类似的规定。从这些规定看,对不可抗力的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定,仅将其限定在“自然灾害”中,而作为社会现象的战争、罢工以及重大政策调整等仅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作了些许规定。环境侵权损害中的侵权行为人依据的不可抗力免责还必须苛以一定条件:一是除了不可抗力致害外不允许有其他因素参与,如若不符合“完全”由不可抗力所致,则是不能免责的;二是若环境侵权行为人欲寻求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就必须证明其在不可抗力发生之后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否则,行为人是不能够免责。实际上,法律也有将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标准降低的例外规定,采用的是单个标准即只要是完全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害就能免责。最为典型的例外规定就体现在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只要是由于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水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环境污染排放者就豁免了赔偿责任,这里的例外规定就没有要求侵权行为人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结果的发生,把不可抗力的双层标准降低为单个标准,标准的下放其作为免责事由的范围自然也就扩大了。
在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将战争行为这一人为灾害有条件的规定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也就是完全是由战争的爆发而引起的,环境侵权行为人也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结果依旧不能够防止战争行为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损害的,那么环境侵权行为人就豁免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美国的有关法律将战争行为规定为免责事由中的不可抗力,是可以豁免责任的一种意外事故。战争作为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美国有关法律也对其进行了严格界定,即需要行为人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人不能避免环境损害结果的产生才能够免责。
对于不可抗力能否作为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争论从未间断过,学界主要有三种学说,分别是肯定的观点、否定的观点以及折衷的观点。否定说无一例外将不可抗力排除在环境侵权免责事由之外;折衷说是以一般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发生了不可抗力。持肯定观点的学者注重不可抗力的客观事实在侵权行为人与环境损害结果之间所起的作用。传统上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换句话说,也就是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与具体环境侵权案件中免责事由的依据无关,过错与否已经排除在免责事由的原因之外。一般情形下,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因果关系,但是不可抗力的发生就像一把利剑将两者的的因果关系切断了。其次,根据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决定了有些环境侵权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是必要的,如若对生产者苛以繁重的义务则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笔者认为,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是需要具有一定条件的,一律不分具体情况将其作为免责事由有失偏颇,理由如下:
首先,不可抗力发生并造成损害结果时,虽然侵权行为人和受害方主观上均无过错,根据肯定说的观点,侵权行为人免责了,但是受损害的一方的损失难道就无从救济吗?在某些发达国家,国家承担着因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受害方的损失。在我国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环境侵权中受害方的损失完全由国家来承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若将受害方的补偿置之不理,一味地寻求环境侵权人在不可抗力环境侵权案件中的责任豁免,而让环境侵权受害人承担环境保护侵权损害的后果,这不仅不符合现代民法追寻的“实质公平”的精神,也不符合现代侵权法中“日益保护受害人利益”的意旨。
其次,在适用高度危险责任归责原则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因发生不可抗力而造成环境污染侵害时,环境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很难说是没有因果关系。正如,拥有剧毒物质的企业在不可抗力发生时导致有毒物质的泄露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一方面不可否认不可抗力是造成环境损害结果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就能够无视污染企业中存在的剧毒物质与环境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吗?显然不能。因为没有企业有毒物质的存在就没有环境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就无所谓环境侵权。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时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这里“高度危险作业”的规定就排除了“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通过分析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可知,某些高度危险环境侵权属于危险责任,而危险责任的理念初衷苛以环境侵权行为人以更高的注意义务。虽然不可抗力的发生切断了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并且也不能从字面上表明侵权行为人具有过错的主观状态,但损害结果在实际层面又与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和物件有关联,如若完全免除侵权行为人的责任,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方得不到合理的补偿,这也就不符合环境侵权中危险责任原则的立法旨意。在“高度危险作业”中,环境侵权人通常已经投了保险,发生环境污染侵权事件时,由侵权行为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是环境危险责任的应有之意,在这个层面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就明显不公平。既然在有些环境污染侵害中,排除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是具有合理性的,那么,能不能根据各种污染物质导致环境污染侵害只是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导致的,进而把环境污染侵害的事实进行一般化,将不可抗力排除在环境侵害的免责事由之外。
最后,若非得将“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对“不可抗力”苛以严格的限定解释是应当并且是必要的。第一,是否发生了属于免责事由的不可抗力,应该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权威机构来认定。是否属于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不可抗力需要具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标准。第二,对不可抗力中“不能预见”的评判标准应当是一般理性人的标准,因为环境侵权行为人自身情况各不相同,若以当事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势必会造成司法不公。再者,作为免责事由中不可抗力的“不能避免不能克服”,除了环境侵权人在不可抗力发生之后及时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之外,还需环境侵权行为人在环境污染侵害之前也采取了合理的措施,而事前预防也是环境法所注重的一个理论趋向。第三,理论上,“及时”与“合理”本身就是一个外延相对模糊的词,但是法律的可预测性要求相关法律法规对“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中“及时”与“合理”作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四、应对“不可抗力”的解释加以严格限制
第一,对“不可避免及不能克服”这两要素需严格把关。若当事人以不可抗力为免责事由,环境侵权人不仅需要对不可抗力进行了有效的预见,而且还需要在不可抗力发生之前以及不可抗力发生之后确实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来防止损害的的发生和扩大;第二,如果环境侵权人在事前对“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情形有所预见,却仍然为己私利铤而走险从事经营活动,则“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不能成立;第三,国家应对企业配备的先进的净化设备和防护措施规定一个技术标准,以便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如未采取或未完全采取,视为过失,则不能免责或不完全免责,对于可预防而未预防所带来的扩散的损害仍然需要承担责任。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不可抗力并不当然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其成立免责的条件是环境侵权行为人有证据证明:其在不可抗力发生之前以及不可抗力发生之后均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防止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无法证明自己在事前以及事后采取了合理措施是不能够免责的。对采取合理措施时间上的双层限定以及对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免责事由的严格解释,无不体现法律解释的慎重与可行性。这样就会苛以环境侵权人较高的注意义务,这已经部分地反映了无过错归责适用不可抗力的精髓,适用不可抗力的大前提应当是行为人于主观上的善意,之后才是个案的责任平衡,视不可抗力的影响因子而予以部分减责,而非不加区别地适用不可抗力以免责。
[1]刘凯湘,张海峡.论不可抗力[J].法学研究,2000,(6).
[2]李显冬.侵权责任法经典案例释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叶林.论不可抗力制度[J].北方法学,2007,(5).
[4]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5]周友军.地震中工作物致害的侵权法救济[J].社会科学战线,2008,(9).
[6]梁清.地震作为不可抗力免除民事责任的原因力规则适用[J].政治与法律,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