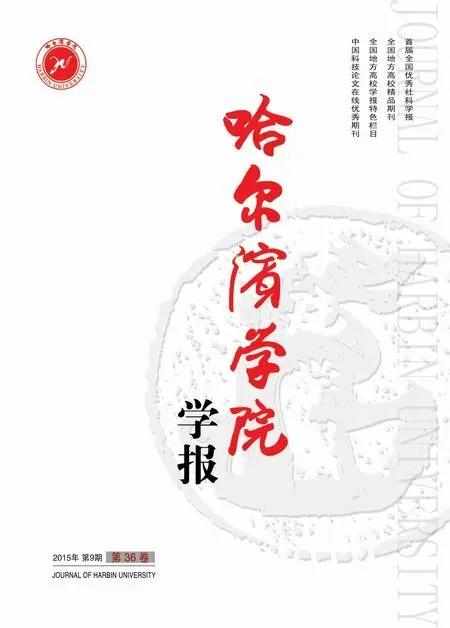福柯论疯狂的“自身”与宗教神秘
张建军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福柯论疯狂的“自身”与宗教神秘
张建军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 商洛726000)
[摘要]疯狂不只是一种生理疾病现象,更是一种文明时代的历史社会产物。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进行发掘,指出疯狂现象是个体人“自身”存在的可能性表述,没有被历史的、社会的、理性的整体概念所淹没的体验式表达;与宗教神秘的疯人船原型意象、死亡与虚无、疯狂寓言、恶德、神秘体验等之间有一种共同的体验或者被表述的关系,这种被宗教所描述和认知的疯狂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还是把其归为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也就是被理性启蒙所否定。
[关键词]福柯;疯狂;可能性表述;宗教神秘
疯狂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福柯用“疯狂”的历史阐述人自身对知识、理性与主体所抱有的质疑和清洗态度,在疯狂“真实的历史”中展示人自身的存在。人不是理性规约下的整体状态,而是处于非理性状态的独立个体。福柯震撼于尼采的疯狂启示,深切感受到“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他这个样子的”(《看,这个人》副标题)。说到底“我们的肉体不过是一种社会结构”,自我的观念是文化生产力和生理展布变动的产物。“必须支持根本不可信的事情”,这是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的“另一种形式的疯狂”。“自我”的表现是主体,福柯认为,这是在进行“自我消解”。[1]这是一个漫长的寻找摆脱主体纠扰的呈现人本身样态的“他者”的过程,“他者”的意义是对自我的找寻和对自身的关怀。于是,“他者”无形中就成了是对自我或者非理性的一种理性表达。
《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就是在寻找非理性的本身存在。寻求人自身的生成,这是福柯“处于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阳光之下”《古典时代疯狂史》的核心思想。从关怀自身的角度,非理性既是一个贯穿全体文化现象的综合理解线索,又是一个解释性的图式。非理性虽然是理性之对立、理性之负面,理性借其排除而自我确立,但非理性对于疯狂的参考坐标理解是深刻的,甚至完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于人类的共同潜能,每个社会都会加以选择,而疾病便是这个社会所忽略或压抑的人类潜能。疯狂这样一个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不完全确定的疾病更是人类潜能的重要挖掘点,却被历史、文化、科学、理性等重重包围,已经看不到庐山真面目了。所以在此意义上疯狂问题的提出,或者“去除包裹”的过程就是福柯对人自身的认知和关怀。“为了找到一个比我们自身更为伟大的存在方式,他决意回归到理性和非理性都淆然一体的状态……他深入到了我们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核心。”[2](P53)
一、疯狂是人“自身”的可能性表述
美国后殖民理论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从“属下”相对于社会精英中心话语权缺失的情况,强调属下“不能说话”的特征,也不存在话语体系。但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一开始中却用荒诞方法表述两个人的存在。爱斯特拉冈说:“我们生来就是疯子。有的人始终是疯子”。弗拉基米尔对:“可是在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一时刻,全人类就是咱们”。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的言语式对话道出:世界的本身是荒诞,荒诞的本质是疯狂。正是这种疯言疯语、荒诞行为表明了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之辈的存在,荒诞或者疯狂也是他们的最真实状态,也就是说,这是他们所有的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在脱离理性压抑下,疯狂中潜藏着他们“自身”的可能性表达。
福柯在《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没有对疯狂进行明确的定义,但这不等于疯狂就不能被表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疯狂是生理疾病、人性缺失、精神紊乱、自我外露、大智若愚、道德悖反等等一切可能的表述。每一种定性的表述都是对疯狂性质那时那处的一种立即性显示,而此时此处可能就不是那种状态或者性质的表述。具有片面性和片段性的危险,这也是从主体和理性视角出发对疯狂的一种想象性分析。从本质上,疯狂是对人本身可能性存在的偶然显现。相对于理性,疯狂就像是具有流动性精神的物质存在,流动性的精神和非理性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所以福柯在《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用疯狂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来表述疯狂的存在及意义,但绝不是非理性。这是社会存在中宗教因素的翻版,非理性是在理性对立面的基础上的存在和言说,所以理性对非理性的把握就必然成为对疯狂的定性或者属性的研究。福柯并没有明确疯狂就是非理性,但理性确信疯狂的本质就是非理性。其实,疯狂具有宗教神秘性及其所表达的不可认知性。上帝在人心目中是人对人自身一种神圣性的表示,人们从不想着上帝是什么、上帝什么样,就是但丁的《神曲·天堂》也把上帝模糊化,把天堂知识化,或者理性化,因为是人的理性和知识认识了星体的存在;魔鬼就是撒旦,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显现,这也许就是疯狂。这是人对自身的与神相对的一种认识。上帝存在是对人类超越性的体现,魔鬼和撒旦是人对自身神秘性的显现。神圣性和神秘性都是人对自身的一种可能超越个体之外的想象。神圣性是个体之外的外,神秘性是个体之内的外。福柯着重强调的是疯狂的“外界思想”。
“凡事都是有必然性的,尽管这种经验涉及走向‘自己的外界’,但是在这种情况的最终实现仍然是为了找到自己,是为了在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内在性中自我缠绕和聚集,而这种内在性恰好就是存在与言谈。换句话说,就是话语,即便它是超越所有语言的沉默,超越所有存在的虚无。”[3]话语与存在是表达具有生存美学思想“外界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萨德侯爵的反复独白就是外界思想的第一次话语暴露。这是,人们“把疯狂当作语言场域中的一项体验,当作人面对其道德真相的一项体验,当作是人面对属于他本质和真相的内部规则时,所产生的一项体验。简而言之,疯狂的批判意识不断被摆在明亮处,而它的悲剧性形象却逐渐步入暗影。不久以后,这些形象将会完全消隐。”[4](P43)因为疯狂进入了论述的世界,成为主体和理性的客观对象,论述的世界“下”最后结论,永远不是真理和世界的结论,是透过论述来为自己辩护,并且论述完全来自理性的批判意识。谈论疯癫,不把他驱逐到客观性之中就得让它自行言说。疯癫以其本质而言就是不可言说的。福柯深刻地指出疯狂是‘作品的不在场’。人们为它编织的桂冠反而套住了它,疯狂的宇宙性和悲剧性体验被批判意识和论述的世界独享的特权遮盖住。正如贝宁顿在分析福柯基础上的简单表达:“一旦我思变成了语言,他就在构成自身时成了排斥疯癫的作品”。[2](P59)但论述无法达到完全对疯狂的化约。在主体压制的终极点,疯狂爆裂就成为必然。疯狂是永远不在,存于一个永久的隐退之中,疯人临在的各种独特类别,清晰可见。所以对于疯狂的认识,只能是描述式的再现或者是萨德侯爵式的反复独白。
福柯认为,对于生存美学思想的疯狂认知也是极限体验及描述式的反影。德勒兹曾经说过:“为了认清‘自己’,一个人必须‘向各种多样性开放自己让这些多样性从头到脚贯穿自己全身’,经受‘非自我化方面的最严格的训练’。”[5]疯狂为什么就不可能是“自己”,认清了“自己”也就知道了疯狂。疯狂是“自己”的表现,“自己”是对疯狂的本质。“我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我的以及我为何要为做现在这个人而受苦受难?”这是福柯对自己的质问,也是疯狂对人自身的拷问,所以疯狂从本质上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是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中对人自身的关怀。但是,现在整个问题的趋势都转向了对“他者”的认识,“他者”是对疯狂的导引,但疯狂却不是“他者”。疯狂是开放的、多样的、体验的,而“他者”是封闭的、单一的、表述的。
体验(或经验)一词意义含糊,福柯对其下的一个简单定义是:一种“能够而且必须被思考”的存有形式,一种经由“真理游戏”被“历史性的确立了的”形式。但是体验预设着主体,在《性经验史》里,体验被明确定义为:“一个文化中,知识诸领域,规范诸形态和主体性形式之间的关联。”我们这里谈的是极限体验,是把身心推向断裂点的个人极端体验。“真理游戏”则是“通过这些断定何者为真、何者为伪的游戏,存有在历史中被建构为体验,也就是说,(存有)成为能够而且必须被思考的事物(体验)。”[4](P47)疯狂在历史中被建构为体验,成为我们思考的事物,并不是由于体验的主体性,而是由于疯狂自身的作为极限体验的身心断裂点,或者说疯狂与极限体验之间的同构性。福柯承认说,即使从某种具有个人转换功能的“极限体验”出发,也“有必要开启通向某种转换、某种变形的道路。这就不只是个人的事了,它势必牵涉到他人”。由于这一原因,他总是力图用某种方式把自己的全部体验,“同一种集体的习惯、一种思维方式”连接起来。[6](P29)所以我们从福柯的极限体验来理解疯狂的生存美学思想,也许就是最准确地在抛离主体和理性后的疯狂本身中对人自身的关怀。
鸦片“能使人产生一种轻飘飘的停滞感,蝴蝶翩翩般的心醉神迷”,这就是对疯狂的身体脱离理性或者心灵脱离感知的通感状态的表述,即麻醉品是一种思想的工具。福柯在服用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迷幻剂)后产生特殊效果:“它一解除范畴的宗主权,就挖去了它的中性的根基,并抹去了无言动物性的那幅愁苦嘴脸;它不仅把这一大块单一的、无范畴的动物性表现为杂色斑驳的、流动的、不对称的、无中心的、螺旋似的和交混回响的东西,而且促使它时时刻刻地涌现为一对乱哄哄的幻觉事件。”[6](P344)疯狂也就是人在脱离理性状态下的极限体验。因为生存是人在世界整体性的脱离,死亡是人对世界整体性的回归,所以疯狂就成为人在生存状态下的对世界整体性的通感性把握。
疯狂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为主体性和理性原则所规约,而单纯是人自身的表现。疯狂作为人自身,在未同他人和他物发生关系之前,在本质上是一种“缺席”,“缺席”就是人自身的生存美学存在。福柯的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就在于对生命本质的显示:生命“时时刻刻面临可能性,时时刻刻同‘过度’、‘极限’、‘冒险’和‘逾越’相遭遇;生存之美,恰恰就在逾越中闪烁出它的耀眼光辉。”[7]疯狂完美的体现了生命的各种可能性,过度、极限、冒险和逾越。“也就是说,这里谈的问题一点也不是知识的历史,而是一种体验的初步运行。这不是精神医疗的历史,而是疯狂本身的历史,是活泼泼的疯狂,在被知识捕捉前的疯狂。因此,我们必须支起耳朵,倾身去听世界的喃喃低语,努力去察觉那许多从未成为诗篇的形象。”[8]所以,疯狂的肯定性表现就是一种对人自身的精神层面的关怀。“正是因为疯狂是非理性,在疯狂身上找到一个合理的掌握点,总是可能而且必要的。”[4](P352)要认知疯狂,可以从宗教神秘和文学实现中找出福柯生存美学渗出的人对自身的关怀。
二、从宗教神秘认知疯狂“自身”
“人们认为,人的具有自身独特特征的一切都来自外部:从时间上讲,它来自遥远的古代;从空间上讲,他降自最高远的穹顶。在我们成形而成为某种存在之前,我们属于某种东西,正如婴儿的世界中已经有了父母的秩序,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投射权威的形象或者时空里的先后次序,其俯仰愿望之链条一直延伸回溯到上帝那里。”[9]疯狂作为人自身一种我们不太熟识的属性,或者被文化、社会、科学等厚厚地裹缠之后,失去人对自身的认知可能之时,更应该在宗教神秘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关联影响及其源起。福柯不赞成康德的历史源起说,主要是反对启蒙观所形成的历史连续性,因为在启蒙运动理性架构的敲诈下,疯狂被变成了“他者”的历史。他者的历史的源头在被认定为麻风病时,其实已经指定了疯狂和宗教之间在世俗层面上的渊源和定性关系。我们对于疯狂的精神关怀就是想通过宗教神秘维度来认识疯狂的不确定性或者可能性。神秘、非理性和疯狂之间的关系就是人自身在理性状态下的未知维度,所以,对疯狂的认知就是对人的本身人性的肯定。
疯狂与麻风病具有明显连带关系的划分、排拒、净化的反应,并不是麻风病的真正遗产。在中世纪末期,麻风病怪异地消失于西方世界。疯狂只是继承了麻风病在西方世界的他者地位,但人们普遍误解疯狂是在麻风病消失的时刻出现于西方世界的地平线,两者之间是一种承继关系。疯狂的形象最早大量出现于宗教经典著作之中,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人文主义之后降低为道德意识。“上帝死了”的宣言必然会导致“人之死”的可能,为把疯狂的神秘性变成他者性创造了历史条件。麻风病明显的生理疾病特征和附加的宗教拯救色彩,完全不同于疯狂外在的神志无序状态下到底是生理病变还是一条神秘的通灵密道,两者之间不同特征的宗教神秘色彩并不决定他们之间的产生早晚。事实上,疯狂的划分、排拒和净化的程序是宗教给与的,不是麻风病的遗风再现。人在寻回子宫的一瞬间是人对自身的认识,疯狂找回其宗教的源起并不是为了正统性,而是宗教的模糊中所可能表达的疯狂意义。在认识疯狂的宗教神秘之时,也是人对表现出疯狂状态的人的认知和自身关怀。
三、原型意象:疯人船
疯人船是文学艺术传奇性和讽刺性之下的历史事实,也象征了中世纪末期突然出现在欧洲文化地平线上的人性焦虑,博斯的绘画作品《愚人船》映照了这一堕落。“桅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传说中伊甸园的智慧树,人走出伊甸园是对人本身的恢复。所以,疯人船由商人和朝圣者团体将这些无理智货物驱逐城市墙外和运载他乡,并不单单是社会效应和市民安全的单一层次考虑。在仪式性划分、不确定性和意识中的堡垒的综合作用下,表面的朝圣和排他之旅却可成为去圣和人性找回之途。因为游离本身就是对人自身的重新认识和思考。
在整个文艺复兴初期,朝圣地这类地点往往是疯人集结的大本营,“这些经常在想象中纠缠不去的疯人船,有可能便是朝圣之船,有可能便是无理智者为了寻找其理性所乘坐的高度象征性船舶”。[4](P15)虽然为数相当可观的疯子们也有可能被船员和商人“抛失”在旅行和市集的重镇,这样他们原出生地的城市便可得到净化,这些地方可能是一些“反朝圣”的地点。但是“到了后来,就跟无理智者们以朝圣者身份被带往的地点混淆起来。治愈和排拒的心愿混在一起;禁闭在发生过奇迹的圣地里施行。朝圣地变成了围地,变成了疯狂等待解脱的圣地。但在此,人们其实是依循一些古老的主题,操作一项仪式性的划分。”[4](P16)这是古老的宗教主题在疯狂中的重新演绎:“抛失”“净化”“朝圣”“反朝圣”“划分”“解脱”,等等。这些划分是宗教在西方世界潜意识中的无形影响。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疯人的离城和其他仪式性放逐之间具有关联。仪式性划分本意在于对疯狂的放逐过程中得到净化,但是疯狂恰恰是在放逐的距离之外得到人对本身的净化。
水能带人远离,还能净化。因此水流和航行就扮演将疯狂寄托在外于其一切的重大不确定性之中的可能。水流所支撑的“航行把人交付给命运中的不确定性。每个人在此都被付托给自己的宿命——每次上船导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当疯子坐上疯狂的小船离开时,他是朝向另一个世界驶去;当他下了船,他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4](P17)净化只是一种想象,疯狂在此被带入了不确定性的怪圈。这是用不确定性的空间意识逐步导致疯狂在自觉中自我意识的不确定性,也即疯狂能够在这样的惩罚中认识到自我的不定状态。对于疯人,“自我”意识确立就是对出身、故乡的记忆和思考。事实是,他们“是来自海洋没完没了的动荡不安,来自它那藏匿许多奇怪知识,为人所未知的路途,来自那奇幻的平原,世界的反面。”[4](P19)并且永远不能将之据为己有。不确定性是一种宗教性的持续惩罚,也是深入灵魂深处的一种矛盾纠结。
“疯人的航行,既是严格的划分,同时亦是绝对的国度。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航行只是在一个半真实半想象的地理之中,展现了中世纪人对疯子门槛处境的焦虑——他们的处境,同时既是象征的,亦是实现的,因为它拥有被监禁在城门的特权:他为人排拒的情况乃是一种圈围;如果说他的监狱只能是,而且只应该是门槛本身,它却是被拘留在旅途的过渡站里。”[4](P18)疯人被人置于外部的内部里,内部的外部里。这个过渡站就是具有高度象征性姿态的“意识中的城堡”。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水和航行是最自由的环境,最开放的路途。这种过客中的过客,“外部的内部里,内部的外部里”就是在强调他们身份的过渡性质。如果用但丁的三界来界定,那就是炼狱。也就是人处于一种边缘情境中,更加有利于人对自身的思考和质问。
四、死亡与虚无
剥除血肉的临在成为人类终结、时间终结的形象,死亡存在于人类世界的内部,但又威胁着个体人的肌理。死亡严肃性焦虑在疯狂的嘲讽中得到重新思考和定位。疯狂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代表断裂,是同一焦虑的内部扭曲,是在把人类整体的视野换成个体人的角度来看死亡问题。死亡本身的严肃性不利于对其进行深层面的思考。“在死亡这个绝对大限面前的恐惧感,如今被内化为一种连续性的反讽,恐惧被预先解除了。被化为可笑的事物,因为人们给了恐惧一种日常可见和为人成功控制的形式——他把它放在生活的场景之中,时时刻刻加以更新,又把它撒散在每个人的恶德、怪癖、滑稽之中。”[4](P24)在死亡的意义上,生命中的噪音、固执、喧哗、空话、妄自尊大等就是另一种疯狂,带有恶德、怪癖、滑稽的隐性特征。所以疯狂就是对死亡在空间中的具化和时间上的提前。疯狂是死亡被征服的临现,用日常可见的征兆来避闪死亡的来临。“疯人之笑的特点,就是他抢先一步,笑出了死神之笑。如此,无理智者在他预兆死神的同时,也消除了死神的力量。”[4](P24)死亡对人自身的思考带有虚无的特征,疯狂则是实实在在的临在思考。
福柯认为空无是外在的终点,存在之虚无是威胁也是结论,疯狂就扮演了由结论到终点的过程。由内在为人所感受的疯狂,是既连续又持久的存在形式。过去,“人们的疯狂,乃是不知死亡大限正在迫近,所以要以演出死亡场景来唤醒他们,使其回到智慧;如今,智慧就是说出疯狂处处存在这个真相,教导人们明白,他们现在的状况,比起死亡高明不了多少,并教人了解,如果说大限已经不远,那是因为普遍的疯狂和死亡本身其实是一回事。”[4](P25)疯狂失去在虚无面前的优越性:疯狂并没有比死亡高超什么。疯狂和死亡之间在形式上是一种存在和陨灭的差异状态,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内在就不存在相似性和共通性,疯狂可能是死亡的先导,内在相似最终演变成形式相同。过去死亡只是一个瞬间,但是疯狂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渐变的过程,疯狂是一种恐惧的死亡等待过程。疯狂是不声不响的入侵,说明世界正濒临其最后劫难,也正是那些疯人的狂呼大叫在呼唤大难,使其灾难成为必然结果。所以,疯狂在人精神的消亡和死亡本身人的形神俱灭之间只是一步之遥,这是人对死亡的过程分解。
五、疯狂寓言
疯狂形象在事实层面上是单一的,在语言意象和造型言论的世界却存在着多重意义。疯狂主题上严格的连续性往往是虚假的表现,在历史过程或者这一形象丰富的连续中必然存在某一裂隙,渗出或混入某种完全不同方向的主题,使疯狂失去本来的人的本身特色。所以疯狂就是寓言本身事实和结构的陈述,至于后来的意义都是某一社会群体的理念或者精神信仰的变形和异化,也即疯狂本身表达的人本身在其他权力派别的作用下边的面目全非。福柯认为:“事物身上超载着各种属性、能指和暗示,并使得事物变得面目模糊。意义已不再能由直接的知觉中得晓,形象也不是一目了然;知识为形象贯注情意,笼罩神气,形象则在形式之中滑动位移。”[4](P28)不同意义寄寓于形象之下,逼使形象脱离形式的秩序。
宗教意义增衍最主要的表达手法就是象征,强迫形象过度负荷附加意义,因此象征的形象很容易就变成了疯狂的侧影。象征的智慧被疯狂梦想所俘,就是因为意义增衍过程中缺少意念上的严谨。疯狂寓言与象征的智慧虽然各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呈交织互借的混乱状态,难分彼此。这样,宗教的象征智慧就有了疯狂寓言的特征。格里尔怪面在中世纪的训诫意味者:欲望者的灵魂是如何一步步变成兽性的俘虏;肚子上的怪诞面孔深含柏拉图式隐喻,说明精神堕落于原罪的疯狂之中。15世纪格里尔怪面被《(圣安东尼的)诱惑》的画面所代表,成为“圣徒之诱惑”的疯狂:“其中所有的不可能、空想、非人性,其中所有的反自然,无理智之物在地面上的蠢动,这一切,带给他一股奇特的力量。”[4](P30)
疯狂的蛊惑力量是来源于宗教与疯狂之间古怪与兽性、知识与欲望、末日与狂怒的相似性。在这一对立中呈现出疯狂对人自身的兽性、欲望和狂怒的认知。
古怪在最后的审判日,犯罪之人以其丑陋的赤身裸体现身之时,外形其实就是一只狂乱的古怪动物;而人的象征和价值不能驯化的兽性“是人对它的狂乱、愤怒、层出不穷、鬼鬼怪怪的荒谬性,感到无比地着迷。现在是它在揭露人心之中的阴森巨怒和荒凉疯狂。”[4](P31)知识象征了种植于尘世乐园中心的禁忌树、长生不死和原罪之树,现在已经被连根拔起,当作疯人船的桅杆;疯狂是知识,才能蛊惑人心,所有这些荒谬的形象事实上是属于一个困难、封闭、玄秘不宣的知识,它是比好奇心更为深藏的刺激或者欲望。宗教的世界末日预言是最终的幸福和最高的惩罚,世界万能会降临,地狱堕落将实现。但是在疯人船上,疯人生活于一片乐土之上,他们不再是万物欲念的玩物。“它就像是一个更新的乐园,人在那儿,即不再有痛苦,亦不再有需求。然而,人却未寻回他的天真。这虚假的幸福,意味着‘反基督’魔鬼般的胜利,也就是末日的即将降临。”即疯狂预言着末日,宗教末日表现疯狂。“看一看丢勒的《启示录四骑士》就会明白:这些骑士都是上帝派来的,他们不是胜利与和解的天使,也不是和平正义的使者,而是进行报复的、披头散发的武士。世界陷入普遍的怒火中。胜利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10]丢勒表现得极为直白:《启示录》是清洗人类世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清洗过程的最终结果在《圣经·启示录》22章有具体叙述。
六、恶德
中世纪疯狂被定为一种恶德,与谨慎成对,即宗教疏于对人性的训诫。这是宗教留下的劣根性,其根基是骄傲。文艺复兴时期,疯狂源于人对自己的幻觉,也就是因为人对自己的执念,成了由人类所有弱点组成的愉悦诗班领队。把错误当作真理,把谎言当作现实,把暴力和丑陋误认正义和美丽。从此出发,疯狂就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疯狂是和人、人的弱点、梦想和幻想相关的综合表现。“疯狂不再躲在世界角落里窥看着人;它钻入人心之中,或者说它毋宁是人跟自己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4](P37)这种微妙的关系也只有在疯狂状态之下才能很好地得到呈现和关照。人对自己想象上的自满或者失望,即失去常态时才会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疯狂。这种分裂就是将自身和自我之间拉开了距离,形成了欣赏的可能,即在疯狂状态形成人对自身的认识。
“疯狂的象征,将是这面特别的镜子:他不反射任何事实的事物,而只是秘密地映照出人对自己的武断梦想。疯狂与真理和世界不大相关,与它有关系的是人,是人对他自己所能察觉到的真相。”[4](P38)疯狂是对人自身认识的一面镜子,关照出人以为重要行为的可笑和愚蠢。所以在察觉真相时就具有绝对领导权,政治家野心的创造,经济家增厚财富的悭吝,哲学家和学者大胆好奇心的驱动。追寻知识的真相,他们最终追求到的是知识本身可笑虚渺。这种荒谬是因为人迷失在积满尘埃的故纸堆和渺无目的的论谈之中,而不去探询经验这本大书。疯狂是对假学问过度发展和愚昧推理的处罚,是对人迷失自身的可笑见证。
伊拉斯谟在《疯狂颂》中说:人之疯狂乃是娱神的戏剧。在宗教或者上帝的眼中,疯狂本身就是一出使奥林匹斯山众神高兴的喜剧;悲剧只是人们对疯狂感到世界熟悉的陌生感。疯狂是人生的一个面貌,是盛演不衰、耳熟能详、早已摸透的戏剧。演出的目的就在于娱神,因为神缺少的就是这种疯狂,疯狂是人所独有的生存美学存在,是人对自身的认知和关怀。
七、神秘体验
在疯狂的统一体中,表述和批判与形象和再现之间分离,使疯狂产生了一道永远不会合拢的裂痕,这就有了狂暴的疯人船与智者的疯人船之分。智者的疯人船是一种知识和理性的建构,而狂暴的疯人船则是一种真实存在,是一种人所呈现出的宇宙性、悲剧性、神秘性的体验。“我们将有一艘疯人船,载着船上狂暴的面孔,缓缓驶入黑夜之中,而围绕它的风景,谈论的是知识的诡异炼金术、兽性的阴暗威胁以及世界末日。”[4](P41)所以,是宇宙力量的幽暗隐晦展示,疯狂是感知的媒介。
绘画可以透过它独特的造型价值,不断地深入到远离表述限制的宇宙性体验领域。福柯说:虚构不在于让人看到不可见物,而在于要让人看到可见物的不可见性,并且这种不可见性是多么不可见。绘画是形象沉默的世界,疯狂就在纯粹视像空间发挥它的威力。“幻想和威胁、梦境中的纯粹表象和世界秘密的命运——在此,疯狂握有一股原始的表达力。它揭露出梦境似幻实真,揭露出幻象薄薄的表层,其实开向一个无可置疑的深度,揭露出形象片刻的闪烁,会让世界成为黑夜里的永远不安形象的猎物;它也作出反向的揭露,却也同样令人痛苦。它说:有一天整个世界的现实会被吸入神奇的形象之中,那是在存在和虚无之间摆荡的片刻,而虚无便是纯粹毁败的热狂。世界早已不再存在,但沉默和黑夜尚未完全将它吸纳。他还在最后的灿烂之中摇摆着,在极端的物质须知中徘徊不定。但不久之后,世界完结所带来单调的秩序便会降临。”[4](P42)绘画把表象和秘密、疯狂的形象和有所保留的谜题完整地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英〕罗伊·博伊恩.福柯与德里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法〕福柯.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美〕布莱恩·雷诺.福柯十讲[M].石家庄: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6]〔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译者导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9]〔加〕诺思洛普·弗莱.世俗的经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思动
[收稿日期]2015-01-14
[作者简介]张建军(1979-),男,陕西礼泉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及西方文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5)09—0039—07
[中图分类号]B565.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5.09.008
The Nature of Foucault’s Madness and Religious Mystery
ZHANG Jian-jun
(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China)
Abstract:Madness is not just a physical disease but also an outcome of civilization of history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Foucault pointed out that madness is apossible expression of man’s existence,which is a pure experience expression with no conceptual intervening from history,society,and rationality. There is a relation of common experience and description with the prototype of boat of mad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n mystery,death and nihility,crazy allegory,evil and mystery. This idea of madness in the domain of religion is not widely accepted by society and finally classified as religious mysticism which,in other words,is negated by rationa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Foucault;madness;a possible expressionion;religious myst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