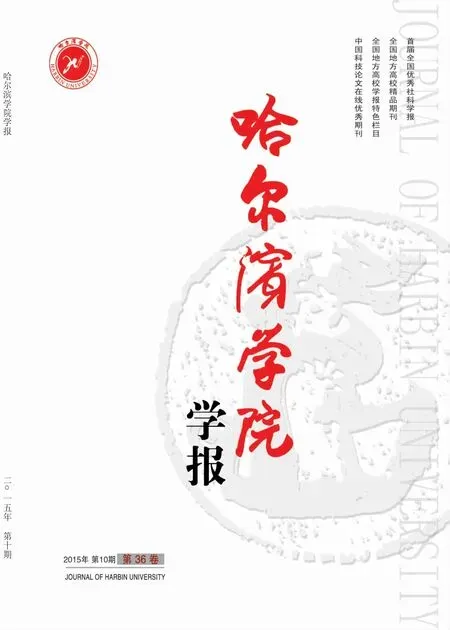“可然”与“必然”——从《诗学》视角读《源泉》
“可然”与“必然”——从《诗学》视角读《源泉》
杨伶俐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225009)
[摘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探讨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如艺术摹仿、情节组合、诗和历史异同等;安·兰德思想中关于理想和客观的部分来自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理念。基于这点,文章试从“可然”与“必然”之原则、情节的可然与必然、冲突的可然与必然、普遍与特殊的可然与必然以及人物性格的可然与必然等几方面分析《诗学》如何影响《源泉》的创作。
[关键词]《诗学》;《源泉》;“可然”与“必然”
[中图分类号]I106.4
[收稿日期]2014-11-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4YJC752035。
[作者简介]丰俊超(1982-),女,哈尔滨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文艺评论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5)10—0091—05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视为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作品,“可然”与“必然”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体现在其《政治学》中的观点之一为“主治的人们永不更替”。[1]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其“客观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都有广泛影响。她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其主要贡献是提出自我主义人生观,提倡一种理性的利己主义,即创造是自我的事情,不需要得到也无须期待他人的认同,她提倡的自私自利概念往往被人误解而引起争议。《源泉》出版于1943年,其主题为“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并非在政治意义上,而是在人的灵魂深处”。[2](P80)在1945年写给《源泉》读者的信中,安·兰德如是说:
“我九岁时立志成为作家,那是经过思考后的决定,我依旧记得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并非从尝试写邻人开始,我想写的是邻人永远不会做的事。我对‘人之为人’兴致不高,但我脑海中印有一副‘人能为人’的醒目画面。这一志向从未改变,但我花数年时间思考一个问题,即小说创作完全属于个人意愿,不必在意他人看法,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受惠于亚里士多德,他说过小说比历史更富哲学意义,因为历史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小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源泉》便是一例。”[3](P669-670)
那么,安·兰德创作《源泉》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启发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然后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发生的事情……”[4](P81)从“可然”到“必然”,安·兰德误引了亚里士多德吗?字面上看或许如此,但她充分理解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可然”的含义。本文试从“可然”与“必然”之原则、情节的可然与必然、冲突的可然与必然、普遍与特殊的可然与必然以及人物性格的可然与必然等几方面分析《诗学》如何启发了《源泉》的创作。
一、“可然”与“必然”之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描述“可能”的事件不仅仅意味着作品中虚构的事件,同时也包含历史事件,“可能发生之事是可信的;我们不相信从未发生过的事是可能的,但已经发生之事则显然是可能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发生”。[4](P81)这里就引出了“可然”与“必然”的讨论。亚里士多德“可然”与“必然”的原则也体现在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刻画性格,就像组合事件一样,必须始终求其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这样,才能使某一类人按必然或可然的原则说某一类话或做某一类事,才能使事件的承继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4](P112)同时,事件“应出自情节本身的结构,方能表明它们是前事的必然或可然的结果”。[4](P88)
性格与情节是文学作品事件中不可缺少、密不可分的两部分。首先,亚里士多德的性格概念以道德为核心,关于性格刻画,应做到“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性格应该好,言论或行动若能显示人的抉择,即能表现性格。所以,如果抉择是好的,也就表明性格亦是好的”。[4](P112)其次,离开某种情景并不能说明人物的道德品格会导致其具体行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并未详细解释这一点。举个例子,安·兰德的道德哲学里,效率是种美德,如种植马铃薯是件有成效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美德的人都会种马铃薯,这里的效率是对无数具体事物进行抽象后的概念,有美德的人会选择某种带来成效的行为,但具体行为取决于情境,如其价值观、知识构成以及所处环境等。
安·兰德将道德理想的描写作为其最终文学目标,她的创作目的是表现一个理想人物,因此,她界定了造就理想人物存在所需要的条件,“既然人的性格就是环境的产物,我必须界定和表现造就理想人物并驱动他行为的环境和价值观”。[5](P6)
为了证明一个人的某个特定行为遵循着其道德性格,首先必须了解其道德源起的情境,而这一情境则贯穿着小说的整个事件。这样,小说作者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便可自然地将道德元素渗透其中。如果人物道德性格是正面的,事件的结果便体现了“可然”与“必然”的原则。《源泉》中的中心事件便是主人公霍华德·洛克炸毁科特兰德大厦,洛克最显著的性格便是独立与正直,他不遵循陈规,认为世上没有权威,能依赖的唯有自身的独立判断,并为其创造性工作的完整性同各种社会反对力量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唯一重要的是,我的目的,我的奖赏,我的开端,我的结局都是工作本身。我的工作按照我的方式来做。”[5](P747)
但一个独立正直的人未必会炸毁政府的居家工程,而洛克的行为是在小说的一系列事件中遵循了人物性格。首先,洛克设计了科特兰德大厦,政府答应原原本本按其设计方案施工,但两名二手货①建筑师高登·L·普利斯特和古斯·韦伯将设计方案改得面目全非。如果洛克不采取措施,改动方案后建成的大厦便永远矗立在那儿,但洛克的成果遭到亵渎,对于一个独立正直的人来说情何以堪,他不能控诉政府,唯一能做出的反击便是摧毁那个庞然大物。如果事先情况完全相反,如果没有违反合同,洛克或许采取不同方法,先前他不是没有摧毁斯考德神庙吗?如果洛克不具有那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如果他是彼得·吉丁,他的行为也会完全不一样。
没有离开情境的人物性格,也没有脱离人物性格的情境。洛克的行为是一种符合逻辑而非确定性的必然之可然,亚里士多德“必然”一词无宿命论色彩,安·兰德刻画的霍华德·洛克也不是相信宿命论的人物,他显示的是一种更纯粹的存在,不是一种“必然”,而是“可然”,他并非必须炸毁科特兰德大厦,但他坚守自己的建筑信仰,现实与信仰的冲突促使其为之。
二、冲突的必然与可然
小说人物性格受先前事件情境影响,但并非所有的先前事件都能构成必然的情境。对洛克来说,设计科特兰德大厦是一项艰巨且让人筋疲力尽的工程。工程竣工后,他度了长达数月的假期,这一行为合情合理,因为在科特兰德大厦工程之前,洛克已忘我工作若干年,需要静养一番。但休假并非出于人物性格或先前事件之必然,如果小说中未提及休假事宜,读者也不会意识到其中的缺失。这一小插曲并非不具有典型意义,它代表了人类行为的普遍模式,即人类行为并非由孤立的事件,而是由人的价值观、知识构成以及环境组成的大情境推动的,而大情境又离不开小细节。安·兰德如此描述洛克的休假事宜,“接下来的几个月,事务所里也没有多少活要求洛克在场。他目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两个新的项目要等春天才开工。”[5](P778)这是大情境中相关的部分情境,逻辑上也不足以使休假成为必然,而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是洛克终于得以休闲。
这让我们想到另一原则,作者为了让人物行为遵循其性格发展必须将先前事件部分融入后发事件的相关情境,典型手法体现为对人物的基本价值观发起挑战。设想有人试图爬向一座休眠火山,离开情境,我们难以猜测他此举的原因;但如果火山爆发,熔岩向他袭来,他一定转身逃离,原因所在是因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同样,我们可以解释洛克炸毁科特兰德大厦一举。别人擅自改动他的设计方案是对洛克自我价值观的最残酷挑战,唯有将其摧毁才能符合这一人物性格。洛克对政府的安居工程虽然不屑,但他喜欢这一项目,因为他想让它真实、鲜活并发挥作用。他捍卫自己的设计,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没有人能够改变或触及,他想看见大厦严格按他设计的样子修建。
女主人公多米尼克同样面临着个人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情形。她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她相信绝大多数男人道德败坏,有真实价值的人容易受到敌意攻击。在生活中,多米尼克并不遵循严肃价值观,这使她能够自我防护并保持内心平静、傲慢不恭。但她爱上了洛克,当她认识到洛克是个建筑天才时,她认为洛克难逃一劫,同时她的价值观念受到威胁,来自洛克的威胁。她对此威胁作出反击的唯一方式是随时寻找机会阻碍洛克的事业,从而减轻外界对他的攻击。多米尼克所做的一切看似对洛克的千般阻挠,实质是出于爱情而予以洛克的保护伞。
可以看出,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充满各种冲突,最终导致某种“必然”,多米尼克与社会以及洛克间的冲突,洛克与高登·L·普利斯特和古斯·韦伯以及政府间的冲突等,在上述隐喻中,爬山者与熔岩的冲突,都体现了冲突在小说中推动事件发展的角色。但现实生活中冲突却不受欢迎,人们可以从小说中审视现实生活可避免的冲突环节,从而领悟“可然”与“必然”间的普遍又特殊的微妙关系。
三、普遍与特殊的可然与必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中写到,“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倾向于记载具体事情。所谓‘带普遍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4](P81)
诗歌或小说如何比历史更能表达普遍性?《源泉》中,洛克炸毁大厦一事使抽象事物具体化,即其独立耿直的性格驱使。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并非简单罗列历史事实,而会进行客观评价,如有历史学家评论说,乔治·华盛顿的勇气以及其对共和国的忠诚使得他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小说事件同时又不仅仅将抽象事件具体化,如前文提及种植马铃薯一例,这是美德的一种具体体现,但并不意味着有美德的人都去种马铃薯。人们追求效率的方案及其多元,而具体的选择很大程度取决于情境。反之,种植马铃薯的人并非都是有德行的,或许他只是继承了家业的因循守旧者,不得已而为之。但设想一个人被困在人迹罕至的沙漠里,唯一可食的仅有马铃薯,这种境况下,种植马铃薯便成为众多普遍选择中的特殊选择。荒岛上鲁滨逊的行为似乎和其价值观格格不入,因为他面临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为了生存而野人般求生。同样道理,面对熔岩的袭来,攀爬火山的人若想活命只能选择转身逃离,洛克想维护自己作品的完整性只能选择破坏。所有这些特殊事件都体现了具体情境下的必然与可然。
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小说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倾向于记载具体事情,因为小说的具体事件在特性情境下体现了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以道德为核心的人物刻画将“可然”置于各种抽象的具体化中,小说作品并非纯粹关于道德的说教,读者期待的是具体情境下的可然。可以存活下来的小说所论述的不是日常的平凡琐事,而是阐释永恒的、普遍的问题以及人类存在的价值,不是忠实的记载或逼真的描绘,而是进行创作或将思想情感加以形象化和具体化。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概括,它所涉及的不是事物实际的状态,而是事物可能的或应该所具有的状态。当人物说话或做事符合他们所属的性格类型时,也就合乎必然与可然之定律,具有了典型的普遍性。
四、人物性格的可然与必然
小说中被具体化的人物性格及价值观往往有其现实性与社会性,那些认为《源泉》没能体现“何为应该”的读者往往忽视这一点,即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里。主人公价值观奠定了小说的基调,洛克的独立与正直是被升华了的道德抽象,同时人物性格刻画似乎有含糊的一面。如,小说结尾,多米尼克意识到自己世界观发生改变,她开始相信善有善报,她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坚持到最后,那就是胜利,对于那些应该取胜,那种推动着世界前进,却从来得不到承认的力量来说,也是一种胜利”。[5](P900)
多米尼克百般阻挠洛克的行为基于她对周围世界的错误判断,并非应该的行为。但换个角度来看,由于多米尼克捍卫完美主义的欲望,其行为可视为“应该为之”,人物性格并非由单个孤立的而是一系列有联系的前提决定的。如果这些前提不具备连贯性,只能通过基本道义判断人物性格的善恶,以及其行为多大程度上受到推崇。再如《悲惨世界》里主教与小偷一例,男主角Jean Valjean出狱后成为社会唾弃的人,在走投无路之际,被和蔼的主教Digne收留。主教使用银器盛装食物,待之如宾客,不料,Jean Valjean半夜却偷了主教家柜子中的银器而逃。被抓后竟谎称是主教送他的礼物。没想到他被带至主教面前对质时,主教不仅承认那些是送他的礼物,还拿起桌上最后的两只银烛台赠予他,后来Jean Valjean逐渐成为一个光明正直的人,读者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Jean Valjean的变化。
当多米尼克的行为未能阻碍洛克前进的步伐时,她意识到作为他的情人会永远撕扯着对他的感情,同时让她承担着对他被摧毁的恐惧,由于忍受不了这样的内心折磨,她选择了离开,向她所鄙视的周遭作出妥协。看似可能的幸福事实上对她的灵魂构成威胁,她用自己能做到的方式进行还击,即嫁给彼得·吉丁。如果“应该”体现了多米尼克理想主义的核心,这场婚姻意味着为了保护洛克而“应该为之”,同时也流露出一种令人心碎的失败感。从吉丁的角度来看,这桩婚姻意味着某种虚无而又不道德行为,因为此时他已经同凯瑟琳·海尔西订下婚约。诚然,彼得·吉丁第一次见多米尼克就被其深深吸引,但突如其来的婚姻让其措手不及,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的爱情成分。某种程度上,吉丁是受埃斯沃斯·托黑的怂恿而做出选择:
“看着今晚的你,我忍不住想起一个原本可以在你身边组成完美图画的女人。”
“谁?”
“哦。不要在意我说的话。只是美学上的奇思异想。生活从来没有如此完美过。人们嫉妒你的东西太多了。你不能把那个人也加到你的成就里。”
“谁?”
“不要再问了,彼得。你得不到她的。没有人能得到她。你很优秀,但是你还没优秀到能够得到她。”
“当然是多米尼克·弗兰肯。”[5](P407)
托黑告诉吉丁这场婚姻会为他带去更多关注,而凯瑟琳缺乏泰然自若和超然出众的社交魅力。这正迎合了吉丁的意愿,作为一名二手货,他依赖于别人予以的赞誉生存。他对洛克说,“我很乐意免费与你分享(我的原则):永远要成为人们希望你成为的样子。这样一来,在你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帮助你。”[5](P332)某种意义上,这体现了吉丁的处世哲学,基于这一前提,面对多米尼克的求婚,他必然接受。一方面,吉丁不关心事实和工作,只关心大家怎么想,不会创作只会作秀,没有能力但有朋友,没有美德但有影响力。另一方面,多米尼克不仅仅是名符其实的白富美,她有自己的社交圈,唯有娶她才能为吉丁提供吸引别人关注的机会。
出于小说情境需要,吉丁娶多米尼克的决定体现了典型的以道德为核心的人物刻画以及叙事方式,然而其前提是违背道德的“不该”行为,也体现了“可然”“不该”“应该”的逻辑。文学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描述美好,邪恶属于枝节问题,《源泉》中的代表人物分别为创造者洛克与二手货吉丁。
洛克对多米尼克的第一次婚姻作出如下反应:
“多米尼克,如果现在我告诉你马上让那桩婚姻去见鬼——忘记这个世界和我的奋斗——不去感受愤怒、忧虑、希望——仅仅为我而存在,为我对你的需要而存在——做我的妻子——做我的财产……”[5](P476)
多米尼克回答,“我会听命于你。”
但洛克说,“如果你现在和我结婚,我会变成你的全部。那时我将不会想要你,你也不会想要你自己——所以你将不会长久地爱我了。为了说‘我爱你’,一个人必须先知道如何说‘我’,现在我本可以从你那儿得到的那种屈从只会让我变成一个徒有外表的躯壳。如果我要求这个,我会毁了你。这就是我不想阻止你的原因。我将让你回到你丈夫那儿。”[5](P477)
鬼子都打到龙游了,那兰溪是不是早已失手?老三还能不能把报丧信送到志浩手上?甚至,志浩是不是早已为国捐躯都是件难说的事。虽说兰溪离衢州不过六七十里地,赶船也就半天的脚程,但这兵荒马乱的,即便志浩回来奔丧,没个一天半截估计是到不了的。
无疑,多米尼克与吉丁的婚姻同样对洛克的价值观构成威胁,但如果劝其放弃则更加挑战了洛克的人物性格,他不愿将多米尼克变成缺乏思考能力的附属品,因此,他必须放弃这一行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25章中提到,“衡量一个人言行的好坏,不仅应该考虑言行本身,而且还应考虑其他因素:言者和行动者的情况,对方是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美好的善,还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4](P178)《源泉》中,安·兰德通过刻画吉丁的不道德,充分利用一系列必要的情境塑造洛克这一理想的创造者形象,尽管一再被否定、被迫害,但总会继续前进,以自己的精神带动整个人类在逆境中继续进步。
五、情节的可然与必然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作品应该具备完整性,即一个完整的事物是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起始指不必继承他者,但要接受其他存在或后来者出于自然之承继的部分,这一承继或是因为出于必须,或是因为符合多数情况。中段指自然地承上启下部分。因此,组合精良的情节不应随便地起始和结尾,其构成应该符合上述要求。[4](P74)
情节是推动故事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又由可然与必然原则推动,这一结构构成逆境统一的整体,并随着故事发展对价值观构成一系列的威胁。《源泉》中的一例便是多米尼克与洛克的偶遇,被对方吸引,接着对洛克事业的阻挠,随后选择离开嫁给吉丁直到小说高潮部分,多米尼克意识到洛克永远不会向外界屈服,不会被击溃,最终其价值观发生转变。小说到此,两人终成眷属,冲突不再。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文学作品中逆境的重要性,“作品要以能容纳可表现人物从逆境转入顺境,或从顺境转入逆境的一系列事件,并按可然或必然的原则依次组织起来为宜。”[4](P75)但同时又说,一个构思精良的情节“应该表现人物从顺境转入逆境,而不是相反,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4](P98)无论如何表述,都说明逆境更能造就一个悲剧人物,洛克经历了各种感情以及事业上的逆境冲突并与之抗争。
某种意义上,安·兰德对情节冲突的依赖又体现了其浪漫主义情怀。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主要特征在于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以及价值观的差异,体现了对传统的颠覆。浪漫派作家寻求强烈的艺术效果,描写不同寻常的情节、事件以及人物性格,基于价值观的冲突刻画便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创新。安·兰德对文学作品中的逆境与冲突做了形而上学的解释,“情节体现了目的行为的戏剧化,不得不基于冲突。可能是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可能是人物之间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目标不能轻易触及,戏剧化过程中必须设置某些障碍,包括人物的抗争”,[6](P77)而作为推动“价值—威胁”前进的逆境与冲突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用例最多的是希腊神话,他认为情节的解开也应是情节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该借助于突然出现的事物,完美的结构应是复杂型的,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不能引发恐惧和怜悯,反而会使人反感;同时不该表现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与悲剧精神背道而驰。[4](P97)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显得自我矛盾,安·兰德也解释了其中的模糊性。逆境代表着某种恶意的形而上观点,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人的成功和失败与道德无关,在以倡导道德为核心的作品中,逆境与整个故事格格不入,而在类似于《永别了,武器》这样以感情为核心的作品中则体现出和谐。
六、结语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既然诗人和画家或其他形象的制作者一样,是个摹仿者,那么,在任何时候,他都必须从如下三者中选取摹仿对象:过去或当今的事,传说或设想中的事以及应该这样或那样的事。”[3](P177)作品往往高于原型,就创作而言,一件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一件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如描写马的两条右腿同时举步不合情理,因为它是在违反可然性的情况下发生的。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要求创作必须符合可然与必然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创作必须符合有机整体。亚里士多德关于“可然”与“必然”定律的论断显明,文学没有必要自惭形秽。
安·兰德在《源泉》中遵循了“可然”与“必然”的原则,从角色冲突、普遍性与特殊性、情节结构安排等方面赋予了小说创作的形式。在1944年一封写给《源泉》粉丝的信中,安·兰德讲了一个关于米开朗基罗的故事,“他的一件雕塑(我想应该是‘大卫’)里有一块真实人体不可能拥有的肌肉,当有人告诉他这不符合自然规律时,他说大自然应该允许他这么做。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家”。[2](P669-670)
有人说《源泉》中的许多事情不可能发生,但它们的确在《源泉》里发生了。安·兰德是一名来自苏联的流亡者,在美国生活过程中对美国的社会价值观显示出高度认同。她认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其道德基础上的国家,也是唯一能让她自由写作的国家。安·兰德借主人公霍华德·洛克之口宣称,世界上没有任何靠得住的权威,只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安·兰德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里引用雨果的一句话表达了其创作态度,“如果一个作家只是为了他自己的时代而写作,那我就得折断我的笔,放弃写作了。”[5](P3)有许多小说从写出至出版仿佛杂志一样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于读者视野,《源泉》虽曾因为太过理性化而连遭十二家出版社拒绝,但出版后却一版再版,拥有广大的受众。对《源泉》中的“可然”与“必然”原则进行一番梳理,读者会找到其中所传达的理念。
安·兰德的创作目的在于表现一个理想人物,所以她界定了可能造就这一理想人物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物的性格受环境影响,所以她表现了驱动理想人物行为的环境、价值观以及道德准则;由于人是社会的人,所以她表现了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社会体系,在《源泉》中,这一社会体系便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人能为人”才是目的,这也是《源泉》魅力所在。
注释:①小说原文为“the second-hander”,指那些没有“自我”,依赖他人生存的人,同“创造者”相对。
[参考文献]
[1]张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启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2).
[2]〔美〕兰德.冯涛.至新知识分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3]Michael S. Berliner, ed.Letters of Ayn Rand[M].New York:Dutton,1995.
[4]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美〕兰德.高晓晴,赵雅蔷,杨玉.源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6]Ayn Rand,“Basic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The Romantic Manifesto:A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Revised Edition[M].Signet,1971.
责任编辑:魏乐娇
“Might Be” and “Ought to Be”
——Interpreting “Fountainhead” With “Poetics”
YANG Ling-li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In Poetics,Aristotle touched upon a series of theories of writing,such as imitation,plot,character and so on. Some of Ayn Rand’s ideas of writing,to certain degree,derive from those of Aristotle’s. This paper aims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elements,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and probability,the role of conflicts in literature,and the union of the universal and the particular,to analyze how and to what extent the writing of the Fountainhead is influenced by Poetics.
Key words:Poetics;Fountainhead;“Might Be” and “Ought to Be”